11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docx
《11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1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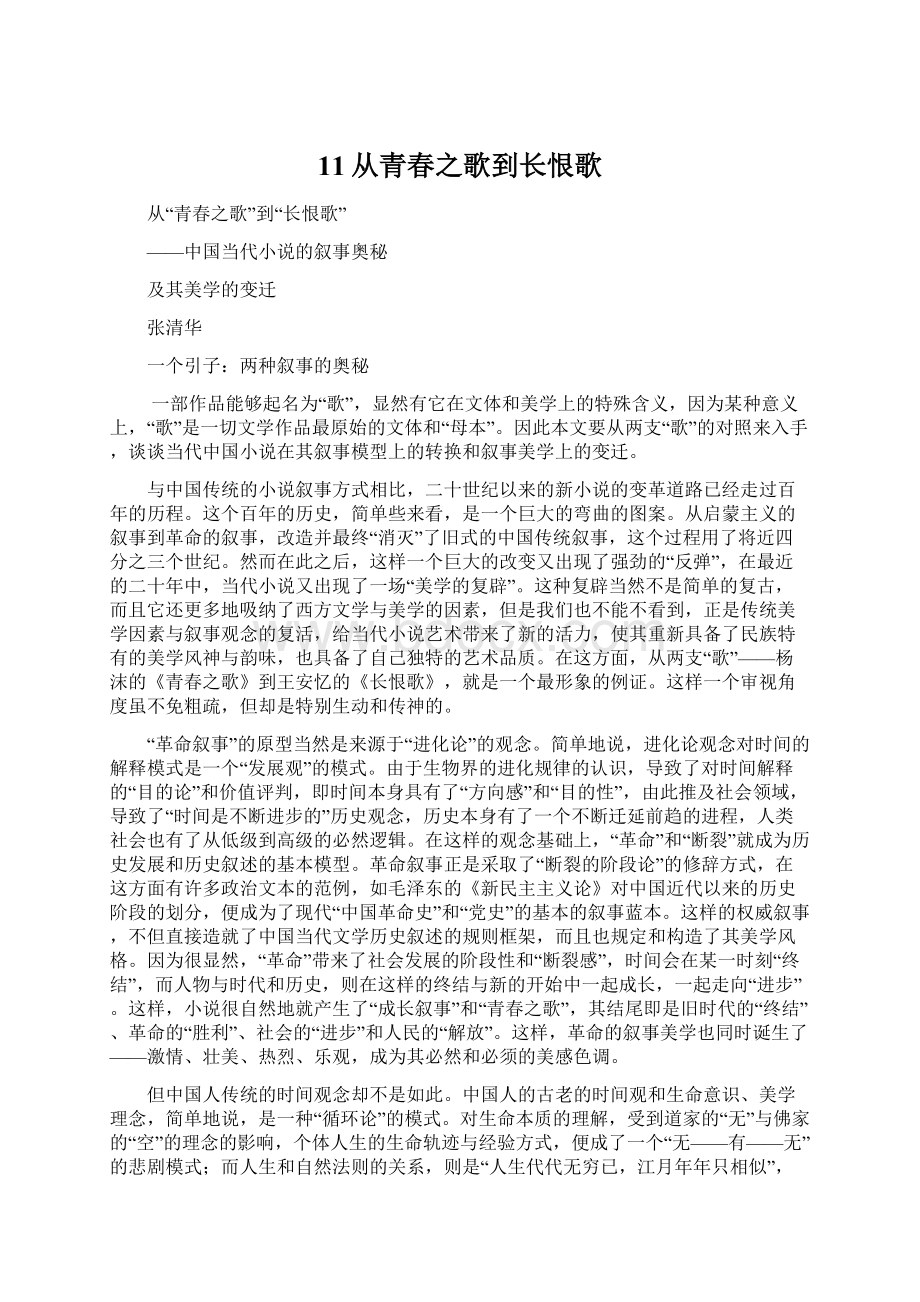
11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
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
——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
及其美学的变迁
张清华
一个引子:
两种叙事的奥秘
一部作品能够起名为“歌”,显然有它在文体和美学上的特殊含义,因为某种意义上,“歌”是一切文学作品最原始的文体和“母本”。
因此本文要从两支“歌”的对照来入手,谈谈当代中国小说在其叙事模型上的转换和叙事美学上的变迁。
与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相比,二十世纪以来的新小说的变革道路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
这个百年的历史,简单些来看,是一个巨大的弯曲的图案。
从启蒙主义的叙事到革命的叙事,改造并最终“消灭”了旧式的中国传统叙事,这个过程用了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
然而在此之后,这样一个巨大的改变又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当代小说又出现了一场“美学的复辟”。
这种复辟当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且它还更多地吸纳了西方文学与美学的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正是传统美学因素与叙事观念的复活,给当代小说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使其重新具备了民族特有的美学风神与韵味,也具备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品质。
在这方面,从两支“歌”——杨沫的《青春之歌》到王安忆的《长恨歌》,就是一个最形象的例证。
这样一个审视角度虽不免粗疏,但却是特别生动和传神的。
“革命叙事”的原型当然是来源于“进化论”的观念。
简单地说,进化论观念对时间的解释模式是一个“发展观”的模式。
由于生物界的进化规律的认识,导致了对时间解释的“目的论”和价值评判,即时间本身具有了“方向感”和“目的性”,由此推及社会领域,导致了“时间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历史本身有了一个不断迁延前趋的进程,人类社会也有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逻辑。
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革命”和“断裂”就成为历史发展和历史叙述的基本模型。
革命叙事正是采取了“断裂的阶段论”的修辞方式,在这方面有许多政治文本的范例,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便成为了现代“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基本的叙事蓝本。
这样的权威叙事,不但直接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规则框架,而且也规定和构造了其美学风格。
因为很显然,“革命”带来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断裂感”,时间会在某一时刻“终结”,而人物与时代和历史,则在这样的终结与新的开始中一起成长,一起走向“进步”。
这样,小说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成长叙事”和“青春之歌”,其结尾即是旧时代的“终结”、革命的“胜利”、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
这样,革命的叙事美学也同时诞生了——激情、壮美、热烈、乐观,成为其必然和必须的美感色调。
但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却不是如此。
中国人的古老的时间观和生命意识、美学理念,简单地说,是一种“循环论”的模式。
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受到道家的“无”与佛家的“空”的理念的影响,个体人生的生命轨迹与经验方式,便成了一个“无——有——无”的悲剧模式;而人生和自然法则的关系,则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自然的无穷更反过来凸显了人生的短暂;再进而影响到对历史的理解,也是一种重复和循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里并没有必然的进步,相反到是有一种悲剧的经验: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样的生命理念和历史理念,合并导致了一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本体论的哲学和美学。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中,大抵不出这样一个基本格局:
人物——从生到死;事件——从开始到结束;时间——一个完整的叙事单位(从“聚”至“散”,从“盛”至“衰”,从“有”到“无”)。
这样,历史和个体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便实现了一种重合,由于“死亡”和“散”、“无”、“空”这样的必然结局的出现,道德和其它的社会意义都受到了“存在”这样的哲学意义上的拷问,“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及其美学的基本的悲剧经验方式。
历史和人生,究其实质是一种相似而同构的永恒的缺憾、悲剧的“长恨”。
最典型的要数《红楼梦》,它的悲剧叙事展现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一个到头来被证明是一场空无一物的“梦幻”。
一个完整的叙事,在中国人这里是尤为重要的,死亡的呈现使叙事出现一个自我完结的终点,所谓只有“大团圆”结局的说法是片面的。
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例,开始描写的是李杨之间缠绵缱绻的爱情,这差不多也是一曲“青春之歌”了,但接下来就是杨玉环的惨死,剩下皇帝一个人苦度余生,生不如死。
这样,“青春之歌”顷刻之间便变成了“长恨歌”,一个时间终结了,另一个时间则在独自向前中证明着这终结,一个香消玉殒,一个心如死灰,天上人间,碧落黄泉。
虽然结尾处白居易用幻想的极至来描写了长生殿上相会的情景,但这毋宁说是痛绝伤怀的反笔,这不过是一声长长的叹息,死亡的遥远回声。
这样,革命叙事的奥秘也就昭然若揭了:
它是删去了“青春”之后的段落的“断裂”了的阶段性叙事,悲剧、死亡、衰落、离散统统被删掉了,胜利的高潮成了结尾,广场上的狂欢被定格。
可是丹尼尔·贝尔却说,“所有的问题都发生的革命的第二天”,第一天是胜利的狂欢,第二天则是要回复平静的秩序与有效的权力运作。
所以,显而易见,特权和差别会依然如故;而克尔凯戈尔也说过,群众总要“从广场上回家,变成单独的个人”。
那时,“青春之歌”将如何续写?
而时间则不会因为胜利而停止,而是依然固执地向前,一切都将腿色和老去,死亡也将不可抗拒地降临,而这时壮美会演变成悲凉,豪情会衰变为荒诞。
而当代小说叙事在八十年代之后的还原,也正是这样一个开端,它沿着时间的脚步继续向前,直到面对那无可回避的终点。
“青春之歌”就这样重新返回到了“长恨歌”。
其实《长恨歌》中的蒋丽莉,也就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的一个延伸,她好比是把林道静暂时终结了的故事又讲了下去,时间的延伸使喜剧变成了悲剧。
从这里看,传统小说叙事的复辟就变得很自然和很简单了,它并非是一个阴谋,而是一个必然,一个“自动”的过程。
……
我把杨沫的《青春之歌》和王安忆的《长恨歌》放在一起,还不只是证明当代小说叙事从“叛逆”到“回归”传统的一个轮回或复位,我还发现,当选择这样一个角度的时候,一个戏剧性的局面出现了——它们实在是两部太有可比性的作品,简直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构成了“对称”:
两个时代的两个代表性的女作家(一北一南),两种相映成趣的价值观,两部典型的女性主人公的叙事,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与命运,两只部分重合又完全不同的“歌”……在小说的修辞方式上,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太多戏剧性的可比成分。
所以,我还不能仅仅从对比的角度作笼统的分析,而是要依次展开,把两部作品中的各种叙事要素都解析出来。
当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这是一个充满了发现的愉快的过程。
从《青春之歌》看“革命叙事”的内部构造
“革命叙事”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叙事,这样说有两层意思,一是革命叙事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自觉和不自觉地承接了来自传统叙事、西方文学叙事、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叙事的诸多因素,是一个各种叙事因素还没有来得及融和的“夹生”着的混合体;二是革命叙事在小说中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合法“伪装”,它真正兜售的还是文学本身的东西,因此它对各种“旧式”的叙事因素,有时是一种出于本能和潜意识的借用。
这种情形不止在《青春之歌》中,在《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甚至在《红岩》中,也有着生动而丰富的表现。
但从整体上来说,它内部的矛盾更多些,比如:
它是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一种比较暴力的改造,这种叙事的时间观念的原型是来自西方的(可参见巴赫金对希腊小说的分析),但却声称是“民族主义”的;在美学上是讲“中国做派”的,但骨子里却是反对中国的美学与话语传统的(就像林道静在最初是喜欢吟诵唐诗的,“革命”以后则喜欢上了现代体诗);看上去是比较“青春”和“现代”的,但骨子里的趣味却是非常陈旧的……总之研究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A.从一个“精神分析”的例证开始
在1962年北京新1版《青春之歌》的第175页中,林道静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梦”,这个梦使我认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它的无法抹杀的“文学意义”与潜意识的精神深度,它蕴藏的非常丰富的潜文本的内容甚至是作者也无法“掩盖”的。
虽然杨沫竭力对之进行修饰,但事实却似乎是欲盖弥彰,这个梦使我们的主人公作出了一个近乎绝妙的“自曝”:
革命的油彩在这里被岁月剥蚀殆尽,而人性的丑恶和复杂却暴露无遗。
她不仅是一个革命的青年,而且也是一个自私而薄情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她为了抛弃旧夫另觅新欢而绞尽了脑汁。
当然,作为一个新青年,按说这也算不得什么惊世骇俗之举,但问题就在于,她一方面是一个薄情之人,同时又有通常的道德感,这样的内心矛盾决定了小说中特别抓人的精神冲突,也使这个革命文本非同寻常地具有了心灵的深度。
道德的问题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
当林道静忘恩负义欲图抛弃对他有过救助之恩的余永泽而选择卢嘉川时,她首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良心的自我谴责,也就是说,她首先要做的,是要突破自己的心理防线。
她用心设计了种种摩擦,包括在对待讨饭的魏三大伯的态度上不同“阶级立场”的根本分歧(余永泽给了他一块钱,而林道静却给了他十块钱——不过那还是余永泽的钱),来夸张他们之间的裂隙和对立。
可是余永泽毕竟曾是她的救命恩人,她无论如何都是难以逃避这种谴责的,所以她必须要通过“修改记忆”来解脱自我,于是就有了这个象征着“愿望达成”的梦。
请注意,做梦之前,林道静有一个心理背景和自我暗示的准备:
“刚一睡下,她就被许多混沌的恶梦惊醒来。
在黑暗中她回过身来望望睡在身边的男子,这难道是那个她曾经敬仰、曾经热爱过的青年吗?
他救她,帮助她,爱她,哪一样不是为他自己呢?
……蓦然,白莉苹的话跳上心来。
——卢……革命,勇敢……‘他,这才是真正的人。
’想到这儿她笑了。
”这个动机是再明确不过的,他正经历着见异思迁的自我谴责和自我宽恕的思想斗争,因而在潜意识中她就要试图了结这一矛盾,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所以——
这夜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阴黑的天穹下,她摇着一叶小船,飘荡在白茫茫的波浪滔天的海上。
风雨、波浪、天上浓黑的云,全向这小船压下来,紧紧地压下来。
她怕,怕极了。
……她惊叫着,战栗着。
小船颠簸着就要倾覆到海里去了。
她挣扎着摇着橹,猛一回头,一个男人——她非常熟悉的、可是又认不清楚的男人穿着长衫坐在船头上向她安闲地微笑着。
她恼怒、着急,“见死不救的坏蛋!
”她向他怒骂,但是那人依然安闲地坐着。
她暴怒了,放下橹向那个人冲过去。
但是当她扼住他的脖子的时候,她才看出,这是一个多么英俊而健壮的男子呵,他向她微笑,黑眼睛多情地充满了魅惑的力量。
她放松了手。
这时天仿佛也晴了,海水也变成蔚蓝色了,他们默默地对坐着,互相凝视着。
这不是卢嘉川吗?
她吃了一惊,手中的鲁忽然掉到水中,卢嘉川立刻扑通跳到海里去捞橹。
可是黑水吞没了他,天又霎时变成浓黑了。
她哭着、喊叫着,纵身扑向海水……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卑鄙的梦,一个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真实想法的“败笔”。
它完完全全地袒露了林道静的潜意识,即:
她宁可希望余永泽是一个“见死不救的坏蛋”,她在难以摆脱这个人的同时,早已喜欢上了更加“英俊和健壮”的卢嘉川,但这种背叛的动机使她充满了犯罪感,所谓惊涛骇浪即是这种心态的隐喻。
这个梦的实际作用是,她可以使得自己对余永泽充满感恩色彩的“记忆”被彻底修改——就像当代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的一篇访谈中所谈到那样,她在一次昏迷中和她的本来“彼此欣赏的好朋友”“克罗德·雷吉闹翻了”,因为她在梦中听到,他在说她的“坏话”,她醒来再三打电话逼问他的时候,她的朋友当然感到莫名其妙,可她却坚持认为“他们之间是完了”,“这种幻觉根深蒂固,我整整六个月都沉浸在被侵犯的感觉里”。
①林道静要在感情上真正产生对余永泽的“恨”,这个可以帮助她“修改记忆”的梦,无疑是非常有效的。
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不失时机的利用,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不光彩的行为,作者一方面批评白莉苹这样的人物,另一方面又借她的嘴说话,这样又可以把“诱惑”的“撒旦式的罪责”加在她身上,因为当林道静做着这个梦的时候,她的犯罪感需要找到一种掩饰。
这样,她既得了移情别恋的好处,又把犯罪的原因转嫁到他人身上,可谓是一箭双雕。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白日梦”也不可忽视,林道静在去定县农村后有一段非常酸涩的“墓地抒情”。
背景是江华来到她在乡村的住处,林道静此时已经在盘算着怎么才能“忘记过去”,与另一个革命青年江华“开辟未来”了。
不要说所爱的人还尸骨未寒,此时她连卢嘉川已经牺牲的消息也根本不知晓,如何才能越过这一道新的心理与道德屏障?
如若说在余永泽那里她还可以容易地找到背叛的理由,那面对卢嘉川呢?
她这时内心斗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虽说与江华之间不像她与卢嘉川的爱情那样如火如荼,刻骨铭心,但她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已经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虚渺爱情再苦等下去了,她决定要再次弃旧图新、舍理想中的卢嘉川而取现实的江华了。
然而在潜意识中,这种再次背叛的罪恶感又在折磨着她,怎么办?
她不由自主地来到了田野的一座坟墓面前——我相信这决不是巧合,我们的前辈女作家还是比较淳朴的,她没有意识到恰恰是这个细节,把林道静的、当然也是她自己的潜意识暴露无遗——她实际上是把这座无名的坟墓在潜意识中当成了卢嘉川的墓地,她试图在心理上提前确认:
卢嘉川已经死了,我现在把一束鲜花放在坟前,也算是举行一个简短的“告别”或“了结”的仪式了,这仪式一过,她便又获得了自由。
……走在一座孤坟前,她低声唱起了《五月的鲜花》。
因为这时她想起了卢嘉川——自从江华来到后,不知怎的,她总是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来相比。
为这个,她那久久埋藏在心底的忧念又被掀动了。
为了驱走心上的忧伤,她伸手在道边摘起野花来。
在春天的原野上,清晨刮着带有寒意的小风,空气清新、凉爽,仿佛还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在飘荡。
她一边采着一丛丛的二月兰,一边想着江华的到来给她的生活带来许多新的可贵的东西,渐渐她的心情又快活多了。
这实在是一个精神分析的绝佳例证。
“愿望的达成”在林道静这里甚至已经变成了典型的白日梦,读者自会体味其中的妙处,我已无须再饶舌了。
林道静的许多“小资”伎俩、这些假惺惺的“忧伤”、欲盖弥彰的小心理活动,可以瞒得过五、六十年代质朴的人们,但却实在经不起现今人们轻轻的这么一碰——自然,这并无“道德审判”的意思,不是要刻意在道德上贬低林道静、贬低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相反这样的分析,实际上是要表明这部作品所达到的那个年代文学所能够具有的最大的心理与精神深度。
毫无疑问,没有哪一部十七年的小说能像《青春之歌》这样,有着几乎挖掘不尽的潜在意蕴,以及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广泛辐射力。
B.小布尔乔亚叙事怎样变成了革命叙事
有了上面的分析,“推翻”《青春之歌》原有的叙事装饰,也就变得简便而顺理成章。
仅仅两个梦,就足以暴露了林道静在“革命”名义和理由下所隐含的个人私欲,表明它的“革命叙事”的合法伪装,实际是完全经不起检验和剖析。
但这样说还不够,要完整地解读《青春之歌》,找出之所以有这样奇怪的叙事改装的深层政治与文化动因,必须还要进行更让人信服的客观和“本体”的分析,要有耐心对其文本的显在和潜在的几个叙事层面和叙述模型作逐层的解剖。
这将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
就叙事的内部结构而言,《青春之歌》显然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的层次:
1.最基本的层面是非常传统的“才子佳人加英雄美人”的叙事,简单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女
人和几个男人的悲欢离合”,这是它的“革命叙事”外表下很旧很俗的东西,但却是小说真正具有原始的叙述动力和阅读魅力的基本原因;
2.比较接近写作者自身经验的是一个女性自我的个人生活叙事,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小布尔
乔亚的叙事”,这是对作者来说最真实的一个层面,它所叙述的故事非常接近杨沫个人生活的经验;
3.一个从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女性叙事”中脱胎的革命女性故事,因为它的核心人物如丁玲
笔下的沙菲一样,是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女性,一个追求所谓个性解放的女性。
但作者把这样一个过程又作了延伸式的处理,她从追求个性解放,走上了追求革命的道路。
但即使这样,小说的“女性主义”思想痕迹仍然是明显的,因为传统的男权主义叙事往往是写“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其男权和政治是一体的,而它正好反过来,女人变成了社会与性交往的核心和主导故事结构的中心;
4.一个常态的人性叙事。
其实《青春之歌》的故事也完全可以像张爱玲的城市女性小说那样不带
有什么政治的色调,林道静的情感生活本身就极具有戏剧性的结构力量与叙述动力,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甚至是消费型的现代小说来处理,或者一个比较“知识分子”的、但又不那么“革命”的小说,一个与钱锺书的《围城》相接近的主题,隐含着关于知识者爱情的某种困境的思考,即,林道静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爱情模式,是余永泽的“无风险”式的常规生活模式呢,还是卢嘉川的理想主义的“冒险模式”?
林道静从一个男人跳向另一个男人的过程,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通常的因“围城内外”而见异思迁的人性弱点的表现;
5.一个启蒙主义叙事的变体,它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为人生的文学理想的一个延伸,即为了所
谓“解救劳苦大众”而献身的道德理想,这一点已经被显著地弱化和扭曲,但依然可以看到其踪迹;
6.作者最终试图要达到的,是所谓的“革命叙事”,“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
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②,表现主人公经过了人生的痛苦探求与选择,终于认识到只有接受党的领导,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找到出路。
这是杨沫最想展示给读者的一个层面,也是在小说问世的年代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叙事规则,是过去读者解读这部小说的唯一角度。
以上是在《青春之歌》这部小说中实际所蕴含着的几种叙事结构,这几种叙述的层面在今天看来都是不难读出的。
但如果不考虑太多的政治、美学或文化传统的因素,就这部小说而言,与其“革命文本”最接近的叙事原型是哪一个呢?
显然是其“小布尔乔亚的叙事”。
究其实,林道静实际不过是一个略显狂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正像杨沫所说的,“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③,如果这里的“阶级定性”不具有什么政治动机和偏见的话,我愿意借用这种说法——用现今时髦的省略用语,可以简称为“小资”。
如果我们剥去她身上的革命油彩,就会发现她不过是一个天生的“不安分”的女性而已。
作者杨沫刻意在她的“出身”上作文章,即暴露了其“小资”的心态,她不是一般地出身“劳动人民”,而只是有一个出身佃户人家的做女佣的母亲,这样她就有了一半的“黑骨头”;但另一方面她又有着大士绅和官僚的一个父亲,有着另一半虽属“非法”但在潜意识中却让她感到自豪的“白骨头”,④前一个血统使她获得了在政治方面的优越感,后一个血统却满足了她作为一个“小资”的虚荣心。
这样她就同时具有了政治和经济两种优越和高贵。
从林道静的生活经历看,是一个十足的“小资”故事,“革命”只是一层附着其上的薄薄的油彩。
虽然一开始杨沫竭力突出她的悲惨遭遇,但她的生活理想和趣味却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
——她不喜继母给他安排的嫁给权贵胡局长的出路,而是有一个事先形成的按照表兄张文清自由恋爱的生活而制定好的模式,所以她就“出走”北戴河去找表兄去了;
——当在北戴河意外地寻表兄不遇,险遭小人暗算时,她又失望之极,欲投海自杀,就在这时遇到了当地士绅的儿子、正在北大读书的“新青年”余永泽。
余眷恋她的美丽和身上所带的浪漫气质,倾力相救并爱上了她,而林道静在这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也就不那么挑剔,况且余永泽还用他的“知识优势”、用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浪漫打动了她,此时他们之间互相的印象是:
在林道静的眼里,余是“啊!
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在余永泽的眼里,林是“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如果小说到这里就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结束,显然便是一个很没有什么新鲜感的旧“才子佳人”的老套路;
——可是林道静注定不是一个安分的女性,这就使得小说又获得了继续向前的动力,就在余永泽刚刚离开北戴河之后,林道静就又爱上了另一个更优秀的青年卢嘉川。
与余相比,卢才是真正的“骑士”,除了同样是北大学生,而且人才出众,也更加具有冒险精神,他正在为唤起民众宣传抗日而到处演讲,林道静与他第一次相见实际就已坠入了情网,在那一刹,她就已经大大地懊悔了,按照她的性格,她真正爱的必然是卢而不是余,可是事情总要有个“先来后到”,余不但是先到,而且还对她有救命之恩,怎么好背叛他呢?
所以也只好先把这爱情埋在心底,然后再寻找机会。
然而,林道静毕竟是林道静,她决心要使自己的命运再次发生重大改变,付出再多代价也在所不惜——实际上,小说正是在这里才产生了真正的戏剧性魅力,获得了新的叙事动力。
林道静借口杨庄的险恶,也来到北京,她先是和余永泽大胆地“同居”了(相信这是她应该付出的代价),但很快她就与同在北大读书的卢嘉川挂上了勾,并屡屡以“找茬”的方式寻找余永泽的过错,这样就有了上面我们所分析的那个“梦”。
其实,细想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实际已接近一种“婚外恋”,每次谈“革命道理”的情景实在是一种显然的寻找“出轨”时机的借口(那些他们见面时的场景和对话根本就经不起分析)。
这样余永泽当然就要反对,反对则必然会在他和她之间产生更大的裂痕,最后不可避免地就是分道扬镳了;然而,为了继续推进小说的情节发展,杨沫又设置了曲折,即卢嘉川的被捕,并且把他被捕的责任加在余永泽的头上,这样既可以使他代本来应受谴责的林道静“受过”,又可以使小说的情节得以继续向前。
——但这个“缓冲”式的波折,并没有掩盖住林道静“小资”式的不专一的感情方式,她在实际上还未获知卢嘉川牺牲的消息时,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投入到了江华的怀抱。
虽说整个小说中最富戏剧性和最动人的爱情描写要数林卢之间,可作者还是和林道静一起背叛了这段爱情,而且还文过饰非地寻找各种合法理由。
看看林道静与江华在“革命”名义下匆促的媾和,实在是像前文分析的那段“墓地抒情”的白日梦一样“欲盖弥彰”,在为他们的私欲“遮掩”的同时又完成了对他们的“暴露”。
在经过了一番煞有介事的“革命工作”(江华和林道静之间的“接头”联系有着明显做作的痕迹)的忙碌之后,江华终于打开天窗摊出了底牌,他说,“道静,今天找你来,不是谈工作的。
我想来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
……”林道静便用了“温柔的安静的声音回答他”:
“可以,老江。
我很喜欢你……”然后是江华的“得寸进尺”: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林道静则“激动地”“慢慢地低声说”:
“真的?
你不走啦?
……那、那就不用走啦!
……”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个“志同道合”的面具下“假公济私”的绝好例证。
……
可以照此推断,随着“革命”的发展,林道静的爱情也会一直不断地更新下去,借了这样的不乏浪漫与惊险色彩的机会,主人公的小布尔乔亚的感情需求与趣味会得到不断的满足。
这动机本来没什么可隐瞒的,可以直接将故事按照其固有的逻辑来写,但作者硬是要并不高明地把这个小布尔乔亚的叙事改成了革命叙事。
这个掩饰的过程简直可以说是破绽百出。
杨沫何以会如此“辛苦”地费尽心机?
答案很简单:
因为“小资叙事”不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必须经过修饰和伪装之后才能出现。
但是,更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这种必须的改装意味着什么呢?
“革命叙事”必须要代替“小布尔乔亚叙事”的潜台词显然是更为丰富的,这不是一个仅仅关涉到形式的小问题,而是一个隐含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它昭示了一条从最初革命的思想启蒙者,到跌落为革命的“同路人”乃至“革命对象”的悲剧性道路。
这样一个命运的转折所导致的,就是知识者不得不“自愿”放弃自己的知识优越感,放弃自己的叙事方式乃至语言的结果。
这结果不但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自信、自尊,而且似乎使他们的叙事能力与智性也发生了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青春之歌》的叙事中的矛盾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当然,这结果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从“自觉”到“自虐”、从“受虐”到“被虐”、最后发展为“集体潜意识”的过程。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政治话语与群众话语的合力,逼使知识分子的话语处在一个尴尬的夹缝里,欲言又止、言不及意、言过其实、闪烁其辞……这种矛盾在《青春之歌》中可以说留下了生动的印记。
可以说,在潜文本的意义上,《青春之歌》也是无意中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