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docx
《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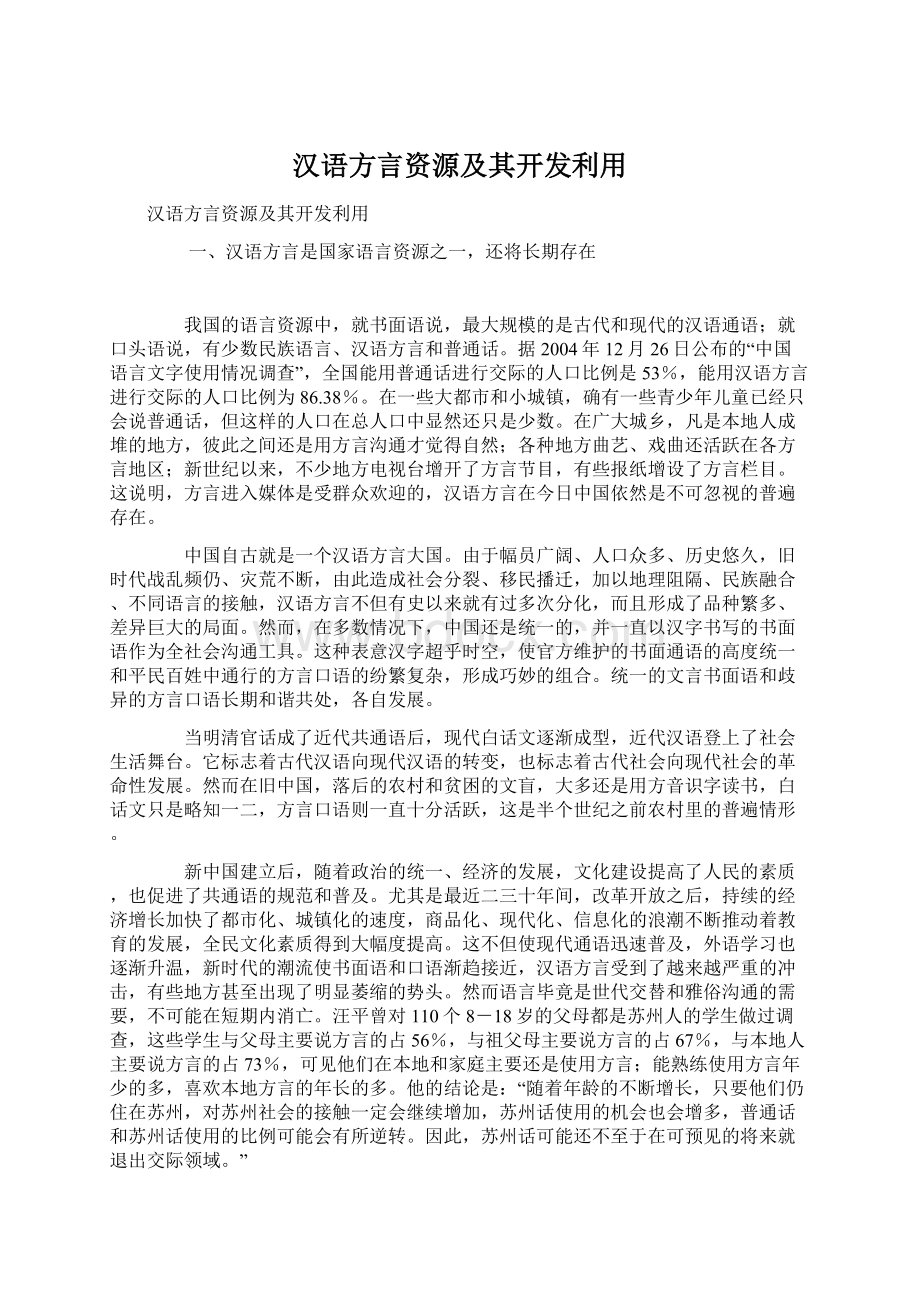
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一、汉语方言是国家语言资源之一,还将长期存在
我国的语言资源中,就书面语说,最大规模的是古代和现代的汉语通语;就口头语说,有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和普通话。
据2004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是53%,能用汉语方言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86.38%。
在一些大都市和小城镇,确有一些青少年儿童已经只会说普通话,但这样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显然还只是少数。
在广大城乡,凡是本地人成堆的地方,彼此之间还是用方言沟通才觉得自然;各种地方曲艺、戏曲还活跃在各方言地区;新世纪以来,不少地方电视台增开了方言节目,有些报纸增设了方言栏目。
这说明,方言进入媒体是受群众欢迎的,汉语方言在今日中国依然是不可忽视的普遍存在。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汉语方言大国。
由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旧时代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由此造成社会分裂、移民播迁,加以地理阻隔、民族融合、不同语言的接触,汉语方言不但有史以来就有过多次分化,而且形成了品种繁多、差异巨大的局面。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中国还是统一的,并一直以汉字书写的书面语作为全社会沟通工具。
这种表意汉字超乎时空,使官方维护的书面通语的高度统一和平民百姓中通行的方言口语的纷繁复杂,形成巧妙的组合。
统一的文言书面语和歧异的方言口语长期和谐共处,各自发展。
当明清官话成了近代共通语后,现代白话文逐渐成型,近代汉语登上了社会生活舞台。
它标志着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也标志着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革命性发展。
然而在旧中国,落后的农村和贫困的文盲,大多还是用方音识字读书,白话文只是略知一二,方言口语则一直十分活跃,这是半个世纪之前农村里的普遍情形。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建设提高了人民的素质,也促进了共通语的规范和普及。
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间,改革开放之后,持续的经济增长加快了都市化、城镇化的速度,商品化、现代化、信息化的浪潮不断推动着教育的发展,全民文化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
这不但使现代通语迅速普及,外语学习也逐渐升温,新时代的潮流使书面语和口语渐趋接近,汉语方言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明显萎缩的势头。
然而语言毕竟是世代交替和雅俗沟通的需要,不可能在短期内消亡。
汪平曾对110个8-18岁的父母都是苏州人的学生做过调查,这些学生与父母主要说方言的占56%,与祖父母主要说方言的占67%,与本地人主要说方言的占73%,可见他们在本地和家庭主要还是使用方言;能熟练使用方言年少的多,喜欢本地方言的年长的多。
他的结论是: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只要他们仍住在苏州,对苏州社会的接触一定会继续增加,苏州话使用的机会也会增多,普通话和苏州话使用的比例可能会有所逆转。
因此,苏州话可能还不至于在可预见的将来就退出交际领域。
”
在方言的保存方面,苏州的情况应届于中间状态,比它强势的有上海话、广州话。
上海话因为使用人口多,数十年来在吴语区的影响早已超过苏州话,广州话则是东南方言中头号强势方言,说得出就写得来,至今还常给通语输送新词语。
比起一些方言区边界上的小方言点和通行不广、使用人口不多的小片方言或其他方言包围的方言岛来说,它明显属于强势方言。
以苏州话这种中间状态作为代表说明汉语方言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消亡,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二、汉语方言普遍处于剧变之中,亟须监测
由于普通话的普及,方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也是当代中国语言发展的主要趋势。
方言的急剧变化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萎缩,一是蜕变。
所谓萎缩,是指方言的使用范围在不断缩小。
据徐睿渊、侯小英2003年在厦门对224个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所做的调查,他们的父母都会厦门话,但学生中只有172人会听会说厦门话,在幼儿园,只会听不会说的达80.56%。
她们的结论是:
那些懂本地话的厦门人,他们使用方言“更多是在家庭中,在亲人、朋友或同学之间,在涉及日常生活的交谈中使用”。
“闽南话在厦门青少年当中已不是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
”闽南话是东南方言中的强势方言,在这个中等城市,少年儿童中竟然也出现了流失的现象,有些小学、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说不来、甚至不会听本地话。
汉语方言的萎缩之势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那些穷乡僻壤的小方言的流失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萎缩”是语言“外部”的变迁的话,方言的“蜕变”便是语言“内部”的演化,即方言结构系统的变动,包括语音系统、语法系统的调整,词汇的更替。
总的说来,现代社会里方言蜕变的基本特征是:
原来固有的方言特征逐渐淡化、减少乃至消失,越来越多地接受通语或周边强势语言的影响。
钱乃荣的《上海方言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急剧变化的典型。
该书拿1853年英国传教士JamesSummers所编的上海方言词典和现代新派上海口音作比较,理出了150年来上海方音所发生的变化。
就音系说,声母从30个减为28个,韵母从63个合并为32个,声调则由8个合为5个;就字音说,文白异读大为压缩,多数是保留白读音,放弃文读音。
词汇方面许多单音词演化为双音词,特征词也发生了变化,还有新词语大量涌现。
语法方面主要是动词的体貌有较多变化,其他原有的许多助词则略去不用(如表关联的“?
ā⒛?
”);有些则是受通语的影响(如吃仔饭→吃了饭,看我勿起→看不起我)。
上海话变化较大,是因为人口的急速膨胀和密集地聚居,使多方杂处的方言在竞争中碰撞,略异存同;都市化进程使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内容频繁更新。
和上海话相比,苏州话100年间的变化则要小得多。
据丁邦新《一百年前的苏州话》就陆基的《苏州同音常用字汇》与1998年出版的《苏州方言志》所作的比较,100年间苏州话的音类系统的差异只有三种ε、uε→E、uE,□→ι,uo、uo?
、ua?
→o、o?
、ua?
,音值的差异也只有四项:
iE→iI,uo、tioη、uo?
、ua→io、ioη、io?
、ia、un、un→uen、yen(可能同音)u→u和eu。
苏州历史悠久、人口变动相对较小,又有许多“苏白”的唱词和文本有过记录和流传,方言上变动较小是在情理之中。
在闽方言区,福州话、厦门话变得慢。
福州话的音类300年间的明显变化只是两个韵母发生合并:
uoi、iu→ui、ieu、iu→iu,声母、声调一如既往;厦门话的语音系统百余年间只发生两个明显变化:
人母混入柳母、参韵混入公韵,而这两点变化牵涉到的字很少;但是我们曾调查过的闽东宁德市碗窑村的闽南方言岛,根据三位发音人(分别为75、44、19岁)的发音,声母和声调并无区别,但韵母中新派把老派的29个韵母合并为11个韵。
可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不同,方言萎缩的速度或蜕变的进度是有差异的。
萎缩的起点何在,蜕变的重点是什么,都需要按照方言的分区和分布特点以及社会文化的特征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比较分析,实施考察和监测。
三、汉语方言资源的理论开发研究
中国现代语言学兴起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第一代语言学家把音韵学研究和方言调查结合起来,用方言事实证明古音流变,才使中国语言学走上了科学道路。
数十年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又为汉语语音史、词汇史乃至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贵的证据。
近20年间,上古音的研究更与汉语藏系诸语言的研究联手,相互论证,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汉语方言资源的开发将可以促进汉语语言学的理论建设。
目前较为迫切的工作是:
第一,为濒危方言作抢救性调查。
尽管不是普遍现象,汉语方言中还是存在着一些萎缩、蜕变中的方言点,如《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2006)就提到:
闽浙边界一带的畲话,两广、湘、琼的水上人家所说的蛋家话,两广、闽、琼不少地方所分布的“军话、正话、儋州话、迈话、伶话”等方言岛,闽北山区及湘桂边界的一些小片方言,使用人口很少,受通语影响很深,如不及时记录,也可能很快失传。
抢救、发掘这些方言,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保持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应该做好抢救、保存濒危的语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和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为此建立了专门的研究项目,为调查和出版有关专著提供资金、组织力量,并且已初步收到了成效。
第二,整理和研究近代方言的民间文献和传教士所编的方言读物。
明清以来,由于方言口语和书面通语日益悬殊,一些方言都编过韵书和其它杂字、小词典,有的记录了本地山歌、童谣、唱本,撰写过反映本地风物的小说、笔记。
这些语料有的整理过,但多半未引起重视和研究。
这些民间文献直接保存着方言的语音、词汇和俗字资料,是我们研究方言史及近代汉语的宝贵资源。
与此同时,还有外国传教士来华所编的各种方言词典、课本、描写语法以及用方言说解的圣经和其他读物。
据游汝杰调查,仅就东南方言材料统计,自1828年起,语音、词典、课本、语法类材料就有251部,其中粤语较多,达90部;方言翻译的圣经(含汉字本、罗马字本)则达1200种,其中以闽语最多,有474种。
他认为:
“这些文献记录描写并研究了当时各地汉语方言口语,在广度、深度和科学性方面远远超过清儒的方言学著作,也是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比如地方志和方言-文学作品所望尘莫及的。
它们对于研究近代中西学术交流、中国基督教史、汉语方言学和方言学史都有相当高的价值。
”利用这些文献,至少可以十分完整地归纳出十几种方言的19世纪的语音系统,整理和研究其词汇和语法,考察这些方言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演变。
近十年来,这项工作已经引起学者注意,初步发表的研究报告证明,游汝杰的说法是正确的。
第三,加强方言词汇和语法的研究,并关注语音结构与词汇、语法的关系。
方言本来就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相联系、相结合的系统,许多词汇、语法现象是透过语音的结构和变化表现出来的。
以往的方言研究多侧重于语音,描写语音系统,作音韵比较,不重视词汇、语法的研究,对于词汇、语法和语音之间的相关联也未加深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言词汇研究受到重视,编了不少方言词典,但是大规模的穷尽式的调查还做得很少,一般只是数千条的规模。
此外,关于词汇的结构系统、语义系统、语用系统的研究,词汇中基本词与一般词的替换迁移,通语词(尤其是书面语词汇)对方言词汇的影响,不同方言在造词方法上的异同,方言中固有词汇与借用词汇之间的竞争和更替,都还缺乏认真的探讨。
至于方言有没有自己的语法结构系统(例如虚词的系统)和语法化演变过程和规律,在学者之中还可能有不同看法。
为了提高汉语方言的整体研究水平,这些研究应该加强。
第四,大力加强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汉语方言的研究,只有广泛、深入地进行纵横两面的比较,如单区内部各点或多区之间的方言事实比较,现实的方言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通语比较,乃至和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比较,才能认识方言之间的异同,了解方言与通语之间的亲疏关系,理清方言与古代通语或古方言之间的演变关系和层次关系,才能探知远古汉语与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渊源关系和接触关系。
总之,只有经过比较,才能真正地建立科学的汉语方言学,并使方言研究更好地为汉语史的研究、为汉藏语言学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比较对方言研究来说是方法问题,也是方向问题,是汉语方言研究寻求理论提升的根本出路。
四、汉语方言资源的开发应用
汉语方言资源在应用开发方面还远没有引起关注。
开发汉语方言资源以利于社会应用有三件事亟待大力推动。
(一)应用于语言教育
语言教育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包括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以及社会语文教育。
利用汉语方言资源与此都有或大或小的关系。
关系最大的是母语教育――语文教育。
现今的青少年大多是在方言母语的环境中长大的,即使方言母语不熟练,所学的普通话也带着方言腔调。
语言习得先入为主,对于入学后接受语文教育不可能没有影响。
对他们教语文,不能一心只教学普通话,不顾方言母语的影响,只有正视它、研究它,找出本地人学好普通话(包括标准音、规范词和正确句型)的难点,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方言普查提出,要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编写了学习普通话手册,现代汉语教科书也增加了“方音辨正”。
但是因为教材没编好,要么太深,用许多语言学术语来分析方言;要么抓不到要害,比较一些人所共知的词汇(日头――太阳,月光――月亮),没有好效果。
事实上,方言普查的成果不能直接搬到课堂上,语文教学中的方言和通语的比较研究需要另辟蹊径。
民族地区的学生往往也有某种汉语方言的母语基础,例如云贵川的学生先学到的汉语是西南官话,他们在学习全国通用的标准语时也会和方言区学生遇到同样的问题。
实行双语教育需要对比的包括民族母语、国家通用语和背景方言,情况更加复杂,需要更多方面的对比和教学研究。
方言区的学生学习外语往往有不同的难点。
为了提高外语教学水平,也应该研究方言和外国语的差异。
至于对外汉语教学也并非与汉语方言无关。
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生提出了学习某种汉语方言的要求。
广州话、上海话和厦门话的教学班已经陆续有人开设,但是如何编写适用于外国学生的教材,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基本上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在社会语文教育方面,为了造成普通话的氛围,提高普通话测试的质量,培训第三行业从业人员的普通话水平,也有针对本地方言特点加强有效普通话训练的需要。
可见,把汉语方言的资源应用于多种语言教育,还有待于方言学者和语言教育工作者联手研究,编好教材,做好教学设计、试验和总结。
(二)应用于语言规划的制定和贯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语言生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正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所指出,“语言生活朝着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新的语言现象大量涌现”,“普通话和方言互动加快,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在新的形势下,对于“方言进入媒体、方言教学进入课堂”的问题,对于要不要坚持“语言规范化”的问题,学术界还有些不同看法。
在对待方言的政策上,也有“保护方言”、“保卫方言”的种种提法。
要制定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首先应该在理论上统一认识。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001年《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
“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切不可分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
”我国的语言政策历来强调,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基本精神与此是相符的。
语言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生活能力的需求。
习惯根据需求而变化。
语言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方面:
全社会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这是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应该说,体现社会主体性的通语和体现语言多样性的方言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尽管二者有着不同的消长过程,却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当前,方言播音要不要进入广播电视?
已经进入的,要不要限制播送时间?
报刊和文艺作品可否使用方言?
小学课堂要不要教学方言儿歌和童谣?
都可以按照“习惯”和“需要”的原则,根据不同方言地区的实际情况,先放放手,进行一番调查研究,考察实际效果和群众反应再做权衡。
既不要轻易指责为“方言回潮”,也不必为之鸣锣开道,使其星火燎原。
习惯可以改变,需要可以调整,决定语言生活取向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千百万群众经过长期选择、磨合而逐渐确定下来的。
至于语言规范问题,近些年来学界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
20世纪50年代提出“规范化”的要求并非无理,在书面语与口头语差别巨大迥异、文言和白话并行、通语和方言尚难划界的年代,提倡和强调规范是必要的。
后来在工作中理解有些片面,划界生硬,对不同文体没有加以区别,因而有些消极影响。
然而也不能抱着“今是而昨非”的看法,认为不该提倡语言规范。
规范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
在人多语杂的时代和地区,完全没有规范是行不通的。
在维护规范时,如果增加些弹性和宽容,对于汉字的字形和读音的规范与词汇语法的应用采取不同尺度,就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三)在文化艺术的传承上发挥作用
中国学者调查方言是从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研究民间歌谣开始的。
歌谣包括儿歌、情歌、童谣等都是能念能唱的,此外还有能说的(民间传说、故事、谚语),配合着唱腔、舞蹈和器乐演奏的还有各方言区都很常见的戏曲和曲艺。
这些千百年来用方言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也是世代交替中规范着社会生活准则的道德信条,培育下一代的口头教科书。
是蕴藏着许多生活经验和艺术创造的宝库,是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民族文化遗产。
在现代社会,共同语不断普及,方言作品和艺术演唱,逐渐不适应紧张繁忙的生活了,许多新的形式(电影、电视、VCD、卡拉OK等)掀起了时尚的新潮。
方言文艺式微了。
近些年来,保护和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了关注,成为各级政府的行为,采取很多措施,取得不少成果。
但是方言文艺、地方戏曲的研究,语言学家介入的还不太多,缺乏深入的探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部领导的全国地方谚语、歌谣、故事“三集成”的编纂,本来很有意义,但没有方言学家参加,把许多生动活泼的方言词语都转换为普通话,失去了原汁原味,降低了这项工作的意义。
关于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在政策处理上目前也存在一些争议。
例如方言小品和连续剧要不要放手发展?
电视剧的某些角色要不要容许方言对白?
地方戏曲要不要维护传统正音?
在这些方面先放宽些,再总结经验,应该是可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