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之路吴稼祥.docx
《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之路吴稼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之路吴稼祥.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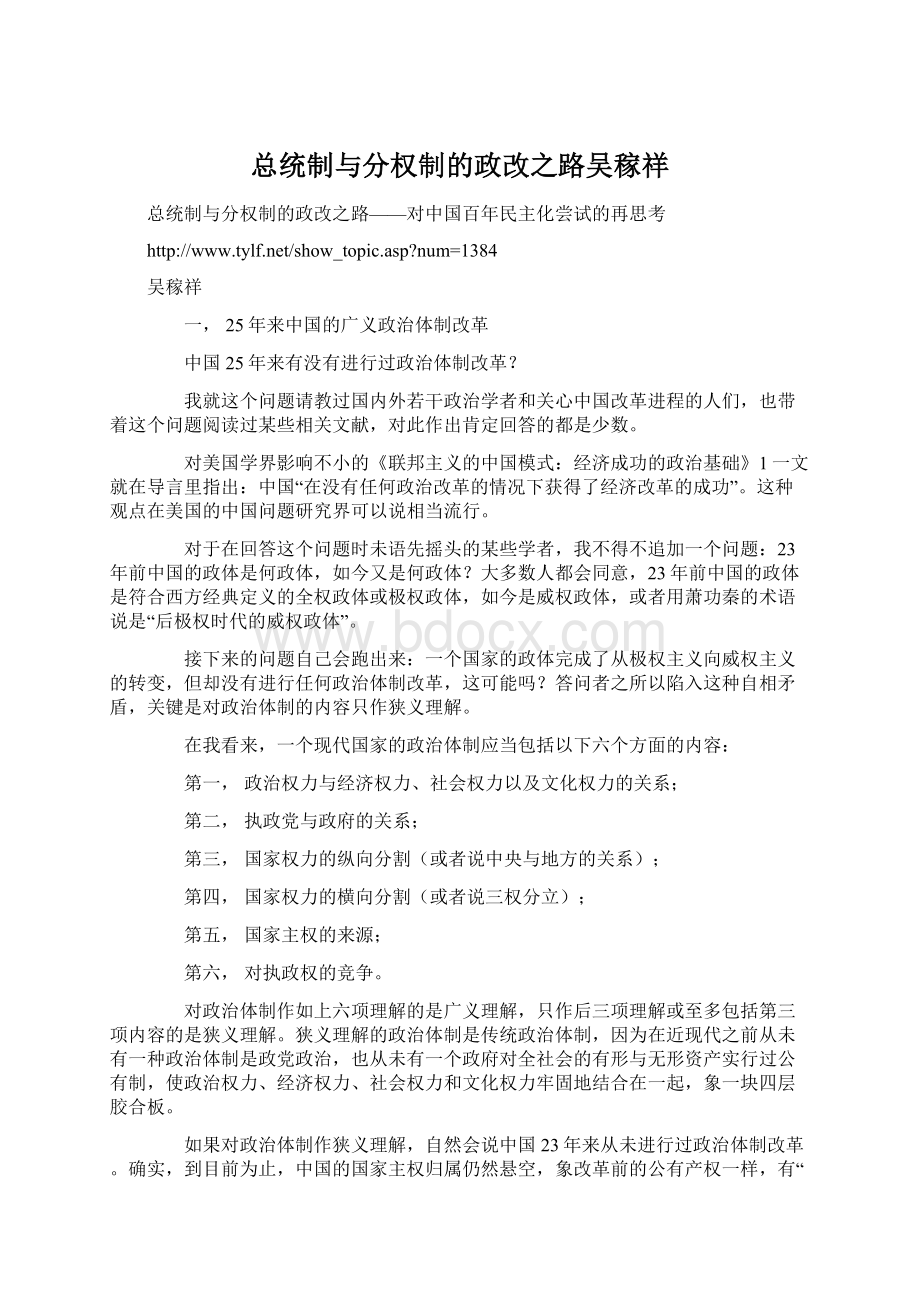
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之路吴稼祥
总统制与分权制的政改之路——对中国百年民主化尝试的再思考
吴稼祥
一,25年来中国的广义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25年来有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
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国内外若干政治学者和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人们,也带着这个问题阅读过某些相关文献,对此作出肯定回答的都是少数。
对美国学界影响不小的《联邦主义的中国模式:
经济成功的政治基础》1一文就在导言里指出:
中国“在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改革的成功”。
这种观点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界可以说相当流行。
对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未语先摇头的某些学者,我不得不追加一个问题:
23年前中国的政体是何政体,如今又是何政体?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23年前中国的政体是符合西方经典定义的全权政体或极权政体,如今是威权政体,或者用萧功秦的术语说是“后极权时代的威权政体”。
接下来的问题自己会跑出来:
一个国家的政体完成了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但却没有进行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吗?
答问者之所以陷入这种自相矛盾,关键是对政治体制的内容只作狭义理解。
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应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以及文化权力的关系;
第二,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第三,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割(或者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四,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割(或者说三权分立);
第五,国家主权的来源;
第六,对执政权的竞争。
对政治体制作如上六项理解的是广义理解,只作后三项理解或至多包括第三项内容的是狭义理解。
狭义理解的政治体制是传统政治体制,因为在近现代之前从未有一种政治体制是政党政治,也从未有一个政府对全社会的有形与无形资产实行过公有制,使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象一块四层胶合板。
如果对政治体制作狭义理解,自然会说中国23年来从未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
确实,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家主权归属仍然悬空,象改革前的公有产权一样,有“人民主权”之名无“人民主权”之实;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割还是一个禁区,虽然司法权力不再是聋子耳朵,人大立法权力也不再是橡皮图章,但远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分权格局;至于执政权竞争问题更是万伏高压线,凡血肉之躯轻易碰不得。
但是,25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在使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分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旧体制对每个社会成员从摇篮到坟墓的管制放松了,包括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和财产自由等在内的人身自由有了长足进步;在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成效相当可观:
党包揽一切,干预一切的情况大大减少,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复存在。
这方面最成功的范例是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分权。
虽然90年代在财政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分权格局依然存在。
这一被西方研究者称为“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权改革,被看成是有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模式,是中国获取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一。
此外,以香港、澳门回归为契机,邓小平先生设计的“一国两制”成了中国单一制国体的突破口,使中国向现代地方分权制政府和复合制国体迈出了拓荒的一步。
本部分的结论是,中国在过去25年里进行的以经济体制为主导的改革,具有广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它的意义在于把中国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威权国家。
这一改革至关重要,它将中国从一个无法进行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国家,还原成了一个可以进行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常国家。
这就是说,中国目前进行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近代以来中国两次失败的民主化尝试
狭义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民主化改革,或者说是立宪改革。
从程序上实现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是选举政治;在主权结构上实行权力制衡,用权力限制权力,是分权政治;在若干政党之间或同一个政党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有序的权力竞争,获胜者在一定期限里执政,是政党政治。
尽管世界各国宪政形式千差万别,但所有真正的民主宪政都包括上述三项内容。
有这三项内容者为真民主宪政,没有这三项内容者是伪民主宪政。
中国的先知们从辛亥革命开始,就试图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
清帝国的大厦还在倒塌之中,辛亥革命的炮声还在轰鸣之时,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创制者们就聚首汉口英租界,起草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把三权分立的政治原理规定为中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原则,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是对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寻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制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
1911年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定新生的国家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诞生了!
”2
这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尝试,但结果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它的失败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未能制止国家分裂。
清室丧失的国家领土非但没有索回,民主革命还导致国家主权继续受损:
外蒙脱离中国,中央政府不能有效行使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主权长达40余年。
第二,最终导致军事专制。
民主革命不仅没有终结中央专制,中央集权的程度反而不断加深:
袁世凯的中央集权超过晚清,蒋介石的中央集权超过“洪宪”,毛体制的中央集权超过蒋氏。
革命最终使中国由比较缓和的君主政治专制,变成了更加严酷的僭主军事专制。
第三,国家陷入连年战乱。
1911年是辛亥战争,1916年是讨袁战争,1916至1928年军阀混战,1927年至1937年爆发第一次国共冲突,1945年至1949年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可以说是3年一小战,5年一大战,饿殍共战尸同卧,血水与祸水一辙。
第四,无力阻挡外敌入侵。
军事暴政与乱灾战祸大伤中国元气,使得往年只能在中国边境偷窃胜利的日本军队,从1937年开始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险遭亡国之灾。
以美国为蓝本的民主化尝试的失败,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目光转向苏联,试图尝试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化。
虽然列宁自诩无产阶级政权比资产阶级政权民主“一百万倍”,但毛泽东清楚,这与其说是对现状的描述,不如说是愿望的表达。
真要搞出一套异于并且高于西方民主的民主,需要挖一番心思。
从毛泽东在延安答问时的情况看,他搞民主,实用多于理想,策略甚于价值,他说他找到了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
显然,他搞“民主”的公共目的是想让他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或者说他的“王朝”长盛不衰,私人目的是保障他生前的权力安全和身后的“庙号”安全。
毛泽东搞的民主化实验便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他用他自己发明的“有领导的造反”,代替西方民主的“有秩序的投票”。
这种被称为“大民主”的尝试,也有有效授权期的思想,按照毛的设计,一次授权最好不能超过8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当然,他本人不受此限。
他这个思想是否可以叫做大民主的僭主非立宪思想,还可商榷,但他的创造性尝试也以悲剧收场。
这个悲剧就是:
政治独裁,经济贫困,社会动乱,文化灭绝,人性堕落。
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
“历史已经判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3
值得关注的是,两次民主化尝试的发动者,分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两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毛泽东:
孙中山缔造了中华第一共和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后帝制国家;毛泽东开创了中华第二共和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逸出现代化常规的非正常国家,是一个全权主义国家。
不同背景下的民主化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能不让中国民主化的后继者们踌躇难前。
一方面,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民主化改革的道路尚未探明。
要改,但又不能盲目改。
不改,坐失良机;盲目改,酿造祸患。
要摆脱这种两难处境,首先要探询一下,民主宪政为什么至今拿不到中国的入境签证。
三,以往中国民主化实验失败的原因
中国两次民主化实验为何都归于失败?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仔细探究,并从中总结出恰当的教训,中国今后的民主化尝试难免不再走弯路。
在经典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中国的民主化难以成功,或者说中国不能马上民主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文化落后。
这一论点经过长期传播,相当深入人心。
其实,这个观点不仅未在已经成功民主化的落后国家得到证实,比如印度,它的民主化成功于半个多世纪前,不能说那时的印度比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文化还要先进;这个观点也被中国当下的乡村自治实践所反驳:
基层民主化没有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居民区,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先启动,反而在相对落后的乡村率先试点。
经过近10年来的思考和对比研究,我发现,使中国的民主化工程半途夭折的基本原因有两个:
第一,幅员辽阔,第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不少民族基本按地区集中聚居。
按照美国制宪之前的古典政治学原理,一个大国搞民主必然失败;按照现代民族自决原则,一个多民族的专制大国如果崩溃,便难以按原样复原,分离出去的民族往往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
大国搞民主包括两重含义:
一是一批小的民主国家聚合成一个大国;二是一个大的专制国家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把这里的“民主”,都读作“直接民主”的话,大国民主不可能性原理就不难理解。
因为在直接民主制下,议行合一,最高立法权和行政权都在公民大会。
如果国家大到不能让全体公民都出席会议,民主权力就可能被寡头篡夺,变成专制。
孟德斯鸠和卢梭都因为爱民主,所以爱小国。
在卢梭看来,实现他《社会契约论》理想的理想国家是日内瓦而不是法兰西4,因为,仔细考察了一切之后,他“认为除非是城邦非常之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
”5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大了,人民民主便会变质。
因此,大国民主的失败也有两个含义,一是若干民主小国联合成一个大国,结果保全了大国,但丧失了民主;二是一个专制多民族大国在民主化过程中崩溃,结果之一是分裂后的国家分别实现了民主,但都丧失了大国地位,结果之二是经过战乱又回到专制,但回不到原来的国家规模,由一个头等专制大国,变成一个专制的次等国家。
美国的联邦党人战胜了前一个宿命中的失败,前苏联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一个结果,中国前两次民主化试验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二个结果。
其实,任何宿命论,都是对创造力的一项挑战。
创造力旭日东升时,宿命论就作雾散。
美国费城制宪时的反对者,包括邦联主义者和君主专制主义者,显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民主仅仅理解为直接民主。
在君主政治的拥护者看来,在美国这样大的国土上,搞直接民主必然产生混乱,“一切自由政府都是与社会秩序不协调的”;6而在邦联主义者看来,邦联一旦变成联邦,民主共和政体便会死亡,他们认为,“共和政体只能在生活于小范围国土上的少数居民中建立起来。
”7
联邦党人理解到民主的实质是共和精神,直接民主的“民主政体”不适合大国,“将限于一个小小的地区”,但经过代议制和联邦制改进的间接民主,即“共和政体”,则“能扩展到一个大的地区。
”8他们真正看懂了孟德斯鸠关于联邦制的一个深刻提示:
“联邦既由小共和国组成,它便享有各共和国的内部内部幸福,至于对外情况,由于联合,它具有大君主国的一切优点。
”9这和托克维尔后来对美国的观察完全一致:
美国“联邦既象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象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10
西方古典政治学揭示的是大国的直接民主必然变质的原理,我在《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一书里,提出的是启动民主化的专制大国易于崩溃的原理。
在我看来,一个专制的超大型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可能不是它拒绝民主化的时候,而是它被迫接受民主化的时候。
那本书提出了一个“瀑布假说”:
一个国家的权威资源象一条瀑布,国家越大,要求的权威落差越大,也就是说对中央集权的程度要求越高,犹如一条瀑布流得越远,要求它的发源地越高。
长江能流到海洋,因为它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
这里的机制很好理解:
国家越大,统治费用越高,要求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和统一政令的能力越强。
当它开始民主化的时候,权威落差会突然下降,原有的中央权威会突然丧失,国家面临分裂、崩溃和混乱。
11袁世凯称帝前的中华民国靠举外债度日,就是中央权威突然下降的结果。
这就是中国第一次民主化尝试中出现的问题(当然更是当年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中国第二次民主化实验中变相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或许直觉到这个危险,他试图在政治造反过程中神化他个人的权威来取代整个中央权威,以维持国家的统一与秩序,结果只能是绝对个人权威与整个社会动乱的畸形并存。
如果一个专制大国同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少数民族还按地区分布,那么,它在民主化中崩溃和分裂的危险性会更高。
在苏联东欧变迁中,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国维持原状,而两个德国反而完成了统一。
从这里可以观察到,那些分裂崩溃的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大国,第二是民族同一性低。
而东德,不仅民族同一性高,而且联邦德国还取代了崩溃的东德政府权威,使德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变革收益:
民主化和民族统一毕其功于一役。
有两种民族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分裂的风险大小不同。
一种是美国式的“沙拉国家”,各民族相互搅拌,混杂居住;另一种是俄国、中国和加拿大式的“拼图国家”,各民族呈块状分布。
后一种国家分裂的可能性远大于前一种国家,即使是早就完成民主化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分离倾向也始终存在。
本节的基本结论是,如同不实行代议制民主,民主化就不可能在西欧各民族国家获得成功一样;如果不实行联邦制民主,民主化也不可能在美国、俄国和加拿大那样的多民族大国获得成功。
四,邓小平的第三条政改之路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邓小平对中国过去民主化失败的原因和今后民主化的条件有过深入思考,并且将自己思考的结果具体化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他的方案未必是民主化本身,但却是为中国的第三次民主化尝试创造条件的预备方案。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这篇讲话让当时渴望政治改革的人们很解渴,但今天看来,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想清楚了:
“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但道路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如何充分发扬民主,他提到的改革措施,也只是设立顾问委员会,建立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系统,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各企事业单位成立工会,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等等12。
很明显,在1980年时,对毛式全权体制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刚刚开始,这时候就全面展开民主化改革,很难不重蹈历史覆辙。
虽然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呼声很高,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却难有作为。
实际上,从1980年到1986年的6年间,中国在充分发扬民主方面难以让人想起什么标志性动作。
这期间,邓小平没有停止思考。
到了1986年,一半因为他决心退休,想在退休前开始施工政治改革工程,一半因为他在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方面有了成熟想法,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一年里先后10次倡言政治体制改革。
5月20日,邓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提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学、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放,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
”13
6月10日,他对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说“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14
6月2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提出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说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明确提出: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
15
9月3日,邓会见日本客人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16
9月13日,邓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经济改革时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
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
”17
9月29日,邓小平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
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18
11月9日,邓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
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
19
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樱内义雄,再次强调,“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
”20
邓还于12月14日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于12月19日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又先后两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在19日的谈话中提出:
“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
”21
原文并无黑体字,本文作者将引文中某些字改成黑体,目的在于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到,10次讲话,主题词主要是两个:
下放权力(或权力下放)与党政分开。
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多内容,邓小平为何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这两项,而且用“首先是”或“是关键”这样的词来突出其重要性和优先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来讨论一下这两个词的含义。
权力下放,在英文里的对应词是“decentralization”或“noncentralization”,是非集权化的意思。
对于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来说,权力下放与“联邦化(federalization)”指称的是同一个政治过程。
美国著名联邦主义理论家丹尼尔•艾拉扎博士曾经为“联邦化”下过定义:
“‘联邦化’一词用来描述分离的若干国家联合成一个联邦政治体的统一过程,也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威或权力在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持续扩散。
正是在这个看似含义模糊的词里,含有联邦原则的精髓:
联合与放权(noncentralization)的不断交替。
”22显然,不论用什么词来描述,邓小平强调的权力下放改革,具有明确的联邦化意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再来看看党政分开。
权力下放,中央的权威相对下降,这会不会影响政治稳定?
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一种平衡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两手哲学”: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它的经典表述形式是“两个基本点”。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应该用两手哲学观点来看待他的“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改革措施。
权力下放是调动基层积极性的一手,党政分开便是改善并保持中央控制力的一手。
旧体制是用党来集权的,而且党权政权连为一体。
如果党政不分开,权力下放便意味着党政权力一起下放,中央权威将受到双重削弱,政治有失去稳定的危险。
党政分开,党从政府权力中退出,当政府权力下放时,党的权威不受根本影响。
所以,邓小平才说,“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
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那么,党从政府退出后干什么呢?
干它自己的正事:
为政府挑选执政者,在议会里保障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政策。
这就是说,党本身不再有指挥政府的权力,党的权力转变为正常的执政权:
一个任期行使一次的政府首脑提名权以及议会开会期间的提案权和表决权。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既要保障党的执政权,又要保障中央的权威,党的最高首脑在政府里要出任最高职务,在中央政府,要出任国家元首,建立总统制政府。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是最后一次由邓小平进行总体布局的党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最意义深远的政治安排是决定党的总书记出任国家主席职务,国家主席职务不再是安排退休元老的荣誉职衔。
这个静悄悄的重大政治变革,当时并未引起它应得的关注。
但以后的历史进程将表明,这是中华第三共和国迈向总统制的第一步。
总结上述,邓小平指明的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从逻辑上必然通向中央总统制和地方分权制。
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这表明,邓小平已经从过去两次民主化失败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已经悟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不可能搞中央集权式的民主,也不能搞内阁制民主。
如果硬要搞,还会走上过去先崩溃混乱后重新集权的老路。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邓小平的第三条改革之路,便是:
要民主,先放权;要分权制,必要总统制。
五,地方分权制
权力下放是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两项根本措施之一,其目标应当是建立地方分权制的国家体制。
这里的地方分权制,显然是相对于中央集权制而言的,它们指称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或政府关系。
在丹尼尔•艾拉扎看来,有三种组织模型(organicmodel),第一种是矩阵模型(Thematrixmodel),第二种是权力金字塔(Thepowerpyramid),第三种是中心—外围模型(Thecenter-peripherymodel)。
23按照他的定义,联邦制政体属于矩阵模型,中央集权制政体是权力金字塔模型。
显然,和联邦制政体一样,地方分权制也是矩阵模型。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既然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都是矩阵模型,二者之间有何异同?
第二,如何理解矩阵模型?
先谈第一个问题。
从政治结构本身看,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没有差别,都是非中央集权体制,地方实行自治,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分享国家权力24,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指令关系被政府之间的协商关系所取代。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两个不同的名词来指称相同结构的政体呢?
这样做的理由是,虽然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权力结构相同,但它们的产生方式不同。
联邦制产生于若干分离的政治体的联合,地方分权制产生于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内部的权力下放。
美国是联邦制的最成功典范,俄罗斯是地方分权制的最新尝试。
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体制,是一种古典的地方分权制;中国20年代末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一种特殊的联邦化冲动。
前者是国家主权者周天子让他的宗族和功臣分享他的王权,后者是从清王朝分裂出来的南方若干省军阀尝试联合成一个联邦制国家。
但这两者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分权制或联邦制。
现代联邦主义或地方分权制的本质在于:
第一,主权在民;第二,各级政治体自治。
春秋体制的主权在君王,联省自治的主权在军阀,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从基层到各级地方的自治。
自治是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的根,根深才能叶茂。
1291诞生于瑞士的联邦制度,之所以能够存活并成长为现代联邦主义政体,一个根本原因,便是它的基层自治。
数百年的政治风暴没有动摇它的自治根基,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它的现代化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邓小平向基层放权的改革看作是中国现代地方分权制的“扎根工程”。
在中国建立地方分权制,就是把中国的政治结构从金字塔结构转变为套箱结构。
在中央集权制的金字塔结构里,中央政府是塔尖;在地方分权制的套箱结构里,联邦政府(即中央政府)是一套箱子外面最大的那只箱子。
在金字塔结构下启动民主化改革,基础一动,全塔崩溃;在套箱结构下开始民主进程,箱子只是从最小的开始变动,它的外面还有一层层更大的箱子。
最后改变的是外面最大的箱子,也就是全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