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贫穷.docx
《贵州的贫穷.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贵州的贫穷.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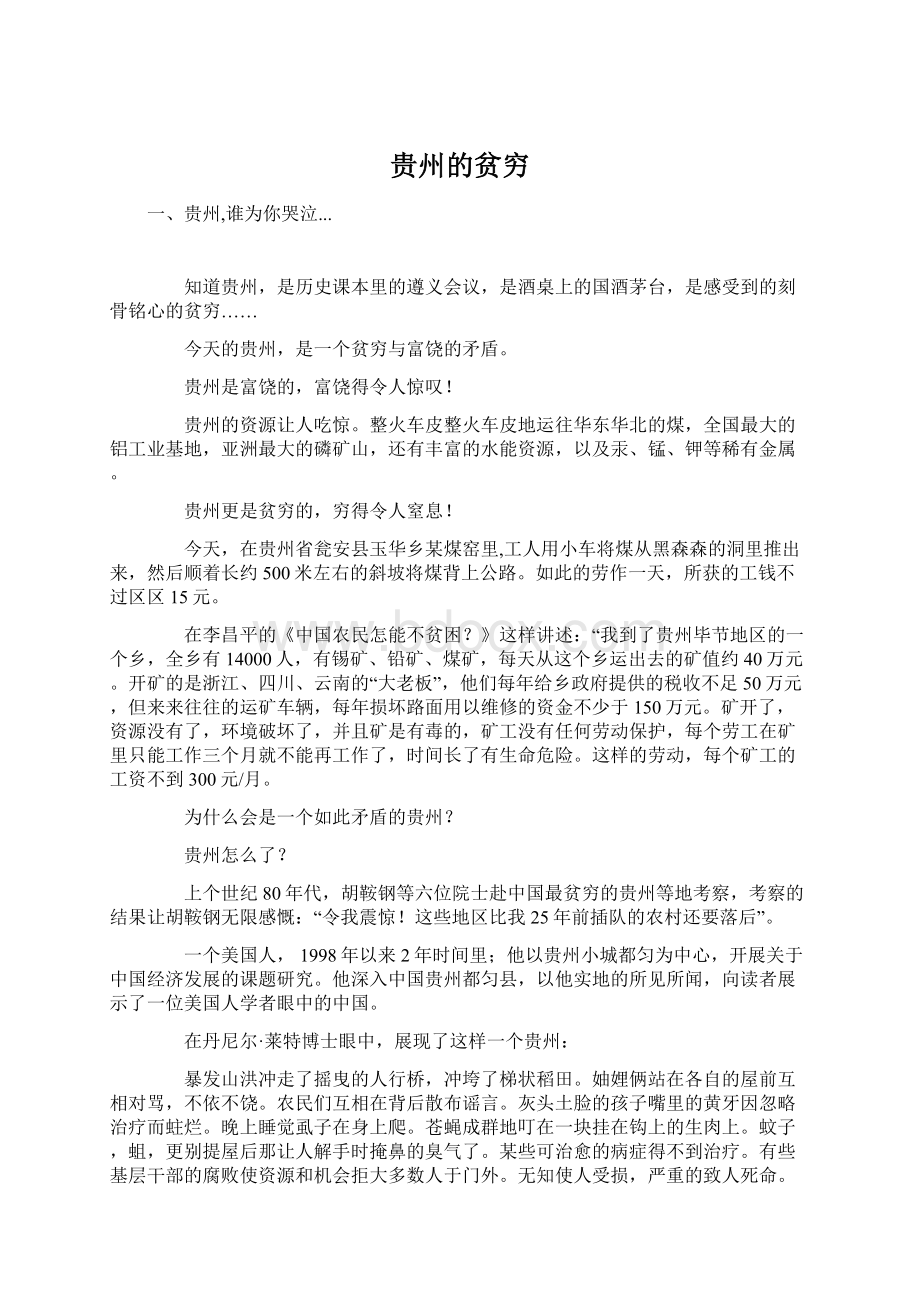
贵州的贫穷
一、贵州,谁为你哭泣...
知道贵州,是历史课本里的遵义会议,是酒桌上的国酒茅台,是感受到的刻骨铭心的贫穷……
今天的贵州,是一个贫穷与富饶的矛盾。
贵州是富饶的,富饶得令人惊叹!
贵州的资源让人吃惊。
整火车皮整火车皮地运往华东华北的煤,全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磷矿山,还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以及汞、锰、钾等稀有金属。
贵州更是贫穷的,穷得令人窒息!
今天,在贵州省瓮安县玉华乡某煤窑里,工人用小车将煤从黑森森的洞里推出来,然后顺着长约500米左右的斜坡将煤背上公路。
如此的劳作一天,所获的工钱不过区区15元。
在李昌平的《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
》这样讲述:
“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
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
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
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为什么会是一个如此矛盾的贵州?
贵州怎么了?
上个世纪80年代,胡鞍钢等六位院士赴中国最贫穷的贵州等地考察,考察的结果让胡鞍钢无限感慨:
“令我震惊!
这些地区比我25年前插队的农村还要落后”。
一个美国人,1998年以来2年时间里;他以贵州小城都匀为中心,开展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课题研究。
他深入中国贵州都匀县,以他实地的所见所闻,向读者展示了一位美国人学者眼中的中国。
在丹尼尔·莱特博士眼中,展现了这样一个贵州:
暴发山洪冲走了摇曳的人行桥,冲垮了梯状稻田。
妯娌俩站在各自的屋前互相对骂,不依不饶。
农民们互相在背后散布谣言。
灰头土脸的孩子嘴里的黄牙因忽略治疗而蛀烂。
晚上睡觉虱子在身上爬。
苍蝇成群地叮在一块挂在钩上的生肉上。
蚊子,蛆,更别提屋后那让人解手时掩鼻的臭气了。
某些可治愈的病症得不到治疗。
有些基层干部的腐败使资源和机会拒大多数人于门外。
无知使人受损,严重的致人死命。
时间再回到2006,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突然被和贵州相关的几件事所牵动:
以报道《基金黑幕》而声名鹊起的《财经》06年第19期封面文章是硕大的《兵败微硬盘》,文章是这样开篇的:
2006年7月2日,星期一。
贵州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关上了大门。
随着外籍员工于当日晚间最后一批撤离硬盘厂,这个地处云贵高原的高科技工厂,在靠存货周转了九个月之后,终于沉寂了。
微硬盘项目,一度是贵州的光荣,也承载了太多梦想。
它身上曾寄托了于三五年内达到100亿美元产值的期待,也是更为庞大的高科技产业跃迁式发展的第一步和最关键的一步——这一宏图的目标,是在2012年之前,以电子科技、新物质(材料)科技和生物科技三大主轴产业,打造1000亿美元的产业链。
这一宏图,曾经那么打动了贵州,这个2005年GDP居中国末位的边远省份。
现在,与空中楼阁一起破灭的,不仅是激情与梦想,还有总计约20亿元的巨额投资。
而在增长最快的2005年,贵州的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不过1942亿元。
在经历了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完美风暴”后,贵州所获得的教训已至为清楚。
在贵州以微硬盘项目突进“知识经济”制高点的努力中,发展高科技产业可能遭遇的所有挑战接踵而至:
知识产权瑕疵及引发诉讼、高科技产品市场朝云暮雨变化无常、企业控制权操于人手、资金流向失控、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制造流程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治理风险层层累积,勾勒出高科技企业投资的高风险图景。
相形之下,地方政府企图依赖本地资源动员能力,以为靠“遇猪杀猪,遇狗打狗”的决心即可突破重重瓶颈,最终的结果是一筹莫展。
9月初,贵阳城郊秋色中,造型现代的微硬盘厂房依旧默默伫立。
这是眼前刚刚发生的教训,它应当不只适用于贵州。
《财经》的报道揭示了作为新世纪贵州光荣与梦想的微硬盘项目这样悲剧性收场的现实,为本已了无话题的贵州再增添一笔难以描述的沉重。
2006年底,当中国各个省份官员的更替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时候,香港《大公报》刊出一篇发自北京的观察文章说,官员更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多位省委书记曾长期在新闻宣传系统工作,石宗源就是一例。
文章这样叙述:
2005年底,石宗源从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位置到贵州履新。
石宗源履新的贵州省,人均GDP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倒数第一,“穷名在外”。
石宗源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后,贵州2006年先后在北京、香港等地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展览、演出等活动。
而以遵义会议和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展览为主打的“红色牌”和“历史牌”,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贵州的知名度,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贵州走入了快车道。
2006年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调到贵州做省长了。
这让有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两天后,我在网上看到了新华社的消息:
中共中央决定,林树森同志任贵州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石秀诗同志不再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我从后来的报道中看到:
2006年6月28日晚上,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离开炎热的广州,飞抵凉爽的贵阳。
第二天上午,天还下着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林书记就参观了贵阳市金阳新区,下午,他又到省政府办公厅跟各处室工作人员见面。
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来,林树森是第一个从东部发达地区来的省级领导。
此前,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来自省外,其中,一半多来自中央部委,另外的人多来自中部省份。
从最近20年贵州话题的不断提起到今天的微硬盘项目悲剧性收场,让我想起来对贵州说点什么。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一本畅销中国的《富饶的贫困》,把贵州守着金山没饭吃的窘况刻画得淋漓尽致。
近几年,一本题名《孤独与超越》的书,由於对贵州现象的评判,引起各界争议。
一位当地经济人士无比辛酸地说,如此长时间居於中国经济榜末,贵州堪称世界贫困研究的一个绝好样板。
贵州无疑是悲剧的,这样一个典型的黄土文明样本里,集中了贫穷的表现和落后的观念。
我曾经和许多从贵州支教回来的人聊起贵州,也和许多贵州的朋友说起他们的家乡,让我对这个“中国贫穷的样板店”有了兴趣。
而当随着了解的深入和对比,当许多贵州人都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谈自己的故乡,当许多从贵州回来的人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我越来越萌发一种念头:
贵州为什么穷?
贵州又仅仅是穷吗?
贵州怎么了?
贵州为什么?
贵州怎么办?
贵州,你又真的甘愿如此?
到底是这片土地的不幸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不幸?
贵州,谁会为你哭泣?
又是谁在为你哭泣?
二、贵州之困
要说贵州,还要从贵州的前世今生说起。
当翻阅贵州历史,我更加沉重,让我难以评述……
1.机遇之困——有多少机会可以重来
三年困难时期,湘渝铁路拟从铜仁过,遭到当政者极力反对,怕把铜仁的粮食拉出去给外地人吃了。
他老人家那一拍板,导致黔东发展整整被耽误了半个世纪!
回顾历史,贵州其实曾经错失不少机会。
探究贵州落后之因,几十年来人们总结的原因不下数十条,其中两例非常典型:
一是烟酒产业的两次重大决策失误;二是整体推介方面的弱势。
历史上,贵州拥有烟(卷烟与烤烟)、白酒传统优势,八十年代初,全国十大名烟中,贵烟名气远甚如今红极一时的红塔山;八大名酒中,茅台、董酒领风骚。
但如今,贵州烟比不上云南,酒比不过四川。
谈及这段起伏,贵州官员及企业界人士唏嘘不已。
八十年代初,国家一笔巨额技改资金拟投给贵阳卷烟厂,但有一个条件,地方财政需配套数亿元。
由於态度不积极,这笔巨资被云南‘吸’走,玉溪卷烟厂这个‘小弟弟’十年内迅速超过了‘老大哥’。
统计表明,一九九九年,贵州卷烟产量一百八十八万箱,占全国的百分之五点八,但只相当於云南的百分之三十一,也低於河南(二百七十五点八万箱)、湖南(二百三十七万箱)、山东(二百二十七万箱)。
九十年代,中国白酒的第一个A股上市指标众望所归地‘判’给了国酒茅台,但据坊间传,当时部分人比较谨慎,认为国酒得保持独特风味,不宜热炒,况且市场融资後,投资的新方向也没有考虑好,结果,礼让给四川的五粮液。
五粮液集团在证券市场上长袖善舞,产值销售量快速膨胀,现已是茅台的十馀倍,市场的高占有率,使五粮液开始冲击茅台的国酒地位,甚至喊出了‘国酒不能搞终身制’的挑战之声,黔中之地一片哗然。
此消彼长,贵州白酒工业优势风光难再,一九九九年七点六万吨,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点五,相当於云南的百分之三十五、四川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贵州各界人士还不无忧虑地提及,昆明有世博会,举世皆知,奇花异草强劲带动经济;广西有山歌节,这边唱来那边和,外资涌入似清江水。
反观贵州,在全省整体推介方面就显弱势,仍在民族风情的老套上打转。
今天,贵州手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还能登上发展的客船?
贵州,还有多少机会可以重来?
2.产业贵州的软肋
贵州将烟草、旅游、酒业、药业、能源等列为贵州五大支柱产业,但从产业现状来看,和行业内对手相比都存在极大的差距。
一云、二贵、三中华,贵烟今何在
在大多数的烟民心中.贵州并非烟草大省,但其“贵烟”的品牌却名气相当,一度似酒中茅台一般。
大凡40岁以上的烟民,或者是烟草行业的老职工,都不会忘记曾经在烟民与烟草行业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一云、二贵、三中华。
这“一贵”,指的便是“贵烟”。
“二云”是指云南的“云烟”,“中华”排列第三。
“一云二贵三中华,黄果树下牡丹花”,这句曾经在上世纪被人们口头传诵高档香烟的话语,显现出了贵烟、黄果树烟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缺乏品牌意识的年代,“贵烟”已经有了相当的品牌知名度和广泛的品牌影响力。
贵州的自然条件适于烟叶的种植。
烟草传到贵州,约在明末清初,贵定曾是烟丝生产的中心。
1938年在贵阳引种烤烟成功,1939年在贵定大面积推广,很快扩展到30多个县,1949年产量达到5.95万吨,居全国第三,与鲁、豫、皖齐名。
贵州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15.44%居全国第二位,落后于云南27.59%的规模。
烤烟产量占全国12.9%居于全国第三位。
但与此对应的是,贵州卷烟产量仅占全国5.31%而居于全国第7位。
贵州在“两烟”存在质量、结构、技术、品牌、效益等诸多问题。
作为传统支柱产业之一的贵州烟草,历史有过数量扩张的黄金时期:
烤烟最高年产量1997年约达1400万担,几乎占全国正常年景烤烟收购量的1/34;卷烟在1996至1997年间全省产销量实际保持在220万至230万箱的水平,1996年和1997年两年,全省两烟税利约达50亿元。
随着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贵州烟草1998年以后每况愈下,“两烟”税收连续几年只维持在35亿元左右,抵掉亏损额后只有30亿元左右,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递减,由占50%以上降至2001年的20%以下。
到2000年,几乎陷入绝境,成为全国烟草行业惟一一个“两烟”双亏省份,潜亏挂账达80亿元,资产负债率22%。
近年来,烟草的高额利润使东部各省市、各厂都在进行最现代化的改造,都在以国际最现代化的标准建厂。
而贵州近年在技改上已无投入,如贵州第一大厂黄果树烟草集团2001年竟无一分钱的技改投入。
而且,贵州为维持生产,不断把东部地区低档品牌卷烟引进来生产,压缩自己的品牌,为别人开辟市场。
贵州烟草的发展起起伏伏。
总的来讲,因种种原因和环境,失去的机会比发展的实际效果要多。
“一云、二贵”始终未能实现,云南年税利多年超过300亿元,贵州却不到100亿。
邻近的云烟给贵烟一个不小的启示。
2005年,云南烟草创利税476亿。
2005年,“红河”“红梅”两个卷烟品牌分别以128.1万箱和126.3万箱的销量继续占据全国品牌第2、3名的位置。
云烟善于抓住机会,1958年上海一个私立烟厂(华美烟厂)在公私合营后进行工业布局调整中,被改为上海第三机床厂,不再生产卷烟,原有的卷烟设备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将之拨往云南昆明卷烟厂。
得知这一消息后,正意图发展烟草工业的玉溪复烤厂,马上意识到对于他们这是不可错过的良机,玉溪烟叶复烤厂迅速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了在烟叶复烤厂基础上扩建玉溪卷烟厂的报告,迅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并拨款180万元,作为建厂初期的第一笔投资,华美烟厂的设备也于报告批准后改调给了玉溪卷烟厂,这套设备成了玉溪卷烟厂得以建成的主要生产设备。
相比较贵州烟草业,云南烟草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市场工作和产品创新工作,云南省政府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甚至发出了“保卫红塔山”的呼吁等等,工作极有成效的。
云南曲靖烟厂的“福”牌,会泽烟厂的“小熊猫”,红河烟厂的“红河”,都是当今国内卷烟市场的热点、亮点,继续保持了云南烟畅通的声誉,在税利上,云南始终保持着300亿元的水平。
旅游——谁记得贵州
人们也许还记得“云贵旅游”这个词,那时这个词几乎就是西南旅游的统称。
一直以来,云南和贵州是“系在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可如今,一个蚂蚱起飞了,另一个蚂蚱却还在原地踏步。
贵州号称“公园省”、“旅游省”,黄果树是最响亮的招牌。
当视角投向沿海,你会发现,贵州的“公园省”、“旅游省”是多么的弱小。
贵州在旅游产业上创造的价值却远远与它巨大的资源潜力毫不相称。
根据国家旅游局2002年统计的数字:
2001年,北京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为人民币1132亿元,广东为1260.83亿元,而贵州只有81.46亿元,差距十分明显。
即使和临近的云南(257亿元)、四川(314亿元)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来黔观光的游客主要集中在“贵阳-黄果树-红枫湖”一线;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低,甚至还处于待开发状态。
短短几年,云南旅游的腾飞谱写了彩云之南的奇迹。
自'99世博会以来,云南旅游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而贵州仅相当于这个昔日兄弟的三分之一。
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相比,贵州全省的旅游收入也显得十分寒酸。
2002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成都市的旅游收入为6.03亿元,重庆市旅游收入8.56亿元,贵州全省旅游收入仅仅为1.8亿元。
在贵州流行一个词——公园省,很多贵州人也以此自豪。
公园一词,老外读做“怕客”。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公园”是个陈旧的概念,是当年过穷日子的时候,唯一可以去转悠转悠的所在。
贵州美丽的女子如同贵州美丽的景点“花开千百处,处处是美景”,但是,却鲜有当选的“世界美女”和知名的世界品牌,这与贵州发展旅游储备条件的多少有关。
贵州旅游的人均消费在全国是21位,但是平均停留天数较少。
我国国内和国际旅游比例是7:
3,贵州是94:
6;按照人数来比全国是9:
1,贵州是99:
1,在总的结构中贵州的入境旅游比例相对太少。
现在贵州50%左右的客源来自省内,还有约20%的来自全国其他地方。
黄果树是贵州的骄傲,曾与云南石林、广西桂林、重庆长江三峡、四川峨眉山齐名,位列我国著名景区金榜。
黄果树风景区在历史上曾创下过每年上亿元的门票收入,可是现在呢?
每年的门票收入已经跌到了三千万元。
而深圳市“世界之窗”在每年黄金周的门票收入就超过这个数字。
黄果树背后的原因竟然是“窝里斗”。
黄果树地处安顺市镇宁、关岭两县,原风景区管理处政企不分,各家都盯着这块唐僧肉,斗得死去活来。
为走出困境,省委省政府1999年出台了旅游体制改革的文件,成立贵州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统筹黄果树的管理开发。
可几年过去了,管委会却和经营者贵州黄果树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斗了起来,致使景区内综合开发停顿,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失败。
黄果树从金榜沦落到了副榜。
如今,黄果树大瀑布正面临着游客断流的威胁。
黄果树瀑布是贵州旅游乃至贵州的象征。
而黄果树所凝聚的旅游症结,也是整个贵州的症结。
在西部的五朵金花中,四川象山、云南似花、西藏如雪、广西如海,而贵州似水,这个“水”就是瀑布。
黄果树已形成的品牌效应,并没有更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定位只是一个“景点”,还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景区。
尼亚加拉瀑布在120年前走的就是黄果树目前的发展路子,门票是瀑布景点最主要的支柱收入,但是120年过去了,今天尼亚加拉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瀑布景观了,它更多地突出以瀑布景观为主的其它公园性的设施和功能,门票的概念已经完全从这里抹去,停车业、餐饮业、娱乐业、酒店业才是瀑布公园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综合功能作用的发挥,尼亚加拉瀑布每年上交政府的税收是1400万美元,每年的游客达到1400多万人,可以说每一个来玩的游人,有1美元是给了政府。
这种发展思路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对于贵州黄果树景区来说,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是目前最迫切的需求。
与贵州守着丰富旅游资源却没做大相比较,华侨城可以说是最好的对照。
华侨城,昔日只是一片荒滩,21年过去,华侨城培育了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深圳湾大酒店和威尼斯酒店等知名企业品牌。
华侨城的主题公园和景区在销售额、接待游客人数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位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在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城写下了中国旅游史上的许多精彩篇章:
以年均近700万的游客量,居全国单一旅游景区年接待量之首;超过30亿元的巨额投资,创建了中国投资密度最高的城市旅游度假区;累计54亿元的旅游景区收入,创下了中国旅游投资效益最好成绩。
“华侨城·旅游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评选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2000年四大主题公园以及华侨城城区并曲阜“三孔”景区同时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最高级别的“AAAA”景区,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主题公园最密集、目前规划最先进、生态环境最好的都市主题旅游城区。
目前,华侨城集团总资产达177亿元、年销售收入过150亿元。
20年来华侨城集团累计向国家交上缴税收40亿元。
在华侨城发展的20年间,贵州的黄果树却守着数十年名声或徘徊或倒退。
“公园省”、“旅游省”没有带来客源和经济收益,却依旧是守着贫瘠和困苦。
问贵州旅游有什么,还真没有人能回答,一定要回答,就只能一个个罗列景点。
不象云南,一句“彩云之南”就把人吸引住了。
2006年春,一股看油菜花的旅游热潮兴起,诸多东南沿海城市里的人开始到山区去寻找原本普通的油菜,去看油菜花开。
在旅行社推荐的线路中,有四川、有湖南,但却鲜有贵州。
殊不知,安顺龙宫盛开的油菜花美不胜收。
但这种美景却没有成为贵州的卖点,虽然有龙宫油菜花旅游节,这片油菜花海依然养在深闺无人知。
“到贵州寻找600年前的老汉人”这句口号,是近两年来屯堡人在开拓南京旅游市场时,一直不变的宣传声音。
在贵州安顺,有一个“世外桃源”。
那里的人们身披一袭艳丽的明朝汉族服饰,操一腔浓郁的江南口音,生活恬静。
这一切,都令人们有仿佛穿越时光隧道,来到600多年前的大明朝的感觉……
在被称为“明清、民国建筑时光隧道”的屯堡村落云山村里,走在细雨霏霏的古巷里,每一块砖每一面墙每一幅门框,都有故事。
口口相传的故事、家事,生动真实地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的画卷。
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并没有多少外人知道。
凡此种种,无不是发展旅游的新趋势,贵州却还是后知后觉。
好山好水出好酒下折射的贵州酒业品牌危机
如果说一般工业产品不敢轻言“贵州造”是贵州的灾难性印象使人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在贵州的传统优势产业,“贵州造”也没有打出应有的影响。
贵州酒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优厚的酿酒自然环境,但偏偏也没有做大做强。
茅台和五粮液的对决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课题。
30年河东,30年河西用在茅台和五粮液之间是非常恰当的。
茅台和五粮液是中国众多白酒中的两个顶级品牌。
多年来,茅台和五粮液双峰对峙,冷战不断。
两个白酒的对决,也折射了贵州与其它省份的对照,在它们身上是开拓与保守两种思潮的体现。
可以说,茅台成名比五粮液早,品牌资源比五粮液厚,在人们心目中是响当当的国酒。
是身份与荣耀的象征。
今天,贵州茅台没有注意确立自己尊贵的形象,没有设法将目标顾客群扩大,大部分购买者都是当年茅台品牌的影响者。
时间流逝,年轻人还认得茅台吗?
到今天,很多人已经只知道五粮液而不知茅台为何物了,酒楼里消费的高档白酒也几乎都是五粮液。
茅台这个曾经的国酒在很多场合被五粮液所超越。
贵州酒除了“茅台”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领导者品牌。
就连第一个开创低度酒革命的“贵州醇”也未能在低度酒消费者市场占有领先位置。
营销观念落后、品牌意识不足、盲目跟随导致了至今仍然缺乏强势品牌群。
如果将“视觉”回放到80年代,“贵州酒”绝不是“茅台酒”的代名词,“习酒”、“鸭溪”、“董酒”、“贵州醇”、“平安酒”、“贵阳大麯”等在省外市场很具亲和力,谈到贵州必定会说“贵州出好酒”。
但时至今日,这些昔日的“贵州名酒”大多已经退回到大本营,省外市场再难觅踪影。
对比川酒雄起的局面,贵州的酒明显老态龙钟。
市场销售量逐渐下滑,品牌知名度、美誉度都在下降。
“贵州醇”、“鸭溪”、“董酒”、“习酒”、“青酒”等全国性品牌在不断老化。
放眼全国白酒市场,贵州酒品牌军唯一能够占据终端销售货架的,只剩下了“茅台酒”和带“茅台”徽记的“茅台集团军”,以及附有与“茅台”二字有着密切关系的“茅台镇”的酒。
贵州酒的优势已经只剩下“贵州茅台”最后一张牌。
就是这最后一张牌,贵州也没有打好。
不管是因“茅台镇”而成就了“国酒茅台”,还是因“国酒茅台”的扬名四海而闻名“茅台镇”,“茅台镇”三个字已经越来越成为省内外消费者认识和接受贵州酒的一个“符号”。
茅台镇的酒,品牌以“茅字当头”为然,或争先竟相一窝峰地“糊涂”,甚至于专做“擦边球”,缺乏像“小糊涂仙”、“小酒保”、“乡巴佬”、“醉知己”、“招财猫”等具有自主品牌专用权、自主包装特色或抢先市场占位的品牌。
透过贵州酒后起之秀“小糊涂仙”的成长,我们看到了“茅台镇”这张牌的能量,但可惜的是,这种能量却只能被外人发现,被外人利用。
刚到茅台镇来投资的“云峰酒业”一开始就只做“小糊涂仙”时,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做“傻事”,当时还流行做特制酒并能赚钱。
但当“小糊涂仙”的销售额从100万、500万----5000万上升到1亿以上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品牌有如此大的销售驱动力。
随之而来一场“造牌运动”在茅台镇乃至与整个白酒行业掀起,但品牌意识淡薄、品牌运作手段上的粗糙、市场行为上的畸形,至今没有几个象样品牌树立起来,更谈不上有信赖感、依赖感、忠诚感可言。
除掉“茅台镇”这最后一张牌,比起四川酒贵州缺乏更多像“小糊涂仙”、“金六福”、“小酒保”、“浏阳河”等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地域品牌。
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全兴大曲、沱牌和郎酒“六朵金花”,在国内白酒行业竞争的格局中,集团作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很强。
为此,业内有人称川酒为“江湖独大,酒业凫雄”。
在中国白酒行业的排名中,四家川酒企业的产量位列前十位,其中五粮液以15.4万吨的产量高居榜首,沱牌居次,剑南春居五,泸州老窖居十。
从销售额来看,2001年,五粮液以81.9亿元位居首席,泸州老窖位列第三,剑南春居五,全兴居六。
在“利税英雄榜”上,五粮液以28.1亿元仍居第一,第三为剑南春,第四为泸州老窖,第六为全兴,沱牌第十。
川酒占据的总体优势,持续给国内白酒业发展带来压力。
川酒发展壮大的历程,有许多启示可以供贵州白酒产业发展参考。
在全国历次名酒评选中,四川的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全兴大曲、沱牌曲酒和郎酒都顺利上榜,构成了川酒的“六朵金花”品牌,从群体规模上看,国内其他省市无人可比。
事实上,川酒“六朵金花”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除了白酒企业产品具有自身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