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部分.docx
《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部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部分.docx(2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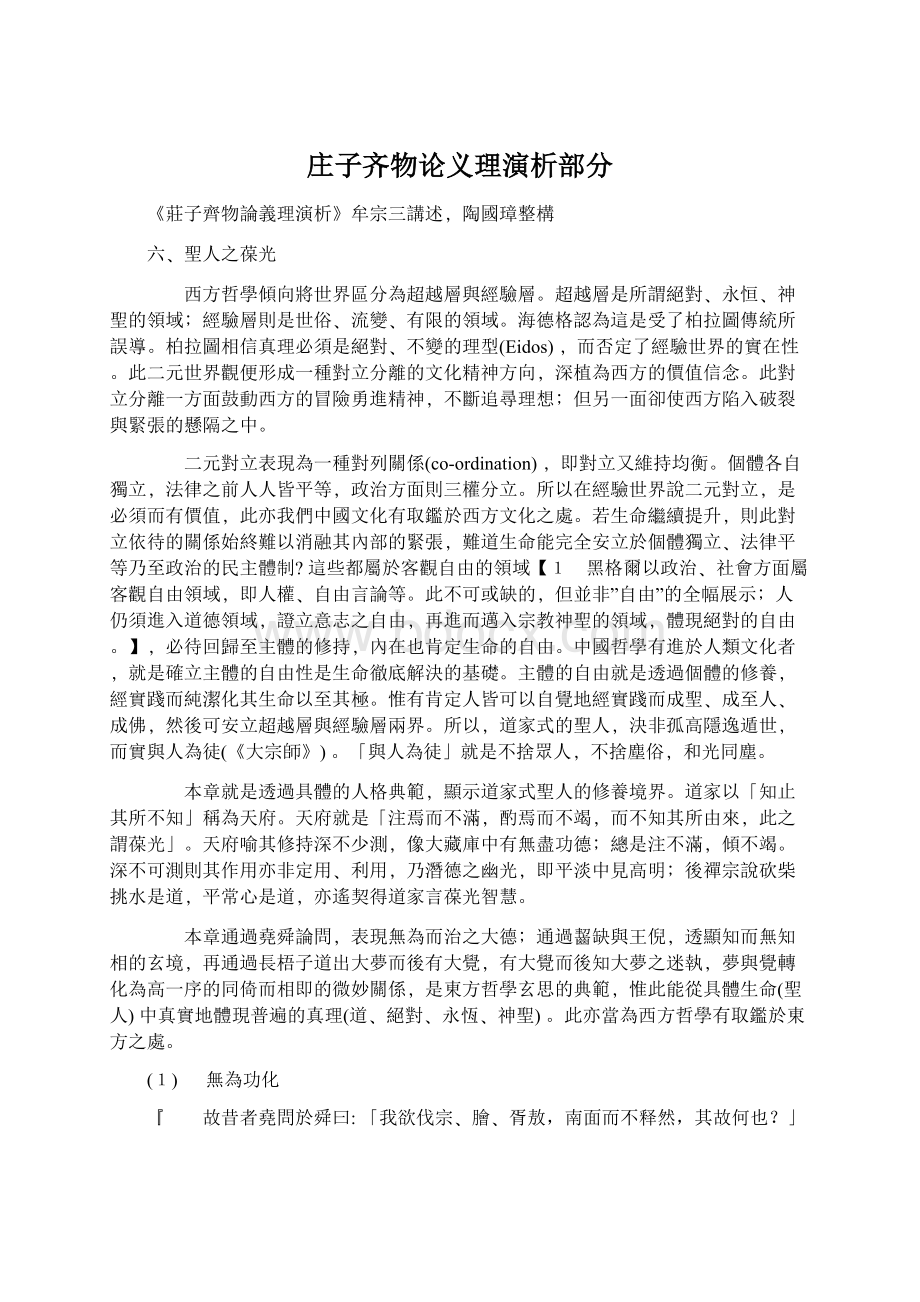
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部分
《莊子齊物論義理演析》牟宗三講述﹐陶國璋整構
六﹑聖人之葆光
西方哲學傾向將世界區分為超越層與經驗層。
超越層是所謂絕對﹑永恒﹑神聖的領域﹔經驗層則是世俗﹑流變﹑有限的領域。
海德格認為這是受了柏拉圖傳統所誤導。
柏拉圖相信真理必須是絕對﹑不變的理型(Eidos)﹐而否定了經驗世界的實在性。
此二元世界觀便形成一種對立分離的文化精神方向﹐深植為西方的價值信念。
此對立分離一方面鼓動西方的冒險勇進精神﹐不斷追尋理想﹔但另一面卻使西方陷入破裂與緊張的懸隔之中。
二元對立表現為一種對列關係(co-ordination)﹐即對立又維持均衡。
個體各自獨立﹐法律之前人人皆平等﹐政治方面則三權分立。
所以在經驗世界說二元對立﹐是必須而有價值﹐此亦我們中國文化有取鑑於西方文化之處。
若生命繼續提升﹐則此對立依待的關係始終難以消融其內部的緊張﹐難道生命能完全安立於個體獨立﹑法律平等乃至政治的民主體制?
這些都屬於客觀自由的領域【1 黑格爾以政治﹑社會方面屬客觀自由領域﹐即人權﹑自由言論等。
此不可或缺的﹐但並非”自由”的全幅展示﹔人仍須進入道德領域﹐證立意志之自由﹐再進而邁入宗教神聖的領域﹐體現絕對的自由。
】﹐必待回歸至主體的修持﹐內在也肯定生命的自由。
中國哲學有進於人類文化者﹐就是確立主體的自由性是生命徹底解決的基礎。
主體的自由就是透過個體的修養﹐經實踐而純潔化其生命以至其極。
惟有肯定人皆可以自覺地經實踐而成聖﹑成至人﹑成佛﹐然後可安立超越層與經驗層兩界。
所以﹐道家式的聖人﹐決非孤高隱逸遁世﹐而實與人為徒(《大宗師》)。
「與人為徒」就是不捨眾人﹐不捨塵俗﹐和光同塵。
本章就是透過具體的人格典範﹐顯示道家式聖人的修養境界。
道家以「知止其所不知」稱為天府。
天府就是「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天府喻其修持深不少測﹐像大藏庫中有無盡功德﹔總是注不滿﹐傾不竭。
深不可測則其作用亦非定用﹑利用﹐乃潛德之幽光﹐即平淡中見高明﹔後禪宗說砍柴挑水是道﹐平常心是道﹐亦遙契得道家言葆光智慧。
本章通過堯舜論問﹐表現無為而治之大德﹔通過齧缺與王倪﹐透顯知而無知相的玄境﹐再通過長梧子道出大夢而後有大覺﹐有大覺而後知大夢之迷執﹐夢與覺轉化為高一序的同倚而相即的微妙關係﹐是東方哲學玄思的典範﹐惟此能從具體生命(聖人)中真實地體現普遍的真理(道﹑絕對﹑永恆﹑神聖)。
此亦當為西方哲學有取鑑於東方之處。
(1) 無為功化
『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
「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
」
舜曰:
「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
若不释然,何哉?
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曰者乎!
」』
本段借堯舜的對話﹐喻示聖人無為而治的功化。
以前堯帝向舜提問:
「我想征代宗﹑膾﹑胥敖這三個小國﹐但每次臨朝卻心裏感到不安﹐是什麼原因呢?
」
舜回答說:
「這三個小國的國君﹐好像生存於蓬艾賤草之中﹐仍未開發。
為何你會感到內心不安呢?
以前﹐曾有十日並出﹐雖然普照萬物﹐但十日之光熱太過﹐以致焦禾稼﹐殺草木﹐封狶長 ﹐成為民害。
何況國君的聖德比曰照更強烈呢﹐當然無幽不燭﹐更使人民受害!
」
這段是借二聖的對話﹐顯示有為之害。
借託歷史故事﹐堯帝得位後﹐希望勵精圖治﹐使天下平定。
而宗﹑膾﹑胥敖三個小藩國曾拒貢賦﹐於是欲興征伐問罪。
但謀事未定﹐每臨朝不怡﹐遂求問於舜。
堯能求問於舜﹐示堯之真誠遜讓﹐無名位的矜持﹐故道家亦以之為聖王。
舜則代表道家所許的聖人﹐能體達無為而治的功化。
舜的回答﹐並不著重評議三國國君的是非對錯﹐而表示三國猶在自然效野之中﹐仍未有文明開發﹐故不懂禮節儀文﹐藩國雖小﹐但自安於天地之間﹐存養自足。
假若堯帝大興征伐之師﹐使他人服從天朝國威﹐反為所累。
於是﹐舜乃擧十日並出的故事﹐暗示德行恩被太過﹐亦為民害。
十日並出是神話故事﹐暗示德行恩被太過﹐亦為民害。
十日並出是神話故事﹐相傳堯帝初﹐天庭中的太陽不顧守則﹐十個太陽嬉戲無度﹐同時騰空。
以至曰光有盛﹐使土地焦裂﹐禾稼禽畜傷亡﹐萬民哀號。
後乃得后羿射下九日﹐天下始復安定。
舜借此故事表示﹐日光普照﹐固能仗萬物欣欣向榮﹐但日光過盛﹐則反為民累﹔由此暗示國君聖德﹐固恩澤萬民﹐若欲興干戈﹐伐令從己﹐則已生是非成見﹐自覺己是而他非﹐主觀自恃要天下服從己見。
一如十日登天﹐萬物普照﹐覆盆隱處﹐尚有暗處﹔而君主的權力﹐比十日更無所不至﹐無幽不燭﹐則其害更甚於十日。
故國君須警覺其有為造作﹐以免使人心民陷於水火。
舜基本上主張無為而治。
一日普照﹐是自然而然﹐是無心而育成萬物﹔反之﹐十日並出﹐即是滲入主觀成見﹐有為而治反使萬民受累﹐後世秦代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正是有為的異化。
故聖王必行無為而治﹐使萬民不礙其性﹐自生存養﹐大德之至。
牟先生在《中國哲學十九講》裡提到道家最反專制政治的。
因為專制政治的特質就是妄作有為﹐作之君﹐作之師﹐專門禁塞國民的個體性﹐成為一種封閉式的社會。
而近代的自由主義正符合道家的政治理想﹐把一切政治的操縱把持解開﹐盡量減少政治的權力﹐並且用社會上的人民來制衡﹐一切的活動作業﹐都是各社團自己在做﹐而政府只在一旁監督大家衝突過份的地方﹐調解持平。
道家深切感受到操縱把持的害處﹐主張不禁其性﹐不塞其源﹐政治上的教人讓開﹐使萬民自生﹑自長。
道家的智慧﹐表面只涉及個人的修持﹐以剝落待對比的對偶關係﹔實則此修持可以在個人生活上受用﹐更有經世致用的指導﹔真正懂得行事者﹐自然明白不居功﹐不求成﹐退讓一下﹐人與人間能各適其性﹐任運自然是更高境界的管理行政之道。
道家無為而治並非正面的政治主張﹐不能負起文化立國建設的重任﹐但其守柔之道﹐則是行事待人的智慧﹐識者當有體會。
(2) 知而無知相
『 齧缺問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
曰:
「吾惡乎知之!
」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
曰:
「吾惡乎知之!
」
「然則物無知邪?
」
曰:
「吾惡乎知之!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且吾嘗試問乎汝:
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處?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
齧缺曰:
「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
王倪曰:
「至人神矣!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及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
王倪亦聖人典範﹐以無知之知寄寓無相境界。
『 齧缺問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
曰:
「吾惡乎知之!
」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
曰:
「吾惡乎知之!
」
「然則物無知邪?
」
曰:
「吾惡乎知之!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
齧缺問王倪說:
「你知不知道事物世情的本源?
」王倪說:
「我哪裡知道?
」齧缺又問:
「你知不知道你的不知道呢?
」王倪說:
「我哪裡知道?
」齧缺又問:
「那麼你對一切事都無所知嗎?
」王倪說:
「我哪裡知道?
」
齧缺心目中認為宇宙萬物世情應有一本體式的本源﹐於是欲求證於王倪。
莊子再次借人物的修養層次﹐以顯大道之玄幽。
王倪答之「吾惡乎知之」﹐是表示此問是知識追逐﹐已是成心了別﹐終不得齊物之旨。
「吾惡乎知之」實暗示語﹑啟發語﹐順機而發﹐後來禪宗大概仿此﹐謂之機鋒。
其作用是中止此「發問--解答」的知識循環。
聽者若得解悟﹐自當反求諸己﹐撫心覕問其問題是否有謬錯。
但齧缺並不契機﹐遂有追問。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此問反映齧缺誤解了王倪的答語﹐以為王倪對世界有共同的本源有所不知﹐此實齧缺仍未脫離其實體化的想法﹐認為世間有一本體﹐乃以為王倪這位高人竟有所不知﹐遂有譏諷之意。
齧缺之問亦可理解為:
你既不知事物世情之本源﹐那麼你是否自知己之無知呢?
假若你能自知自己之無知﹐亦一種境界﹐不愧為世人頌稱高人。
但王倪再答以「吾惡乎知之」﹐則表示若知其不知﹐不知還是知﹐仍是成心起了別﹐故重複答之﹐以示他不願落入是非對比之中﹐亦不介意齧缺問中帶有譏諷之意。
此實道家至人無相境界的表現﹐忘機達道。
齧缺更不明王倪的心境﹐乃有輕視之意﹐遂問:
「然則物無知邪?
」難道你既自無知﹐萬物豈無知可言嗎?
齧缺既本乎常識的頭腦發問﹐將齊一觀誤解為萬物各有本體根源義﹐其想法是實在論頭腦﹐自然認為萬物各自有定相﹐乃各自有其知識可言﹐比如火是熱的﹐水是濕的﹐各物有各物的特性﹐此為客觀的事實﹐王倪怎可以否定世界的客觀性呢?
所以越發覺得王倪不合常理﹐此再問實有點不耐煩﹐責求王倪正面承認自己並非得道之士。
王倪再三答以「吾惡乎知之」。
從王倪的角度﹐知識內容只是識心之了別﹐並非真知。
故惟知止其所不知﹐能當下止住其驚騖之心﹐始是生命之真常。
知止則豈獨不知我﹐亦不知物之同是同非。
唯物與我﹐內外相忘﹐以不知知。
不過王倪亦考慮到對方不能順機而應﹐故純答以不知﹐已不能啟悟問者﹐遂補充以下一段話﹐以芒忽的詭辭方式說之: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
雖然如此﹐姑且讓我為你說明之。
怎麼知道我所說的「知」其實卻是無知愚昧呢?
怎麼知道我說的「不知」其實卻是真實智慧呢?
王倪背後的意思是:
知物之所同只不過是成心的虛妄分別﹐有同則有異﹐終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故雖有知實已自陷於知識追逐﹐失其心靈本位﹐是為不自覺的迷執﹐為芒昧無知。
反之﹐自覺自己不應該追逐知識了別﹐復歸於無知。
復歸於無知是去掉成心之執的無相境界﹐洞悉大化之機﹐是以為睿智之知﹐知而無知相。
所以王倪不斷答以「惡乎知之」﹐即以否定方式保存其心靈渾一整存﹐無所分化﹔同時亦希望齧缺有所契悟。
但齧缺始終不悟﹐遂分解說之:
「且吾嘗試問乎汝:
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處?
!
」
王倪首先從經驗事例﹐舉例說明是非對比﹐僅是認知分解所牽引﹐是非得失實皆無自性可執持。
王倪說:
「我姑且反問你:
人若睡在潮濕的地方﹐就要患上腰痛風濕或者半不遂﹐泥鰍卻悠然安樂﹐為何如此呢?
人若爬上高樹就會驚懼不安﹐但猿猴卻悠然安樂﹐為何如此呢?
這三種生物生性不同﹐合宜各異﹐那裡有客觀的標準呢?
」王倪續說: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
再從口味對比之﹐人類喜嗜牛羊的家畜﹐麋與鹿則喜食長薦茂草﹐蜈蚣喜歡吃小蛇﹐貓頭鷹和烏黑喜歡吃老鼠。
哪種食物才是最佳味道呢?
四種生物各有飲食喜好﹐肉食或素食﹐各有不同。
若不同者而否定之﹐則不明物性自然﹐各好其好。
此處實對比出齧缺先前問「物之所同是」﹔若以知識言之﹐此「所同是」不亦與常識相衝突?
由此暗喻知識領域﹐一切皆相因對比而牽連﹐並無必然性。
「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
王倪續以生物的性向對比之。
猵狙欲求雌猿作配侶﹐麋欲求鹿交合﹐泥鰍則與魚相交游。
毛嬙和麗姬是世人認為最美的﹐但魚見了她們卻逃入深山﹐鳥見了就要高飛﹐麋鹿見了就要急速奔跑。
這四類動物﹐性好各異﹐究竟哪種性向或美色才是最高的標準呢?
王倪借用經驗事例﹐表示物各有物性﹐隨其特性﹐乃各有所好。
好是價值判斷﹐是以經驗世間中並無絕對的價值標準﹐價值取向只是隨緣而起。
所謂緣起﹐是指事物之如此存在﹐並非有一客觀定然的本質﹐而是由許多條件和合而成﹐是以事物之如此表現﹐乃偶然的﹐沒有必然性的。
比如人之居平地﹐猨猴居高樹﹐魚居水中﹐乃生物隨其生物特性而適應其環境﹐是適者生存的條件。
又問何以人會居平地﹐則又可答之人類群居﹐守望相助﹐故可在平地獵食云云﹔又或問猨猴何以居樹﹐則可答之猨猴手長宜在樹上間攀躣﹔而高樹可避猛獸襲擊云云。
此中的處境﹐各隨其緣起關係而暫時交織而成。
而一旦和合交織而成某某物性﹐則自然有其性向要求:
人願居平地而不願居高樹﹔若反其物性﹐則有不適﹐進而生厭惡之情﹔同理﹐若客觀條件順適其物性﹐則生舒服享受之感﹐進而生喜悅之情。
王倪著重回應齧缺問「物之所同是」。
若物是經驗對象﹐則各有物性﹐各有所好﹐不能有所謂絕對的共同標準。
由此﹐再暗示齧缺此問﹐已經是成心了別﹐將事物從自我的角度看待之﹐成一主觀的投射。
假若要真正明白萬物之所同﹐必待化掉成心之了別﹐復歸於無分別的道智﹔則萬物畢同﹐無有分殊也。
莊子以王倪已達聖人境界﹐故明乎萬物畢同畢異這兩重存有論﹔要達萬物畢同之境﹐終須涉及工夫修持﹐非可從客觀知識方面判別之。
於是王倪乃總結: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
依我看來﹐世間對仁義的端緒﹐是非的判別﹐都是從彼我而互觀之﹐損益不同﹐或於我為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是故價值標準是紛然交錯﹐若殽饌之雜亂﹐既無定常﹐我哪裡知道分別它們的定準呢?
王倪表示俗情世間的道德標準﹑是非得失皆緣起對比﹐是無絕對性。
若執持某某為價值定準﹐此即「眾人辯之以相示」﹐終成偏執而有所不見。
至於王倪答以「吾惡乎知之」﹐實「聖人懷之」之意﹐故辯中有不辯﹔不知即是自知﹐自知即是真知﹐是知而無知相之知。
「齧缺曰:
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
齧缺的實在論頭腦仍未領悟王倪的比喻﹐遂有求問。
其求問的態度實帶譏諷﹐此為矜持作崇﹐始終不願承認王倪修持高於自己。
是以反問王倪雖然不明事物間有利害得失的差別﹐難道至人亦不懂得趨吉避凶嗎?
此問暗示你若是至人﹐應知利害﹔但你竟不知利害﹐難稱至人了﹐運用了歸謬反諷。
「
王倪曰:
至人神矣!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及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
此段於後世每多誤解﹐其中道教中人崇奉神通怪異﹐乃徵引此段引證道家之至人﹐有大能神通﹐入火不熱﹐寒冰不侵﹐以示至人的高明。
道教始終未達道家的精神境界﹐遂將此段的內容實化﹐以為追求升仙入道的神幻想像﹐實則我們稍看《逍遙遊》未段﹐莊子以列子雖能御風而行﹐汵然善也﹐但猶有所待﹐非真逍遙也。
故此莊子並不以神通方術為得道的徵符﹔得道之旨﹐乃在於主體復其本位﹐渾然與道同體﹐渾然與道同體是精神修養境界。
所以我們應從兩重存有論的角度看待此段描述。
首先﹐在成心了別的層次﹐一切依彼是的對偶關係而分立﹐遂有是非得失的差別。
於是生命於生死中流轉﹐於不同的處境﹐仍患得患失﹐有生死榮辱之牽連。
是以蹈火則懼焚﹐涉水則懼溺﹐履冰則懼寒。
此為現實生命的限制﹐故有礙焉。
道家則主張至人的修持﹐能破除成心負累﹐物物而不物於物﹐是則在主觀的心境下﹐一切皆在道心之觀照中﹐去礙無執﹐則渾忘外在得失榮辱的對比﹐一切皆渾化在道術之中。
在去礙之下﹐一切現象的浮動相皆止息矣。
浮動息﹐則依待之限制網破裂矣﹐全幅世界只呈現為大美﹑至樂。
《天下》篇謂「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即此觀照下的藝術境界。
如此﹐至人能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所以此段形容至人﹐「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及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乃大想像的類比﹐作用是以荒唐之言﹐以烘至人之無待。
無待則當體具足﹐一切放平﹐是以不能將此段內容實化﹐否則徒加嬌扭。
是以至人「乘雲氣﹐騎曰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亦意趣的表達﹐憑空說起﹐似天外飛起﹐發揮其最大的想像。
莊子《天下》篇自況: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并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
忽乎何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
時恣縱而儻,不觭見之也。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諔詭可觀。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
其于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雖然,其應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
此中是莊子內心的寄言。
文句比較複雜﹐大意是莊子心境嚮往的是「獨然與天地精神往來」﹐但又「不敖倪于萬物﹐以與世俗處」。
「獨然與天地精神往來」是出世間﹐而「與世俗處」則是入世間。
惟有入世與出世渾融如一﹐始有悲天憫人的感懷﹐願以其文字普渡眾生﹐不落入功名得失之間﹔惟此而能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如是﹐我們得知莊子言及「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是運用比喻將無分別說的境界具象形容出來。
至人不懼大澤焚﹑河漢沍﹐只是烘托無待逍遙﹐非通方術也。
全段實以王倪為聖人典範。
王倪答以「吾惡乎知之」﹐即聖人修持內歛的表現。
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猶有所說﹐故王弼謂之「有者」也﹔莊子比較顯豁而透脫﹐更隱而不發﹐道既不可道﹐故不說也。
不說之說﹐無知之知﹐則無迹相可執﹐是道境的呈現。
所以後段的詮釋﹐只是嘗試言之﹐乃論而議。
故末段乃以大想象之形容﹐擴展齧缺的心懷﹐接應其機。
(3) 大夢而後大覺
『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
「吾聞諸夫子:
“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
」
長梧子曰:
「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且女亦大早
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
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
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后悔其泣也。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也。
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
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
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
萬世之后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
聖人葆光﹐具體而微。
舜以無為顯示道家的應世哲學﹐王倪以無知之知寄意無相境界﹐長梧子則以大夢﹑大覺表現真理的雙重性格﹐迷悟與覺悟是不即不離。
此段落呼應第二章〈存在的感應〉。
〈存在的感應〉中﹐慨嘆生命的芒昧相﹐它總是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之能止﹔所以人之生也﹐即不自覺坎陷於虛夢之中。
至此﹐莊子卻以大夢然後有大覺﹐重新肯定生命﹐必須下凡歷刧﹐經歷坎陷的途程﹐始能達至真正的覺悟。
於是就夢與覺﹑迷與執再作高一序的演辯﹐玄理精微﹐教人嘆為觀止。
『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
「吾聞諸夫子:
“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
」
長梧子曰:
「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且女亦大早
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
長梧子與瞿鵲子是虛擬的人物﹐可能是師徒關係﹐此乃寓言寄意。
瞿鵲子如是問長梧子說:
「我曾聽孔子批評過這樣一種說法:
聖人不去積極從事世務﹐不貪利益﹐不刻意去趨利避害﹐營求攀緣﹐不刻意去說什麼﹐也不刻意不說什麼﹐以此而周遊列國﹐然卻一無掛礙。
孔子說這種境界太粗略流蕩了而不合於。
但我卻以為是妙道的境界﹐老師以為如何呢?
」
瞿鵲子不贊成孔子對道家聖人的批評﹐故認為孔子仍未達道﹐並自許為道家正宗﹐遂求證於長梧子。
此節是意譯﹐以便疏通以下的思路。
瞿鵲子此問﹐是想表示已經領悟老師的教誨﹐沾沾自喜﹐並以孔子為對比﹐自覺所理解較其高明。
長梧子自然了解此弟子心態﹐遂對機啟示其自矜之心。
長梧子說:
「以上的聖人境界﹐即使黃帝聽了都會迷惑困解﹐何況孔丘道行尚淺﹐如何得悟呢!
不過﹐你亦不可沾沾自喜﹐自以為完全明白那番道理。
你現在好像見到一攻雞蛋﹐就立即投想到﹐此蛋孵化成雞﹐求得公雞報時的功效﹔或好像見到一顆彈丸﹐立即就投想得到一隻燒熟了的鴞雀﹐以為可以飽餐﹔其實你們都是玩弄光景﹐好高鶩遠。
」
『 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
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
長梧子繼續對瞿鵲子說:
「我姑且為你說說﹐你亦姑且聽聽好嗎?
你不要憑空想像﹐將聖人所修持的境界﹐視作與日月同光﹐懷抱著整個宇宙﹐而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
其實﹐聖人所能做到的無非是無所計較﹐超越是非的紛亂而不顧﹐於是內心平平蕩蕩﹐而無貴賤厚薄尊卑之分。
世俗的人勞勞役役﹐各自競爭表現自己的聰明才智﹔而聖人卻保存其含蓄沉潛的葆光﹐外表愚昧魯鈍﹐故其生命能純然直往﹐保持精純無雜而與永恒渾然摻糅為一﹐無所分別。
此時﹐萬物皆純一無雜﹐而得以互相平齊蘊含渾樸之大化中。
」
「旁日月﹐挾宇宙」是文采的大浪漫﹐並無實指意含。
其作用是以大浪漫的想像﹐經圖象化的開決﹐使聽者放下質實的思維﹐放下種種不平的計較﹐此之謂「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聖人不著重誇張的神通大能﹐此仍屬量上的偉大相﹔真正的達道之士﹐就即一切而放平一切﹐不高亢﹐俯就萬物而與民同憂同樂。
故莊子突顯此平凡中見高明的大平等精神﹐《齊物論》至此亦由芒忽而歸於平淡。
惟真正的平淡﹐始能消融西方式的浮士德精神﹔真理並不在向上求超越﹔反之﹐即當下而邁入永恆。
故「參萬歲而一成純」是齊物所達至的道境。
聖人在古往今來的無數變化中﹐獨然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此非天機自張乎!
此中的「參萬歲而一成純」的意境﹐深遠優美。
聖人非一光板般的靜穆境界﹐其生命必注入具體的歷史﹐摻糅變化﹐與人為徒。
此聖人境界在萬象變化﹐始終保存其渾一的葆光﹐故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一方面不離塵俗﹐但又不為塵俗所累﹐是為既超越而內在。
此種既超越而內在的境界是中國哲學最深微的形上智慧。
具體言之﹐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這些哲人﹐並非如西方式的哲學家﹐以純思為職能﹔他人都對現實人生有所悲惻感懷﹐此即存在主義所謂存在的呼應﹔惟此悲感始使他們對世間有所不安﹐有所不忍﹐而求解決眾生的痛苦。
比如就孟子肯言仁義之本﹐根源於人性之中﹐盡其心者知其性。
再由此盡心知性的工夫實踐﹐體現天道﹔於是生命得以由世俗中超拔出來﹐上遂於永恆的天道世界﹐此即內在又超越。
道家老莊﹐進路或有所不同﹐則求去掉俗世中的牽連偏執﹐使生命回歸於其自己﹔所以在去掉俗世的歷程中﹐體驗生命的內涵。
即是說﹐此生命之自己﹐是歷盡俗世的歷程中﹐體驗生命的內涵。
即是說﹐此生命之自己﹐是歷盡俗世一切煩惱﹐得以參破其彼是對偶的根源﹐而回環地歸向其自己﹔所以生命的途程一面是坎陷﹐另一方面正是即於此坎陷而提撕上遂﹔最終是上遂於道的境界。
此乃從具體中見普通﹐由內在而證超越。
是以聖人最後所體現之道﹐實為由內在的主觀修持﹐涉歷客觀萬化流變﹐而經辯證的途程﹐消融綜合至絕對的大道。
生命處於葆光之中﹐始終仰望著神聖永恒的世界﹐雖涉歷萬化遷流﹐而無所迷執陷溺﹐得保存生命純一不雜。
參萬歲一成純﹐即是從具體的歷史變化中﹐體現永恆﹔生命與道純一無隔﹐是以萬物於此超越而內在的道心觀照下﹐平平蕩蕩﹐互相蘊合於精純渾樸的大化之中。
至此「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乃得真實體現﹐而非一思辨的空構想。
對比之下﹐西方的形上學偏向超絕型態﹐是因為不能體會此種即生命具體而普遍真理的洞見﹐遂將變化與永恒對立起來﹐變成形下形上的兩重世界﹐即使經哲學家以精深的思辨建構﹐終是緣木求魚﹐徒勞無功﹐原因在於西方形上學始終隱藏著一種二元對立的緊張關係。
莊子借聖人境界之形容﹐提示聖人的修持﹐不牽連於俗務名利得失﹐此為聖人超越一面﹔而此超越一面乃經工夫磨練﹐從具體生活中﹐一一面對成心之顛倒偏執﹐勉力而攝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