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三辑.docx
《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三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三辑.docx(3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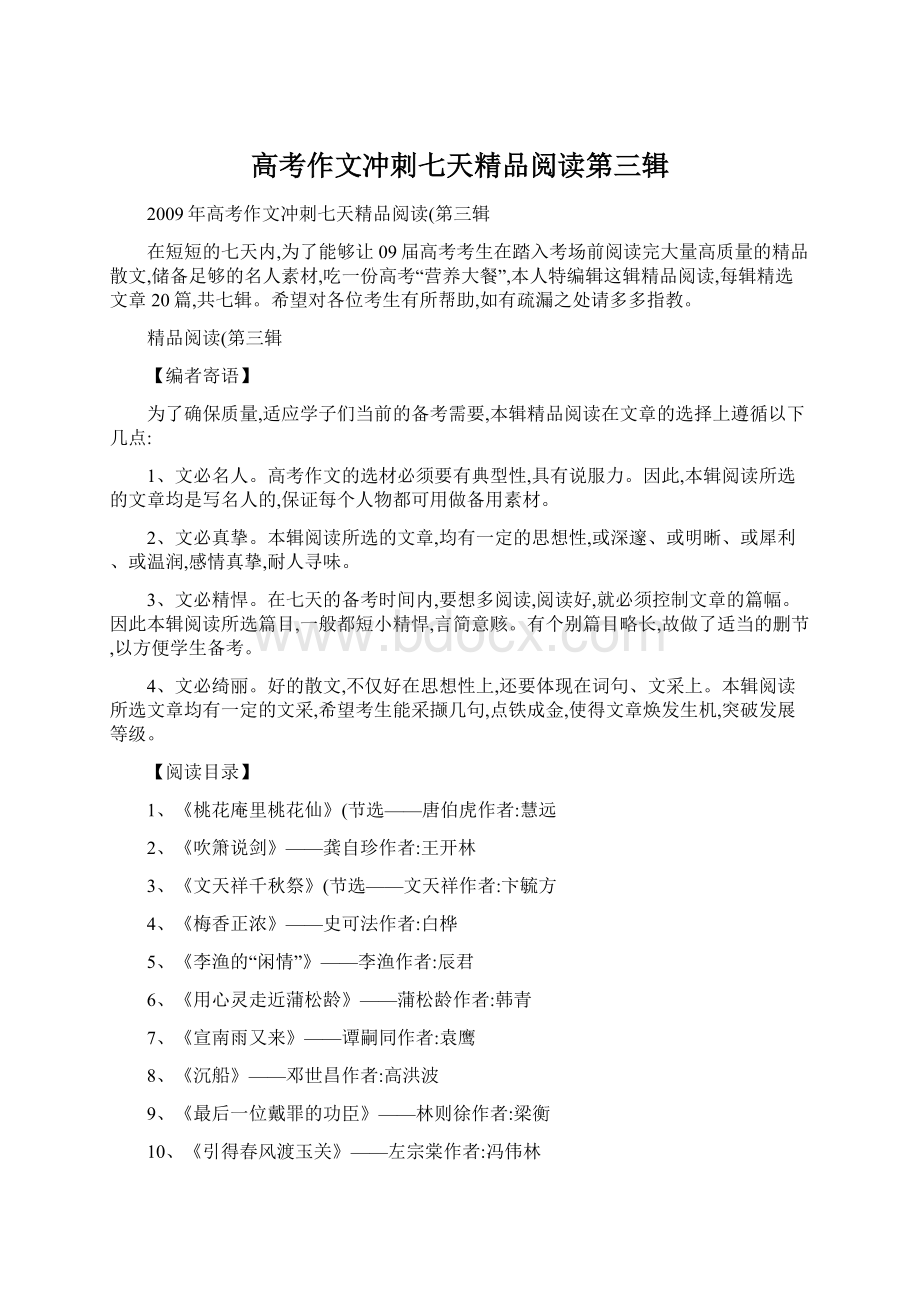
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三辑
2009年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三辑
在短短的七天内,为了能够让09届高考考生在踏入考场前阅读完大量高质量的精品散文,储备足够的名人素材,吃一份高考“营养大餐”,本人特编辑这辑精品阅读,每辑精选文章20篇,共七辑。
希望对各位考生有所帮助,如有疏漏之处请多多指教。
精品阅读(第三辑
【编者寄语】
为了确保质量,适应学子们当前的备考需要,本辑精品阅读在文章的选择上遵循以下几点:
1、文必名人。
高考作文的选材必须要有典型性,具有说服力。
因此,本辑阅读所选的文章均是写名人的,保证每个人物都可用做备用素材。
2、文必真挚。
本辑阅读所选的文章,均有一定的思想性,或深邃、或明晰、或犀利、或温润,感情真挚,耐人寻味。
3、文必精悍。
在七天的备考时间内,要想多阅读,阅读好,就必须控制文章的篇幅。
因此本辑阅读所选篇目,一般都短小精悍,言简意赅。
有个别篇目略长,故做了适当的删节,以方便学生备考。
4、文必绮丽。
好的散文,不仅好在思想性上,还要体现在词句、文采上。
本辑阅读所选文章均有一定的文采,希望考生能采撷几句,点铁成金,使得文章焕发生机,突破发展等级。
【阅读目录】
1、《桃花庵里桃花仙》(节选——唐伯虎作者:
慧远
2、《吹箫说剑》——龚自珍作者:
王开林
3、《文天祥千秋祭》(节选——文天祥作者:
卞毓方
4、《梅香正浓》——史可法作者:
白桦
5、《李渔的“闲情”》——李渔作者:
辰君
6、《用心灵走近蒲松龄》——蒲松龄作者:
韩青
7、《宣南雨又来》——谭嗣同作者:
袁鹰
8、《沉船》——邓世昌作者:
高洪波
9、《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林则徐作者:
梁衡
10、《引得春风渡玉关》——左宗棠作者:
冯伟林
11、《伟大的二重性格》——鲁迅作者:
孔庆东
12、《一代儒僧李叔同》(节选——李叔同作者:
来新夏
13、《林语堂的生活艺术》——林语堂作者:
竺晓
14、《觅渡,觅渡,渡何处?
》——瞿秋白作者:
梁衡
15、《天才徐志摩》——徐志摩作者:
余杰
16、《老舍之舍》——老舍作者:
刘美芹
17、《狷者朱自清》——朱自清作者:
叶兆言
18、《上善若水》(节选——沈从文作者:
谢伦
19、《我读汪曾祺》——汪曾祺作者:
陈喜儒
20、《北岛:
在语言中漂流》——北岛作者:
刘鹏凯
桃花庵里桃花仙(节选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
慧远
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
且不说关于他的各种野史逸闻滥觞于民间,旧时的一部《四杰传》以及评弹《三笑姻缘》亦可谓深入人心,遍传于大江南北之街头巷尾与茶楼酒肆。
再加上近世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唐伯虎的形象带有了浓重的世俗文化意蕴,他本人也日益被打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
唐伯虎的形象向以风流倜傥和潇洒不羁为其标准的民间定式,各种版本的唐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现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游戏人间的才子本色,无论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还是当代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其间一脉相传的无不是唐才子对传统道德的藐视和对世俗规范的颠覆,他的所作所为既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风流韵事却又为一般大众所艳羡和津津乐道,其微妙之处的确耐人寻味。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唐伯虎,其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呢?
我们先来翻阅一下《明史》。
这部由清代官方所修的卷帙浩繁的正史,留给唐伯虎的不过只有区区二百多字而已。
在五十多人的文士合传中,唐伯虎名列倒数第十六,其志传的内容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
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
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
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
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
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童,得试题。
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
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
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
宸濠不能堪,放还。
筑室桃花坞,与客日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
”另外,一些地方志诸如《江南通志》、《苏州府志》和《吴县志》等,对唐伯虎的记载也基本如此,其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
由此可见,唐伯虎除了的确以才华名动一时之外,其个人经历与宗法社会中所有的落拓士人一样,也并无多少特殊之处,至少,这个唐伯虎与民间传说中的那个风流才子形象相距甚远,两者之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唐伯虎生活的年代正值明代承平日久的中后期,正德年间也曾经被许多古今学者视之为明代社会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转捩点。
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时代,从皇帝到平民都充满了一种玩世不恭的精神,正像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那样,十四岁即位的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像力。
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
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
的确,正德皇帝虽然算不上是称职的皇帝,倒不失是一位性情中人,而且,他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均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就使得商业行为与意识悄悄地越过了政治所能容许的范围而自行发展,都市时尚与各种奢华的交易也开始萌芽,明代初期的那种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体系则逐渐瓦解。
虽然这些未必出自正德皇帝的本意,但其结果却是无可避免地打破了农耕社会原有和谐的阶级关系——既然连皇帝都在向往自由,士人自然更是上行下效、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直接促成了一种新的士绅文化品格的形成。
唐伯虎生活的苏州自古就是曹雪芹所说的“最后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苏州更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真个是“说不尽富丽乾坤,话不完繁华景象”(《四杰传》。
这就为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文化的多元自然少不了狂士的点缀。
苏州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英才辈出、群星璀璨,亦显然是得益于商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包括唐伯虎在内,祝枝山、文征明、张灵等人俱为苏州当地一时的才俊。
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可以说印象中江南风物的钟灵毓秀与天宝物华,是与这些才子们紧密相连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成为江南人文地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商业文化的繁荣虽然带来了明代士风的转变,却也使得身处红尘世界中的士人们
陷入了精神上的躁动以及满足欲望与保持道德之间日益紧张的两难选择之中:
一方面他们要面对物质享乐的诱惑,另一方面则要面对世道沦落所带给自己的忧患意识。
他们既是商业文化的得益者,却又对商业文化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朴素的生活和对“学而优则仕”按部就班的追求方式,正是商业文化的繁荣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屏障,让他们一时之间即变得失魂落魄、手足无措起来。
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中,唐伯虎伊始就对科举抱有一种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从情感上难以接受,理智上却又不得不去俯就绳墨,虽然科举制度与他的思想个性格格不入,但又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供选择;虽然他早年即以“才子”名世,但“才子”这个称谓只是一种民间荣誉,既不能拿来当作吃饭穿衣的本钱,也不能给个人前途带来任何的实惠。
除了继续走“学而优则仕”这条老路以开辟自己的美好前程之外,唐伯虎根本就别无选择。
不过,仕途这条路也不是谁想走都能够轻易走得通的,论才华,唐伯虎固然是才华超绝,足以恃才傲物,但仅有才华却是远远不够的。
在传统社会中,仕途就是官场,而官场又是什么呢?
官场的规则与性情中人的生活原本就截然不同,入官场首先需要练就一身趋炎附势的软硬功夫,同时还必须深谙厚黑之术,只有那些老于世故、虚与委蛇之辈才有可能在其中如鱼得水——这是由宗法社会官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那些才气纵横、锋芒毕露的才子们不但会弄得大家都没有饭吃,而且,由于他们的才气和自信,也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遭到体制的排挤。
所以文人在世俗社会中大抵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事功,那就只有隐藏起自己的本来面目,夹起尾巴去等待时机;或者自娱,满足于个人心性,那就干脆放浪形骸、笑傲江湖。
这两者之间形同水火,根本就是难以折中的。
然而不幸的是,唐伯虎身上既具有才子百无禁忌的傲气,又有着孩子般的单纯与不谙世事。
所谓“性格就是命运”。
唐伯虎虽然和天下所有的士人一样,想依靠科举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但即使没有科场舞弊案的发生,他也未必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地走下去。
对此,经过一番磨砺之后的唐伯虎才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他曾在《与文征明书》中不无悲愤地作了如下反省:
“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
从容晏笑,已在虎口。
庭无芜桑,贝锦百匹,谗舌万丈,飞章交加。
至于一辈子震赫,如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
……海内因以寅为不齿之士,仍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
唐伯虎的诗词向以“语殊俚浅”名世。
他认为创作就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声言“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
”这种论点在以“前七子”为首的“复古派”把持文坛的当时,无疑具有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俚俗入诗对唐伯虎在民间的文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他的这种创作态度对晚明文坛影响甚巨,非但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深受启发,我们甚至在清初“性灵派”文人的创作中也仍然能够看出唐伯虎的流风余韵。
唐伯虎经常在自己的诗文中以李白自比,民间也曾传说他与祝枝山、张灵在雨雪天扮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则沽酒去寺中痛饮,并大呼“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
”这一方面可见其放浪形骸、荒诞不经之一端,另一方面亦可见他们对李白诗境的刻意追求。
但是,与李白相比,唐伯虎的诗文无论在格局上还是气魄上都明显小了许多。
这当然怪不得唐伯虎,因为明代社会的逼仄与大唐气象从来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古代士人似乎总会对时间与生死之类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唐伯虎的诗文既然是为了“以口传心”,我们在其中读到的除了他对个人身世的感叹之外,还有一种徘徊于大地的大感伤与大悲悯,即使是在唐伯虎的那些描述寻欢作乐的诗文中,也仍然蕴含着一丝对于时光流逝的永恒恐惧。
比如唐伯虎的那首广为人知的《桃花庵歌》,他虽然在诗中以“桃花庵里桃花仙”自命,表现出一副安贫乐道的旷达胸怀和一种诗酒逍遥的人生境界,但他最终还是将时间看做了衡量人类一切希望和欲望的尺度,其结局也仍然不免要归结到虚无,归结到一个不可抗拒的人生宿命。
另外,像《一世歌》、《感怀》、《叹世》、《怅怅词》等作品,也大致表现了同样的创作意象。
应该说唐伯虎民间形象的形成,的确是与他创作的通俗易懂分不开的。
而他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则与徐渭、袁宏道、沈季、尤侗等人的大力彰显不无关系。
所以,后人一般都把唐伯虎归之于
晚明人物,因为真正开启晚明一缕文脉的,从理论上讲自然属王阳明最有建树,但如果从精神人格与身体力行方面来说,却是唐伯虎的影响更大一些。
吹箫说剑
王开林
龚自珍(定庵以其卓然不俗之姿进入我的视野,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那时,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入了他的《病梅馆记》。
老实说,我背熟了这篇文章,心头便斧刻下一痕磨灭不去的印象:
江、浙两地的文人墨客爱梅成癖,乖悖自然精神,“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颇有点像是薜萝村中的东邻女儿,竟以西施捧心为美。
要使病态美的效果臻于极致,他们多有绝招——“斫直、删密、锄正”,扭曲梅的天性,不惜夭阏其生机。
于是乎,龚自珍感叹道:
“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作者同情病梅,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同情封建时代的士子,从小到大,个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还被礼教牢牢地束缚,时时处处低眉垂首,察言观色,活得极不自然,而且缺乏应有的趣。
其后,高中课本续选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仍是与《病梅馆记》同一路数的作品,进步也显而易见,由同情病梅转为呼唤强者。
单从这一文一诗,我还不清楚他身上究竟有几分狂狷豪侠的成色,也不明白他为何能高蹈狂舞二十余年,被誉为“文坛之飞将”。
怪只怪我接触《龚定庵全集类编》较晚,对他的作品和身世所知寥寥。
想起来真好笑,在我心目中,长时期,他只不过是清代的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诗文家”,属于《小说面面观》(英国小说家弗斯特著里所讲的那种“扁平的人物”类型,缺乏立体感和纵深感,一团影像,十分模糊。
定庵出生在杭州的诗礼簪缨之家,母亲段驯是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的女儿,同样善于“以字解经,以经解字”。
这样的家学渊源,不用讲,龚自珍受惠良多。
他髫龄早慧,十五岁分韵作诗,十九岁倚声填词,二十三岁作《明良论》四篇,送给外公段玉裁斧正,得到很高的评价,其语为:
“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
《定庵先生年谱》大体是粗线条的,细节不多。
我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
龚自珍孩提时,只要过了正午,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及至长大了,仍旧如此,可谓应验如神。
谁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可是龚自珍的诗词中总是充满了剑气和箫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之一,“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两样销魂味”(《湘月》,“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之一,难怪他一生多病多灾。
定庵常说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听不得箫声?
真是咄咄怪事。
在科举考场上,大才子蹭蹬者多,顺遂者少,定庵也不例外。
直到三十八岁那年,他才勉强通过春闱,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进士,这个成绩够悬的,离落第并不太远。
清代的殿试以书法为重,龚自珍的毛笔字马马虎虎,就为这一条,他便跻入不了鼎甲、二甲之列,点不了翰林。
龚自珍的官运也平淡无奇,四十六岁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便封了顶,再也没有升迁的迹象。
有一回,定庵去拜访身为部长高官(礼部尚书的叔叔,刚落座,叔侄尚未寒暄数语,阍者就报告说,有位小门生到府中求见。
来人新近入了翰林,正春风得意着呢。
龚自珍只好暂去耳房回避,外间的谈话听得倒也一清二楚。
尚书问门生最近都忙些什么,那人回答,也没啥要紧的事情,平日只是临摹字帖。
尚书夸道:
“这就对啦,无论大考小考,首要的是字体端庄,墨迹浓厚,点画工稳。
若是书法一流,博得功名直如探囊取物!
”那位门生正唯唯诺诺地恭听教诲,定庵忍不住在隔壁鼓掌哂笑道:
“翰林学问,原来如此!
”这话直弄得那位门生大窘,慌忙告辞,尚书则大怒,将龚自珍狠狠地呵斥了一番,叔侄间竟为此断绝了长年的亲密来往。
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也很可能认为它格外的甜。
定庵未入翰苑,受到的刺激还真不小呢,后来,他干脆让女儿、媳妇、小妾、宠婢都日日临池,而且专练馆
阁体。
平常,若有人说到翰林如何如何,他就会嗤之以鼻地挖苦道:
“如今的翰林,还值得一提吗?
我家的女流之辈,没有一人不可入翰林,不讲别的,单凭她们那手馆阁体的毛笔字,就绝对够格了!
”瞧,他这讽刺牢骚的话说得多滑稽。
你称这是狂吧,他也真狂得妙趣横生。
大凡性情中人,喜欢讲怪话,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动辄触犯时忌,在官场里就休想混出多大的名堂。
定庵作过一副对联:
“智周天下而无所思,言满国中而未尝议。
”这种证悟法华三昧的话,说说而已,他如何能臻达化境?
定庵只好认命,做个诗酒风流的名士,感觉也不错嘛,至少比那些削尖脑袋苦苦钻营的家伙活得更潇洒快意。
放浪形骸之外的人,身上总难免会有长年改不掉的毛病。
定庵平日身上不可有钱,有钱即随手化尽,花酒也没少吃,樗蒲之戏(赌博也没少玩,而且场场必输。
所幸他诗名大,崇拜者不乏其人,借钱给他,似乎还嫌不够客气和义气,有人干脆送钱给他,索性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这位名士的快乐之上。
定庵嗜赌,多半花别人的钱,得自家的快活,如果真要他破财,他一早就倾家荡产了。
令定庵最沉迷的赌戏是摇摊(即压宝,他经常吹牛说他能用数学公式解出大小输赢的概率,分毫不差。
令人咋舌的是,他的“研究工作”竟做到了卧室里,帐顶画满一大堆数字,没事时,他就躺在床上,抬头琢磨那些数字的排列组合,从中探寻消长盈虚的信息。
定庵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的赌术天下独步,了解他的人则清楚,其所谓独步天下的赌术,只不过是赵括那样的纸上谈兵,全无实际效果。
有一回,扬州某盐商家大排宴席,名流巨贾齐聚,酒过三巡,照例要开赌局。
有位喜欢附庸风雅的王姓客人,是定庵的崇拜者,那天晚到,看见龚大诗人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云,似有萧然出尘之想,便凑到跟前来搭讪:
“您不喜欢热闹吧?
独自游园,可真是雅人深致啊!
”
定庵却笑道:
“陶靖节(渊明种菊看山,哪里是他的本意,只不过无可奈何,才纵情山水之间,以寄托满怀忧郁。
所以他的诗文越是旷达,就越是表明他不能忘怀世事。
我拂水弄花,也是这种境况而已,没什么特别。
”稍停,他又说:
“今天的赌局,我早看得雪样分明,只因阮囊羞涩,才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可惜世间没有豪杰之士,肯借赌本给我去大博一场!
”王君正愁没有进一步攀结定庵的契机,听他这样海侃神吹,还能不倾囊相助?
两人联袂入局,赌小赌大,呼卢呼雉,转眼间,就连输五把,一千两银票顿时化为乌有。
王姓客人多的是钱,倒没怎么着恼,定庵却气得嗷嗷直叫,一跺足,扬长而去。
是真名士自风流。
可是定庵风流过了头,代价未免太高了一点。
定庵的情敌很不简单,是荣恪郡王绵亿的儿子,姓爱新觉罗名奕绘,文学上的造诣也不浅,著有《明善堂集》。
奕绘受封为贝勒,其妻太清西林春则为福晋。
太清本姓顾,是江苏吴门人,才色双绝。
奕绘不仅会做官,还特别爱才,家中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四十四岁时,定庵任宗人府主事,是奕绘的部员,常去府邸交差。
贝勒把他尊为上宾,随他在府中行走,时或与太清诗词唱和。
定庵《己亥杂诗》中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的诗句,浪漫温馨,即真实写照。
久而久之,两人通了情款。
太清常穿白衣,披红斗篷,凌波微步,胜似天仙,手指洁白如玉,尤其喜欢骑在高头骏马上弹铁琵琶,见过的人都说她是王昭君再世。
定庵有绝活,他与太清用蒙语聊天,用汉语写诗,用吴语调情,表面上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
但情之所至,神魂为之颠倒,又怎能长期避人耳目?
贝勒暗中派人追杀定庵,一定要致他于死命。
所幸太清的仆人忠心爱主,侦获这一阴谋,及时通知了定庵。
事出仓促,定庵孤身逃往江东,路费不足,竟差点污面做了乞丐。
定庵五十岁时(1841年殁于浙江丹阳。
《年谱》上说他是“暴疾捐馆”——当时他是云阳书院讲席——此事令人疑窦丛生。
莫非奕绘不依不饶,一直穷追不舍,到底还是用鸩酒取了定庵的性命?
嘉(庆、道(光之际,定庵与魏源并肩齐名,有“龚魏”之称。
就文学而言,龚胜于魏;以政见而论,魏胜于龚。
定庵也极力主张御外侮,焚鸦片。
他一直关注塞防与海防,曾撰《蒙古图志》,洞悉沙俄的狼子野心。
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定庵写了一篇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劝老友多带兵,多筑炮台,多留神,准备一战,他的确很有先见之明。
定庵真有侠肝义胆吗?
“狂来说剑,怨去吹箫”,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惜豪情都付流水飘风,虽是极佳曲调,时人和后人都听不分明。
弱质书生自古好为大言,连诗仙李白也未能免“俗”。
定庵在《己亥杂诗》中称好友黄玉阶“亦狂亦侠亦温文”,此语又何尝没有自况之意?
他的豪情都落在纸上,这样也好,一百多年后读他的诗,我的鲜血仍能烨然着火。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在内受箝制,外遭欺侮的年月,纵有侠骨也沉沦啊。
林则徐可谓大侠,却被冤里冤枉地充军伊犁。
此前,定庵已然魂归西土,要不然,眼看着老友踽踽西出阳关道,真不知他的赠别诗该怎样下笔。
定庵死于五十岁,未终天年,尤其是未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龚孝珙于咸丰十年(1860年乐颠颠地带着英法联军去火烧圆明园,可算绝顶幸运了!
文天祥千秋祭
卞毓方
那天,牢房里苦热难耐,天祥无法入睡,他翻身坐起,点起案上的油灯,信手抽出几篇诗稿吟哦。
渐渐地,他忘记了酷热,忘记了弥漫在周围的恶气浊气,仿佛又回到了“夜夜梦伊吕”的少年时代,又成了青年及第、雄心万丈的状元郎,又在上书直谏、痛斥奸佞,倡言改革,又在洒血攘袂,出生入死,慷慨悲歌……这时,天空中亮起了金鞭形的闪电,随后又传来了隐隐的雷声,天祥的心旌突然分外摇动起来。
他一跃而起,摊开纸墨,提起笔,悬腕直书: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
文天祥驻笔片刻,凝神思索。
他想到自幼熟读的前朝英烈:
春秋的齐太史、晋董狐,战国的张良,汉代的苏武,三国的严颜、管宁、诸葛亮,晋代的嵇绍、祖逖,唐代的张巡、颜杲卿、段秀实,他觉得天地间的天气正是充塞、洋溢在这十二位先贤的身上,并由他们的行为而光照日月。
历史千百次地昭示,千百次啊;一旦两种健康、健全的人格走碰头,就好比两股涌浪,在大洋上相激,又好比两颗基本粒子,在高能状态下相撞,谁又能精确估出它所蕴藏的能量!
又一道闪电在空中划过,瞬间将土牢照得如同白昼,文天祥秉笔书下: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一串霹雳在天空炸响,风吹得灯光不住摇曳,文天祥的身影被投射到墙壁上,幻化成各种高大的形状,他继续俯身狂书: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室外,突至的雨点开始鞭抽大地。
室内,天祥前额也可见汗淋如雨。
然而他顾不得擦拭,只是一个劲地笔走龙蛇。
强风吹开了牢门,散乱了他的头发,鼓荡起他的衣衫,将案上的诗稿吹得满屋飘飞,他兀自目运神光,浑然不觉。
天地间的正气、先贤们的正气仿佛已经流转灌注到了他的四肢百骸、关关节节!
啊,古今的无穷雄文宝典,在这儿都要黯然失色。
这不是寻常诗文,这是中华民族的慷
慨呼啸。
民族精魂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常常要推出一些人来为社会立言。
有时它是借屈原之口朗吟“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它是借霍去病之口朗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这一次,便是借文天祥之口朗吟《正气歌》。
歌之临空,则化为虹霓;歌之坠地,则凝作金石。
五岳千山因了这支歌,而更增其高;北斗七星因了这支歌,而益显其明;前朝仁人因了这支歌,而大放光彩;后代志士因了这支歌,而脊梁愈挺。
至此,文天祥是可以“求仁得仁”、从容捐躯的了,他已完成在尘世的使命,即将跨入辉煌的天国。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
写完最后四句,文天祥掷笔长啸。
室外,滂沱大雨裂天而下,夹杂着摧枯拉朽的电闪雷鸣,天空大地似乎将要崩裂交合了。
天祥凝立不动,身形俨如一尊山岳!
梅香正浓
白桦
我自幼酷爱诵读中华民族英烈们所给我们遗留的诗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秋瑾……也酷爱诵读他们的同代人或后人关于他们的记述。
只要有可能,我都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墓地和留有他们血迹及深深脚印的土地。
我以为和他们相关连的风物倍加亲切,虽然每一次都有一种悲愤苍凉的思绪久久不能释然,我还是要去寻觅、登临,并感念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
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
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件我9岁时遇到的一件事。
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就是京剧里的宋士杰住的那个信阳州,他的小旅店开在西门之外,我家住天西门之内。
1939年,苦难中原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一年。
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小队日本宪兵牵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年轻抗日志士,押往西门外的乱尸岗,那里是历朝历代行刑杀人的屠场。
一群无知的顽童(其中也有成人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被这股愚味、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被卷进他们的行列。
刚刚走到西邻豆腐坊王大娘的门前,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差一点被摔倒在臭水沟里。
抬头一看,是王大娘。
她怒不可遏地问我:
“你去哪儿?
……你起什么哄?
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
……你!
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使我在一陈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
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不敢在街坊邻居们面前抬头,我开始知耻了。
每当我在多乖命运的途中走近污秽泥潭的时候,那位可敬而严厉的王大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及时伸出有力的手把我牢牢抓住。
今年我才有机会访问苏北文化名城扬州,5月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登上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立即想起我曾熟读过的两篇散文。
一篇是清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篇是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学者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
前者并未直接记述史可法,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