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文阅读.docx
《时文阅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时文阅读.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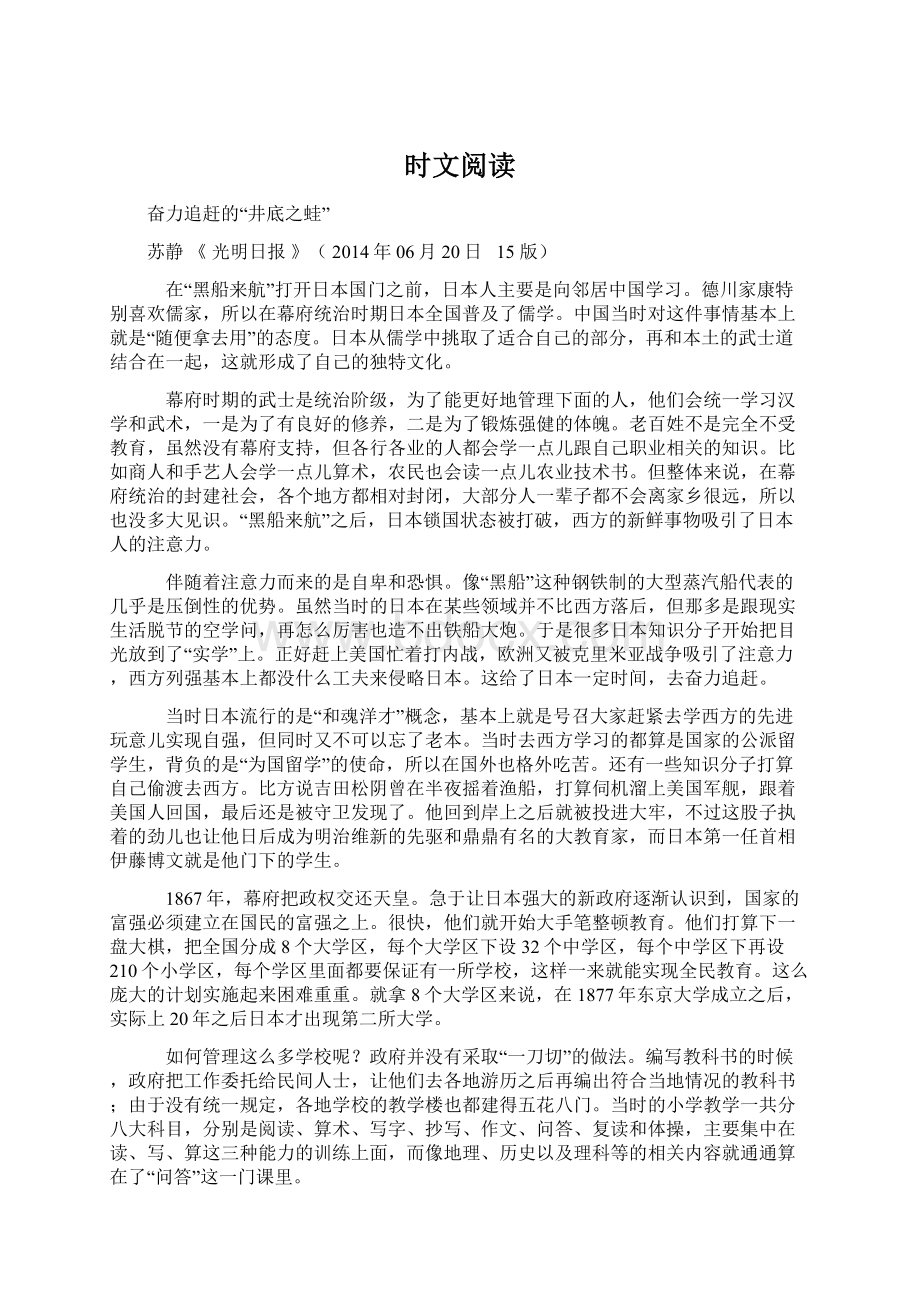
时文阅读
奋力追赶的“井底之蛙”
苏静《光明日报》(2014年06月20日 15版)
在“黑船来航”打开日本国门之前,日本人主要是向邻居中国学习。
德川家康特别喜欢儒家,所以在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全国普及了儒学。
中国当时对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随便拿去用”的态度。
日本从儒学中挑取了适合自己的部分,再和本土的武士道结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幕府时期的武士是统治阶级,为了能更好地管理下面的人,他们会统一学习汉学和武术,一是为了有良好的修养,二是为了锻炼强健的体魄。
老百姓不是完全不受教育,虽然没有幕府支持,但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学一点儿跟自己职业相关的知识。
比如商人和手艺人会学一点儿算术,农民也会读一点儿农业技术书。
但整体来说,在幕府统治的封建社会,各个地方都相对封闭,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会离家乡很远,所以也没多大见识。
“黑船来航”之后,日本锁国状态被打破,西方的新鲜事物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力。
伴随着注意力而来的是自卑和恐惧。
像“黑船”这种钢铁制的大型蒸汽船代表的几乎是压倒性的优势。
虽然当时的日本在某些领域并不比西方落后,但那多是跟现实生活脱节的空学问,再怎么厉害也造不出铁船大炮。
于是很多日本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放到了“实学”上。
正好赶上美国忙着打内战,欧洲又被克里米亚战争吸引了注意力,西方列强基本上都没什么工夫来侵略日本。
这给了日本一定时间,去奋力追赶。
当时日本流行的是“和魂洋才”概念,基本上就是号召大家赶紧去学西方的先进玩意儿实现自强,但同时又不可以忘了老本。
当时去西方学习的都算是国家的公派留学生,背负的是“为国留学”的使命,所以在国外也格外吃苦。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打算自己偷渡去西方。
比方说吉田松阴曾在半夜摇着渔船,打算伺机溜上美国军舰,跟着美国人回国,最后还是被守卫发现了。
他回到岸上之后就被投进大牢,不过这股子执着的劲儿也让他日后成为明治维新的先驱和鼎鼎有名的大教育家,而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就是他门下的学生。
1867年,幕府把政权交还天皇。
急于让日本强大的新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国民的富强之上。
很快,他们就开始大手笔整顿教育。
他们打算下一盘大棋,把全国分成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下再设210个小学区,每个学区里面都要保证有一所学校,这样一来就能实现全民教育。
这么庞大的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就拿8个大学区来说,在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之后,实际上20年之后日本才出现第二所大学。
如何管理这么多学校呢?
政府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编写教科书的时候,政府把工作委托给民间人士,让他们去各地游历之后再编出符合当地情况的教科书;由于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学校的教学楼也都建得五花八门。
当时的小学教学一共分八大科目,分别是阅读、算术、写字、抄写、作文、问答、复读和体操,主要集中在读、写、算这三种能力的训练上面,而像地理、历史以及理科等的相关内容就通通算在了“问答”这一门课里。
为了迅速提升国民的教育水平,政府派遣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同时还高薪聘请外籍教师前来教学。
1868年到1872年间,日本光是付给外教的工资就占了当年国家预算的3.98%。
一直到1882年,政府才停止了引进外教。
这自然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狂追猛赶,日本教师在那时已经能够胜任各个领域的教学工作了。
(摘自《知日知日》,苏静主编,中信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愤怒,是因为有爱
马秀琴《光明日报》(2014年06月20日 15版)
那是2010年初春。
天仍微冷,我坐在电脑前查若泽·萨拉马戈的资料。
《失明症漫记》、《修道院纪事》……似乎都很熟悉,可仔细一想,从来没有读过。
甚至,若泽·萨拉马戈的照片也是第一次看到,面容清癯,透着些许固执。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正计划在秋天二度访华,也不知道就像他第一次来华时寂寂无名般,他的二度访华也终将无法成行。
6月,他在西班牙去世。
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他,缘于南非世界杯上葡萄牙队员臂膀上的黑纱。
若泽·萨拉马戈1922年生于里斯本北部一个名为阿金尼亚加的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
由于经济原因,高中时他放弃了学业,转而学习技术,之后辗转于各个服务行业。
1947年,第一部小说Terra do Pecado(暂译《罪孽之地》)出版,使他从电焊机售货员一跃成为文学杂志作者,但直到33年后的1980年,他才完成了第二部小说Levantado do Chao(暂译《从地上站起来》),以新秀的姿态登上文坛。
在诗歌、专栏之外,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风格和文学创作的体裁——长篇小说。
那一年,我刚出生。
33年后,我面前摆着《复明症漫记》的原稿与译稿,冒冒跌跌地走进了他的文学世界。
缠绕如同密林的大段大段的句子,以职业或身份称呼轮番登场的纷乱人物,只用逗号与句号淋漓表达的充沛情感(中文版中,译者范维信先生为了还原作者通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人物对话的方式,增加了一个分号),正如其葡语名Saramago近似Serámago(意为他或许是魔术师)般,萨拉马戈指挥着语言的魔术棒,让我在没有特定地域与历史的城市中,见证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与4年后这座恢复正常的城市所遭遇的“选票危机”。
紧张辛辣,却不斥抒情,不乏温柔,彻底的怀疑主义与对人类自身的有限热情交织在一起,嘲讽与忧虑同在。
萨拉马戈在创作于2004年的《复明症漫记》中,以清亮的眼力、连续的诘问、幽默的语言让我们看到社会管制动力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理性。
大雨瓢泼的日子,无人前去投票选举。
正在有关部门忧心忡忡时,下午四点钟,既不提前一个小时也不推后一个小时,选民们纷纷涌向投票点。
选举结果出人意料,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公民投了空白选票。
作为一个自称“具有共产主义的荷尔蒙”的作家,他的这部作品似乎是在用重拳挥击西方的民主制度。
公务人员在这场没有信心的选举中惶恐如小丑的表现、政客的虚伪和官僚运作的荒诞,让《纽约观察家》称赞此书是“一部彻底、冷酷又精准的政治寓言”。
然而,萨拉马戈的作品,常常丰富而多义。
《复明症漫记》看似一部政治寓言,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话题,而是融入了与之相联系的人本关怀。
比如,随着当之无愧的主角警督避开监视器、穿过铁丝网、隐姓埋名地潜入被隔离的首都,偷偷摸摸地出场——在故事发展超过二分之一处——我们才发现,政治其实也是作者想要悄无声息地跨过与超越的藩篱。
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且一向忠诚于此的警督——被内政部长视为完成任务的唯一人选,去寻找4年前这座城市里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发现证据(证明她是这场选举的组织者)并实施逮捕。
然而或许是被作为医生妻子的她一直以来的真诚与平和所感动,又或许是自她从《失明症漫记》中的角色开始所凝聚的救赎力量的作用,警督慢慢地将手中的“证人”视为普通的“人”。
他对其中一个“证人”的称呼,由“妓女”到“戴墨镜的姑娘”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女人”……在这些细节中,萨拉马戈镂刻了人物的变化和逐渐生发的爱。
语言也一改前半部分的冷酷而变得温文柔和。
前台的国家机器运作与后台的小人物故事,构成了交错爬梳的两处空间。
在这两处空间的裂隙处那隐晦的阴影里,我们开始思考警督的那句话:
“出生的那一刻我们仿佛为一生签署了契约,有一天我们会问自己,是谁替我们签署的。
”萨拉马戈所关怀的世界是广袤深邃的,人类的整个社会生存环境才是他的着眼点。
《复明症漫记》同其“前传”《失明症漫记》一样都具有荒诞的情境,也因此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写作。
但事实上,就纯阅读感受来说,萨拉马戈所营造的氛围更具有积极意义,他对人类和未来持有一丝信心。
止庵先生曾说过:
寓言式写作容易深刻,但不容易深厚;容易警醒人,但不容易感动人。
《一九八四》《鼠疫》读罢,至今想起仍觉得惊心动魄,后背发冷,总担心世界成为那样便是末日。
然而,萨拉马戈的作品,无论《失明症漫记》还是《复明症漫记》,在思考的同时,都有一种淳朴的感动,以及与人物的互动,会喜欢上那个在失明中伸手帮助老人搓洗后背的“戴墨镜的姑娘”,会惋惜于坐在湖水边满意地感叹一声之后被一颗子弹无声地射进身体的警督,甚至会惦记帮医生的妻子拭泪的那只狗。
1997年3月,萨拉马戈访问北京,出席他的小说《修道院纪事》中译本首发式。
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在墓碑上刻下如下文字:
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
或许,之所以愤怒,正是因为有爱。
(作者为新经典文化欧美文学编辑,《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责编)
在夜晚的麦田里独行
刘庆邦
《人民日报》(2014年06月21日 12版)
已经是后半夜,我一个人在向麦田深处走。
人在沉睡,值夜的狗在沉睡,整个村庄也在沉睡,仿佛一切都归于沉静状态。
麦田上空偶尔响起布谷鸟的叫声,远处的水塘间或传来一两声蛙鸣,在我听来,它们迷迷糊糊,也不清醒,像是在发癔症,说梦话。
它们的“梦话”不但丝毫不能打破夜晚的沉静,反而对沉静有所点化似的,使沉静显得更加深邃,更加渺远。
刚圆又缺的月亮悄悄升了起来。
月亮的亮度与我的期望相差甚远,它看上去有些发黄,还有些发红,一点儿都不清朗。
我留意观察过各个季节的月亮,秋天和冬天的月亮是最亮的,夏天的月亮“质量”总是不尽如人意。
这样的月亮也不能说没有月光,只不过它散发的月光是慵懒的,朦胧的,洒到哪里都如同罩上了一层薄雾。
比如月光洒在此时的麦田里,它使麦田变成白色的模糊,我可以看到密匝匝的麦穗,但看不到麦芒。
这样的月光谈不上有什么穿透力,它只洒在麦穗表面就完了,麦穗下方都是黑色的暗影。
我沿着一条田间小路,自东向西,慢慢向里边走。
说是小路,在夜色里几乎看不到有什么路径。
小路两侧成熟的麦子呈夹岸之势,差不多把小路占严了。
我每往里走一步,不是左腿碰到了麦子,就是右腿碰到了麦子,麦子对我的深夜造访似乎不是很欢迎,它们一再阻拦我,仿佛在说:
深更半夜的,你不好好睡觉,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窄窄的小路上长满了野草,随着麦子成熟,野草有的长了毛穗,有的结了浆果,也在迅速生长,成熟。
我能感觉到野草埋住了我的脚,并对我的脚有所纠缠,我等于趟着野草,不断摆脱羁绊才能前行。
面前的草丛里陡地飞起一只大鸟,在寂静的夜晚,大鸟拍打翅膀的声音显得有些响,几乎吓了我一跳,我不知不觉站立下来。
我不知道大鸟飞向了何方,一道黑影一闪,不知名的大鸟就不见了。
我随身带着一支袖珍式的手电筒,却没有打开。
在夜晚的麦田里,打手电是突兀的,我不愿用电光打破麦田的宁静。
我们家族的墓园就在村南的这块麦田里,白天我已经到这块麦田里看过,而且在没腰深的麦田里伫立了好长时间。
自从1970年参加工作离开老家,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在麦子成熟的季节回过老家,再也没有看到过大面积金黄的麦田。
这次我特意抽出时间回老家,就是为了再看看遍地熟金一样的麦田。
放眼望去,金色的麦田向天边铺展,天有多远,麦田就有多远,怎么也望不到边。
一阵熏风吹过,麦浪翻成一阵白金,一阵黄金,白金和黄金在交替波涌。
阳光似乎也被染成了金色,麦田和阳光在交相辉映。
请原谅我反复使用金这个字眼来形容麦田,因为我想不出还有哪个高贵的字眼可以代替它。
然而,如果地里真的铺满黄金的话,我不一定那么感动,恰恰是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成熟的麦子,才使我心潮激荡,感动不已。
那是一种生命的感动,深度的感动,源自本能的感动。
它的美是自然之美,是壮美、大美和无言之美。
它给予人的美感是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的。
因为白天看麦田没有看够,所以在夜深人静时我还要来。
白天为实,夜晚为虚,阳光为实,月光为虚,我想看看虚幻环境中的麦田是什么样子。
站在田间,我明显感觉到了麦田的呼吸。
这种呼吸在白天是感觉不到的。
麦田的呼吸与我人类的呼吸相反,我们吸的是凉气,呼的是热气,而麦田吸进去的是热气,呼出来的是凉气。
一呼一吸之间,麦子的香气就散发出来。
麦子浓郁的香气是原香,也是毛香,吸进肺腑里让人有些微醉。
晚上没有风,不见麦浪翻滚,也不见麦田上方掠来掠去的燕子和翩翩起舞的蝴蝶。
仰头往天上找,月亮升高一些,还是暗淡的轮廓。
月亮洒在麦田里的不像是月光,满地的麦子却像是铺满了灰白的云彩。
一时间,我以为自己站在云彩里,在随着云彩移动。
又以为自己也变成了一棵小麦,正幽幽地融入麦田。
为了证明自己没变成小麦,我掐了一只麦穗儿在手心里搓揉。
麦穗儿湿漉漉的,表明露水下来了。
露水湿了麦田,也湿了我这个从远方归来的游子的衣衫。
我免不了向墓园注目,看到栽在母亲坟侧的柏树变成了黑色,墓碑楼子的剪影也是黑色。
从麦田深处退出,我仍没有进村,没有回到我一个人住的老屋,而是沿着河边的一条小路,向邻村走去。
在路上,我想我也许会遇到人。
夜行的人有时还是有的。
然而,我跟着自己的影子,影子跟着我,我连一个人都没遇到。
河上有一座桥,我在那座桥上站下了。
还是在老家的时候,也是在夜晚,我曾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这座桥上谈过恋爱,那个姑娘还送给我一双她亲手为我做的布鞋。
来到桥上,我想把旧梦回忆一下。
桥的位置没变,只是由砖桥变成了水泥桥。
桥下还有水,只是由活水变成了死水。
映在水里的红月亮被拉成红色的长条,断断续续。
青蛙在浮萍上追逐,激起一些细碎的水花儿。
逝者如斯,那个姑娘再也见不到了。
到周口市乘火车返京前,我和作家协会的朋友们一块儿喝了酒。
火车开动了,我还醉眼蒙眬。
列车在豫东大平原的麦海里穿行,车窗外金色的麦田无边无际,更是壮观无比。
我禁不住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说大平原上成熟的麦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观,你想象不到有多么好看,多么震撼……我没有再说下去,我的喉咙有些哽咽。
为一滴水祈祷
苏轼冰
《人民日报》(2014年06月21日 12版)
身在山清水秀的彩云之南,这几年却越发知道了水的可贵。
我的家乡,位于云南中部,江河断流,库塘见底,田地龟裂,农作物枯死,数以万计的人畜饮水严重困难,旱情火急……这样的干旱已经五年了。
五年,每到秋冬季节,每到春夏之交,看报、看电视,干旱缺水的内容几乎天天可见。
到乡镇走走,特别是到山区村寨,见到的都是干渴,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都是水。
水啊,水!
几年之间,为何一下子变得如此金贵?
我亲眼目睹,有的人家为了洗衣服要走二三十公里,有的年轻人为了洗一次澡,竟要坐上百里的客车专门到县城……在一所严重缺水的彝族地区小学校里,我亲眼看到校长把全校的学生集中起来发放矿泉水的过程。
那位校长高举着一瓶矿泉水十分动情地对学生说:
“矿泉水是恩人们从千里万里之外送来的,一定要节约,一瓶水要喝三天,实在渴了,就含一口。
”
而无数的人又在天天浪费水。
我曾看到城市的供水管爆裂,柏油马路成为汪洋。
在几所大学校园里,我还看到坏了的水龙头无人修,清澈的水白天黑夜哗哗流。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没有节水的意识,为洗一双球鞋、几件衣服不惜消耗几桶水,更不用说那么多的洗车店,为了图省事、方便,高压水枪接连喷射,水流成了小河,还有无数的洗浴中心,一个人洗澡要浪费一大池水……
更让人心痛的是,有的人为了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惜砍掉大片大片能蓄水的水冬瓜树,挖去无数能蓄水的榕树,栽上汲水性特别强的桉树。
干旱的几年里,我常在想,为什么森林密布的彝山会没有水?
我家乡森林覆盖率高达84%,竟然会山涧无水、叶黄草枯?
四年前干旱缺水的季节,我曾到一个较大的村庄。
多年前,我曾在离这个村不远的地方教书。
这个村由于山上有很多茂密的水冬瓜林,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一股茶杯粗的山泉水从山下汩汩地冒出来,村里的几百口人吃水、用水都不愁。
后来,村里人为了能赚钱,栽上了数十万棵生长快、几年就能卖钱的桉树。
后来,山下的水不知不觉地断流了,过去的富水村也成了缺水村,这不是只顾眼前利益、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带来的后果吗?
还有一些人为了眼前利益、为了所谓的政绩,乱作为、瞎作为,使无数美丽的江河湖泊受到严重污染,昔日清澈见底、秀水盈盈的河坝,今天满目污浊、臭气熏天。
这样的环境鱼虾必死,庄稼必被污染,人必病,水必然枯竭!
痛定思痛,我们不得不承认平时人们对水的认识还是太少,节水意识还是太差!
扪心自问:
平时不注意,只有到了干旱缺水,才知道水的重要,才开始节水,会不会觉得太晚?
!
一个诗人说:
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自己的眼泪。
我在为一滴水而祈祷,更呼唤全民的节水意识。
人们啊,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透明血液,一旦枯竭,任何金银宝钻都无法换回,是该到了深刻反思的时候了,不要到了水成为人类自己的眼泪时才喊渴!
走在弯弯的山路上
祁玉江
《人民日报》(2014年06月21日 12版)
久居繁华现代的都市里,心却怎么也安放不下,时不时会想起故乡那弯弯的山路来,甚至出现在梦境里——那山路像一条细线,兜得很长,仿佛永远没有尽头;又如一条曲折的河流,千回百转,一直向前奔涌;更似一条天赐长绫,缠来绕去,裹挟在高耸的山腰间,时隐时现。
我曾无数次走在这弯弯的山路上,已经谙熟了它那博大、憨厚、纯洁的秉性。
不管是谁,无论何物,它都不加阻拦,总是敞开胸怀热情接纳。
它从不索取,更不需要回报,总是默默地为前行的脚步奉献着,即便被踩压得遍体鳞伤,也会通过自身“免疫”功能逐渐恢复、延伸。
走在这弯弯的山路上,就像回到了家,投入到母亲的怀抱,走进亲人们的心田,有享受不尽的温馨和愉悦!
春日里,走在这弯弯的山路上,百花盛开,万木争荣,满眼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路走来,望了这山看那坡,观了一树又一花,那漫山遍野的绿意,让你兴奋,使你流连,总会惹得一颗热乎乎的心骚动不安。
夏日里,走在这弯弯的山路上,看满山的庄稼茁壮成长,牛儿、驴儿在寸草湾里悠闲地吃草,狗儿懒洋洋地躺在村头院落的树荫下昏头酣睡,鸟雀在树林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孩子们赤身裸体,在小河里戏水,发出一阵阵的欢笑声,远处的山梁上不时传来农人们的信天游: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满山的庄稼风摆动,一株株一苗苗都连咱的心……”此时,你早被这纯朴的山乡美景打动了,干脆躺在树荫下,伴随着歌声鸟语,仰望云卷云舒,与天地融为一体,宛若神仙一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竟然是那么踏实,那么香甜。
秋日里,走在这弯弯的山路上,满目金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黄澄澄的糜谷,金灿灿的玉米,伴着红彤彤的苹果、枣儿,到处硕果累累。
春种秋收嘛!
人们一边割着谷子,一边便扯开了嗓子唱道: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的是好光景;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此时此刻,你不知是高兴还是伤心,更不知为谁高兴为谁伤心,脚下的步子却迈得更欢实了。
冬日里,走在这弯弯的山路上,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大地一片荒凉。
四周空旷静寂,几声鸡鸣狗吠竟是那么响亮,那么清晰,顿时打破了山野的沉寂,让你脚底生风,步履加快,使你并不孤寂,并不觉得寒冷,反倒身上汗津津的,浑身充满了力量。
如果遇上下雪天,天灰蒙蒙的,空中飞舞着雪花,大地银装素裹,天地相接,合二为一。
这个时候,弯弯的山路失了踪影。
如果是生人,定会困顿窘迫,不知所措。
可山里人不以为然,他们熟悉了这蛛网般的路径,再大再厚的雪也阻挡不住前进的脚步。
弯弯的山路,山路弯弯。
我是多么地怀念你!
与你相伴,虽然身是劳累的,但心是踏实的、轻松的,甚至是愉悦的。
老泡桐树的守望
杨春光(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06月20日 16版)
题记:
1963年春寒之时,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根治兰考“三害”,试验性地种下了一棵泡桐树。
51年过去了,斯人已长逝,泡桐树正值壮年,默默守望其间,如同焦裕禄精神的化身一般,天天、月月、年年。
为此而赞之。
50多年了,好像就在昨天,你始终植根泥土,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心相连,寄托了焦书记对人民的深深情感;50多年了,你已经大树参天,郁郁葱葱,迎风颔首,饱含焦书记对群众的无限眷恋;50多年了,你站在那儿,把焦裕禄精神守望;50多年了,你挺立在那儿,将焦裕禄的期盼流连绵绵。
你展示了共产党人高山般的英雄楷模,忠诚于党,服务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爱永在世间;50多年了,你诉说着焦书记做过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
你记得同事们常说,焦裕禄“心里只有人民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在1962年的那个冬日里,“焦书记来兰考工作了”,同志们要接,同事安排见。
但是,久而见不到,他已深入村子里,到了人民群众中间。
无论是大雪封门的日子,还是洪水泛滥的当口,无论是初到兰考工作时,还是病重之中,他都是这样忘我。
那晚,在雪夜中看望两位孤寡老人,一句“我是你们的儿子啊”,道出了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
他那张拿着铁锨,挽着裤腿,淌着泥水,与群众在一起的照片,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那年、那月、那天,你见证了崇尚“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的焦裕禄书记,在飞沙中,在风雨中,在寒风里,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接触地气;在骄阳下,在救灾现场,在泥泞中,在田里,在最困难的群众身旁;走农家,到牛圈,看五保户;找专家,问地力,测水流量,探寻实施“三害”(风沙、盐碱、内涝)治理;“晴天一身土,雨天满身泥”。
那辆老式自行车记得,在1年零3个月的475天里,焦裕禄书记靠着它,抱着病体,竭尽全力跑遍了全县149个生产队中的127个,行程五千多里;那架带着一个大窟窿的老藤椅记得,焦裕禄书记病痛难忍时,就用手硬撑在身体和右椅背之间,久而久之,竟把藤椅挤穿。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你深深懂得焦裕禄书记,对人民、对家人,心中满怀无限的爱。
但他是那样的公私分明,严于律己。
从看电影、找工作,到救灾;从退鲜鱼、西瓜,到排号理发……点点滴滴,令人信服,感人心怀。
他常说,“干部不领,水牛跳井”,对个别违法乱纪的干部,他耐心教育,依规严肃处理,从不姑息。
他亲手制定的“十个不准”,至今仍高悬在大墙上,烙在干部群众心间;那满是补丁的棉衣,展示着他带头践行清贫和艰苦奋斗的诺言。
就像明灯,指引着无数领导干部走好未来。
你永远不会忘记,焦裕禄书记为了人民群众的明天,提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山河换新天”“革命者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豪”,用其毕生的精力,消灭“三害”。
让沙丘贴上“膏药”,扎了“针”,洪水乖乖进河道;让泡桐树郁郁葱葱,粮食丰产,老百姓再不去逃荒要饭,日子富足,和和美美,从心里真正喊出“共产党好”。
这是焦裕禄最大的愿望。
不能忘呵,乡亲们痛哭“焦书记是为我们兰考累死的”;直到今天,很多老乡逢家里有事情,仍习惯到焦书记坟上念叨念叨,“就像焦书记还在我们身边一样”。
不能忘呵,焦书记曾发誓,“拼出老命,也要让兰考变个模样”;那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的遗言,激励了共产党人万万千千。
老泡桐树啊,请你告慰焦书记吧。
今天,他带领大家绘制的蓝图已经变为现实。
兰考大地,天蓝、林翠、水净,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兰考人民,正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努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兰考,这块他全身心付出和魂牵梦萦的地方,正在插翅腾飞!
老泡桐树呵,斗转星移,你的志向不移;时光飞逝,你的丰采不减;岁月沧桑,你的赤诚之心犹在;你与焦裕禄书记相依相伴,传承精华,撒播大爱,天地之间,代代年年。
你的精神永远在人民群众心间!
(作者为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梦里的家乡
冯其庸(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06月20日 16版)
我离开家乡已经整整六十年了。
20岁前我一直在前洲镇冯巷农村种地。
这是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前后都是农田,我是在农田和竹树丛中长大的。
我上学必须翻过一个大坟岗,叫松坟岗,名字叫松坟岗却没有一棵松树,连一棵小树都没有,只是一大片荒草离离、高低不平的坟地。
走完坟地,右边就是一条小河,叫葫芦头沟,河不长,约半华里,形如葫芦。
再往前,就可进前洲镇街道,到达学校了。
以上是我从家里上学校——小学和初中——每天必须来回走过两遍的地方。
我家门前是一片菜圃,满园是碧绿的油菜,还有两株桃树和一株石榴。
每到春末,桃花盛开,之后,就是火红的石榴花。
每到这个季节,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