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法》第11条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辨析.docx
《《专利法》第11条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辨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专利法》第11条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辨析.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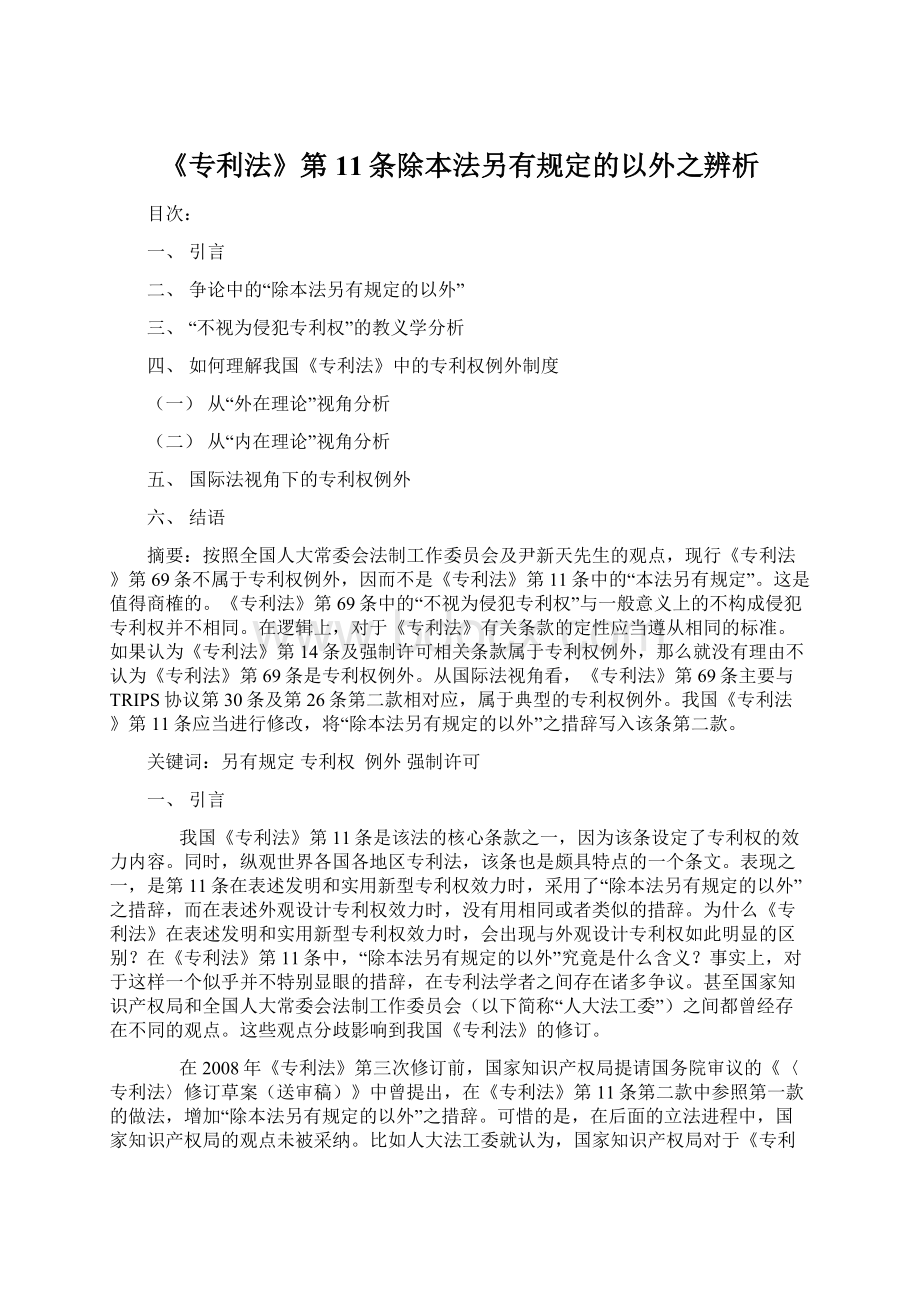
《专利法》第11条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辨析
目次:
一、引言
二、争论中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三、“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教义学分析
四、如何理解我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例外制度
(一)从“外在理论”视角分析
(二)从“内在理论”视角分析
五、国际法视角下的专利权例外
六、结语
摘要: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尹新天先生的观点,现行《专利法》第69条不属于专利权例外,因而不是《专利法》第11条中的“本法另有规定”。
这是值得商榷的。
《专利法》第69条中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与一般意义上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并不相同。
在逻辑上,对于《专利法》有关条款的定性应当遵从相同的标准。
如果认为《专利法》第14条及强制许可相关条款属于专利权例外,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认为《专利法》第69条是专利权例外。
从国际法视角看,《专利法》第69条主要与TRIPS协议第30条及第26条第二款相对应,属于典型的专利权例外。
我国《专利法》第11条应当进行修改,将“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措辞写入该条第二款。
关键词:
另有规定专利权 例外强制许可
一、引言
我国《专利法》第11条是该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因为该条设定了专利权的效力内容。
同时,纵观世界各国各地区专利法,该条也是颇具特点的一个条文。
表现之一,是第11条在表述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效力时,采用了“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措辞,而在表述外观设计专利权效力时,没有用相同或者类似的措辞。
为什么《专利法》在表述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效力时,会出现与外观设计专利权如此明显的区别?
在《专利法》第11条中,“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究竟是什么含义?
事实上,对于这样一个似乎并不特别显眼的措辞,在专利法学者之间存在诸多争议。
甚至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法工委”)之间都曾经存在不同的观点。
这些观点分歧影响到我国《专利法》的修订。
在2008年《专利法》第三次修订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请国务院审议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曾提出,在《专利法》第11条第二款中参照第一款的做法,增加“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措辞。
可惜的是,在后面的立法进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观点未被采纳。
比如人大法工委就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专利法》第11条中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理解有误,因而无须在该条第二款中加入“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措辞。
2015年4月,《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工作正式启动,国家知识产权局向社会公众公布了《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
这一次,国家知识产权局似乎已经为人大法工委所说服,没有对《专利法》第11条提出任何修改建议。
2015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对专利法第11条也没有作任何改动。
但是笔者认为,2008年《专利法》修订时,人大法工委认为“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不应当写入《专利法》第11条第二款的理由并不成立。
在《专利法》再次修订之际,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究,以期对《专利法》第四次修订有所裨益。
二、争论中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对于《专利法》第11条第一款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措辞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究竟是指哪些条款,存在很大的争议。
汤宗舜先生认为,“在本法另有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即可以不经专利权人许可,或者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他主张《专利法》中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条款是“本法另有规定”情形。
在《专利法解说》一书中,汤先生明确而具体地指出,这些“本法另有规定”的情形,就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而言,包括:
国务院批准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某些需要推广应用的发明(第14条)、根据强制许可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第48条至50条)、权利用尽后的实施、先用权人的实施、临时过境实施及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专利(第63条)。
但是正如尹新天先生所指出的,如果上述观点是正确的,则《专利法》第11条第二款不写入“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的措辞就是不正确的。
因为至少权利用尽、先用权及临时过境情形同样应当适用于外观设计专利权。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06年12月27日提请国务院审议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曾经提出修改建议,在《专利法》第11条第二款中相应增加“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的措辞。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建议并未被采纳。
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大法工委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人大法工委认为,就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而言:
(1)第63条列举的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而不是专利权效力的例外情况。
(2)专利权效力的例外情况包括《专利法》第14条关于国家推广应用的规定以及第48条至51条关于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规定。
(3)1984年制定的《专利法》第11条第一款采用的措辞是“除本法第14条规定的以外”,这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年采用这一措辞的本意并非要将当时的《专利法》第63条列举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囊括在专利权的例外情况之中。
简而言之,人大法工委认为,在2000年《专利法》第11条中,“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措辞中的“另有规定”必须是专利权例外,而《专利法》第63条(“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内容不是专利权例外。
尹新天先生在其影响甚大的《中国专利法详解》一书中接受了这个观点,并对此进行了解释和强调:
第一,在依照《专利法》第14条的规定由国务院做出推广应用发明的决定、依照《专利法》第48条至51条的规定给予实施专利的强制许可的情况下,有关实施行为本来应当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但出于种种考虑可以豁免其侵犯专利权的民事责任。
而在《专利法》第69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下,“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表明这些实施行为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原本就无须承担侵犯专利权的民事责任,谈不上豁免其民事责任的问题。
第二,“侵犯专利权的例外”与“视为不侵犯专利权”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需要注意避免混淆,不可将它们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人大法工委的观点自相矛盾,而尹新天先生对于人大法工委观点的解释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特别是,尹新天先生关于避免“侵犯专利权的例外”与“视为不侵犯专利权”相混淆的观点,很可能在专利法理论上造成混乱,有必要加以澄清。
三、“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教义学分析
现行《专利法》第69条规定了五种“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
这里的一个关键用语是“不视为”。
在法律中,“视为”这一术语有其独特的含义。
基本公认的说法是,法律条文中的“视为”用语属于法律拟制。
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法学上的拟制是:
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
黄茂荣教授指出,拟制性法条的特点在于:
立法者虽然明知其所拟处理的案型与其所拟引来规范该案型之法条本来所处理之案型,其法律事实由法律上重要之点(构成要件上所指称的特征)论,并不相同,但仍将二者通过拟制赋予同一的法律效果;申言之,通过拟制将不同的案型当成相同,然后据之作相同的处理,并非由于立法者之错误而然。
我国大陆学者也指出,“视为”作为法律拟制,起到多方面的作用。
比如,立法者基于相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事实上不同的事物等同处理。
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此,《专利法》第69条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用语表明该条所列举的五种情况,和一般意义上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是不同的。
“不视为侵犯专利权”是一种法律拟制,它将本来属于某种判断结果(侵犯专利权)的情况,基于某种特定原因(比如公共政策)考虑,不归入该结果。
反过来说,如果按照未加拟制的结果,应当是侵犯“专利权”,或者至少有侵犯专利权的高度盖然性。
人大法工委主张《专利法》第69条“本来就不构成侵权”的意思,等于是说,在《专利法》第69条规定的情形下,实施人本来就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而实施专利。
这种观点如果成立,一个合理的质疑是:
为什么还要专门规定第69条?
在《专利法》立法之初,的确有观点认为,专利法中规定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条款其实是多余的,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那是对专利权结构的一种误解。
专利权是一种高度类型化的权利。
但是类型化也带来一些问题。
典型的是,专有权条款(即《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专有权范围过大,很可能与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相背离,也与公共政策的考虑不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专有权进行适当的减损。
从国内法角度来说,通常都是对专有权的减损加以具体列举,只有对于这些具体列举的情形,才不执行专有权,这是为了避免对于专有权造成任意减损。
如果没有专门规定减损,就应当执行专有权条款,而不能直接以公共政策、社会习惯本身来抗辩。
四、如何理解我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例外制度
权利存在边界。
但是,权利边界是因权利限制而产生,还是未经限制就事先存在权利边界?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石。
大体上,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外在理论”。
德国学者科恩认为,权利限制意味着两个事物——权利和限制。
所谓权利指本义上的权利(rightinitself),这项权利本身是没有限制的。
然后,存在一个经限制以后而存在的权利,这个权利可称为受限制后的权利(rightaslimited)。
尽管在一般意义上,权利是应该受限制的,但权利本身完全可以以无限制的状态而存在,限制与权利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有当要求某个人的权利与其他人的权利或者公共利益和谐相处时,这种联系才凸显出来。
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内在理论”,该理论认为,法律规制就是权利边界的基础,权利依法仅享有一个确定、唯一的内容,权利限制是确定权利的外延或者内容的方法,故而权利必含限制。
基于公共利益等要求对权利的限制,也是从权利的内部进行的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应被称作内部限制。
如果按照“内在理论”进一步推论,权利例外或权利滥用等其实是不应当存在的:
既然权利当中已经包含了必要的限制和边界,就无从再谈权利例外了,这样的权利不需要例外。
同时,这样的权利在逻辑上也不允许滥用的存在。
因为当发生滥用问题时,行为已经越出权利的范围或边界,本质上并不是在行使权利了。
对于权利限制的这两个理论基础,笔者在此不作太多的评判。
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其中,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当人们运用一定的理论(当然可能是隐含的)对某些法律现象进行分类时,必须统一标准。
比如,当人们分析某部法律中哪些条文属于权利例外时,可以用“外在理论”为工具进行分析,也可以用“内在理论”为工具进行分析,但对同一部法律中的不同条文,在同一时间,只能用一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否则,在逻辑上就会混乱。
就我国《专利法》中的相关条款而言,在认定它们是否为专利权例外时,必须同时采用相同的标准。
下面分别从“外在理论”视角和“内在理论”视角进行分析,看看《专利法》第14条、强制许可相关条款及第69条是否属于专利权例外。
(一)从“外在理论”视角分析
“外在理论”视角下,在受到限制前,专利权为单纯由《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专有权。
因此,如果有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某一项专利,应认定为专利侵权,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这也就是人大法工委所说的“本来是专利侵权行为”。
但是,《专利法》现在规定了第14条和强制许可相关条款,允许国家机关在符合第14条或者强制许可相关条款的情况下,给予特定的实施人以“许可”。
此种“许可”使得实施人的行为不再被认定为专利侵权,不必承担“本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就是人大法工委所说的“豁免其侵犯专利权的民事责任”。
可见,人大法工委对于《专利法》第14条和强制许可相关条款所采用的标准是“外在理论”。
《专利法》第69条规定了五种情况,包括专利权用尽、先用权、临时过境、科学实验及医药行政审批,按照第69条的规定,在这五种情形下,对于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或设计进行实施,并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换言之,这些实施专利的行为不会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外在理论”视角下,专利权是单纯由《专利法》第11条设定的专有权,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在这些情况下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专利,当然是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比如,如果没有《专利法》第69条专门规定,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有没有落入专利权人禁止的范围内呢?
当然落入了。
这种情况完全满足为生产经营而使用专利产品的法律规定。
专利权人可以主张其侵犯专利权,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只是由于《专利法》第69条的专门规定,实施人才不必承担这样的责任。
所以,从“外在理论”的角度来说,《专利法》第69条的确“豁免”了专利实施人本来应当的责任。
但显然,就《专利法》第69条而言,人大法工委并没有采用“外在理论”标准。
(二)从“内在理论”视角分析
如前所述,“内在理论”主张,权利中已经包含了对于权利的限制。
这样看来,《专利法》第11条所设定的,并不是完整的专利权。
《专利法》第11条中所说的专有权只有和《专利法》中的其他条款及制度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专利权。
所以,在“内在理论”看来,有没有侵犯专利权,不能光看《专利法》第11条,还要看其他条款,例如,《专利法》第69条。
再以《专利法》第69条规定的临时过境为例,如果将《专利法》第11条及《专利法》第69条第三款结合起来看,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就没有落入专利权人禁止的范围之内:
因为虽然《专利法》第11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专利,是专利权人可以禁止的行为,但《专利法》第69条却明确指出,这种行为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从而此种行为并没有落入由《专利法》第11条和第69条第三款共同构成的“专利权”。
这也就是人大法工委所说的“本来就没有侵犯专利权”的原因。
可见,就《专利法》第69条而言,人大法工委的分析工具其实是“内在理论”。
但是,如果以“内在理论”的视角来审查《专利法》第14条及强制许可相关条款,同样可以得出,在符合《专利法》第14条或者强制许可相关条款的情况下,有关实施行为也“本来就没有侵犯专利权”。
以强制许可实施为例,当国家有关机关依照强制许可相关条款,批准实施人在一定条件下实施专利时,这种实施行为就是合法行为,并没有侵犯专利权。
如果同时考虑《专利法》第11条及强制许可相关条款,就无从得出实施人本来应当承担侵犯责任的结论。
当然,如前所述,对于《专利法》第14条及强制许可相关条款,人大法工委并没有采用“内在理论”的视角,恰恰相反,人大法工委采取了“外在理论”的视角。
事实上,“外在理论”和“内在理论”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应当如何理解专利权及其边界。
“外在理论”强调了权利的本位性,有利于对专利权人进行比较充分的保护,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例外或者限制的情况下,专利权才可能加以减损。
除此以外,专利权人可以依法禁止一切未经许可的为生产经营目的而实施专利的行为。
“内在理论”强调从完整的意义上来理解专利权,强调专利权本身就包含了对于公共利益的尊重,强调了专利权范围的有限性,这些都是相当有益的理解。
但是,在运用这两种理论对法律现象进行分类时,并不应当“各取所需”,随意地运用这两种理论,而应当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
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对于《专利法》第14条,强制许可相关条款及第69条进行定性分类时,应当采用同一个标准。
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人大法工委对于《专利法》第14条及强制许可相关条款所采用的分析工具是“外在理论”,而对于《专利法》第69条所采用的分析工具却是“内在理论”。
这是我国《专利法》第11条“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只出现于第一款的理论根源。
但这样的做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也容易引起混乱。
五、国际法视角下的专利权例外
就条文在《专利法》体系中的作用来看,我国《专利法》第11条是TRIPS协议第28条和第26
(1)条的国内法体现。
这两个条文分别对发明和外观设计的专有权作了要求。
TRIPS协议第28条要求成员对专利权人授予制造权、使用权、许诺销售权、销售权及进口权。
TRIPS协议第26
(1)条则要求成员对外观设计权利人授予制造权、销售权和进口权。
根据TRIPS协议的要求,WTO成员的法律对于发明及外观设计专有权内容的规定,至少应当达到TRIPS协议第28条和第26
(1)条的最低要求。
2000年,我国《专利法》第二次修订时对第11条所进行的修改,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
无论是TRIPS协议第28条、第26
(1)条,对于专有权的设定都是粗线条的。
比如,单纯从TRIPS协议第28条字面上看,临时过境的交通工具中对于专利的使用是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这与各国专利法普遍认可的临时过境例外不相符合。
事实上,《巴黎公约》中就有对临时过境的规定。
TRIPS协议的制定者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TRIPS协议本身在注重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反复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TRIPS协议第7条阐明了制定该协议的目标,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作者与使用者相互受益并且是以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式,以及有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TRIPS协议第8条第1款规定了如下原则:
各成员在制定或者修改其法律和规章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以及在对其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促进公共利益,但以这些措施符合本协议的规定为限。
TRIPS协议第8条所说的“以这些措施符合本协议的规定为限”是大有深意的。
一方面,TRIPS协议制定方充分认可公共利益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允许TRIPS协议成员在国内法中采取“必要措施”,但同时又对这些措施加以限制,要求其符合TRIPS协议本身的规定,就专利制度而言,这些规定体现于TRIPS协议第30条、第31条及第26
(2)条,分别对应发明专利的专有权例外、强制许可及外观设计的专有权例外。
其中TRIPS协议第26
(2)条与TRIPS协议第30条的措辞大体一致。
为了讨论的简化,下文只讨论我国《专利法》第69条与TRIPS协议第30条的对应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TRIPS协议第26
(2)条的忽视。
TRIPS协议第30条规定:
成员可以对专利所授予的专有权规定有限的例外,但是,在顾及第三方正当利益的情况下,这些例外以并未与专利的正常利用不合理地相冲突,而且也并未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正当利益为限。
值得注意的是,TRIPS协议第30条的标题是“所授予权利的例外”。
第31条的标题是“未经权利持有人授权的其他使用”,而第31条的注释则称:
这里所称的其他使用,是指除TRIPS协议第30条以外的其他使用。
这体现出,在TRIPS协议的制定者们看来,协议第31条是对于协议第30条的补充。
从专利权例外的典型性上来说,与TRIPS协议第31条相比,TRIPS协议第30条是更为典型的专利权例外条款。
我国《专利法》第69条中“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与TRIPS协议第30条不同。
TRIPS协议第30条采取的是概括式的描述,而我国《专利法》第69条则采取了列举的方式,但这并不影响我国《专利法》第69条与TRIPS协议第30条的对应关系。
事实上,在TRIPS协议谈判和起草过程中,第30条之行文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1990年6月12日文本(该文本由欧共体、美国、日本、瑞士、5个发展中国家分别递交的5个草案结合而成):
(所授予权利的例外)对于某些行为可以规定对所授予的排他性专利权的有限例外,例如基于先用的权利,以私人和非商业性为目的的行为,以及以实验为目的进行的行为,只要它们考虑了专利所有权人和第三方的正当利益。
该文本所提到的先用权、实验例外,都规定在我国《专利法》第69条中。
此外,在WTO争端解决中,曾发生过著名的“加拿大药品专利保护案”。
在该案中,欧共体及其成员国起诉加拿大,称加拿大《专利法》规定的两个条款,即“行政审批例外”和“存储例外”违反了加拿大在TRIPS协议下的条约义务。
加拿大则以TRIPS协议第30条加以抗辩,认为其《专利法》中规定的这两个例外符合TRIPS协议第30条所规定的专利权例外。
最后,该案专家组认定,加拿大《专利法》中的行政审批例外符合TRIPS协议第30条规定的“三步检验法”,而存储例外则不满足TRIPS协议第30条的要求,因而违反了加拿大应当承担的TRIPS协议义务。
该案所说的“行政审批例外”,在2008年以后的中国《专利法》中也存在,那就是现行《专利法》第69条第五项。
实际上,正是由于“加拿大药品专利保护案”认定“行政审批例外”符合TRIPS协议第30条的要求,很多WTO成员包括中国,在该案发生后,陆续在其国内《专利法》中加入“行政审批例外”。
总之,从TRIPS协议角度来看,我国《专利法》第69条所规定的五种情形都是TRIPS协议第30条所称的“所授权利的例外”,该条文是典型的专利权例外条款。
六、结语
我国《专利法》第14条、强制许可相关条款、第69条都是专利权例外,其中第69条更是典型意义上的专利权例外条款。
《专利法》第11条中所称的“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中的“另有规定”,应当包括第69条。
因此,《专利法》第11条第二款同样应当加入“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之措辞。
正在进行中的《专利法》第四次修订,应当对现行《专利法》第11条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