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docx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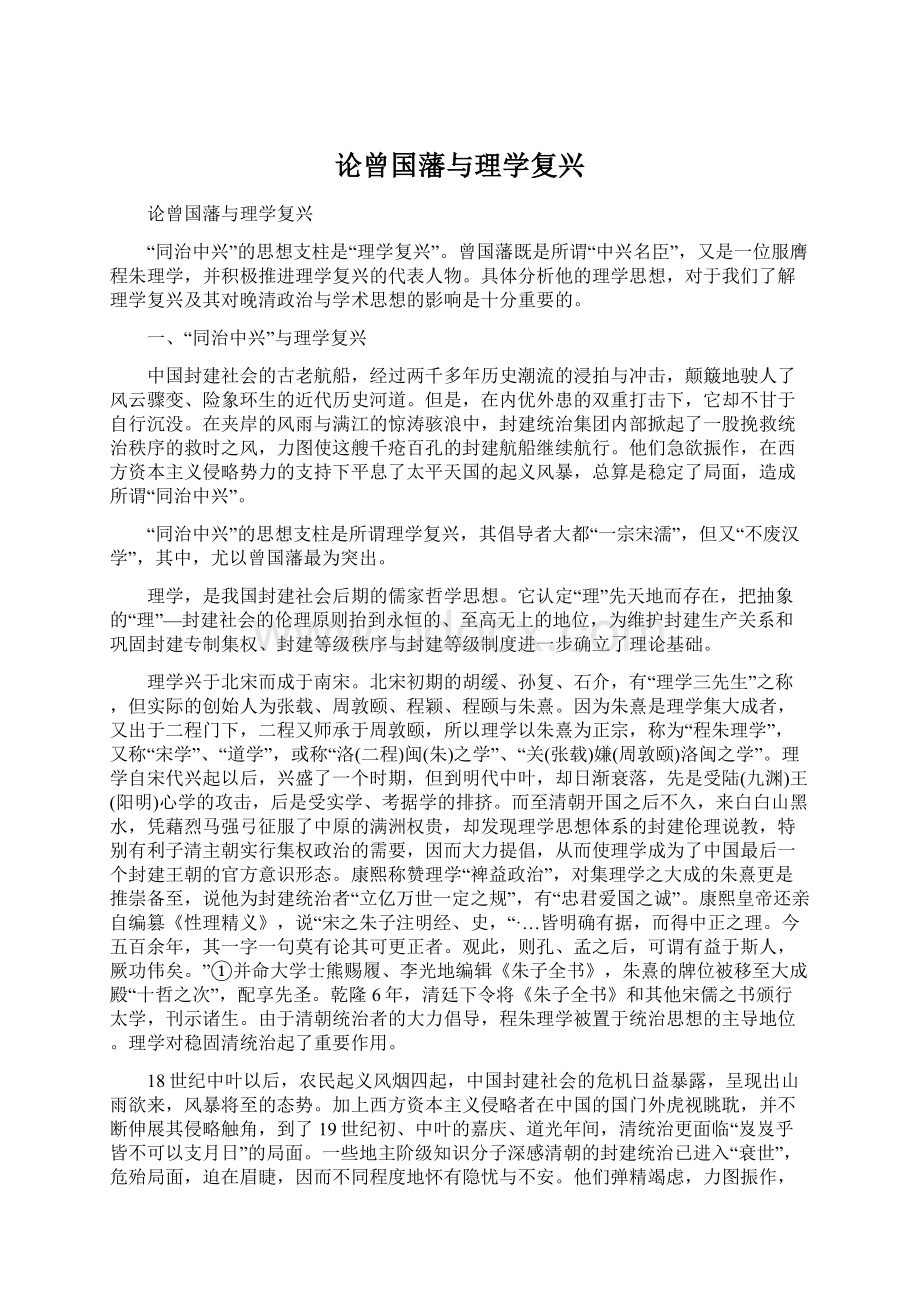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支柱是“理学复兴”。
曾国藩既是所谓“中兴名臣”,又是一位服膺程朱理学,并积极推进理学复兴的代表人物。
具体分析他的理学思想,对于我们了解理学复兴及其对晚清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一、“同治中兴”与理学复兴
中国封建社会的古老航船,经过两千多年历史潮流的浸拍与冲击,颠簸地驶人了风云骤变、险象环生的近代历史河道。
但是,在内优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它却不甘于自行沉没。
在夹岸的风雨与满江的惊涛骇浪中,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一股挽救统治秩序的救时之风,力图使这艘千疮百孔的封建航船继续航行。
他们急欲振作,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支持下平息了太平天国的起义风暴,总算是稳定了局面,造成所谓“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支柱是所谓理学复兴,其倡导者大都“一宗宋濡”,但又“不废汉学”,其中,尤以曾国藩最为突出。
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哲学思想。
它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封建社会的伦理原则抬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巩固封建专制集权、封建等级秩序与封建等级制度进一步确立了理论基础。
理学兴于北宋而成于南宋。
北宋初期的胡缓、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但实际的创始人为张载、周敦颐、程颖、程颐与朱熹。
因为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又出于二程门下,二程又师承于周敦颐,所以理学以朱熹为正宗,称为“程朱理学”,又称“宋学”、“道学”,或称“洛(二程)闽(朱)之学”、“关(张载)嫌(周敦颐)洛闽之学”。
理学自宋代兴起以后,兴盛了一个时期,但到明代中叶,却日渐衰落,先是受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攻击,后是受实学、考据学的排挤。
而至清朝开国之后不久,来白白山黑水,凭藉烈马强弓征服了中原的满洲权贵,却发现理学思想体系的封建伦理说教,特别有利子清主朝实行集权政治的需要,因而大力提倡,从而使理学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康熙称赞理学“裨益政治”,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更是推崇备至,说他为封建统治者“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有“忠君爱国之诚”。
康熙皇帝还亲自编篡《性理精义》,说“宋之朱子注明经、史,“·…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
今五百余年,其一字一句莫有论其可更正者。
观此,则孔、孟之后,可谓有益于斯人,厥功伟矣。
”①并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编辑《朱子全书》,朱熹的牌位被移至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
乾隆6年,清廷下令将《朱子全书》和其他宋儒之书颁行太学,刊示诸生。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程朱理学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
理学对稳固清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18世纪中叶以后,农民起义风烟四起,中国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暴露,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暴将至的态势。
加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国门外虎视眺耽,并不断伸展其侵略触角,到了19世纪初、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统治更面临“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的局面。
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感清朝的封建统治已进入“衰世”,危殆局面,迫在眉睫,因而不同程度地怀有隐忧与不安。
他们弹精竭虑,力图振作,急需思想依托。
这时,坚守封建伦理的程朱理学虽然照旧是受清统治者表彰优宠的正统思想,由清初萌芽发粗的正统汉学(考据学)在思想界也仍然有巨大影响,但是,由于程朱理学主要甚至全部都是内省修身,而极少经世致用的探讨,由于正统汉学严重脱离现实,埋首故纸堆里,所以两者都不能满足某些关心国事民虞的封建士人挽救统治秩序的迫切需要。
出路何在?
因为他们生活的根基仍然是封建生产方式,传统思想文化对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他们谁也不能真正离开旧的基地,完全摒弃汉学与宋学。
这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开罢茶糜花事了”,现实是“满耳号饥寒”,因而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强化封建纲常与中央集权,又能解决封建末世种种弊端的应变哲学(或政治哲学)。
在这种社会氛围和政治需求下,于是有了具有某种新形态、新特点的所谓理学复兴,即既坚守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巩固其在思想界的正统地位,又能对近代危机作出反映,尤其是能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以适应封建末世统治的需要。
二、曾国藩对理学的探研
曾国藩自5岁人塾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到62岁死于任所,50余年中,他博通群籍,泛览百
家,自谓“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埃”②。
门生故吏也说他“无学不窥,默观精要”③。
尽
管如此,但他始终以“一宗宋儒”相诩。
1838年春,曾国藩又一次进京并入仕,在进京前,对理学即有一定根基,在中进士后不久的朝考中则初露头角。
在题为《顺性命之理论》这篇文章中,他对“理”、“命”、“性”等的内涵及其关联的精辟阐述,表现了他对程朱理学的悟性。
为此,道光皇帝亲自将其从一等第三名拔播为第二名,可谓恩宠有加。
曾国藩真正致力于理学的探研,是从阅读《朱子全书》开始的。
1841年8月(道光21年7月),他从京城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回到寓所即认真研读。
为了弄清楚治学的门径,他又登门拜访他的同乡长辈、当时蜚声京门的理学家唐鉴。
唐鉴“潜研性道,崇尚闽洛”,和大学士楼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
曾国藩以前辈之礼事之,虔诚地向他求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④。
店鉴告诉他说:
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⑥,“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⑥。
还说“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
若遐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⑦。
为了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
“为学只有三门:
日义理、曰考核、日文章。
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鑫测。
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矣。
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⑧又说:
“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
”⑨
唐鉴的一番议论,对曾国藩来说,真乃如雷贯耳,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
在拜渴唐鉴前,他只知“寻声逐响”,研习八股试帖,以猎取功名。
自1835年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才由时文而入于古文,“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镊而从之”⑩,并由文学而稍进于知“道”。
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为何物,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
及至他和唐鉴、侯仁交游,尤其是与唐鉴畅谈之后,他才大彻大悟,明白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宗,于是最终确立了以宋学为其治学的基本目标。
这一求道过程,他在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
他在拜渴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在给贺长龄的信中则说:
“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⑩。
在日后写给兄弟的信中,对其治学道路则更有一番总结性的概述:
“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兄弟之先导”⑩。
他决心沿着唐鉴指引的方向,“考信于载籍,问途于亡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⑩,终于成为一名理学大师。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的确下过一番工夫。
这事始于1842年的冬天。
1842年11月3日(道光22年10月初一日),曾国藩又向当时另一位理学大师楼仁请教修身之道,屡仁告诉他:
“‘研几’工夫最要紧。
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
周子日:
‘几善恶。
’《中庸》日:
‘潜虽伏也,亦孔之照。
’刘念台先生曰:
‘卜动念以知几’。
皆谓此也。
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⑩。
还说“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⑩。
最后,楼仁郑重地告诫他,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不宜再因循”O。
这一点,当他向唐鉴求道时,唐鉴也举楼仁的例子,说他“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扎记,或心有私欲不去,外有不及检,皆记出”⑩。
希望曾国藩以楼仁为榜样,在“慎独”上下番工夫。
唐鉴、楼仁的议论,道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
所谓“几”,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或苗头。
“研几”者,即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
通过“自省”,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这扰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的理论。
曾国藩遵循唐鉴、楼仁的教导,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躬行实践,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他不仅格守唐鉴的读书方法,而且按楼仁的要求写所谓修身日记,记录自己种种不符合封建圣道的思想和行为。
例如,他在1842年12月10日的日记记载:
“醒早,沽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
真禽兽矣!
要此日课册何用?
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
尚觑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
”“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
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⑩日记中这类痛自刻责的话语随处可见,表明其理学慎独是如何严格。
他还为自己订立一课程表,规定每日必须做到:
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刚开始静坐很不适应,每坐片刻即昏然入睡,等到醒来,半夭已经过去。
为此他常常是气恼交加,在日记中痛下决心,要从头开始。
这样反反复复,经过十余天才逐渐适应。
但是,曾国藩原本体质居弱,自从修练这种“圣贤工夫”,刻刻留心,无时不俱,结果弄得精神紧张,心理压抑,郁郁寡欢,甚而咯血,再也无法坚持。
既要效法圣贤,立志自新,又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理学家修身养性的方式达到理想境界,这就成了曾国藩在“悟道”途径上的两难选择。
曾国藩在苦苦地思索。
他在咯血病后不久致诸弟信中说:
“夭既限我不能苦思,是夭不欲成我之学问也。
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⑩。
但是这个“打脱牙和血吞”的刚烈汉子并没有从此就放弃了对理学的追求。
在同信中,他又说: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
是故经则专宗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谈经史则专主义理,此则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⑧。
这些话表现了他对理学一往情深,坚定地认为理学在儒学的全部文化领域中具有核心地位与支配作用。
但是,经过前段时间的躬行实践,他感到理学家那套“修己”工夫与治学方法终究不适合自己。
客观环境和曾氏的主体素质推动他在理学迫求上的改弦易辙,另辟蹊径:
一是将探研理学的主要目标定在领会其精神实质,即所谓“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庚”,不再盲目效法他人练“静”字工夫;二是治学内容以理学为经,博采众说;即使治理也不仅限于《朱子全书》,还兼顾宋代其他理学家的著作。
这种变化,使曾国藩迈出了理学经世途程中关键性的一步。
他以明确的目标,轻松的心态,徜徉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海洋之中,力行从墨子,刑名重法家,静虚学黄老,词章崇古文,从各种文化学术流派中撷取精萃而集之于理,从而在学术见解、道德修养和政治思想上都步入了一个新境界。
如果按照理学家关于“研几”和治国相通的思维逻辑,我们可以理解,动荡不安的封建衰世,是不可能让曾国藩定在“圣贤工夫”境界之中的。
远大的抱负同拘谨的自省,在他的心灵深处不断地冲突着,搏击着。
这也许是这位休气屏弱而性格刚强的卫道者心理燥动,不能自制,以至咯血成疾的精神根源。
三、曾国藩对理学的贡献
曾国藩在晚洁诸多理学家中,带有几分“改革”色彩。
他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使理学与经世思想结合,为这门在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衰微的理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
曾国藩在理学复兴中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恢复理学的经世功能,在原有义理、考据、辞章之外特别加上“经济”一门,使理学与经世之学达到合谐的统一。
曾国藩服膺程朱理学,宣称他“一宗宋儒”,但同时又“讲求经世之学”。
薛福成赞扬说.“盖自公始于朝,即侃侃言天下大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柜”,。
他一变理学家的传统,抛弃了理学只讲心性的空疏、迁腐的学风,不仅大力发挥理学维系封建纲常的作用,而且特别注重恢复理学的经1让功能。
为了从理论上强调理学的经世功能,曾国藩不同意唐鉴、姚勇、戴震等学者关于为学只有三种学科的分类。
如前所述,唐鉴对曾氏谈过“为学只有三门”,“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的见解。
曾国藩不甚满足,曾问道:
“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
”⑩由此可见,曾国藩那时已特别关注“经济”,他虽然同意唐鉴的“经济不外看史”,但却不同意他把“经济”包融在“义理”之内。
他要打破三种学问的旧说:
“为学之术有四:
曰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
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
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
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并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
他把“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的见解,超越了唐鉴等理学大师,突出了理学经世功能。
“经济”,意谓“经世济民”,它当时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实用学科领域,与今天的经济一词有不同的内涵。
曾国藩把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目的是为了转移世风,力图使传统思想文化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和社会。
为此,他一生躬身实践,不尚虚文。
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
于山川险要、河潜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⑧。
他曾上疏清廷,主张按经世治国的能力来考核人才,“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黝浮”⑩。
至于倡办洋务,更是这种统一的集中体现。
他说: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若在我者,抉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亦罪也,德之亦罪也。
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曾国藩的自白,既概括了洋务运动的总目标,也反映了他的思想突破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唯一目标的理学范围,而把经世之学与理学和谐地统一。
这种统一,是从晚清政治思潮的一个侧面,或者从统治集团的一个派别,反映了其在时代冲击下的应变要求。
第二,提倡汉宋交融,以汉学充实宋学,弥合两者的矛盾。
如果说复兴理学的经世功能是地主阶级经世派在时代变动中的思维转向,那末,弥合汉宋矛盾则是这种转向的逻辑延伸。
为了经世应变,而调整和统一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与学术思想。
汉学又称朴学,原指汉儒考据训话之学,是与宋学相对的一个儒学流派。
汉学以儒家经典作为说经者的对象,为经书中的名物、制度作注释,它与以性、理解经的宋学迥然不同。
两派“互为胜负”,门户森严。
曾国藩以理学为其言行的依归,但是却“不废汉学”,对汉宋之争持批评态度。
他在复夏搜甫的信中说: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话之学者,薄汉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⑩。
他对汉宋两派断断未已,不无讥讽,说他们“屏弃群言以自隘”,是“殊妹自悦”的”斗答者”⑩。
他企望汉宋交融,“综合一归”,共同担负起救时的重任。
曾国藩治学就不固闭自守,认为汉学与宋学可以相互沟通。
在上引信中,他阐明了自己的宗旨:
“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
必从事《礼经》,考盛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宝应讨论之事。
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顿息渐诸说之争”⑩。
这就是说,学术原有“博通”、“精深”两种学凤,是相辅相成,互补为用的,必须先具备博通的知识,始能为专经之用,这就是“由博返约”。
反之,又必须具备专精之功,才可能成博通之才,这就是“由约返博”。
他力主治学应由博返约,格物正心,由理学而汉学,提出人人应学习礼经,以礼为归,因为礼学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
曾国藩与汉学家刘传莹的交往,可视为汉宋交融的例证。
在1846~1848年,曾氏与刘传莹时相往来,切磋学问。
曾国藩深受汉学的影响,刘氏也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中受到莫大启示。
由相互影响而融会贯通,两人都豁然而知为学须反本务要,义理、考据、词章各有是非,应互相补充,恰当运用它们的长处,固闭自守,偏执其一是不足为训的。
曾国藩称颂刘传莹的学识说:
“汉阳刘传莹椒云实究心汉学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笔宋贤,闲尝谓余:
‘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
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则当一一详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以’。
又日:
‘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国藩则大匙之,以为知言者徒也”。
。
“君之为学,其初熟于德清胡渭、太原阎若檬二家之书,笃嗜若渴,治之三反。
既与当世多闻长者游,益得尽窥国朝六七矩儒之绪。
所谓方舆、六书;九救之学,及古号能文诸者之法,皆已规得要领。
“一君自伤少年赢弱,又所业繁杂,无当于身心,发愤叹日:
‘凡吾之所为学者,何为也哉?
取孝弟与之不讲,而旁鹜琐琐,不以滇乎?
’于是痛革故常,取镰洛以下切己之说,以意时其离合而反复之。
·“…尝语国藩:
‘没世之名不足较,君子之学,务本焉而已,吾与子敝精于雄校,费日力于文辞,以中材而谋兼人之业,檄幸于身后不知谁何者之誉,自今以往,可一切罢弃,各敦内行,没齿无闻,而誓不后悔”@。
曾国藩对此深表敬意和赞同。
这里表面上看是刘传垄由汉学而人于宋学,实际上乃曾国藩由宋学而入于汉学。
他们殊途同归,从两端汇合归一,所谓“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对于身、家、国三者,都应详核而求其是。
其意义是以考据为方法,而达到义理的境界,最后折中于礼,使汉宋矛盾得到统一。
第三,强调“礼”的地位,认为经世之术就是以礼治人。
在曾国藩看来,沟通汉宋的理论根基是礼。
“仁”与“礼”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常为人们相提并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曾国藩说: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
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O。
在他看来,仁是内在的思想情操修养,礼则是外在的社会行为的规范。
仁的极致就是“民胞物与”,民物的大体同于一源—理。
所以曾国藩说:
“幽以究民物之同源”⑧。
“仁”与..tLj,也同样为曾国藩所看重。
程朱理学对儒学的礼作了透彻的阐述。
礼则理也,“理”与“礼”是相互贯通的。
理即天理,乃事物至高无上的准则。
礼是理的外部表现,在人事上,体现为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伦理,是人们“以礼自治”的准则;在政治上,体现为以礼为中心的封建“礼治”,即“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O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秩序。
礼的根本目的即在于此。
所以曾国藩说:
“礼显以纲维万世,弥世乱于未形”0。
正因为礼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尤其重视对礼与礼学的阐幽发微,他说: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
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
又说:
“先主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
亦曰礼而已矣”⑩。
曾国藩对礼学的见解具有发孔学义蕴的意义。
他认为礼学实乃“经世宰物”之学,是儒学四种学科的综合体,是“不可以一方体论的”。
它体大思精,故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
应当指出,曾国藩所谈的礼与礼学,在更大意义和范围内是指经济之学与经世之术。
他说: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
《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桨座市巫卜缮臭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⑩,又说:
“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
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
苟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
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
秦惠田氏辑《五礼通考》,”一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赅,则来为失也”⑩。
曾国藩对于礼学就是古代经l珍之学的源流、功用以及范围在这里详论无遗。
所以,曾国藩认为,学礼就是学“经世之术”。
曾国藩在晚清理学复兴中,基本上是继承而较少独创性见解,但重要的是他能在社会急邃变化,改革思潮已见端倪的时代,敢于对流于空疏的理学的基本观点作出新的发挥,注人实际内容,弥合汉宋矛盾,力求使汉宋这两个儒学流派共同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理学复兴满足了清统治的需要,成为“同治中兴”的思想依托。
曾国藩也因此成为“理学复兴”的代表和“中兴名臣”。
当然,理学经世从总体上讲,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幕里,一部分统治阶级当权派对于时代变动的典型传统式回应,其思想方向还没有超越以“修齐治平”为核心的一套古老的经世条目。
所以,这种“经世”不可能达到他们预期的“中兴”。
1869年,垂暮之年的曾国藩又到了京师,他看到的是洋人猖撅,政局腐败,民生萧索。
这位毕生为“中兴”奋斗的名臣,面对紫禁城的黄昏,其心情悲凉是可想而知的。
近代地理学的传播与中国中心观念的嬗变
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地理和文化的中心,这种中国中心观念阻碍了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和其他文化的热情,同时也抑制了中国地理学和文化的发展。
明末清初西方近代地理知识由传教士带来,中国中心观在少数开明之士中间开始有所动摇,但这点星星之火很快就被旧有的势力扑灭。
中国近代,列强的枪炮逐渐打消了天朝的自大,人们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局势和各国文化知识,由此形成了一股贯穿整个近代史的学习地理学的热潮,地理学被认为是诸学科之基础。
中国近代思想家大多都是从地理学开始了解、并且进而宣传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地理学在他们有限的西学知识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地理学中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所蕴含科学精神对中国中心观的嬗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古时由于地理学水平低下,人们往往认为大地有一个中心点。
中国古代关于大地的学说主要有盖天说和浑天说两种。
盖天说认为大地是平的,浑天说虽认为大地是球形的,但认为人只生活在上半球,所以这两说所描绘的模型中都有一个中心,中心就是中国。
至于具体在中国何处,尚有争议,主要有昆仑地中说和阳城地中说两种说法。
在西方,人们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地球说,根据所知道情况,认为陆地在北半球,中心在耶路撒冷。
由于古代人涉足和交流的范围较小,所以远方的地理和文化情况只好凭传闻和想象填充。
因此,许多民族在一定时期都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和地理为中心的意识。
除古代中国外,古代希腊、罗马、印度、泰国等许多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国王居住于大地的中心,是宇宙的主宰。
西方近代地理大发现,和万有引力理论的问世,使得人们抛弃了地理中心说,理解了全球皆可居人的现象,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使得文化中心观也发生了动摇,多元文化观渐渐兴起。
当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东亚大地正在沉睡。
中国在西方列强用枪炮叩开中国大门之前,始终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位置。
传统儒家力主严“夷夏之防”,但更主要的是要“用夏变夷”,即以儒家文化归化中原周围的部落民族,而万万不能“用夷变夏”,所以虽时有亡“国”,但未亡“天下”。
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中心的观念日益坚定,代代相传,这有碍于对其他文化的学习,所以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注定是困难和漫长的。
鸦片战争后西学传入,人们知道:
一个民族在政治文化上充满自信时,就会称自己为“中国”。
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说:
“释典言佛降生,必于大地之中……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
……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
”[1](P1849)这对当时视中国中心观为天经地义之说的士大夫们是一个打击,原来世界有那么多文化,且各家典籍都自称“中国”。
中国在列强面前一次次败北的惨痛经历,使得士大夫们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灿烂的文化。
他们在经典中寻章摘句考据的功夫渐渐用不上了,因为即使连篇累牍,也将只是一家之言,中国中心观需要更多可以以理服人的证据来捍卫。
二中国地理中心说面临的最有力挑战就是“地球说”(不是只有上半球居人的浑天说,而是全球居人的西方近代地球说),近代中国人对待地球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一些有科学造诣的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人像他们的科学前辈徐光启、梅文鼎等一样顺利接受了地球说。
可能是西方地圆说所持的理由(比如:
向北行进可以见到北极星的地平高度增加、远方驶来的船先出现桅杆之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