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docx
《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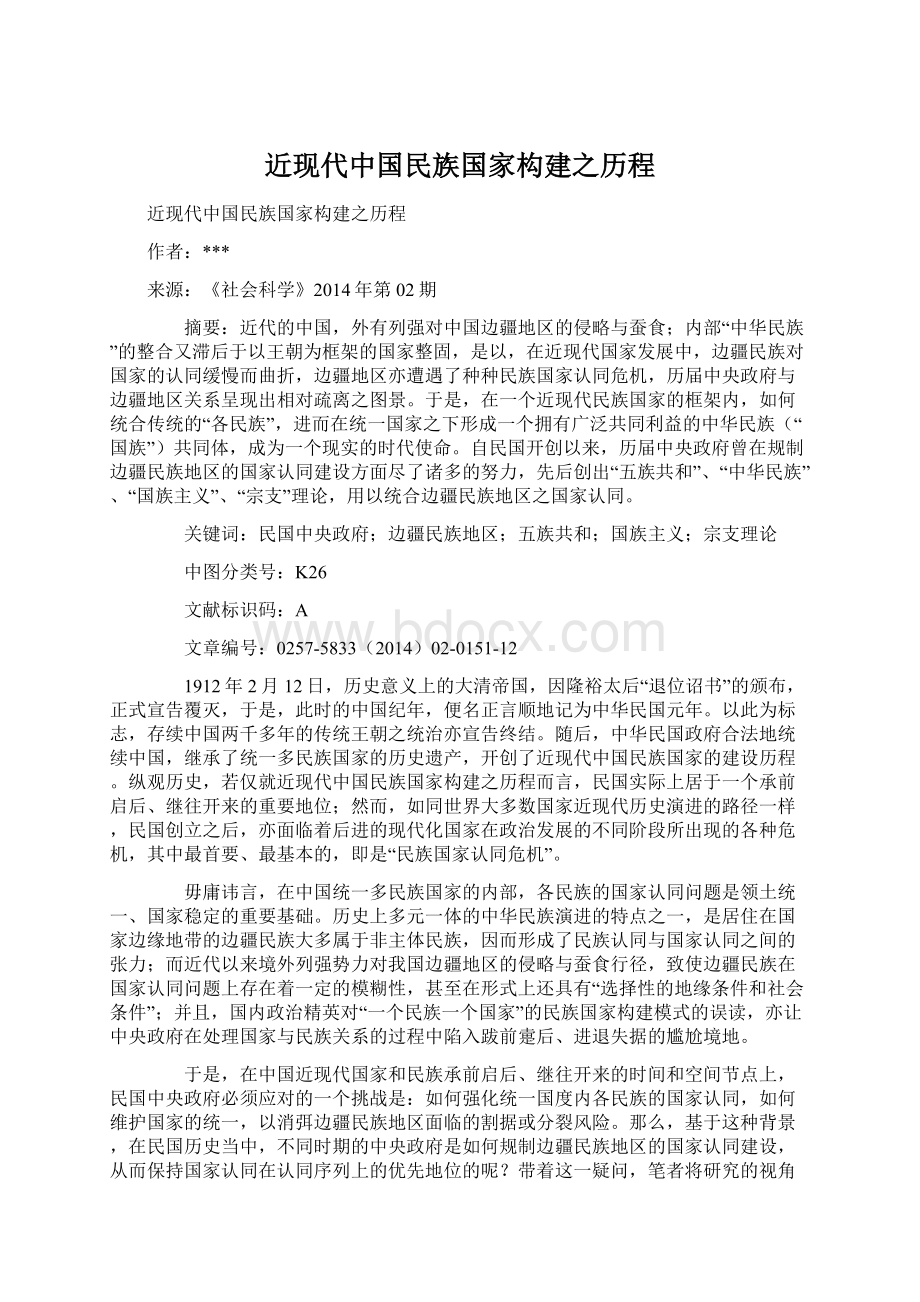
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
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
作者:
***
来源:
《社会科学》2014年第02期
摘要:
近代的中国,外有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与蚕食;内部“中华民族”的整合又滞后于以王朝为框架的国家整固,是以,在近现代国家发展中,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缓慢而曲折,边疆地区亦遭遇了种种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历届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关系呈现出相对疏离之图景。
于是,在一个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如何统合传统的“各民族”,进而在统一国家之下形成一个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国族”)共同体,成为一个现实的时代使命。
自民国开创以来,历届中央政府曾在规制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方面尽了诸多的努力,先后创出“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国族主义”、“宗支”理论,用以统合边疆民族地区之国家认同。
关键词:
民国中央政府;边疆民族地区;五族共和;国族主义;宗支理论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4)02-0151-12
1912年2月12日,历史意义上的大清帝国,因隆裕太后“退位诏书”的颁布,正式宣告覆灭,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中华民国元年。
以此为标志,存续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王朝之统治亦宣告终结。
随后,中华民国政府合法地统续中国,继承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遗产,开创了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历程。
纵观历史,若仅就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而言,民国实际上居于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然而,如同世界大多数国家近现代历史演进的路径一样,民国创立之后,亦面临着后进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各种危机,其中最首要、最基本的,即是“民族国家认同危机”。
毋庸讳言,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各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是领土统一、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
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演进的特点之一,是居住在国家边缘地带的边疆民族大多属于非主体民族,因而形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而近代以来境外列强势力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与蚕食行径,致使边疆民族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甚至在形式上还具有“选择性的地缘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国内政治精英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的误读,亦让中央政府在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过程中陷入跋前疐后、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于是,在中国近现代国家和民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间和空间节点上,民国中央政府必须应对的一个挑战是:
如何强化统一国度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以消弭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割据或分裂风险。
那么,基于这种背景,在民国历史当中,不同时期的中央政府是如何规制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从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的呢?
带着这一疑问,笔者将研究的视角触及民国中央政府统合边疆民族的理论构想和制度安排。
基于此切入点,本文研究的主旨是,将特定条件下拥有重要政治地位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合理念作为考察对象,从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民族国家认同与统合的角度,探究此期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之关系,检讨此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合历程及构建边疆民族地区之国家认同问题。
一、从“五族共和”概念到“中华民族”理念
18世纪以降,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整个西欧乃至整个近现代世界典型和主要的国家形式。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亦认为,“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不同于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等等时代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能最容易完成其任务的国家形式”。
显然,仅从实现国家职能和提高社会效率的视角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国家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形式。
然而,诸多研究表明,中国历朝的古代国家和近现代民族国家(modemnationstate)虽有承前启后的继承关系,但在体制和内容上有诸多的相异。
直至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才在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对峙中,开始逐步将其版图整合到一元化的中国(中华)之中,通过同构型、排他性领土主权的确立,试图将传统的“天下中国”概念调整为近代民族国家。
自是,近代中国开始模仿欧、美、日各国,将民族国家构筑的终极目标亦设定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这一政治诉求意味着最终否定居民(或臣民)中的族群多样化与文化多样性,希冀将整个版图上的居民(或臣民)铸造成国民,并使其统合于一个“民族”(国族)之下。
但是,受制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清统治者对民族国家的整合并不成功。
例如,北方外蒙古等边疆地区,临近辛亥革命之际,外有沙俄的蚕食与蛊惑,内有朝廷“新政”引发的某些负面作用,当地部分民族上层对中国国家认同之态度出现游离。
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中的先贤们目睹朝廷的无奈和无措,遂各自对中国民族国家之未来做了设计。
它们围绕未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提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革命派从推翻清朝“满族”统治出发,结合传统的华夷观和西方的民族建国理论,提出“十八省汉族建国理论”;而立宪派在论争中认识到了革命派建国理论的缺陷,遂提出“建立多民族的近代民族国家”理论。
此两种理论之间的争执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的爆发。
其时,革命派率先提出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口号,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即是:
“哪些人才是中国人?
”在革命派看来,中华民国应当是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所说的单一民族国家,不少革命派主张“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
由此认定:
在未来的国家构建中,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被汉族同化:
“夫一国之中,数种杂处,不相为谋,而唯利是竞,其非福也明矣。
于是欲求解决之方,不出二途。
其一即为同化……其一则为分离……故革命者,所以解满汉之倾轧,或与割然分离,或遂相同化,皆有利而无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在文章和演说中亦有强调恢复汉族政权的内容,在未来国家设想中忽略了其他民族的政治地位,强调未来的中华民国,“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二元论性质。
一方面,试图通过创建民族国家来振兴中华民族;另一方面,又无法改变中华民族整合滞后的局面,在理念上无法摆脱种族民族主义因素,在清朝贵族集团专制统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倡导创建民族国家必须通过“驱逐鞑虏”来实现。
在革命的发起阶段,以“驱逐鞑虏”为核心的“革命排满”口号被放大了许多,较之其国家主义因素来得更为强势。
不可否认,这种强势的种族民族主义,起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效果,对于推翻清朝统治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对于建设一个统一多民族的近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其功能却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辛亥革命初期,内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
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中所包含的剔除东北、内外蒙古、新疆与西藏,在内地十八行省恢复汉人地盘的理念,对边疆政治现实的冲击更是显而易见的;在此理念下,内地的独立是脱离清政府,则边疆的“独立”意味着要脱离内地中原。
对于初创的民国政府而言,从国家治理的立场出发,首先必须维持构成国家要素的领土、主权、人民合而为一的三要素。
作为执政者,彼时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
民国欲继承清帝国的主权、国民与领土,必然涉及“驱逐鞑虏”问题,即涉及东北三省、内外蒙古与西藏等边疆地区是否归属民国的问题。
与此相悖的是,革命党人既然把民族和种族等同起来,就很难反对日益发展的外蒙古独立运动及“独立的蒙古国”的建立,亦无法应付西藏和新疆的危险局面。
正是在这严重的边疆危机和国家分裂危险面前,民初中央政府在统合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方面率先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模式;其次,在具体操作层面,从政治制度建设、权益让与、文化教育等层面,以培育国民认同。
于是,一贯被革命党排斥的“五族共和”口号便被孙中山等人拾了起来,几乎原封不动地加以运用。
历史的演变有时候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的革命党人在政治实践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反而成了自己的政敌——梁启超学说的实践者。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
”随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亦发布命令曰: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
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画,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
”是为时人所谓“五族共和”之思想。
“五族共和”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其功效彰显于一时;但同时亦应看到,“五族”之说未必能够涵盖民国政府辖下中国的所有民族和地区。
对此概念,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异议:
“依近世学者之说,谓中国原始之住民,实为苗族。
……而苗族独不得厕于五族之列,所谓共和,果如是乎?
故我以为不举种族之名词则已耳,苟言及种族,则必日六族共和、六族平等,不得仅以五族称也。
”时任护理西藏办事长官的陆兴祺亦在致民国政府的电文中提到:
“且有廓尔喀者,本一极富强之小国,向修贡职,尊中土为上国,目前尚极恭顺。
此次藏乱,廓人调停之力,亦颇不鲜。
惟谓廓人心中有一疑意,中国动称五族共和,不知廓人究属何族。
盖廓人所奉者回教耳。
如为回族,则土耳其亦回族也,亦可列于五族共和中耶?
”上述犀言直指“五族”口号的局限性,认为此说间接造成了中国内部“五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亦模糊了此间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以故,对“五族”概念做进一步的阐述和提升实属必要。
“五族共和”的口号具有明显的缺陷,袁世凯本人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可从他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往来函件中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可见端倪。
显然,作为政治家的袁氏,他可能较注重于操作层面的实用性,至于理论上的建构尚需由学者来完成。
在这一方面,梁启超的追随者、《庸言》杂志的实际主编吴贯因先生提出“融合五族为中国民族”的理念,具有相当的创见。
1913年初,他在《庸言》上发表了《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地论证了五族的“混合性质”,进而说明了各族之间血统互相渗透融合的历史。
为此,吴氏建议:
“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Nation,而Nation之义既有二:
一日民族,一日国民,然则今后我四万万同胞,称为中国民族也可,称为中国国民也亦可。
”其中的中国民族、中国国民融合说,对于当时和后来“中华民族”的统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中华民族”的理念在处理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上层的关系中得以确立和应用。
可以这样认为,辛亥革命使“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学说从最初的思想理念变成了政治实践,因革命而昌盛的“五族共和”观念作为初创的民国政府整合中央——边疆地方的思想,形成了当时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边疆地方对中国民族国家之认同的重要动力,并一直影响着中国之中央——边疆地方政治关系的演进。
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来说,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二、孙中山创建“一族一国”的“国族”理念
民初中央政府建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国民族国家主义运作比较典型的时期。
从民族——国家统一体的角度看,于对外层面,国家是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维护、争取国家利益就是为了民族利益。
任何国家代表都应是其民族利益的代表;但在对内层面,一个国家之内,两者未必能够等量齐观。
国家表现为行政、立法、司法等具体的组织形式,民族则幻化为由其领导的社会大众。
政府的意志能否代表大众的利益,则得由具体的制度及历史情势决定。
以袁世凯政府为例,当它派出代表参与西姆拉或恰克图会议,与英俄等代表展开交涉,力图维护国家主权之时,显然,这时候民族——国家之利益是一致的;相应地,当它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口号,以武装力量介入为前导,无视蒙古族王公贵族方面的合理要求,强力推进,实现内蒙古的地域统合,确立中央集权支配体制,则这时候民族——国家双方的利益是背离的。
由此亦可蠡测,民族国家主义是一体的两面,它承载着民族、国家双边利益,但它又容易在具体的情境下分离为互为割裂的两面:
有时候它可能演化为全能的国家主义——盲目地强调贯彻国家意志;有时候则蜕变为单纯的种族民族主义——狭义地呼吁维护某一民族的特别利益。
彼时,无论是中央政府的权首,或是掌控一方的地方政要,大都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近代民族国家主义必须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偶像与附着物。
换言之,近代民族国家主义只能效忠于近代民族国家。
正因为如此,在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必然会存在一种国家全能化的倾向。
袁世凯上台以后,他从国家、民族、政府、国民的统一性出发,选择在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中强化“政府”这一要素的权力,而加强政府权力又内化为强化国家政府首脑的权力,即表现为加强袁世凯个人权力。
至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内部各派系心怀私念,致使争权夺利的内部政争甚至超越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意识。
此间,虽然不同的经营集团都曾表达过相似的民族国家主义言词和目标,但是,即便当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之时,中央政府自我削弱的内部政治冲突依然持续,而对于边疆地方利益的诉求考虑相对较少,以“五族共和”名义颁布的各种边疆民族待遇条例并未得到切实的施行。
在时人看来,民初以来用于统合边疆民族乃至全体国民的“五族共和”以及“中华民族”理念,似已陷入名存实亡之状态。
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的演讲中亦不无失望地指出,“五族共和”实为一种欺人之语,这在事实上否定了此前民国中央政府抱持的边疆民族统合理念。
既然旧有的理论在统合边疆民族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缺陷,又抑或在实践中业已被异化,那么,构建一种新的理论实属必要。
其时,孙中山对此问题的具体构想是,“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融合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一个中华民族”。
1923年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提出将“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理念应用于多民族的中国,“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
在同年颁行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则开宗明义地规定:
“民族主义:
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
”据此可见,这一时期,孙中山仍然怀有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倡导“大熔炉”的民族整合路径。
然而,应当认识到,他以“国父”威望,提出整合中国民族、构建一个统一“中华民族”的理念,并将之贯彻于政治实践当中,已是在吴贯因“中国民族、中国国民融合说”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
毋庸置疑,其对于构建一个“中华民族”的远景目标不无积极意义。
如果说,1910年代孙中山的民族国家理念经历了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然后再到以汉族为中心的“大中华民族国家”之演进,那么,时至1920年代,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构建理念又有了新的衍变。
1924年,孙中山在“民族主义六讲”中正式创出了“国族理论”。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作了理论分析。
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但与此相抵牾的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致使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正因如此,中国人眼里只有宗族利益,没有国家观念,而对于国家,则没有相应的牺牲精神。
基于此诸状况,孙中山倡言,要塑造一个统一的“国族”。
至于其操作路径,他提出了一条与传统中国“家国”观念具有类似逻辑的理路,即用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族——宗族”观念作为较小的基础,用以整合国族观念。
孙中山对此理论作了推演,他说:
“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人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
”如此一来,必将在原有的松散的宗族团体之基础上,结合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
在其看来,“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
“国族”概念的提出,就理论意义而言,乃是为解决中国民族与国家之间二元关系而提出的制度构建,力图化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用以促使二者达到和谐的统一。
不言而喻,在国族构建的征途中,亟需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存异求同”,即要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建立国族文化,强化国族意识,统一国族身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族固然是民族,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而是由国家倡导、并与国家统合于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
此外,就实践意义而言,“国族理论”之要旨,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大中华民族国家”,更是为了从意识形态层面化解当时中国面临的边疆民族危机,间接地利用“单一国族”的同质性来统合“多元民族”的异质性,用以消除当时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对多民族中国带来的“拆分性”风险。
1924年前后,围绕外蒙古是否具备“独立”或“自决”资格问题,国内不同政治派系的代言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这场论战中,论者谈论得最多的是,倘若遵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建国模式,外蒙古是否可以实行“民族自决”。
随后,民族自决是否适用于蒙古,复细化为如下子命题:
其一,通常所谓“self-determinationofnations(民族自决)”中之“nation”,究指“民族”抑或“国家”;其二,蒙古是否系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是否有“绝对的自决权”。
就在各派系代表学者聚讼不休、争论纷纭之际,孙中山“国族”理论适时创出,成为影响论战之关键性因素,它推动了国内舆论之逆转,促使所谓赞同外蒙古“民族自决”之派系因以偃旗息鼓。
依照时人理解的“民族国家理论”,国族认同指称的应当是社会成员“国”、“族”身份的同一性,其所认同的、具有法理性的国家应与本民族或族群身份完全重叠,从而建构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亦即坚持“国家疆界”和“民族或族群整体的地域”相统一。
设若依照这种理解,孙中山所言的“国族”,就其本初所指,应当是一个与中国国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能够重合、统一,并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华民族。
然而,诚如孙中山本人所言,“大凡一种思想,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不能说是好不好,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
在民族国家构建层面,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服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活动,焕发着实用主义的色彩。
事实上,由于孙氏所能控制的政治区域范围仅及于两广一带,故而其提倡的“国族理论”及其演绎的“家族宗族”路径,从其适用范围来看,显然主要是为了统合汉民族内部之各自然的、血统的“宗族”,然后成一同质性国民身份,对彼时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大部分族群而言,并没有与汉人类似的“宗族”概念。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大致经历了“排满建国——五族共和——(汉族中心的)中华民族——(家族、宗族的)国族主义”的演进轨迹。
然而,这并不是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了一套前后贯通的严密体系。
从1924年孙中山逝世前发表的演讲稿中可以观察到,这种变动的轨迹,绝非简单的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
至少在这个时期,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根基中仍有汉族中心主义的思想。
亦应看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包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外壳多有变化,但“光吾国而发挥种性”的内核始终保持不变。
自从事革命事业起,直至溘然去世,孙中山一直秉持民族主义思想,且构建一个“国族”的理念一直萦绕其左右。
正因如此,以孙中山研究见长的美国学者史扶邻认为,“乍看起来,孙氏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其实,在这里我们仍可以发现他的目的基本上是前后一致,始终不变的”。
其时,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在对外一层,由于与反帝废约运动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包含着强烈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意识,对唤起中华民族的独立意识具有较强的动员作用;在对内一层,对于回应边疆民族地区所谓“民族自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出于政治继承性因素的考虑,亦继承了孙中山的“国族”理论。
三、蒋介石“宗支理论”之构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中国东北边疆,构建中华民国“近代国家”之组织,团结全体民族(国民)组成统一抗日战线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号召。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
此时的外蒙古、新疆、西藏等诸边疆地区面临种种危机,并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及前苏联民族自决主义之冲击,随时有可能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边疆地区卷入“肢解化”的境地。
鉴于上述状况,中国政治界、知识界的精英们开始检省既有的边疆民族政策。
当时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在现有的中央政府边疆民族政策之下,往往将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纠合在一起,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顿,基于此,应当树立新的民族政策,在制度设计范畴可将现有的专门处置边疆民族事务的行政机构——“蒙藏委员会”予以调整。
其时,有一种见解认为,应从国家利益的全局上来认知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
有论者撰文指出,蒙藏委员会成立后,致使国人对边省的认识是,只知有蒙、藏问题,造成“一种畸形及恶劣的现象”:
第一,蒙藏本来没有骚乱或变乱,煞有其事宣抚,反倒产生问题,若无彻底办法或合理政策,宣抚并无效用;第二,过分重视和骄纵蒙藏民族,以致奔走活动的蒙藏人士出现背离国民统合的趋向,比如,由用汉姓又改蒙姓,由不会蒙语文字重新学习蒙语蒙字,由习用边省籍贯改用蒙古籍;第三,使蒙人脱离旧日所属各边省同乡关系,“另以种族单位来组织蒙古同乡会”,反倒形成汉、蒙间的民族斗争。
上述所谓的“畸形及恶劣的现象”决非妄谈或想象。
据时人观察,包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分校的蒙古族学生,“昔多以改用汉姓为荣,今日则多用蒙文汉译姓名”。
改用蒙文汉译姓名,可谓乡情之举,未必招致离贰,本不必过于在意,但汉族精英从“它者”的视角看待,则认为其中隐藏着边疆民族意识勃兴的内在成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消解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己力量。
为此,对于今后国民政府应当采取何种边疆政策的问题,该氏建议中央政府应着重培育各民族从“片面的种族思想着想”到“整个国家利益上考虑”的理念转换,同时,将蒙、藏民族与汉族一视同仁,“务使各族间造成政治上、经济上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不使形成一族的单独生活关系”。
另有论者从淡化“民族”的角度考虑制度层面的边疆民族政策,提出用“行政区域的统合”替代既有的“民族的统合”,以期解决日渐凸显的边疆民族问题和日益深重的中华民族生存危机。
萧铮即呼吁,将来全国应当只有省域的区分,而无各小民族特立独行、界限分明的景象,“如果有人以民族口号来划分,那便是历史的倒退!
也就是世界大同的障碍”!
此种观点得到了一般社会精英的认同。
有论者撰文呼应,认为化除民族畛域确是实现民族平等最为切要的途径,汉、满、蒙、回、藏、苗、夷等皆为历史名词,历史上各族的相互斗争使人触目此类名词而引起狭隘的民族观念,为此,中央政府应在名义上避免使用某某族字样,但中央或地方立法机关应设法使各民族产生议员代表该族利益。
亦即在名义上取消民族之区分,但在立法上应予适当的倾斜,以维护边疆民族之利益。
受上述讨论之推动,至1939年前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学科的前沿学者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探讨了构建一个能够得到全体国民认同的“国族”的可能性。
至于其名称,“中华民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