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oseforEmily完整版译文.docx
《ARoseforEmily完整版译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ARoseforEmily完整版译文.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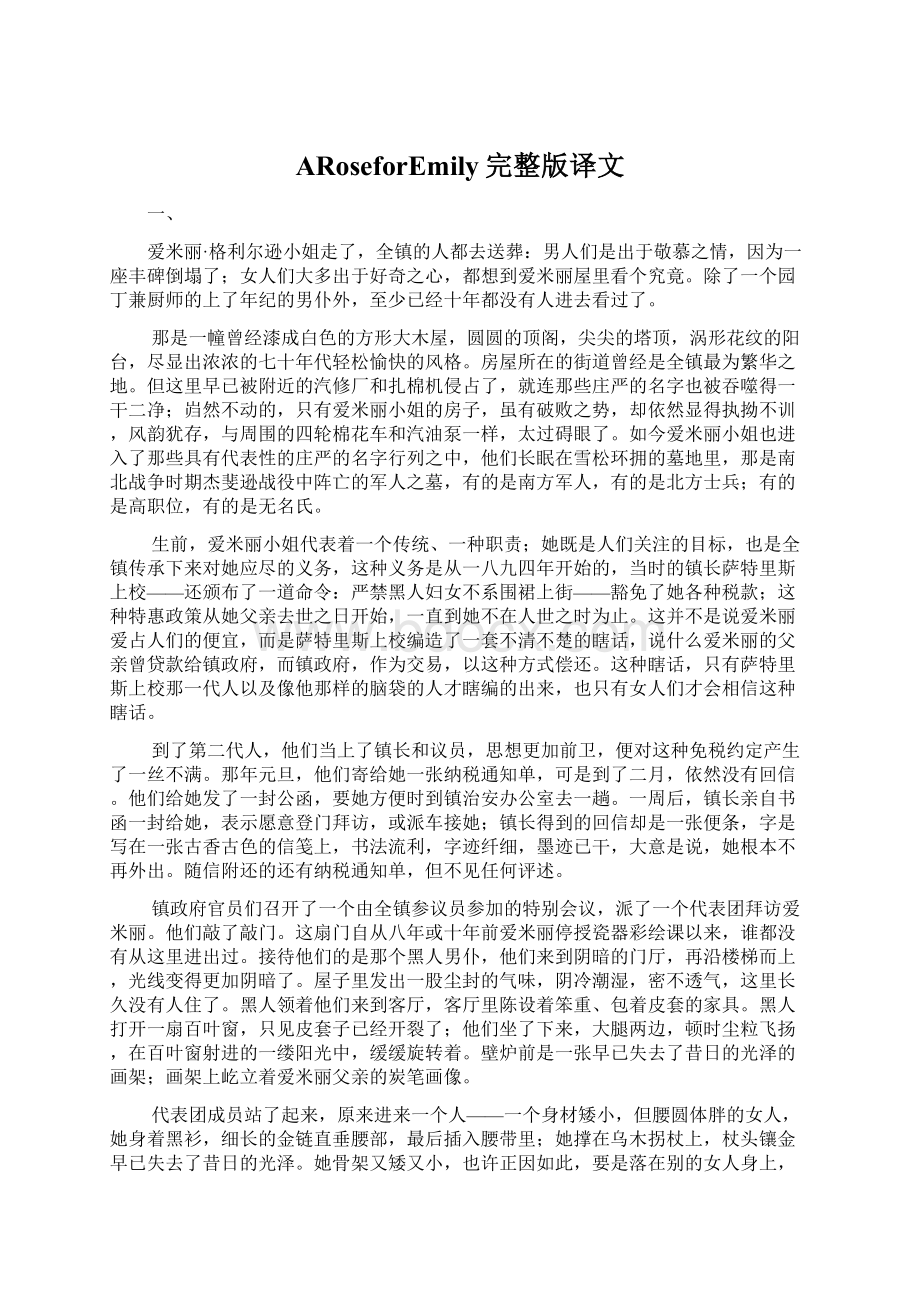
ARoseforEmily完整版译文
一、
爱米丽·格利尔逊小姐走了,全镇的人都去送葬:
男人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座丰碑倒塌了;女人们大多出于好奇之心,都想到爱米丽屋里看个究竟。
除了一个园丁兼厨师的上了年纪的男仆外,至少已经十年都没有人进去看过了。
那是一幢曾经漆成白色的方形大木屋,圆圆的顶阁,尖尖的塔顶,涡形花纹的阳台,尽显出浓浓的七十年代轻松愉快的风格。
房屋所在的街道曾经是全镇最为繁华之地。
但这里早已被附近的汽修厂和扎棉机侵占了,就连那些庄严的名字也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岿然不动的,只有爱米丽小姐的房子,虽有破败之势,却依然显得执拗不训,风韵犹存,与周围的四轮棉花车和汽油泵一样,太过碍眼了。
如今爱米丽小姐也进入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庄严的名字行列之中,他们长眠在雪松环拥的墓地里,那是南北战争时期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军人之墓,有的是南方军人,有的是北方士兵;有的是高职位,有的是无名氏。
生前,爱米丽小姐代表着一个传统、一种职责;她既是人们关注的目标,也是全镇传承下来对她应尽的义务,这种义务是从一八九四年开始的,当时的镇长萨特里斯上校——还颁布了一道命令:
严禁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上街——豁免了她各种税款;这种特惠政策从她父亲去世之日开始,一直到她不在人世之时为止。
这并不是说爱米丽爱占人们的便宜,而是萨特里斯上校编造了一套不清不楚的瞎话,说什么爱米丽的父亲曾贷款给镇政府,而镇政府,作为交易,以这种方式偿还。
这种瞎话,只有萨特里斯上校那一代人以及像他那样的脑袋的人才瞎编的出来,也只有女人们才会相信这种瞎话。
到了第二代人,他们当上了镇长和议员,思想更加前卫,便对这种免税约定产生了一丝不满。
那年元旦,他们寄给她一张纳税通知单,可是到了二月,依然没有回信。
他们给她发了一封公函,要她方便时到镇治安办公室去一趟。
一周后,镇长亲自书函一封给她,表示愿意登门拜访,或派车接她;镇长得到的回信却是一张便条,字是写在一张古香古色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纤细,墨迹已干,大意是说,她根本不再外出。
随信附还的还有纳税通知单,但不见任何评述。
镇政府官员们召开了一个由全镇参议员参加的特别会议,派了一个代表团拜访爱米丽。
他们敲了敲门。
这扇门自从八年或十年前爱米丽停授瓷器彩绘课以来,谁都没有从这里进出过。
接待他们的是那个黑人男仆,他们来到阴暗的门厅,再沿楼梯而上,光线变得更加阴暗了。
屋子里发出一股尘封的气味,阴冷潮湿,密不透气,这里长久没有人住了。
黑人领着他们来到客厅,客厅里陈设着笨重、包着皮套的家具。
黑人打开一扇百叶窗,只见皮套子已经开裂了;他们坐了下来,大腿两边,顿时尘粒飞扬,在百叶窗射进的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着。
壁炉前是一张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泽的画架;画架上屹立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
代表团成员站了起来,原来进来一个人——一个身材矮小,但腰圆体胖的女人,她身着黑衫,细长的金链直垂腰部,最后插入腰带里;她撑在乌木拐杖上,杖头镶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泽。
她骨架又矮又小,也许正因如此,要是落在别的女人身上,那种胖就是丰满,而落在她身上,就显得臃肿。
她看上去肿胀发白,就好像长期浸泡在死水中的死尸一般。
当客人说明来意时,她的那两只眼睛不停地转悠着,一会儿瞧瞧这张面孔,一会儿看看那张脸蛋,那眼睛啊,都深陷在满脸隆起的赘肉里了,就像掐在生面团中的两个小煤球。
她并没有叫他们坐下,而径直站在门口,一声不吭地听着,直到发言代表结结巴巴地说完。
这时,只听见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那是金链另一端隐没在裤袋里的怀表发出来的声音。
她说起话来,声音冷酷无情。
“杰斐逊时,我无须纳税。
萨特里斯上校早已给我交待过了。
兴许你们可以派个人去查一查镇政府档案,事情就清楚了。
”
“可我们查过了。
爱米丽小姐,我们就是镇政府当局的。
难道你没有收到司法长官亲手签署的通知吗?
”
“不错,我是收到过一张纸,”爱米丽小姐说道,“司法长官,也许他真把自己当回事……杰斐逊时,我无须纳税。
”
“可是,纳税册上并没有无须纳税的说明,要知道,我们必须依……”
“找萨特里斯上校要去。
杰斐逊时,我无须纳税。
”
“可是,爱米丽小姐……”
“找萨特里斯上校要去,(萨特里斯上校已经死了将近十年了)杰斐逊时,我无须纳税。
托布!
”黑奴应声而来。
“把这些绅士们给我带出去。
”
二、
就这样,爱米丽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收拾了,这种场面在三十年前也发生过,他们的父辈因熏天臭气而闹事,她照样把他们的父辈给收拾了。
那事发生在她父亲死后两年,也就是她的心上人——我们一直以为一定会与结婚的那个人——抛弃她后不久才发生的事。
父亲死后,她很少出门;但心上人走了后,人们几乎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了。
有几个冒失的女人曾去过她的家,但却吃了闭门羹。
房屋四周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那个黑人——当时他很年青——拎着菜篮子进进出出。
“好像,要是男人——不管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的话,”女人们说道;那种气味越来越来浓时,她们也并不感到吃惊。
这种气味毕竟是芸芸众生的平凡世界与大官贵族的格利尔逊家族之间的另外一种联系方式。
邻家一妇人向年已八十的镇长史蒂文斯法官投诉。
“可是,太太,这件事,你叫我怎么办呢?
”他说道。
“嗯,那,通知她把气味去掉呗,”女人说,“不是有法律吗?
”
“绝对没有必要,”史蒂文斯法官说,“也许是她家那个黑鬼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什么似的。
我去跟他说说这事儿。
”
第二天,镇长又接到两起投诉,一起是来自一个男的,语气温和。
“法官,对这气味,我们真的该采取措施了。
可我又最不想打扰爱米丽小姐,但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
”那天晚上,全体参议员召开了一个会,参加会议的人有三位老人和一位较年轻的新兴代成员。
“这事再简单不过了,”年轻人说,“通知她叫人把屋子打扫干净,限期搞好,否则……”
“滚蛋吧,你。
先生……”萨特里斯法官说,“当着一个贵妇的面,你怎么能说她家里有难闻的气味呢?
”
接着,第二天子夜过后,有四个男人越过爱米丽小姐家的草坪,像盗贼一般在屋子周围潜行,沿着墙角和在地窖通风处吸气闻嗅,其中一人还从肩上的麻袋中掏出东西,做着播种的样子。
他们打开地窖门,在地窖里和所有的裙楼外都撒上了石灰。
当他们再回头穿过草坪时,原本黑暗的窗户亮起了一扇灯光。
灯光中爱米丽坐在那儿,灯在她的身后,挺立的身躯一动不动,活像一座雕像。
他们鬼鬼祟祟地弓着腰,越过草地,进入街道两旁的洋槐树影中。
一两周后,气味消失了。
而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感到难过。
我们镇上的人想起了爱米丽小姐的姑奶奶怀亚特,这老太太后来完全变成了一个疯子;我们都相信格利尔逊一家人都太过自命清高了。
年轻男人在爱米丽小姐这类的女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好货色。
长久以往,我们都把她们这家人看作是一幅活人画:
爱米丽小姐身材苗条,立于父亲身后;父亲站在前面,双脚叉开,背对爱米丽,手里握着马鞭;二人站在一扇后开的前门中间。
所以当她接近三十岁,依然孑然一身,准确地说,我们并没有欣喜之心,反而觉得我们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即使她家有疯癫的遗传,要是遇到机会,她也不应断然放弃。
父亲死后,传说那幢房子全部留给了她;人们也有点高兴。
他们终于可以向她表达怜悯之情了。
孤单清苦,她早该懂人情世故了。
如今她也该体会到多一分钱则喜,少一分钱则愁的那种人之常情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镇上所有的女人都准备去她家吊唁和提供帮助,这是我们的习俗。
爱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了她们,依着和往日一样,脸上也没有丝毫悲伤。
她告诉来访者,她父亲没有死。
连续三天都这样,无论是来访的牧师们,还是医生们,都劝她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
正当他们准备诉诸法律和武力时,爱米丽崩溃了,这时,他们才赶紧把她父亲给埋掉了。
我们并不是说她当时就疯了,反倒认为她的反常是身不由己,还记得,她父亲把所有的青年小伙都驱赶走了,也知道她如今一无所有了,她才死死的抓住剥夺她一切的那个人,其实,是人都会这样。
三、
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
再见她时,她已剪短了头发,小姑娘打扮,那样子有点像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有些悲伤,有点肃穆。
原来镇政府刚刚签订了铺设人行道的合同,而动工时间就在她父亲去世那年夏天。
建筑公司带来了一批劳工、骡子和机器,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霍默.巴伦,大个子、黑皮肤,大嗓门儿,做事手脚麻利,黯黑的脸色衬出炯炯的眼神。
他身后跟着一群群孩子,听他咒骂劳工,而劳工们却随着凿子起落有节奏地哼着劳动号子。
不久,全镇的人他都认识了。
在广场四周,只要能听到呵呵笑声的地方,霍默.巴伦必定在人群的中心。
没过多久,每逢礼拜天下午,都可以见到他和爱米丽小姐一起驾着轻便马车出游,枣红色的马是从出租店租来,与黄色车轮的马车十分匹配。
起初,我们都很高兴,爱米丽小姐总算有了爱好,因为女人们都说:
“格利尔逊肯定不会看上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劳工。
”不过也还有一些人,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即使悲伤也不至于叫一个高贵的妇女忘记自己“贵人责重”吧,贵人责重无须叮嘱啊。
他们只是说:
“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属应该到这儿来一下。
”她有亲戚在亚拉巴马州;但多年前,她父亲为争疯癫婆怀亚特的房产问题而与他们闹翻了,从此以后,两家再也没有往来了。
即使是爱米丽父亲的葬礼,他们也没有派代表参加。
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老人们就是开始交头接耳了。
他们议论道:
“你看,当真有那么回事吗?
”“当然啦。
那还能有什么别的事……?
”声音从他们的手指缝传出来;只听见清脆而疾驰的马蹄声声,只见马车百叶窗紧闭以抵御周日午后骄阳,窗后的绸缎发出窸窣声:
“可怜的爱米丽。
”
爱米丽高昂着头——即使我们都认为她已经堕落;仿佛她不仅仅想要人们承认她就是格里尔逊家族末代的尊严;仿佛需要同世俗接触才能重新确认她那倔强的性格。
拿她买耗子药砒霜的事来说吧。
也就是人们开始说“可怜的爱米丽”之后一年多发生的事,当时她的两个堂姐妹正好来看望她。
“买点毒药,”她对药剂师说道。
当时她已经三十多了,依然是一个身细腰纤的女人,比平常还要清瘦,一双黑色的眼睛显得冷峻高傲,脸上太阳穴和眼窝处,肌肉紧绷,那副模样好像只有灯塔守望者才应该具有的。
“买点毒药。
”爱米丽说道。
“好的,爱米丽小姐。
要买哪一种?
是毒耗子一类的药吗?
我建议……”
“拿店里最灵的药。
种类不论。
”
药剂师一连说了好几种药名。
“这些药什么都毒得死,就是大象也不例外。
不过,你想要……”
“砒霜,”爱米丽小姐说,“灵不灵?
”
“是……砒霜?
好的,小姐。
可你想要……”
药剂师朝下看着她。
爱米丽挺直着身,回敬了他一眼,那脸绷得像凿出来的石板。
“嗯嗯,当然有,”药剂师说道,“如果你真想要这种药。
可是,按法律规定,你得说明用途。
”
爱米丽小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头向后仰着,双眼正视着他,直到药剂师移开目光,转身拿砒霜包好。
把那包药送出来的是店里的黑人送货员,而药剂师再也没有露过面。
爱米丽回到家,打开药包,盒子上有个骷髅标记,标记下注明:
“杀鼠专用。
”
四、
第二天,我们都说:
“她要自杀。
”要说啊,这事再好不过了。
第一次看见她与霍默.巴伦在一起时,我们就说过,“她会嫁给他。
”接着,我们又说,“她还得说服他才行,”因为霍默自己说喜欢跟男人在一起——,谁都知道他和年轻人在麋鹿俱乐部一起喝酒——照他的说法,他这个人不宜结婚。
后来,每当礼拜日下午那耀眼的马车路过时,爱米丽总是高昂着头,霍默.巴伦斜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戴着黄手套的那只手握着马缰和马鞭;见此情景,我们都会在百叶窗后禁不住说一声:
“可怜的爱米丽。
”
后来,有些女人开始说,这是镇上的一大耻辱,给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而男人们又无意介入,但最后还是女人们敦促浸礼会牧师-----爱米丽一家人都信奉圣公会-----去拜会她。
拜会过程,牧师不愿透露,但他再也不愿去了。
第二个礼拜天,他们又驾着马车在街上兜风,第二天,牧师的老婆写信给爱米丽住在亚拉巴马的亲戚。
于是,她家直系亲属又来了一趟,我们呢,回家坐等事态的发展。
起初风平浪静。
接着,听说他们就要结婚了,后来还听说,爱米丽小姐去过珠宝店,还订购了一套男人盥洗用品,每件用品上都刻有“霍.巴”。
两天后,我们又听说,她购买了一套男士服装,还有睡衣,所以我们说:
“他们结婚了。
”我们为此还真高兴,高兴的原因是,如果说爱米丽小姐曾经代表了格里尔逊家族的传统,那么如今两位堂姐妹更具有格里尔逊家族的风范。
霍默.巴伦走了后,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因为街道铺设工程完工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让我们感到有点失望的是缺少了吹吹打打的欢送场面,但我们还是相信霍默.巴伦走了是去准备迎娶爱米丽小姐,或者给她一个机会好打发走两个堂妹。
(当时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私党,力挺爱米丽小姐,帮她收拾这对堂姐妹。
)一点不错,过了一星期,这对堂姐妹就走了。
不出所料,霍默.巴伦又回来到了镇上。
一个邻居亲眼目睹了爱米丽家的黑仆在一个黄昏把他从厨房门接了进去。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霍默.巴伦。
爱米丽小姐呢,我们则有一段间没有见过她了。
黑人倒是提着篮子进进出出,但前门总是关着。
偶尔还可以从窗户上看到她的身影闪现,就像人们撒石灰那天晚上见到的情景一样,但几乎有六个月没见她上过街了。
我们知道,这一切也是可以预料的;好像父亲的性格对她这样的女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麻烦,而这种性格似乎太恶毒,太极端了,至今难以消除。
再次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身体发福,而头发逐渐灰白起来。
随后几年里,她的头发越来越灰,变成了白盐参胡椒般的铁灰色,随后再也没有变过。
到了她七十四岁过世时,都保持着她那旺盛的铁灰色,像是正值当年的男人的头发。
从那时起,她的前门再也没有打开过,只有她四十开外时,大约有六七年时间前门开过。
在那段时间,她开课教授瓷器彩绘。
她在楼下的一间房里布置了一间画室。
萨特里斯上校同时代的人都把女儿,孙女送到她那儿去学习,而且很按时,那精神与礼拜天把她们送去教堂,给她们二毛五分硬币以备放在募捐盘中的情形没什么区别。
那时,她的税收早已豁免了。
后来,新一代成了镇上的骨干和灵魂,那些学画的孩子已经长达成人,相继离开了,她们没有让自己的女儿带着调色盒,讨厌的画笔和从女士杂志上剪下的图画到爱米丽小姐家学绘画。
最后一个学生走后,前门就关了,而且再也没有打开过。
镇上实行免费邮递时,唯独爱米丽小姐拒绝在她家门上钉金属门牌号,附设邮箱。
她也不听他们解释。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只见那黑人,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依然提着菜篮子进进出出。
每年十二月,我们都寄给她一张纳税通知单,但一星期后,又被邮局退了回来,无人认领。
时不时地,我们在楼下的一个窗口——显然她把自己封闭在阁楼上了——还可看到她的身影。
那身影活像神龛中供奉的无头神像,是不是在看我们,我们也拿不准。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过去了,她始终保持着——高贵傲然,临危不惧,性格倔强,镇定自如,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走了。
死前,她病倒在一栋尘埃遍地,魅影憧憧的屋子里,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黑人侍候她。
她病倒了,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懒得从黑人那儿打听消息了。
况且,那黑人见谁也不啃声,恐怕见了她也是如此。
由于长期不啃声,他的嗓子早已沙哑了。
她死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笨重的胡桃木床挂着床帏,她那长满铁灰色的头枕着枕头,因长年不见阳光,枕头已经泛黄发霉了。
五、
黑人站在前门口迎接第一批妇女,把她们引进了屋子。
她们悄声细语,好奇地东瞧瞧西瞅瞅。
黑人转眼就不见了。
他穿过屋子,出了后门,再也不见踪影了。
说来,两位堂姐妹就来了,他们第二天就举行了葬礼,全镇的人都来吊唁鲜花覆盖的爱米丽,棺材架上方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表情严肃深沉;女人们悄声细语、战战兢兢。
而那些老年男人呢——有些还床上刷洗干净的南方同盟军制服——在走廊里,草坪上议论着爱米丽小姐,仿佛她就是他们同时代的人,还说,跟她逃过舞,兴许还向她求过婚呢,他们按数学级数来推算,混淆了时间,这是老年人的通病。
对老人来说,过去不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而是一片没有冬天的大草地,而只是最近十年才像窄小的瓶颈般将他们与过去隔断了。
我们早就知道,楼上那个地方有一间屋子,四十年了谁也没有进去过,只能踹门而入了。
要等爱米丽小姐下葬后,他们才去开门。
门砰地一下踹开了,顿时屋里仿佛弥漫着灰尘。
房间仿佛曾是一间装饰一新的新房,如今如坟墓一般发出淡淡的、呛人的气味,四处渗透出阴森森气氛:
褪色了的玫瑰色窗帘,阴暗的玫瑰色灯光,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饰品,还有白银底色的盥洗用品,不过白银制品已经失去的光泽,连刻在上面的字迹也都看不清了。
其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是从身上取下来的,然后提起来,在台面上留下淡淡的月牙形尘埃痕迹。
椅子上挂着一套精心折叠的衣服;椅子下是两只寂寞的鞋子,还有一双丢弃的袜子。
床上躺着那个男人。
我们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俯视着那枯瘦阴深,呲牙咧嘴的头颅;尸体躺在那儿,那躺姿明显是曾一度拥抱过,但如今的长眠比爱情更加长远,甚至战胜爱情的折磨,彻底让他驯服了。
破烂的睡衣下,躯体腐烂后的遗骸与他躺着的床早已难分难解了。
在他身上,在他身旁的枕头上,均匀地铺满了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
后来,在旁边的枕头上,我们发现有人头压过的痕迹。
有人从上面提起某种东西,凑近一看,一股淡淡的、无形的、干燥呛人的尘埃味扑鼻而来,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