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docx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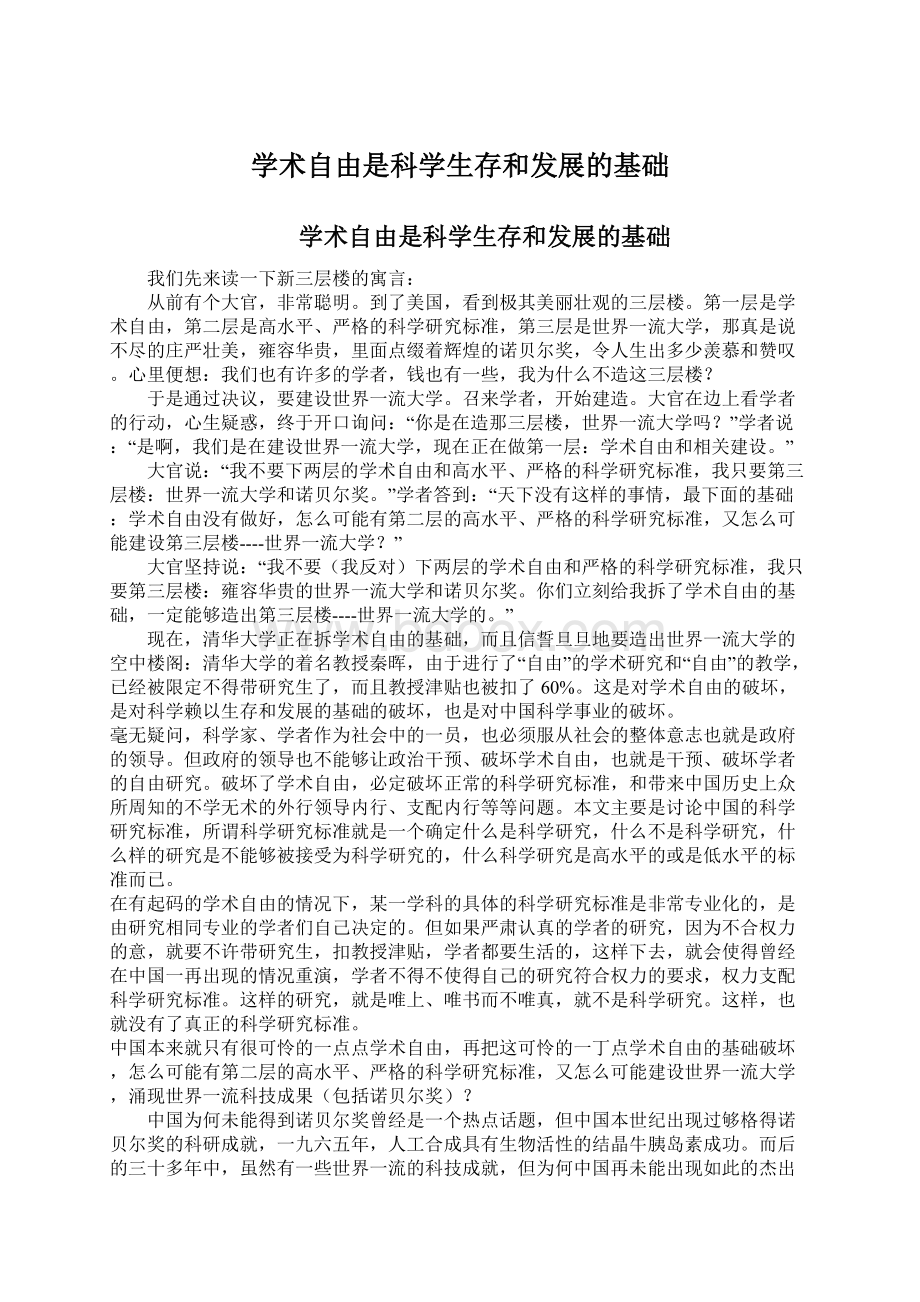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
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
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
心里便想:
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召来学者,开始建造。
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
“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
”学者说:
“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
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
大官说:
“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
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学者答到:
“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
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
大官坚持说:
“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
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
清华大学的着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
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
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
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
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
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
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
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
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
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
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
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
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
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
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
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
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
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
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
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
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
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
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
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
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着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
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
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着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
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
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
可能我的判断有误。
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
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
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
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
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
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
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
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
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
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
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
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
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
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
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政治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
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
为什么如此“愚忠”?
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建立、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
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1],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
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
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成了西方和中国儒学传统的怪异混合体;但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
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价值,等等。
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
中国是在与西方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
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
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
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
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
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
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
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
“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
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
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
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
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
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
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
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着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
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
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
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
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
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
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
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
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
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看到,有人披露:
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
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发表论文、专着的数量,看等级,即发表论文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
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
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
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大跃进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反党”谁受得了!
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
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
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
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