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向乡村学习.docx
《王澍向乡村学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澍向乡村学习.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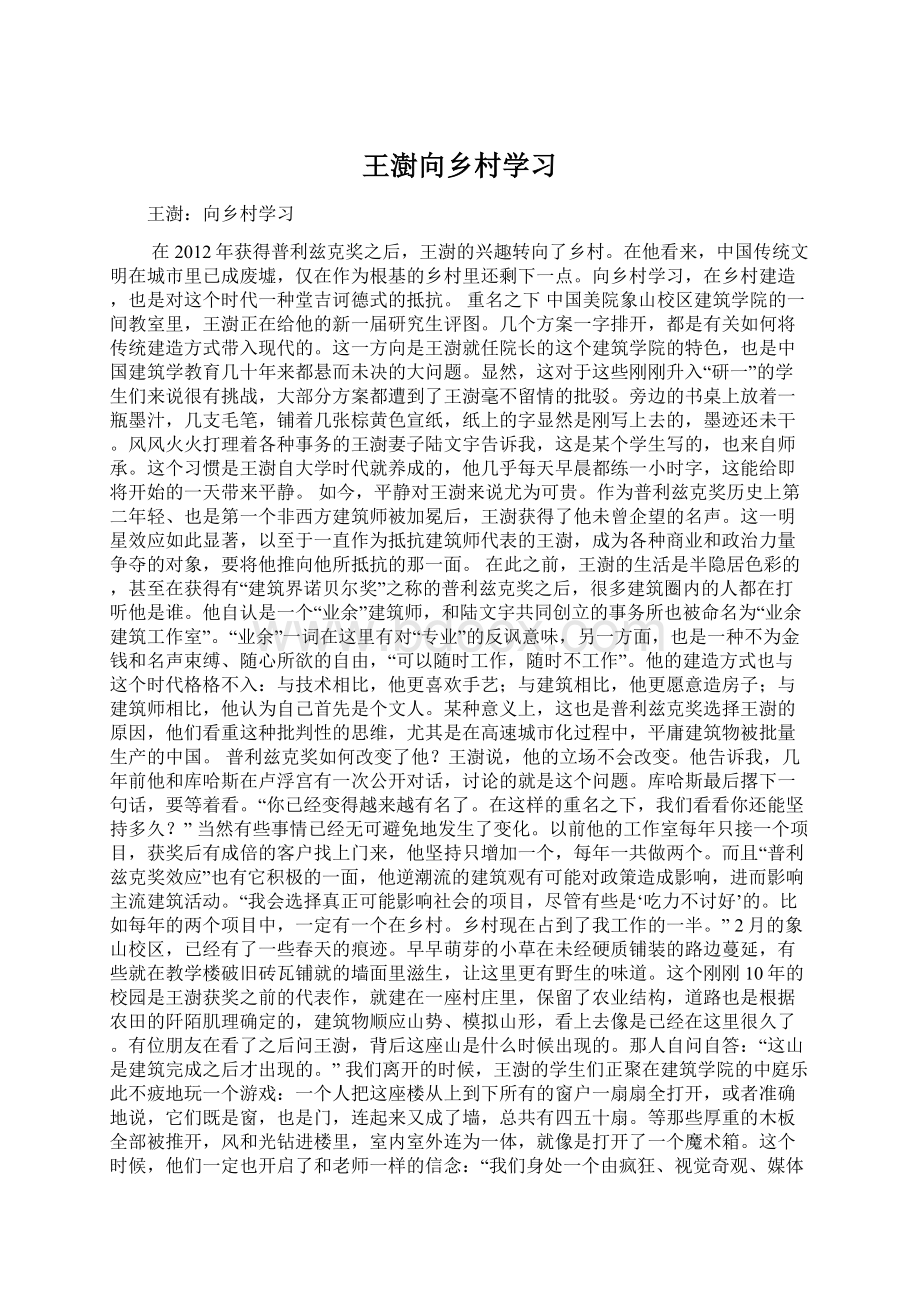
王澍向乡村学习
王澍:
向乡村学习
在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王澍的兴趣转向了乡村。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明在城市里已成废墟,仅在作为根基的乡村里还剩下一点。
向乡村学习,在乡村建造,也是对这个时代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抵抗。
重名之下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筑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王澍正在给他的新一届研究生评图。
几个方案一字排开,都是有关如何将传统建造方式带入现代的。
这一方向是王澍就任院长的这个建筑学院的特色,也是中国建筑学教育几十年来都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显然,这对于这些刚刚升入“研一”的学生们来说很有挑战,大部分方案都遭到了王澍毫不留情的批驳。
旁边的书桌上放着一瓶墨汁,几支毛笔,铺着几张棕黄色宣纸,纸上的字显然是刚写上去的,墨迹还未干。
风风火火打理着各种事务的王澍妻子陆文宇告诉我,这是某个学生写的,也来自师承。
这个习惯是王澍自大学时代就养成的,他几乎每天早晨都练一小时字,这能给即将开始的一天带来平静。
如今,平静对王澍来说尤为可贵。
作为普利兹克奖历史上第二年轻、也是第一个非西方建筑师被加冕后,王澍获得了他未曾企望的名声。
这一明星效应如此显著,以至于一直作为抵抗建筑师代表的王澍,成为各种商业和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要将他推向他所抵抗的那一面。
在此之前,王澍的生活是半隐居色彩的,甚至在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之后,很多建筑圈内的人都在打听他是谁。
他自认是一个“业余”建筑师,和陆文宇共同创立的事务所也被命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
“业余”一词在这里有对“专业”的反讽意味,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为金钱和名声束缚、随心所欲的自由,“可以随时工作,随时不工作”。
他的建造方式也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与技术相比,他更喜欢手艺;与建筑相比,他更愿意造房子;与建筑师相比,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文人。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普利兹克奖选择王澍的原因,他们看重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尤其是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平庸建筑物被批量生产的中国。
普利兹克奖如何改变了他?
王澍说,他的立场不会改变。
他告诉我,几年前他和库哈斯在卢浮宫有一次公开对话,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库哈斯最后撂下一句话,要等着看。
“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名了。
在这样的重名之下,我们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当然有些事情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以前他的工作室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获奖后有成倍的客户找上门来,他坚持只增加一个,每年一共做两个。
而且“普利兹克奖效应”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他逆潮流的建筑观有可能对政策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主流建筑活动。
“我会选择真正可能影响社会的项目,尽管有些是‘吃力不讨好’的。
比如每年的两个项目中,一定有一个在乡村。
乡村现在占到了我工作的一半。
”2月的象山校区,已经有了一些春天的痕迹。
早早萌芽的小草在未经硬质铺装的路边蔓延,有些就在教学楼破旧砖瓦铺就的墙面里滋生,让这里更有野生的味道。
这个刚刚10年的校园是王澍获奖之前的代表作,就建在一座村庄里,保留了农业结构,道路也是根据农田的阡陌肌理确定的,建筑物顺应山势、模拟山形,看上去像是已经在这里很久了。
有位朋友在看了之后问王澍,背后这座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那人自问自答:
“这山是建筑完成之后才出现的。
”我们离开的时候,王澍的学生们正聚在建筑学院的中庭乐此不疲地玩一个游戏:
一个人把这座楼从上到下所有的窗户一扇扇全打开,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既是窗,也是门,连起来又成了墙,总共有四五十扇。
等那些厚重的木板全部被推开,风和光钻进楼里,室内室外连为一体,就像是打开了一个魔术箱。
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也开启了和老师一样的信念:
“我们身处一个由疯狂、视觉奇观、媒体明星、流行事物所引导的社会状态中,在这种发展的狂热里,伴随着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混合着由文化失忆症带来的惶恐和轻率,以及暴富导致的夸张空虚的骄傲。
但是,我们的工作信念在于,我们相信存在着另一个平静的世界,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地隐匿。
”富春山居何在?
普利兹克奖之后,王澍的两个最新项目都在富阳,一个是富阳山馆,一个是文村。
他称为相互呼应的“一对项目”,正好是一城一乡。
或者放在《富春山居图》的情境中去看,“一个是‘山’,一个是‘居’”。
《富春山居图》是它们共同的文化背景。
元朝末年,古稀之年的黄公望云游至杭州西南角的富春江畔庙山坞,被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恬静野逸打动,在此结庐隐居十几年,往来于两岸,模山范水,几年后完成了名作《富春山居图》。
600多年过去,黄公望隐居的庙山坞仍在富阳境内有迹可循,这一段富春江也被普遍认为是《富春山居图》的自然范本。
据富阳学者史庭荣考证,这一带的山水与画作所绘景物相契合:
“画中采用的以平远法为主展开的长卷式构图,给人空旷开阔的意境;以长披麻皴为主的疏松笔法,概括了清净明朗的山体;而圆浑柔和的山峰,水天交接处墨色渲染的一抹远山,正是富阳富春江两岸的山形。
”这幅名作的传奇还在于多舛的命运。
300多年前,《富春山居图》被焚为两断,前段称《剩山图》,后段称《无用师卷》。
几经周折,《无用师卷》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剩山图》则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直到2011年6月,分离300多年的两段才终于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
而对富阳来说,更遗憾于没能将《无用师卷》迎回“家”,没有供画作展出的场地,后来也因此启动了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三馆合一的“富春山馆”项目。
“这个馆要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但是人们往往容易沉浸在对历史的想象中,看不见现实。
现实的这张《富春山居图》里面,已经高楼大厦成群了,哪还有当年《富春山居图》的影子呢?
”王澍直截了当对找上门来的原富阳县委书记说。
他告诉我,做一个山水画传统背景下的美术馆,这本身是有意义的,这种自觉意识也促使他接下了这个项目。
但是真要做的话,其实是带有某种反讽意味的:
“富春江水长流,富春山居在哪里?
”所以他认为,不能完全从一张画的美学角度去美化地方传统,在想象中说有多美。
“我要用这样一个建筑来让人们重新意识到:
我们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与自然山水间形成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的文化曾经有这个能力,现在或许也保留了一点这个能力。
但同时,这个建筑还要反衬出现实的丑陋。
”即将完工的富春山馆坐落在富阳的高架桥入口处,背靠鹿山,面对富春江。
王澍称之为一个“大山大水的结构”,他设计的起点就是如何让建筑与山水间形成真实而强烈的映照。
工程负责人洪青龙带我进入还在施工中的馆舍内部,他告诉我,这里是一座“建筑的《富春山居图》”。
这不仅是一种字面上的形容,事实上,王澍的设计思路直接与这张山水画有关。
怎样让一个建筑的观赏体验,就像在看一张中国山水画?
关于建筑和山水绘画结构的讨论,一直是王澍建筑思考和实践的一个重点。
中国画讲究“三远”,指三种不同的透视角度——“高远”“深远”和“平远”。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里曾定义:
“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问题是,“三远”是指二维的画面,怎么用三维的房子呈现出来?
这样的转换让人好奇。
富春山馆的入口,要先穿过一组小桥流水,就像山水立轴下方的近景,有一种“山外观山”的体验。
进入馆内,则要行走一段盘旋的通道,黄色木板在灰色墙面上形成鲜明的视觉冲击,是从山下向山上仰望的“高远”观法。
王澍说,这也是借鉴了黄公望的手法,将入口部分压得很低很低,到后面逐级抬高。
从“外山”进入“内山”,则进入了一个异常繁复的世界,“山内观山”,也是在山体间盘旋而上。
走出门,从顶部盘旋而下,又有一种形而上的回望。
至于“深远”,王澍则转换成了“阔远”。
他说,这是受了黄公望《山水画论》里的启发:
“江南地势局促,山多,但不是很开阔,所以黄公望说‘阔远’,是说人站在这儿,隔着一条河,对面有座山拔地而起,这时候人的眼睛像被拉成了宽荧幕一样,出现了扩张感。
不是想象中天高云淡的阔远,而是在某种压迫下产生的扩张。
”所以王澍在主体建筑对面专门建了一个观山厅,这是一个典型的宋代山水画“正观”的位置,眼前的富春山馆显得特别大,像一座山一样。
另一个直接借鉴黄公望的是皴法,黄公望认为皴法是决定性的,在构思任何山水画之前,都要先想好画什么山,画什么皴。
所以在富阳山馆里,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山形主建筑屋顶的皴法,王澍将一些红色的旧瓦片不规则地嵌入灰瓦中。
王澍说,富阳山馆是介于单体和群体之间的建筑——美术馆、博物馆一左一右构成主体,小体量的档案馆相对独立,后面还附设了长条形的后勤部分,几部分正好构成了一个三山结构——主山、次山和远山。
三山的对面建了一座塔,“望山楼”,我们从这里登高,可以俯瞰到建筑的“主山”,远处是“远山”。
这是“平远”的视角,也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经典角度。
而将视线继续延伸,这座建筑的“山馆”已经与更远处自然的“山”融为一体了。
王澍接受富阳山馆委托的前提,是同时要在富阳境内做一个村居的保存。
如今富阳已经成为杭州的一个行政区,当时还是个县级市,境内有297个村庄。
王澍调研后认为,已经有277个没救了,还剩下20个破破烂烂的,带有一点村居的痕迹。
他告诉我,当时稍微带一点要挟的意味,说如果不做一个村子,那么他对做这个博物馆也不是特别有兴趣,因为他已经做过很多博物馆,不需要在名单上再增加一个。
所以后来的文村项目,相当于是他“生造出来的”。
“普通”村庄从杭州到富阳,大约60公里,再到文村,又有50公里。
文村,是富阳区甚至杭州市的最西端,再往前走就是山,没路了。
这个村子看上去再普通不过,建在半山,有一点农田,有一些日益没落的家庭小工厂,年轻人大都去了城里打工。
说它是老村,这里大多数人家都盖起了“小洋楼”;说它是新村,这里又保留着一些破旧的老房子,不过最老的也就上百年。
王澍说,当时浙江省建设厅的领导专门来看他的选址,直接就傻了:
“王老师您怎么选这个村子?
太普通了。
”其实王澍看中的,就是文村的普通。
他告诉我,浙江省这几年对保护乡村越来越重视了,从一开始的“保护一千个乡村”,到现在的“保护两千个,展望保护三千个”。
无论如何,这些被列入保护名单的村子,省里会给钱,给政策,有人管。
问题是,省里至少还有3万个村子,大部分是没人管的。
他觉得,有人管的他可以暂时不管,他要管的是那些没人管的村子。
“像文村这样看上去特别普通的村子,我称为‘半残废’。
‘半残废’现在已经算是好的了,我做了普查,整个富阳充其量也就剩下20个,还有救,但基本上属于病入膏肓,需要华佗和扁鹊那样的手段,要有回天之术,才可能救得活。
”王澍上一次为乡村做建筑,是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也是那届世博会唯一的中国乡村主题馆。
“实际上那是个超级土豪村,村里的钱多到准备办银行了。
当我一看到村委会里那个美国郊区别墅群大沙盘,就知道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对宁波市领导说,只表现滕头的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有兴趣做一个建筑,剖切一下这个地区乡村建筑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也许能推断一下它的未来。
”王澍给村民设计了全新的农民公寓。
因为他们住的都是别墅,乡村里那种社会邻里关系荡然无存。
他反过来做公寓,每个公寓里有三五户,希望村民能重新形成邻里关系。
滕头村当然是一个极端。
但是在富裕的浙江,很多乡村即便不像滕头那么土豪,大多也已经以一种低版本的方式彻底切断了与历史的联系。
在我们从富阳到文村的沿途,目光所及基本都是“小洋楼”,三层,四层,甚至五层,一幢一个样式,混乱无序地拥塞在路边。
当地人说,之所以看着乱,也是因为这十几年的流行变化快,一开始是屋顶尖尖的“埃菲尔铁塔”,后来是串葫芦式的“东方明珠”,现在则是坡屋顶的“田园别墅”。
从洞桥镇到它下属的文村只有一条路通到山边,景色也越发开阔了。
可以想象,这个山脚下最后一片居留地,因为地处偏远,和外界的各种物资、人力及信息交流都是相对滞后的,这也让这里有慢半拍的感觉:
河对岸的老村,还有些几十年、上百年的房子留在那里,或者有老人依恋老宅,或者没来得及拆。
王澍第一次来到文村的时候,也是被这种半新半旧的状态打动了:
“出于偶然,也出于远见,他们建新村的时候,隔了一大块农田在对面建,没有直接去破坏老村。
新村里建了新房,但老村里只是零零星星有一些老房拆了重建。
村子里半新半旧,两种状态对在一起,而整体的道路肌理还在。
如果说我是一个建筑医生的话,看了之后会觉得,下药重一点应该还能救得回来。
”新与旧的错位如今文村的门面当然是王澍设计的房子,从村口向河对岸望过去,一排两三层高的民居沿河排布着,以现代建筑语言汇成不同的空间院落组合,杭灰石、夯土、抹泥、白灰、混凝土……似曾相识的材料和工艺又搭出了传统质地的墙面,放在这个破旧的小村庄里也不觉得突兀。
村支书沈樟海告诉我,王澍这些新房子其实是在旧民居中间穿插着建的,中间一些有保留价值的老房子都没拆,建好了很多人来看,一下子竟然分辨不清到底哪幢是新的,哪幢是旧的。
就连村民自己,现在也有点混淆新和旧,本来河北岸是新村,南岸是几乎被遗弃的老村,结果现在老村“拆新建旧”,成了新的焦点。
沈樟海在2014年3月第一次见到王澍。
之前他只听说有建筑大师要来农村建房子,并不知道“王澍”是谁,特地上网查了一下,看到他在世界上拿了什么奖,觉得“名人效应”总归没错。
其实一开始,洞桥镇有四个村子让王澍挑,文村先被选中。
沈樟海事后分析,这是因为文村有一条河穿村而过,位置开阔一些,而且还有些老房子,相对符合改造要求。
还有个巧合,是他们正计划在河的南岸建一个新的民居点,新建15幢房子。
文村之所以形成目前新旧并置的格局,其实是来自历史上不同寻常的风水选择。
沈樟海找出族谱给我看,里面保留了一张老村的地图,村庄夹在两座山之间,中间一条河穿过,所以最初建房有两个选择,一是山之南,水之北,在风水上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本来可利用的地块就不大,这样一来,田地就只能选在河的南岸了,再南面的另一座山会把阳光挡住,对庄稼生长不利。
所以文村的祖先们做了相反的选择,将人居住的房屋建在背光的一侧,田地则放在阳光充足的另一侧。
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要新建房屋,就将新村建到采光更好的对面去了。
这样的选择也是特别让王澍感慨的地方。
他意识到,风水实际上是敬畏与道德双重约束的文化。
“当人必须为生存做出选择时,风水就帮他们做出一个貌似不合理的选择,就是背南面北,这样对农田产生的阴影是最小的。
所以我对村民说,他们的祖先绝对是值得敬仰的。
相比之下,现代人的道德觉悟不如祖先,他们只满足这个时代自己的物质愿望,不考虑后代的利益。
这是个很有趣的案例,直接折射出传统和现代之间更深刻的关系。
”“‘沈’是文村第一大姓。
据族谱记载,唐朝时祖上在朝当武官,一次打仗输了,带着五个儿子往五个方向跑,其中一支就到了这里,开枝散叶。
”沈樟海摊开那张老地图,“老村的形状像是一艘船,沿着河的流向,上村种着几棵银杏树,下村有几棵柏树,相当于船的两根桨。
以前的村庄格局特别讲究,农田阡陌,移步换景,我小时候还有‘文村八景’,每一处景观都配了一首诗,现在只剩下一两处了。
祠堂还在,但过年过节不再使用,变成了老人去世停灵的地方,平时人就去得少了。
”沈樟海告诉我,文村自古“七山二水一分田”,每户平均有一亩稻田,冬天再种点油菜,只够自己吃。
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开始养蚕,规模达到每期1000多张,一年有三期,一张能卖几百块钱,成了主要经济来源。
但好久不长,这个产业逐渐衰落了。
2000年后乡镇企业转制,很多技术人员回乡办厂,沈樟海也是其中之一。
他原来在洞桥镇上的机械精加工厂,机械精加工是洞桥的两大支柱产业之一,没改制前这个厂有400多人,销量一度占到全国市场的六成以上。
他做了十几年技术,改制后决定回村自己办厂,最红火的时候做到30多人的规模。
后来村里陆续有20多户办了小五金厂,全村1800人,有200多人从事这一行,远近闻名。
沈樟海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也在那个时候被推举为村支书,如今已经12年了。
文村十几年“工厂时代”的家底,都体现在河北岸的新村了。
因为以前土地管得松,一部分菜地改成了宅基地,几乎每家每户都新建了楼房,而且一家比一家时髦。
沈支书家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像座城堡,还有个东方明珠似的尖顶,远远就能看见。
几年前因为工厂要扩大规模,他把搬走的村小学所在地买了下来,建成工厂,一家人也住在这里。
这个厂主要做装订书籍的胶装机,楼上的库房里整齐摆放着几十台成品。
沈樟海自信地说,除了大型机械做不了,他们什么配件都能做。
他站在机器旁边操作起来,动作娴熟。
只是如今这个产业也辉煌不再,他的厂里只剩下七八个人,都在50岁以上。
“一方面是现在都用数控技术了,另外也越来越难招到人。
三五千元一个月没人愿意来。
因为文村地处桐庐、临安、富阳三县交界处,只有一条路从镇上通进来,和城市离得远,本村的年轻人都想到外面去,外面的人也招不进来。
”他们不是没有想过别的办法。
因为最近几年浙江整体乡村旅游的兴盛,文村也开始挖掘自己这方面的资源。
想来想去决定搞“生态+观光”农业,把村集体所有的那块田里种上了油菜花,每到春天,金灿灿的油菜花开,再加上山上还有一片野生的杜鹃花海,也是诱人的美景。
只不过,几公里内的村子里都已经种上油菜花了,相邻的贤德村更是别出心裁地想出了在田里作画的办法:
将小麦穿插种在油菜田里,春天一到,绿色的小麦在黄色的田里非常显眼,爬到对面山上的某一处位置,就可以看出精心设计的图案。
每年的图案都不一样,据说有一年是“状元看书”,因为那里出过唐朝第一个状元,去年是“杭州G20”,还有一年是《富春山居图》。
这个季节正是农闲,村里每家每户凑了份子,多则500元,少则100元,把富阳的越剧班子请了来,让他们在村里唱上几天戏。
晚上7点天就黑了,以往这个点准备睡觉的村民们,也兴冲冲跑去礼堂看戏。
一开始是村里的戏迷轮番上台过瘾,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扮上行头的演员正式开唱,来看热闹的年轻人们有点不耐烦了。
越剧的节奏太慢,唱词也有些听不懂,能真正陶醉在咿咿呀呀戏文里的还是老年人。
和居住方式一样,乡村里传统的余韵还在,但是怎么在现代生活里延续,还是个问题。
给农民造房子王澍一直强调,他不是造个房子放在乡村里,而是真的给农民造房子,让农民能住进去。
所以他一来,就重新设计了新的民居点方案,新建加上改建,总共30多幢。
他和陆文宇挨家挨户去调查,让村民提意见。
原来的新民居点方案是整齐划一的“小洋楼”。
这正是王澍认为现在乡村的最大问题,他称为“内部的贫困”。
“如果说村庄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只有粗略的外部,它的内部几乎没有与生存关联的细密构造。
”他认为,强调差异性,也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
“很多人一说江南就是‘黑瓦白墙’,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材料。
但是如果去农村逛一逛,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化的‘黑瓦白墙’,它比想象的丰富得多,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它概念化了,其实是假模假样地以所谓的某种风格把乡村文化的生命给断绝了。
”所以他给这些房子设计出24种变化,也是实验多种可能性。
首先从格局出发,有8种空间类型——正三合园、偏三合园、前后院、单前院……类型确定后,再把材料的变化加进去,杭灰石、夯土、抹泥、混凝土……最后形成了24种排列组合。
空间重建的实质,其实是试图重建社会结构。
王澍说,一方面是以比现在的新农居密度更高的方式,重建乡村邻里结构;另一方面,也在每一户的内部,重建以小庭院为核心的文化结构。
他希望每一户都能有独一无二的识别,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家,我们家和你们家不一样。
尽管都在一个村子里,就像一个家族里的兄弟姐妹,有点像,但是能分得出来谁是谁”。
南方传统民居的文化核心,是天井,王澍这一次把天井加进了每一幢新设计的房子里。
现在农民建房时都把天井舍弃了,觉得是浪费面积。
王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宅基地政策的不明确导致的,所以他专门去找政府。
“既然是实验,能不能给个政策,10平方米的院子不算在宅基地内?
有了这个许诺,农民就能接受天井。
当然接下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得陇望蜀的要求,能不能在顶上加个盖?
这是不允许的。
”他觉得,这个精神核心不可或缺。
“中国人自己家的小天地都带着某种类宗教的含义,人和祖先的关系、和天地的关系,都靠天井来体现。
哪怕只有10平方米,也是要透气的。
”这些房子是要拿来住的,村民们对王澍提出了不少功能需求。
比如有人觉得,一开始设计的卫生间不够大,因为农村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卫生间里还会放好多东西,其实是卫生间加储藏室。
还有厨房,基本上一层楼里有半层都得是厨房,连柴灶也要放进去。
王澍调查下来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山上常年产生大量死去的杂木,树林需要清理,在一定程度上,砍柴是一种生态的做法。
有人提出需要一个农具室,就是在一楼要有一个地方,放锄头、镰刀这些粘泥土的东西,得一进门就能用。
还有的家里要开小五金厂,或者要养蚕,也需要透气好的大空间。
所以王澍设计出一种空间类型,一进门就有个大空间,可以有多种用途。
可选的房屋类型多了,接下来更复杂的问题是怎么选。
村民们就分配规则讨论了半年,最后还是靠抓阄来决定了。
王澍认为,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博弈,准备了一个足够多样性的背景。
之后制定博弈的规则,最后得到一个对个体家庭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选择结果。
当然抓阄后的选择也不完全偶然:
“一开始大家觉得夯土房子会没人要,但实际上它第一个就被选走了。
因为农民觉得,这个房子拿来开民宿,生意一定会很好。
”另一种可能性村民们对王澍的房子,一开始是难以接受的。
看上去半新不旧,还带个天井,完全不是想象中的“别墅”。
沈樟海花了一年多时间来说服15户待迁入的人家,还组织他们去附近旅游搞得好的村庄取经,看看另一种可能性。
郎根强看到了“老房子”的价值,觉得眼前一亮。
他原来自住的三层楼房建好只有十几年,因为正好在这次整治的沿河一线,“半土不洋”,影响景观,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
他本来觉得这次置换得有点亏,因为他原来的那幢房子建好只有十几年,施工成本大约每平方米2000元,两年前拆掉时按每平方米800元赔偿,去年底搬入新建好的这幢房子,成本大约每平方米3000元,按1500元置换给他,装修又花了50万元,算算亏了30万元。
有的邻居一算这笔账,选择不搬,只愿意让王澍改造一下建筑立面,还有人连免费的立面改造也不情愿,就维持原样不动。
他们现在都追悔莫及。
“农村小洋楼顶天100万元。
现在王澍设计的房子,听说有人出到800万元了。
”郎根强这些年一直承包村里的各种工程,建房,修路,架桥,算是见多识广,也愿意做出改变。
这一次王澍为了让当地人接受,同时又把造价控制在足够低,尽量采用了当地的材料,又将一部分工程承包让当地人建,郎根强就是承包人之一。
用当地的物料——砖、瓦、石料和混凝土相结合的建造技术,王澍这些年一直在实践,他称为“循环建造”,也是一种和“时间”的交易。
对村里人来说,也像是重新发现了这些几十年不怎么用的材料。
比如杭灰石,后山就有,90年代后就不用了,重新开采后发现,这种石头稍一敲击就能形成平整的片状,不用怎么加工就可以直接铺设在墙体上。
还有夯土,就是把山上的黏土挖来,晾晒,粉碎,和砂石、水按照一定配比混合,搅拌,再借助新的技术,可以夯得特别牢固,而且细腻。
郎根强说这种土墙配方特别生态,“几百年后这房子拆了,泥墙里可以直接种菜”。
分房时先抓阄,郎根强幸运地抽到了2号,挑走了尽端的那幢抹泥房。
他当时考虑得也很实际,一是周围遮挡少,视野好,二是面积大,格局好,三层楼的使用面积达284平方米,有5间卧室。
他们夫妻俩拿出一间卧室来自住,其余4间改成民宿,取名“逸山居”,也是王澍这批房子里目前唯一开的民宿,供不应求。
入住前去以乡村游出名的地方参观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在装修时实践了一种“古朴”美学:
家具尽量用实木,装饰物去找当地有名的篾匠章樟荣来编,甚至去老人家里回收一些陶罐或者饲料槽,再去山上采些兰花。
郎根强将刚掌握的抹泥技术也用在了室内,抹泥墙成了这里最大的标签。
“你看这黄泥也有各种变化,太阳一晒是金黄,下雨天又变成了橙色。
”住了一段时间,他更体会到传统材料和格局的好处:
天井通风透气,抹泥墙的厚度有45厘米,冬暖夏凉。
王澍和陆文宇后来也来看过他改造后的房子,陆文宇对二楼房间里美元图案的地砖印象很深:
“特别后现代,也反映了目前的一种心态。
”我在村委会见到了吕胜新,他是众安公司在文村项目的负责人,已经在村里住了4个多月了。
因为王澍的这批房子,他们想在文村投资开发旅游产业。
吕胜新是台湾人,有国内一家著名民宿连锁品牌的工作经验,但是那家民宿开在景区,而文村只是一个偏远的村子。
他认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