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docx
《国学经典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学经典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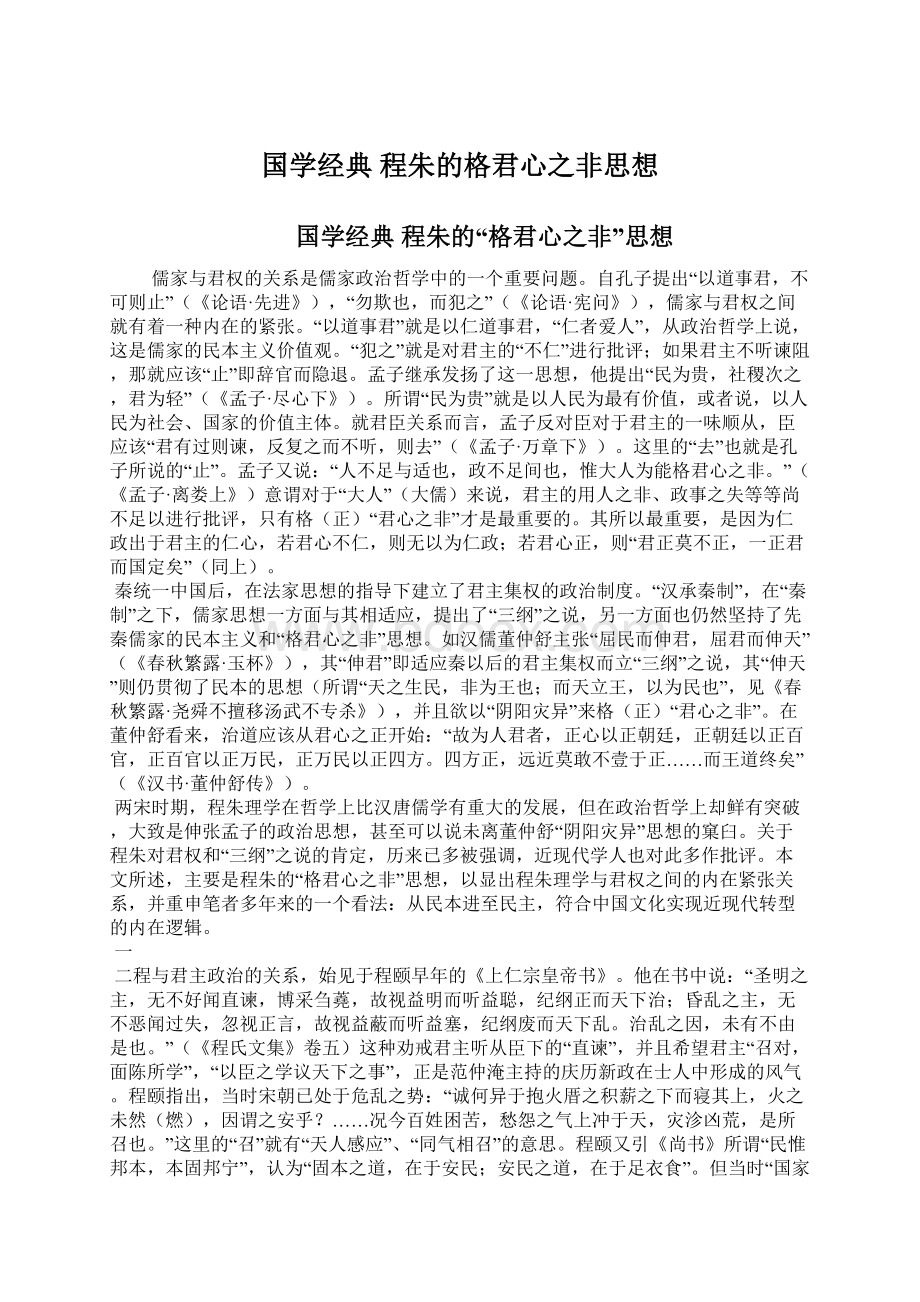
国学经典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国学经典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儒家与君权的关系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儒家与君权之间就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
“以道事君”就是以仁道事君,“仁者爱人”,从政治哲学上说,这是儒家的民本主义价值观。
“犯之”就是对君主的“不仁”进行批评;如果君主不听谏阻,那就应该“止”即辞官而隐退。
孟子继承发扬了这一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所谓“民为贵”就是以人民为最有价值,或者说,以人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
就君臣关系而言,孟子反对臣对于君主的一味顺从,臣应该“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
这里的“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止”。
孟子又说:
“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离娄上》)意谓对于“大人”(大儒)来说,君主的用人之非、政事之失等等尚不足以进行批评,只有格(正)“君心之非”才是最重要的。
其所以最重要,是因为仁政出于君主的仁心,若君心不仁,则无以为仁政;若君心正,则“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同上)。
秦统一中国后,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
“汉承秦制”,在“秦制”之下,儒家思想一方面与其相适应,提出了“三纲”之说,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和“格君心之非”思想。
如汉儒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其“伸君”即适应秦以后的君主集权而立“三纲”之说,其“伸天”则仍贯彻了民本的思想(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见《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并且欲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
在董仲舒看来,治道应该从君心之正开始: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
关于程朱对君权和“三纲”之说的肯定,历来已多被强调,近现代学人也对此多作批评。
本文所述,主要是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以显出程朱理学与君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重申笔者多年来的一个看法:
从民本进至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
二程与君主政治的关系,始见于程颐早年的《上仁宗皇帝书》。
他在书中说:
“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视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
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
”(《程氏文集》卷五)这种劝戒君主听从臣下的“直谏”,并且希望君主“召对,面陈所学”,“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正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士人中形成的风气。
程颐指出,当时宋朝已处于危乱之势:
“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之未然(燃),因谓之安乎?
……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灾沴凶荒,是所召也。
”这里的“召”就有“天人感应”、“同气相召”的意思。
程颐又引《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
但当时“国家财用,常多不足”,为充财用则“急令诛求”于民,“竭民膏血”,使百姓“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
“彼庶民者,饥寒既切于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顾忠义哉?
非民无良,政使然也。
”他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当时政治的批判,由此批判而提出实行“王道”的主张。
他说:
“窃惟王道之本,仁也。
臣观陛下之仁,尧舜之仁也。
然而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
”(同上)在此,程颐肯定宋仁宗“有仁心”,但“无仁政”,这是对当时君主政治的一种乐观看法。
此后,二程便由强调君主必须“正志先立”,终至明确提出“格君心之非”是治道之“本”。
治平二年(1065),程颐写有《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
此书仍强调了“民惟邦本”,“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治道的“本”与“用”之分:
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
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
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
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请为陛下陈之。
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
……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
有其本,不患无其用。
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
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
”(《程氏文集》卷五)
这段话把君主的“立志”作为最根本的急务,其精神与后来程颢写的《上殿劄子》相一致。
程颢说:
“君道之大……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
……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
”(《程氏文集》卷一)小程和大程几乎同时提出了治道必须“君志先定”的问题,这有鉴于庆历新政的夭折以及此后的无所作为正是由于“君志”不定。
在他们看来,只有“君志先定”,才能够正确地择宰相(“责任”)、任贤臣(“求贤”);有了这样的“本”,则“不患无其用”。
反之,“顾三者不先,徒虚言尔”(《程氏文集》卷五)。
程颐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本是响应宋英宗的诏勅,“以比年以来,水潦为沴,八月庚寅大雨”,诏求臣僚“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病”,代其父程珦而写。
程颐在书中也趁势以“阴阳灾异”儆戒人君:
臣闻水旱之沴,由阴阳之不和;阴阳不和,系政事之所致。
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灾变,则必警惧以省躬之过,思政之阙,广延众论,求所以当天心,致和气,故能消弭灾异,长保隆平。
……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阴沴,圣心警畏,下明诏以求政之阙,诚圣明之为也。
(同上)
这里说的君主因“阴阳灾异”而下“罪己”引咎之诏,听闻对时政阙失的批评,可以说是历朝的惯例。
程颐在此只是更希望宋英宗出于“至诚”,而不要使其只成为“虚饰”。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病死,其子神宗继立。
熙宁元年(1068),程颢向新即位的宋神宗上了《论王霸劄子》。
他说: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
……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
……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尽于道而莫之御也。
(《程氏文集》卷一)
程颢从“王霸之辨”的高度来讲君主“立志”的重要。
他希望宋神宗“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
这仍是强调君主必须先“立志”,只有君主“正志先立”,才能“任贤勿贰,去邪无疑”,从而确立“致世如三代之隆”的改革方向,以实现“王道”的理想。
在《论王霸劄子》之后,程颢又向宋神宗上了《论十事劄子》,就“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同上)。
然而,当时宋神宗正“日益信用”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便开始了熙宁变法。
是年四月,程颢曾与其他七人被派遣到各地考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
此后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暴露了熙宁变法是以“理财”为急务之后,朝臣中就兴起了“新党”与“旧党”之争。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述: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对之日,从容咨访……(先生)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
先生不饰辞辨,独以诚意感动人主。
……尝言:
人主当防未萌之欲。
……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
……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
……荆公与先生虽道不同,而尝谓先生忠信。
……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
(《程氏文集》卷十一)
此处所说王安石与程颢的“道”不同,即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是“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所谓“理财”即国家如何多征收钱财,如青苗法是“官放息钱”,由国家贷钱给农民,然后收取本金和十分之二的利息),而程颢则主张实行“王道”,他劝说宋神宗“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
这里的主要分歧就是王霸、理欲、义利之辨。
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之后,程颢“数月之间,章数十上”。
现《程氏文集》卷一载其在熙宁三年上的两道《谏新法疏》,大意如《明道先生行状》所述,批评熙宁变法“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等。
程颢力主“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回督促新法施行、扰乱地方行政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为“去息”的仁政。
他更看重的是,由于宋神宗不能“正志先立”,以致熙宁变法汲汲于财利,当反对熙宁变法的“旧党”纷纷被罢贬之后,王安石就更多地任用“晓财利”之人,于是“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这就使他所希望的宋神宗能够“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完全走向了反面。
程颢对宋神宗先是“独以诚意感动人主”,但是在谏止新法的《再上疏》中却不得不以“天意”儆戒人君。
他说:
“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
”(《程氏文集》卷一)数年之后,程颐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中也以“彗(星)之为变多矣,鲜有无其应者,盖上天之意,非徒然也”,希望宋神宗敬畏“天戒”,“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为政,思己之自处,然后质人之言”,以己之“诚意”感动天心,消弭灾害,“奋然改为”(《程氏文集》卷五)。
熙宁变法之后,二程退处洛阳,几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
在此期间,一方面,道学的思想体系臻于完成;另一方面,二程把王安石新学视为超过释氏之害的“大患”。
从学术上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程氏遗书》卷二上);从治道上说,最根本的是要“格君心之非”。
二程说: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
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
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
(《程氏遗书》卷十五)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
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
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程氏外书》卷六)
从强调治道之本是“君志先定”,到明确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其间的思想是一贯的,但其微妙的变化却是道学家对于君主自身“立志”的自觉已感到失望(此不同于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所说“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而“君心之非”正是道学家实现“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
二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被尊为太皇太后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建年号元祐。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反对新法的旧党得势,司马光、吕公著任左右仆射。
此年,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而病逝。
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
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后世;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之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程氏文集》卷十一)
这段话不仅是小程称颂大程,而且是二程共同担当儒学“道统”的宣示。
此中包含的一个深意是,既然“善治”要由“真儒”来恢复,“政统”要由“道统”来确立其合法性,那么“道统”之尊要胜过“政统”的王权之尊。
宋哲宗即位后,程颐经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应诏入朝,获太皇太后的召见,被授以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等职。
在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程颐身为处士,未能施展其“外王”之志,如今得主持经筵,担当教导幼主、启沃君德的重任,这对于程颐是一个培植治道之“根本”,期以将“道统”用之于转化“政统”,从而恢复三代之“善治”的大好机会。
程颐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
”程颐听说哲宗“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乃问:
“有是乎?
”哲宗答:
“然,诚恐伤之尔。
”程颐说:
“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
”有一天,程颐讲罢未退,哲宗“忽起凭栏,戏折柳枝”,程颐进言:
“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
”哲宗对此劝阻“不悦”(《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
有时候,程颐也藉“天人感应”来说事。
他曾对哲宗说:
“天人之间甚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
昔子陵与汉光武同寝,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
子陵匹夫,天应如此。
况一人之尊,举措用心,可不戒慎?
”(《程氏遗书》卷二十三)
对于程颐在经筵的良苦用心,明儒薛瑄曾评论说:
“伊川经筵讲疏,皆格心之论。
三代以下为人臣者,但论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从本原如程子之论也。
”(《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这里说的“本原”,就是以“格君心之非”为治道之“本原”。
尽管程颐在启沃君德、格正君心上“潜思存诚”,“毕精竭虑”,但其以师道自居,教导严毅,却引起哲宗的“不悦”。
此时,朝臣中又有蜀党、洛党和朔党之争。
程颐在蜀、洛之争中被“巧为谤诋”,于元祐二年八月罢崇政殿说书职,差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离经筵去洛阳就职后,决意辞官退隐,以保持儒者的“进退之大节”。
他连上三道《乞归田里状》,接着又上两道《乞致仕状》。
元祐七年,程颐服父丧毕,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他又上《再辞免表》云:
“……惟今日冒死,为陛下陈儒者进退之道,为臣去就之义,觊望有补,乃区区上报之心也。
(《程氏文集》卷六)这次辞免被认为有“怨望轻躁”语,改授管勾嵩山崇福宫,程颐以“腰疾寻医”辞。
元祐九年,宋哲宗始亲政,复申秘阁、西监之命,程颐辞免,仍不准,又上《再辞免状》云:
“臣窃思之:
岂非朝廷以臣微贱,去就不足轻重,故忽弃其言,陛下不经省览,而辅臣莫以告也?
臣诚微贱,然臣之言,本诸圣贤之言;臣之进退,守儒者进退之道。
虽朝廷不见省察,臣恐天下后世有诵其言、思其义,而以进退儒者之道议朝廷也。
”(同上)程颐的这些辞免状,意味着道学的政治主张已经被君主的政治权势所挫败;他之所以屡申“儒者进退之道,为臣去就之义”,不过是要在现实的政治权势下保存“道统”的相对独立性和尊严,俾能“不得行于时,尚当行于己;不见信于今,尚期信于后”。
宋哲宗亲政后,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起用新党,召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将旧党打入“元祐党案”,“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
程颐被“放归田里”,绍圣四年(1097)“辅臣因历数元祐言者过当”,而哲宗更“怒颐为甚”,遂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三)。
程颐在涪州编管期间作成经学和理学的名著《伊川易传》。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言者论其(程颐)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
”(《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此年,程颐“下河南府体究,学者往别,因言世故,先生曰:
‘三代之治,不可复也。
有贤君作,能致小康,则有之。
’”(《程氏遗书》卷十一)在北宋末年的昏暗政治下,程颐的政治理想降格以求,虽然三代之治不可复,但仍寄希望于“有贤君作,能致小康”。
然而,“君心之非”构成了道学家“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
程颢曾经说: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程氏遗书》卷一)所谓“把持天下”就是把天下视为私有,这是与儒家的民本“公天下”思想相对立的。
程颐也曾论及君主制的得失:
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
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
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
后世既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
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程氏遗书》卷十八)
受历史的局限,程颐把五帝的禅让制看作“至公之法”,而又承认后世的传子制也是“天下之公法”。
在此所谓“公法”之下,“守法者有私心耳”,道学家希望君主能够“正心窒欲”,希望“大人”能够“格君心之非”,但君主的“私心”却又是道学家所难以克服、不能格正的。
这一治道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道学家的“外王”理想也就只能是“徒虚言尔”。
三
朱熹在政治思想上继承二程,把“格君心之非”或君主的“正心诚意”作为治道的“大根本”。
但是,南宋的皇帝比北宋的皇帝更加昏愦,朱熹的“外王”理想不能实现也是历史注定的。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向皇帝第一次上“封事”。
此年六月,高宗将皇位内禅给孝宗。
朱熹认为,秦桧死,孝宗即位,这正是“大有为之大机会”(《朱子语类》卷一三三)。
新即位的孝宗“诏求直言”,朱熹便于此年八月上《壬午应诏封事》。
在此“封事”中,朱熹首先提出“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
此“帝王之学”就是《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亦即“内圣外王之道”。
朱熹说:
“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
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
”朱熹希望孝宗能够延访深明《大学》之旨的“真儒”,“置诸左右,以备顾问”,将《大学》之旨“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后知体用之一原,显微之无间,而独得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传矣”(《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显然,朱熹在此所希望的就是能使二程所继承的儒学“道统”与南宋的“政统”相合一,而合一的条件就是君主能够“正心诚意”,克去“人心”的私欲,达到“道心”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从而由体而达用,由内圣而外王。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说:
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
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
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
推此数端,余皆可见,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这段话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朱熹的政治思考。
他所关切的政治问题包括任贤相、杜私门以立政,择良吏、轻赋役以养民,公选将帅、不由近习以治军,等等。
这些“要切”问题都有待于治道的“大根本”即君主能够“正心诚意”、使“人主之心术”归于正才能解决。
淳熙七年(1180),朱熹第二次向宋孝宗上“封事”。
他说:
“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
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
”在这段话之后,朱熹引董仲舒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可见在政治思想上,从董仲舒到朱熹也是一脉相承。
朱熹在对恤民、省赋、治军作出种种论述后,又“昧死”发出以下议论:
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
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
原其所以然者,诚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则天下万事将无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谨也。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
此处“君心不能以自正”,如同二程失望于君主自身的“正志先立”,从而由“大人”来“格君心之非”就是必要和当然的。
在这篇“封事”的“贴黄”(附文)中,朱熹说:
治天下当以正心诚意为本。
……比年以来乃闻道路之言,妄谓陛下恶闻“正心诚意”之说。
臣下当进对者,至相告戒,以为讳忌。
臣虽有以决知其不然,然窃深虑此语流传,上累圣德,下惑群听。
伏望睿明更赐财(裁)幸。
”(同上)
由此可见,宋孝宗“恶闻‘正心诚意’之说”,在当时早已是路人皆知;而朱熹说“决知其不然”,亦不过是朱熹的一厢情愿。
史载,宋孝宗在读了这篇“封事”后,大怒曰:
“是以我为妄也!
”(《宋史·道学三》)只因宰相赵雄奏:
“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适成其名。
若天涵地育,置而不问,可也。
”(《宋史·赵雄传》)孝宗才没有将朱熹治罪。
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再次入朝面奏。
“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
朱熹说:
“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这次面奏,朱熹向宋孝宗上有五劄,前四劄是讲刑狱与赋税的问题(朱熹此时担任江西提刑),第五劄即讲“正心诚意”,认为孝宗即位二十七年来“因循荏苒,日失岁亡,了无尺寸之效”,其原因在于“天理者有未纯”,“人欲者有未尽”;只有留意于“舜、禹、孔、颜所授受者”,存天理,去人欲,“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朱文公文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劄》)。
在朱熹戊申延和奏事的同年,他与陆九渊展开“无极太极之辩”。
朱熹在给陆九渊的信中提到:
“熹两年冗扰,无补公私,第深愧歉。
不谓今者又蒙收召……所恨上恩深厚,无路报塞,死有余憾也。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敬》五)陆九渊在回书中有云:
“吾人进退,自有大义,岂直避嫌畏讥而已哉。
……孟子曰:
‘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
’所谓行之者,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
”(《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二)可见,陆九渊对于朱熹的“格君心之非”是予以赞同和鼓励的。
淳熙十五年九月,朱熹又收到入朝的召命,他于十月上《辞免召命状》,十一月上《戊申封事》。
在此“封事”中,朱熹痛陈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
“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
……是必得如卢、扁、华佗之辈,授以神丹妙剂,为之湔肠涤胃,以去病根,然后可以幸于安全。
”朱熹为此“重病”所开列的“医国之方”仍是以正君心为“天下之大本”,外加以六事为急务,他说:
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
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
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
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朱熹的这道“封事”长达万言,疏入宫中时“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宋史·道学三》)。
但是,宋孝宗对于道学家早就有“好为高论而不务实”的成见,对于朱熹的“正心诚意”之说尤所厌闻,他对这道“封事”也不可能认真对待,而他本人此时已有“倦勤之意”,打算退休当太上皇了。
淳熙十六年二月,宋孝宗下诏传位给皇太子。
宋光宗即位后,朝政更加昏暗,道学人士纷纷被排挤出朝。
朱熹在此年写有《己酉拟上封事》,但鉴于当时的恶劣形势,最终拟而未上。
此年五月,陆九渊受诏知荆门军,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
“新天子即位,海内属目,然罢行升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群小骈肩而骋,气息怫然,谅不能不重勤长者忧国之怀。
”(《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三)朱熹在当年八月给陆九渊复信说:
“荆门之命,少慰人意。
今日之际,惟避且远,犹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为厌。
三年有半之间,消长之势,又未可以预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为也。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当时,朱、陆二人因“无极太极之辩”而争之甚烈,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惺惺相惜。
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朱熹说“非人力所能为也”,可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