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1.docx
《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1.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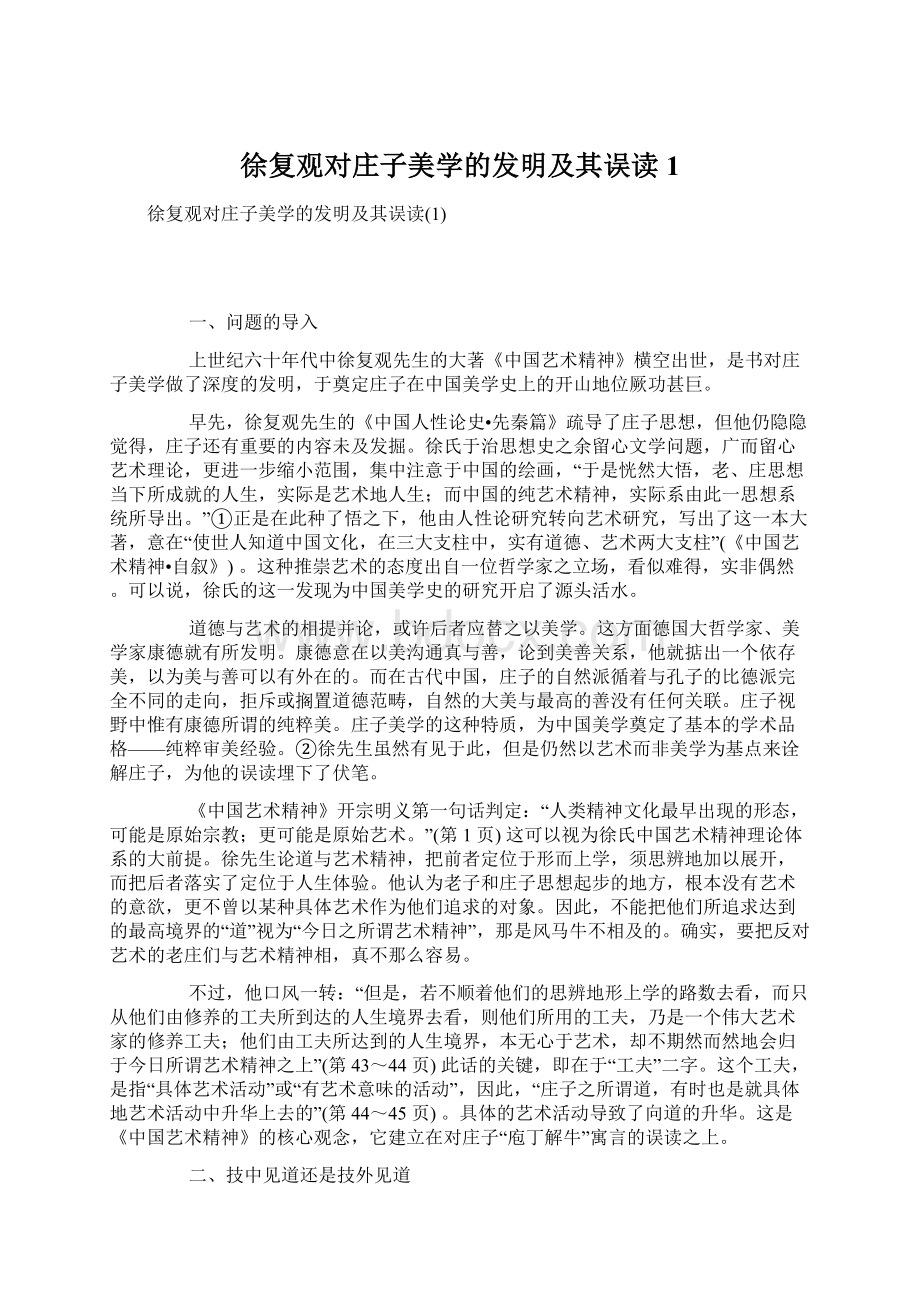
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1
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
(1)
一、问题的导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徐复观先生的大著《中国艺术精神》横空出世,是书对庄子美学做了深度的发明,于奠定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开山地位厥功甚巨。
早先,徐复观先生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疏导了庄子思想,但他仍隐隐觉得,庄子还有重要的内容未及发掘。
徐氏于治思想史之余留心文学问题,广而留心艺术理论,更进一步缩小范围,集中注意于中国的绘画,“于是恍然大悟,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地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
”①正是在此种了悟之下,他由人性论研究转向艺术研究,写出了这一本大著,意在“使世人知道中国文化,在三大支柱中,实有道德、艺术两大支柱”(《中国艺术精神•自叙》)。
这种推崇艺术的态度出自一位哲学家之立场,看似难得,实非偶然。
可以说,徐氏的这一发现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开启了源头活水。
道德与艺术的相提并论,或许后者应替之以美学。
这方面德国大哲学家、美学家康德就有所发明。
康德意在以美沟通真与善,论到美善关系,他就掂出一个依存美,以为美与善可以有外在的。
而在古代中国,庄子的自然派循着与孔子的比德派完全不同的走向,拒斥或搁置道德范畴,自然的大美与最高的善没有任何关联。
庄子视野中惟有康德所谓的纯粹美。
庄子美学的这种特质,为中国美学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纯粹审美经验。
②徐先生虽然有见于此,但是仍然以艺术而非美学为基点来诠解庄子,为他的误读埋下了伏笔。
《中国艺术精神》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判定:
“人类精神文化最早出现的形态,可能是原始宗教;更可能是原始艺术。
”(第1页)这可以视为徐氏中国艺术精神理论体系的大前提。
徐先生论道与艺术精神,把前者定位于形而上学,须思辨地加以展开,而把后者落实了定位于人生体验。
他认为老子和庄子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
因此,不能把他们所追求达到的最高境界的“道”视为“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确实,要把反对艺术的老庄们与艺术精神相,真不那么容易。
不过,他口风一转:
“但是,若不顺着他们的思辨地形上学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工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所谓艺术精神之上”(第43~44页)此话的关键,即在于“工夫”二字。
这个工夫,是指“具体艺术活动”或“有艺术意味的活动”,因此,“庄子之所谓道,有时也是就具体地艺术活动中升华上去的”(第44~45页)。
具体的艺术活动导致了向道的升华。
这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观念,它建立在对庄子“庖丁解牛”寓言的误读之上。
二、技中见道还是技外见道
非常自然,《养生主》篇③中著名的“庖丁解牛”寓言成为徐先生说明“工夫”的首选个案。
庖丁回答文惠君“善哉,技盖至此乎”之问云: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徐氏提出,首先应注意道与技的关系。
技是技能,庖丁说他所好者道,而较之于技是更进了一层,由此可知道与技是密切地关连着。
庖丁并不是在技外见道,而是在技之中见道。
徐氏着重指出两个“解消”:
首先,庖丁“未尝见全牛”,说明心与物的对立解消了;其次,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技术对心的制约性解消了。
于是他的解牛,成了无所系缚的精神游戏,他的精神由此而得到了由技术的解放而来的自由感与充实感。
徐氏把它当作逍遥游的一个实例。
徐氏谓:
庄子所想象出来的庖丁,他解牛的特色,乃在“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不是技术自身所须要的效用,而是由技术所成就的艺术性的效用。
所谓“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是就技术自身所得到的精神上的享受,是艺术性的享受。
这种效用和享受,正是庖丁“所好者道也”的具体内容。
至于“始臣之解牛之时”以下的一大段文章,乃庖丁说明他何以能由技而进乎道的工夫过程。
徐氏进而把它诠解为由技术进乎艺术创造的过程。
到此,庖丁那句“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于不知不觉中颠倒为“由技进乎道”,“进乎”也被奇怪地诠解为“升华”。
④徐氏的解读思路在学界并非孤立的现象。
⑤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徐氏在同一节中又举出两个例子。
其一,《大宗师》篇中的“南伯子葵问道女须女”寓言,女须女讲述自己学道的过程:
“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这是说,经由一个三日、七日而九日的守志过程,天下、万物、肉体生命等一切外在者都被忘却而遗落,精神趋于自由。
于是,“朝彻”,物我两忘以后心中如朝阳初升般通明透亮;“见独”,透过万物万象而发现那个绝对的道;“无古今”,时间被一举超越,主体进入永恒之境。
三日、七日和九日之守本身也是一个时间过程,它同时被超越。
这样一种“守”的经验,又被称为“心斋”、“坐忘”。
其二,《达生》篇中的“梓庆削木”寓言。
梓庆回复鲁侯之问曰“必齐(斋)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
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
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骸也”。
梓庆发挥他那“以天合天”的神技,原来也须心斋为之创造条件。
这两则寓言,徐氏评之曰:
前者讲人的闻道经历,以人的自身为主题,是庄子思想的中心、目的;后者以乐器的创造为主题,只不过是前者的比喻、比拟。
他尤其重视前者。
庖丁解牛经过了三个阶段:
其一,“始解牛时”所见无非全牛;其二,“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其三,“方今之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那么,这三个阶段是否正是“由技进乎道”的工夫过程呢?
无独有偶,徐氏上引两则寓言,也有一个三阶段(在庄子其他寓言中也可以是更多阶段)的时间过程,这一过程中所耗去的时间实际上并非用于艺术创作(或技巧训练)的工夫,而是用于守志。
“南伯子葵问道女须女”中三日、七日而九日的守志过程中一连串的“外天下”、“外物”、“外生”,其实是一个连续地忘却和排除已有的世俗经验的过程,可想而知,这种排除当然会包含已经习得的一切技巧。
梓庆在回复鲁侯“子何术以为焉”之问时坚决否定这是术:
“臣工人,何术之有”。
同理,庖丁也并不以为解牛靠的是技。
将此三个寓言综合起来看,当可推断:
庖丁解牛寓言中的三个时间阶段,其实正是心斋的忘却和排除过程,它恰恰是技外见道的,而并非“由技进乎道”的升华过程。
关于这一点,庄子书中证据多多,如《田子方》篇著名的“宋元君将画图”寓言中解衣般礴的画史,他被宋元君判为“真画者”时根本就没有进入实际的绘画创作,手上没有笔,眼前没有墨,只是脱去了衣服而已。
有意思的是,这则寓言的题材是最合乎徐先生所倡中国艺术精神的。
固然,庄子书中也有根本无关于艺术精神的寓言,如《达生》篇中“纪省子为王养斗鸡”寓言说将斗鸡连养四十日,以至望之似木鸡状,才可斗。
徐先生把它认同于庄子的人生体道之工夫过程,称其“由斗鸡的游戏活动,以追溯到鸡的艺术主体性,因而藉此以显示艺术精神之修养过程及其呈现之情状”(第109页)。
且不论把斗鸡到艺术精神是否牵强,我们只是设问:
此处连技也不存在,遑论技进乎道的升华过程?
《中国艺术精神》第十七节“庄子的艺术欣赏”一篇连引庄子书中九个寓言,一一细读,无不可如此概之。
《达生》篇判定所谓的“体道”,“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此处“知巧”即艺术训练的工夫,它外在于“纯气之守”的体道过程而被否定。
在庄子看来,在守志的过程中,最好的技巧也将隐于后台,而须将前台让位给由虚静之守所创造的新的经验。
这样一种被称为“心斋”、“坐忘”的经验非常特别,它强调“守”,似乎颇为消极。
其实不然,心斋经验正是通过排除道德关注、权力关注、技术关注和经验关注而获得审美关注———纯粹经验,循着回归自然的途径把世俗的人提升为审美的人。
其中消极向积极的转换显得非通常情、不达常理,不过,却真正是技外见道。
看来,徐先生所高标为艺术精神的所谓技中见道或技进乎道的积极的升华过程(所谓修养工夫)在庄子书中其实并不存在,那种自由的逍遥游是由“心斋”“坐忘”的看似消极的“守”经验来保证的。
有理由怀疑,徐氏在技与道之间作了合乎常识然而却违异庄子本意的跳跃,结论与前提判然为二,无由联结。
三、“心斋”是艺术精神还是审美观照
如果正如上所述,庄子“心斋”“坐忘”的经验向世人贡献了技外见道的纯粹经验而非技进乎道的工夫,自然可进一步追问:
此种经验究竟是艺术精神还是审美观照?
徐先生说:
“因为庄子所追求的道,实际是最高地艺术精神,所以庄子的观物,自然是美地观照。
”(第83页)推论中先是把老庄的“道”与近代的艺术精神挂在一起,进而再把美的观照与艺术精神挂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径直把“道”与美的观照挂在一起呢?
其实在讲到心斋时,徐氏已经走了这一步。
《中国艺术精神》引著名的“心斋”“坐忘”寓言的一节名为“心斋与知觉活动”。
强调知觉活动,是此节的旨意所在。
颜回向孔子请教“心斋”,孔子答曰:
“若一志。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
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
虚也者,心斋也。
”(《人间世》)颜回谈“坐忘”的经验: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大宗师》)脱离肢体,排除心智(分化的知识和智慧),进入虚的境界,直接体会大道。
徐先生论《逍遥游》中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断言“心斋”“坐忘”为庄子整个精神的中核。
达到心斋有两条路。
其一,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说“欲望解消了,‘用’的观念便无处安放”(第62~63页);其二,不让心对物作知识的活动,从对知识的无穷追逐中得到解放。
庄子的“堕肢体”、“离形”,指的是摆脱由生理而来的欲望;“黜聪明”、“去知”,则指的是摆脱普通所谓的知识活动。
两者同时摆脱,即所谓“虚”,“静”,“坐忘”,所谓“无己”、“丧我”。
徐氏认为庄子尤其重视后者,“忘知,是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剩下的便是虚而待物的,亦即是徇耳目内通的纯知觉活动,这种纯知觉活动,即是美地观照”(第63页)。
以“纯知觉活动”诠释心斋,强调其“纯”,将其定义为美的观照。
“心斋之心的本身,才是艺术精神的主体,亦即美地观照得以成立的根据。
”(第65页)此处徐先生解说心斋经验,已经脱开技进乎道的思路,而将之径直还原为知觉活动,以纯粹为其品格,离作为修养工夫的技是越来越远了。
看来,徐氏正走向庄子美学的核心。
他分析说:
所谓观照是对物不作分析的了解,而只出之以直观的活动。
这是看、听的感官活动。
不过,在审美观照中,因为此时知觉孤立化、集中化了,并不停留在物的表面,而是洞察到物之内部,直观其本质,以通向自然之心,因而使自己得到扩大,以解放向无限之境。
知觉的孤立化、集中化显然是心斋或坐忘的结果。
徐氏判定,孤立化、集中化的直观活动的根柢就是审美态度。
徐先生接着将现象学的纯粹意识引入,进入了比较美学的语境。
所谓的纯粹意识,是不能放入括弧的意识的固有存在,它是比经验意识更深入一层的超越意识,换言之,它不是经验的而是超验的东西。
徐氏认为美的观照也应以此为根据。
依现象学看来,在美的观照中,有经验的意识层和超越的意识层两层意识。
前者是指向美的意识的契机,后者则是其根据。
在纯粹意识中,对象与作用是同时的,两者成为相关项。
没有对象在前,作用在后的前后关系或因果关系,而是成为根源的关系,同时呈现。
两者是根源的“一”,这成为美的意识的特质和本质。
徐先生以现象学的纯粹意识来诠解心斋之心:
庄子忘知后是纯知觉活动,在现象学的还原中,也是纯知觉活动。
在此活动中,物我两忘,主客合一,如此才能直观本质,而庄子的心斋生洞见之明,可以给现象学以更具体的解答。
“因为是虚,所以意识自身的作用(Noesis)和被意识到的对象(Noema),才能直往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