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暴风雨三.docx
《走进暴风雨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走进暴风雨三.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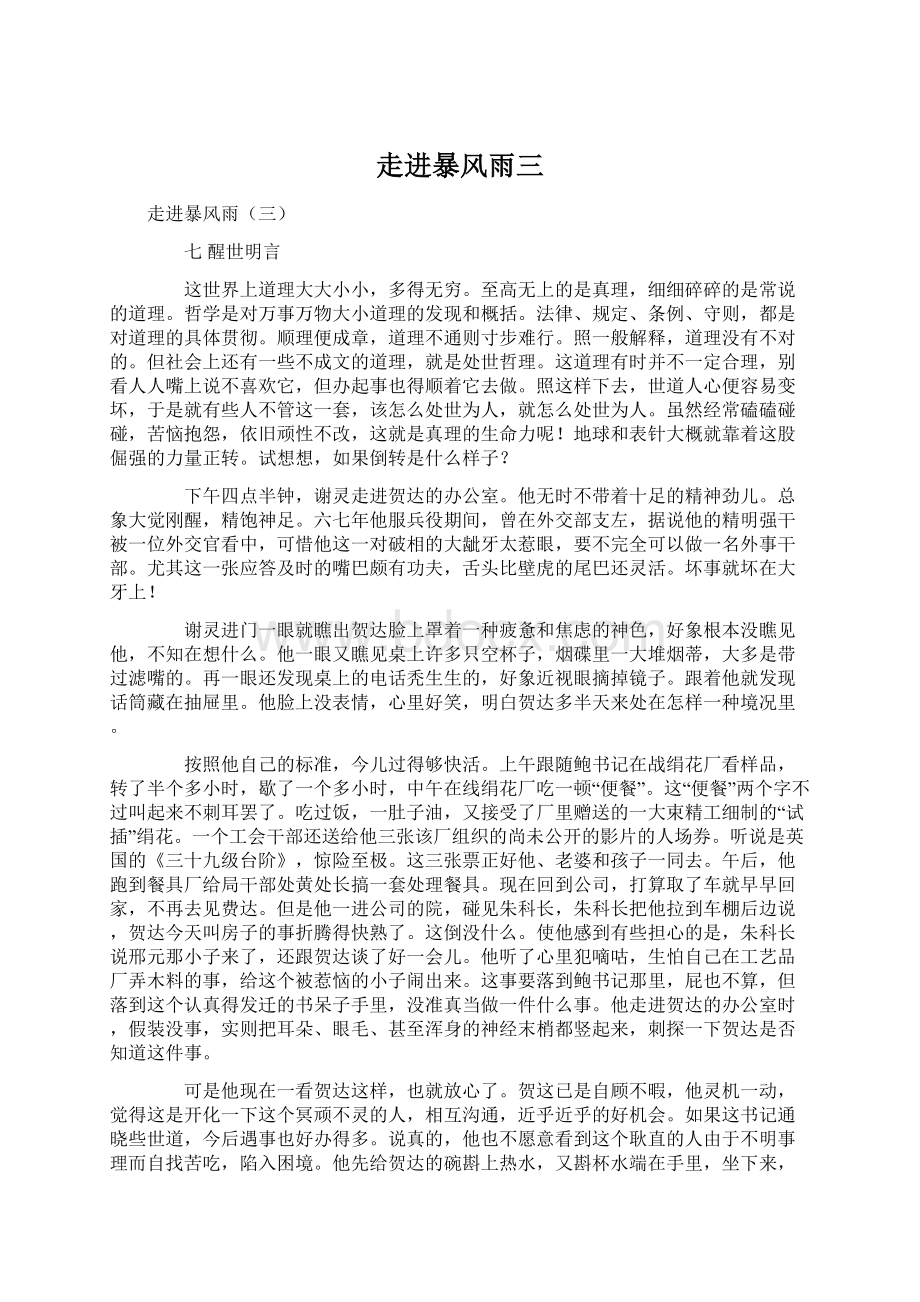
走进暴风雨三
走进暴风雨(三)
七醒世明言
这世界上道理大大小小,多得无穷。
至高无上的是真理,细细碎碎的是常说的道理。
哲学是对万事万物大小道理的发现和概括。
法律、规定、条例、守则,都是对道理的具体贯彻。
顺理便成章,道理不通则寸步难行。
照一般解释,道理没有不对的。
但社会上还有一些不成文的道理,就是处世哲理。
这道理有时并不一定合理,别看人人嘴上说不喜欢它,但办起事也得顺着它去做。
照这样下去,世道人心便容易变坏,于是就有些人不管这一套,该怎么处世为人,就怎么处世为人。
虽然经常磕磕碰碰,苦恼抱怨,依旧顽性不改,这就是真理的生命力呢!
地球和表针大概就靠着这股倔强的力量正转。
试想想,如果倒转是什么样子?
下午四点半钟,谢灵走进贺达的办公室。
他无时不带着十足的精神劲儿。
总象大觉刚醒,精饱神足。
六七年他服兵役期间,曾在外交部支左,据说他的精明强干被一位外交官看中,可惜他这一对破相的大龇牙太惹眼,要不完全可以做一名外事干部。
尤其这一张应答及时的嘴巴颇有功夫,舌头比壁虎的尾巴还灵活。
坏事就坏在大牙上!
谢灵进门一眼就瞧出贺达脸上罩着一种疲惫和焦虑的神色,好象根本没瞧见他,不知在想什么。
他一眼又瞧见桌上许多只空杯子,烟碟里一大堆烟蒂,大多是带过滤嘴的。
再一眼还发现桌上的电话秃生生的,好象近视眼摘掉镜子。
跟着他就发现话筒藏在抽屉里。
他脸上没表情,心里好笑,明白贺达多半天来处在怎样一种境况里。
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今儿过得够快活。
上午跟随鲍书记在战绢花厂看样品,转了半个多小时,歇了一个多小时,中午在线绢花厂吃一顿“便餐”。
这“便餐”两个字不过叫起来不刺耳罢了。
吃过饭,一肚子油,又接受了厂里赠送的一大束精工细制的“试插”绢花。
一个工会干部还送给他三张该厂组织的尚未公开的影片的人场券。
听说是英国的《三十九级台阶》,惊险至极。
这三张票正好他、老婆和孩子一同去。
午后,他跑到餐具厂给局干部处黄处长搞一套处理餐具。
现在回到公司,打算取了车就早早回家,不再去见费达。
但是他一进公司的院,碰见朱科长,朱科长把他拉到车棚后边说,贺达今天叫房子的事折腾得快熟了。
这倒没什么。
使他感到有些担心的是,朱科长说邢元那小子来了,还跟贺达谈了好一会儿。
他听了心里犯嘀咕,生怕自己在工艺品厂弄木料的事,给这个被惹恼的小子闹出来。
这事要落到鲍书记那里,屁也不算,但落到这个认真得发迁的书呆子手里,没准真当做一件什么事。
他走进贺达的办公室时,假装没事,实则把耳朵、眼毛、甚至浑身的神经末梢都竖起来,刺探一下贺达是否知道这件事。
可是他现在一看贺达这样,也就放心了。
贺这已是自顾不暇,他灵机一动,觉得这是开化一下这个冥顽不灵的人,相互沟通,近乎近乎的好机会。
如果这书记通晓些世道,今后遇事也好办得多。
说真的,他也不愿意看到这个耿直的人由于不明事理而自找苦吃,陷入困境。
他先给贺达的碗斟上热水,又斟杯水端在手里,坐下来,嘴唇不自主地蠕动一下,润泽那暴露在外、很容易风干的板牙,这样子好象蜘蛛准备好唾液要拉网了,他对着低头沉思的贺达说:
“贺书记,屋里没旁人。
我想跟您说几句私话,不知您愿意听不?
”
“嗯?
”贺达抬起眼瞧着他。
其实他看见了谢灵进来,但脑子里的事一时扯不断。
谢灵的话,使得他把心中所想的事暂时掐断。
他说:
“什么话,你说呀!
”
“我看得出您的心事很重。
”他说。
这句话有些象算命的。
“是的,你说为什么?
”
贺达点头承认,这就使谢灵来了兴致。
“那还用说,当然为了那八间房子呗!
我猜得出今儿一天,您给这件事缠住了。
来麻烦您的总有一二十人吧!
准都不是一般人,叫您左右为难,对不?
“谢灵目光忽闪闪紧盯着他,等着他的反应,一时大板牙露出半截。
贺达愈来愈感到他这几句颇象算命占卦的江湖口。
忽然他也来了兴致,微笑中连连点头:
“你都说对了。
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表现出一种钦慕佩服的神态。
谢灵得意非凡,用嘴唇抿了抿门牙,那牙给唾沫一抹闪出光亮。
他说。
“其实我昨天就料到了!
”
“噢?
你简直料事如神。
告诉我,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
“就在昨天您叫我通知工艺品厂,叫关厂长他们三天内必须搬出来时,我就知道您要陷进麻烦里来了。
”
“噢!
我明白了……”
“不,您还不明白。
”
“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根由?
”
“不,不!
”谢灵此刻完全象一位满肚子处世经验的老者,对待一个初入世道的小雏儿。
说话时,客气中含着几分教诲的意味:
“贺书记,您是领导,我是一般干部,按理我不该什么都说。
可是我完全为了您好,才肯说出心里话。
我以前认识您时,只觉得您平易近人,学识渊博,交情并不深。
仅此而已。
三个月来,和您天天相处,对您的印象的确很好。
您为人正派,脑子清楚,懂业务,一心用在工作上,办事泼辣,哈,这是从外表看不到的、我不多说您的优点,面对面这么讲话不好,反正公司里人人都这么认为。
可是……”
“你说,你说。
”贺达迫切想知道下边的话。
“哈,您就好象从天上掉下来的。
您可别生气,我并不是说您坏,只是打个比方。
就是说,你是不是过于认真?
人不能不认真,又不能太认真。
认真就象车上的闸皮。
没有问皮就会刹不住车,闸皮太紧车又开不动。
您别笑,社会就是认这套。
我知道您瞧不起社会这套,所以您现在就不好办了。
人在社会上生活,就得服从社会的这套,社会不会顺从人的意愿。
高英培说相声,把走后门的骂得够狠的,我就不信他买东西从来不走后门,办事从来不靠关系!
现在这社会不是应该堵后门,而是应当堵正门。
堵了正门照样有办法,没有后门反而不好办事。
您说,一个人从生到死谁离得开后门,在产院出生得走后门,托人照顾,找好病房和好医生,别出问题。
死后去火化也得走后门。
去年我岳母去世,送火葬场,殡仪馆就是不来车,最后还是托了人情才来车。
不然死了也没地方去。
再拿这八间房子来说,您何苦来呢,管它干什么?
如今房子是第一热门。
为了房子人们的眼睛都瞪红了。
每一平米里边都一大堆麻烦,您管它干什么?
再说这社会,看上去每个人都是孤零零一个,其实上下左右都连着一大群人。
别看一个厂长的职位有限,他在职位上,有人事权,有财权,有东西,就有人求他。
上边有人戳着,左右有人保着,下边有人撑着。
牵一动百,为什么一个单位换一个新领导,底下跟着就陆陆续续调换一批人?
社会是人和人组成的,动一个就惹一串。
人和人又是怎么连上的,您想想,说得太明白反没意思了。
我并不是赞成这套,可是如果您是个平民百姓,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也不求,照样过得下去,只不过时常有点为难事罢了。
但您是一个公司的书记,下属厂子就几十个。
每天学习、生产、人事、财务、技术等等多少事,得上上下下和多少人打交道?
为几间破房子就得罪这么多人,不是生把自己的路都堵上了吗?
您不是,这,哈哈哈……“他一口气说到这里,由于有句碍于情面的话就嘎然卡住了。
“傻瓜”贺达替他说。
“这话您能说,我不能说。
话别说这么直,但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您身为公司领导,上边求您的事多,下边求您的事更多。
您又是刚来,原先公司的人事矛盾您没参预过。
而且您又宣布过,不纠缠任何历史旧账。
这都很好,几方面的人都想拉您。
本来您是既得天时,又得地利,还得人和。
不过这么一来,您可就把所有有利之处一脚踢了。
贺书记,我在您面前瞎逞能了。
我说的都是事理,没有别的意思……”
“不,你这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
”贺达说。
“我哪来的真东西!
”
“确是真的!
我听你这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贺达郑重地说:
“我这个人看上去聪明,实际愚顽得很。
人都说‘入境随俗’,我总是自命清高,不肯随俗,也确实不大懂得世间的道理。
‘今儿经你这么一点,清醒多了,学到的东西可不少,于今后处世为人肯定有益。
过去有两本书,一本叫《醒世恒言》,一本叫《喻世明言》。
我把这两个书名合在一起赠给你,叫做’醒世明言‘。
”贺达的表情真象是如梦方醒。
谢灵以为贺达赞扬他,美滋滋而愈发得意地说:
“主要因为您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是感情用事,容易冲动。
感情一冲动就容易坏事。
感情这东西可得节约着用,否则就会把自己搞得不清醒,不分利害,最后白白吃亏。
我最初也和您一样,动不动就冲动起来,净吃亏,现在聪明多了,不再缺心眼儿了。
社会磨练人。
咱这公司更磨练人。
别看您现在这样,在咱公司呆上半年,经几件事,保证您不变也得变了!
”
贺达听了哈哈大笑。
他摸摸自己光洁的圆下巴说:
“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真难以想象!
”他再一瞧谢灵时,神情变得分外认真,“这么看,应付社会这一套你算齐全了。
可是再换一个角度看,你又并非十全十美,至少你缺少一样东西。
”
“什么?
”谢灵听得出贺达这两句郑重的话后边隐隐藏着讥讽。
他不觉闭上嘴。
无论他怎么拉长上嘴唇,也盖不上那讨厌的牙齿。
贺达笑了:
“看不见,摸不着,但十分关键。
”
“学习太少?
”
“不对!
”
“党性?
”
“你猜可猜不着。
”
“什么?
您说吧!
”
贺达忽问他:
“你现在有事吗?
”
谢灵犹豫一下说:
“什么事?
时间长吗?
我晚上看电影。
”
“那来得及,我现在领你去一个地方。
就在附近,顶多五分钟的路。
”
“干什么?
”
“找你缺少的东西。
”贺达笑着说。
他笑得挺神秘,象开玩笑,又不象开玩笑。
谢灵忽然有种感觉,他觉得贺书记不象自己刚才长篇大论所描述的那么简单。
他不知道自己这种感觉对不对。
八寻找
贺达领他走出公司大楼,穿过两个路口,拐进一条小街,再向右一拐,走入一条烂鸡肠子一样弯弯曲曲、忽宽忽窄的长胡同。
别看这儿离公司很近,抬头可以看到公司大楼竖着旗杆、避雷针和鱼骨天线的蘑菇状的楼顶,他却从来没去过,更不知这一片街道胡同的名称。
胡同的地面是黄土铺的,没有柏油罩面,中间凸两边回,靠近院墙根是排雨水的阳沟。
下雨天地面踩上去肯定滑哧溜,此地人把这种道儿叫“泥鳅背”。
当下旱情重,沟槽不但没水,也不潮,净是些烂纸、破塑料、断树枝、瓶盖、鸡毛什么的。
院墙都很矮,打外面一伸脖子就能看进去。
里边的房子更矮,一间紧挨一间,这倒不错,这家打开无线电,那家没有无线电也一样能听。
但要是晾尿布、煮腥鱼、熬臭胶,可就一臭十家了。
谢灵不知贺达为什么领他到这儿来。
贺达也不说,好象故意要把这件事搞成一个谜,答案叫谢灵自己去猜。
走到一个敞开的院门前,贺达只说:
“到了,请进吧!
”两人就进去了。
谢灵刚迈进院门,一脚踩空,险些跌倒,多亏贺达拉住他。
贺达说:
“你进这种院可得记住,这儿院子比街面低一截,屋里又比院子低一截。
俗称‘三级跳坑’。
你大概是头一次到这种院子来吧!
”
谢灵一看,这个进身只有五六尺的小院,果然比胡同低半尺,只有两三间房,院里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只留着走道。
迎面一扇矮矮的、油漆剥落并补修过的小门里,传出嘻嘻哈哈的说笑声,还有鱼呀、肉呀、油炸面食的香味飘出来。
贺达上去敲门。
应声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小脚老太太。
这小脚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代了。
这小脚所象征的封建社会的残余能够一起灭绝吗?
很难!
这老太太一见贺达就说:
“呀!
您呀!
贺书记,您又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您今儿来得正是时候!
”
“什么好事叫我赶上了?
我可不是有福气的人呢!
”贺达笑呵呵开着玩笑。
谢灵听着有点奇怪,三个月来,他不知道贺达还能说笑话。
“今儿是老头六十五岁生日,您进来喝一盅吧!
”
“噢?
那好:
进去拜个寿!
”贺达满面高兴,与刚才那副愁眉苦脸的模样一比,完全象换了一个人。
两人猫腰钻进这扇大约只有五尺高的小门。
谢灵记着贺达刚才的话,进屋时分外留意,以免又踩空。
屋里的确比院子又低半尺。
刚进门,堵着门口站起男男女女。
大大小小七八个人。
人人穿得干干净净,脸上都喜笑颜开,朝他俩客气地点头招呼。
这些人中间放着一张小小的方桌。
糖酒饭菜,摆得满满的。
谢灵发现其中一个老头挺面熟,但猛然见面,一时想不起是谁来了。
“您怎么有空儿来了?
”老头说。
那张满是深折的老脸上显得微微有些紧张和局促。
“我不是正好赶上给您拜寿来了?
”贺达笑道,“您欢迎吗?
”
“欢迎欢迎。
嘿!
”老头惊喜地在原地转了两圈,要给客人们找坐位,但屋里的人挪来挪去,竟挪不出一个空儿。
贺达和谢灵无法进去,好象堵在挤满乘员的公共车厢的门口。
老头歉意地对贺达和谢灵说:
“今儿我大儿子一家都来了,就挤点。
”
然后扭头对那些年轻人说:
“你们先出去呀,请客人进来坐。
”
“不!
‘客不压主’!
贺达摇着两只手说,”你们正吃得好好的,哪能我们一来就停了。
“
不等这老头说话,屋里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都挤出屋去,贺达拦也拦不住。
“他们都到哪儿去?
这怎么行?
这怎么行?
要是这样,我们可就走了!
”贺达着急起来。
“没关系!
”老太太轻轻一拍贺达的肩膀说,“他们到邻屋坐坐。
老街坊了,互相都这样,谁家里来客人坐不下,都到别人家躲躲。
他们不走,这屋子就实在进不来人了:
”她苦笑着。
人走净,谢灵一怔。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屋子,更想不到这样小屋装得下这么多人。
最多恐怕只有八千米吧!
一张床占去一半。
另一边放着一个小木柜,上面给暖壶茶碗,瓶罐筐盒占满了。
中间临时支起这折叠式小桌,一边靠床放着,这边的人就可以坐在床上,另外三面都是小凳子,凳子腿互相交错,刚好挤下来。
怪不得刚才那些年轻人挪来挪去竟然挪不出一个坐位来。
这儿的人口密度真够得上世界第一了。
谢灵抬头再一瞧,更使他吃惊!
床上那空间,居然打了两层阁楼,好象鸽子窝,里边铺着褥垫,塞着棉被枕头。
他抬头仰望的当儿,老太太在一旁说:
“这是孩子们睡觉的地方。
最上边一层是二儿子和媳妇,中间一层是孙女和小儿子。
这下边是我们老两口,带一个外孙。
七口人,分三层。
”
老头截住她的话说:
“人家来串门的,别跟人家叨叨。
人家是公司领导,又不管房子。
你这么大岁数。
嘛时候才能懂点事。
”然后对贺达说,“别听她唠叨,我这儿还可以。
全家老少住在一起倒热乎,嘿嘿。
”
老太太挨了训,心里不高兴,一边给贺达斟茶,一边嘟嘟囔囔小声叨叨着:
“你当然不错了,那些盆花就占了一大块地界。
人都没地方呆,还摆弄花。
过些天下雨,又得往外淘水了。
你淘?
”“
老头因为有客人在,忍气吞声装听不见。
贺达见了,就把老太太斟给他的茶让给老头,好把老头心里的火岔开。
谢灵瞧见,洞式的小窗口摆着十来盆上好的花。
米子兰,茉莉,玉树,西番莲,倒挂金钟……还有一块上苔的水山石。
当下西晒的窗子正是夕照斜入,一片鲜翠碧绿,生意盈盈,尤其那苍石,毛茸茸好象裹了一块鲜薄的绿毡。
但这些盆花的确占了不小的一块空间。
“大爷,您的花养得真不错呀,我家养过不少盆花,没过两个月就死了,也有这么一块山石,无论怎么搞也长不出苔来。
我得好好向您学点养花经验呢:
”谢灵笑嘻嘻说,“您是花匠吧!
”
老头花白的粗眉朝他惊讶地一跳,跟着脸就沉了下来。
贺达说:
“怎么?
你不认识他?
他不是工艺品厂传达室的老龚头吗?
”
“哟!
对!
”谢灵叫道,“怪不得刚才一见面我就觉得挺面熟。
”
老龚头瞥他一眼,抬起相茬丛生、四四方方的下巴,厚嘴唇一动,似乎要说什么,但没开口就把话咽下去,在喉咙处化为沉闷的一声,低下头来。
贺达完全明白老龚头想说什么、就替他说:
“小谢,你眼睛可不能总盯着上边的人呢!
”说完笑起来,表示他这话是开玩笑。
谢灵当然听得出这不仅仅是玩笑。
他挺窘,似笑非笑,大板牙在嘴唇中间一闪闪地忽隐忽现。
老龚头顿时眉开国朗。
贺达说出他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这使他痛快又激动。
他站起身,端起桌上的酒递过来说:
“贺书记,您们二位都喝一盅吧!
”
贺达接过酒说:
“好,给您祝寿!
给大娘道喜。
祝您们——”刚说了这两句,目光无意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一扫,下边的话就象横在嘴里卡住了,满脸兴冲冲的表情忽然变得沉重和不安。
他把尚未沾唇的酒盅放在桌上,垂下头,半天没说话。
谢灵差一点把酒倒进肚里,多亏他眼疾手快停住了。
但他对贺达这突变的表情不明其故。
只见贺达带着一种深深的愧疚说:
“我,我们当干部的无能,自私,忘记了群众,没有为群众的疾苦着想。
辛辛苦苦劳动了一辈子的老人,至今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可是我们干部、尤其我们自己的条件为什么好得多?
”他说到这里,感情冲动起来,脸颊顿时通红,连耳朵都红了,好象给夕照映上去的,又象心里的火蹿上来的。
他一眼瞧见窗前那几盆姿态生动的花草,声调转向深沉:
“您使我感动!
老龚头!
身居斗室,还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了养育这几盆美丽的花。
热爱生活!
我们中国人民多么热爱生活。
但是,真正而美好的生活为什么只能得到这样一块窄小的天地?
怨谁,只能怨我们!
我们把党交给我们分配给人民的东西抢占了,私分了!
把人民交给我们的权力变为图谋个人私利的权力!
权力依仗权力,权力交换权力,这样下去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人民。
一旦变成可以随便借用的名义,它实际上就十分卑微可怜了。
老龚头……原谅我,今天我喝不下去你的酒。
“说到这里,他背转过身去,摘下眼镜,抬起手背抹了抹眼角,这使谢灵莫名其妙。
“不,不……”老龚头声音发抖,“您别这么说。
没有党,我老龚早完了。
国家有困难,干部也不易。
我们厂里那几间房又不是您分的。
再说我已经退休了,在厂里补差,房子就不该有我的份儿了。
我这已经挺足了,真的!
嘿嘿。
”
老太太在一旁说:
“你也别跟贺书记说这些假话了。
你平时在家里说话时是这个意思吗?
书记什么不明白,你何苦再来‘骗自己’?
”
谢灵听了,好似想到了什么,好奇地问。
“老龚头,我听人家都叫你‘骗自己’。
干嘛‘骗自己’呢?
”
老龚头苦涩地一笑,说出一句真心话:
“为了不找别扭。
人不能太明白。
过去老人们不是爱说一句,叫做‘难得糊涂’吗?
”
贺达再果不下去,匆匆向龚家老夫妻俩告辞而去。
他在返回公司的路上步履匆匆,好象竞走一样,话也不说,仿佛有股气顶着他朝前奔。
谢灵迈着大步才勉强跟上,扯得大腿叉子疼,裤裆的扣子绷掉一个也来不及去拾。
进了公司大楼,人已下班。
大楼显得分外宁静。
值班的老商递给贺达一个纸条,说是一个青年人留给他的。
他打开一看,竟是邢元留给他的。
上面的字真难看,好象一堆横七竖八爬在上面的苍蝇,内容却叫他耳目一新;
贺书记:
您托我的事办了。
没想到郗师傅住得这么难。
今后有房子,先让他住,我决不跟他争。
邢元
贺达心里感到象阳光透入那样亮堂和舒适。
他心里生出许多感触,只是一时来不及往深处思索,谢灵却在旁边问:
“您刚才说我缺少点什么,您一直役告我。
跑了一圈,现在该告诉我了吧!
”
贺达一怔。
望着他笑嘻嘻、龇着门牙、过分精明的一张脸,歪着头面对他,话里不无讥消地说:
“你缺的,竟然还没找到?
”
“找到什么?
”
贺达告诉他普普通通两个字:
“感情。
”
“感情?
您别开玩笑了,这算什么呢。
”谢灵笑道。
他以为贺达在和他打哑谜。
贺达忽然懂得一个道理:
缺钱好办,缺少感情无法补充。
感情不能借,挤也挤不出来。
缺乏感情的人很难被感动。
这就使他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面对别人的艰难困苦。
竟会那么无动于衷!
谢灵晚上要去看电影,急匆匆走了,贺达回到家,爱人去接孩子,还没回来。
他把一天来经历的事细细想一遍。
有时,人在一天里比十年中成长得还快。
他今天就是这样。
特别是谢灵讲的那些处世格言,使他多年来不曾看透的东西一下子彻底清楚了。
他应当感谢谢灵,帮助他把那么多感性认识概括出精辟的理论。
这也就使他心里的主意更加坚定。
他一时心血来潮,捉笔展纸,画了一大块顽石,还题了一首顽石歌:
凿不动,砸不开,不挂尘土不透水,老君炉里炼三年,依旧这个死疙瘩。
写完之后,不由得孤芳自赏地念了两遍。
他大喜欢自己瞎诌的这四句打油诗了,心里有种痛快的感觉。
这感觉象把扫帚,一时把白日积在心里的烦扰扫却一空。
九欲进则退,再用一招
倒霉!
赶上一段上坡路,比顶着五级风蹬车还费劲。
从公司到工艺品厂本来有一条道宽人少、平平坦坦的柏油马路。
可是贺达偏要走这条道。
他为了在到达工艺品厂之前,有时间把那里刚刚又发生的一件意外的事琢磨一下,这就给他自己找了麻烦。
麻烦都是自找的。
“无欲自然心似水,有营何止事如毛。
”
他想起来人这两句诗,拿这诗嘲笑自己。
“凡是找麻烦的人必定自食其果!
”
他又想起妻子骂他的话。
这话说得并不错。
可是这些话现在对于他毫无效用。
他想,自己恐怕天性就是自找麻烦的。
爱管事,爱揽事,不怕事。
当麻烦死缠着他,他一点点冲开这麻烦的包围圈,也是一种快乐。
这样,各种麻烦就象寻找知音一样专来找他。
真是倒霉蛋儿!
他觉得自己挺好笑,倒霉蛋儿才总碰上倒霉事儿,就象他赶上的这一段上坡路。
车链绷得笔直,和轮盘的齿牙磨得轧轧响。
但他不能松劲,一松就倒回去。
他感到,这情况很象他着手的工艺品厂的事——他从中得到了启发。
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把蕴藏在身体各处的力量都运到两条腿上使劲蹬。
任凭这两天由于天阴而犯风湿的膝关节隐隐作疼,脚腕子已经酸累发软,一想到工艺品厂那团虎视眈眈等待着他的麻烦,两条腿竟然又加倍地生出力气来。
原来力气不在肌肉内,而在精神里。
自从他通知关厂长等人限期三天搬出来后,三天间他顶住四面八方、重重叠叠的压力。
这三天是一场艰苦的、全力的、针锋相对的较量,他一个人与那么一股人多势众的力量抗衡,有生以来也是头一次。
他豁出去一切,不肯倒退半步,软的、硬的、软里带硬的,他一概都尝到了。
现在看来不过如此,哪有小说电影编造得那么多惊涛骇浪呢?
如果一个人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捍卫真理也并不那么艰难。
三天里,他的支持者为他担心,他的反对者等着瞧他的笑话。
他却天天叫谢灵给工艺品厂上下午各打一次电话,反复重复那句话,只字不改:
如果不交出房间钥匙,就交出党票!
二者必取其一!
他坚信这些靠职权巧取豪夺房屋的当权者,在最后的抉择中,不会舍弃党票而要房子。
对于这些人来说,为一两间房子,一次性使用党票,太不值得。
但前天他从那“老同学”车永行那里,得知关厂长把原先住房让给亲友,自断后路,可就叫贺达骑虎难下。
贺达猜想,关厂长也许要用“拖兵”之计,赖在房里不走,拖过一年半载,造成既成事实,他就败了;不仅败在房子上,而且他这个堂堂的公司书记从此也就再也别想神气起来。
他想赢又没办法,反正他不能把关厂长他们轰出来,轰到哪儿去?
眼看着限期三天就到,他急得火上来,眼眶通红,嗓子眼儿一跳跳地疼,多年戒掉的烟,昨儿又买了一包,他暗暗发誓:
拿下这八间房就立即把这盒烟扔掉。
发过誓,他又担心这烟卷永远拍下去了。
谁料到今儿一早,谢灵在他桌上留个条子说,关厂长他们都已经搬出来,房子腾空,他惊喜又惊异,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可是谢灵不在,也没说到哪儿了,他便打电话给工艺品厂,只听对方气冲冲又粗野地说:
“你他妈别在上边坐着喝茶了,下来看看吧!
”
跟着“啪”地撂了电话。
他听不出对方是谁,但决不是上次那小伙子,分明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而且带着恼怒和敌意。
他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预感关厂长另有高招,他绞尽脑汁,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来。
这些天关厂长每一招大都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他想,一个人本来应当把别人往好处想,为什么生活逼着他不这样思考问题呢?
有时他觉得自已不应当把别人猜测成这样那样,但事实总比他猜想得还要复杂……他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工艺品厂。
一进门,他就感到有些异样。
远远看见办公楼前放着许多箱子、大柜、小柜、炉子、烟囱和高高的衣架,还有一堆堆装杂物的荆条筐和牛皮纸盒子。
大柜上的镜子照着院里来来去去的人。
他放下车,迎面碰上技术股长矬子伍海量。
这张跟帽檐宽窄差不多的短脸上,满是焦急神情,不等他问就说:
“关厂长他们昨夜全都搬到厂里来了。
他们说,搬不回去,只能住在办公室,这一下就乱套了!
我那间办公室叫王魁的儿子占去了。
现在只能在车间里乱转。
”
贺达感到脑袋里嗡地一响,好象冷不丁挨了照面一拳。
但他这次没懵。
几天来遇事不少,真长经验。
他马上就看破,关厂长这是“欲进则退”新的一招,从那房子一直搬进厂里来,有意搅出一个更大的乱摊子,把他摆在中间,叫他拔不出腿来。
请神容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