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袁的小说《师母庄瑾瑜》《师母》.docx
《阿袁的小说《师母庄瑾瑜》《师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阿袁的小说《师母庄瑾瑜》《师母》.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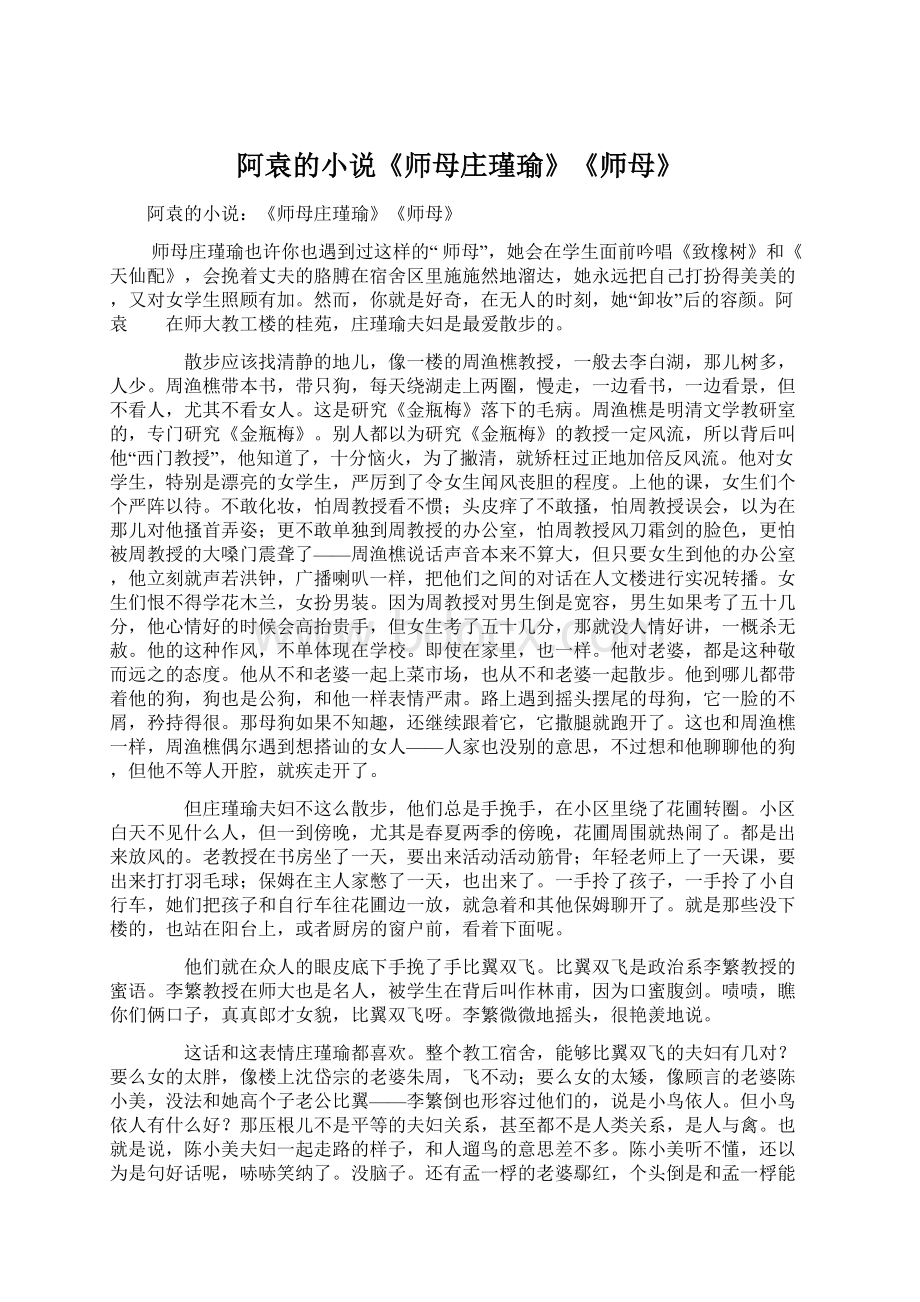
阿袁的小说《师母庄瑾瑜》《师母》
阿袁的小说:
《师母庄瑾瑜》《师母》
师母庄瑾瑜也许你也遇到过这样的“师母”,她会在学生面前吟唱《致橡树》和《天仙配》,会挽着丈夫的胳膊在宿舍区里施施然地溜达,她永远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又对女学生照顾有加。
然而,你就是好奇,在无人的时刻,她“卸妆”后的容颜。
阿袁 在师大教工楼的桂苑,庄瑾瑜夫妇是最爱散步的。
散步应该找清静的地儿,像一楼的周渔樵教授,一般去李白湖,那儿树多,人少。
周渔樵带本书,带只狗,每天绕湖走上两圈,慢走,一边看书,一边看景,但不看人,尤其不看女人。
这是研究《金瓶梅》落下的毛病。
周渔樵是明清文学教研室的,专门研究《金瓶梅》。
别人都以为研究《金瓶梅》的教授一定风流,所以背后叫他“西门教授”,他知道了,十分恼火,为了撇清,就矫枉过正地加倍反风流。
他对女学生,特别是漂亮的女学生,严厉到了令女生闻风丧胆的程度。
上他的课,女生们个个严阵以待。
不敢化妆,怕周教授看不惯;头皮痒了不敢搔,怕周教授误会,以为在那儿对他搔首弄姿;更不敢单独到周教授的办公室,怕周教授风刀霜剑的脸色,更怕被周教授的大嗓门震聋了——周渔樵说话声音本来不算大,但只要女生到他的办公室,他立刻就声若洪钟,广播喇叭一样,把他们之间的对话在人文楼进行实况转播。
女生们恨不得学花木兰,女扮男装。
因为周教授对男生倒是宽容,男生如果考了五十几分,他心情好的时候会高抬贵手,但女生考了五十几分,那就没人情好讲,一概杀无赦。
他的这种作风,不单体现在学校。
即使在家里,也一样。
他对老婆,都是这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从不和老婆一起上菜市场,也从不和老婆一起散步。
他到哪儿都带着他的狗,狗也是公狗,和他一样表情严肃。
路上遇到摇头摆尾的母狗,它一脸的不屑,矜持得很。
那母狗如果不知趣,还继续跟着它,它撒腿就跑开了。
这也和周渔樵一样,周渔樵偶尔遇到想搭讪的女人——人家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想和他聊聊他的狗,但他不等人开腔,就疾走开了。
但庄瑾瑜夫妇不这么散步,他们总是手挽手,在小区里绕了花圃转圈。
小区白天不见什么人,但一到傍晚,尤其是春夏两季的傍晚,花圃周围就热闹了。
都是出来放风的。
老教授在书房坐了一天,要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年轻老师上了一天课,要出来打打羽毛球;保姆在主人家憋了一天,也出来了。
一手拎了孩子,一手拎了小自行车,她们把孩子和自行车往花圃边一放,就急着和其他保姆聊开了。
就是那些没下楼的,也站在阳台上,或者厨房的窗户前,看着下面呢。
他们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手挽了手比翼双飞。
比翼双飞是政治系李繁教授的蜜语。
李繁教授在师大也是名人,被学生在背后叫作林甫,因为口蜜腹剑。
啧啧,瞧你们俩口子,真真郎才女貌,比翼双飞呀。
李繁微微地摇头,很艳羡地说。
这话和这表情庄瑾瑜都喜欢。
整个教工宿舍,能够比翼双飞的夫妇有几对?
要么女的太胖,像楼上沈岱宗的老婆朱周,飞不动;要么女的太矮,像顾言的老婆陈小美,没法和她高个子老公比翼——李繁倒也形容过他们的,说是小鸟依人。
但小鸟依人有什么好?
那压根儿不是平等的夫妇关系,甚至都不是人类关系,是人与禽。
也就是说,陈小美夫妇一起走路的样子,和人遛鸟的意思差不多。
陈小美听不懂,还以为是句好话呢,哧哧笑纳了。
没脑子。
还有孟一桴的老婆鄢红,个头倒是和孟一桴能比翼的,但其他方面没法比翼,一个教授,一个无业游民;一个北大中文系的,一个没有学历的文盲,怎么比翼?
也就她和胡丰登,当得起比翼双飞这四个字。
他们夫妇俩,不论生理高度,还是文化高度,还是社会地位高度,都十分匹配——虽然也略有参差,比如胡丰登是一米七,她一米六八;比如胡丰登是博士后,她是博士;比如胡丰登是中文系主任,她是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但这参差也正好,没有这参差,就不是我们中国式的夫妇关系了,中国式的夫妇关系,美妙之处在于,要“照花前后镜,花面相辉映”——辉映自是要的,但同时也要前后。
而她和胡丰登正是这样,有前有后,相互辉映。
当然,关于参差这部分,她基本是秘而不宣的,没必要宣,这种夫妇伦理和审美观,多少还有封建的意味,再说,她的价值也不在参差,而在比翼。
所以,她喜欢再三表现的,还是比翼那部分。
每年系里的新年联欢晚会,她都会表演一个节目,诗朗诵,舒婷的《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庄瑾瑜朗诵得声情并茂,字正腔圆,每次都能获得系里师生的热烈掌声,包括胡丰登主任——当然包括胡主任,因为庄瑾瑜朗诵时一直是深情凝视他的。
教务员小冯十分伶俐地塞给胡主任一个大红气球,要胡主任上去当玫瑰献,胡主任半推半就,上去献了。
两个人站在台上,昂首挺胸,真是两棵树的样子。
师生们又一次热烈鼓掌。
小冯起哄般喊:
《天仙配》《天仙配》。
一边喊,一边对学生干部摇手示意,学生干部立刻会意,马上站起来指挥同学一起喊,一二三,《天仙配》;一二三,《天仙配》。
这也是中文系新年晚会的仪式之一,每年都是这样的,《致橡树》之后,就是主任夫妇合唱黄梅调《天仙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
”最后一句,他们是一唱三叹,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
庄瑾瑜看着胡丰登,胡丰登也看着庄瑾瑜。
庄瑾瑜还翘了兰花指,双手摆动,学小鸟做飞翔状。
师生们再一次热烈鼓掌——一边鼓掌,一边低声议论。
他们刚刚是树,现在是鸟,倒是进化得快,一个老师说。
一对鸟夫妇,另一个老师说。
这些话庄瑾瑜夫妇听不见,他们在台上,正容光焕发地接受小冯献的红气球和两条洁莱雅毛巾——这是纪念品,每个表演了节目的老师都有的。
不过老师们拿的纪念品不一样,有的是两块钱一柄的牙刷,有的是二十几块钱一条的毛巾,都由小冯随手拿。
不单在别人面前,就是在私底下,庄瑾瑜也逮了机会在胡丰登面前表现他们夫妇的这种好。
当然不是用《致橡树》《天仙配》那种直接的形式,而是言彼意此,用反衬的手法。
她在厨房里,摘着四季豆角——胡丰登喜欢吃橄榄菜炒四季豆角,就白米粥,他原来最喜欢吃的是红烧肉,浓油赤酱的,拌饭,他一气能吃两大碗,但自从当了几年系副主任之后,他的饭量小了,口味也转向清淡,这是自然的,外面的宴席一多,他肠胃的膏腴就厚了,不论是从健康的角度,还是从饮食美学的角度,都势必会有一种反璞归真的必要。
他对这种返璞归真,是颇为自得的,经常拿到饭桌上来炫耀。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几杯酒之后,他会摇头晃脑地背苏轼的《浣溪沙》,每次都背,背完之后,就感慨万端地说,苏轼的清欢,是一盘蓼茸蒿笋,我的清欢,更简单,一碗粥,加一碟橄榄菜清炒四季豆,就可。
语意里似乎他比苏轼的人生境界更高。
他的这说法,一开始有人嗤之以鼻,比如社科处的副处长许彦群,许彦群是苏轼的忠实粉丝,对苏轼的迷恋,按他老婆的说法,远远超过了对她的迷恋。
师大行政人员的业余爱好一般是麻将,稍微风雅一点的,是下棋,或者垂钓,但许彦群的业余爱好不一般,是背苏轼词。
什么《念奴娇》,什么《水调歌头》,什么《江城子》,那是小菜数碟,不算什么,他的理想,是在退休之前把苏轼的三百几十首词全背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在给办公室打开水的路上——打开水本来是科员小乔的事,但如果遇到下雨天,许处就亲自去打了,这是怜香惜玉,也是许处想要情景交融地吟哦苏东坡的《定风波》。
在雨里吟哦苏东坡诗,太有境界了!
而这个胡丰登,竟敢拿自己和苏轼相提并论,不仅相提并论,还有僭越之意,实在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但校长说话了,校长说,橄榄菜炒四季豆?
这个好,好,比蒿笋好。
校长一开腔,在师大几乎算御批了,许彦群再有意见,也不能说什么了。
全师大的人有一半现在都知道中文系胡主任的清欢,有学生甚至篡改了苏轼的《浣溪沙》:
白米稀饭盛晚盏,橄榄季豆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胡丰登每次晚宴回来,保姆都歇下了——就是没歇下,庄瑾瑜也不会让她染指这道菜,倒不是因为保姆的手艺不好,事实上,她家的保姆虽然长得不怎么样,菜还是做得不错的,但这道菜庄瑾瑜还是想亲自做,因为校长说过那话之后,做这道菜,就有奉旨的意思了。
保姆有什么资格奉旨呢?
再说,庄瑾瑜也喜欢在这个时候和胡丰登聊天,胡丰登这时心情总是很好,他喝了酒,是微醺的状态,没了主任的端谨,笑嘻嘻的——他不笑时,颧骨高耸,眼神冷漠,有一种哥特似的阴森,学生都怕他,即使庄瑾瑜,不知为什么,有时也生出几分怯意,但一笑,又有一种妇人似的和煦。
庄瑾瑜这时候就喜欢和胡丰登闲话。
有一种平常夫妻的岁月静好。
沈岱宗家还真是特别,是沈岱宗下厨房。
一个堂堂大教授——庄瑾瑜自然知道沈岱宗其实是副教授,但此刻为了强调他和他老婆朱周的差距,她就很慷慨地把他破格提拔为教授了——竟然系了围裙,为他老婆洗手做羹汤。
她老婆算什么?
一个外语系资料员!
倒是吃得心安理得。
庄瑾瑜这话,是复调,表面是批评沈岱宗夫妇。
其实呢,是表扬自己。
有几个女人能和她一样?
出得厅堂,入得厨房。
但这话不能直接说,也不能由她自己说,说了,就太没韵味了。
做女人和做文章是一样的,讲究意在言外,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这个胡丰登懂,他们夫妇琴瑟和谐,庄瑾瑜没说出口的,胡丰登就替她说了:
可不,有几个女人能和我们庄教授一样?
出得厅堂,入得厨房。
还有书房。
不过,在书房庄瑾瑜就不说沈岱宗家的事了,而是说孟一桴家的事。
孟一桴也是中文系的教授,他前几年离了婚,娶了现在的孟师母。
孟师母又年轻,又漂亮,还会做饭,但孟师母是没读过大学的。
在教工宿舍住的女人,没读过大学的,怕只有保姆了。
所以,厨房是沈师母的短,书房是孟师母的短。
这是庄瑾瑜说长道短的方式,几乎用的是忧心忡忡的语气。
孟一桴和他老婆,怎么进行精神交流呢?
孟一桴可是北大中文系出身,而他老婆,天知道她打哪儿来。
听她说话,似乎读过大学,可读的什么大学呢?
庄瑾瑜进一步试探的时候,孟师母又讳莫如深的,实在可疑得很。
或者是克莱敦大学——《围城》里方鸿渐那种,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想想也不对,人家方鸿渐不是还有个克莱敦大学的毕业证?
或者读的是什么短期进修班?
许多人会这样的,比如经济系的上官丽,总喜欢说复旦,说复旦的食堂如何难吃复旦的宿舍如何不是人住的,别人一听,还以为她是复旦的呢,其实哪里是,不过在复旦进修过两个月。
再或者,只是个陪读,和朱周那样的,老恬不知耻地说伦敦和伦敦大学,可伦敦和伦敦大学和她有个屁关系。
然而,这些都只是庄瑾瑜的臆测,孟师母的真实学历是什么,是个谜,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也就是没有。
在这种事情上,人们会无中生有,总不会有中生无。
那样的话,北大的孟一桴和没有学历的孟师母说什么呢?
他们之间会有共同语言?
夫妇共同生活,不单意味着共同的物质生活,还意味着共同的精神生活。
可孟一桴的精神生活和他老婆的精神生活能一致?
她问胡丰登。
胡丰登心情不好时,也会和她唱反调,说:
你那么关心孟一桴的精神生活干什么?
或者,你还真爱忧国忧民——类似于这样的话,当然有点重,他们之间一向相敬如宾的,有文化的夫妇不都这样?
只有那些小市民,才动不动吵架。
庄瑾瑜不想把他们夫妇的格调降低到小市民的层次,所以每次遇到这种有可能起争端的时候,都选择不作声。
好在胡丰登一般只有心情特别恶劣时才这么尖酸,多数时候他还是很能领会庄瑾瑜的意思的,庄瑾瑜无非又是在言彼意此自我表扬。
孟一桴遇人不淑,娶了没文化的老婆;沈岱宗也遇人不淑,娶了不会做饭只会吃饭的老婆;只有胡丰登上算,娶了庄瑾瑜。
庄瑾瑜多淑?
在厨房里淑,会做饭;在书房里淑,会读书;在银行里也淑,会挣钱——她是经常暗示这个的,她是教授,工资收入虽然和系主任胡丰登尚有些差距,但差距也不大,基本还是参差的程度。
却是朱周鄢红之流不能望其项背的。
娶了这么多淑的庄瑾瑜为妻,他胡丰登难道不应该一辈子感恩戴德?
应该的。
只可惜,全师大只有一个庄瑾瑜。
不然师大的男人人手一个,也不至于让其他男老师遇人不淑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庄瑾瑜几乎有杜甫一样的胸襟和遗憾了。
庄瑾瑜夫妇之所以每天散步,是因为鹦鹉,她家养了只漂亮的小绯胸鹦鹉。
那只鹦鹉心野得很,每天都要出门遛弯儿。
不带它出去遛,就发脾气,脾气还大得很。
庄瑾瑜喂它麻子儿,不吃,仰躺着一动不动装死。
等庄瑾瑜要把麻子撤出来,它又急了,噗地啄一口庄瑾瑜,又快又狠,把庄瑾瑜的食指都啄青了。
或者,趁庄瑾瑜一个不留神,猛地从笼子里飞出来,直奔书房去啄窗台上的那盆墨兰。
那盆墨兰是庄瑾瑜的心肝宝贝,以前的一个学生送的。
那个学生说,他之所以送庄老师墨兰,是因为墨兰是高洁精神的象征,“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屈原的《离骚》里,出现了十多处兰,他用兰来托物言志。
兰和屈原一样,也是贵族,植物里的贵族,身份比荷花、菊花甚至牡丹都更高贵。
牡丹虽然被武则天宠幸过,但毕竟还是俗物,从文化意义上而言,它没有身份。
而菊呢,被诗人陶渊明爱过,荷呢,被理学家周敦颐爱过,文化身份很高。
可植物的身份要从文化和政治两个角度来定义。
牡丹有政治身份,却没有文化身份;荷菊有文化身份,却没有政治身份。
唯有兰,两者兼而有之。
学生对植物的象征性和符号性很有研究,他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植物在中国古典文学里的符号性》。
而且,他还说,庄老师不单精神上有兰之高洁,形象上也有兰之优美——对于这后一说,庄瑾瑜听了更是受用——她对自己的精神很有自信,但对自己的形象,还是略有些心虚的。
所以,她一直在胡丰登面前厚此薄彼,此是女人的精神,彼是女人的身体,甚至引经据典,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证红颜祸水的观点。
每每这时候,胡丰登都不置可否。
也就是说,他对红颜还是持保留态度的。
这让庄瑾瑜暗暗气愤,又无奈。
毕竟女人的长相不是学位,她通过努力,或者其他手段就可以拿的。
但那个学生启发了她,女人原来如花,有些是牡丹,虽然美,却是庸俗之美;而有些是兰,代表的是一种脱俗之美,像她。
于是,那盆既代表了庄瑾瑜精神,又代表了庄瑾瑜肉体的墨兰,在庄瑾瑜这儿,地位就特别高,明显高于其他所有的花草。
对这一点,甚至鹦鹉都看出来了。
所以,它会有事没事拿墨兰撒气,是忌妒的意思。
墨兰开出一朵花,它就啄一朵,没开花时——庄瑾瑜家的墨兰很少开花的,也不知为什么。
它就啄茎,或者啄萼片,这比啄庄瑾瑜的食指还让她更疼,又好笑,一只鸟,竟然也像女人一样,会吃醋,会忌妒。
她假装恶狠狠的样子威胁鹦鹉,你再啄一次试试,小心我把你当鹌鹑烤了吃。
可下一次,鹦鹉还是照啄不误。
女儿胡敏听见了,讥笑她,你以为鹦鹉智商多少?
还听得懂鹌鹑什么意思?
烤什么意思?
想要鸟听懂你的话,你就不要养鹦鹉,养乌鸦。
《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乌鸦才是鸟类里智商最高的。
《伊索寓言》里不是就有《乌鸦喝水》吗?
乌鸦不单能想办法解决自己的吃喝,还能预知灾难,还能猜测人的意图,尤其是恶意——胡敏的专业虽然也是文学,但她说,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她自己真正的兴趣是生物学。
当初胡丰登庄瑾瑜坚决要她学文学,是考虑到他们夫妇都搞文学,在这个圈子里有许多人脉资源,以后她读研读博或者就业,他们能有效利用上这些资源。
如果胡敏学生物的话,这些资源可就白白浪费了。
胡丰登和庄瑾瑜夫妇,生活态度都是十分朴素的,持物尽其用的观念,不喜欢浪费。
但胡敏却不怎么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更不领情,经常在庄瑾瑜面前,持一种反文学的情绪。
胡丰登一不在家,她就看《科学》《自然》《国家地理》,或者对文学和庄瑾瑜极尽讥诮之能事——知道卡尔维诺吗?
哦,你不知道,不可能知道。
你是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道冰心,知道郭沫若,不知道卡尔维诺,因为他是意大利作家。
你不知道卡尔维诺,更不知道卡尔维诺的父母。
他们都是植物学家,热带植物学家,研究蕨和苔藓。
在他们家,蕨和苔藓比文学重要,所以搞文学的卡尔维诺,被看成是家里的败类。
多么朴素的价值观!
我就奇怪,老妈你怎么就没有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呢?
我外公,也就是你父亲,不是农民吗?
难道农民的女儿不应该觉得植物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
庄瑾瑜最忌惮别人说出身,英雄不问出处,这一点,她和胡丰登有共识。
若要论及个人历史,庄瑾瑜最愿意谈论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在上海复旦读博,再往前追溯,庄瑾瑜就不太愿意了。
她的第一学历是地方上读的专科,研究生读的是在职同等学力,都如庶出的贾环一样,上不了台面,真正体面的学历背景,是复旦博士——这也足够了。
钱钟书说,文凭就如亚当夏娃遮挡私处的那片树叶,如果真是的话,复旦的这片树叶可不是一般的树叶,是芭蕉叶,它不仅可以遮挡私处,简直大得想遮哪儿就遮哪儿。
可这片巨大的芭蕉叶在胡敏这儿不管用,她会绕过叶子,直接去戳庄瑾瑜的根。
庄瑾瑜那个恼,却也不好恼到面上来。
胡敏也没说错,她是农民的女儿,农民的孙女,农民的曾孙女,怎么啦?
你不也是农民的外孙女?
农民的曾外孙女?
以前她这么气急败坏地反问过胡敏。
可胡敏就一句,那你恼什么?
是呀,她恼什么?
到底恼什么?
她自己都不明白。
农民有什么不好?
生产粮食,生产棉花,生产瓜果蔬菜。
不像知识分子,什么也不生产。
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搬弄是非。
当初读《庄子·盗跖篇》,读到盗跖这么骂孔子,她内心也是极痛快淋漓的。
这证明了她的阶级立场还是十分朴素的,是农民的立场。
可为什么她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是农民的女儿呢?
为什么在潜意识里她还是愿意自己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知识分子出身,和朱周一样——这也是她为什么那么恨朱周的原因。
胡敏的这种态度,让她觉得委屈。
本来,在她的专业选择上,胡丰登才是罪魁祸首,她不过是从犯。
敏儿学文学如何?
胡丰登问她,用商量的语气。
这是他惯用的一套,在单位这样,在家也这样。
其实根本没有“如何”二字,不过是告诉她“敏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