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下.docx
《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下.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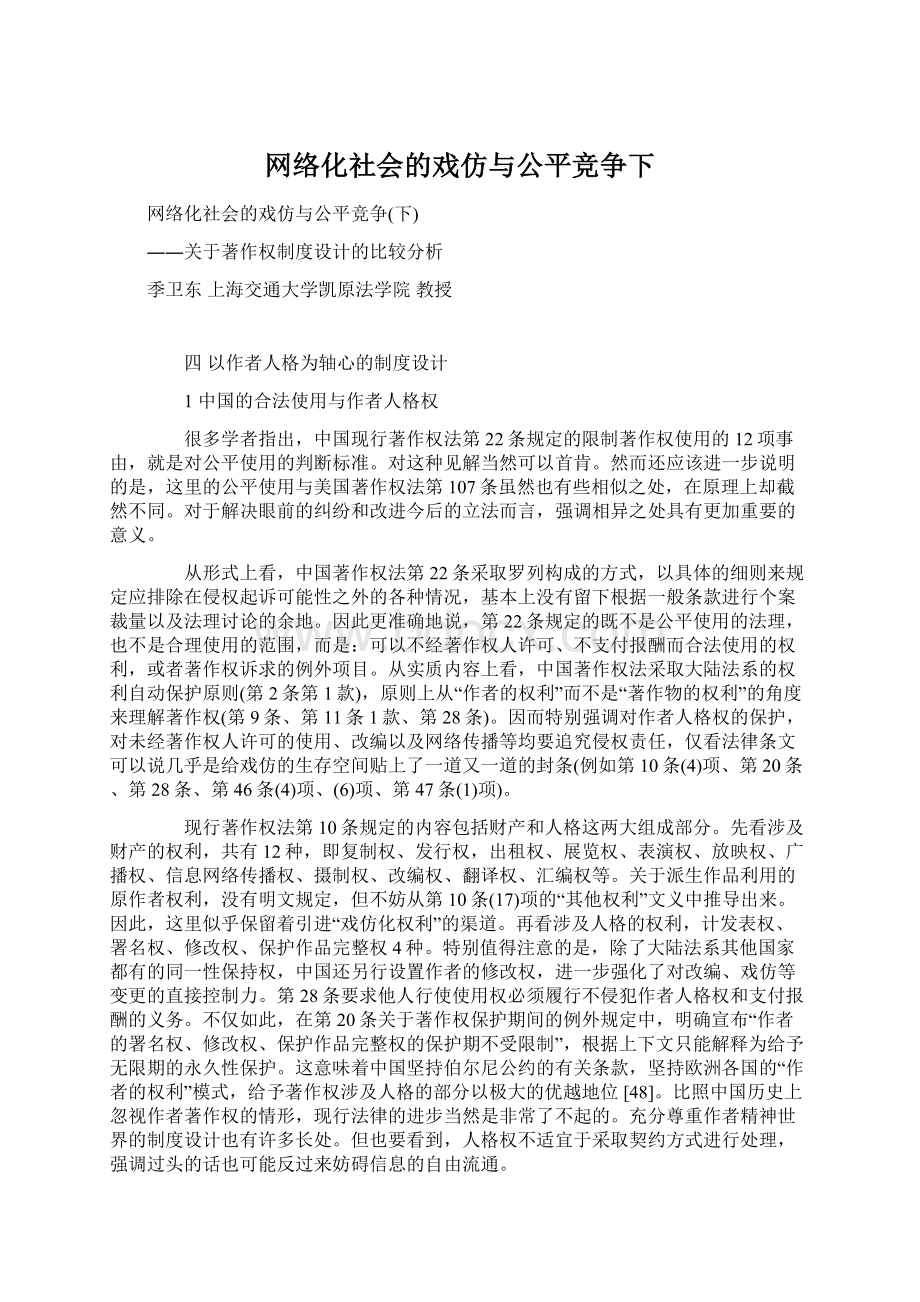
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下
网络化社会的戏仿与公平竞争(下)
――关于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四以作者人格为轴心的制度设计
1中国的合法使用与作者人格权
很多学者指出,中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限制著作权使用的12项事由,就是对公平使用的判断标准。
对这种见解当然可以首肯。
然而还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的公平使用与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虽然也有些相似之处,在原理上却截然不同。
对于解决眼前的纠纷和改进今后的立法而言,强调相异之处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从形式上看,中国著作权法第22条采取罗列构成的方式,以具体的细则来规定应排除在侵权起诉可能性之外的各种情况,基本上没有留下根据一般条款进行个案裁量以及法理讨论的余地。
因此更准确地说,第22条规定的既不是公平使用的法理,也不是合理使用的范围,而是: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支付报酬而合法使用的权利,或者著作权诉求的例外项目。
从实质内容上看,中国著作权法采取大陆法系的权利自动保护原则(第2条第1款),原则上从“作者的权利”而不是“著作物的权利”的角度来理解著作权(第9条、第11条1款、第28条)。
因而特别强调对作者人格权的保护,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使用、改编以及网络传播等均要追究侵权责任,仅看法律条文可以说几乎是给戏仿的生存空间贴上了一道又一道的封条(例如第10条(4)项、第20条、第28条、第46条(4)项、(6)项、第47条
(1)项)。
现行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内容包括财产和人格这两大组成部分。
先看涉及财产的权利,共有12种,即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
关于派生作品利用的原作者权利,没有明文规定,但不妨从第10条(17)项的“其他权利”文义中推导出来。
因此,这里似乎保留着引进“戏仿化权利”的渠道。
再看涉及人格的权利,计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4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大陆法系其他国家都有的同一性保持权,中国还另行设置作者的修改权,进一步强化了对改编、戏仿等变更的直接控制力。
第28条要求他人行使使用权必须履行不侵犯作者人格权和支付报酬的义务。
不仅如此,在第20条关于著作权保护期间的例外规定中,明确宣布“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根据上下文只能解释为给予无限期的永久性保护。
这意味着中国坚持伯尔尼公约的有关条款,坚持欧洲各国的“作者的权利”模式,给予著作权涉及人格的部分以极大的优越地位[48]。
比照中国历史上忽视作者著作权的情形,现行法律的进步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充分尊重作者精神世界的制度设计也有许多长处。
但也要看到,人格权不适宜于采取契约方式进行处理,强调过头的话也可能反过来妨碍信息的自由流通。
2著作权法内在矛盾的探讨
具体到“馒头血案”来看,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46条第(4)项和第(6)项,胡戈对《无极》的改编未经电影著作权人的许可,也有歪曲、篡改的情节,的确存在侵权的嫌疑。
但是,根据该法第22条第
(1)项和第
(2)项,既然搞笑剧以个人欣赏为目的,也有引用说明某一问题的旨趣,侵权的指控其实又颇难成立。
如果进一步推敲该法第10条第(12)项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与第(3)项,第(4)项规定的作品人格权,可以发现“馒头血案”导致《无极》的镜头不能保持同一性,因此还是存在侵权的问题。
但如果再进一步推敲著作权法第14条涉及的汇编作品的著作权,考虑“馒头血案”已经形成独自的印象,不属于《无极》的派生作品,而具有独立戏仿作品的特征,因此判定侵权还是论据不足。
尽管如此,虽然网络搞笑剧“馒头血案”与电影《无极》未产生直接的利益竞争关系,但还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原作带来这样或那样的损失(特别是人格权上的损失),如何判断的确非常微妙。
阅读有关的议论还会发现,著作权法的上述内在矛盾不仅没有消解,甚至还变得更尖锐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除了对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区分作业还嫌不足之外,文化心理结构也当是原因之一。
正如前面已经述及的,传统社会比较轻视作者的财产权保护,说得好听些则是重视知识成果的社会效益,把文化著述完全当作公共物品。
这使得我们更容易接受国家机关对有关利害关系的调整甚至规制,而不倾向于把著作权理解为纯粹的“私权”,因此也就在朦胧中对美国的公正使用原则感到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较容易产生共鸣。
但是,另一方面,受儒家关于道德文章经世济民的思想的薰陶,至少在公开的话语里中国的作者一贯更在乎的是人格尊严和精神上的满足,对物质利益看得相对淡些,这又使得欧洲的著作权制度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更容易得到立法者的支持,更容易获得正当化根据。
其结果,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政策似乎介于两种模式之间,具有折衷性。
此外,数码网络化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影响还没有充分反映到著作权法的内容之中,造成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脱节,则成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人们都承认著作权法是信息时代的制度基础,但却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著作权法本身往往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现实。
3数码网络化与人际关系的改组
透过“馒头血案”引起的波纹可以强烈感受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基调的确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质变,对人格以及社群关系的理解与过去大有不同。
首先需要指出,这一事件显示出传媒和娱乐产业正处在解构之中,有关组织、规范以及权利义务关系也在分离和重组[49]。
毫无疑问,影像复制、编辑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制片人、导演、剧本作家、男女明星等现有体制内权威的垄断地位[50]。
电影爱好者不再局限于对已经给定的剧情的咀嚼式消费,还可以尝试自我创作;其结果,影像音响领域的职业活动与业余活动之间的界限逐步淡化甚至消失,制作者与消费者之间能作面对面交流,亦无需其他中介环节。
市场的制度条件因此也将改观——参入的资格要件、经营管理的各种装置在一定程度上会变得可有可无,自由竞争中讨价还价的行情就成为评判高下的尺度。
也就是说,当文化产业不能垄断操作技术,就不能继续垄断产品销路,因而也就不再享有对供求关系的调节权以及价格体系的支配权。
不久前“超女”与大众投票互动的火爆场面已经预示,在这样的解构后,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一种新型的筛选机制将有可能在彻底的市场化过程中成型和发展[51]。
从比较法社会学的视角看,这预示着行为类型和游戏规则的更换,竞争的自由度和公平性将成为制度设计的轴心。
制作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势必导致沟通方式的改变。
例如在电影时代,也就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是导演垄断了话语权和涵义诠释权,所有的脚本剧情都是单一渠道的单向流传,观众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但进入网络视频的时代,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制作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特别是到了搞笑剧大流行的今天,改编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从多媒体空间获取素材并进行二次创作,可以独立发声并对信息和主张的内容进行不同的诠释。
在这样双向沟通的背景下,传媒活动的主体多样化了,某一现象的涵义和评价标准也多样化了,制作者的意图与消费者的理解甚至可能出现云泥之差——《无极》与“馒头”就是非常典型的实例。
过于强调对制作者的声望、名誉甚至心情意向的保护,就有可能引起广大观众、听众以及读者的抵制。
网络搞笑剧的流行,是传媒、娱乐以及其他社会沟通机制双向化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其实胡戈代表了这一代新人类的总体形象,体现了一种专注于追求美感和快感的柔性自由主义。
新人类不同于著名民法专家梁慧星所提倡的为权利而斗争的务实的刚性自由主义者[52]。
他们也不像摇滚乐前卫崔健那样从心底发出震撼魂魄的野性呐喊并试图借此改变外部环境[53]。
他们是纤细的、温静的、内向的,甚至有一点玩世不恭;有时类似闭门慎思的田螺,但有时却宛若蜘蛛大侠,能以光纤和宽带织出任意伸缩的大网并自如地游走其间。
他们借助IT技术在多媒体中嬉戏,把自己的才智、创意、幽默感以及自我表现的欲望和技艺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用一个社会学术语来概括,他们的存在方式迹近“游戏人”(homoludens)[54],追求一瞬间的自我表现机会和价值实现——在这里倒有点像《无极》里的那株象征性的杂交树,触目动心者只有杏花或樱花盛开时的落英缤纷。
对数码网络时代的“游戏人”而言,自我认同的基础是可变的、碎片化的ID,与他者最亲密的关系是网恋,归属的集体是没有边界、实体以及地图的在线聊天室。
他不希望别人正视自己,甚至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心存疑惧,而宁愿自己化作网络搞笑剧的各种声色光影或者其中的某一主角。
因此,在数码化环境里逐步形成的社群关系,将主要表现为像圣诞节的手机短信或者BBS留言那样轻松的、清淡的形态。
在这样的情境里,人格权的概念内容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不会不波及重视人格因素的著作权制度设计。
五数码网络中的权利处理问题
1信息流量与权利处理方式
在无边无际的数码网络中,大量的信息不断累积,也迅速地流动,有时还会发生“爆炸”。
信息技术和多媒体使人们可以自由传递和加工各种各样的信息,相互沟通也变得极其便捷。
但是,由于在网络浑沌中人格处于反复涨落之中,认同的基础也发生突变,现阶段的社会似乎沟通技术越发达反倒越频繁地出现“沟通失灵(discommunication)”。
正是这样的状态,导致围绕著作物的商谈和权利处理日益复杂棘手,作者与使用者很难继续采取过去那种方式来从容地分别进行谈判,并决定是否给予授权许诺。
也就是说,由于数码网络中的信息流量太大、流速太快,正在瓦解作品价值的物权性构成,把著作权分割成许多诉因碎片,让它们在信息网络中浮游扩散。
2005年初发生的央视公众诉多普达的“电视手机”案,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实例[55]。
而2006年初的“馒头血案”则表明:
戏仿,也为这样的法律解构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显而易见,既存的著作权人许可、版税或使用费等保障机制现在已经在很多场合捉襟见肘,而新的救济方式还有待创立。
归根结底,著作权法的本质在于承认作者(或著作权持有者)享有垄断性利益;而对作品价值高下的判断和利润大小的调整,一般都付诸市场竞争机制。
为了维护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必须明确区别模仿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被允许与不被允许,以减少免费搭车现象。
这意味着任何人要使用作品,都必须与作者或著作权持有者谈判,就权利处理的各种事宜缔结契约书。
在数码网络化社会,技术的发达使任何人都有条件轻而易举地获取信息,而信息的流通量却又成几何级数增加,要一一谈判非常困难。
这就造成不得不面对大量的权利处理的事态,有关交易费用也成倍扩大,侵权行为几乎是防不胜防。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数码网络中戏仿的限制是严、还是宽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过严,会造成信息流通的阻滞;过宽,则很可能使著作权贬值、有关法律规定只落得一纸空文,形成广阔的非法地带。
如果采取事后发现、严惩不贷的司法政策,实践中就会出现太多的命令被告支付巨额赔偿的判决,长此以往难免会削弱向虚拟空间的信息使用内容进行开发性投资的诱因。
2思考实验与制度设计的多样性
鉴于这种两难困境,人们考虑出许多制度设计方案。
例如设立集中管理著作权的组织机构,作者以信托性转让方式把权利交付出去,不再亲自进行个别的谈判处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使用作品的个人或企业只与管理机构签约,如发生侵权行为也都由管理机构出面去追究法律责任。
由于大量的权利集中在特定机构,可以产生维权行为的规模效益,因此,管理机构比作者个人更能充分地对侵权行为进行监督、提起诉讼[56]。
又例如对所有使用者统一收费的方式,实际上使著作权完全转化成某种对价的请求[57]。
另外,美国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提出了国家法律的限制与私人利用代码技术(标准暗号、电子认证等)建构防护性栅栏的“两手抓”思路[58]。
但是,由于正版光盘之类在旧货市场上可以自由转卖,而数码技术已经使复制品的质量与正版相比毫无逊色之处,这就提供了很多“钻法律孔子”的机会――试图取巧的个人不妨先买正版,复制后再转卖。
为了堵塞这样的漏洞,著作权保护水准较高的国家采取的对策是建立补偿金制度,即对具有复制功能的机器征集补偿金,在权利持有者中进行分配[59]。
现有的著作权法以及学说虽然还没有承认那些把数码空间存在的大量素材进行重组的作品也应获得制度性保障,但已有人主张其中投资很大并具有创意的,可以考虑给予与著作权相区别的合法地位并提供一定的保护措施。
例如EU数据库指令(CouncilDierctiveof11March1996ontheLegalProtectionofDatabases)第三章(特别是第7条)提议把这些作品的合法利益作为“另类特色权(suigenerisright)”加以保护[60]。
特别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些为适应数码网络化后保护著作权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例如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网络传播认可权[61]。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通过彻底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数码网络中权利处理问题的理论设想。
其中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是,日本国际高等研究所副所长北川善太郎教授提倡的“复制集市(Copymart)”[62]。
概括地说,这一方案的基本特征是,把前面提到的著作权信托性转让管理、统一收费以及补偿金等设计思路逆转过来,因而制度化的出发点从防止侵权改为著作权自由交易。
具体做法如下:
著作权持有者在“复制集市”对作品整体以及各组成部分的权利数据进行登记并开列许可使用条件,使用者到“复制集市”――包括著作权市场和作品市场这两个不同层面――采购,从这里获取使用权和复制品,并向指定的帐户电汇使用费。
实际上,“复制集市”本身就是由数码信息技术编织的网络,使用者不仅可以从中检索必要的信息、预估有关成本,还能就价格等问题与权利持有者直接进行谈判。
“复制集市”的法律基础是三种系统化的契约群(大量分散契约的整体结构化):
(1)著作权数据登记契约,
(2)复制集市利用契约,(3)以提供著作物的复制为目的的契约[63]。
上述设想还有一个难题留待解决,这就是怎样保护作者的人格权。
因为人格权并不是“复制集市”契约的目的,所以有关的纠纷不得不通过事后的司法救济手段和互动来解决。
3结束语:
基于反思理性的选择
总而言之,把视野扩大到社会结构的质变以及数码网络时代的法律基础就会看到,《无极》对“馒头”的重要性不在于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导演与一个网络红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以及官司胜负,也不在于对著作权法如何解释的辩论,甚至还不限于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和解构。
这场吸引举国上下无数眼球的纠纷其实提出了一些涉及体制转型的根本问题:
在信息技术普及之后,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立法和司法政策?
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相关,个人、企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件将以何种方式重组?
以复数或大量的契约群体的整体结构化为特征的系统契约方式(与互联网公约在形式上颇有类似之处,但却不失私约的本质),还有强调法律决定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反思理性以及功能和涵意之间联系的新程序主义,建构在这样两个极轴上的规范框架能否充分容纳平面互动、网络沟通并避免权利体系的解构和贬值?
站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观察和思索,在21世纪人际互动以及秩序将呈现什么特征,法治范式究竟应该怎样创新?
要回答这些问题,仅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当然不行,但片面强调现实的已变或将变的格局、不负责任地在信息和戏仿的大海里随波逐流也不行。
所以本文要把分析的焦点对准条文与事实之间,强调作为两者媒介项的反思化和著作权重构的不同组合方式,即制度设计的多样性、可比性以及合理选择性。
注释:
[48]在这个方面,日本著作权法与中国同样,甚至比伯尔尼公约规定的内容更进一步,在关于同一性维持的第20条中把保护人格权的范围从声望、名誉伸展到心情(不得违反作者的意思进行变更)。
参阅作花《详解•著作权法》(前引)213-216页。
因此,日本的立法和判例都倾向于严格限制戏仿。
[49]但还是不能贬低专业化节目制作的重要性。
广播也是典型的实例。
参阅报道“多媒体时代广播的复苏”
[50]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李旭等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0章第1节中分析了信息技术与著作权的战争状态及其结局。
[51]有关争论,参阅陈壁生“大众文化的狂欢和人文启蒙的尴尬”《凤凰周刊》2006年第2期。
[52]参阅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现代世界法学名著集》(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53]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到《无能的力量》,按时间顺序听一下这些摇滚乐盘,我们就可以体味到崔健个人主页里出现的“不是我不明白,这网络变化快”这句标语的丰富涵意。
[54]SeeJohanHuizinga,HomoLudens;AStudyofthePlayElementinCulture(Boston:
BeaconPress,1986).高桥英夫的日译本于1973年由中央公论社出版。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游戏形成秩序的命题。
与该书互补的重要论述,参阅RogerCailloisMan,PlayandGames(trans.byMeyerBarash,Urbana:
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01).多田道太郎、冢崎干夫的日译本于1990年由讲谈社出版。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规则与虚构的关系的论述。
[55]详见拙稿“网络空间也需维权”《财经》2005年2月7日号。
[56]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新书版,东京:
岩波书店,1996年)64-65页。
[57]同上,159-161页。
[58]见莱斯格《代码:
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前引)第10章的引言。
[59]例如日本现行著作权法第5章“私人录音录像补偿金”。
另外,关于各种著作物流通中的竞争秩序的概论和具体考察,参阅石冈克俊《著作物流通与反垄断法》(东京: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
[60]参阅作花《详解•著作权法》(前引)118-119页。
[61]这是日本在1986年率先确立的防止网络传播恣意化的著作权组成部分,见该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条(9)项第5点规定。
这项新权利的重大意义在于免除著作权持有者关于传播发信的举证责任,只要能证明输入和储存的事实就可以起诉。
[62]详见北川善太郎《复制集市――信息社会的法律基础》(东京:
有斐阁,2003年)。
这一想法的雏形是:
ZentaroKitagawa,“Copymart:
ANewConcept:
AnApplicationofDigitalTechnologytotheCollectiveManagementofCopyright”,WIPOWorldwideSymposiumontheImpactofDigitalTechnologyonCopyrightandNeiboringRights(HarvardLawSchool,March31toApril2,1993)pp.139-147.
[63]与戏仿有关的作品组成部分的使用,涉及数码素材交易业务和契约。
有关法律处理的技术性问题,参阅日本电子出版协会、马克斯法律事务所《数码时代的著作权事业――契约实务指南》(东京:
因普雷斯公司、1999年)。
出处:
知识产权法学,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