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docx
《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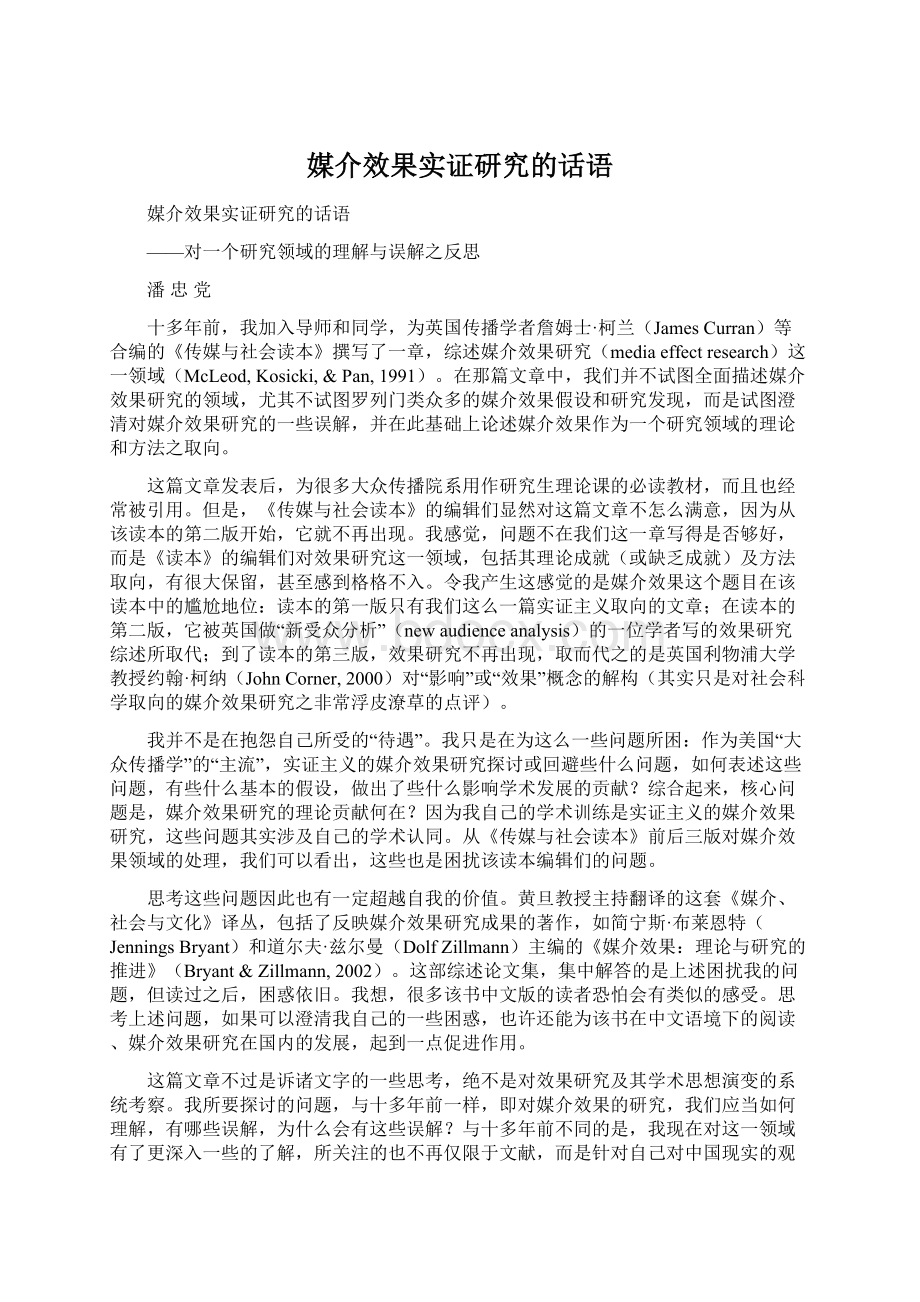
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
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
——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反思
潘忠党
十多年前,我加入导师和同学,为英国传播学者詹姆士·柯兰(JamesCurran)等合编的《传媒与社会读本》撰写了一章,综述媒介效果研究(mediaeffectresearch)这一领域(McLeod,Kosicki,&Pan,1991)。
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并不试图全面描述媒介效果研究的领域,尤其不试图罗列门类众多的媒介效果假设和研究发现,而是试图澄清对媒介效果研究的一些误解,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媒介效果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之取向。
这篇文章发表后,为很多大众传播院系用作研究生理论课的必读教材,而且也经常被引用。
但是,《传媒与社会读本》的编辑们显然对这篇文章不怎么满意,因为从该读本的第二版开始,它就不再出现。
我感觉,问题不在我们这一章写得是否够好,而是《读本》的编辑们对效果研究这一领域,包括其理论成就(或缺乏成就)及方法取向,有很大保留,甚至感到格格不入。
令我产生这感觉的是媒介效果这个题目在该读本中的尴尬地位:
读本的第一版只有我们这么一篇实证主义取向的文章;在读本的第二版,它被英国做“新受众分析”(newaudienceanalysis)的一位学者写的效果研究综述所取代;到了读本的第三版,效果研究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约翰·柯纳(JohnCorner,2000)对“影响”或“效果”概念的解构(其实只是对社会科学取向的媒介效果研究之非常浮皮潦草的点评)。
我并不是在抱怨自己所受的“待遇”。
我只是在为这么一些问题所困:
作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主流”,实证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探讨或回避些什么问题,如何表述这些问题,有些什么基本的假设,做出了些什么影响学术发展的贡献?
综合起来,核心问题是,媒介效果研究的理论贡献何在?
因为我自己的学术训练是实证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这些问题其实涉及自己的学术认同。
从《传媒与社会读本》前后三版对媒介效果领域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也是困扰该读本编辑们的问题。
思考这些问题因此也有一定超越自我的价值。
黄旦教授主持翻译的这套《媒介、社会与文化》译丛,包括了反映媒介效果研究成果的著作,如简宁斯·布莱恩特(JenningsBryant)和道尔夫·兹尔曼(DolfZillmann)主编的《媒介效果:
理论与研究的推进》(Bryant&Zillmann,2002)。
这部综述论文集,集中解答的是上述困扰我的问题,但读过之后,困惑依旧。
我想,很多该书中文版的读者恐怕会有类似的感受。
思考上述问题,如果可以澄清我自己的一些困惑,也许还能为该书在中文语境下的阅读、媒介效果研究在国内的发展,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这篇文章不过是诉诸文字的一些思考,绝不是对效果研究及其学术思想演变的系统考察。
我所要探讨的问题,与十多年前一样,即对媒介效果的研究,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有哪些误解,为什么会有这些误解?
与十多年前不同的是,我现在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入一些的了解,所关注的也不再仅限于文献,而是针对自己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希望能更加有的放矢。
我的目的是为理解来自美国的媒介效果研究的文献,提供一个场景;为中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学科发展,提出一些警示。
媒介效果研究做什么?
在十多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们首先描绘了一幅大众传播研究的“春秋战国”场景。
今天,不仅这种局面没有改观,而且诸侯争斗的战火蔓延至如何看待学科发展的历史。
在这十多年中,一批大众传播研究史的著作相继问世,有的讲述“建制内的历史”(“theestablishmenthistory”,Rogers,1994;Dennis&Wartella,1996),有些讲述被“主流”所掩藏甚至歪曲了的历史(Glander,2000;Simpson,1994)。
“建制内的历史”基本是大众传播这门学科从无到有的“创业史”,其主角和“英雄”,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字。
当然,他们也为时代所造就,得到了基金会、企业和政府的慷慨资助。
所谓“反对派的历史”(McChesney,1997),不仅意在颠覆这一“建制内的历史”,而且力图建构了一个大众传播研究由“资本”和“权力”所孕育、带着与生俱来之罪恶的诞生史。
根据这个历史叙事,那些所谓“创业者”,其实是些趋炎附势的机会主义者,不惜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烟草公司、石油或汽车大亨那里拿钱,为他们的政治宣传和市场营销出谋划策,将传播研究生生地引上了为特殊利益服务、为思想控制服务的歧途。
这些学科史的著作,并没有挖掘出太多令人瞠目的史料,更没有对传播研究的学科发展提出具有建设意义的观点,甚至没能更清楚地回答“大众传播研究做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
它们倒是进一步显示,大众传播研究缺乏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的身份认同也很模糊。
多年来,学科的这种特征令很多传播学者们沮丧,也令初学者们无所适从。
针对这样的局面,美国《传播学季刊》于1983年和1993年曾先后出版了两期论坛,召集学科内的知名学者反思“这个学科在干什么,有什么特点”这样的学科定位问题。
曾先后担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的罗杰斯(EverettRogers)和查菲(StevenChaffee)在每期论坛上都发表了一篇对话。
他们间隔十年的两篇对话观点相当一致,即大众传播研究,或范围更广的传播研究,缺乏一门学科应有的理论整合(Rogers&Chaffee,1983;1993)。
这种状态至今没有改观,它不仅继续困扰我们,而且隐含着传播研究这一学科的深层危机。
这种大局面,当然也反映在媒介效果研究这个领域,但这不等于说这个领域没有任何内在的定性特征。
在十多年前的那篇综述中,我们认为媒介效果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中一个具有独特取向的领域,其特征是:
着重考察受众,试图确认各种影响,力图将这些影响追溯到媒介的某个相面,并采取实证科学的方法和语言,以检验理论的假设。
我们强调,在这些共同点下,媒介效果研究复杂多样,要将之统一为“主导范式”或“传播科学”,难免有削足适履的粗暴和武断。
为显示这一点,我们提出如下可概括媒介效果研究的分类相面:
a.微观与宏观:
二者的区别在于考察媒介影响个人的心理或行为还是影响更高层次的社会单位、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
b.变化与稳定:
二者的区别在于媒介效果的形式,它可能是改变已有状况(如态度、行为或社会关系),也可能是稳固现有状况(如维护现存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
c.累积与非累积:
二者的区别在于认识到媒介的效果可能是短暂的,一瞬即逝的,也有可能积存于系统,由少积多、由小积大;
d.短期与长期:
这就是说,媒介的效果可能在媒介接触后即刻产生,但属昙花一现,也有可能孕育良久后才出现,或经久不衰;
e.态度、认知、行为:
这个相面强调,媒介的效果可能发生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集合体,这三者都是理论上可区分的领域,而且,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原理,也是必须区分的领域;
f.离散一般型与内容具体型:
这个区别强调的是产生效果的媒介元素,媒介的效果可能源自媒介的存在(如比较通过媒体中介与没有媒体中介的社会或历史时期),媒介再现的一般特征(如涵化理论认为电视无处不在,其极度重复的“资讯体系”是影响群体的社会现实观念之祸根),也可以源自某一具体的媒介资讯,如某一条新闻或某一集电视连续剧;
g.直接效果与条件性效果:
这个区别强调媒介效果的产生形态,媒介可能直接影响某具体变项(如个人的态度、认知或行为),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影响到该具体变项。
如果用这些相面及其类别来建构一个矩阵,我们会得到192种不同类型的媒介效果。
这种多元的特征,显然否定了一些批判和文化研究学者对媒介效果研究一叶障目式的概括,认为它只研究“态度和行为的短期变化”(Gitlin,1978;Guantlett,1998)。
[2]但是,这些相面显然不是理论的概念,它们强调的是分辨和区别,而不是整合或系统。
“效果研究”的这种多样的特征,也令从事媒介效果研究的学者们惶然:
究竟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将这些众多的“诸侯小国”整合为一个内部统一的领域?
如果一个研究领域尚且如此,更遑论传播研究这个学科?
媒介效果研究,或更广泛地说,大众传播研究,如何步入了今天这个丰富多彩或支离破碎的局面?
上述两个截然对立的历史叙事,从不同的角度,都聚焦于拉扎斯费尔德,以及他领导下的所谓“哥伦比亚学派”(Gitlin,1978;Rogers,1994;Rogers&Chaffee,1983;1993;Simpson,1994)。
显然,那些将拉扎斯费尔德等人的研究概括为“有限效果论”,并将其标榜为“媒介社会学中的主导范式”的做法,令拉氏的学生和合作者,艾利休·凯茨(ElihuKatz),非常不爽,乃至年过7旬之后,他仍奋起撰文(Katz,2001),为其导师“翻案”。
凯茨说,后人太多地通过伯尔荪(Berelson,1953)过早演奏的大众传播研究的“安魂曲”,以及拉氏的学生之一克拉帕(Klapper,1960)的教条化总结,来理解拉扎斯费尔德。
其实,拉扎斯费尔德并不认为媒介只会产生“有限的效果”,并不将媒介的效果局限于短期的个人态度或行为转变,也并非将媒介及其信息看作既成事实,不加区分或批判地接受为先决条件。
有趣的是,凯茨的“翻案”文章没有引用罗杰斯1994年的《传播研究史》,似乎是在间接地表达他对罗杰斯将拉扎斯费尔德贬为“工具制作者”(toolmaker)的不满。
但是,凯茨引用了拉扎斯费尔德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写于1948年的两篇文章。
在这一节,我们首先看拉扎斯费尔德独自署名的一篇论文(Lazarsfeld,1948),它的主要内容是勾勒“媒介效果”这一领域的范围。
他认为,“效果”或“影响”(effect)一词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因为,大众传媒影响个人的知识、态度、意见和行为。
这些影响可以是即刻发生的,也可以是延迟发生的;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持久的。
对个人的影响可能逐渐积累而转换为制度的变迁。
这些影响既可以是个人对传媒的直接反应,也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因果链而产生,也就是说,媒介导致制度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影响到个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察传媒自身的各个相面。
我们也许是在考察教育影片的技术特征,也许会对某一杂志文章或广播节目的影响感兴趣,有可能考察英国的政府控制和美国的企业控制等不同广播体制产生的影响,更一般而言,我们可能会考察如电视等新科技的影响。
(pp.249-250)
如此推理,拉氏提出了两个考察媒介效果的相面:
(1)不同类型的传播研究,包括考察某一内容单位,某一内容类别,媒体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媒介的技术特性;
(2)不同类型的效果,包括即刻的反应,短期效果,长期效果,和制度变迁。
将这两个相面交互,拉氏得到了有16类可确认的效果矩阵(p.250)。
在解读了拉氏的论文之后,[3]凯茨(2001)认为,把“有限效果论”作为拉扎斯费尔德的媒介效果观,其实是曲解。
拉氏的传统,即对传媒效果的探讨,依照凯茨的意见,包含了如下5个方面:
“
(1)效果的特性——变化还是固化;
(2)影响的对象——意见或社会结构;(3)受影响之单元——个人、组群或民族等;(4)效果反映的时间单位——短期还是长期;(5)产生效果的媒介因素——内容、技术、拥有权,以及接触的场景”(p.278)。
显而易见,那种认为拉扎斯费尔德建立了以个人的短期态度变化为核心、以人际影响超过媒介影响为主要结论的“主导范式”的观点(Gitlin,1978),其实反映了对历史的误读。
当然,是否为拉氏翻案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它离我们太远。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的目的是为显示“媒介效果”的多种多样。
由于多种类型的区别,媒介效果研究不可笼统地归属于某个“范式”或“学派”;对不同类型的效果之考察,本身就可能代表了不同的“范式”或“学派”。
但是,考虑了众多种类和形态的“媒介效果”后,我们也可看到“媒介效果”研究的基本话语特征,即以因果关系的形态,建构传媒使什么成为可能、使什么发生或者使什么得到抑制的叙事;这是个描述型叙事,即对媒介或其某一相面如何引起某些变或不变的描述,而不是对这些变或不变作出文化或政治价值的评判;这个叙事的视野是全景式的,包含了媒介所涉及的人类行为、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研究“媒介效果”,也就是建构一个关于在“媒介时代”,人类生活如何依赖媒介或围绕媒介而发生或者变化的话语。
它当然不是“媒介与社会和文化”之关系的话语全部,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问题导向与理论建构
上一节没有完全回答“媒介效果研究做什么”这个问题。
在重申了传媒效果的形式和种类之多样后,我们面临这么个问题:
究竟有什么理论原理可以将媒介效果的研究整合于一个学术的家园?
查菲指出,这种统一学科的原理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尚不存在(Rogers&Chaffee,1993),因此,与其说大众传播研究是门学科,还不如说它是个“聚集的场所”(agatheringplace,Rogers&Chaffee,1983)。
大众传播研究的这种尴尬境地,究其根源,还是回到了拉扎斯费尔德、拉斯威尔(HaroldLasswell)、霍夫兰(CarlHovland)、勒文(KurtLewin)等所谓“学科建设之父”。
也许,他们在二战前后的选择,极大地限定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基本参数,舍弃了其它有可能采纳的研究途径(Rogers,1994)。
从科学发展的轨迹来说,这也极其自然。
极具创意、成果斐然的研究项目,如拉扎斯费尔德等人对竞选过程中态度和投票选择的研究,霍夫兰等人对说服过程和效果的研究等等,往往成为功率巨大的研究“范例”或“典范”(Kuhn,1970),起到彰显某一研究取向的作用,也成为模仿的对象。
从负面来看,这种彰显和模仿,往往强化某种思维定式,局限研究者们社会学批判的想象空间(Mills,1959)。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学术发展的这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特点,归罪于拉扎斯费尔德等人?
我们是否有理由要求,“学科建设之父”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拓出整个学科的完整天地?
对这样的问题,恐怕吉特林本人也不大可能给予肯定的答复。
我感觉,吉特林及其他批判和文化学者对拉扎斯费尔德等人的批判,其意还在于从意识形态和认识论上排斥甚至是彻底否定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本模式的媒介效果研究。
[4]
按吉特林(Gitlin,1978)的说法,拉氏等人的“罪状”之一是,他们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problem-oriented),而不是以理论建构或理论批判为导向。
确实,拉扎斯费尔德主持下的“应用社会研究所”,从企业、基金会和政府部门承接了很多服务性的应用项目,其中多数没有多少理论价值(Rogers,1994)。
可是,在拉扎斯费尔德和后来的罗杰斯等人看来,媒介效果研究的问题导向,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对传媒的学术考察,由现实的实际问题所激发。
这一导向,使得大众传播研究带上了极强的应用学科的特点(Lazarsfeld&Merton,1948;Rogers,1994),这一特点值得继续发扬光大,而不应当被简单地贬斥。
[5]
当然,以问题为导向有其负面作用,其中之一是吉特林所指责的立场和视角的局限,对此,我在后面一节再讨论。
在这里,我要特别讨论另一个负面作用,即问题导向可能阻碍理论的发展,尤其是阻碍学科的整合。
虽然拉扎斯费尔德等人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他们留给后来者的、对大众传播研究的学科起到奠基作用的并不是他们的应用研究,而是他们发展的一些理论观点,例如信息的“二级流动”、“舆论领袖”、人际网络、创新(或信息)扩散等。
[6]这些理论观点的背后,是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动态、大众传媒的角色及其功能,以及媒介效果的形态及其产生方式等的理论建构。
这当中有社会学理论家默顿(RobertMerton)的贡献,也有拉氏本人的努力(Rogers,1994)。
后来者往往为拉氏等人的具体假设或概念所吸引,而忽略了他们更高层次的理论框架。
凯茨(2001)的“翻案”文章其实是试图纠正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误。
拉氏等人的基本理论框架,清楚地表述在拉扎斯费尔德与默顿发表于1948年的一篇论文中(Lazarsfeld&Merton,1948)。
这篇文章是我们理解媒介效果研究这一领域、在理论的层面阅读并理解《人民的选择》(People’sChoice)和《人际影响》(PersonalInfluence)等里程碑式专著所必需的“奠基文本”(acanonictext,见Katz,Peters,Liebes,&Orloff,2003)。
在这篇文章里,拉扎斯费尔德和默顿首先指出,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产生于社会变革的具体历史场景。
犹如工业革命引起了对劳工、老年人福利、女权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一样,大众传媒的兴起,代表了社会控制及其运作内容与形态的变革,传媒的力量及社会角色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
关注这样的课题,拉氏和默顿指出,也就是考察“社会的权势利益或群体如何以新的方式,行使其社会控制”(p.96),这种社会控制的重心已经由“直接的经济剥削转向通过大众传媒扩散的宣传,即一种更加微妙的心理剥削(psychologicalexploitation)”(p.96),其中包括通过大众传媒而庸俗化流行文化,侵蚀受众的审美品位(p.97)。
大众传媒的效果虽是“难以明确定义的问题”(p.98),但它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必要课题。
他们强调,大众传媒有可能被用作有力的工具,利用者的目的可能有好有恶,因此,研究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产生的过程,能够武装人民抵抗邪恶力量,帮助人民利用传播媒介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7]
拉氏和默顿显然是将对大众传媒及其效果的研究作为具有强烈应用色彩的领域来看待,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控制之内容及形态的理论研究和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那些对媒介效果研究横加扫荡的批判学者,应当仔细读读拉氏和默顿这篇文章,看看自己的“批判传统”是否真的与拉氏等人的传统格格不入,看看是否真的能将从事媒介效果研究的人统统划为“体制”或“特殊利益团体”的“帮凶”。
拉氏和默顿指出,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建制(socialinstitution),镶嵌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内;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和媒介控制体制,传媒的效果可能会多种多样(p.98)。
在当代美国社会,在民主政体、资本主义经济、传媒私有等结构条件下(p.106),大众传媒具有三大功能:
[8]
(1)地位确认功能,即大众传媒确认公共议题、个人、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地位,包括被关注议题的焦点地位、名人的公众人物地位,以及社会组织或行为的合法或合理性(legitimacy)地位;
(2)社会规范的行使(enforcement)功能,即宣扬规范、贬斥(或边缘化)规范的偏离、缩小“个人的内在态度”与“公共道德体系”之间的沟壑、制度化符合社会规范的言行;
(3)麻醉的负面功能(thenarcotizingdysfunction),即助长民众中的政治冷淡和惰性,为他们制造自己“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幻像,抑制他们的民主参与热情。
因为这个功能并非有利于现代民主社会的运作,所以被称为“负面功能”。
拉氏和默顿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的运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传媒的这些功能,这种认知本身就是权力,其中对前两个功能的认知,是“可被用来服务于特殊利益或社会公益的权力”(p.104)。
“由于大众传媒为现存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拥有,因此它的服务是维护现存体制”。
这种维护,不仅来自传媒公开了什么内容,而且来自将哪些内容秘而不宣,来自传媒从不对现存社会结构提出根本性的挑战问题,来自社会归顺(socialconformism)这一基本的社会压力机制。
因此,就其特性而言,传媒不会意在诱导社会制度变革,甚至难以导致哪怕是微小的变革(p.106)。
因为传媒具有这些功能,所以它可被用作“服务于社会目标”(forsocialobjectives)的宣传工具。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工具最为有效呢?
拉氏和默顿指出三个基本条件:
(1)传媒内容之垄断;
(2)传媒宣扬或光大(canalize)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3)大众传播与人际间的交流相辅相成。
这三个条件中的后两点,在拉氏与凯茨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实证的支持,体现在如下“有限效果论”的结论中:
(1)传媒在大选宣传中的影响主要是强化或稳定选民已有的态度,明朗化选民们的隐性态度,而不是改变他们的态度;
(2)传媒与人际渠道相辅相成,其效果通过人际关系的网络得以扩散、消解或强化。
拉氏和默顿的这些观点,预示了后来发展出的一些假设和观点,如“公共议题”的地位确认,其实就是后来的“议程设置”假设;“行使社会规范”和“麻醉”的功能,包含了“涵化假设”(cultivationhypothesis)的基本因素;对“社会归顺”这一基本机制的论述已经预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核心元素;““麻醉”的负面功能和维持现存制度的功效,预告了后来对媒介的“意识形态霸权”效用的阐释(Hall,1982)。
因此,在45年后重读拉氏和默顿,Simonson和Weimann(2003)认为,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并不存在一个“媒介社会学的主导范式”,也并没有一门心思地研究媒介的“效果”,所谓“批判”与“行政研究”的分野,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
在拉扎斯费尔德和默顿的“双子星座”下,哥大保持了学术思想的开放。
他们二人1948年的这篇经典文字,代表了批判研究与实证的行为研究之结合。
这当然不是说后人只是在拾拉扎斯费尔德和默顿的牙慧,因为,近30余年的理论发展,确实超出了拉氏和默顿所表述的范畴及层次。
但是,拉氏与默顿的这篇文章勾勒了传播效果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即具有浓烈批判取向的结构功能主义,它因此孕育了后来提出并得到检验的很多具体假设。
该学派为后人所称道或批判的主要理论发现和假设,发轫于对突出社会问题的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宏大理论的框架内,丰富并拓展了这个理论框架。
也就是说,所谓“哥伦比亚学派”的一个核心传统,是以理论来分析现实的社会问题,并以这样的分析来发展理论。
遗憾的是,当批判学者们嘲弄媒介效果研究的问题导向之琐碎、理论深度之缺乏和想象力之局限时,他们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效果研究者们确实常常遗忘了自己传统的核心。
如果从《媒介效果》这本书中,我们只得到零碎的理论概念和繁琐的实证检验,而得不到统领全书或整个效果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那不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也不完全是该书的编辑方针有问题。
该书反映的是目前效果研究领域的实际状况。
可以这么说,媒介效果研究缺乏理论,同时又“理论”过多;缺乏的是具有整合力度的理论,过多的是局限于具体现象的“中层”或“低层”理论(middle-range或lower-rangetheories,见Merton,1967)。
更具体地说,媒介效果研究者不是以自己的理论分析,去发现并建构问题,而是经常追随业界,考察其操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关注方法服务于理论、与理论逻辑地配套,而是狭隘地追求技术的精密;不是以理论建构为核心,以理论的解释为灵魂,而是轻视理论,将现象或对现象的名词概括误认为理论;不是将关于“效果”的假设置于整合的理论框架内,而是安然地“偏于一隅”,满足于瞎子摸象式的局部具体和细致。
这是传播效果研究,甚至更广地说,大众传播研究缺乏理论发展和整合的症结。
什么是理论?
从结构上来说,理论由一组陈述句构成,它们以逻辑的相互关联而组成一个内部统一的体系;从功能上来说,这个结构体系可以描述、解释和预测现实的现象,导致或加深我们对特定现象的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它不具体描述个体或个案,但却明确地描述和解释对象,它加深我们对研究对象及其运动在更抽象和普适层面的理解,并帮助我们辨认、区分、解释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的个体或个案(即现象)。
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媒介效果领域的很多所谓理论,并不具备理论应有的特征,或者,很多实证研究者经常淡忘了发展符合这些标准的理论这一科学研究之根本目标。
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