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问题的真相.docx
《口供问题的真相.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口供问题的真相.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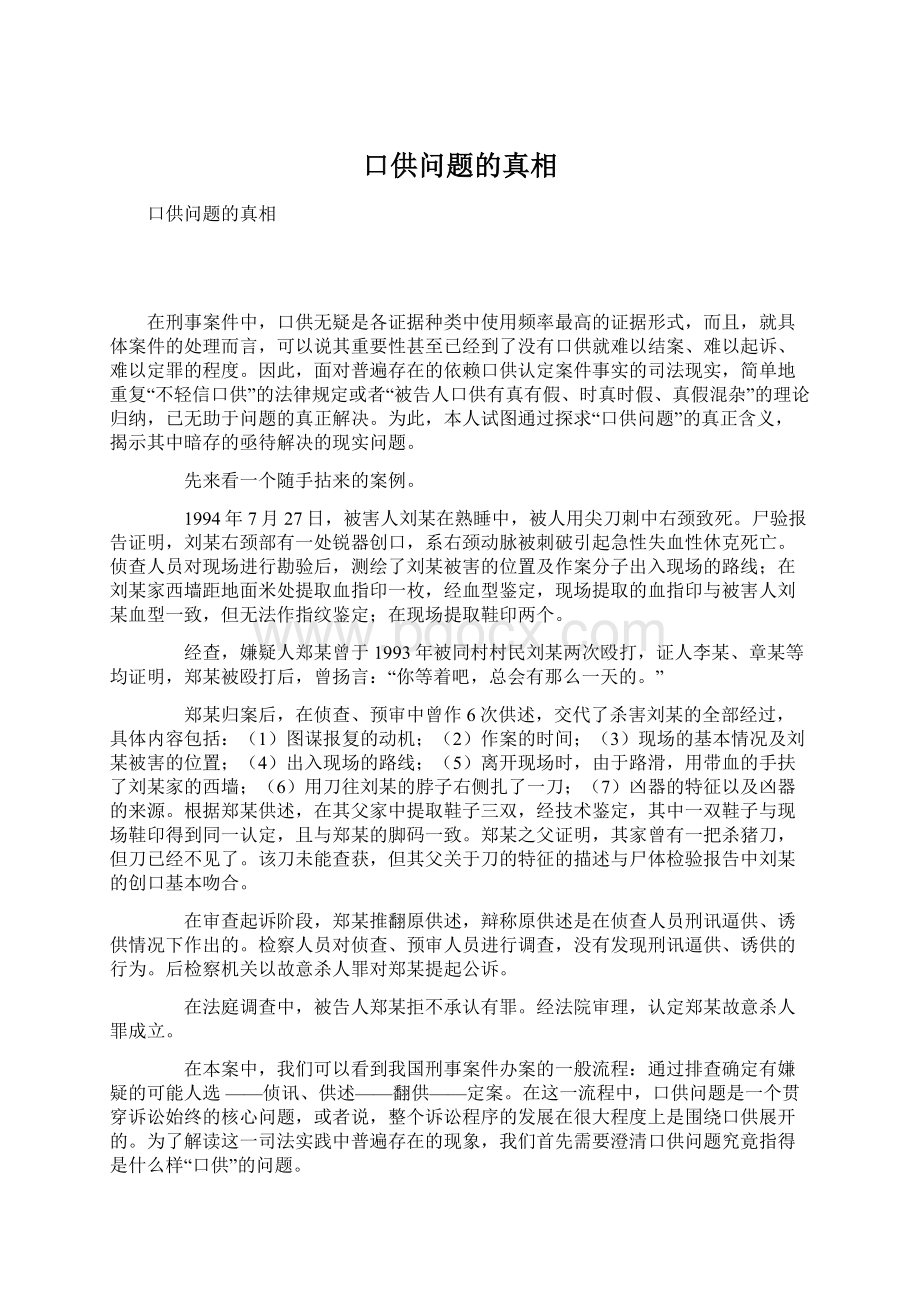
口供问题的真相
口供问题的真相
在刑事案件中,口供无疑是各证据种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证据形式,而且,就具体案件的处理而言,可以说其重要性甚至已经到了没有口供就难以结案、难以起诉、难以定罪的程度。
因此,面对普遍存在的依赖口供认定案件事实的司法现实,简单地重复“不轻信口供”的法律规定或者“被告人口供有真有假、时真时假、真假混杂”的理论归纳,已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为此,本人试图通过探求“口供问题”的真正含义,揭示其中暗存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先来看一个随手拈来的案例。
1994年7月27日,被害人刘某在熟睡中,被人用尖刀刺中右颈致死。
尸验报告证明,刘某右颈部有一处锐器创口,系右颈动脉被刺破引起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侦查人员对现场进行勘验后,测绘了刘某被害的位置及作案分子出入现场的路线;在刘某家西墙距地面米处提取血指印一枚,经血型鉴定,现场提取的血指印与被害人刘某血型一致,但无法作指纹鉴定;在现场提取鞋印两个。
经查,嫌疑人郑某曾于1993年被同村村民刘某两次殴打,证人李某、章某等均证明,郑某被殴打后,曾扬言:
“你等着吧,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
郑某归案后,在侦查、预审中曾作6次供述,交代了杀害刘某的全部经过,具体内容包括:
(1)图谋报复的动机;
(2)作案的时间;(3)现场的基本情况及刘某被害的位置;(4)出入现场的路线;(5)离开现场时,由于路滑,用带血的手扶了刘某家的西墙;(6)用刀往刘某的脖子右侧扎了一刀;(7)凶器的特征以及凶器的来源。
根据郑某供述,在其父家中提取鞋子三双,经技术鉴定,其中一双鞋子与现场鞋印得到同一认定,且与郑某的脚码一致。
郑某之父证明,其家曾有一把杀猪刀,但刀已经不见了。
该刀未能查获,但其父关于刀的特征的描述与尸体检验报告中刘某的创口基本吻合。
在审查起诉阶段,郑某推翻原供述,辩称原供述是在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诱供情况下作出的。
检察人员对侦查、预审人员进行调查,没有发现刑讯逼供、诱供的行为。
后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郑某提起公诉。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郑某拒不承认有罪。
经法院审理,认定郑某故意杀人罪成立。
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刑事案件办案的一般流程:
通过排查确定有嫌疑的可能人选 ——侦讯、供述——翻供——定案。
在这一流程中,口供问题是一个贯穿诉讼始终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整个诉讼程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口供展开的。
为了解读这一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首先需要澄清口供问题究竟指得是什么样“口供”的问题。
一、“口供”词义之辨正
“口供”一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只出现过一次。
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却是一个普遍接受并频繁使用的习惯用语。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在外延上,既包括供述,也包括辩解。
这一解释,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待“口供”的基本态度。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5条(现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
”很显然,立法者是在不同于“被告人供述”含义上使用“口供”一词的。
因此,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口供即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普遍共识, 而且,这一解释后来被写入各种法学教材沿袭至今, 并广为传布。
那么,将口供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对此,对此,有学者论证说,“我们认为把口供等同于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可以的,这不仅符合司法机关的习惯称谓,而且有利于纠正以往单纯把口供理解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交待这种片面认识。
在以往司法机关办案时有一种错误倾向,似乎口供就只能是被告人的认罪陈述,把被告人正常的辩解一概斥之为‘狡辩’,不把辩解当作证据,这些错误地认识和做法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 读着如此解释,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一,在我国司法实践的习惯表达中,“口供”真的包括辩解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司法实践中,当侦查人员说“突破口供”、“拿下口供”时,首先指的当然是“撬开犯罪嫌疑人嘴巴”(让其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但是,其意思却绝非止于“开口说话”;相反,其实质上强调的是“被追诉人交待了什么”。
因此,如果一个侦查人员获得了被追诉人辩解就宣称“拿下了口供”,非让同行笑掉大牙不可。
在此问题上,论者的论证自身就前后矛盾。
如果真的如论者所言,“把口供等同于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可以的,这……符合司法机关的习惯称谓”的话,那么,又何来“以往单纯把口供理解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交待这种片面认识”呢?
第二,将口供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真的有如此神力,将改变司法实践中重供述轻辩解的传统习惯吗?
论者的逻辑很简单:
由于过于将口供错误地解释为“只能是被告人的认罪陈述”,所以,造成了“把被告人正常的辩解一概斥之为‘狡辩’,不把辩解当作证据”的后果。
然而,二者之间真的具有因果吗?
——美国不也是将自白等同于有罪供述么,为什么他们不把被追诉人的辩解斥之为狡辩呢?
更何况,我国法律不是已经明确规定“被告人辩解”也是证据吗?
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二者具有因果关系,那么,对口供做超出传统字面含义的解释使之涵盖“辩解证据”就是对症的良药吗?
十年之后的今天,“把正常的辩解一概斥之为‘狡辩’”不依然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吗?
在上述案例中,侦查机关收集了六份犯罪嫌疑人供述却对犯罪嫌疑人辩解只字未提,不是依然没有像论者期待的那样把辩解当作证据吗?
——当然,也有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确实没有辩解。
不过,如此推测的话,案件移交审查起诉后,作了六次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却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就难以理解了——难道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怕得连辩解都不敢了么?
即使不考虑上述论证的荒谬,单就“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一理解自身而言,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在证据法中,供述和辩解是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证据形式:
二者具有不同的证明方向。
其中,前者与被追诉人不利,属于控诉证据,后者则属于辩护证据。
因此,将二者笼统地归入口供名下,有什么实际价值呢?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供述与辩解承载着截然不同的的宪法要求。
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被追诉人享有不得自证其罪其罪的特权,而不再负有协助国家追查所涉嫌犯罪的法律义务。
因此,就供述而言,在宪法层面上,它实际上内在地暗含着一种法律上的限制,即不得以物质或精神上的强迫,强制被追诉人做不利于己的陈述。
另一方面,作为证据而存在的被追诉人辩解,在因果关系上,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自然结果。
因此,在法律意义上,辩解证据首先表现为一种与被追诉人辩护权密切相关的辩解行为,然后,才是作为证据意义的辩解陈述。
辩护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
尊重、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必然要求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价值;不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价值,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在宪法层面上,与对待供述证据的态度相反,立法对辩护权的强调,实质上包含着鼓励辩解、应当不拘一格听取被追诉人辩解的必然要求。
很明显,传统诉讼法对“口供”的解释,不但无助于揭示上述两种不同宪法意蕴与相对立的证据价值,而且,在一个笼统的解释中,上述问题反而被“遮蔽”了起来,致使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实,在我国司法传统上,“口供”一直都是特指“承认有罪的供述”。
如,“断罪必取服输供词”、“无供不录案”、“罪从供定”等。
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口供即“供述”也是多数学者们的共识。
如,匡保之在其1957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被告人口供实质上就是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承认。
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词典》是我国建国以来编写的第一部法学词典。
该词典对“口供”解释如下:
“刑事被告人向司法机关就案件情况所作的口头供述。
” 由于该词典的编写始于1978年仲夏,而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邀请北京和各地法学教学、研究等单位部分同志编写完成的,因此,可以说,该解释反映了刑事诉讼法颁布生效前刑事诉讼法学者对待口供的一般观点。
在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口供指的是“供述证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而且,如果考虑到,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人员绝大多数都曾经受过基本的法学教育,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关于“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谆谆教导是完全失败的;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反思,多年来奉为圭臬的理论解释本身是否就是个错误:
一个在理论上有害且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错误?
为此,我们认为,关于口供的理解,应当以司法实践中的通用语义为准,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只有如此,才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口供问题”。
二、口供问题的关键
根据供述的时空条件不同,口供可以分为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与庭外供述。
其中,在诉讼实践中,后者通常表现为审前阶段形成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笔录。
从各国立法看,当庭供述与庭外供述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前者具有当然的证据资格,后者只有在具备特定条件下才能够取得接受法庭调查的资格。
在现代诉讼制度下,一般认为,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具有可以推定的自愿性、任意性,当然具有证据资格。
其中,在英美法中,如果被告人在法庭上当庭对指控犯罪供认有罪,即构成有罪答辩。
如果法院认为该供认是“自愿、明知且明智”的并予以接受,那么,案件将不再进行审判而直接进入量刑阶段。
在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也承认当庭供述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但基于国家刑罚权必须公正行使的理念,法庭不得仅仅因为被告人自愿供述而认定其有罪。
即,只有被告人供述,不得确认被告人有罪。
一般认为,对于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必须适用补强规则,即必须在足够的补强证据担保下,才得确定有罪。
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规定:
“不论是否被告人在公审庭上的自白,当该自白是对其本人不利的唯一证据时,不得认定被告人的有罪。
前两款的自白,包括对起诉的犯罪自认有罪的情形。
” 对此,日本学者解释说,“现行法的立场是,即使信用性高到光凭口供就能达到100%的有罪心证,如果没有补充强化证据,也不能判决有罪(宪法38条第3项、刑诉法319条第2项,称之为补充强化证据的形式性要求,或叫做自由心证的例外的补充强化法则)。
这是因为有偏重口供的倾向。
基于为防止万一误判应慎之又慎的想法,法律上作了特别的要求,形成了自由心证主义的一种例外。
”
与当庭供述不同,被追诉人的庭外陈述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资格,相反,却受到证据规则严格控制。
也即,庭外陈述必须经过相应证据规则的检验,才能够获得证据资格接受法庭的调查。
在英美证据法上,庭外供述尽管往往表现为固化的文字笔录,却并不适用传闻规则。
“允许接受一名当事人的承认为证据,是一项重要的传闻规则的例外,因为这一例外不论在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中都是最为常见的。
……在许多刑事案件中,也涉及到被告人在审判以前所作的承认。
这些承认既可能是在谈话中无意作出的,也可能是在回答警察或控诉机关官员的讯问时作出的。
(通过正当方式的讯问取得的供述,对这种传闻例外而言,仅仅是一种可成为证据的特殊类型的承认。
)”
在英美国家,判断一项庭外供述是否具有可采性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任意性。
任意性规则(又称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的含义是,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即承认有罪的陈述),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者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口供,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均不具可采性。
任意性法则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一项传统证据法则。
但是,其理论根据却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英国,排除非任意性自白最初是基于排除虚假陈述的考虑。
在英国诉沃利克沙尔案件(1783年)中,法院认为,“供认被当作证据而被采证,或者由于不能采证而被驳回,考虑的是这些供认是否值得相信”。
随着被追诉人人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任意性法则开始与公民基本权利在了一起。
在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
“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自证其罪。
”据此,被追诉人不得被迫供认有罪,缺乏任意性的供述不得采纳为证。
20世纪40年代后,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关于排除非任意性自由的依据,已经由强调“供述的任意性”,转向程序的违法性,即如果口供是在非法延长被告拘禁期后取得或侵犯了其律师帮助权,或未遵守沉默权告知义务,不问此项自白的可信性与自愿性如何,均不得采用。
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作的判例对此立场虽有所修正,但仍然保留了必须信守正当程序的观念。
为了消除警察违法逼取口供的诱因,一些传统上的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也逐步确立了以保障供述任意性为目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法国,对于用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态度。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则明确规定,如果违背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第1款、第2款的规定,对被告人使用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诈欺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可以采用。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以保障被告人的精神自由为目的,要求“不得使用足以影响人的自由决定权或者足以改变对事实的记忆和评价能力的方法或技术,即便关系人同意”。
根据该法典第191条的规定,违背该法律禁令而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辩护方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审级中都有权要求排除此项证据。
因而,尽管两大法系在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但是,在保障被告人自由供述问题上却存在较大的一致性。
二战之后,日本以美国为样本重新制定的宪法、刑事诉讼法对庭外供述的证据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定。
其中,以自白排除法则最为有名。
《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出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1款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以及其他可以怀疑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
二者共同构成了自白排除法则的法律依据。
依照判例,否定自白任意性的要件有二:
一是自白的获得程序违法或不适当,二是该违法或不适当的程序和自白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日本法律和判例,下述自白不具可采性:
1.出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
2.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
所谓“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 不单单指超期羁押,如果综合全案情况认为不宜羁押或不宜长期羁押的,即使没有超过法定羁押期,亦属于“不适当情形”。
3.通过其他方法取得的,怀疑不是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所作的自白。
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此类自白包括没有告知沉默权而获得的自白、通宵讯问而获得的自白、戴手铐讯问而获得的自白、限制辩护人会见时间而得的自白等。
其中,针对夜间讯问、没有取下手铐进行的讯问、在代用监狱中的强迫性讯问以及出于承诺和诡计而取得的自白,日本判例具体阐明了以下观点:
(1)夜间调查的自白。
判例认为,夜间调查本身并不一概使自白丧失证据能力,除非夜间调查与自白的非任意性之间有因果关系。
(2)没有取下手铐进行的调查。
判例认为,正确的解释是,正在受羁押的被疑人受讯问时,如果是在施加手铐的情况下进行的,推定其身心受到一定的压迫,不能期待任意的供述。
只要没有反证,应当对该供述的任意性抱有怀疑。
(3)出于承诺的自白。
判例否认了以下承诺下作出的自白的证据能力:
①如果自白将不起诉;②如果自白即处以罚金;③如果自白就不逮捕并以罚金结案;④如果自白将尽快释放;⑤若自白将得到恩赦;⑥即使自白也不将其作为证据;⑦若自白将给提供兴奋剂;⑧若自白将允许与亲属,带来律师费用等。
总之,对出于承诺的自白,判例否认其证据能力的较多。
(4)出于诡计的自白。
判例确定的标准是,诡计是否使被疑人受到心理强制,从而是否有诱导虚假自白的可能性。
如有的判例认为,专卖局官员诈称私人侦探虽然不是希望的方法,但却不会伴随诱发虚假自白的危险,因而确认了自白的证据能力。
(5)当自白笔录是唯一的直接证据时,若该自白是侦查当局将被告人拘禁在代用监狱中强迫取得的,则该自白不具有任意性,因而也不具有证据能力。
在日本,如果辩护人能够以“优势证据”证明被告人自白非出于自由意志或怀疑非出于自由意志,对该自白任意性的证明责任即由检察官承担,并且必须以“严格证明”的方式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上,“被告人在法庭外供述的自白属于传闻证据,在形式上除适用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外,也适用第322条、第324条第一款的规定。
” 因此,在日本,庭外供述同时受制于传闻规则与任意性规则;只有通过二者的检验,庭外供述才能被法庭采纳。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20条在“排除传闻证据的原则”标题下规定:
“除第321条至第328条规定的例外,不得以书面材料作为证据代理公审期日的供述,或者将以公审期日外起他人的供述为内容所作供述作为证据。
”之后,作为传闻规则的例外,该法第322条规定了“被告人的供述书和供述记录书的证据能力”问题,并在第325条进一步规定了“对供述任意性的调查”。
但一般认为,对庭外供述影响最大的还是第319条的规定。
我国立法没有规定自白任意性规则。
但无可否认,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已包含了自白任意性规则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我国《刑法》第247条将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
这些立法规定都体现了自白任意性规则所要求的“供述自愿”的基本精神。
不过,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立法默认了违法取得的供述的证据资格,致使司法实践中为了破案,采用非法手段,甚至是刑讯逼供的行为逼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事例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我国刑事司法部门的权威形象。
为此,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贯彻《刑事诉讼法》而作的司法解释,都否定了以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资格。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据此,可以说,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供述的证据规则,尽管该规则在是否非法取得的证明责任等具体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法律的抽象规定不等同于具体的司法实践。
因此,当我们转向司法实践时,所看到的情形却不容乐观。
一方面,像案例显示的那样,庭外供述笔录可以毫无限制地涌入审判阶段。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被告人供述一样,都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经过查证属实后,都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因此,在法庭调查中,侦查起诉阶段形成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笔录几乎丝毫不受限制地涌向法庭,致使讯问被告人几乎沦为了对庭外供述笔录的调查核实。
于是,在法庭调查阶段,一旦被告人推翻或否认之前的庭外供述,法庭就必须在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与庭外陈述之间做出选择。
另一方面,像案件表明的那样,非法证据规则很少被付诸实践。
非法证据规则的立而不用造成了以下两方面的对立发展:
第一,该规则对侦查人员违法逼取供述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遏制作用,刑讯逼供等恶性事件像以前一样仍时有发生。
第二,抽象权利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地激励着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被告人坚定地以此为由要求排除非法取得的庭外供述。
于是,被告人当庭推翻庭外供述 的现象迅猛增多,法庭被一次次地逼进了“死胡同”:
不得不就庭外供述的真实性做出明确表态,而不能像被告人继续供述的案件那样顺理成章地依靠庭外供述作出裁判。
因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谓的口供问题其实与被告人的当庭供述无关,而只涉及犯罪嫌疑人的庭外供述。
更准确地说,在于被告人当庭推翻庭外供述时,法律/法庭应当如何对待庭外供述笔录。
在司法实践中,这一问题更多地表现为“法庭如何判断庭外供述的真假”。
三、口供问题的实质
对于“法庭如何判断庭外供述的真假”这一实践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上的回答其实很简单:
“这属于证据评价问题,只能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出判断”。
如果强求做更详细的解答,理论所能提供的也只能是一种评价方法。
其中,重点审查口供中的“隐秘细节”是一种普遍接受的审查方法。
审查“隐密细节”的理论根据是这样的:
尽管具体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是确定不变的,并因此属于同一罪名的犯罪必然具有共同的相似特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犯罪案件都必然具有自身的特殊之处。
这些特殊之处不仅是一个案件区别于其他案件的重要标志,而且也决定了犯罪过程的大量细节只有犯罪人才可能知晓。
因此,可以说,每个案件的犯罪人都必然拥有关于犯罪过程的大量细节知识,此种细节知识作为一种与特定案件密切相联的知识,别人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知识只能是“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别人是根本无法完全掌握的。
因此,通过犯罪过程的细节知识,犯罪案件与犯罪人密切地勾连在一起。
可以说,每个犯罪案件中都必然存在一些他人无法知晓、只有犯罪人才知道的细节知识,而对于这些“隐密细节”,只有真正的犯罪人才有可能具体、详细地予以描述。
所以,一般认为,对犯罪案件细节知识掌握与否,可以作为检测被告人是否是犯罪人的基本手段。
然而,在我国,法官并非不知道上述方法,而是上述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有效地甄别庭外供述的真假。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开头的案例。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郑某在侦查、预审过程中曾6次供述,但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推翻原供述,拒不承认有罪。
如果仅就郑某侦查阶段的供述而言,其内容包含了诸多细节知识,而如果确实不存在侦查人员诱供的现象,除犯罪人本人外,其他人几乎是无法知晓这些知识,例如,扎的次数、出入现场的路线、具体的作案时间等。
尤其是,犯罪嫌疑人郑某还谈及到了西墙血指印的形成原因。
这些细微之点的印证比较有力地说明,犯罪嫌疑人郑某对犯罪经过非常清楚,辅以其他证据,如鞋印的同一认定、作为凶器的刀的特征等,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然而,不幸的是,本案像其他绝大多数案件一样,同刑讯逼供纠缠在了一起。
于是,当被追诉人在审判阶段推翻先前供述翻并辩称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诱供时,再运用这里提出的“隐蔽性知识”来判断被追诉人供述的真实性,就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
天知道这些“隐蔽性知识”是不是侦查人员“教诲”的产物呢?
对于这些细节内容,侦查人员在勘查现场和侦查过程中已经知道,以侦查人员已经知道的内容验证后来获得供述的真实性,显然无法保证这些细节知识确
实是被追诉人亲身所知的“隐蔽性知识”。
因为,通过诱供、逼供,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制造”出能够供述细节内容的被追诉人。
于是,问题又转了回来:
究竟有没有刑讯、诱供?
显然,对于身处司法实践第一线的司法人员,他们几乎都知道侦查讯问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此,在庭外供述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问题纠缠在一起时,法官一方面会按照法院的习惯做法,在外观上确认公诉机关出示的“绝无刑讯”的证明,另一方面,职业责任和每一个善良人都必然具有的良心却迫使他不得不慎重地考虑:
可能发生的非法取证行为究竟会对庭外供述产生什么影响?
?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窥见了口供问题的真相:
在我国,所谓的口供问题,其实质却并不在口供本身,而在于我国侦查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已经受到了普遍的怀疑。
由于我们已经无法相信侦查人员不会利用其侦查中的优势地位“帮助”犯罪嫌疑人制造出所需要的供述,所以,在庭外供述的评价问题上,我们的法官不得不完成一个谁也没有能力完成的任务:
判断刑讯等违法手段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口供的真实性。
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第八次刑事庭会议决议选编 91 年台上字第 2908 号刑事判例一则
裁判字号:
20XX年台上字第2908号
案由摘要:
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
裁判日期:
20XX年05月24日
相关法条:
刑事诉讼法 第 155、156 条
要 旨:
被告供认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