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一.docx
《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一.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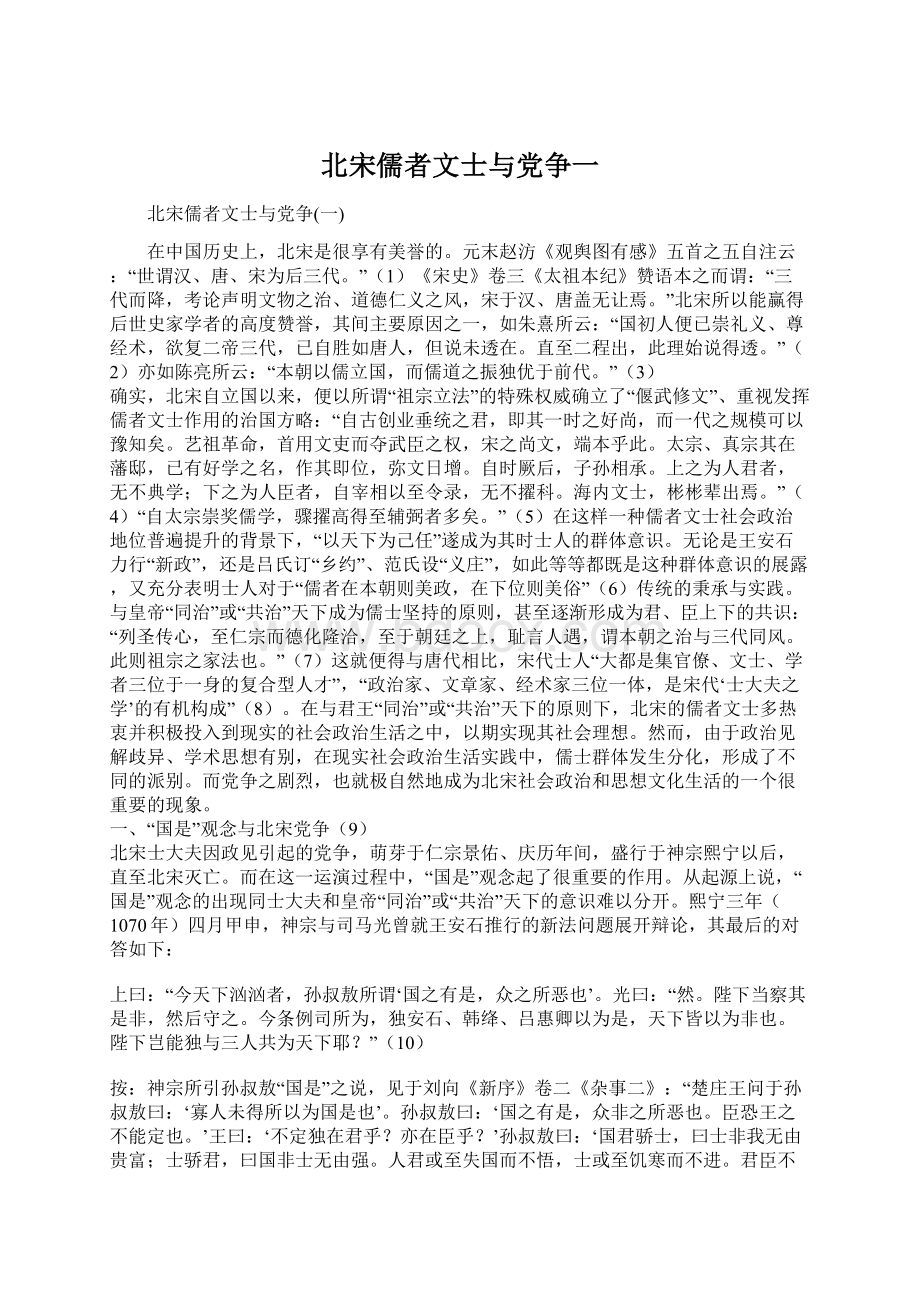
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一
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一)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很享有美誉的。
元末赵汸《观舆图有感》五首之五自注云:
“世谓汉、唐、宋为后三代。
”
(1)《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语本之而谓:
“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北宋所以能赢得后世史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其间主要原因之一,如朱熹所云: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
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
”
(2)亦如陈亮所云:
“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3)
确实,北宋自立国以来,便以所谓“祖宗立法”的特殊权威确立了“偃武修文”、重视发挥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国方略: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
自时厥后,子孙相承。
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
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4)“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得至辅弼者多矣。
”(5)在这样一种儒者文士社会政治地位普遍提升的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遂成为其时士人的群体意识。
无论是王安石力行“新政”,还是吕氏订“乡约”、范氏设“义庄”,如此等等都既是这种群体意识的展露,又充分表明士人对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6)传统的秉承与实践。
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成为儒士坚持的原则,甚至逐渐形成为君、臣上下的共识:
“列圣传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于朝廷之上,耻言人遇,谓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
此则祖宗之家法也。
”(7)这就便得与唐代相比,宋代士人“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8)。
在与君王“同治”或“共治”天下的原则下,北宋的儒者文士多热衷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以期实现其社会理想。
然而,由于政治见解歧异、学术思想有别,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实践中,儒士群体发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而党争之剧烈,也就极自然地成为北宋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一、“国是”观念与北宋党争(9)
北宋士大夫因政见引起的党争,萌芽于仁宗景佑、庆历年间,盛行于神宗熙宁以后,直至北宋灭亡。
而在这一运演过程中,“国是”观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起源上说,“国是”观念的出现同士大夫和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的意识难以分开。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甲申,神宗与司马光曾就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问题展开辩论,其最后的对答如下:
上曰:
“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
光曰:
“然。
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
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
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10)
按:
神宗所引孙叔敖“国是”之说,见于刘向《新序》卷二《杂事二》:
“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
孙叔敖曰:
‘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
臣恐王之不能定也。
’王曰:
‘不定独在君乎?
亦在臣乎?
’孙叔敖曰:
‘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由贵富;士骄君,曰国非士无由强。
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
君臣不合,国是无由定矣。
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为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
’庄王曰:
‘善哉!
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
’”年轻的神宗在引用孙叔敖之语时,于“众”下失一“非”字,此或因其记忆有误,然其源自于《新序》当无可疑。
(11)至于学识渊博的史家司马光熟知《新序》记载的这一故事,更不足为奇前因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宗与司马光这次有关新法问题的论辩中,孙叔敖的“国是”观念成为他们君臣共同的出发点。
所以会出现很有意趣的历史现象,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
“《新序》这一故事是战国晚期士阶层在政治上逐渐得势时的产品,绝非春秋时代的史实,……但故事中的楚庄王愿意和相国及士大夫‘共定国是’的主张则恰好适合熙宁变法的需要。
”北宋“士大夫回向‘三代’的革新要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参与意识都是从仁宗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
庆历变法的短暂挫折并没有降低他们追求变法的热诚,但这些抱着革新理想的士大夫只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因此仅能鼓吹变法,却不能发动变法。
只有皇帝才能发动变法,因为他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
在这个关键时刻,年轻而富于理想的神宗恰好为士大夫的议论所掀动,决心进行变法,于是两个原动力在‘千载一遇’的情况下合流了。
如果神宗一切‘率由旧章’,无意改变现状,‘定国是’的问题便根本不会发生,孙叔敖的话也不会在他心中引起任何反应。
正由于他已决定变法,而士大夫之中不但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并且在同主变法者之间也有怎样变的异议,所以‘定国是’才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天下汹汹’的纷乱将无终止的一日。
这是《新序》孙叔敖故事特别能引起神宗共鸣的基本原因。
”(12)
神宗接受了《新序》提出的“国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作单方面的决定,而应“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仅怀抱回各“三代”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参与意识的士大夫之中,而且士大夫与帝王(如神宗)之间对于何为真正的“国是”,以及帝王应怎样与“士大夫共定国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很严重的意见分歧。
如司马光说神宗“独与三人(按:
指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三人共为天下”,实际指责当时神宗与安石等所“定”者为“国非”而非“国是”,这与神宗所引“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一语不啻针锋相对。
不过,尽管歧异尖锐,却都以欲“共定国是”为原则前提。
这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原则前提或内在精神理念支配,“国是”之说就绝非空洞观念,而是神宗朝及其后宋代政治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一切政争、党争皆必自“国是”始,并且,也只有“国是”确定之后,政争、党争才会有息止的可能。
《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云:
元丰五年(1082)……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
“非司马光不可。
”又将以为东宫师傅。
蔡确曰:
“国是方定,医少迟之。
”
同书卷三一二《王珪传》亦记此事道:
“元丰官制行……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蔡确为右仆射。
先是,神宗谓执政曰:
‘官制将行,欲新旧人两用之’。
又曰:
‘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
’珪、确相顾失色,珪忧甚,不知所出。
确曰:
‘陛下久欲收灵武,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
’珪喜,谢确。
……珪意以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虽召,将不至。
已而,光果不召。
”这两则资料所反映的史实颇能说明“国是”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功能。
尽管神宗在用人上始终有新、旧两派兼用之意,但他毕竟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在与司马光的辩论中即已有意定王安石的“新法”为“国是”,故同年七月壬辰在“吕公弼将去位”,讨论谁代其为枢密使问题时,曾公亮力荐与安石政见相左的司马光,且抬出真宗“且要异论相揽”的祖训为据,而王安石则以为“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事无可为者”,又谓:
“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揽,即治道何由哉?
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
”王安石的意见打动了神宗,他以“要令异论相揽,即不可”终结了对这问题的讨论(13)。
不仅司马光没能代吕公着为枢密使,而且“新法”从此不再是王安石个人关于改革的设计,更已成为了神宗与士大夫“共定”的“国是”了。
“国是”亦即是“最高国策”,自然不容“异论相揽”,由此也使其成为儒者文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大理由。
北宋党争之烈,与政治系统中出现了“国是”这样一个新的文化范畴确有重要关联。
从此角度来分析上面提到的元丰五年蔡确以“国是方定”四字为由阻止司马光复出之事,就很易理解了。
尽管其时王安石已遭二度罢相,但不仅“新法”是神宗亲自肯定过的“国是”,而且所行“官制”乃“神宗因见《唐六典》,遂断自宸衷,锐意改之,不日而定,却不曾与臣下商量也”(14),如此“变法改制”之“国是”显然已与其政治生命合为一体,故而深悉圣意的蔡确很轻易地以“国是方定”为由达到了阻止司马光复出的目的。
神宗虽然始终坚持“国是”,但他在王安石去位后毕竟一直有意起用一部分以前因“异论”而遭斥退的旧人,《续通鉴长编》卷二九二记:
吕公着曰:
“自熙宁以来,因朝廷论议不同,端人良士例为小人排格,指为沮坏法度之人,不可复用。
此非国家之利也。
愿陛下加意省察。
”上曰:
“然。
当以次收用之。
”
这段对话发生在元丰元年(1078年)乙酉,而元丰四年后新官制行,神宗所以欲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则是要实践其“当以次收用”旧人的诺言。
他大约认为熙宁变法之局已定,司马光纵有“异论”也不致触及到“国是”层次。
但蔡确的话点醒了他,——神宗纵究还是担心执拗的司马光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仍会成为“异论”的“宗主”,使“方定”的“国是”再起波澜。
所以,终神宗之世,司马光只能在奉敕撰修《资治通鉴》;及至书成进御的次年三月戊戌,神宗便逝世。
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同“国是”观念紧密关联,于此可见一斑。
“国是”的威力不但阻止了神宗兼用“新旧人”的计划,而且也使宰相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
因为一旦持“异论”者复出并说动上意,“国是”变易,则宰相必将换人。
这也就是王珪、蔡确两位新上任的左、右仆射听到神宗要起用司马光便“相顾失色”的原因。
自神宗朝以来,至少在理论上,宰相是必须对“国是”负责;而在权力运行实践中,则是必须与“国是”同进退的。
如“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允元佑所革一切复之。
”(15)《宋史》卷二四二《宣仁皇后传》则记道:
哲宗嗣位,尊为太皇太后。
驿召司马光、吕公着,未至,迎问今日设施所宜先。
未及条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正禁庭工技,废导洛司,出近侍尤亡状者;戒中外毋苛敛,宽民间保户马。
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预知。
又起文彦博于既老,遣使劳诸途,谕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且令疏可用者。
……光、公着至,并命为相,使同民辅政,一时知名士汇进于廷。
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
元佑年间,在宣仁支持下复出的司马光执政期间,尽废王安石新法。
不过,宣仁、司马光们虽尽变神宗的“国是”,却不肯以“国是”的名目加之于元佑新政,而宁可自称为“复祖宗法度”。
这是因为“国是”早已与熙宁变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王安石一派的专用品了。
但神宗的“国是”在元佑朝被彻底推翻了,这个事实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故而尽管有“复祖宗法度”相标榜,宣仁殁后还是立即爆发了“绍述”运动。
司马光派在元佑朝“复祖宗法度”——实即否定神宗“国是”——的政治举措,本就为新法支持者所不满,他们一直伺机重翻“国是”。
而最早提出“绍述”观念的,是位叫邓润甫的人物:
元佑末,以兵部尚书召。
绍圣初,哲宗亲政,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
(16)
邓润甫其人初由曾布推荐而得到王安石的重用,故其在元佑时期和曾布都没放弃对新法即神宗“国是”的信仰。
司马光曾谕令曾布增损“役法”,布则辞以“义不可为”(17)。
像曾布、邓润甫这样的人显然时刻期盼着重翻“国是”的。
那么,哲宗的心态和举措又如何呢?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他嗣位时年仅十岁,由祖母宣仁太皇太后听政,而如前所述,宣仁是信用司马光等旧派儒臣,力主变更神宗“国是”的。
蔡·《铁围山丛谈》卷一云:
哲宗即位甫十岁,于是宣仁高后垂帘而听断焉。
及浸长,未尝有一言。
宣仁在宫中,每语上曰:
“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
”上但曰:
“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
”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
……宣仁登仙,上始亲政焉。
上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
“朕只见臀背!
”
《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记:
哲宗常使一旧桌子,不好,宣仁令换之,又只如此在。
问之,云:
“是爹爹用底。
”
宣仁大恸,知其有绍述意。
又,刘挚尝进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
宣仁曰:
“常与孙子说,然未尝了得。
”宣仁亦是见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衔之。
绍述虽是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
《宋史》卷三四○《苏颂传》则说:
方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诸臣太纷纭,常曰:
“君长,谁任其咎耶?
”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
惟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
及贬元佑故臣,御史周秩劾颂,哲宗曰:
“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者。
”
将以上三段资料参互读之,大体可以对哲宗的心态及其亲政后所以会即行“绍述”并贬元佑故臣的举措得到比较客观而又同情地理解。
哲宗以十岁之少年而即天子之位,凡起用司马光、吕公着等旧党人物乃至元佑朝司马光执政时尽变神宗之“国是”。
悉由其垂帘听政的祖母宣仁作出决断。
“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
每临朝,哲宗所见诸臣者仅“臀背”而已。
少年的哲宗对于这种状况,尽管声言:
“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
”但内心深处是很不满的。
不肯更换一张曾是其“爹爹用底”“旧桌子”,虽为父子天性使然,但更是他内心深处不满情绪的一种渲泄。
宣仁不仅了解乃孙的这番内在心结,更由此引申出“其有绍述意”即亲政后将重翻“国是”的忧虑,故而一面常以“君子、小人之辨”教诲其孙,一面对政事更加“不肯放下”。
而这皆使“哲宗甚衔之”,其反抗情绪更为炽烈。
元佑八年(1093年)九月,宣仁卒,哲宗亲政,总揽朝纲,终于有了将其压抑已久的不满之情全面发泄出来的机会。
改弦易辙,尽复熙宁、元丰之旧,罢黜元佑旧党,乃至元符二年(1099年)章惇等进《新修敕令式》,哲宗见其中有元佑敕令修令者而很诧异地问曰:
“元佑亦有可取乎?
”(18)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事理之必至。
所以,朱熹所说:
“哲宗甚衔之。
‘绍述’虽是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实在是很中肯的判断。
以上的描述,不过是北宋时期自神宗而损失宗几十年间的历史陈迹而已。
但这几十年间的几经变易,都是在作为专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或“同治”天下名义下进行的,而这其间涌动着的却又是波涛翻澜、惊心动魄的党争。
所不同者,神宗在变法之初似以为绝大多数士大夫都会支持“新法”,而“新法”既行,尤其是他亲自主持的官制,更被钦定为“国是”,与其全部政治生命合为一体。
作为“异论”之“宗主”的司马光本已通过曲折的渠道(如外戚、宦官等)对神宗的祖母(光献后)及其母(宣仁后)发生了重大影响,她们俩人早在熙宁初期便已向神宗“流涕为言安石乱变天下了”(19)。
殆至神宗驾崩,宣仁“垂帘听政”,遂经其与司马光等士大夫“共定”元佑“国是”,将神宗所变之法尽行推翻,但这时的儒士群体不但已公开分裂为新、旧两派,而且旧派之内也开始分化为洛、朔、蜀三支了。
至于哲宗亲政后,则是与邓润甫、曾布等士大夫“共定”“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的“绍述”“国是”的。
这样的历史事实使“我们无法不承认‘国是’的观念这时已确成为宋代政治系统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无论是君权或相权,其合法性都必须由‘国是’提供,否则便‘名不正,言不顺’了。
”(20)
北宋时期与“国是”观念紧相关联的最后一场激烈的党争,发生在徽宗朝。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记之曰:
徽宗有意复熙宁政事,起居舍人邓洵武党京,撰《爱莫之助图》以献,徽宗决意用京,……代曾布为右仆射。
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
“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
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京顿首谢,愿尽死。
(崇宁)二年正月,进左仆射。
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时元佑群臣贬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群国……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
此处所谓“两遭变更,国是未定”,第一次指的是元佑朝变更“国是”,第二次则指哲宗殁后、钦圣太后同听政的六个月期间(即元符三年正月至七月)所发生之事。
后者据史载为:
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按:
时徽宗年十九)。
帝泣拜,移时乃听。
凡绍圣、元符以还,(章)惇所斥逐贤士大夫稍稍收用之。
……才六月,即还政。
明年(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崩,年五十月(21)。
钦圣力主徽宗继位,而章惇反对,赞成者则有曾布、蔡卞、许将等。
所以,元符三年这一年的朝政布置基本上取决于钦圣的意向。
如果说仁宗、英宗、神宗三代皇位在政治上都同情旧党,那末,钦圣虽不像光献、宣仁那样激烈地反对“新法”,但在感情和政见上也都是偏向于元佑旧臣的。
这才有所谓“两遭变更,国是未定”之说。
钦圣收用元佑旧臣,却不拟在政治上大事更张:
“时议以元佑、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失消释朋党。
明年(元符四年),乃改元建中靖国,邪正杂用,(韩)忠彦遂罢去。
(曾)布独当国,渐进‘绍述’之说。
”(22)这是钦圣与徽宗“同听政”时期的一种折衷调和政策,似可称为以“建中”为“国是”,在此“国是”原则下,兼用新、旧两党。
徽宗称之为第二次“变更”,显然对此并不满意。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钦圣死,韩忠彦很快便于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被罢相,“绍述”之说又昂然抬起头来了。
在这背景下,蔡京、蔡卞兄弟“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不仅充分反映了“国是”的功能,而且最能展示出蔡氏兄弟是如何藉“国是”之名目以掀动党争的。
始作俑者是蔡京之弟卞,其事起于哲宗绍圣时期,《宋史》卷四七二《蔡卞传》云:
卞以“(绍圣)四年(1097年)拜尚书左臣,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
”按:
蔡卞乃王安石女婿,长期从之受学,又收藏了安石的《日录》孤本,不仅拥有阐述安石新法即神宗“国是”的独特权威,而且其说也能得到新党中人的普遍接受。
而反对派亦因此而将他列为抨击的首选目标。
下引陈瑾驳论,很能反映出当时新、旧两派“国是”这一核心观念而呈露出的严重政见分歧:
安石所撰《士师八成义》,以谓守正特立之士,以邪诬而不容于时,此祸本之所注而大盗之所以作也。
蔡卞“继述”之说,其本在此。
守此意者谓之守,不然则指为邪朋;立此说谓之特立,不然则指为流俗。
非我类者皆邪朋也,异我说者皆邪诬也。
于是,用其所谓守正特立之士,废其所谓邪朋邪诬之人,从而喜曰:
“祸本消矣,大盗息矣。
”此(蔡)卞之所谓国是也。
人主不得违,同列不敢议,(章)惇、(曾)布在其术内而不知也。
(23)
文中“继述”即是“绍述”的同义语。
意即“全面继承神宗(王安石)的政治遗产”。
此处,陈瑾驳斥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最合蔡卞、蔡京当时的政治需要。
熙宁三年,神宗和王安石早已决定不许朝廷上再存在反对“新法”的议论,甚至公然否定了真宗提出的“且要异论相揽”的原则。
则“新法”既被定为“国是”,则等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已经订立了必须共同遵守的“契约”;皇帝固然不再有片面毁约的便利,而执政更可借“国是”以排斥异党,王安石《士师八成义》中以“守正”自许而指斥“异论”者为“邪诬”便由此而来。
至于哲、徽二宗既然都曾公开承认“绍述”为“国是”,则自然不能不受其约束,而蔡卞于哲宗朝便可“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了,蔡京则于徽宗朝“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对现实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了。
崇宁朝,蔡京更正式用“正邪”来划定士大夫的政治成分:
“(崇宁元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
……庚子,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贵有差。
”(24)至于其后又立《元佑奸党碑》和禁“元佑学术”,那就更是尽人皆知之事,无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