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docx
《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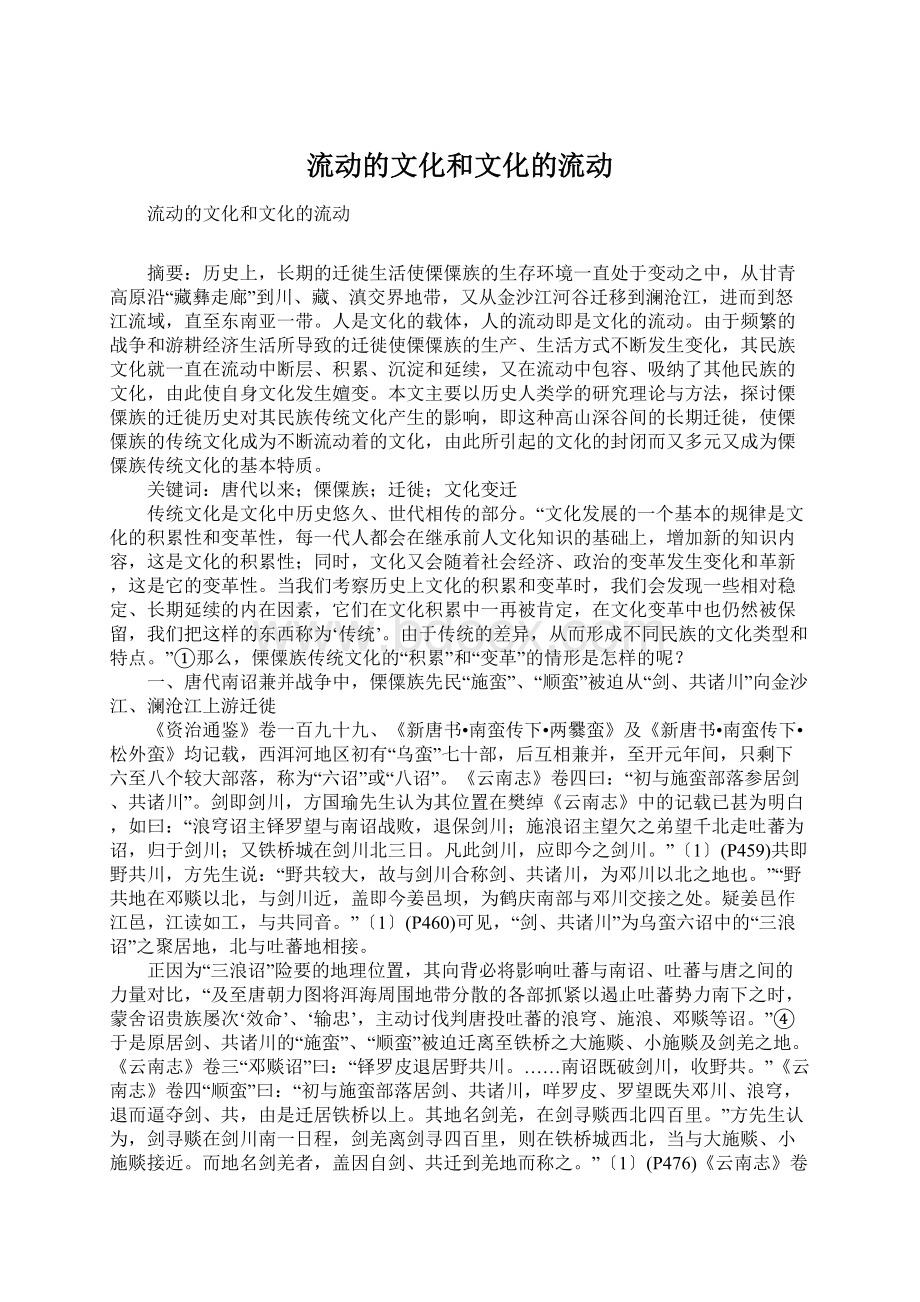
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
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
摘要:
历史上,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傈僳族的生存环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甘青高原沿“藏彝走廊”到川、藏、滇交界地带,又从金沙江河谷迁移到澜沧江,进而到怒江流域,直至东南亚一带。
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流动即是文化的流动。
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游耕经济生活所导致的迁徙使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其民族文化就一直在流动中断层、积累、沉淀和延续,又在流动中包容、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由此使自身文化发生嬗变。
本文主要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傈僳族的迁徙历史对其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即这种高山深谷间的长期迁徙,使傈僳族的传统文化成为不断流动着的文化,由此所引起的文化的封闭而又多元又成为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关键词:
唐代以来;傈僳族;迁徙;文化变迁
传统文化是文化中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部分。
“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文化的积累性和变革性,每一代人都会在继承前人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内容,这是文化的积累性;同时,文化又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发生变化和革新,这是它的变革性。
当我们考察历史上文化的积累和变革时,我们会发现一些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内在因素,它们在文化积累中一再被肯定,在文化变革中也仍然被保留,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为‘传统’。
由于传统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类型和特点。
”①那么,傈僳族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变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一、唐代南诏兼并战争中,傈僳族先民“施蛮”、“顺蛮”被迫从“剑、共诸川”向金沙江、澜沧江上游迁徙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新唐书•南蛮传下•两爨蛮》及《新唐书•南蛮传下•松外蛮》均记载,西洱河地区初有“乌蛮”七十部,后互相兼并,至开元年间,只剩下六至八个较大部落,称为“六诏”或“八诏”。
《云南志》卷四曰:
“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
剑即剑川,方国瑜先生认为其位置在樊绰《云南志》中的记载已甚为明白,如曰:
“浪穹诏主铎罗望与南诏战败,退保剑川;施浪诏主望欠之弟望千北走吐蕃为诏,归于剑川;又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
凡此剑川,应即今之剑川。
”〔1〕(P459)共即野共川,方先生说:
“野共较大,故与剑川合称剑、共诸川,为邓川以北之地也。
”“野共地在邓赕以北,与剑川近,盖即今姜邑坝,为鹤庆南部与邓川交接之处。
疑姜邑作江邑,江读如工,与共同音。
”〔1〕(P460)可见,“剑、共诸川”为乌蛮六诏中的“三浪诏”之聚居地,北与吐蕃地相接。
正因为“三浪诏”险要的地理位置,其向背必将影响吐蕃与南诏、吐蕃与唐之间的力量对比,“及至唐朝力图将洱海周围地带分散的各部抓紧以遏止吐蕃势力南下之时,蒙舍诏贵族屡次‘效命’、‘输忠’,主动讨伐判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邓赕等诏。
”④于是原居剑、共诸川的“施蛮”、“顺蛮”被迫迁离至铁桥之大施赕、小施赕及剑羌之地。
《云南志》卷三“邓赕诏”曰:
“铎罗皮退居野共川。
……南诏既破剑川,收野共。
”《云南志》卷四“顺蛮”曰:
“初与施蛮部落居剑、共诸川,咩罗皮、罗望既失邓川、浪穹,退而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以上。
其地名剑羌,在剑寻赕西北四百里。
”方先生认为,剑寻赕在剑川南一日程,剑羌离剑寻四百里,则在铁桥城西北,当与大施赕、小施赕接近。
而地名剑羌者,盖因自剑、共迁到羌地而称之。
”〔1〕(P476)《云南志》卷四“顺蛮”条曰:
“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掳其王傍弥潜者宗族,置于云南白崖养给之。
”又其书“弄栋蛮”条曰:
“率众北奔,后分散在磨些江侧,并剑、共诸川悉有之。
”《新唐书•南诏传》:
“施蛮者,居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即施蛮部落所居也。
”《云南志》卷四:
“施蛮,本乌蛮种类也,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
”。
方先生考证说:
剑寻赕在剑川城南,为施蛮初居之地,后迁至铁桥西北,其地名施赕者,盖因施蛮所居也。
不详其位置,惟今塔城关西北其宗、普喇等处,有较广阔之地,或即在此。
“总而说之,西洱河以北邓赕、浪穹地带居民为施、顺二蛮,开元年间,邓赕、浪穹及施浪三浪诏主为其部族之统治家族,被南诏皮罗阁击败,失邓赕、浪穹之地,其统治家族退至吐蕃占据之剑川、野共川,受吐蕃封王。
历五十余年后,南诏异牟寻又攻破剑川、野共,俘其统治家族安置于永昌、蒙舍、白崖等处,惟施浪诏主傍罗颠脱走。
至于部族居民迁出,《云南志》说:
‘傍罗颠走泸北’,‘施蛮、顺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于东北诸川’,以地理审之,当是由剑川出走,渡泸而北,在南诏之东北境,应即元代所设北胜府境。
”
这场由战争引起的民族迁徙,还有一部分人口向西北迁徙到了澜沧江流域。
《云南志》卷六:
“宁北城……即至铁桥城北九赕川;又西北有罗眉川。
又西有牟郎共城,又西至傍弥潜,西有盐井,盐井西有剑寻城。
皆施蛮、顺蛮部落今之所居也。
”罗眉川即今之兰坪县,傍弥潜城西部的盐井即今兰坪西部的拉鸡井。
而盐井西部的剑寻城,显然已延伸到了碧落雪山东部进入今怒江州福贡县和原碧江县的境内。
《云南志》卷二也载:
“澜沧江源出吐蕃中。
……又过顺蛮部落,南流过剑川大山之西。
”正德《云南志》卷十一《丽江府》:
“兰州,旧时地属南诏,为卢蛮所居。
名罗眉川。
”可见,唐代还有一部分“施蛮”、“顺蛮”向西迁徙到了澜沧江两岸直至碧落雪山东部,散居于滇西北澜沧江东西两地。
这一部分在史籍中记载不多,或许是因为从规模上没有迁到金沙江那一部分大,也可能是地域偏僻,中原王朝的统治还未深入其地,外界对此了解甚少。
但就是后一条原因使其成为迁徙到金沙江流域的那部分“施蛮”、“顺蛮”之后裔到元朝以后迁徙的主要方向和路线。
“施蛮”、“顺蛮”原来既同是“乌蛮种类”,在唐贞元之前同属于“三浪诏”,共同居住于洱海以北地区;贞元后,向东北迁徙的“施蛮、顺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于东北诸川”,方先生考释曰:
“北胜州、顺州居民,唐贞元年从弥河三浪迁来为主要,又有白人、罗落、磨些诸族,盖当地相传如此。
”〔1〕(P468)而向西北迁徙的一部分,从九赕川、罗眉川一直到剑寻城“皆施蛮、顺蛮部落今之所居”。
也就是说在迁徙前后“施蛮”、“顺蛮”二蛮均居处于相同的地域内——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带,内部的联系并未因为迁徙而中断,相反因为被迫向山高皇帝远的僻壤迁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容易被保留下来,而与“六诏”中的其他“乌蛮”部落产生了差别,同时导致二者之间,顺蛮“男女风俗,与施蛮略同”,文化特点相似,为逐步演变为同一民族——“卢”或“栗粟”奠定了基础。
至于被南诏“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俘其统治家族安置于永昌、蒙舍、白崖等处”的那部分“施蛮”、“顺蛮”,在其后的历史中不见于纪录,该是融入当地部族之中了。
从历史记载看,17至19世纪的200多年时间里,因不堪忍受满清政府的统治和异族土司的兵丁劳役之苦,〔2〕(P23-24)居住在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先后掀起了3次起义:
清嘉庆八年维西恒乍绷起义,道光元年永北唐贵起义,光绪二十年永北丁洪贵、谷老四起义。
每次起义失败后整个家族就沿着先民的足迹由东向西迁徙,用他们自己的话是“顺着太阳落的地方迁移”。
〔2〕(P20)
二、游猎和采集经济生活所导致的迁徙
促使历史上傈僳族迁徒的其他原因还有其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
从史书记载看,明代的傈僳族还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经济生活,《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
其妇人则掘草木以给日食;岁输官者,维皮张耳。
”嘉靖年间杨慎编纂的《南诏野史》下卷“南诏各种蛮夷”记载:
“力些,即傈僳,衣麻披毡,岩居穴处,利刀毒弩,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
以土和蜂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
”这是14至16世纪傈僳族的情况,说明到明代傈僳族尚处于游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这样的经济特点决定其不断迁徙是可以想见的。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往往是生产力水平越低,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越大,或者说在明代以前,傈僳族的经济生活绝对不会超越采集和狩猎生活而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生活,而且是完全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获取兽皮、野麻以御寒,采集野果、野菜以果腹,猎获野兽、野禽肉食为美食。
到了清代,因居住地和经济生活之不同,有了定居的“家傈僳”和仍然游猎的“野傈僳”的区别,嘉庆七年云贵总督党罗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叙述了维西及澜沧江以西傈僳族的社会经济生活:
“野傈僳住居江外,山硐密箐,并无村寨头人,不通汉语,亦不服官约束,惟种有青稞、苦荞,并无钞粮,每遇冬季江水浅涸之时,即过江在山后一带,打牲为食,与家傈僳认识。
近年以来,野傈僳亦有潜入江内山硐密箐,搭盖草棚居住者。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五》:
“力些,惟云龙州有之,男囚首跣足直衫,披以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
妇女裹白麻布。
善用弩,发无虚矢。
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发弩,中其盾,而妇无伤,以此制服西番”。
《续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
“傈僳相传楚庄蹻开滇时便有此种。
无部落,居姚安、大理、永昌、怒江四府,其居六库山谷者为最悍;其居赤石岩金沙江、边地与永北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居无常”。
《盐源志•种人》:
“傈獭,即栗粟,居于雅砻江之峻岭,为爨蛮之种族,刀耕火种,迁徙不常”。
和锡光《中甸县志稿•种人》:
“狸苏,即《通志》所称之傈僳也。
居于金沙江畔之峻岭崇峰间,种荞麦为食,织麻缕以为衣。
喜猎,射则必中。
性狡悍,好杀戮,惟敬畏么些头目”。
可见,随着傈僳族人口的增长、对猎物需求量的增长以及狩猎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必将导致猎物数量的锐降,也就是说,相对更广大的地理范围才能满足一定数量人口对肉食的需求,采集的情况亦然,由此决定了傈僳族长期“迁居无常”。
傈僳族居住地大多处于高山深谷,不利于发展农业经济,因此他们更习惯于狩猎和采集这样直接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的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过渡到与刀耕火种农业相互补充的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定居、半定居的生活就一直持续到清代的乾隆年间。
余庆远《维西见闻录》曰:
“喜居悬岩绝顶,恳(垦)山而种,地脊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日尽之,粒食罄,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封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
乾隆《丽江府志略•官师略•种人》:
“栗粟,有生、熟二种,岩居穴处,或架木为巢,囚首跣足。
高鼻深眼,身着麻布,披毡衫,猎取禽兽为食。
居无定所,食尽即迁。
佩弩带刀,虽寝息不离,性凶暴嗜酒,一语不同,即持刀相向,俗好仇杀。
近惟居澜沧江边者,称为熟栗。
”克勒脱纳《云南地理考察报告》内有《关于栗粟种族之考源》:
“黎苏人,乃藏缅族之一支,彼等现在似尚继续向南迁移。
其居地为高山,与住于山谷低处之掸人,恰成一个对照。
”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傈僳族逐步改变了采集、游猎的不定居生活方式,但是“打牲为食”、“善弩”、“喜猎”的特点始终未变。
而且刀耕火种的农业特点也决定傈僳族“恳(垦)山而种,地脊则去之,迁徙不常”。
如果说民族战争引起的是傈僳族民族大迁徙,那么,狩猎、采集以及后来的刀耕火种农业引起的迁徙规模相对要小得多,但这种迁徙如涓涓细流,不绝不断,使傈僳族的居住地越来越分散。
三、长期的民族迁徙,使傈僳族在横断山脉纵谷地带与周边众多民族“参错而居”,使其文化有封闭的一面,又有多元的特点
如上所述,从唐代贞元以后,民族战争和经济生活所引起的傈僳族迁徙在其历史上相互交织,连续不断,迁徙的方向则从唐代的同时向东北、西北两个方向迁徙,到元以后主要由东到西,由内地到边疆乃至境外,从金沙江到澜沧江、独龙江、恩梅开江迁徒;分布格局由唐代的基本聚居到近现代的大分散、小聚居。
《元一统志》“丽江路”条明确有了“卢蛮”的记载,其书曰:
“丽江路,蛮有八种:
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
”方国瑜先生等学者均断定“卢蛮”为今天之傈僳族,并说当时“卢在西部之南北多有之”,相对于同一境内的其他民族更具有散居的特点。
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卷),第846页。
乾隆《丽江府志略》、《中甸县志稿》、《维西见闻录》等也将傈僳族与纳西族、怒族、独龙族、藏族、普米族、白族等并列纪录,说明长期以来傈僳族就与以上诸族在横断山脉地带杂居共处。
20世纪40年代,“傈僳民族之中心分布地带,多在云南西北部横断山脉中之高原及澜沧江、恩梅开江之峡谷地带中。
在东经98度到99度30分,北纬25度到27度30分之间。
住于云岭山、碧罗山、高黎贡山岩谷里,分属于维西、贡山、福贡、碧江、泸水、兰坪等县局。
人口约10万余,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竞不履城市,可谓为独居之中心地带。
其他散布于雅砻江、金沙江、恩梅开江、曲江、沧江下游之峡谷之村落,亦复不少。
”〔3〕(P18)进入21世纪,中国境内的傈僳族人口有55.74万多人,云南有55.71万人,其中近一半的人聚居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其余散居在丽江、保山地区和迪庆、德宏、楚雄、大理等自治州。
可见,进入20世纪,傈僳族分布格局大都确定,主要居住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两岸的河谷、山坡、台地上,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矿产丰富。
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怒江河谷两岸,土质多为腐质土及黑沙土,宜于种植包谷、稻谷;河谷气候炎热,常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7度至26度之间;平均降雨量为2500毫米,每年日照约为1900小时。
怒江地区丛山逶迤,江河汇聚,澜沧江、怒江、独龙江自北而南纵贯境内。
怒江东岸为海拔4000多米的碧罗雪山,西岸为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两岸峭壁千仞,峰崖嶙峋。
从河谷到山巅高差达三四千米,形成寒、温、热三种不同的气候。
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北方的动植物能沿着高寒山脊向南渗透,南方的动植物沿暖湿河谷向北分布。
因此,这一带一向被称为我国南北动植物交汇的“十字路口”,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2〕(P1-2)然而,正是这种“过于宽大的自然,使人类依赖于自然就像儿童依赖引绳一样”。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0页。
斯大林也指出: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要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
”斯大林: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6~217页。
实际上地理环境不仅对社会发展进程有着影响,甚至对人种、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起到影响和制约作用。
澜沧江、怒江河谷动植物王国对于当时人口稀少的傈僳族便是建立家园的乐土,使其易于苟且偷安,很少关注生产的改进,致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其二,历史上,傈僳族总的迁徙趋势是向着环境闭塞、交通不便的生存环境迁徙,造成傈僳族与外界的隔离,成为傈僳族社会发展迟缓、文化封闭的另一个原因,使其传统文化不易于受外界干扰而长期保留下来而具有较为原始封闭的特点。
余庆远《维西见闻录•夷人》曰: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皆有之。
男挽髻戴簪,编茅草为璎珞缀于发端,黄铜勒束额,耳带铜环,优人依旧则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杂以麻布棉布织,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齐膝,臁裹白布。
出入常佩利刀,妇挽发束箍,耳带大环,领盘衣,系裙曳袴。
男女常跣足。
喜居悬崖绝顶,恳(垦)山而种,地脊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日尽之。
粒食磬,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
获禽兽或烹或炙,对坐共食。
虽猿猴亦炙食。
俟水一沸即食,不尽无归。
餍复采草根树皮食之。
采山中草木为和合药。
男女相悦,暗投其衣,遂奔而从,跬步不离。
婚以牛聘,丧则弃尸,不经佛而信鬼,借贷刻木为契,负约则延巫祝置膏于釜,烈火熬沸对誓,置手膏内不沃烂者为受诬。
失物则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
触忿则弩刀具发,着毒矢处肉,辄自执刀刳去,性刚狠,嗜杀”。
20世纪40年代,“上帕夷民,原有三种,曰怒子,曰傈僳,曰拉玛。
……傈僳族概由沧江一带移来,亦无姓氏,内分四族:
一名瓦咱,二名括咱扒,三名亥咱扒,四名獗咱扒,均系傈僳语以汉语译之。
挖为鱼,从余姓;括为荞,从乔姓;亥为鼠,从褚姓;厥为蜂,从风姓;扒为老者之称。
此外别无姓氏,亦不知年龄,不通汉语。
……上帕夷民,虽分三种,而性质则互相传变,习染成风,素性犷悍,桀骜不驯,身旁随时带有刀弩,无分稚老,专以抢劫为生。
且极怠惰,不事生产,每年仅种杂粮少许,一家之计,尚不能足。
青黄不接之际,尽皆乏食,概行以树皮草根充饥,形容枯槁,菜色憔悴,惨不忍观。
在群相结伴,往沧江一带,掠人勒赎,已成惯技。
现在高官治理,严行查禁,始各敛迹销声。
惟团结性最坚,各人均持大同主义,乐则同享,苦则同受。
一家有粮,则任意煮酒,合村共饮,日夜欢笑,食尽则散,并无怨言。
故全属虽赤贫,而向无乞丐倚门求食,殊足钦羡。
”《纂修上帕沿边志》,载《怒江旧志》,第54~62页。
另一方面,不断的迁徙,造成了今天傈僳族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也造成傈僳族所接触的周边民族甚多,使其自然生态文化和人文生态文化类型多样,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
“人间四月芬芳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不惟自然物候如此,文化方面也是“十里不同风”,居住在各区域内的傈僳族支系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从元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导致“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之间的文化差异,(清)管学宣修,万咸燕纂:
乾隆《丽江府志略》(二卷),清乾隆八年(1743)刻本。
同见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院《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党罗琅奏折等。
或者说是“家傈僳”与“野傈僳”、“生傈僳”与“熟傈僳”之间的差异。
(清)吴大勋:
《滇南见闻录》(二卷),云南省图书馆藏民间年间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清乾隆刻本传抄庋藏本。
同见(清)管学宣修,万咸燕纂乾隆《丽江府志略》(二卷)、党罗琅奏折等。
而这种差异实际上就是方国瑜先生所论述的“乌蛮”与“白蛮”之间的区别,即“同一地区诸部族间,或同一部族不同地区间,或同一地区同一部族的不同统治者间,社会经济文化的高低差异,风俗习惯的文野差别,汉族文化成分的多少不同,保有本族固有特点不同。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三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记载说:
“本族向无部落,迁移无定,与各夷族杂居,每因环境而与他族发展关系,所以形成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三支系。
”该书对傈僳族三个支系如何形成以及与他族之关系,详尽论述道:
黑傈僳与么些族发生关系,黑傈僳之社区,其近中心地带在维西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及金沙江上游之中甸县属之江边境,丽江县属之鲁桥乡之高山上,其住地多与么些族接近。
或通婚,或互相交易,彼此往来,联络感情,且本族最爱么些族之文化,仿其俗习,循其礼教,甚而服饰也喜改为么些装束,学么些语言,能操么些语者极其普遍,并且统治本族之土司头目,多系么些族人,因此关系尤为密切,于无形中发生同化作用。
……白傈僳之社区,其中心地带在永胜之五郎河、蕨菜坪及宾川之感古山、姚安铁索箐、保山之登埂、鲁掌、卯照、六库、老窝等土司地,与汉人错居。
其统治土司头目多系汉人,因有政教、俗习、贸易、往来,有密切之关系,所以白傈僳多能操汉语,尽量吸收汉人文化、婚丧、礼制,每喜仿汉人俗习。
其住宅之大门贴对联、门神等物,其男女服饰亦多改为汉装,农具什物等亦模仿汉制。
盖汉人文化水准高于傈僳之上,且汉人文化有潜移默化之伟功。
因此,白傈僳族为汉族半同化之演进,是以白傈僳文化水准,较黑傈僳族进化。
……花傈僳之社区,其中心地带,在腾冲之滇滩、古永、狼牙山、明光、鲁仰各寨及龙陵之平戛、六根、象达各地,亦与汉人杂处。
其宰官、头目亦多系汉人。
互相通婚为亲戚,互相交易为朋友,与汉人关系比白傈僳族尤为密切。
农田耕种方法弃其刀耕火种之古老式,而采用灌溉稼穑也。
其主因,由于气候炎热、土司肥沃所致,受汉人之农作影响而成。
故花傈僳的生活每模仿汉人为标准,于无形中受着汉人之支配。
故花傈僳知汉礼,能操汉语,在傈僳族中属较优秀、较先进之分子矣。
《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第5-8页;《怒江旧志》,第44页。
对于傈僳族接受基督教的情况,史书也多有记载:
《泸水志》载:
“自民国十八年春,有龙陵县人民傈僳来泸赶澡堂会,与夷日益结合,用英文字母编成夷语,传耶苏教,自后有美国教士,贝牧师者,来泸借民房暂住,夷人入教逐渐增,十九年向老窝土司属之托基住民买有屋基一场,近已修成木板房,成为教堂,其教规以不宰杀、不吸烟、不饮酒,不盗,每一星期附近三四十里者,俱来集会一次,教长贝牧师,学校每村设一校,入教人数,全区在三百户以上,概系傈僳,他族入耶苏教者无一人。
”“花傈僳族不惟能吸收汉文化,且受欧西之基督教化。
自英传教士傅能仁用拉丁文发明傈僳字,译就傈僳语之《圣经》,始传授于龙陵社区之傈僳,继续扩大到各处之傈僳寨后,向之无文字者,今则祈祷上帝而忏罪恶也。
”〔3〕(P8)可见,傈僳族不仅受到周边纳西族、汉族、白族等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可以说,傈僳族文化同时包容了诸多异族文化于内。
宋蜀华、陈克进:
《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总之,一方面,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决定了傈僳族文化的传统性,“传统文化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等方面表现得尤为鲜明。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在各民族中顽强地保留着,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傈僳族传统文化亦然,负载着傈僳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傈僳族的生活方式,增强了傈僳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由于傈僳族居处分散,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傈僳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并且因为傈僳族长期处于迁徙之中,其文化也一直处于流动、嬗变的状态。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傈僳族与其他民族接触的增多、频繁、密切,这种文化的流动、嬗变的特点就更为明显,因而其多元及包容特征也随之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卷)[M].北京:
中华书局,1987.
〔2〕本书编写组.傈僳族简史[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3〕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院.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R].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