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邦武三峡最后的船工.docx
《谭邦武三峡最后的船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谭邦武三峡最后的船工.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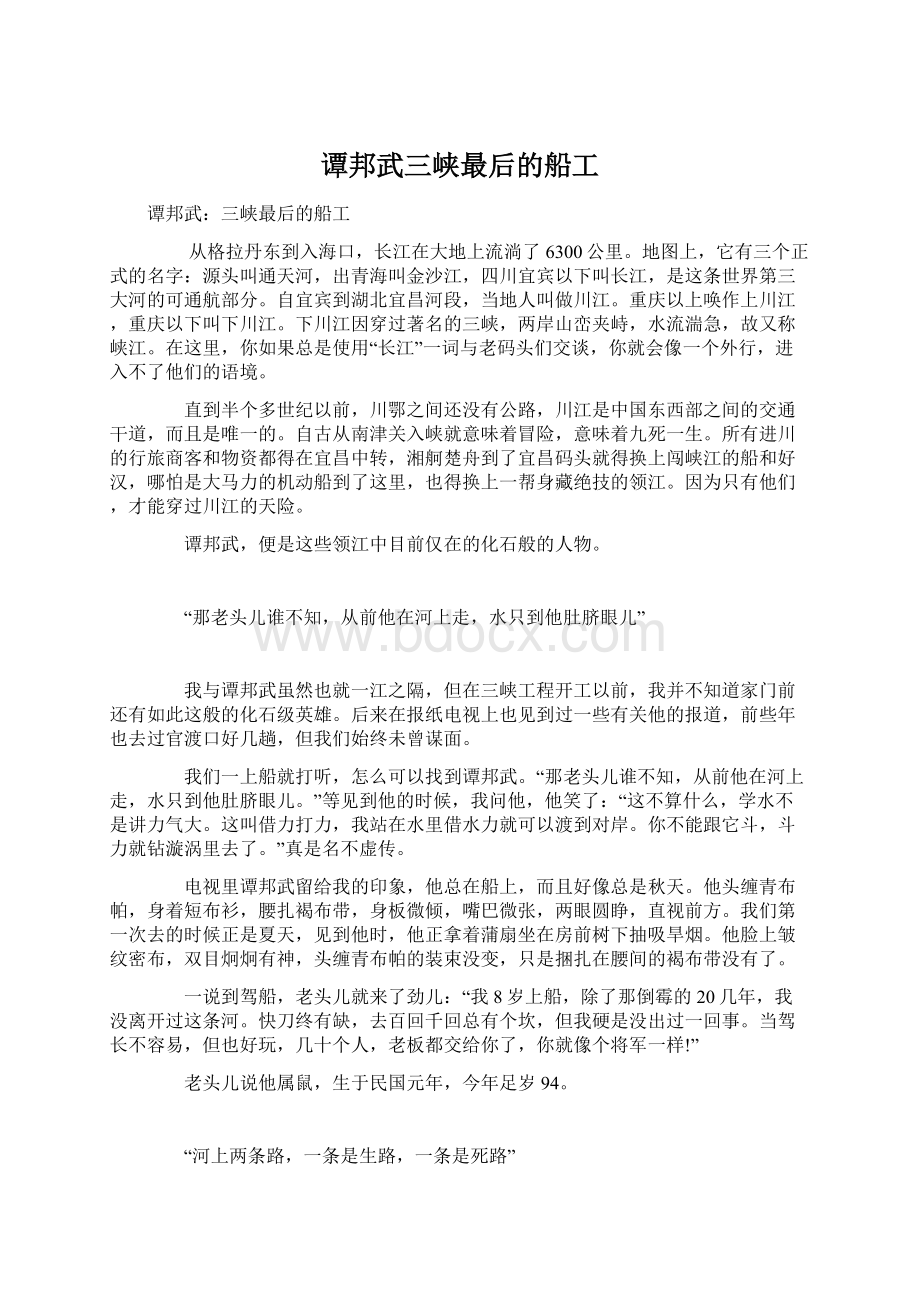
谭邦武三峡最后的船工
谭邦武:
三峡最后的船工
从格拉丹东到入海口,长江在大地上流淌了6300公里。
地图上,它有三个正式的名字:
源头叫通天河,出青海叫金沙江,四川宜宾以下叫长江,是这条世界第三大河的可通航部分。
自宜宾到湖北宜昌河段,当地人叫做川江。
重庆以上唤作上川江,重庆以下叫下川江。
下川江因穿过著名的三峡,两岸山峦夹峙,水流湍急,故又称峡江。
在这里,你如果总是使用“长江”一词与老码头们交谈,你就会像一个外行,进入不了他们的语境。
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川鄂之间还没有公路,川江是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交通干道,而且是唯一的。
自古从南津关入峡就意味着冒险,意味着九死一生。
所有进川的行旅商客和物资都得在宜昌中转,湘舸楚舟到了宜昌码头就得换上闯峡江的船和好汉,哪怕是大马力的机动船到了这里,也得换上一帮身藏绝技的领江。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穿过川江的天险。
谭邦武,便是这些领江中目前仅在的化石般的人物。
“那老头儿谁不知,从前他在河上走,水只到他肚脐眼儿”
我与谭邦武虽然也就一江之隔,但在三峡工程开工以前,我并不知道家门前还有如此这般的化石级英雄。
后来在报纸电视上也见到过一些有关他的报道,前些年也去过官渡口好几趟,但我们始终未曾谋面。
我们一上船就打听,怎么可以找到谭邦武。
“那老头儿谁不知,从前他在河上走,水只到他肚脐眼儿。
”等见到他的时候,我问他,他笑了:
“这不算什么,学水不是讲力气大。
这叫借力打力,我站在水里借水力就可以渡到对岸。
你不能跟它斗,斗力就钻漩涡里去了。
”真是名不虚传。
电视里谭邦武留给我的印象,他总在船上,而且好像总是秋天。
他头缠青布帕,身着短布衫,腰扎褐布带,身板微倾,嘴巴微张,两眼圆睁,直视前方。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正是夏天,见到他时,他正拿着蒲扇坐在房前树下抽吸旱烟。
他脸上皱纹密布,双目炯炯有神,头缠青布帕的装束没变,只是捆扎在腰间的褐布带没有了。
一说到驾船,老头儿就来了劲儿:
“我8岁上船,除了那倒霉的20几年,我没离开过这条河。
快刀终有缺,去百回千回总有个坎,但我硬是没出过一回事。
当驾长不容易,但也好玩,几十个人,老板都交给你了,你就像个将军一样!
”
老头儿说他属鼠,生于民国元年,今年足岁94。
“河上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
谭邦武总是称川江为“我们这条河”,似有不在话下之意,但他同时又说:
“河上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
”
虽然川江已是高峡平湖,如果不盯紧一个漂浮物,你已经分不清水是在往哪边流。
然而在葛洲坝工程修建以前,它可能是中国长江,甚至是全世界最险恶的一段航道。
川江660公里,哪一里没有沉船,哪个月没有船难!
十个师傅万个法,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川江走船唯一的法宝,就是经验。
这是首开机动船航行三峡的英国人阿奇博尔德?
约翰-立德眼中的峡江:
“瞧!
这就是大江,缩至400码宽,在陡峻的石灰岩峭壁之间奔流,巍峨、壮观!
两边的山崖似乎要合拢起来,大江似乎流不过去……沿扬子江上溯重庆,可通航里程为1400海里,其中宜昌以下为1000海里,乘汽船只需一周时间。
其余400海里则需5至6周,比从伦敦到上海的时间还要长。
”“巴水急若箭,巴船去若飞。
”这是李白笔下的川江。
谭邦武说:
“这个河里的文章可大了!
远远望去,水还是平平和和的,走拢就变了,你得赶紧打主意,三分钟不对就死了。
”这是一个由上千个险滩礁石和峡谷的名字所组成的河段。
半个多世纪以前,这些地名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瞬间决定船工们的生死。
“死了球朝天,不死又过年”
三峡地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峡江两岸山高坡陡、重峦叠嶂、沟壑纵横、人多地少,不少人靠在河上冒险养家。
沿江的职业无数,驾船这一行是最风光的,他们走南闯北见世面。
巴东的老一代桡夫子说:
“忠县的人,没有出过三峡,我们叫他土鳖,见过世面的人叫打广,打广的都是桡夫子。
”“桡夫子”是历史上人们对驾船人的蔑称,但桡夫子们并不以为然。
拉纤他们是不穿裤子的,因为拉不了好远就得过河。
他们最自豪的就是告诉你:
“这条河不是我吹,上到重庆,下到南京,我哪儿都走过,什么都见过。
”
然而风光是有代价的。
“炭狗子(煤矿工人)是埋了才死的,桡夫子是死了没埋的,驾船就是提着脑袋玩。
你一上船,就有数千个急流、漩涡和暗礁在等着你,更兼有匪盗出入,杀人越货。
身在江湖漂,怎能不挨刀!
那种事我8岁就见过。
船过了峡江,到达宜昌,拴住了,你活过来了,算命大,死了,算个球!
”这是我知道的,不怪老头儿说得那么轻松。
有资料记载,解放前,从宜昌到重庆的600多里的江面上,每年至少要死亡上千人。
当时的红十字会在峡江设立的水上搜救船队生意十分红火,峡江险滩天天有尸收。
但桡夫子们并不过多考虑生死:
“死了球朝天,不死又过年。
”
“十年能读个举人,十年难造个江湖”
“驾船你得认识那水。
这个河里一季水一季船,船大一尺不同,小一尺又不同。
河里的水三分钟一变,你得看什么水走什么路。
有些人看了一辈子,也没看清楚。
炸滩之前这条河蛮嘶人的,又是泡又是漩,两个泡相互旋转着挤在一起,如果你从中间过,船就会被压到水底去,要辗着漩轮子走船。
还有,前面的船摇橹时会在船后留下一条舵线,叫做一串铃。
遇到了,你不能动舵,把舵梆起,坚持两三分钟后水就分开了。
舵不能跟水拗,你得借它的力,水就给你当驾长,船像蛇娃子一样就过去了。
“你还要认那个杂种的风。
有风上水可以走一两百里路,没得风,只能靠拉靠摇,走五六十里路。
船有多长,帆有多高。
冬天的风平平和和,二三月青草发芽时的风朝篷尖尖上吹(篷就是帆,帆翻同音,为船工所忌),要拴住篷子,把力坐下来,要不一碰风就要翻船。
在这个河里,风一来,河床满面都是风,你必须知道风打哪里来,河床怎么走。
河道一变,风向跟着变,你得用勾子把篷擒住,等到篷上有风了才能放掉。
如果江边有槽,又在一个拐拐上,风到那里就会漫将出来,搞不好,会被它恶狠狠地一抵。
这时间,那个船你看它走得好好的,一到拐弯的地方就滚了。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在这个河里,没有五里路是一帆风顺的。
从夔府到宜昌七八百里路,年年都要出一些事,都要死一些人。
“8岁,爷爷把我抱上船,16岁,我就摇橹摆渡,风行浪走,记得清600里峡江的弯弯拐拐,辨得出几十个险滩的不同水声,记得住峡江上空不同时节的星宿位置。
20岁左右我就避得开暗礁漩涡,认得到生路死路,会接浪冲浪见风使舵。
不是我吹牛,在官渡口这一带,好多人都喊我叫水府三官(水神)。
”
“格杂种,你真是个神人”
“三峡十二滩,滩滩都是鬼门关,青滩最难过,天天打破船。
”谭邦武最喜欢和人聊他闯滩的经历。
“民国三十年腊月,我和外公从南京回巴东,被挡在青滩。
我一数,格老子,有200多条船。
青滩两道坎,一天扯三帆(有专人守候在此收费拉船,谓之拉滩扯帆),如不自己闯,几时轮到我?
那天太阳还没出,我就来到陡滩跟前,坐在礁石高头,观察那水,最少看了四个钟头。
突然,一阵上行风来,两岸树木哗哗作响。
我赶紧跳上船,喊:
伙计们,快把船拉出去。
我在船头指挥舵工扳舵,其余船工全部在岸上拉纤。
我手持小旗,一手指挥舵工扳舵,一手指挥纤夫拉纤,借着风力和大浪回流,不多时我们就爬上斜坡进到了险滩中段。
船越近滩口,舵越不起作用。
这时小船突然往左边一窜,左边是漕流,那是经常翻船的地方,格杂种的,女人娃儿们都哭了。
我飞快取下一个抓子甩出去,解开备用绳,三下两下拴在一个大石头上。
“我指挥船工将小船拉回正道,接着又往上扯。
滩口风大浪急,一个大浪打来,船一簸,缆绳成了两截,我一个箭步,将一个‘8’字套环挂到旁边的轮船上,这才稳住了我们的小船。
歇了一阵,我们又接着拉,其实离滩口上游的大船就只两丈远,可就是靠不上去。
那时也没办法了,只有拼起老命往上奔。
我吼一声,船往前进一步,吼一声,进一步,船往大船上刚一贴,我就喊:
框起!
船就绑在栋梁上了。
”
“爬上来后,扯滩的人都把我看着。
驾长上了船,他把我的肩膀一拍:
格杂种,你真是个神人!
哪个敢走青滩出满塞往南边走?
我说那也没有办法,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是腊月三十哒。
”
“你说这是不是日天的胆?
”
比闯滩更精彩的是闯关。
“偷关不点灯,下雨为最好。
民国二十八年,格杂种的巴东土膏局在万县买了13箱土货要运回来。
我打摆子在家,大哥派两个人来谈,我说病了不能去,两人回去回话,大哥问,站不站得起来。
他们说站得。
大哥说:
去,接来。
“我们在万县旅馆里往下,船是现做的,连我13人。
虽说钱多,但那是把命拿去拼的。
我们半夜装船,夜里上路。
下码头叫红沙碛,有禁烟局守着,他在河对岸点个亮,有人望着,两个钟点一换,船过就有影子。
还差半里地,我远远看见一盏灯,灯光照在江面上,莫说一个船,一个蚊子过都晓得,但已经转不回来了,只好硬闯。
我把船横起慢慢滑下去,让船影子小一点。
守关的人发现了,问:
什么船?
接着,汽筏子就下来了。
他往下水撵,我就往他开船的地方靠,那是强盗的计策。
汽筏子走远了,我再悄悄出来。
走了两里路他们回来了,但他们上水,我下水,一下就下去了。
“到了巫山大峡的青石洞,天亮了。
我知道大岩屋前有条河,几十里上下无人,我把船停了,把13箱土货抬上坡,搬石头把船沉到水里,人在岸上前汉后明、左春秋右礼记地摆古。
老板说,你硬是胆大,所以打摆子都要把你请来。
“天黑了,我们把水舀干,装货上船。
过涪石,乡长晓得有土货偷关,在背水岩架起机关枪。
船到漕口,他们问:
什么人?
我说:
棒老三!
子弹白花花地射来,我抵着岩子边推船,一下就过去了。
“中日战争时,两三条枪十来个人就设个关收税。
收到是你的福气,收不到是我的赚头,我的脑壳是下定钱的。
不冒险找不到吃的,只能拿命去闯。
我在这河上冒的险都是多数人不敢搞的,可恨青年太短暂啊!
”
那是他最威风的时代,他闯政府的关,也闯鬼子的关。
“1941年日本人来了,我有两个又能共金钱,又能共患难的弟兄买了一个船,装了30吨梨,闯日本人的关。
这里买梨几分钱一斤,到湖南买几角钱一斤。
运梨船跟水贼一样,来无影去无踪。
宜昌下面,八百里洞庭,好大的场合,乌龟王八都成了精了,会变人扒在船头看你。
那是脑袋提在手里玩,活下来我们就赚了。
到湖南后卖了梨,把船也卖了,卖一船梨2000块大洋,缠在腰间,衣服往肩上一搭,棒老二看你就不是有钱的料。
你说这是不是日天的胆?
”
“按照我的为人,硬是不得弄到这个程度”
可恨青年太短暂啊!
这个感慨稍有点年纪的人都有,但谭邦武要比常人丰富深刻得多。
从1952年到1969年,谭邦武是在大牢里度过的,刑满释放后当地干部也没让他回家,把他弄到离家十多里的山村又呆了十年。
入狱的缘由是,30多岁,谭邦武就以他超人的技艺和敢日天的胆量,坐上了官渡口哥佬会二哥的位置。
这也不难想像,旧中国人治的历史渊源久远,在川江这样险恶远僻的地方,中央王法鞭长莫及,袍哥当然就是王统之外的另一部王法。
但我们并没听到他杀人放火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或有其他恶行,周围人多是讲,他的水性怎样好,河里救起的人怎样多。
在我们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所唱的小曲也是劝人为善的:
“老仙唉时刻哦云端呀站,看着呀世上哦女和呀男,他有的行恶啊不行唉善啦,造的耶罪恶啊堆如啊山勒……”我曾听到他这样教育他的后人:
“再遭业,丑事搞不得。
”他说的遭业就是受穷,丑事就是坏事。
说到坐牢的缘由,他觉得那倒霉的十几年全是他的才能惹的祸。
“十个指头有长短,我就要把高些的这个拿掉。
我们这个地方,码头小,地方薄,黑白不分,要不,按照我的为人,硬是不得弄到这个程度。
唉!
多少忠臣遭错杀,多少贤良在困土,你去哪个城隍庙,总有一些冤鬼哭。
”
但就是在劳改队,老头儿也是不同凡响的人物。
“我管着格杂种的两百多亩田,喂着他妈的160多头大牯牛,帮劳改队长安排生产,好多人放牛,好多人挖沟,好多人种地,你别以为我只会驾船,提篮撒种犁田打耙我样样会。
”能人就这样,走到哪里他还是能人。
“只要眼睛还看得见,耳朵还听得见,明年我还要打条船”
谭邦武和他几个儿子都是官渡口镇的后靠移民,老伴儿去世以后,他和二儿子住在一起。
眼看就要蓄水了,大部分田地要淹掉,一家人生活成了问题。
老人主张打条木船,蓄水后搞点特色旅游,儿子却想开商店。
“我们祖辈都驾船,怎离得开船呢!
俗话说,肥田赶不上一个瘦店,瘦店赶不上一个烂船,船是个好东西。
等大坝蓄水,神农溪链子溪的水都满了,我们划船带人到溪里去玩,小河比大河好看。
“这个船有好大,好宽,我脑壳里已经有一个活生生的船在水上走。
那是这河上最漂亮的船,它不是笨船,打风不偏,无风时会漂。
”
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船已下水。
船是两用的,升起帆是自行船,没有风就用发动机。
天气好的时候老头儿也上船,他说他不想把一肚子宝贝带到土里去,他要赶紧把驾船的经验告诉他的子孙,同时,他也向他的孙子讨教机动船的开法。
“只要眼睛还看得见,耳朵还听得见,明年我还要打条船。
”
我总觉得,老爷子造这艘木船是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宣言。
他的生命里有一段空白,一段江湖英雄被侮辱被损害的惨痛。
他怀念他的时代,他不能肯定这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他要造这艘川江上唯一的帆船,他说是民国时代的样子,是末代皇帝时候的样子,他要留住时代的影子,通过它向后代、向江上来来往往的钢铁巨船,讲述那个仁义的木船时代的过往。
又有好久没去官渡口了,快95了,不知老人现在怎样。
前两天打电话问,卫国说老人还活着,精神也还好,在家清理前些年记者们留给他的那几箩筐名片、光盘和照片,但打船的事,他再也没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