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梅《暗香》摘选.docx
《丁立梅《暗香》摘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丁立梅《暗香》摘选.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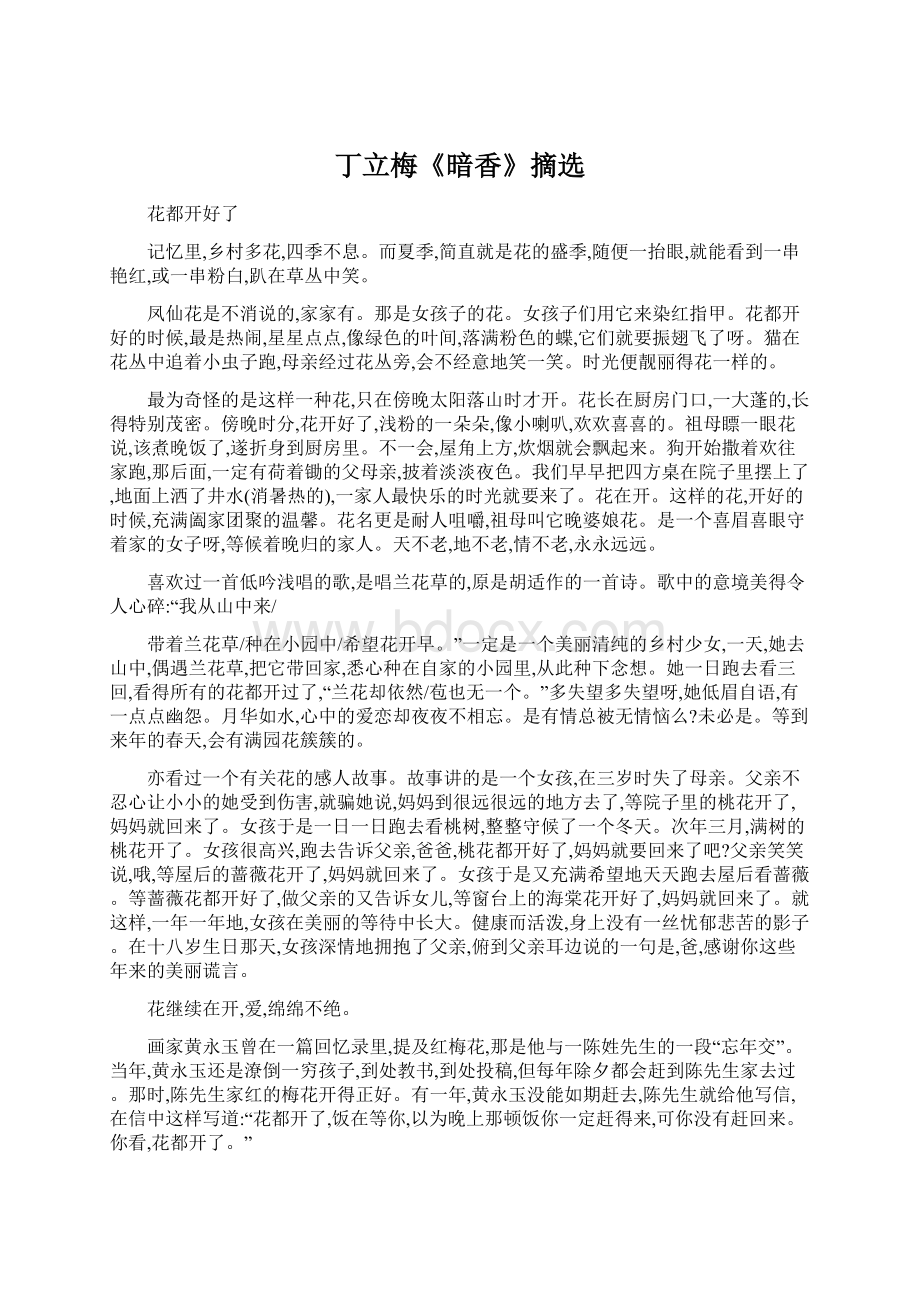
丁立梅《暗香》摘选
花都开好了
记忆里,乡村多花,四季不息。
而夏季,简直就是花的盛季,随便一抬眼,就能看到一串艳红,或一串粉白,趴在草丛中笑。
凤仙花是不消说的,家家有。
那是女孩子的花。
女孩子们用它来染红指甲。
花都开好的时候,最是热闹,星星点点,像绿色的叶间,落满粉色的蝶,它们就要振翅飞了呀。
猫在花丛中追着小虫子跑,母亲经过花丛旁,会不经意地笑一笑。
时光便靓丽得花一样的。
最为奇怪的是这样一种花,只在傍晚太阳落山时才开。
花长在厨房门口,一大蓬的,长得特别茂密。
傍晚时分,花开好了,浅粉的一朵朵,像小喇叭,欢欢喜喜的。
祖母瞟一眼花说,该煮晚饭了,遂折身到厨房里。
不一会,屋角上方,炊烟就会飘起来。
狗开始撒着欢往家跑,那后面,一定有荷着锄的父母亲,披着淡淡夜色。
我们早早把四方桌在院子里摆上了,地面上洒了井水(消暑热的),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就要来了。
花在开。
这样的花,开好的时候,充满阖家团聚的温馨。
花名更是耐人咀嚼,祖母叫它晚婆娘花。
是一个喜眉喜眼守着家的女子呀,等候着晚归的家人。
天不老,地不老,情不老,永永远远。
喜欢过一首低吟浅唱的歌,是唱兰花草的,原是胡适作的一首诗。
歌中的意境美得令人心碎: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定是一个美丽清纯的乡村少女,一天,她去山中,偶遇兰花草,把它带回家,悉心种在自家的小园里,从此种下念想。
她一日跑去看三回,看得所有的花都开过了,“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多失望多失望呀,她低眉自语,有一点点幽怨。
月华如水,心中的爱恋却夜夜不相忘。
是有情总被无情恼么?
未必是。
等到来年的春天,会有满园花簇簇的。
亦看过一个有关花的感人故事。
故事讲的是一个女孩,在三岁时失了母亲。
父亲不忍心让小小的她受到伤害,就骗她说,妈妈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等院子里的桃花开了,妈妈就回来了。
女孩于是一日一日跑去看桃树,整整守候了一个冬天。
次年三月,满树的桃花开了。
女孩很高兴,跑去告诉父亲,爸爸,桃花都开好了,妈妈就要回来了吧?
父亲笑笑说,哦,等屋后的蔷薇花开了,妈妈就回来了。
女孩于是又充满希望地天天跑去屋后看蔷薇。
等蔷薇花都开好了,做父亲的又告诉女儿,等窗台上的海棠花开好了,妈妈就回来了。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女孩在美丽的等待中长大。
健康而活泼,身上没有一丝忧郁悲苦的影子。
在十八岁生日那天,女孩深情地拥抱了父亲,俯到父亲耳边说的一句是,爸,感谢你这些年来的美丽谎言。
花继续在开,爱,绵绵不绝。
画家黄永玉曾在一篇回忆录里,提及红梅花,那是他与一陈姓先生的一段“忘年交”。
当年,黄永玉还是潦倒一穷孩子,到处教书,到处投稿,但每年除夕都会赶到陈先生家去过。
那时,陈先生家红的梅花开得正好。
有一年,黄永玉没能如期赶去,陈先生就给他写信,在信中这样写道:
“花都开了,饭在等你,以为晚上那顿饭你一定赶得来,可你没有赶回来。
你看,花都开了。
”
你看,花都开好了。
冰天雪地里,红艳艳的一大簇,直艳到人的心里面。
它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世界有好人,有善,有至纯至真。
多美好!
像菜花一样幸福地燃烧
油菜花开了,不多的几棵,长在人家檐下的花池里。
这是城里的油菜,绝对不是长着吃的,而是长着看的。
跟他说,菜花开了呢。
他一脸惊喜,说,找个时间看菜花去。
这是每年,我们的出行里,最为隆重的一节。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城里人兴起看菜花热,每年春天,都成群结队的,追到城外看菜花。
一些地方的菜花,因此出了名,譬如江西婺源的菜花,云南罗平的菜花。
有一年秋,我对婺源着了迷,收拾行装准备去。
朋友立即劝阻,说,你现在不要去呀,你等到春天再去呀,春天
有菜花可看呢。
笑着问他,婺源的菜花,怎样的好看?
他说,一望无际燃烧呀,就那样燃烧呀。
笑。
哪里的菜花,不是这样燃烧着的?
所有的菜花,仿佛都长了这样一颗心,热情的,率真的。
一朝绽开,满腔的爱,都燃成艳丽。
有坡的地方,是满坡菜花,有田的地方,是满田菜花。
整个世界,亲切成一家。
我是菜花地里长大的孩子。
故乡的菜花,成波成浪成海洋。
那个时候,房是荡在菜花上的,人是荡在菜花上的。
仿佛听到哪里噼啪作响,花就一田一田开了。
大人们是不把菜花当花的,他们走过菜花地,面容平静。
倒是我们小孩子,看见菜花开,疯了般地抛洒快乐。
没有一个乡下的女孩子,发里面没戴过菜花。
我们甚至为戴菜花,编了歌谣唱:
“清明不戴菜花,死了变黄瓜。
”现在想想,这歌谣唱得实在毫无道理,菜花与黄瓜,哪跟哪呀。
可那时唱得快乐啊,蹦蹦跳跳着,死亡是件遥远而模糊的事,没有悲伤。
一朵一朵的菜花,被我们插进发里面,黄艳艳地开在头上。
也去扫坟。
那是太婆的坟,坟被菜花围着,是黄波涛里荡起的一斗笠。
想太婆日日枕着菜花睡,太婆是幸福的罢。
感觉里,不害怕。
这个时候,照相师傅背着照相器材下乡来了。
他走到哪个村子,哪个村子就过节般的热闹。
女人们的好衣服都
被翻出来了,穿戴一新地等着照相。
背景是天然的一片菜花黄,衬得粗眉粗眼的女人们,一个个娇媚起来。
男人看女人的目光,就多了很多温热。
我祖母是不肯我们多多拍照的,说那东西吸血呢。
但她自己却忍不住也拍了一张,端坐在菜花旁,脸笑得像朵怒放的菜花。
读过一首写菜花的诗,极有趣:
“儿童疾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诗里,调皮的孩子,追逐着一只飞舞的蝴蝶。
蝶儿被追进菜花丛,留下孩子,盯着满地的菜花在寻找,哪一朵菜花是那只蝶呢。
张爱玲的外国女友炎樱,曾说过一句充满灵性的话:
“每一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若果真如此,那满世界的菜花,该变成多少的蝶?
这实在是件美极的事。
菜花开得最好的时候,我选了一个大晴天,和他一起去乡下看菜花。
一路观着菜花去,一路看着菜花回,心情好得菜花似的,幸福地燃烧。
这个时候想的是,就算生命现在终止,我们也没有遗憾了,因为我们深深爱过,那一地的菜花黄。
栀子花开
书房内放有两朵栀子花,是前晚在外吃饭时一朋友送的。
朋友先送我一朵,吃完饭,又从上衣口袋里小心地掏出一朵来,笨拙地,像护着一只小小的蝶。
我极感动,一个大男人,把花藏在口袋里,这样的细节,特别特别动人,顶得上千言万语。
又,能让一个男人,以如此喜爱的方式藏在口袋里的,大概只有栀子花了。
我对栀子花怀有特殊的感情,这样的感情缘于我的乡下生活。
我童年最香的记忆,是有关栀子花的。
那时,乡下人家的院子里,都栽有一小棵栀子树的,也无需特别管理,只要一抔泥土,就长得枝叶葱茏了。
一进六月,满树馥郁,像打翻了香料瓶子呀,整个村庄都染了香了。
一朵一朵的栀子花,息在树上,藏在叶间,像刚出窝的洁白的小鸽似的。
女孩子们可喜欢了,衣上别着,发上戴着,跑哪里,都一身的花香。
虽还是粗衣破衫地穿着,但因了那一袭花香,再平常的样子,也变得柔媚千转。
我家院子里也长有一棵,每到栀子花开的时节,我和姐姐,除了在衣上别着,发上戴着,还把它藏袖子里,挂蚊帐里,放书包里,甚至,把家里小猫尾巴上也给系上一朵。
那些栀子花开的日子,快乐也是一树的香花开啊。
早些天,在菜市场门口,我就望见了栀子花的。
一朵一朵,栖落在篾篮里,如白蝶。
旁边一老妇人守着,在剥
黄豆荚。
老妇人并不叫卖,栀子花独特的香气,自会把人的眼光招了去。
就有脚步循了花香犹疑,复而是低低的一声惊呼,呀,栀子花呀。
声音里透出的,全是惊喜。
买菜找零的钱,正愁没处放,放到老妇人手上,拣上几朵栀子花,香香地招摇。
当时,我也在篾篮前止了步的,老妇人抬头看我一眼,慈祥地笑笑,复又低头剥她的黄豆荚了。
不知为什么我没买花,我走了很远,还回过头去看,空气中,有隐约的花香袭来。
现在,朋友送的两朵栀子花在书房,伴我已有两天了,原先凝脂样的白,已渐渐染了淡黄,继而深黄,继而枯黄。
但花香却一点没变,还是馥郁绕鼻,一推开书房门就闻到。
这世上,大概没有一种花,能像栀子花一样,香得如此彻底了,纵使尸骨不存,那魂也还是香的,长留在你的记忆里。
打电话回家,问母亲院子里的栀子树是否还在。
母亲笑说,开一树的花了,全被些小丫头摘光了。
眼前便晃过乡村的田野,晃过田野旁的小径,一群小丫头奔跑着,发上戴着洁白的栀子花,衣上别着洁白的栀子花,还在衣兜里装了罢?
还在衣袖里藏了罢?
上网去,碰巧读到一解读花语的帖子,其中栀子花的花语挺有意思,那花语是:
喜欢此花的你有感恩图报之心,
以真诚待人,只要别人对你有少许和善,你便报以心的感激。
满架蔷薇一院香
迷恋蔷薇,是从迷恋它的名字开始的。
乡野里多花,从春到秋,烂漫地开。
很多是没有名的,乡人们统称它们为野花。
蔷薇却不同,它有很好听的名字,祖母叫它野蔷薇。
野蔷薇呀,祖母瞟一眼花,语调轻轻柔柔。
臂弯处挎着的篮子里,有青草绿意荡漾。
野蔷薇一丛一丛,长在沟渠旁。
花细白,极香,香里,又溢着甜。
是蜂蜜的味道。
茎却多刺,是不可侵犯的尖锐。
人从它旁边过,极易被它的刺划伤肌肤。
我却顾不得这些,常忍了被刺伤的痛,攀了花枝带回家,放到喝水的杯里养着。
一屋的香铺开来,款款地。
人在屋子里走,一呼一吸间,都缠绕了花香。
年少的时光,就这样被浸得香香的。
成年后,我偶在一行文字里,看到这样一句:
“吸进的是鲜花,吐出的是芬芳。
”心念一转,原来,一呼一吸是这么的好,活着是这么的好,我不由得想起遥远的野蔷薇,想念它们长在沟渠旁的模样。
后来我读《红楼梦》,最不能忘一个片段,是一个叫龄官的丫头,于五月的蔷薇花架下,一遍一遍用金簪在地上划“蔷”字。
在那里,爱情是一簇蔷薇花开,却藏了刺。
但有谁会介意那些刺呢?
血痕里,有向往的天长地久。
想来世间的爱情,大抵都要如此披荆斩棘,甜蜜的花,是诱惑人心的猸。
为了它,可以没有日月轮转,可以没有天地万物。
就像那个龄官,雨淋透了纱衣也不自知。
对龄官,我始终怀了怜惜。
女孩过分的痴,一般难成善果。
这是尘世的无情。
然又有它的好,它是枝头一朵蔷薇,在风里兀自妖娆。
滚滚红尘里,能有这般爱的执著,是幸运,它让人的心,在静夜里,会暖一下,再暖一下。
唐人高骈有首写蔷薇的诗,我极喜欢。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天热起来了,风吹帘动,一切昏昏欲睡,却有满架的蔷薇,独自欢笑。
眉眼里,流转着无限风情。
哪里经得起风吹啊?
轻轻一流转,散开,是香。
再轻轻一流转,散开,还是香。
一院的香。
我居住的小城,蔷薇花多。
是午后时分,路上行人稀少,且都是懒懒的。
蔷薇从一堵墙内探出身子来,柔软的枝条上,缀满一朵一朵细小的花,花粉红,细皮嫩肉
的样子。
此时此刻,花开着,太阳好着,人安康着,心里有安然的满足。
蔷薇几度花
喜欢那丛蔷薇。
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趴着。
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它了。
这个时节,花开了。
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
眼尖的我发现了,欢喜地叫起来,呀,蔷薇开花了。
我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便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地朝前过着。
也顺带着打量从蔷薇花旁走过的人。
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
看久了,有一些人,便成了老相识。
譬如那个挑糖担的老人。
老人着靛蓝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
他的糖担子,也绝对像幅旧画:
担子两头各置一匾子,担头上挂副旧铜锣。
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
惹得不少路人循了声音去寻,寻见了,脸上立即浮上笑容来。
呀!
一声惊呼,原来是卖灶糖的啊。
可不是么!
匾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
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
久远了啊,它是贫穷年代的甜。
那时候,挑糖担的货郎,走村串户,诱惑着孩子们,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
只要一听到铜锣响,孩子们立即飞奔进家门,拿了早早备下的破烂儿出来,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的,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
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
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担儿,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
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
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为的是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
当当,当当当——好,来了!
等待终于落了地。
有时,我也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五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
跟他聊天。
“老头!
”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
“你不要跑那么快,我追都追不上了。
”我跑过那丛蔷薇花,立定在他的糖担前,有些气喘吁吁地说。
老人不紧不慢地回我:
“别处,也有人在等着买呢。
”
祖上就是做灶糖的。
这样的营生,他从十四岁做起,一做就做了五十多年。
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
只有四根半指头。
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就是因喜吃他做的灶糖嫁给他的。
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
“这灶糖啊,就快没了。
”老人说,语气里倒不见得有多愁苦。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
“以前我在别处卖的。
”
“哦,那是甜了别处的人了。
”我这样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两块灶糖给我。
奶黄的月亮,缺了口。
他又敲着铜锣往前去,当当,当当当。
敲得人的心,蔷薇花朵般地,开了。
一日,我带了相机去拍蔷薇花。
老人的糖担儿,刚好晃晃悠悠地过来了,我要求道:
“和这些花儿合个影吧。
”老人一愣,笑看我,说:
“长这么大,除了拍身份照,还真没拍过照片呢。
”他就那么挑着糖担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儿在欢笑。
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薇花。
他看一眼,笑。
复举起手上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
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
我想起南朝柳恽的《咏蔷薇》来:
“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
”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
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罢。
菊有黄花
一场秋雨,再紧着几场秋风,菊开了。
菊在篱笆外开,这是最大众最经典的一种开法。
历来入得诗的菊,都是以这般姿势开着的。
一大丛一大丛的。
倚着篱笆,是篱笆家养的女儿,娇俏的,又是淡定的,有过日子的逍遥。
()代陶渊明随口吟出那句“采菊东篱下”,几乎成了菊的名片。
以至后来的人一看到篱笆,就想到菊。
陶渊明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能被人千秋万代地记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家篱笆外的那一丛菊。
菊不朽,他不朽。
我所熟悉的菊,却不在篱笆外,它在河畔、沟边、田埂旁。
它有个算不得名字的名字:
野菊花。
像过去人家小脚的妻,没名没姓,只跟着丈夫,被人称作吴氏、张氏。
天地洞开,广阔无边,野菊花们开得随意又随性。
小朵的清秀不施粉黛,却色彩缤纷,红的黄的、白的紫的,万众一心、齐心合力地盛开着,仿佛是一群闹嚷嚷的小丫头,挤着挨着在看稀奇,小脸张开,兴奋着,欣喜着。
乡人们见多了这样的花,不以为意,他们在秋天的原野上收获、播种,埋下来年的期盼。
菊花兀自开放、兀自欢笑。
与乡人各不相扰。
蓝天白云,天地绵亘。
小孩子们却
无法视而不见,他们都有颗菊花般的心,天真烂漫。
他们与菊亲密,采了它,到处乱插。
那时,家里土墙上贴着一张仕女图,有女子云鬓高耸,上面横七竖八插满菊,衣袂上亦沾着菊,极美。
掐了一捧野菊花回家的姐姐,突发奇想帮我梳头,照着墙上仕女的样子。
后来,我顶着满头的菊跑出去,惹得村人们围观。
看,这丫头,这丫头,他们手指我的头,笑着,啧啧叹着。
现在想想,那样放纵地挥霍美,也只在那样的年纪,最有资格。
人家的屋檐下,也长菊。
盛开时,一丛鹅黄.另一丛还是鹅黄。
老人们心细,摘了它们晒干,做菊花枕。
我家里曾有过一只这样的枕头,父亲枕着。
父亲有偏头痛,枕了它能安睡。
我在暗地里羡慕过,曾决心给自己也做一只那样的枕头。
然而来年菊花开时,却贪玩,忘掉了这事。
年少时,总是少有耐性的。
于不知不觉中,遗失掉许多好光阴。
周日逛衔,秋风已凉,街道上落满梧桐叶,路边却一片绚烂。
是菊花,摆在那里卖。
泥盆子装着,一只盆子里只开—两朵花,花开得肥肥的,一副丰衣足食的模样;颜色也多,姹紫嫣红,千娇百媚。
我还是喜欢黄色的。
《礼记》中有“季秋之月,菊有黄花”的记载,可见,菊花最地道的颜色还是黄色。
我买了一盆,黄的花瓣,黄的蕊,极尽温暖,会焐暖一个秋天的记忆和寒冷。
绣球花
绣球花是在五月开始做梦的,做着无数个红粉香艳的梦。
它把它的梦,攥成一粒一粒的绿“珍珠”。
又别具心裁地,让许多粒绿“珍珠”相偎在一起,成一个大球球。
这么一看,那是一朵花。
可分明又不是,因为每一粒绿“珍珠”里,都是一个艳红或粉白的小世界。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
你今日去看,绿苞苞是绿苞苞。
明日去看,绿苞苞依然还是绿苞苞。
它完全一副处世不惊的样子,哪管外面夏潮涌动。
可是,有那么一天,你再去看时,却突然发现那些绿苞苞,已然绽开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真是让你又欢喜又气恼。
欢喜的是,它终于绽开了。
气恼的是,它怎么就不让你知道呢。
它也仅仅是轻启绿唇,边缘上染上一圈红晕。
像是陡然遇见陌生人的小女孩,不好意思得很,只低了头,羞红着脸。
别以为它就要全部盛开了,早着呢。
它似乎握着一个极大的秘密,不舍得一下子告诉你。
又像是怀了绝技的女伶,水袖轻舞中,你不知她会抖落出什么绝技来。
你得再等上十天八天,它才彻底地把一颗心交出来。
三瓣儿一起,
艳红,或是雪白的,像纷飞着的小蝴蝶。
每朵之上,密匝匝的,便都是这样的小蝴蝶。
怎么形容它才好呢,美丽?
丰腴?
清雅?
都不对。
它好比横空出世的美人王昭君,无有可比性。
我便养着一盆这样的绣球花,是仲爹送我的。
我曾在他的小区租房住,三层的居民楼,我住三楼,他住一楼。
他的一楼有小院子。
木门,木栅栏,看上去有种古朴朴的好。
院墙上爬满丝瓜藤和扁豆藤,院子里,是热热闹闹的花世界。
每日里上下班,路过他家门前,我总忍不住探头往院子里看一看。
有时,看见他在侍弄花草,花草们绿是绿,红是红,特别惹看。
有时,刚好碰到他把他的老伴抱出来,放到院子里的躺椅里。
听人说,他老伴瘫痪在床已十几年了。
他依然,待她好。
一旁的花草,姹紫嫣红。
天地悠远,时光绵长。
某天,他的老伴突然患病,去了。
吹吹打打的号子手,在楼下吹打,给人凄惶之感。
他红着眼睛,捧一盆开得好好的绣球花,去给老伴送葬。
有人要替他捧着花,他不肯。
大朵的绣球花开在他胸前,艳丽得像塑料花。
让人望着,竟忘了悲哀了。
他的小院子沉寂了。
一些日子后,又重新打开,我见他又在院子里侍弄花草,一院子的红花绿草。
其中,绣球花开得最是轰轰烈烈,几盆红,几盆白,红白相映。
我走
过去,蹲下细看。
他见我喜欢绣球花,很高兴,说,我老伴最喜欢这种花了。
我老伴啊,一辈子就喜欢这些花花草草。
我怔一怔,正想着用什么措词来应答他,好避免碰了他的伤痛。
却听他又笑道,我帮你培育一盆吧,到秋天的时候,你来拿。
秋天,我搬离那里,再没去过那个小区。
偶尔想起绣球花,也只是想想,想仲爹随口的一个承诺,哪能当真。
却在某天,有人辗转捎信给我,说,仲爹帮你育好了绣球花,等着你去拿。
我当即愣住,眼角湿润。
我想起那一院子的灿烂,那是俗世里最庸常的温暖啊,照得见人世间的爱与永恒。
一树一树紫薇花
紫薇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开花的梦的?
四月暮春的天,它还一副沉睡未醒的样。
别的植物早被春光唤醒,争先恐后地兜出自己的好颜色,争奇斗艳,一决高下。
独独它,光溜溜的枝干上,看不出一丝显摆的迹象——它真是沉得住气。
后来的后来,有那么一天,我的眼光,不经意滑过路旁的紫薇,立即顿住了,它的花开,真是不得了的事,端的就是云锦落下来。
不是一朵一朵地开,而是一树一树地
开。
哗啦哗啦,紫的,白的,红的,蓝的……颜料桶被打翻了,一径泼洒下来。
每瓣花,都镶了蕾丝一般的,打着好看的褶子。
瓣瓣亲密地挤在一起,朵朵亲密地挤在一起,于是你看到的,永远是大团大团的艳。
惊艳——它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一只大蜘蛛在花间做网。
蜘蛛真会找地方。
大太阳下,蜘蛛织的那张网上,紫薇花的影子在轻轻摇晃。
很自然地,我想到那堵高高的围墙,它与我的少年时光,密不可分。
围墙内,是花草的栽培之地,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紫薇最多。
乡下人把那地方,称作苗圃。
苗圃有专人把守。
把守它的是个面相挺凶的男人,他总是牵着一只大狼狗,在他的领地里,来回巡视,寻常人进不去。
花却不愿受束缚,它从围墙内探出头来,逗引着过往的行人。
尤其是紫薇盛开的时节,远远就能瞥见一片一片红色的云彩,在那里飘荡,苗圃成瑶池仙境。
我上学放学,都要路过,每次都会在那里驻足停留许久。
那时,我尚不知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紫薇,乡下人唤它痒痒树的。
因它枝干滑溜,轻轻一触,满树花枝乱颤,似怕痒的小女儿,你挠她痒痒,她咯咯笑着躲藏。
终于有一天,我和同桌女生,逃了课,躲过守园的男人,翻过围墙去。
围墙上的玻璃,把我们的手臂划伤,那是顾不得的。
云锦一样的花,很快让我们忘记了伤痛。
我
们并排坐在一棵花树下,看蜘蛛织网,看花的影子,在彼此的脸上跳舞。
围墙外,有人声渐渐近了,渐渐远了。
蜘蛛的那张大网,被我们捣毁,它又重新织起。
守园的男人,一直呆在大门口他的小木屋里,收音机里唱着我们不懂的京剧,铿铿锵锵。
那只爱吠的大狼狗,整个下午,却一声未吠。
我们一直呆到日暮才走,还是翻围墙。
守园的男人,未出现。
让我们害怕的大狼狗,未出现。
我们很顺利地,偷得两枝开好的紫薇花。
那时只道寻常,一树花开,两个年少的人。
可是经年后,我却沉在其中,欲罢不能,恨不能坐了时光的车,再回过去看一看。
都记得都记得的,青砖的围墙,里面长着数棵紫薇树。
大门口有守园男人的小木屋,还有他的大狼狗。
男人不是想像的那么凶,在我们翻越围墙后的某天,我路过,大狼狗冲我叫,他喝住大狼狗,安慰我,小姑娘不要怕。
当年的那个苗圃,早已不在了。
当年守园的那个男人,后来去了省城。
谁知道他竟是个书法家呢。
我听人说起时,微微笑起来,眼前晃过一树一树的紫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