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欲行禅与祖师西来.docx
《在欲行禅与祖师西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欲行禅与祖师西来.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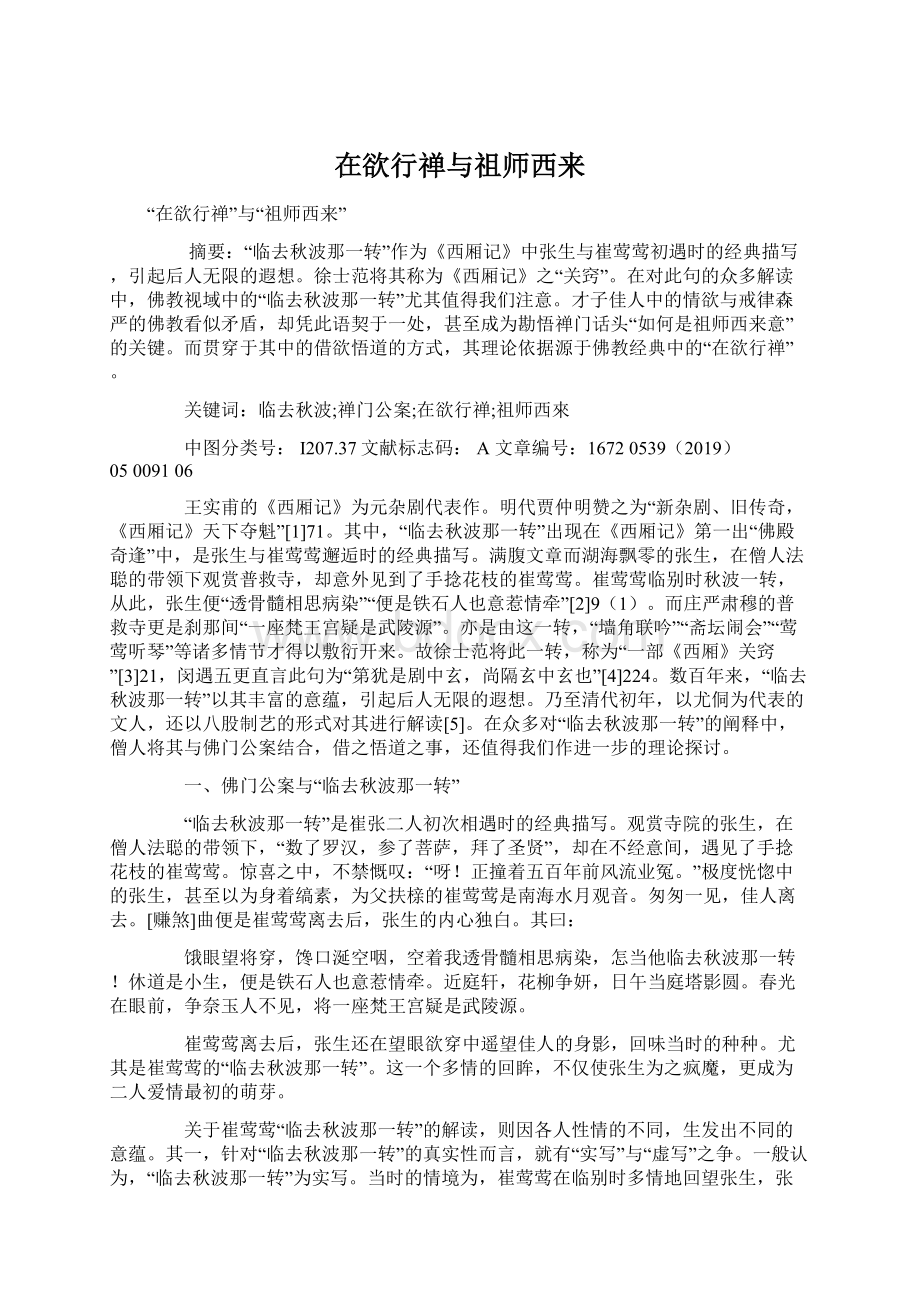
在欲行禅与祖师西来
“在欲行禅”与“祖师西来”
摘要:
“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初遇时的经典描写,引起后人无限的遐想。
徐士范将其称为《西厢记》之“关窍”。
在对此句的众多解读中,佛教视域中的“临去秋波那一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才子佳人中的情欲与戒律森严的佛教看似矛盾,却凭此语契于一处,甚至成为勘悟禅门话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关键。
而贯穿于其中的借欲悟道的方式,其理论依据源于佛教经典中的“在欲行禅”。
关键词:
临去秋波;禅门公案;在欲行禅;祖师西來
中图分类号:
I207.37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2 0539(2019)05 0091 06
王实甫的《西厢记》为元杂剧代表作。
明代贾仲明赞之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1]71。
其中,“临去秋波那一转”出现在《西厢记》第一出“佛殿奇逢”中,是张生与崔莺莺邂逅时的经典描写。
满腹文章而湖海飘零的张生,在僧人法聪的带领下观赏普救寺,却意外见到了手捻花枝的崔莺莺。
崔莺莺临别时秋波一转,从此,张生便“透骨髓相思病染”“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2]9
(1)。
而庄严肃穆的普救寺更是刹那间“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
亦是由这一转,“墙角联吟”“斋坛闹会”“莺莺听琴”等诸多情节才得以敷衍开来。
故徐士范将此一转,称为“一部《西厢》关窍”[3]21,闵遇五更直言此句为“第犹是剧中玄,尚隔玄中玄也”[4]224。
数百年来,“临去秋波那一转”以其丰富的意蕴,引起后人无限的遐想。
乃至清代初年,以尤侗为代表的文人,还以八股制艺的形式对其进行解读[5]。
在众多对“临去秋波那一转”的阐释中,僧人将其与佛门公案结合,借之悟道之事,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一、佛门公案与“临去秋波那一转”
“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崔张二人初次相遇时的经典描写。
观赏寺院的张生,在僧人法聪的带领下,“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却在不经意间,遇见了手捻花枝的崔莺莺。
惊喜之中,不禁慨叹:
“呀!
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极度恍惚中的张生,甚至以为身着缟素,为父扶榇的崔莺莺是南海水月观音。
匆匆一见,佳人离去。
[赚煞]曲便是崔莺莺离去后,张生的内心独白。
其曰:
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
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
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
崔莺莺离去后,张生还在望眼欲穿中遥望佳人的身影,回味当时的种种。
尤其是崔莺莺的“临去秋波那一转”。
这一个多情的回眸,不仅使张生为之疯魔,更成为二人爱情最初的萌芽。
关于崔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的解读,则因各人性情的不同,生发出不同的意蕴。
其一,针对“临去秋波那一转”的真实性而言,就有“实写”与“虚写”之争。
一般认为,“临去秋波那一转”为实写。
当时的情境为,崔莺莺在临别时多情地回望张生,张生便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情谊,于是深陷爱河不能自拔。
这种观点以毛西河为代表,其曰:
“于伫望勿及处又重提‘临去’一语,于意为回复,于文为照应也。
”[6]20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为虚写。
如金圣叹认为,崔莺莺为相国之女,其言行必有礼教约束,故“临去秋波那一转”必定是张生意乱情迷时的幻想。
其曰:
“妙眼如转,实未转也。
在张生必争云‘转’,在我必为双文争曰‘不曾转’也。
忤奴乃欲效双文转。
”[7]70其实,“临去秋波那一转”不论是虚写还是实写,皆持之有故,有其内在合理性。
其二,清代初年,以尤侗、黄周星等为代表的文人,还以八股制艺的形式对“临去秋波那一转”进行解读。
其中,尤侗更以绝妙的文笔,得到顺治皇帝的赏识。
这些八股制艺的文章使“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意蕴更为丰富。
如尤侗认为,秋波一转即为情转。
其曰:
“盖秋波非能转,情转之也。
然则双文虽去,其犹有未去者存哉?
”[4]666黄周星亦美誉之,曰:
“所可知者,惟是临去之一瞬耳,则非临去,不足见一转之妙。
”[4]668简言之,这些讨论意味着,“临去秋波那一转”在随着《西厢记》的不断传播中,逐渐生发出脱离原始文本的意涵。
而在这些丰富多彩的解读中,其还与佛教产生交集,牵扯出一段佛门公案。
《西厢记》在传播中逐渐与佛教产生交集,这具体表现为,佛教寺院中出现崔莺莺的画像、佛教僧人喜欢观看《西厢记》的戏曲表演,以及佛教僧人将《西厢记》视为修行的重要辅助。
现逐一分析之。
佛教寺院出现崔莺莺的画像并非孤例。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蒲东普救寺的僧舍中有崔莺莺的画像,其曰:
余丁卯春三月,衔命陕右,道出于蒲东普救之僧舍,所谓西厢者,有唐人崔氏女遗照在焉。
[4]375
祝允明《怀星堂集》亦载,疁城僧院有崔莺莺的画像。
《怀星堂集》还对画像作出相关评论。
其曰:
崔娘莺莺真像,乃旧传本,非宋即元人名手之所摹也。
余向者都下曾从一见之,继于疁城僧院中见一本,大略相类。
妖妍宛约,故犹动人,第似微伤肥耳。
[4]401
以上记载表明,至少在元代山西与明代上海的两处佛教寺院中,有崔莺莺的画像。
我们不禁疑惑,戒律森严的佛门清净地,怎么会出现崔莺莺的画像。
然而,不仅如此,更有“善入戏场”的佛教僧人,喜欢亲自去戏场观看《西厢记》的戏曲表演。
并且该僧人还特意指出,《西厢记》剧中的佳境便是“临去秋波那一转”。
闵遇五《会真六幻序》载:
昔有老禅,笃爱斯剧。
人问佳境安在?
曰: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此老可谓善入戏场者矣,第犹是剧中玄,尚隔玄中玄也。
[4]224
若说闵遇五笔下的佛教僧人,还只是“笃爱斯剧”,那么,另有佛教僧人将“临去秋波那一转”视为其修行的重要辅助,则更显得玄妙非常。
张岱《快园好古》曰:
邱琼山过一寺,见四壁俱画《西厢》,曰:
“空门安得有此?
”僧曰:
“老僧从此悟禅。
”问:
“从何处悟?
”僧曰:
“老僧悟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8]49
此处,佛教僧人借“临去秋波那一转”而修行悟道之事,便成为佛门中一桩公案。
我们不免惊诧,事关男女情爱的短短几字,缘何成为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机缘。
相传,顺治皇帝曾以此事询问弘觉禅师,禅师不答,只道:
“不是山僧境界。
”[3]518可见其中确是玄妙非常。
要言之,《西厢记》与佛教产生的三处交集,都证明其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这其中,“临去秋波那一转”则是联结《西厢记》与佛教的关键。
二、“在欲行禅”与“临去秋波那一转”
“临去秋波那一转”事关男女情欲,却与佛教修行产生关联,成为佛教僧人借以悟道的契机。
将“临去秋波那一转”与佛教修行并提,似觉鹘突,其实有其合理之处,而这便不得不提及佛教经典中的“在欲行禅”。
在探讨“在欲行禅”与“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关联之前,我们须明白,将情欲视为佛教修行过程中的重要辅助,是受到清代世俗文人的深刻认同的。
如尤侗《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文,提出“盖一转者,情禅也”的观点。
其曰:
此一转也,以为情多耶?
吾惜其止此一转也。
以为情少耶?
吾又恨其余此一转也。
彼知为秋波一转,而不知吾之魂梦有与为千万转者。
吾即欲闭目不窥,其如一转之不可却何!
噫嘻!
招楚客于三年,似曾相识;倾汉宫于一顾,无可奈何。
有双文之秋波一转,宜小生之眼花缭乱也哉!
抑老僧四壁画西厢,而悟禅恰在个中。
盖一转者,情禅也,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
[4]667
尤侗认为,情之为物,玄妙非常,若修行者可以勘悟此种空相,必对其修行大有裨益。
与其同一时期的黄周星更认为,佛教僧人借“临去秋波那一转”而修行,最终效果可以超越阅读千函经藏。
故其于《秋波六艺》一文,曰:
莺乎?
秋波乎?
吾何福以当之?
抑此语本才士之言情耳,而禅宗且以之悟道。
空之与色,一耶二耶?
若然,则罄大藏之千函,固不如绘西厢之四壁。
[4]668
其中,黄周星提出“空之与色,一耶二耶”的疑问,并且,黄周星还认为,若能正确看待“空”与“色”二者之间的关系,便会有极大的收获。
对此,潘书馨持相同的意见,其曰:
“是此临去秋波那一转也,其功宏,其效大,可以悟道,可以参禅也,宁区区情焉云耳哉?
”[4]748尤侗、黄周星、潘书馨等人的观点,均显示出清代世俗文人对僧人借“临去秋波那一转”悟道的深刻认同。
但若要论及蕴含于其中的深刻理论依据,则未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其实,“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佛教修行的辅助,其合理性源于佛教经典中的“在欲行禅”。
“在欲行禅”这一理论命题见于《维摩诘所说经》,其曰:
示受于五欲,亦复现行禅,令魔心愦乱,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
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
[9]862中
“示受于五欲”中的“五欲”分別指财欲、色欲、名欲、饮食欲与睡眠欲。
佛教认为,这五种欲望为世人带了无量的痛苦。
如《大智度论》载曰:
“五欲增诤,如鸟竞肉。
五欲烧人,如逆风执炬。
五欲害人,如践恶蛇。
五欲无实,如梦所得。
五欲不久,如假借须臾。
世人愚惑,贪着五欲,至此不舍,为之后世受无量苦”[10]397上。
然而,与此同时,佛教亦认为,借助世人所执之物,可以引导其开悟。
《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中,便以五欲中的色欲为例,曰:
“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
”可见,在“在欲行禅”的理论规定中,即便是淫女,亦有可能成为悟道的重要机缘。
可以说,佛教对色欲始终保持着谨慎而理智的态度。
一方面,其认识到色欲对世人的危害。
另一方面,又认识到色欲在修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以马鸣著、昙无谶译的《佛所行赞》为例分析之。
《佛所行赞》叙述了释迦牟尼一生的事迹。
其中涉及的色欲描写共有两处。
一处在释迦牟尼出家前,释迦牟尼之父净饭王为防止其遁入空门,而以情色诱之。
另一处在释迦牟尼出家后于苦行林修行之时,魔王波旬率领魔女,企图扰乱其修行,其中具体描述如下:
贤妃美容貌,窈窕淑妙姿,环艳若天后,同处日夜欢。
(《处宫品》)[11]406下
或有执手足,或便摩其身,或复对言笑,或现忧戚容,视以悦太子,令生爱乐心。
(《离欲品》)[11]408中
歌舞或言笑,扬眉露白齿,美目相眄睐,轻衣见素身,妖摇而徐步,诈亲渐习近。
(《离欲品》)[11]408下
魔王有三女,美貌善仪容,种种惑人术,天女中第一:
第一名欲染,次名能悦人,三名可爱乐。
(《破魔品》)[11]441上
上述文献中,《处宫品》描写净饭王为释迦牟尼迎娶了名门淑女耶输陀罗。
耶输陀罗不仅美貌若天后,而且其与释迦牟尼婚后还恩爱非常。
《离欲品》的两则文献材料则叙述释迦牟尼出城游玩时,净饭王命人将其引至一座光耀夺目的园林。
园林中众女逢迎,竞相献媚。
“或有执手足,或便摩其身”“妖摇而徐步,诈亲渐习近”等句更是直白露骨。
《破魔品》讲述魔王波旬率领有惑人之术的魔女,欲打乱释迦牟尼的修行。
总之,这些艳丽多情的叙述,可谓极尽刻画之能事。
然而,尽管情色的诱惑重重,释迦牟尼却不仅没有沉溺其中,反而由此认识到色欲乃是空相。
其曰:
不薄妙境界,亦知世人乐,俱见无常相,故生患累心。
若此法常存,无老病死苦,我亦应受乐,终无厌离心。
若令诸女色,至竟无衰变,爱欲虽为过,犹可留人情。
人有老病死,彼应自不乐,何况于他人,而生染着心?
悲常无欲境,自身俱亦然,而生爱乐心,此则同禽兽。
汝所引诸仙,习着五欲者,彼即可厌患,习欲故磨灭。
又称彼圣王,乐着五欲境,亦复同磨灭,当知彼非胜。
善言假方便,随顺习近者,习则真染着,何名为方便。
[11]409上、中
释迦牟尼认为,情色带来的欢乐转瞬即逝,生与死的问题却迫在眉睫。
众生沉溺于欲海的幻相中不能自拔,自己又怎能安心享乐?
由此,释迦牟尼从一己的悲欢中走出,以悲悯的情怀怜悯众生。
尤其是在经过幻化而来的沙门点拨后,释迦牟尼便下定决心向净饭王提出出家的请求。
由《维摩诘所说经》可知,情色的诱惑不仅是修行者悟道的重要契机,而且还是修行者修行过程中的重要考验。
魔王波旬带来的诱惑表明,一旦苦行林中的释迦牟尼被其诱惑,那么,所有的修行便会付之一炬。
可以说,正是释迦牟尼在面对诱惑时,以坚定的意志对待之,才得以保证其最终修成正果。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杨歧派法眼禅师曰:
“红粉佳人,风流公子。
一一为汝诸人发上上机,开正法眼”[12]372-373。
可见,《西厢记》作为才子佳人题材的作品,出现在佛教修行中,本就有本可依。
既然“在欲行禅”的理论命题表明,佛教僧人借“临去秋波那一转”具有合理性,那么,其具体的表现内容是什么呢?
一者,《西厢记》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一部《西厢记》的“关窍”,其出现必定是以《西厢记》的整体情节为基础的。
《西厢记》不仅有以“普救寺”“法本”“捻花”“业冤”等为代表的佛教元素所营造出的浓厚的佛教氛围,而且还有诸多情节暗合佛理。
如《西厢记》之初,作者便借老夫人之口,点明生死之机。
其曰:
“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行因病告殂。
”这便为整部作品笼罩上一层死亡的阴影。
我们不仅慨叹,即便是官拜相国的崔父,亦不能摆脱生死轮回,更何况是两个势单力薄的小儿女!
这不就是生命的无常么!
二者,“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出现,在佛教视域中并非偶然,而实为业冤所致。
崔张二人,一个是闺阁千金,一个是落魄书生。
二人今生本无交集,却又因缘际会,相遇于佛寺之中,生出一段旷古情事。
张生初遇崔莺莺,便情不自禁道:
“呀!
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何为“业冤”?
二人相遇便是业冤。
对此,潘廷章评曰:
“正在参菩萨、拜圣贤之际,一举头转眼间,忽现出风流业冤来。
此正色空相禅之介,为一部《西厢》起头。
词意接而不接,情事联而不联,陡然若逢宿债,恍然若睹前因。
此无明种子立地成魔,一时犯手,便不知何缘了却。
不是一刀两断,终无省头日子。
故直至《草桥》而后觉也。
‘风流孽冤’四字,并说尤妙,便可参破多少因缘幻妄诸义。
”[3]12佛教认为,众生自无始旷劫以来,受無明所惑,不明白事物的本质为空性。
由此生出贪嗔痴,造业受报,无解脱之时。
其中,若不是“一刀两断,终无省头日子”便暗指借助佛法之力,摆脱生死轮回。
试想,崔张二人自从相遇,便历经许多挫折。
老夫人从中作梗,更是让二人长亭送别,泪染霜林。
然而,即便是张生及第,二人有情人成了眷属,就真的迎来了大团圆的结局么?
不然,二人依旧受业力驱使,流转于轮回之中。
僧人以之悟道,定是认识到情色之欲本为空,而以崔张为代表的众生,亦不过是受业力驱使的木偶罢了。
总而言之,在“在欲行禅”为理论依据的前提下,佛教僧人借助“临去秋波那一转”而悟道,便不再显得突兀。
僧人以此为依据,参之于《西厢记》的诸多情节,以勘悟世界本来面目,从而生起对众生的悲悯之心与修行佛法的不退转之心。
三、“祖师西来”与“临去秋波那一转”
佛教视域中,“临去秋波那一转”还与以“祖师西来”为核心的佛教禅宗话头联系在一起。
“话头”常见于佛教禅宗,多以问句为触发点,以引起参学者的思考,从而帮助参学者达到开悟之境。
在以“祖师西来”为核心的话头中,“祖师”指东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
此话头借询问菩提达摩来中土的原因,以辅助修行者修行。
可以说,如何勘悟这一话头,是事关禅门修行的大事。
那么,“临去秋波那一转”是怎样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呢?
杨绪容《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中,附记《语录》一则,其曰:
渚山一日在普救上堂,学者进曰:
“如何是西来意?
”师曰:
“随喜到上方佛殿。
”复进曰:
“如何是西归意?
”师曰:
“千种相思对谁说。
”又进曰:
“如何是西来复西归意?
”师曰:
“临去秋波那一转。
”使当日面壁老僧觌覿面受偈,便当撇下蒲团矣。
[3]518
参学者提出三个问题,分别是“如何是西来意?
”“如何是西归意?
”“如何是西来复西归意?
”禅师听闻以后,以《西厢记》中的三个语典回答之。
即“随喜到上方佛殿”“千种相思对谁说”“临去秋波那一转”。
既然其中的问答均以达摩祖师西来为核心,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菩提达摩作一个必要的了解。
关于菩提达摩,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释道宣《续高僧传》等著作皆有涉及。
其中,又以普济《五灯会元》中的记载最为翔实。
此处,试以《五灯会元》为例,分析菩提达摩西来的具体情况。
《五灯会元》载曰:
祖乃告尊者曰:
“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
愿垂开示。
”者曰:
“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
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设大法药,直接上根。
慎勿速行,衰于日下。
”祖又曰:
“彼有大士,堪为法器否?
千载之下有留难否?
”者曰:
“汝所化之方,获菩提者不可胜数。
吾灭后六十余年,彼国有难,水中文布,自善降之。
”[13]38
般若多罗曾经叮嘱菩提达摩在其灭度六十七年后,前往震旦(中国)弘扬佛法。
于是,菩提达摩听从师命,于梁普通七年,前来中国。
当时,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
此后,菩提达摩又受到梁武帝的接待。
但无奈二人因缘未契,菩提达摩便索性渡江北上
(2)。
并于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寓止于嵩山少林。
后来,菩提达摩意欲离开,便将法印传于慧可,并留下一偈,其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祖又曰:
“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
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
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
我尝自出而试之,置石石裂。
缘吾本离南印来此中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踰海越漠,为法求人。
际会未谐,如愚若讷。
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
”言已,乃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
[13]45
留下此偈后,菩提达摩于魏文帝大统二年离世,葬于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
然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三年以后,魏宋云自西域返回中土时,于葱岭一带见到了已经“圆寂”的菩提达摩。
宋云见其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便问其何往,菩提达摩以“西天去”[13]46回答之。
宋云回中土后,具陈其所见。
于是菩提达摩门人闻后起圹,只见棺中无人,仅存一履。
这便是菩提达摩西来与西去的全过程。
至此,菩提达摩西来西去的线索便清晰起来。
关于其西来,般若多罗特意交待,须在其灭度后六十七年来中国,并言:
“彼国有难。
”达摩临别前,则自言:
“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
”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总之就是因缘际会,传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关于其西去,亦是时机成熟。
菩提达摩将法印传于慧可时,已经预料到中国禅宗会有“一花开五叶”的盛况。
可以说,菩提达摩本为传法而来,法既已传,则功成身退自在情理之中。
那么,菩提达摩的西来与西去,是如何与《西厢记》联系在一起的呢?
现分别以“随喜至上方佛殿”“千种相思对谁说”“临去秋波那一转”等三个回答为核心,进行分析:
第一,以“随喜至上方佛殿”回答“如何是西来意”。
“随喜至上方佛殿”出自“佛殿奇逢”。
其中,[村里迓鼓]曲云:
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
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
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
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
〔莺莺引红娘拈花枝上云〕红娘,俺去佛殿上耍去来。
〔末做见科〕呀!
正撞着五百年前业冤。
张生自西洛而来,“闻上刹清闲幽雅,一来瞻仰佛像,二来拜谒长老”。
张生来到普救寺,恰好长老外出赴斋,不在寺中,于是便在僧人法聪的带领下,游览普救寺,之后种种因缘便由此生发出来。
这一情境,着实与菩提达摩西来有相似之处。
菩提达摩“西来”,张生“西洛”而来,都暗合一个“西”字。
菩提达摩之来,是观中国有“大乘气象”,而张生则是“闻上刹清幽”,此又一处暗合。
对此,潘廷章曰:
“《西厢》何意?
意在西来也。
以佛殿始,以旅梦终,于空生即于空灭,全为西来示意也。
生自西来,灭亦从西去,来前去后,乌容一字,而其中所构诸缘,俱在西厢”[4]324,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以“千种相思对谁说”参解“如何是西归意”。
“千种相思对谁说”见于“草桥惊梦”,有人认为,王实甫《西厢记》至此终结。
其中,[鸳鸯煞]曲有:
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呜咽。
斜月残灯,半明不灭。
畅道是旧恨连绵,新愁郁结;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泻。
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
崔张二人于长亭分別后,张生便星夜兼程。
行至草桥,欲暂宿一宿。
张生于旅途中,对莺莺百般思念。
不料深夜便见到连夜赶来与之相会的崔莺莺。
张生自然万般欢喜,可醒来以后,才知是空梦一场。
[鸳鸯煞]曲,便是张生梦醒后的情境。
柳丝如情思万缕,水声似离人呜咽。
斜月残灯,各种情绪澎湃于襟怀。
“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的意思是,心中之情非纸笔以记,更无从说与他人。
一句“千种相思对谁说”,确实较为传神的体现出菩提达摩西去时的心境。
菩提达摩在中国所开创的禅宗,本就不注重语言文字对思想的阐释性。
并且,在菩提达摩的来去之间,贯穿于其中的是对众生的深厚情谊。
第三,以“临去秋波那一转”阐释“如何是西来复西归意”。
世人难免疑问,既然菩提达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为何要离去?
其实,菩提达摩的来去自有定数,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同样,崔张二人的相遇亦是“业冤”所致。
再者,菩提达摩“西去”,却非真的离去。
在其留下的佛偈中,已经预料到中国禅宗在中国的发展盛况。
世人执着其色身的离去,却没有想到其法身尚在,其在中国留下的法脉尚在。
与此相对应的是,崔莺莺虽然已经离开佛殿,却留下了万种情愫付予张生。
回想崔张二人初次见面,崔莺莺手捻花枝的情态,倒真与佛祖传授禅宗法门时,手捻金色婆罗花的场景有几分相似。
以上便是对以“临去秋波那一转”为代表的《西厢记》典故,参解以“祖师西来”为核心的禅宗话头的全部解释。
这些解释尚不能完全领会佛教借此悟道的深刻义理,只是暂且将其作为一种理解罢了。
还期待后来者,可以给出更为圆满的答案。
综上所述,佛教视域下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有着区别于传统认知的意义。
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因为佛教的介入,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哲理性意蕴。
注释:
(1)本文凡引用《西厢记》原文的,均出自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帝问曰:
‘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
’祖曰:
‘并无功德。
’帝曰:
‘何以无功德?
’祖曰:
‘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帝曰:
‘如何是真功德?
’祖曰:
‘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又问:
‘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祖曰:
‘廓然无圣。
’帝曰:
‘对朕者谁?
’祖曰:
‘不识。
’帝不领悟。
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
”见普济、苏渊雷点校:
《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页。
参考文献:
[1]钟嗣成,贾仲明.新校录鬼簿正续编[M].浦汉明,校.成都:
巴蜀书社,1996.
[2]王实甫.西厢记[M].王季思,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杨绪容.王实甫《西厢记》汇评[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伏涤修.西厢记资料汇编[M].伏蒙蒙,辑校.合肥:
黄山书社,2012.
[5]王汉民.《西厢记》“临去秋波”的八股阐释[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
(1):
1-3.
[6]周锡山.《西厢记》注释汇评[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7]金圣叹.金圣叹评《西厢记》[M].陈德芳,校点.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8]张岱.快园道古[M].高学安,佘德余,标点.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9]中华大藏经·维摩诘所说经(汉文部分第15册)[M].鸠摩罗什,译.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0]中华大藏经·大智度论(汉文部分第25册)[M].鸠摩罗什,译.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1]中华大藏经·佛所行赞(汉文部分第50册)[M].昙无谶,译.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2]颐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M].萧萐父,吕有祥,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4.
[13]普济.五灯会元[M].苏渊雷,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4.
“IntheDesiretoCultivateZen”,and“BodhidharmaCameHerefrom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