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发生学初探.docx
《文学经典发生学初探.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经典发生学初探.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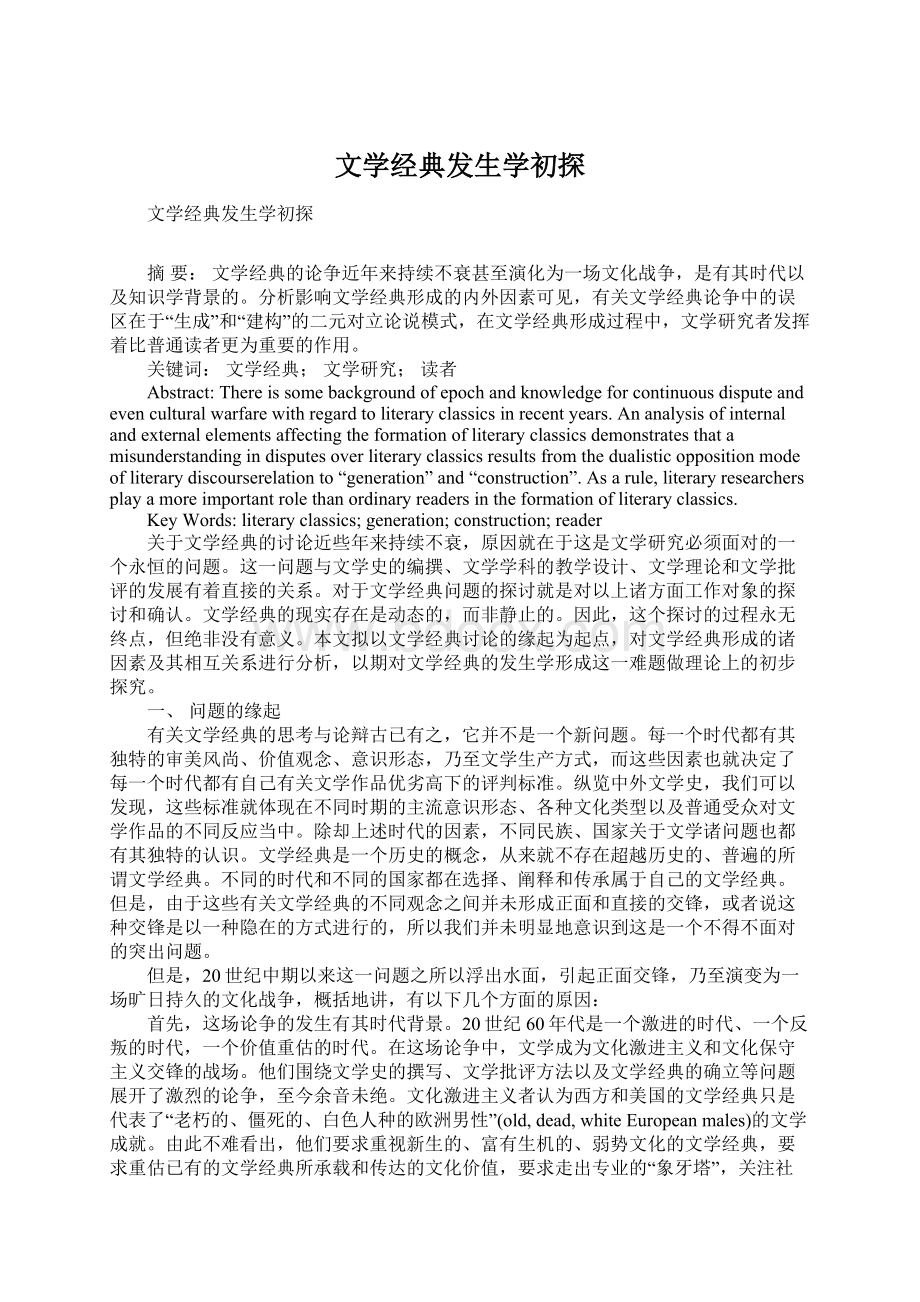
文学经典发生学初探
文学经典发生学初探
摘要:
文学经典的论争近年来持续不衰甚至演化为一场文化战争,是有其时代以及知识学背景的。
分析影响文学经典形成的内外因素可见,有关文学经典论争中的误区在于“生成”和“建构”的二元对立论说模式,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文学研究者发挥着比普通读者更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文学经典;文学研究;读者
Abstract:
Thereissomebackgroundofepochandknowledgeforcontinuousdisputeandevenculturalwarfarewithregardtoliteraryclassicsinrecentyears.Ananalysisofinternalandexternalelementsaffectingtheformationofliteraryclassicsdemonstratesthatamisunderstandingindisputesoverliteraryclassicsresultsfromthedualisticoppositionmodeofliterarydiscourserelationto“generation”and“construction”.Asarule,literaryresearchersplayamoreimportantrolethanordinaryreadersintheformationofliteraryclassics.
KeyWords:
literaryclassics;generation;construction;reader
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近些年来持续不衰,原因就在于这是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这一问题与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学科的教学设计、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于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就是对以上诸方面工作对象的探讨和确认。
文学经典的现实存在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
因此,这个探讨的过程永无终点,但绝非没有意义。
本文拟以文学经典讨论的缘起为起点,对文学经典形成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文学经典的发生学形成这一难题做理论上的初步探究。
一、问题的缘起
有关文学经典的思考与论辩古已有之,它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审美风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乃至文学生产方式,而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有关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评判标准。
纵览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标准就体现在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文化类型以及普通受众对文学作品的不同反应当中。
除却上述时代的因素,不同民族、国家关于文学诸问题也都有其独特的认识。
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来就不存在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所谓文学经典。
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都在选择、阐释和传承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
但是,由于这些有关文学经典的不同观念之间并未形成正面和直接的交锋,或者说这种交锋是以一种隐在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并未明显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
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问题之所以浮出水面,引起正面交锋,乃至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概括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场论争的发生有其时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一个反叛的时代,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
在这场论争中,文学成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交锋的战场。
他们围绕文学史的撰写、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文学经典的确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至今余音未绝。
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西方和美国的文学经典只是代表了“老朽的、僵死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男性”(old,dead,whiteEuropeanmales)的文学成就。
由此不难看出,他们要求重视新生的、富有生机的、弱势文化的文学经典,要求重估已有的文学经典所承载和传达的文化价值,要求走出专业的“象牙塔”,关注社会民生问题。
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文学文本的限制,目光直逼文本遮盖之下的政治。
其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重估文学经典创造了客观条件。
随着“全球化”趋势突破经济领域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得到了极大地拓展,文化“他者”(otherness)的出现,使得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挑战,文化多元主义蓬勃发展,边缘、女性、殖民等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
在这种新的参照系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经典问题。
最后,包括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各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当代思想在立场、方法、思想形态等方面的改变,促进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彻底改变。
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语言学观念形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态的主要结构,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思想变化又促使学科结构发生着更为深刻的转变和改造。
这就造成了以新批评为主要代表注重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和语言特色的传统批评方法日益边缘化,而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异军突起,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
二、生成抑或建构:
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考
关于文学经典之所以形成的论争焦点集中在,文学经典究竟是自然生成的(thegiven),还是人为建构的(themade)。
那么,生成与建构难道真的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吗?
我们不妨从对文学经典这一概念的梳理做起,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已有不少文章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经典”及其英语的对应表达“canon”和“classic”的含义。
[注:
在英语中,与汉语“经典”相对应的是classic和canon。
Classic源于拉丁文classius,用以区分纳税的等级。
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classic来区分作家的优劣高下,到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采用,后来由于与“古代”相联系,特指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
Canon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芦苇”或者“棍子”,引申为度量长度的工具,进一步引申为“法度”、“规则”等义。
后来多用于《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宗教文本,有“神圣、正统”之义。
18世纪之后,这一概念方超越了宗教领域,被用于文学等其他文化领域。
而在汉语中,所谓“经”就意味着“三极彝训,其书言经。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
而“典”本义则是“常道、法则”,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语境下,所谓“文学经典”就是指那些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
那么,影响“文学经典”构成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作品、世界和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恰恰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即作者没有直接的关联。
原因在于,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具有被“追认“的特点。
正如艾略特所指出的,“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
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
”[1]这种“追认”的特点不惟是作家个人的意识,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文学经典的“有机构件”,变成了经典文本的基本要素;文学经典是被创造出来,不仅仅是作家的创造,更是历史和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品、世界和读者这三个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
内部因素指作品本身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外部因素就是指世界和读者,它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
[注:
这一划分参考了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文学世界的内外因素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单单从任何一个方面分析都是片面的。
内部因素的先验结构、外部因素的社会历史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因素。
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是主生成说者立论的出发点,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
他们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写出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共通心理,因而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和想象,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是超越历史、民族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是一种专属于人、有别于动物的情感和心理。
而主建构说者认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其谬误在于假定文学经典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绝对永恒的价值。
在建构论者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文学经典。
文学以及文学经典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该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待。
历史本身是变动不居的,甚至历史本身都是被建构起来,何来“超历史”的文学经典呢?
他们认为,文学经典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操控下被建构起来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不同的文学作品便会被推上“经典”的神坛。
其实,建构说者在批评生成说者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的同时,自己也迈入了同样的认识误区,他们把对“否定”、“解构”和“差异”本质化、绝对化了。
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些像《哈姆雷特》、《红楼梦》那样的文学作品,他们是虽经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刷而永不褪色的文学经典。
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承载了能够穿越时空的人类普遍的情感和普适的价值。
经典作品在本身的审美价值之外,一般还蕴含着广阔的可阐释空间。
经典之作往往兼具“深、约、宏、美”的特点,其思想之深邃、描述之含蓄、画卷之宏阔、形式之精美相得益彰。
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派苍凉沉郁的气象,道尽了生命存在因不能突破时空局限而产生的根本的孤独之感。
经典作品正是由于自身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才变得“经久耐说”,不管是赞是弹,人们总能从作品当中获得阐述自己观点的灵感和材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面对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
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在激发读者想象和情感的同时,也给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提供了用武之地。
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操控,也正是建立在文学作品自身的经典性之上的。
原因在于,“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为它本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但是艺术并不需要意识到这些目的,而且它愈是不关心这些目的,就愈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根据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艺术的功能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3]。
或许,将艾略特的这段论述改成“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被它以外的目的所利用”,可以更准确地表述艺术作品本身的这种远离现实功利的“无目的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在“旗手”领导下,“政治挂帅”以“三结合”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所谓“样板戏”肯定是行之不远的。
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发生变迁之后,这些“经典”很快被推下了神坛。
尽管这些“经典”在今天并未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但是人们看重的恰恰是其审美的价值,而非它所灌输的“革命思想”。
由此可见,“建构”是建立在“生成”的基础之上的;外部的操控总须以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阐释空间为前提。
如此而论,并不是要断然否认意识形态、文化权力、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外部因素对于经典形成的影响。
首先,必须肯定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是决定性。
自汉以降,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奉为圭臬的《诗经》,它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神圣性不容亵渎、权威性不容置疑。
但是到了“五四”时期,《诗经》连同其他儒家经典的命运却发生了倒转。
《诗经》逐渐恢复了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人们开始用对待文化、文学的方法来批评、研究这部饱含喜怒哀乐、有声有色的“诗歌总集”了。
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经典地位从古到今始终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先秦两汉时期《诗经》是“经”的经典,近代以来《诗经》是文学经典,这个区别是明确的,古人从来没有过“文学式”的诗经观。
及至“文化大革命”,《诗经》连同其他绝大部分的古今中外文学经典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非禁即毁。
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历史上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所谓“文学经典”分明处在意识形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肆意摆布之下,何来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
进而,我们就会认为,文学经典就是被建构而非生成的。
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之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
尽管时而被奉若神明、时而被弃若敝履,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些文学经典还是流传至今,甚至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以各种更为新颖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
由此可见,建构说者看似在强调还原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语境,其实他们的缺陷恰恰在于历史眼光的欠缺,只强调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忽略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次,在强调意识形态对文学经典的形成所发挥的建构作用的同时,建构说者忽略了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乌托邦因素。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从内、外两个方面,发挥着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变奏作用。
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换言之,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现的。
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就是肯定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的依据。
外在于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将文学作品作为其发挥作用的一个途径,并通过这一途径向人们灌输认同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传声筒,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文学史经典及其批评诚然无法脱离其处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制约,但它作为“文学的”而具有自己的规则和语汇及其内部法则,正如布鲁姆所说:
“一首诗无法单独存在,但审美领域里却存在一些固定的价值。
这些不可全然忽视的价值经由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建立起来。
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
[4]
但是,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并不是为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提供一个手段。
文学艺术是人们寻求情感寄托、心灵慰藉和精神超越、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所分裂的人性的乌托邦,它寄予了人们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对于现实苦难的反抗。
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间,乌托邦与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文学经典的生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任何各执一端的二元认识都会导致“生成”和“建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三、文学研究者和读者:
谁的经典
在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影响文学经典形成的因素还有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和普通读者的期待。
“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5]虽然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也是作为读者出现的,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普通的读者,绝不能把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的读者相提并论。
文学研究者由于其专业眼光和权威地位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文学研究者由于其专业素养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使一些原本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作品经由他们的发现、修订和阐释,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进而跻身经典之列。
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他们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不仅可以影响到某一部作品的命运,甚至对某一种文体的兴衰都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小说这一文体在明朝以前已经存在了逾千年之久,但是它的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以虚构、新奇为基本特点的小说,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环境下难登大雅之堂。
“小道可观”是对小说这一文体最具肯定性的评价了。
然而,首先由于文人对于小说文本的介入,使其文学价值得到了提升。
施耐庵、罗贯中首先从一个读者,但绝不是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早已流传在市井当中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进行了再创作,使其文学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为其经典化奠定了文本基础。
李贽、袁中郎、金圣叹的推崇则使小说的经典化得以最终完成。
李贽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苏东坡和李梦阳的作品相提并论,称其是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
袁中郎在《觞政》中将《水浒传》、《金瓶梅》列为文人雅士必读的“逸典”。
《水浒传》也被金圣叹列为“六才子书”。
这些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作用是普通读者所不能企及的。
另一方面,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
若非《水浒传》等小说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是不大会引起文学研究者关注的。
金庸的武侠小说几十年间在普通读者中间长盛不衰,引起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金庸及其小说在一些新编的文学史当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作品也被收进了文学教材,进入了“国民教育”系列。
但是,金庸的作品是否就是文学经典恐怕还要经受更长时间的历史检验。
通过这个事例,只是想说明普通读者对专业研究者的影响。
当然,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于文学经典认定的差异是不尽相同的。
世纪之交,在西方国家评选出的“百年文学经典”当中,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名列榜首。
但是,乔伊斯的这一作品并没有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如中国文学当中的《诗经》、《楚辞》等经典之作在今天同样也没有庞大的读者群。
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学经典的“精英化”和“专业化”。
这一过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经典存在的社会与群众基础,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它们作为经典的地位。
原因就在于,文学经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对于民族精神记忆的保存,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因为强调文学经典的动态特征而否定了经典的相对稳定性。
同时,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型,其中的因素多且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对文学经典“精英化”的应对,而绝非对于文学的反叛。
虽然说,作品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经过三方对话、商兑,并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的取得谈何容易。
[6]正是由于对三者中任何一方的强调,导致了关于经典的种种论证。
批评家的批评是文学作品赢得高贵的知识标签的基础,积极地讲,没有严格的批评就没有文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文学就永远是玩物,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是一门学科;消极地讲,文学批评为文学作品的树立起了可能本不属于它的外在表现,假设了各种通向文本的途径,只有借助那些观念、概念和范畴,人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所表达,否则的话根本不存在任何“文学交流”的可能性。
读者的阅读是文学作品的现实形态,作品只有进入阅读,形成读者在自己的生活世界基础上的“理解”和“阐释”,文学的“功能”才能体现出来,尽管这可能是一种主观的“功能”,但因为它是建立在整个经验世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东西,所以它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也是不能否认的。
需要强调的是,批评和阅读所形成的“文学经典”不是一种和经验科学一样的可验证、可预测的结果,它是在现实的社会结构,现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结果。
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理论学科的主要观点就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与传统观念不同,当代新的文学理论不会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在客观根源,他们讲这种科学性集中在文学作品的“外部”。
本文要指出的是,这里不存在一种内部和外部的辨证关系,因为这关涉到的实际上是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具体选择,但存在这一种非常具体的文学发生学的知识分析,对文学研究学科的整体理解将取决于这种知识分析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189-190.
[2]鲁迅.《绛洞花主》小引[M]∥鲁迅.鲁迅全集:
第7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19.
[3]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66.
[4]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5:
17.
[5]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M]∥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4.
[6]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2(5):
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