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关于文学思维论.docx
《第五章关于文学思维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五章关于文学思维论.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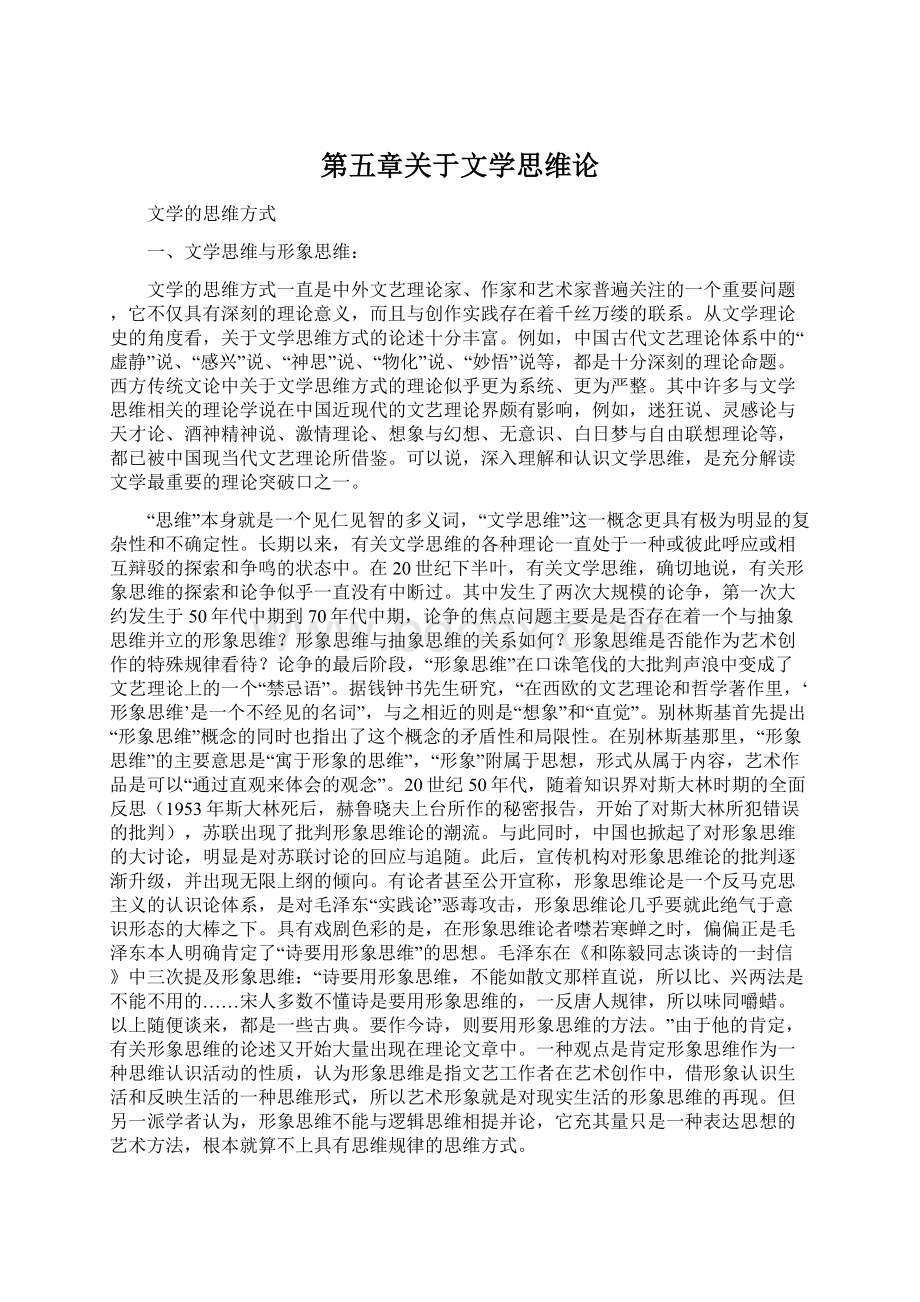
第五章关于文学思维论
文学的思维方式
一、文学思维与形象思维:
文学的思维方式一直是中外文艺理论家、作家和艺术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与创作实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文学理论史的角度看,关于文学思维方式的论述十分丰富。
例如,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中的“虚静”说、“感兴”说、“神思”说、“物化”说、“妙悟”说等,都是十分深刻的理论命题。
西方传统文论中关于文学思维方式的理论似乎更为系统、更为严整。
其中许多与文学思维相关的理论学说在中国近现代的文艺理论界颇有影响,例如,迷狂说、灵感论与天才论、酒神精神说、激情理论、想象与幻想、无意识、白日梦与自由联想理论等,都已被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所借鉴。
可以说,深入理解和认识文学思维,是充分解读文学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口之一。
“思维”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多义词,“文学思维”这一概念更具有极为明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有关文学思维的各种理论一直处于一种或彼此呼应或相互辩驳的探索和争鸣的状态中。
在20世纪下半叶,有关文学思维,确切地说,有关形象思维的探索和论争似乎一直没有中断过。
其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论争,第一次大约发生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论争的焦点问题主要是是否存在着一个与抽象思维并立的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如何?
形象思维是否能作为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看待?
论争的最后阶段,“形象思维”在口诛笔伐的大批判声浪中变成了文艺理论上的一个“禁忌语”。
据钱钟书先生研究,“在西欧的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里,‘形象思维’是一个不经见的名词”,与之相近的则是“想象”和“直觉”。
别林斯基首先提出“形象思维”概念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个概念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在别林斯基那里,“形象思维”的主要意思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形象”附属于思想,形式从属于内容,艺术作品是可以“通过直观来体会的观念”。
20世纪50年代,随着知识界对斯大林时期的全面反思(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所作的秘密报告,开始了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批判),苏联出现了批判形象思维论的潮流。
与此同时,中国也掀起了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明显是对苏联讨论的回应与追随。
此后,宣传机构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逐渐升级,并出现无限上纲的倾向。
有论者甚至公开宣称,形象思维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实践论”恶毒攻击,形象思维论几乎要就此绝气于意识形态的大棒之下。
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在形象思维论者噤若寒蝉之时,偏偏正是毛泽东本人明确肯定了“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思想。
毛泽东在《和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三次提及形象思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
”由于他的肯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又开始大量出现在理论文章中。
一种观点是肯定形象思维作为一种思维认识活动的性质,认为形象思维是指文艺工作者在艺术创作中,借形象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一种思维形式,所以艺术形象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形象思维的再现。
但另一派学者认为,形象思维不能与逻辑思维相提并论,它充其量只是一种表达思想的艺术方法,根本就算不上具有思维规律的思维方式。
20世纪80年代的论争,虽然基本观点并没有超出50年代,但是论争的积极意义和丰硕成果却是令人欣慰的。
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形象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规律得到了大多数文论家的肯定。
一般而言,人们普遍认为,与抽象思维相比,形象思维至少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一、形象思维始终不脱离活生生的感性材料,它总是与事物的感性形象同起伏、共始终,常以形象、典型和意境来显示事物的本质;二、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想象、联想和幻想具有突出的意义;三、形象思维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
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学思维是一种融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为一体的综合创新思维。
一般来讲,形象思维所特别致力的,是作品题材内容上的生动和丰满;抽象思维所特别致力的,是主题思想的深刻与鲜明。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它们同体异用,异能同功。
可以说,作家的创作过程既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又是抽象思维的过程。
许多研究思维与人脑关系的著述认为,作家、艺术家大多是些大脑“右半球”比较发达的人,即所谓“右半球人”,因为作家、艺术家主要以形象思维来从事创作活动,而人脑的右半球主管形象思维。
但自相矛盾的是,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家必定是语言天赋甚高的人,而主管人们的说话。
阅读、书写的,却偏偏是大脑的“左半球”。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是否同样也有充足的理由说,文学家是“左半球人”?
一般说来,大多数人的左脑对于语言性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强,右脑对于非语言性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强。
研究人员正是根据这种差别得出了“左脑在抽象思维方面占优势,而右脑则在形象思维方面占优势。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两侧大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而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而且是互相交织、互相补充和互相转化的,从而达到对客观世界最完美、最本质的认识。
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必要将文学家看出所谓的“右半球人”或“左半球人”。
二、中国古代的文学思维论
1、“虚静”与“神思”: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国学大师黄侃在其《文心雕龙札记》中有精彩的阐释:
“《庄子》之言曰:
‘唯道集虚。
’《老子》之言曰:
‘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尔则宰有者无,制实者虚,物之常理也。
文章之事,形态蕃变,条理纷纭,如令心无天游,适令万状相攘。
故为文之术,首在治心,迟速纵殊,而心未尝不静,大小或异,而气未尝不虚。
执璇机以运大象,处户牖而得天倪,惟虚与静之故也。
”“虚静”一词是道家哲学中的重要范畴,老庄以“虚静”解释支配万物的道,并将其奉为养身、处世和治国的法宝。
《老子》十六云: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其根。
归根曰静。
”
在儒家学说中,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谈论“虚静”,但《论语》中“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和“吾日三省吾身”等说法却能让人联想到“虚静”。
《荀子·解蔽》篇云:
“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
曰:
心。
心何以知?
曰:
虚壹而静。
”大儒言“治之要”,俨然道家之论,可见,“虚静”之说并非道家专利。
荀子将“虚、静、壹”视为认识事物时精神状态的三个方面,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比较普遍的影响。
法家也讲“虚静”,《韩非子·解老》篇有:
“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
”,不过这种“虚静”具有非常明确的功利目的——治人。
刘勰所说的“虚静”,其基本含义大抵可以说是一种有利于冷静思考的创作心理状态。
作家构思时,宁静专一,洗雪心境,除去杂念和主观偏见,即所谓“书瀹(yue)五藏,澡雪精神”。
朱熹在《清邃阁论诗》中对“虚静”进行了更好的解释:
“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
心理闹如何见得。
”相比之下,苏轼以诗论诗,说得更为清晰: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显然,苏轼所说的“空且静”,就是佛家的“澄空”和道家的“虚静”。
在苏轼看来,“无厌空且静”是创作美妙诗语的前提必要条件。
这无疑受到了道家“虚静”论的影响。
综合而言,道家“虚静”说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美学意义:
第一,道家“虚静”论强烈突出的是摆脱功利欲望,排除知性干扰,专注于对象的形式,对对象进行孤立的观照,要求主体心境的孔明澄澈,以达于“凝神”的境界。
《庄子·达生》有:
梓庆削木为鐻(ju),鐻成,见者惊犹鬼神。
鲁侯见而问焉,曰:
“子何术以为焉?
”对曰:
“臣,工人,何术之有!
虽然,有一焉:
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
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
当是时也,无公朝。
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
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与!
“鐻”是一种乐器,梓庆制造的鐻,巧夺天工,如有神助,令人惊奇。
虽然他自谦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但他成功的诀窍却非同一般:
做鐻之前,一连斋戒七日,逐渐达到了一种高度“忘我”的虚静状态,此时,世事的烦扰消失殆尽,也就能专心于技巧。
以人之“天性自然”合树之“自然天性”,从而由“虚静”状态进入创作状态,这就是梓庆为鐻的奥秘所在。
这里的关键词“静心”,是创作前所酝酿的一种有利于冷静观察和思考的创作心理状态,即“凝神”的状态。
“凝神”是“虚静”的突出特征之一,凝神之时,创作主体如同禅家入定,守一念而驭万念,以无欲而却众欲,进入了一种高度专注的状态。
《庄子·田子方》有“解衣般礡”的故事,可以说是对“凝神”和“虚静”的生动注解: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后至者,寖寖(qin)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
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礡,裸。
君曰:
“可矣,是真画者也。
”
这个后来的画者,神态自若,“寖寖然不趋”,行礼以后也不像其他人那样恭敬地站立一旁,而是径直回到了寓所,然后居然光着身子,禅家入定一般坐在那里,想着要画的东西。
“解衣般礡,裸”就是意念高度集中,忘掉一切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虚静的极致,历来为人称道。
宋代郭熙说:
“画史解衣般礡,此真得画家之法。
”
第二,古人还把“虚静”的心态与创作兴会、灵感的降临相联系,认为心灵的虚静孤寂状态是产生灵感最佳状态。
在《庄子》一书中,与“虚静”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概念是“心斋”和“坐忘”。
《庄子·人间世》有: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可见,心斋就是一种摒弃外界感性搅扰的“虚而待物”的“空虚”状态。
所谓“坐忘”,即《庄子·大宗师》中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显然,“坐忘”就是要忘掉形体躯壳的自我、人为化和世俗的自我,忘掉外在于人之本体的形骸、智巧、嗜欲的小我,而获得真正的健全的自我,获得与宇宙万物相通的大我,以达到一种通达万物,“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
魏晋时的嵇康在《释私论》中说:
“夫气静而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所欲;矜尚不存严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唐代皎然也说:
“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
”宋郭熙也有:
“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境界已熟,心手相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世人将就率意,触情草草便得。
”所有这些言论,既说明了虚静状态对创作的重要意义,也表明了创作灵感的降临与虚静的心态间的联系。
第三、与集中注意力、清除杂念欲念、忘知忘我以对对象进行孤立观照相适应的,是强调虚静与把握对象结构的关系。
《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已经包含着虚静对于掌握对象形式结构的作用。
庄子借庖丁之口说: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存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
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
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仿佛无心运刀,却能切中肯綮,这正是庄子一再强调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圣人境界。
这种游刃有余的境界得益于与虚静有关的“神遇”和从实践中得来的对事物结构的把握。
不具备“虚壹而静”的心理素质,没有对事物结构冷静透彻的掌握,任何技艺要达到这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都是不可能的。
从“虚静”说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涉及“艺术思维”的多数概念都与“虚静”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例如“神思”、“凝思”、“冥搜”、“苦吟”、“兴会”、“妙悟”等,在文学创作或文学鉴赏过程中,或以“虚静”为前提,或以“虚静”为助力,或以“虚静”为补充,或以“虚静”为契机,它们在文学思维的体系中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有“虚壹而静”的精神境界就不能进入“凝神静思”的创作状态;不经一番呕心沥血的“冥搜”或“苦吟”,通常就很难遇见“兴会”或“妙悟”的佳境。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细致探讨了文学思维的规律:
古人云: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
”神思之谓也。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其思理之致乎!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刘勰开宗明义,借助《庄子·让王》中“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名言,说明“神思”是一种不受身体局限的形象思维活动。
文学构思过程始终会有“珠玉之声”和“风云之色”相伴相随,“神思”这种“绘声绘色”品性正是艺术思维活动的重要特征,即始终不脱离具体的感性形象。
显而易见,刘勰所说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直接秉承了西晋陆机《文赋》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思想。
的确,文学思维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无往而不至的自由与随意。
更为可贵的是,《神思》篇还提出了“神与物游”的重要思想。
“神与物游”深刻地概括了艺术活动中创作主体(神)与创作客体(物)所达到的融合化一的重要特点。
可以说,就对文学思维和艺术构思活动的描述而言,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比刘勰的“神与物游”更为精辟的概括与总结。
2、“凝思”与“苦吟”:
“凝思”即“凝神静思”,是指在艺术构思中潜心的虚构与想象。
从文学思维的角度提出“凝思”概念的是陆机。
陆机在其《文赋》中对作家创作时聚精会神的运思过程有过精彩的描述: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
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龃龉(juyu)而不安。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这段话的大意是,进入谋篇阶段,开始处理意与辞的关系,按部就班,选择事义,思考词句,把握住有声有色的外物景象,力求给予艺术的表现。
这时,思绪纷繁,变幻莫测。
但只要尽心专意地思索琢磨,因宜适变,就可以把许多思绪组织成文,把天地万物概括进形象描绘之中。
我们注意到古人往往把“凝思”与“冥搜”相提并论,有时将其视为一谈,正缘于这两个概念具有一定的共生与互补的特征。
明谢榛《四溟诗话》说:
“陆士衡《文赋》:
‘其始也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此但写冥搜之状耳。
”清薛雪《一瓢诗话》也说: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陆士衡之言也。
欲求工到,必藉冥搜。
”从谢榛和薛雪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凝思”与“冥搜”在本质上是相近相通且能互释互补的“姊妹概念”。
“冥搜”概念中的这个“冥”字本身就隐含着“虚静”的玄机,一个“搜”字,生动活泼地表现出了文学思维中想象活动的具体性、主动性、自由性和创造性。
“冥搜”一语,较早见于东晋孙绰《游天台赋》:
“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
”李白《月中秋怀》有:
“分明画相似,爱此从冥搜。
”唐廖融《谢翁宏以诗百篇见示》:
“高奇一百篇,造化见工全。
积思游沧海,冥搜如洞天。
神珠迷象罔,端玉匪雕镌(juan)。
”清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
“诗人一字苦冥搜,论古应从象罔求。
不是临川王介甫,谁知暝色赴高楼。
”由此可见,“冥搜”与刘勰所说的“神思”是一个意义非常接近的概念。
二者所讨论的都主要是文学想象问题。
当然,从“神珠迷象罔”和“论古应从象罔求”中还隐含着另一层含义,即处心积虑的“冥搜”对于佳句好诗是无益的,这从道家“象罔”典故的原意不难看出。
《庄子·天地》有一则寓言:
黄帝游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
还归,遗其玄珠。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讫索之而不得也。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黄帝曰:
“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
这里的“玄珠”实际上就是庄子所谓的“道”,“知”即智慧的“智”,“离朱”以眼光锐利著称,“吃讫”以能言善辩闻名。
前三者找不到的“玄珠”,最后却被没有心的“象罔”找到了。
此事连黄帝也惊叹“异哉”。
处心积虑不如漫不经心,刻意相求不如无心相遇。
这是道家美学思想的显现。
从文学思维理论发展历程看,“冥搜”促成了“虚静”概念从“无为”向“有为”的转向。
“冥搜”和“虚静”虽同属于描述艺术想象活动的概念,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
“虚静”比较接近于写作准备阶段的常见心理状态,“冥搜”则更接近于进入写作状态后的紧张思维活动。
可见,“苦吟”与“凝思”、“冥搜”是意义相近的概念。
唐代诗人卢延让的《苦吟》诗有: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
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
”以“险觅”、“狂搜”释“苦吟”,也说明这些概念具有大体相同的含义。
我们之所以把“苦吟”列入文学思维的范畴,是因为“苦吟”在整个思维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王国维所谓的文学思维“三境界”中,“苦吟”与“冥搜”相当于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那种境界。
凝思已久,仍不分神,冥搜无果,决不罢休,这就与“苦吟”结果含义基本相同。
“苦吟”对于文学思维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苦吟”是成就诗人、作家的最有效的技术训练和艺术探索途径之一。
元代杨载在其《诗法家数》中说:
“诗要苦思。
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
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以为?
古人苦心终身,日锻月炼,不曰‘语不惊人死不休’,则曰‘一生精力尽于诗’。
今人未尝学诗,往往便称能诗,诗岂不学而能哉?
”所以,“苦吟”既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开拓创新的过程。
其次,“苦吟”是文学创作中促成老庄的“虚静”从“无为”转向“有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子的虚静,意味着“无为自化,清净自正”,在庄子看来,“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
但如果固执于真正意义上的虚静无为,则文学创作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苦吟”在“虚静”的心灵内环境的涵养下,实现了文学创作在操作上的可能性。
再者,“苦吟”有助于催生灵感。
它为灵感将来而呼唤,为灵感既来而欢呼,为灵感去而复返坚守着思维的阵地。
诗人之所以“苦吟”不倦,是因为他们坚信,一旦灵感出现,潜心的苦吟必将获得加倍的报偿。
实践证明,“苦吟”往往是通往“兴会”的可靠阶梯。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提倡的“苦吟”,不仅是写作过程中的文字推敲,而是泛指文学创作紧张而持久的运思过程。
陆游《夜吟》诗云:
“六十年来妄学诗,功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从“苦吟”到“兴会”,如禅家所谓的由“渐参”到“顿悟”。
最后,“苦吟”作为一种文学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以表现为一种写作态度或文学风格。
资料表明,“苦吟”原指体现在孟郊、贾岛、李贺等中晚唐诗人的创作态度中,即以冥思苦虑、字锻句炼的方法来表现来自困顿失意生活的感情内容。
到了宋代江西诗派提倡“诗非苦思不可为”,“苦吟”将渐成一种诗风。
当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苦吟”常常以锤炼语言和开掘诗意的面貌出现,但更高的目标是在整体上追求一种表现的力度。
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了一则趣事:
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
“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
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
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
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
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六也记载了此事,并说:
“余谓陈公所补四字不工,而老杜一‘过’字为工也。
如钟山语录云:
‘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儿语也。
‘无人觉来往’,下得‘觉’字大好。
足见吟诗要一两字工夫。
”在魏庆之看来,句以一字为工,自然新异不凡。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所云:
“富于万篇,贫于一字”。
当然,苦吟之不足也说毋庸讳言的。
苦吟虽能使诗歌语工句奇,但要创作出“韵格高妙”的好作品,更需要诗人先具有高雅脱俗的情志。
宋葛立方在其《韵语阳秋》中说得很好:
陈去非尝为余言:
“唐人皆苦思作诗,所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chanchu)影里清吟苦,舴艋(zemeng)舟中白发生’之类是也。
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高,故不能参少陵逸步。
”余常以此语示叶少蕴,少蕴云:
“李益诗云:
‘开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沈亚之诗云:
‘徘徊花上月,虚度可怜宵’,皆佳句也。
郑谷掇(duo)取而用之,乃云:
‘睡轻可忍风敲竹,饮散那堪月在花’,真可与李沈作仆奴。
”由是论之,作诗者兴致先自高远,则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与郑都官无异。
有学者指出,苦吟派的一味苦吟,往往脱离生活中鲜活的诗性而堕入一种偏执心理,反而丧失了诗的情趣,成为“为作诗而作诗”之流,既没有了作诗之审美愉悦,也使得诗歌本身失去了真性情,诗之面目变得可憎。
3、“兴会”与“妙悟”:
“兴会”作为我国古代文艺创作理论提炼出的审美范畴,通常是指审美感兴或艺术直觉中的灵感。
大约自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开始,“兴会”就被用于文学批评:
“灵运之兴会标举”;《颜氏家训·文章》则有:
“标举兴会,引发性灵”;明王世贞《池北偶谈》说:
“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
”这些都是“兴会”用于文学批评的例证。
虽然“兴会”与西方文论所说的“灵感”概念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创作灵感现象的许多论述却常与“兴会”有关。
陆机《文赋》中的一段描述颇具代表性: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
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
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
……虽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
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知夫开塞之所由也。
这里所讲的“应感之会”,照字面理解是心应外物而有所感发,与“心会”意思基本相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创作灵感。
陆机认为,灵感有或通畅或阻塞的时候,来时不可阻挡,去时不可挽留。
陆机对“兴会”这一特征的描述对后代影响深远。
例如,邓绎在《日月篇》中说:
“陆机《文赋》云:
‘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东坡所云‘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又云:
‘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东坡所云‘如万斛(hu)泉源随地涌出’者也。
不惟东坡,虽彦和之《文心雕龙》亦多胎息于陆。
”
历代学人对“兴会”的理解与阐释各有不同,其中明代散文集归有光的曾孙归庄在《吴门唱和诗序》中的论述较为精辟:
余尝论作诗与古文不同:
古文必静气凝神,深思精择而出之,是故宜深室独坐,宜静夜,宜焚香啜茗。
诗则不然,本以娱性情,将有待于兴会。
夫兴会则深室不如登山临水,静夜不如良辰吉日,独坐焚香啜茗不如与高朋胜友飞觥(gong)痛饮之为欢畅也。
于是分韵刻烛,争奇斗捷,豪气狂才,高怀深致,错出并见,其诗必有可观。
南皮之游,兰亭之集,诸名胜之作,一时欣赏,千古美谈。
虽邺下、江左之才,非后世之可及,亦由兴会之难再也。
认为创作灵感来自“登山临水”、“与高朋胜友飞觥痛饮”之时,这说明“兴会”需要特定的环境,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外物触发,非静坐空想所自动产生。
正如古人所谓“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陆游语)。
灵感之来,往往得益于外物的刺激,这正像钱钟书所言“石中有火,必敲始现”。
苏轼的《琴诗》云: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也同样说明了好的灵感往往来自一种复杂的各种因素的巧合。
当然,“兴会”产生的更重要的条件还是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勤奋的创作实践。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有一段广为称引的有关“成竹在胸”的论述: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
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
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
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现实生活激发了创作主体的创作冲动,创作者常常会“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但是,这种敏感的反应是有前提的。
灵感是一位苦求不应而又不请自来的任性女神。
因此,若胸中本无“高远兴致”,纵然“苦吟”良久也无济于事。
灵感必须与高潮的技艺融为一体,必须与勤奋扎实的实干结合起来。
清姚鼐在《与石甫侄孙莹》中说:
“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