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德育的可能性.docx
《第五章 德育的可能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五章 德育的可能性.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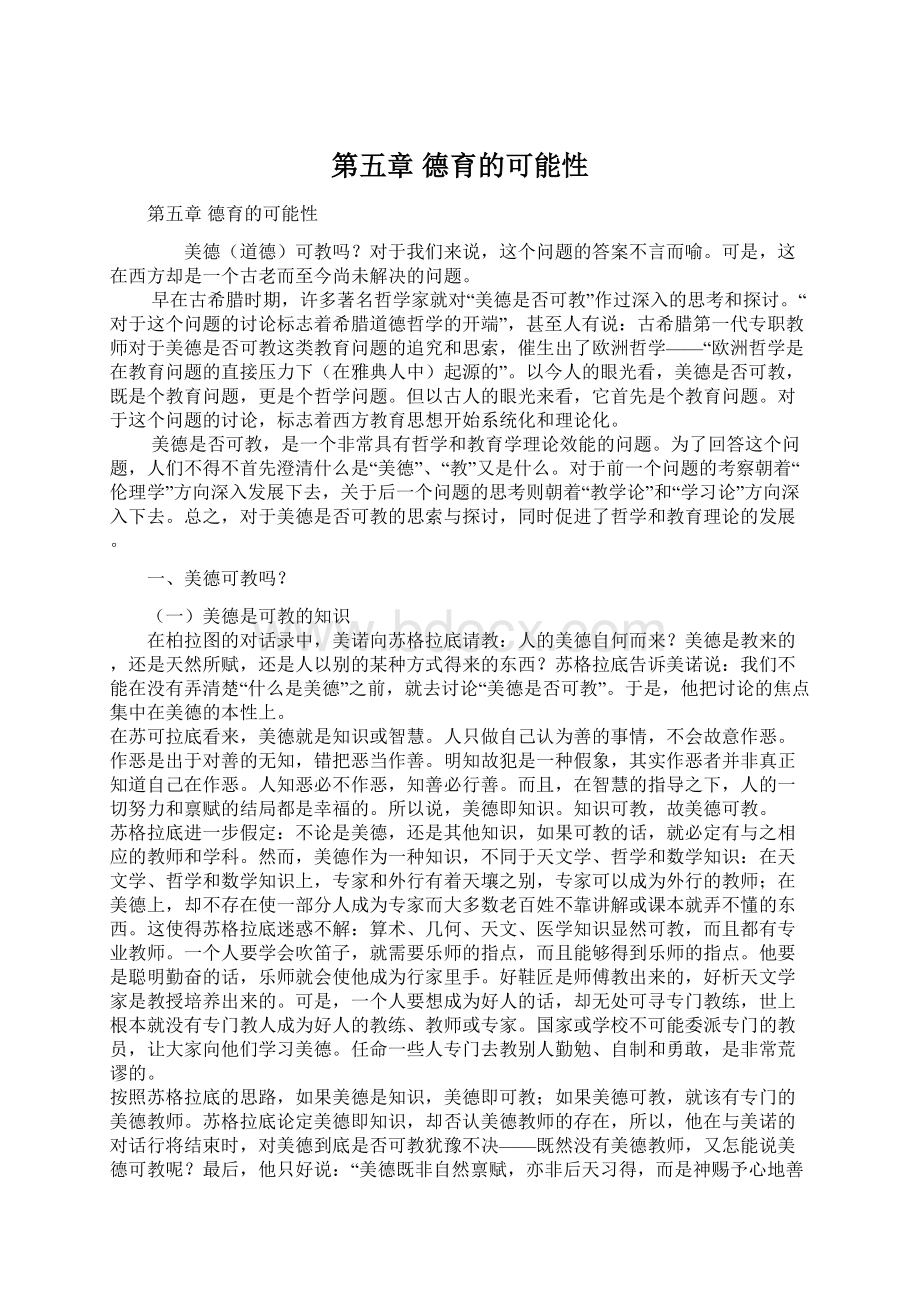
第五章德育的可能性
第五章德育的可能性
美德(道德)可教吗?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
可是,这在西方却是一个古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早在古希腊时期,许多著名哲学家就对“美德是否可教”作过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标志着希腊道德哲学的开端”,甚至人有说:
古希腊第一代专职教师对于美德是否可教这类教育问题的追究和思索,催生出了欧洲哲学——“欧洲哲学是在教育问题的直接压力下(在雅典人中)起源的”。
以今人的眼光看,美德是否可教,既是个教育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
但以古人的眼光来看,它首先是个教育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标志着西方教育思想开始系统化和理论化。
美德是否可教,是一个非常具有哲学和教育学理论效能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不得不首先澄清什么是“美德”、“教”又是什么。
对于前一个问题的考察朝着“伦理学”方向深入发展下去,关于后一个问题的思考则朝着“教学论”和“学习论”方向深入下去。
总之,对于美德是否可教的思索与探讨,同时促进了哲学和教育理论的发展。
一、美德可教吗?
(一)美德是可教的知识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美诺向苏格拉底请教:
人的美德自何而来?
美德是教来的,还是天然所赋,还是人以别的某种方式得来的东西?
苏格拉底告诉美诺说:
我们不能在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美德”之前,就去讨论“美德是否可教”。
于是,他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美德的本性上。
在苏可拉底看来,美德就是知识或智慧。
人只做自己认为善的事情,不会故意作恶。
作恶是出于对善的无知,错把恶当作善。
明知故犯是一种假象,其实作恶者并非真正知道自己在作恶。
人知恶必不作恶,知善必行善。
而且,在智慧的指导之下,人的一切努力和禀赋的结局都是幸福的。
所以说,美德即知识。
知识可教,故美德可教。
苏格拉底进一步假定:
不论是美德,还是其他知识,如果可教的话,就必定有与之相应的教师和学科。
然而,美德作为一种知识,不同于天文学、哲学和数学知识:
在天文学、哲学和数学知识上,专家和外行有着天壤之别,专家可以成为外行的教师;在美德上,却不存在使一部分人成为专家而大多数老百姓不靠讲解或课本就弄不懂的东西。
这使得苏格拉底迷惑不解:
算术、几何、天文、医学知识显然可教,而且都有专业教师。
一个人要学会吹笛子,就需要乐师的指点,而且能够得到乐师的指点。
他要是聪明勤奋的话,乐师就会使他成为行家里手。
好鞋匠是师傅教出来的,好析天文学家是教授培养出来的。
可是,一个人要想成为好人的话,却无处可寻专门教练,世上根本就没有专门教人成为好人的教练、教师或专家。
国家或学校不可能委派专门的教员,让大家向他们学习美德。
任命一些人专门去教别人勤勉、自制和勇敢,是非常荒谬的。
按照苏格拉底的思路,如果美德是知识,美德即可教;如果美德可教,就该有专门的美德教师。
苏格拉底论定美德即知识,却否认美德教师的存在,所以,他在与美诺的对话行将结束时,对美德到底是否可教犹豫不决——既然没有美德教师,又怎能说美德可教呢?
最后,他只好说:
“美德既非自然禀赋,亦非后天习得,而是神赐予心地善良者的一种本能。
这种本能并不与理性相随。
”从理性上说,这不啻是一种观念上的倒退。
后人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即知识”、“美德可教”的观点,这种观点成为西方理性德育的思想源泉。
但是,他提出的“如果美德可教,为什么没有专门的美德教师?
”这一疑问,依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二)美德可教但无需专门教师
对于苏格拉底的迷惑,普罗塔哥拉解释说:
学习美德类似于学习母语。
希腊婴儿不像天生蓝眼睛那样天生就有希腊语知识和技能,他们必须通过后天学习,才能掌握自己的母语。
尽管如此,希腊各地却依然没有教口语的专业教师。
道理很简单,儿童的父母、同伴以及儿童遇到的所有人,都是他学习希腊口语的非专业教师。
学会说母语,并不需要特别向某个人学习,更不必向任何语言学专家学习,而是普遍地向每个人学习。
同样的道理,尽管人们确实在学习各种道德规范,但不必在大师所上的课上学习这些规范;人们在家庭、街道、操场和集市中,向每一个人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道德规范。
这就是说,道德规范并不是只有少数专门研究者才知道的深奥事物,而是几乎人人都了如指掌的普通事物。
在道德上,无所谓专家,也无所谓业余爱好者。
当然,有些道德问题错综复杂,并且不常见,确实需要向有丰富的经验、生动的想象力和明智的判断力的顾问请教,就好比在学习母语时,偶然会碰到一些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问题,必须请教词典、课本或语音学家才能掌握。
总之,品德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学习的结果。
但是,这种学习并不需要教人正直、宽厚和宽容的教授。
美德可教,同不存在专门的美德教师,并不矛盾。
(三)美德可以通过榜样示范和批判性指导下的训练来教
亚里士多德解释苏格拉底的迷惑析方式,与普罗塔哥拉稍有不同:
苏格拉底一方面相信美德即知识,美德可教,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在美德方面,像在其他学科知识方面那样,有所谓的专家导师或应试教师。
在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迷惑不解,原因在于,人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往往只想到那种老师讲学生听的教与学方式:
教师忙于告诉学生这是事实或那是事实,学生忙于记下老师说过的东西。
如果他们日后能够背诵或复述老师讲过的东西,就意味着他们学会了自己的功课。
其实,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东西人们能够学会但不能逐字逐句复述出来的东西。
例如技能。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小孩子不是一下子就会骑自行车的,他得学习怎样平衡,怎样驾驶,怎样使劲,怎样刹车。
不论他父亲口头上作过多么精确的指导,他都不能仅靠记住父亲的口头信息学会骑自行车。
做父亲的不能靠讲述使儿子学会在骑自行车,他不能只告诉孩子做什么,还得在石子路上向他示范怎么骑。
更重要的是,让他自己去骑,一遍又一遍地在不听使唤的车子上尝试、操作、模仿、练习,直到学会。
技能是通过模仿和练习获得的,因此教技术的主要方式是示范和训练。
当然,适当的口头指导也是需要的,但是,这种口头指导通常并不是一种系统讲授,而是针对学习者的模仿和练习的纠正性或批判性指导。
教师不能通过纯口授式谈话,把一项技能填塞给学习者。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踢足球、划船、做木工、射击、唱歌、游泳和飞行,也适用于诸如计算、翻译、发音、绘画、解剖、推理以及鉴定证据之类更具学术性或智力性的事情。
无论学习动作技能,还是学习心智技能,都必须依赖于实践。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美德的学习。
仅仅记诵五篇告诫我们克制自己的贪婪、恶意或懒惰的道德讲演,是不够的。
这种记诵,并不会使我们获得自制、公正或勤劳之类的美德。
是别人树立好榜样,以及接下来我们自己的实践和失败、再实践和再失败,使我们逐渐养成了这样或那样的美德。
在道德事务上,就像在技艺上那样,我们首先通过别人的示范来学习,然后通过别人的训练(自然地伴随着一些言语说教、表扬和指责)来学习,最后通过自我练习来学习。
行为规范并不是通过讲课就能够传递的东西,而是中国人民有通过榜样、训练和自我练习才能灌输的东西。
有人认为,如果美德可教的话,就该有教行为规范的教授,就该有行为规范百科全书,就该有行为规范的课程和考试。
这是一种荒谬的想法。
如果臆想出来的美德教授企图通过口授进行道德教导的话,那么,他们教小孩子关心他人,就无异于小孩的父亲用单一的口授,教他骑自行车。
总之,美德像技能那样,不能单独通过讲述来教,但能通过榜样示范和批判性指导下的实践来教。
因为行为规范就像技能一样,不是一堆理论或学说,因而不是通过记诵别人口授可以学会的东西。
我们通过练习学会行为规范。
如果我们学会做该做的事情的话,那是通过做来学会做的。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美德是否可教”时,将学与教的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他把学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学知识,第二类是学技能和学美德。
与此相应,他把教也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口授式教(teachingbydictating),第二类是训练式教(teachingbytraining)。
通过口授式教可以学到知识,却学不到技能或美德,技能和美德主要通过训练式教获得。
人们往往把学美德错误地划入了第一类学习,与学知识相提并论,在口授式教的意义上讨论美德是否可教,所以才产生美德可教却为什么不存在专门的美德教师的疑惑。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并没有完全解答苏格拉底的疑惑:
如果美德和技能一样主要是通过训练式教获得的,那么,为什么许多技能的学习需要专门的教练的示范、指导和训练,道德规范的学习却不存在这样的教练呢?
难道说,道德规范就像是跑、跳、母语口语、捉迷藏那样过于“小儿科”,不需要专门的教师,让一些临时的业余工作者去教小孩子就够了?
(四)美德可学不可教
普罗塔哥拉用母语学习作类比,亚里士多德用技能的学习作类比,都没有圆满地解决“美德可教却为什么不存在专门教授美德的教师”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因为,美德学习既不同于普通知识的学习,也不同于技能的学习。
亚里士多德把美德学习与技能学习混为一谈。
一个人通过训练式的教可能身怀绝技,但此人既可能用自己的绝技做好事,也可能用这种绝技干伤天害理的坏事。
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当然可以用自己的医术治病救人,但是,如果他道德败坏,接受患者财产继承人的贿赂,也可以用自己的医术谋财害命。
一个人不想老老实实赚钱的话,培训他练书画,就可能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书画伪造者。
书画培训本身并不能使他不想去伪造,广而言之,技能的培训本身并不教会他凭良心办事。
所以,美德的学习不同于技能的学习,学习道德规范并非在什么事情上获得专长,有道德并非在什么事情上成了专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承认在美德或行为规范上存在培训我们的专家。
美德学习和母语学习确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普罗塔哥拉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
可是,两种学习还有极其不同的一面。
年龄相仿、资质不同、受的培养不一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可能远比另一个口齿伶俐,能言善辩,说话连贯,他口语上远比另一个孩子好,但他在运用这种精熟的技能时却依然可能比另一个孩子坏得多。
他可能是一个口齿伶俐爱撒谎的小家伙,可能是个有口才爱泄密的小家伙,可能是个说话连贯好搬弄是非的小家伙。
他学会了怎样陈述事情,却没有学会哪种事情该说,哪种事情不该说。
所以,儿童确实能够从同他所结交的人的会话中,学习会话技能,但这不足以使儿童学到行为规范(包括会话的行为规范)。
教孩子不要说刻薄话,同教孩子怎么有效地说他想说的话(包括刻薄话),不是一回事。
同样的道理,教孩子怎样打扑克牌,不同于教这个孩子宁可输牌也不靠欺骗赢牌。
美德虽然与知识和技能不无关系,但它不同于知识,也不同于技能;学美德不同于学知识,也不同于学技能。
美德学习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学习,其核心或根本是态度学习。
普通的知识通过口授式教可以学到,普通的技能通过训练式教可以学到,但是这两种教的形式都不足以使人学到普通的美德。
美德可以通过何种形式的教学到呢?
是什么样的教,使得一个孩子逐渐变得公正、勇敢、体谅人、值得信赖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英国哲学家赖尔(G.Ryle)回顾了普通人在道德成长历程中受到的各种重要影响:
正是在他人的榜样、表情、言劝、劝诫和约束的影响下,我们逐渐深深地关心他们深深关心的事物;正是在别人的潜移默化之下,我们耳濡目染,学到了各种行为规范。
这类影响在日常语言中被大家非常自然地称作“教”。
显然,赖尔认为从“教”一词的日常意义上说美德是可教的。
所谓日常语义的“教”,指的是无意之中对人的潜移默化析影响。
那么,谁是使年轻人学会正直、不怀恶意、勤勉之类美德的教师呢?
赖尔的回答与普罗塔哥拉回答如出一辙: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年轻人的力图成为像谁一样的人。
有的所轻人力图成为像自己父母或兄长、教师那样的人,这些人便是他道德学习榜样;有的年轻人力图成为自己偶然遇见的某个人那样的人,这个人就是他道德学习的榜样;有的年轻人力图成为像某个英雄人物那样的人,这个英雄就是他道德学习的榜样。
但是,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正力图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无意之中成了某个年轻人学习榜样。
赖尔认为,即使滥用“教师”一词,也不能把他们看成是美德“教师”。
他们是年轻人的“道德榜样”,却不是年轻人的“道德教师”。
这样一来,赖尔依然没有解答苏格拉底提出的千年疑问:
美德可教,为什么又没有专门教授美德的教师?
赖尔只好怀疑“美德是否可教”这个问题的合法性了。
在赖尔看来,儿童是通过向好榜样学习,获得各种美德的,正如他们通过向好榜样学习,获得各种技能,所不同的是,在技术上有意树立的好榜样有助于技能的学习,出于某种教诲的目的去树好榜样却无助于道德学习。
假定一位教师内心对某种不公平的现象并不反感,但是,为了教育学生,作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
这样一种自以为有教育意义的表演,实际上是一种虚情假意的装腔作势,给年轻人树立的,是一种为了教育别人而假装气愤的榜样。
广而言之,为了教人以美德而特意树立好榜样,并不能使人学到这种美德,至多使人学会了为了教人美德而故意去树立好榜样这种做法。
教师即使有意利用自己的人格和行为,去培养学生的道德态度和行为,其效果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
根据赖尔的意思,从“教”的日常语义上说,美德是可教的;从“教”的严格意义上说,美德是不可教的。
就是说,如果把人们无意之间对年轻人品德潜移默化的影响称作“教”的话,美德是可教的;如果“教”限指有意识地树立好榜样之类的活动的话,美德就不可教。
所以,与其讨论美德是否可教,不如讨论美德是否可学。
(五)美德可间接教不可直接教
赖尔认为美德不能单纯通过口授和训练的方式来教,这个论点总的来说是可取的。
很显然,单纯用口授的方式确实可以教人以知识,用训练的方式(伴随于口授的方式)确实可以直接受人以技能,单纯以口授和训练的方式却不可能直接教人以美德。
用直接的方式教授美德,对学生品德的影响即使有,其数量也是少的,其程度也是轻微的。
但是,如杜威所言:
如果注意教材固有的社会性质,把它们当作引导儿童的社会意识的手段来教,用它们来帮助儿童理解并掌握社会进步的基本手段,如果注意教法与社会生活总的精神相一致,诉诸于儿童主动参与、积极贡献、相互合作、互惠共享的精神和能力,如果精心安排学校和班级的集体生活,使之与社会生活保持生动的联系,那么,教师在教授知识和技能过程中就渗透着有意的而且有效的道德影响,学生在学知识和学技能的过程中,就会逐渐地形成理解社会生活的理智、控制社会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乐意为社会服务的兴趣。
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同时学到了社会生活所需的美德。
所以,美德可教,但不能直接教,而只能通过直接的教间接地渗透道德影响。
从“教”的间接意义上说,学校教师和家长等都是教美德的“专家”。
赖尔注意到书画教学本身不可能直接教人以不伪造书画的行为规范,却忽视了通过书画教学间接地教人以这种行为规范的可能性。
他把这种间接的却是有意的教划归为日常用语之“教”所指的道德影响,进而又把它混同于无意识的道德影响。
此外,他把教师出于教育学生的目的树立好榜样一律看成是装腔作势的表演,忘记了教师至少具有普通人的道德水准。
作为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无需装腔作势就会自然地显示出普通人所具备的美德;而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学校生活中,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展示普通人所具有的美德,不但不会引起人们(包括学生在内)的警觉和反感,反而会受到欢迎。
因为,教师的天职就是教育人,培养人,这是大家普遍接受的信念。
一个有失道德水准的人,企图通过假惺惺的道德示范教人以道德,那是办不到的。
但是,伪君子不能作道德榜样,并不说明美德不可教。
二、伦理学分歧
综上所述,关于美德是否可教,历史上有过许多争论,至今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由于对什么是“美德(道德)”、什么是“教”、到何种程度才算“可教”众说纷纭,人们对“美德是否可教”意见各异。
而对于“美德是否可教”的争论,又不断地深化着人们对道德和教学的认识。
千百年来,人们围绕这个问题的探讨,不断地促进着道德理论和教与学理论的进步。
(一)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断言:
万物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若要成为善,就要系于智慧。
智慧(知识)使人受益,人的一切努力和禀赋若在智慧的指导下,其结局都是幸福,若被无知所左右,其结局则是不幸。
因此,正常的人必定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不做自认为错误的事情。
人知善必行善,美德即知识。
他根据“知识可教”,推出“美德可教”,并强调道德教育的核心是使人获得关于善的理性知识。
这种观点的合理内核,已经大部分被当代道德教育理论和模式所继承,甚至成为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
但是,“美德即知识”的观点,遭到了后人的大量抨击。
在道德的本质和属性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包尔生、赖尔等人都提出了不同于苏格拉底的观点。
(二)美德最终落实在行动上
亚里士多德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知善而行善的现象,但人们更多的是知恶而作恶。
善的知识渊博的人,未必是道德高尚者。
否则,伦理学专业的教师、学生就会是世上最有道德的人。
美德和技术一样,必须通过现实的活动才能获得。
例如建造房屋,才能成为营造者;弹奏竖琴,才能成为琴手。
同理,做公正的事,才能成为公正的人;进行节制,才能成为有节制的人;表现勇敢,才能成为勇敢的人。
品质来自相同的现实活动,正是在犯难冒除之中,由于习惯于恐惧或习惯于坚强,有的人成了勇敢者,有的人成了懦夫。
总之,任何一种美德都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并且最终都体现在行动上。
因此,美德和技艺一样,其首要问题不是知识的教与学,而是行为习惯的培养和获得。
美德不能像知识那样用口授的方式教,但能像技艺那样以示范和实践、训练和练习的方式教。
(三)道德主要诉诸情感或态度
另一些人可能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式的行为主义观点。
他们注意到,一种行为道德或不道德是不确定的。
例如,偷人提包的贼碰巧使人因为耽误登机逃过一场悲惨的空难,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偷窃提包的行为是一种道德行为。
同样的道理,一个精神失常的泥水匠,成天寻找白色鹅卵石铺路,我们也不能因此说这种行为是道德行为。
断定一种行为道德或不道德,必须诉诸于行为人的内在的取向、态度、情感、动机。
因此,情感和态度是道德的关键因素。
(四)道德归根结底是意志的体现
康德认为,道德是一种服从善良意志的绝对命令的义务感,与人的好恶情感无关。
例如,孝敬父母与喜爱不喜爱父母的情感无关。
无论喜爱不喜爱父母,都应该孝敬父母,这才是真正体现了无条件的义务感,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同样的道理,教师对学生负责,与教师热爱不热爱学生无关。
无论教师喜欢不喜欢学生,都应该对每一个学生负责。
康德承认人在经验世界有向善的倾向,但强调人在先验世界有下达绝对命令的善良意志。
所以,人不但是唯一需要教育的存在,而且是唯一可救的存在。
但是,在把道德归结为意志的人中,也有人认为道德不可教。
例如,叔本华也断言,道德受自由意志支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意志之所以为意志,就在于意志不可改变。
正因为意志不可改变,美德是教不会的。
教人有美德,跟教人成为天才一样是不可能的。
指望道德制度和伦理学唤起有美德的人、高尚的人、圣人,就跟指望美学唤起诗人、雕刻家、音乐家一样,是愚蠢的。
人的意志和性格与生俱来,不可改变,教育无论建立在对人性内在价值的兴趣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对人类发展能力的认识的基础上,对改变人性都无能为力。
赫尔巴特反驳说:
人具有从意志转化为道德的可塑性,因此人在道德上是可教的。
但他同时承认,人的可塑性并非永无止境。
可塑性,意味着道德上的不定型,儿童的不定型程度受个性的限制,通过教育使儿童在道德上定型,受环境和时间的限制;成年人的定型过程是一种内部过程,教育对此无能为力。
总之,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因人而异;儿童在道德上是可教的,成年人在道德上已经定型,因此是不可教的。
同是儿童,道德上的可塑性也不一样。
中国古代所谓“孺子可教”,“竖子不可教”,也是同样的道理。
(五)美德是理智与情意的综合表现
包尔生继续反驳说:
叔本华的学说根本不顾及道德教育和道德影响的事实。
通过对人的情感和意志的理性训练,赋予人理智,是可以培养有美德的人的。
美德是可教的。
包尔生理解的道德教育包括意志的教育和情感的训练,但是他所谓的“意志教育”是赋予意志以理性的教育,他所谓“情感训练”是赋予情感以理性的训练,因此,他所理解的“道德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理性教育。
这种若明若暗的观点到了20世纪被明确起来。
人们把品德一分为三:
理智、情感、意志(或行动)。
有的人认为只有理智可教,而情感和意志是不可教的。
而像包尔生那样的人则认为,理智驾驶感情和意志,理智可教,就意味着情感和意志也可教。
但是,赖尔指出,一切将人心一分为三,分别讨论知、情、意是否可教的学说,都是荒谬的。
正如把“被笑话逗乐”这件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思考并理解笑话的意思的智力操作,一部分为因笑话可乐而笑痛肚子的感觉,一样是荒谬的。
很难想象一个人被笑话逗乐了却未领会笑话的意思,反之,此人领会了笑话的意思却觉得没有什么可乐,也是很难想象的。
其实,领会笑话的意思、欣赏笑话的机智或谎谬、被笑话逗得不可支的感受、忍不住大笑或微笑,这一切都是可以分解示范来的一个个操作,而是同一件事情(即欣赏笑话)的所有特征。
同样的道理,假如通过教育能够使人对某件不正义的事情义愤填膺,那么,他一定知道了这件事不正义。
反之,假如通过教育能使一个人知道了某事不正义,他必定会对这件事感到愤慨,必定会采取某种行动。
一个人的品德是通过它的思想、行动、言语和面部表情等全面表现的。
因此,不能分别从知、情、意几个方面讨论品德以及道德是否可教的问题。
(六)美德即体认之知
赖尔的观点接近美德的实际状态,但是包尔生把“意志教育”和“情感训练”还原为“理智的训练或教育”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倾向。
尽管受到赖尔等人的批评,这种倾向在20世纪相当流行,它与现代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理性化运动相呼应,另一方面又使人们重新审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论断的意义和价值。
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人会故意做自认为不对的事情,假使知道善是什么,他必定会行善。
因此,道德是可教的。
只要使人知道善是什么,就可以保证他会行善。
但大多数人与他的意见相左,认为人类确实经常排斥自认为正确的东西,明知故犯。
可见,徒知不足以成德,道德完善还要有行善的意志。
教人道德,只能启迪人的道德智慧。
要促进道德完善,我们还要增强意志,使良心更加敏感。
总之,道德就其认知方面也许是可教的,但就其整体而言是不可教的。
这是对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及“美德可教”论述最为常见的批评。
可是,多数人可能都把他关于“美德即知识”的论断理解得过于简单。
其实,他所谓的“知识”与多数人理解的“知识”有别,杜威对此作过现代意义上的诠释。
苏格拉底和杜威所说的关于善的知识,用我们容易理解的话来说,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或者从书本学到的间接经验,而是一种直接经验。
它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包含着个人信念上的认同,必然会导致与之相应的行动。
换句话说,如果美德即知识,那么它是一种“德性之知”或“体认之知”,而非“见闻之知”。
“德性之知”系宋儒张载所创,言:
“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
”(《正蒙·大心》)现代新儒杜维明赋予其现代意义:
“德性之知”即其所谓“体知”,强调德性之知是体之于身的真知,它包括赖尔所谓“知什么(know-what)”之“知”和“知如何(know-how)”之“知”(即“会”)。
这种诠释的不足在于,未突出美德作为一种特殊知识的特点——认识主体在信念或价值取向上对美德的认同。
因此,把作为知识的美德称作“体认之知”,也许更为恰当。
正是在把美德作为体认之知或直接经验的“知识”的意义上,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杜威进而说“学校中的道德教育问题就是获得的问题”。
三、教学论分歧
纵观历史,随着人们对道德是否可教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对学与教的认识日趋全面。
起初的讨论把“美德”等同于“知识”,美德的学与教问题因而成了知识的学与教问题,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知识学习”以及与之相应的“口授式教(teachingbydictating)”上。
后来,人们发现美德的学与教更近似于技能的学与教。
而“技能学习”以模仿、练习、实践为主,不同于以听讲、记诵、复述为主的“知识学习”。
支持“技能学习”的,主要是“训练式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