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docx
《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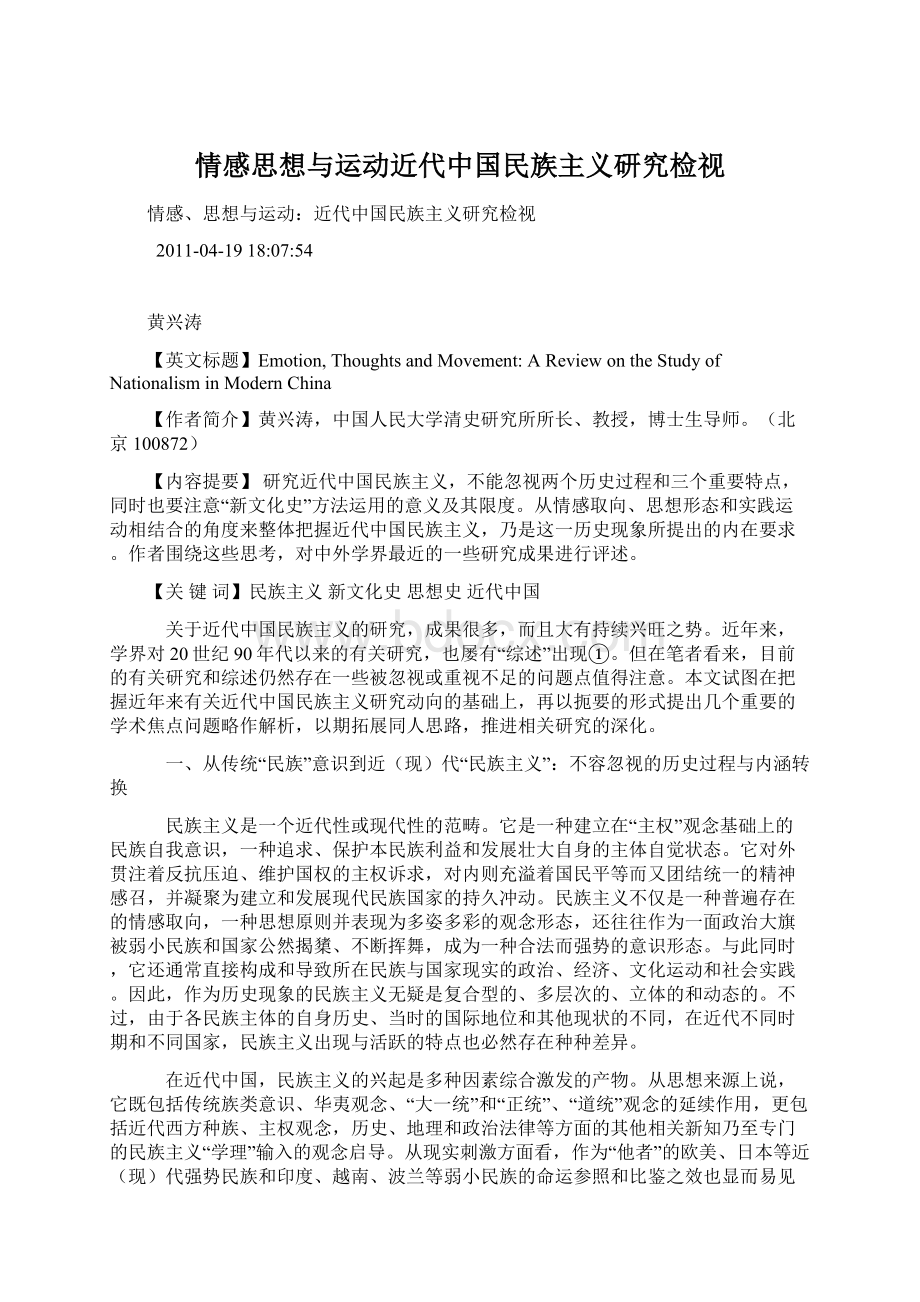
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
情感、思想与运动: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
2011-04-1918:
07:
54
黄兴涛
【英文标题】Emotion,ThoughtsandMovement:
AReviewontheStudyofNationalisminModernChina
【作者简介】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能忽视两个历史过程和三个重要特点,同时也要注意“新文化史”方法运用的意义及其限度。
从情感取向、思想形态和实践运动相结合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乃是这一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内在要求。
作者围绕这些思考,对中外学界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关键词】民族主义新文化史思想史近代中国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很多,而且大有持续兴旺之势。
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有关研究,也屡有“综述”出现①。
但在笔者看来,目前的有关研究和综述仍然存在一些被忽视或重视不足的问题点值得注意。
本文试图在把握近年来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再以扼要的形式提出几个重要的学术焦点问题略作解析,以期拓展同人思路,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化。
一、从传统“民族”意识到近(现)代“民族主义”:
不容忽视的历史过程与内涵转换
民族主义是一个近代性或现代性的范畴。
它是一种建立在“主权”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一种追求、保护本民族利益和发展壮大自身的主体自觉状态。
它对外贯注着反抗压迫、维护国权的主权诉求,对内则充溢着国民平等而又团结统一的精神感召,并凝聚为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持久冲动。
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取向,一种思想原则并表现为多姿多彩的观念形态,还往往作为一面政治大旗被弱小民族和国家公然揭橥、不断挥舞,成为一种合法而强势的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它还通常直接构成和导致所在民族与国家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和社会实践。
因此,作为历史现象的民族主义无疑是复合型的、多层次的、立体的和动态的。
不过,由于各民族主体的自身历史、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其他现状的不同,在近代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民族主义出现与活跃的特点也必然存在种种差异。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综合激发的产物。
从思想来源上说,它既包括传统族类意识、华夷观念、“大一统”和“正统”、“道统”观念的延续作用,更包括近代西方种族、主权观念,历史、地理和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其他相关新知乃至专门的民族主义“学理”输入的观念启导。
从现实刺激方面看,作为“他者”的欧美、日本等近(现)代强势民族和印度、越南、波兰等弱小民族的命运参照和比鉴之效也显而易见,而列强对中国不断进行的军事侵略、政治讹诈、经济掠夺以及文化与种族歧视所导致和强化的民族现实危机,更成为驱动近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发展的直接动力。
有学者认为,与民主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不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来源于传统的族类观念,特别是“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②,这种见解值得商榷。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王尔敏先生就曾敏锐地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实际上由三种自觉意识组成,一种是族类自觉意识,一种是文化自觉意识,一种是近代国家“主权”自觉意识。
前两种东西中国自古并不缺少,只有“主权”观念乃属近代时从外新来,并且构成近代中国区别于中国古代民族意识(他称之为古代民族主义)之特色所在。
他以王韬、曾纪泽等几个“思想先知”为代表,勾勒了19世纪60年代之后近代“主权”意识在中国逐渐觉醒的历程。
同时还以戊戌时期的学会活动为依据,对此期以“保国、保种、保教”三者并提且以“保国”的主权意识为首的近代民族主义勃兴的情形,给予了清晰揭示③。
应当说,王尔敏先生简洁、朴实而睿智的看法,对今人了解传统中国民族意识与近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
不过,笔者对王先生的见解虽多表赞同,却觉得其中也仍有不甚完备之处。
一则,他把“主权”观念仅局限在外交层面,实忽略了民族国家“主权”的拥有者主体是平等、自主的“国民”而不是专制君主这一层基本连带意涵。
孙中山先生后来强调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价值,正是基于这一层面的内涵;二则,他对清初尤其是晚清以来西方传入的新的种族知识、政治文化观念及其由此带来的变化与影响似也不甚重视。
这不免会妨碍我们更为全面准确地认知相关问题。
在笔者看来,今人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问题时,应不能忽略两个历史过程,一个是清代尤其是晚清以来中国就与早已进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的欧美各国及其人民打交道的历史过程;一个是西方“种族”、历史和地理、政治法律等新知识、新思想和价值观念传入中国,并与传统民族意识互动而发生作用、导致相应变化的历史过程。
这两个过程之间又是不可分割的。
比如,就中国人带有明显现代性因素的国家疆域和边界意识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从戊戌时期才开始,甚至也不能说从19世纪60年代初《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出版,现代“权利”特别是“主权”概念以及国际法知识得以正式形成和传播才开始,实际上至少从康熙皇帝与欧洲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康熙和雍正时期通过与俄罗斯无数次的谈判,以一系列条约形式划定了长达数千俄里的边界线的行为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更是明确宣称:
“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
……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④。
1820年完成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不仅在前朝几部“一统志”的基础上增添了划界与边疆统部辖境内容,还明确绘有全国总图,并标明与邻国的边界。
这些无疑都是鸦片战争前近代国家(领土)主权意识因素在中国不断积聚的重要证据⑤。
又比如,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开始部分见证、传播,清末民初大肆流行开来的新“人种”知识,其对近代中国民族意识形成的推动作用也不能忽视。
早在1853~1854年传教士慕维廉编著的《地理全志》一书中,有关世界人种就被分为白人、黄人、红人、黑人、铜色人(又称“棕色人”)五种,且附有人种形象插图⑥,此后关于这些人种的外形特征,他们的历史和风俗文化,以及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命运等信息和知识,也随之逐渐流传,正是因此,中国人那种以“黄种人”自我定位、自我期许的民族意识得以逐渐形成,并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人“亡国灭种”危机意识和奋发进取的民族自信之重要组成部分。
戊戌时期,生物和社会进化论之所以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也不能说与这种建立在新“种族”知识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无关。
在这方面,梁启超1897年发表的那篇具有民族自觉宣言性质的《论中国之将强》一文可以为证。
在此文中,梁氏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所谓黄种人的“优越性”。
他慷慨激昂地说:
“吾请与国之豪杰,大声疾呼于天下曰,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
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为之事,黄人无不能者。
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
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而谓彼之所长,必我之所短,无是道也。
……
夫全地人类,祗有五种,白种既已若是,红种则湮灭将尽,棕黑两种,其人蠢而惰,不能治生,不乐作苦,虽芸总犹昔,然行尸走肉,无所取材。
然则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黄人末由也。
今夫合众一国,澳大一洲,南洋一带,苟微华人,必不有今日。
今虽获兔烹狗、得鱼忘筌,摈之逐之,桎之梏之,鱼之肉之,奴之仆之,然筚路蓝缕之功,在公论者终不没于天下。
……殆亦天之未绝黄种,故留此一线,以俟剥极将复之后,乃起而苏之也。
”⑦
由此可见西方种族知识对于中国近代民族自觉影响之一斑。
与此同时,进化论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观念,将“竞争”、“尚武”和物质层面发展的内涵也纳入其中⑧,并由此使中国人同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意识。
凡此,都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完整形态最终发生于甲午战争以后的重要因素。
当然,清末民初现代民族主义成熟思想形态的出现,也是梁启超、康有为、蒋智由、汪精卫、孙中山、陶成章等先进知识分子从日本接受现代“民族”、“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思想概念,“收拾西方学理”(章太炎语),并结合传统的民族意识资源,借用传统民族象征符号,加以创造性发挥和动员的结果⑨。
他们的有关思想文本,遂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自觉的直接象征。
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值得深入透视的几个现象与特点
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总不免要对其特点加以思考。
然而一旦真正探讨起这个问题来,才发现已有的说法虽有不少,但真正得到学界较为认同的观点其实并不多。
由此也可见该问题的难度。
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现象,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些许启示。
首先,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列强欺压和侵略予以自觉回应的现代性思潮和运动,始终与“日本因素”特别是其连续不断的侵华活动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这样一个似乎相当明显的事实和特点,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全局的角度加以把握者并不多见,从“民族主义”的心理、思想和运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自觉进行整体性剖析的,就更为少见了。
实际上,同为“黄种”、过去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不为中国所重的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成功改变自己被列强欺辱的民族命运,并最终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不仅成为刺激中国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勃然兴起的标志性开端,随后大批中国人到日本留学和由日本大量转输西方新式文化资源,还孕育出清末第一批完全自觉的民族主义者。
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支配下,对“同文同种”的中华民族不断实施侵略、掠夺与歧视的残酷打击,可以说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为重要和持续性的动力来源,同时也塑造了这一民族主义耻愤交加、空前奋发和最终在绝境中通过涅槃获得重生与自信的情感品格和精神素质。
“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具象征性的论题之提出及其思想建设;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并将“民族性”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特性之首的重要转变⑩;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和认同的基本形成,也都是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1935年日本入侵华北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对于日本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柯博文(ParksM.Coble)1991年出版的《走向“最后关头”:
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一书(11),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对国民党政权的有关努力及其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一致关系的审视,尤为难得,不过其探讨的时段主要限于日本大规模侵华时期(12)。
最近,有中国学者著文尝试从甲午战后中日关系全局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将中日关系的事件史与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结合起来的可贵自觉(13)。
该文以1895、1905、1915、1925、1935、1945六个关键年度为视点,考察了伴随中日关系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历程,透视了各个时间点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与日本因素的关系。
当然,这一问题所涉范围极为广泛,难度不小,作者的有些分析似还存在可以商讨的余地,比如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1905年,就未必妥当;而他认定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一民族主义就走向了“基本的终结”之结论,恐也难以服人。
在笔者看来,此后以“沈崇事件”为标志,以反美帝侵略为主题,以至不少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也都卷入其中的民族主义浪潮,应该才是鲜明地体现了该思潮时代特色和历史功能的终结标志(14)。
其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包涵“抗议与建设的两面”,总的说来两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的关系(15),但与前述现象相关,它也表现出“反抗”或“抗议”的一面更受关注、并凸显“建设”的一面相对发展不足的特点。
“反抗”、“抗议”本身,既彰明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防御”性质、政治正当性和激烈悲壮的道义色彩,同时巨大的生存危机对“民族自信力”的本能呼唤,又为“文化民族主义”的繁蘖创造了条件;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建设”面向的展开,则蕴涵了其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复杂胶合的历史多面性及其内在张力。
其中“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选择,至今仍是一个亟需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由于始终不断的救亡逼迫,对内建设“民族国家”的许多任务不及着手,遑论完成?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建设因此发生现实矛盾乃至思想冲突,实不足怪。
但如果仅以此来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则是偏颇的。
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的最终价值根据恰是独立和平等的民主原则,而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开始就以激昂的声音呼唤“新国民”,无论是提出“三民”思想的严复,还是鼓吹“新民说”的梁启超,实际上都已成为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自觉的民族主义思想先驱。
不过,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提法在西方学术界虽早就存在,国内的研究者在相关民族主义分类中也早有提及,而有关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系统深入的专题研讨却一直相当缺乏。
这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的热闹情形恰成对照。
在这方面,许纪霖教授近年发表的《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一文,颇值得关注(16)。
该文不仅认真梳理了从梁启超到张君劢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而且细致论析了其内部由政治民族主义向文化民族主义演化的思想脉络和该思潮的一些重要特点。
其自觉将文化民族主义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里而不是以往学界通行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框架下来认识,的确对今人认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和复杂性有所助益。
不过,对于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研究也不能情绪化,有学者不分时段,也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是一厢情愿地把那顶“理性民族主义”的桂冠戴到那些身份待定且不断游移的所谓“自由民族主义者”头上,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本身就未必是“理性”的和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回到“反抗”与“建设”的关系上来。
事实上,在有的自由民族主义者看来,自觉、持久、有组织有准备地“对抗”过程不仅是“建设”即民族建国的前提,甚至其本身就是“建设”的一部分。
傅斯年和张君劢等人就都曾具有以“反抗”求“建设”的自觉意识。
如日本占领东北后,傅氏就曾激动地声言:
“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
中国之彻底腐败,非借机锻炼一下子不可的。
譬如打铁,钢是打出来的。
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力效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
打个落花流水,中国人才有翻身之一日”(17)。
可见对于傅斯年等人来说,“反抗”只不过是“建设”的一个手段而已。
在民族主义“建设”的面向里,尤其是在强烈不满政治文化现状的“未来取向”的思路中,还会自然出现程度不同的所谓“反传统”倾向问题。
明确提出“反传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特殊形态”并由此引人深思两者之间“历史”关系的,仍然是罗志田教授(见前引文)。
不过对此一断言,笔者虽大体接受,却以为尚需要做点分辨。
在近代受外来列强欺压而又专制严重、缺乏近代民族传统的弱小民族里,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不会绝对不反“传统”,他们也会干着以“以传统反传统”,或确切地说“以此传统反彼传统”,以历史反现实,以“复兴”相号召的事情。
但真正思想上自觉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却一般不笼统地、全方位地、整体性地“激烈反传统”,而是在批评某些传统的同时,又特别自觉、有选择地积极强调、阐发和弘扬主流传统或至少是部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只有少数强烈认同现代民族国家价值的“政治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危机相对弱化的特定时期,才会有全盘激烈反传统的异常之举,故罗志田称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笔者也表示认可。
但是,这与有些学者将“激烈反传统”径直归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认识(18),实在仍存在差别。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还愿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异同角度,再略作一点发挥。
在笔者看来,若暂不考虑“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西方来源,仅就两者汉字字面和近代中国人的习惯用法而言,它们当属既有密切关联和重合内涵、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
“爱国主义”大体可以与“政治民族主义”的有关诉求相对应,但其也不排斥文化民族主义的有关诉求。
由于“民族”(或译为“国族”)主要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社会文化范畴,故“民族主义”必然含具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其主体历史延续性的固执强调,而“爱国主义”则不。
“爱国”主要是一个带有文化性的政治范畴,作为政治范畴的“爱国主义”并不必然要求对“传统”的忠诚。
换言之,爱传统和反传统,都可以构成“爱国主义”的表现,但激烈的全面的反传统,即便在当时也难以被“民族主义”同道所容纳,甚至连激烈反传统者自身也不会去进行这种自我身份认同。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批评民族主义或至少不愿认同民族主义价值的人,却可以也愿意声称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或不是“非爱国者”的原因(19)。
在这方面,五四时期以激烈反传统著称的陈独秀、鲁迅,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鼓吹“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和胡适等,可谓突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激烈和全方位反传统之际,恰恰并不以“民族主义”相标榜,而明明自觉地认同于与民主民族建国取向并不必然矛盾的“世界主义”。
在近代中国,如果说改革导向的“国语”运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关怀,那么保守取向的“国学”运动则较多地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学术追求和时代特色。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别与联系。
还有,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中,以“中华民族”为主要符号标志,在通常所谓的“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的双重认同并存的局面,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现象和特色。
这种双重认同曾不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困扰,不过在抗日战争的血火洗礼中,其整体认同最终还是得以形成并不断趋于巩固。
值得指出的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也曾有所差别。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曾一度机械地按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将整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全体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同时,把国内包括汉族在内、清末以来特别是民国之初即已普遍取得现代“民族”称谓和身份的满、蒙、回、藏(20)等转称为“宗族”,结果遭到许多抵制;相比之下,中共在基于长期历史文化和血缘交流关系的政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似更显政治智慧(21);潘光旦等社会学家在介于“种族”和“国家”之间互动内涵的“民族”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有其学理创造性。
当然,还有其他的理解。
不过,不管当时作为认同主体的中国人所秉持的“民族”概念有何差别,也不论学者们对此认同过程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华民族”的共同符号的确最终成为了现代中国各民族普遍认同的身份象征,完全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也终于诞生。
这无疑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问题上,笔者不太赞同那些过于夸大认同者的主观人为性“建构”努力,而较为轻视历史文化重要影响和制约因素的认识倾向。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许多也曾具有双重“民族”认同的历史。
一方面他们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而同时又无不想或实际上入主内地和中原,接受或至少是部分接受汉族的制度和文化,从而表现出对包涵庞大汉族在内的“大中国”的认同。
这一点,在满族建立的大清朝的历史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雍正皇帝亲撰并发布的《大义觉迷录》可谓这种双重认同的绝佳文本。
清末当西方现代“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之初,不仅在梁启超、杨度等汉族知识分子那里激起一种各民族基础上建成“大民族”共同体的构想,在满蒙回等一些留日学生那里,也同时出现过类似的观念,这种现象便实在绝非偶然(22),它对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基础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三、“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思想分析力度强化之需求
长期以来,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吸引中外学者共同兴趣的学术领域,特别在西方汉学界,作为一种认知工具的“民族主义”,还一直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家们最惯见而又常常能使其研究新见迭出的视角。
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方法的介入,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开始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总体而言,“民族主义”由原来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等传统史学领域分别研究的问题,逐渐变成了一个真正跨领域综合把握的历史对象。
所谓“新文化史”或称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文化”的大视角出发,始终关注文化与政治、社会一体化互动的主体“实践”(Practice)史,重视揭示思想观念的社会化过程及其功能。
就其追求而言,它乃是一种力图将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关怀结合起来的史学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引入之后,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过去的研究通常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思想形态来把握,“问题意识”是认知它如何形成,又如何具体渗透和影响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具体领域历史发展的进程;“新文化史”的有关研究,则不仅将民族主义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形态,同时还将它直接视作为一种连接心态、思想,并贯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主体社会化“实践”,研究者除了原有的那些问题意识并对其加以调整之外,某种程度上还特别关心政治和文化诸领域如何因“民族主义”而互动的历史情形。
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大体以这种“新文化史”的追求来关照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课题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也是五花八门、互有差异(23),但总的说来,这种方法的引入还是有助于克服以往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使相关的探究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活力,不仅扩展了关注范围,提高了综合深度,也在整体上推进了研究的进展。
这是因为,“新文化史”方法的综合性,正好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现象集社会心理、价值倾向、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于一身,合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于一体的综合特点一拍即合。
在以新文化史的方法来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著中,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和英国牛津大学葛凯(KarlGerth)的《中国制造:
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两书,最见风采。
《唤醒中国》以“睡狮”被唤醒作为一语双关的民族主义隐寓,以国民革命的领导集团如何“唤醒”中国民众为研究主题,从立体角度全方位展开分析和论述,它既注重领导人的有关思想、政治和文化活动,更注重政府宣传机关和部门的结构、运作与功能,并将许多关于民族主义重要的思想问题如“阶级”与“民族”关系,民族利益的“代表”及其资格,以及“封建主义”等政治概念如何发挥民族主义作用等问题,置于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去把握,同时通过对一些涉及中外关系的特别事件如“临城劫车案”,美国新闻记者甘露德(R.Y.Gilbert)具有民族歧视性的作品《中国怎么了》等引起的风波之意义透视,来综合揭示此间“民族觉醒”的全息图景。
笔者阅读此书,对“新文化史”那种纵横捭阖、综合立体的研究风格留下极深印象。
应当承认,许多思想问题的民族主义意涵,也的确只有在这种多维历史关系的实际透析中,才能更好地了解与把握的(24)。
《中国制造》则从近现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民族国家”创建之历史关系的独特角度,生动地揭示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成长及其影响问题(25)。
该书关于“男性形象的民族化”、“女性消费群体的民族主义化”的讨论,将社会史的性别关注与传统思想文化史的“民族主义”关怀有机结合起来考察,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此外,该书以民族资本家吴蕴初为例对“塑造爱国企业家”问题的讨论;以“民族主义商品展览会”为例对所谓“民族主义视觉认知”问题的论析等,也多新颖独到,别具匠心。
特别是书中精心选配的各种精彩的图片,不仅有助于揭示研究主题的内涵,还能使读者展开相关联想。
这也是新文化史研究能格外吸引人的魅力所在之一。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史的研究,近年来也有两部带有新文化史研究风格的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美国学者柯瑞达(RebeccaE.Karl)的《登上世界舞台: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26),一部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