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课时骆驼祥子赏析.docx
《第十四课时骆驼祥子赏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十四课时骆驼祥子赏析.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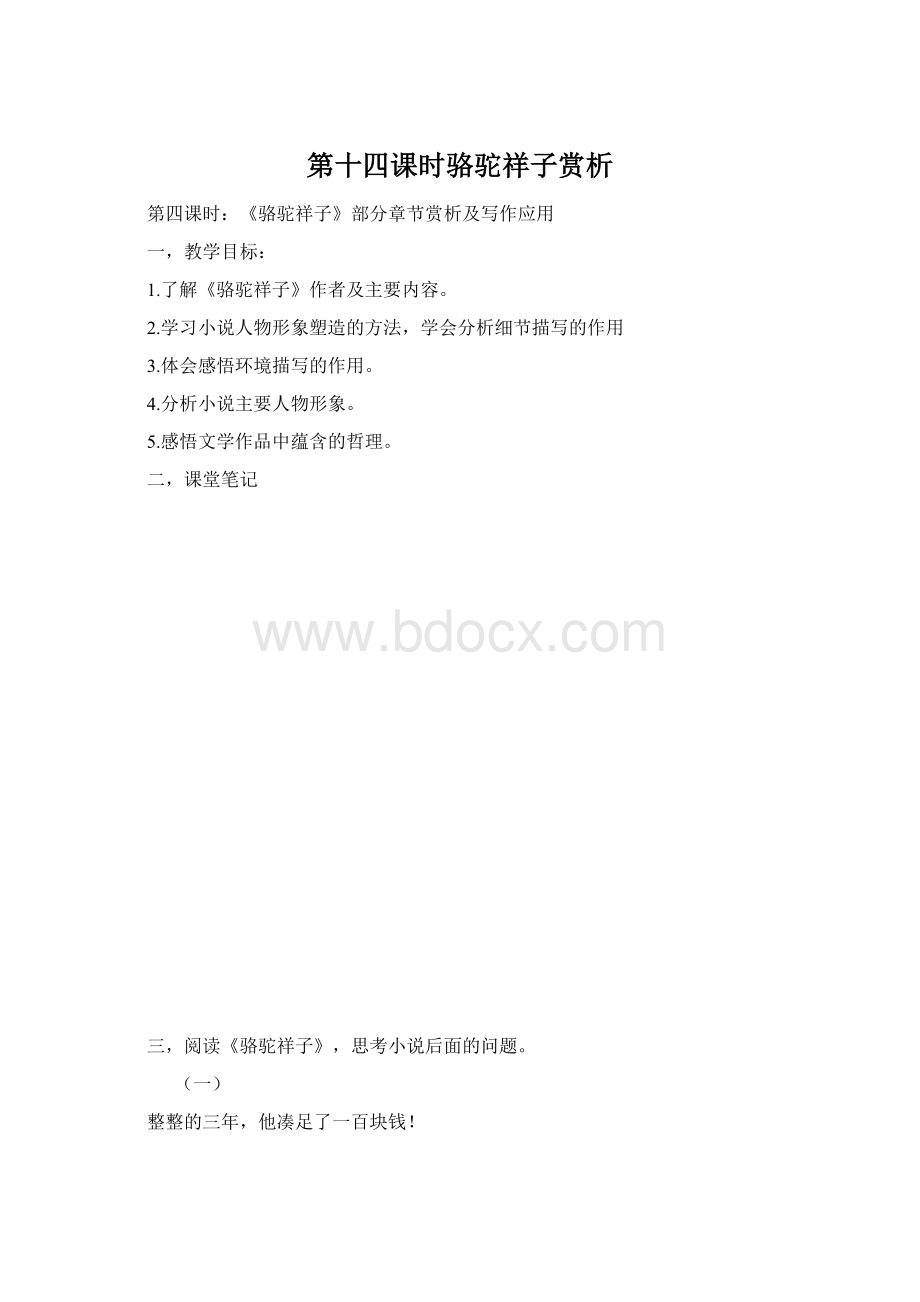
第十四课时骆驼祥子赏析
第四课时:
《骆驼祥子》部分章节赏析及写作应用
一,教学目标:
1.了解《骆驼祥子》作者及主要内容。
2.学习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学会分析细节描写的作用
3.体会感悟环境描写的作用。
4.分析小说主要人物形象。
5.感悟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哲理。
二,课堂笔记
三,阅读《骆驼祥子》,思考小说后面的问题。
(一)
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他不能再等了。
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
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
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作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
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
"我要这辆车!
"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
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
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
"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
"我要这辆车,九十六!
"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祥子,叹了口气:
"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保六个月:
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修理;保单,拿着!
"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
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
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
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
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
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
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
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
祥子有主意:
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
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
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
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
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他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
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
拉了半年,他的希望更大了:
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
①车口,即停车处。
②拉晚儿,是下午四点以后出车,拉到天亮以前。
③嚼谷,即吃用。
④从前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交民巷。
⑤胶皮团,指拉车这一行。
⑥杀进腰,把腰部勒得细一些。
⑦一边儿,即同样的。
⑧主儿,即是人。
这里是指包车的主人。
⑨饭局,即宴会。
⑩吹,就是散了,完了的意思。
(二)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
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
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
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
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
。
。
。
。
。
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
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
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
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
"前门,东车站!
""哪儿?
""东——车——站!
""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
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祥子把车拉出城去。
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东西已都涨了价,可是战事似乎还在老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打到北平来。
祥子还照常拉车,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
有一天,拉到了西城,他看出点棱缝来。
在护国寺街西口和新街口没有一个招呼"西苑哪?
清华呀?
"的。
在新街口附近他转悠了一会儿。
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西直门外正在抓车,大车小车骡车洋车一齐抓。
他想喝碗茶就往南放车;车口的冷静露出真的危险,他有相当的胆子,但是不便故意的走死路。
正在这个接骨眼儿,从南来了两辆车,车上坐着的好象是学生。
拉车的一边走,一边儿喊:
"有上清华的没有?
嗨,清华!
"
车口上的几辆车没有人答碴儿,大家有的看着那两辆车淡而不厌的微笑,有的叼着小烟袋坐着,连头也不抬。
那两辆车还继续的喊:
"都哑吧了?
清华!
"
"两块钱吧,我去!
"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
"拉过来!
再找一辆!
"那两辆车停住了。
年轻光头的楞了一会儿,似乎不知怎样好了。
别人还都不动。
祥子看出来,出城一定有危险,要不然两块钱清华——平常只是二三毛钱的事儿——为什么会没人抢呢?
他也不想去。
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他就豁出去了;他一眼看中了祥子:
"大个子,你怎样?
"
"大个子"三个字把祥子招笑了,这是一种赞美。
他心中打开了转儿:
凭这样的赞美,似乎也应当捧那身矮胆大的光头一场;再说呢,两块钱是两块钱,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
危险?
难道就那样巧?
况且,前两天还有人说天坛住满了兵;他亲眼看见的,那里连个兵毛儿也没有。
这么一想,他把车拉过去了。
拉到了西直门,城洞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
祥子的心凉了一些。
光头也看出不妙,可是还笑着说:
"招呼吧①,伙计!
是福不是祸②,今儿个就是今儿个③啦!
"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了,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
出了西直门,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祥子低下头去,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
他的心好象直顶他的肋条。
到了高亮桥,他向四围打了一眼,并没有一个兵,他又放了点心。
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他盘算着,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俏的事。
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可是这阵儿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街上清静得真可怕。
"抄土道走吧?
马路上——"
"那还用说,"矮子猜到他的意思,"自要一上了便道,咱们就算有点底儿了!
"
还没拉到便道上,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
虽然已到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夜里的寒气可还不是一件单衫所能挡得住的。
祥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累赘,除了一件灰色单军服上身,和一条蓝布军裤,都被汗沤得奇臭——自从还没到他身上的时候已经如此。
由这身破军衣,他想起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与那套阴丹士林蓝的夹裤褂;那是多么干净体面!
是的,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阴丹士林蓝更体面的东西,可是祥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已经是怎样的不容易。
闻着现在身上的臭汗味,他把以前的挣扎与成功看得分外光荣,比原来的光荣放大了十倍。
他越想着过去便越恨那些兵们。
他的衣服鞋帽,洋车,甚至于系腰的布带,都被他们抢了去;只留给他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和满脚的疱!
不过,衣服,算不了什么;身上的伤,不久就会好的。
他的车,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没了!
自从一拉到营盘里就不见了!
以前的一切辛苦困难都可一眨眼忘掉,可是他忘不了这辆车!
吃苦,他不怕;可是再弄上一辆车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至少还得几年的工夫!
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
祥子落了泪!
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
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
凭什么?
"凭什么?
"他喊了出来。
这一喊——虽然痛快了些——马上使他想起危险来。
别的先不去管吧,逃命要紧!
他在哪里呢?
他自己也不能正确的回答出。
这些日子了,他随着兵们跑,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
走,得扛着拉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站住,他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
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心中成了块空白。
到了夜晚,头一挨地他便象死了过去,而永远不再睁眼也并非一定是件坏事。
最初,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
及至到了后山,他只顾得爬山了,而时时想到不定哪时他会一交跌到山涧里,把骨肉被野鹰们啄尽,不顾得别的。
在山中绕了许多天,忽然有一天山路越来越少,当太阳在他背后的时候,他远远的看见了平地。
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有几个扛着枪的牵来几匹骆驼。
。
。
。
。
。
。
(三)
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
他在世界上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条命。
就是地上的一根麻绳,他也乐意拾起来,即使没用,还能稍微安慰他一下,至少他手中有条麻绳,不完全是空的。
逃命是要紧的,可是赤裸裸的一条命有什么用呢?
他得带走这几匹牲口,虽然还没想起骆驼能有什么用处,可是总得算是几件东西,而且是块儿不小的东西。
他把骆驼拉了起来。
对待骆驼的方法,他不大晓得,可是他不怕它们,因为来自乡间,他敢挨近牲口们。
骆驼们很慢很慢的立起来,他顾不得细调查它们是不是都在一块儿拴着,觉到可以拉着走了,他便迈开了步,不管是拉起来一个,还是全"把儿"。
。
。
。
。
。
。
村犬向他叫,他没大注意;妇女和小孩儿们的注视他,使他不大自在了。
他必定是个很奇怪的拉骆驼的,他想;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这样呆呆的看着他呢?
他觉得非常的难堪:
兵们不拿他当个人,现在来到村子里,大家又看他象个怪物!
他不晓得怎样好了。
他的身量,力气,一向使他自尊自傲,可是在过去的这些日子,无缘无故的他受尽了委屈与困苦。
他从一家的屋脊上看过去,又看见了那光明的太阳,可是太阳似乎不象刚才那样可爱了!
村中的唯一的一条大道上,猪尿马尿与污水汇成好些个发臭的小湖,祥子唯恐把骆驼滑倒,很想休息一下。
道儿北有个较比阔气的人家,后边是瓦房,大门可是只拦着个木栅,没有木门,没有门楼。
祥子心中一动;瓦房——财主;木栅而没门楼——养骆驼的主儿!
好吧,他就在这儿休息会儿吧,万一有个好机会把骆驼打发出去呢!
"色!
色!
色!
"祥子叫骆驼们跪下;对于调动骆驼的口号,他只晓得"色……"是表示跪下;他很得意的应用出来,特意叫村人们明白他并非是外行。
骆驼们真跪下了,他自己也大大方方的坐在一株小柳树下。
大家看他,他也看大家;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足以减少村人的怀疑。
坐了一会儿,院中出来个老者,蓝布小褂敞着怀,脸上很亮,一看便知道是乡下的财主。
祥子打定了主意:
"老者,水现成吧?
喝碗!
"
"啊!
"老者的手在胸前搓着泥卷,打量了祥子一眼,细细看了看三匹骆驼。
"有水!
哪儿来的?
"
"西边!
"祥子不敢说地名,因为不准知道。
"西边有兵呀?
"老者的眼盯住祥子的军裤。
"教大兵裹了去,刚逃出来。
"
"啊!
骆驼出西口没什么险啦吧?
"
"兵都入了山,路上很平安。
"
"嗯!
"老者慢慢点着头。
"你等等,我给你拿水去。
"
祥子跟了进去。
到了院中,他看见了四匹骆驼。
"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一把儿吧?
"
"哼!
一把儿?
倒退三十年的话,我有过三把儿!
年头儿变了,谁还喂得起骆驼!
"老头儿立住,呆呆的看着那四匹牲口。
待了半天:
"前几天本想和街坊搭伙,把它们送到口外去放青③。
东也闹兵,西也闹兵,谁敢走啊!
在家里拉夏吧,看着就焦心,看着就焦心,瞧这些苍蝇!
赶明儿天大热起来,再加上蚊子,眼看着好好的牲口活活受罪,真!
"老者连连的点头,似乎有无限的感慨与牢骚。
"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成一把儿到口外去放青。
欢蹦乱跳的牲口,一夏天在这儿,准教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
"祥子几乎是央求了。
"可是,谁有钱买呢?
这年头不是养骆驼的年头了!
"
"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把它们出了手,好到城里去谋生!
"
老者又细细看了祥子一番,觉得他绝不是个匪类。
然后回头看了看门外的牲口,心中似乎是真喜欢那三匹骆驼——明知买到手中并没好处,可是爱书的人见书就想买,养马的见了马就舍不得,有过三把儿骆驼的也是如此。
况且祥子说可以贱卖呢;懂行的人得到个便宜,就容易忘掉东西买到手中有没有好处。
"小伙子,我要是钱富裕的话,真想留下!
"老者说了实话。
"干脆就留下吧,瞧着办得了!
"祥子是那么诚恳,弄得老头子有点不好意思了。
"说真的,小伙子;倒退三十年,这值三个大宝;现在的年头,又搭上兵荒马乱,我——你还是到别处吃喝吆喝去吧!
"
"给多少是多少!
"祥子想不出别的话。
他明白老者的话很实在,可是不愿意满世界去卖骆驼——卖不出去,也许还出了别的毛病。
"你看,你看,二三十块钱真不好说出口来,可是还真不容易往外拿呢;这个年头,没法子!
"
祥子心中也凉了些,二三十块?
离买车还差得远呢!
可是,第一他愿脆快办完,第二他不相信能这么巧再遇上个买主儿。
"老者,给多少是多少!
"
"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看得出,你不是干这一行的!
"
祥子说了实话。
"呕,你是拿命换出来的这些牲口!
"老者很同情祥子,而且放了心,这不是偷出来的;虽然和偷也差不远,可是究竟中间还隔着层大兵。
兵灾之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着常理儿说。
"这么着吧,伙计,我给三十五块钱吧;我要说这不是个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拿一块,也是个小狗子!
我六十多了;哼,还教我说什么好呢!
"
祥子没了主意。
对于钱,他向来是不肯放松一个的。
可是,在军队里这些日子,忽然听到老者这番诚恳而带有感情的话,他不好意思再争论了。
况且,可以拿到手的三十五块现洋似乎比希望中的一万块更可靠,虽然一条命只换来三十五块钱的确是少一些!
就单说三条大活骆驼,也不能,绝不能,只值三十五块大洋!
可是,有什么法儿呢!
"骆驼算你的了,老者!
我就再求一件事,给我找件小褂,和一点吃的!
"
"那行!
"
祥子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拿着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两个棒子面饼子,穿着将护到胸际的一件破白小褂,要一步迈到城里去!
①谱儿,即样子。
有近似的意思。
②大宝,重五十两的银元宝。
③放青,放牧牲口去吃青草。
(四)
祥子在海甸的一家小店里躺了三天,身上忽冷忽热,心中迷迷忽忽,牙床上起了一溜紫泡,只想喝水,不想吃什么。
饿了三天,火气降下去,身上软得象皮糖似的。
恐怕就是在这三天里,他与三匹骆驼的关系由梦话或胡话中被人家听了去。
一清醒过来,他已经是"骆驼祥子"了。
自从一到城里来,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没有个姓;如今,"骆驼"摆在"祥子"之上,就更没有人关心他到底姓什么了。
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
不过,三条牲口才换了那么几块钱,而自己倒落了个外号,他觉得有点不大上算。
。
。
。
。
。
。
打扮好了,一共才花了两块二毛钱。
近似搪布①的一身本色粗布裤褂一元,青布鞋八毛,线披儿织成的袜子一毛五,还有顶二毛五的草帽。
脱下来的破东西换了两包火柴。
拿着两包火柴,顺着大道他往西直门走。
没走出多远,他就觉出软弱疲乏来了。
可是他咬上了牙。
他不能坐车,从哪方面看也不能坐车:
一个乡下人拿十里八里还能当作道儿吗,况且自己是拉车的。
这且不提,以自己的身量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笑话;除非一交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他满地滚也得滚进城去,决不服软!
今天要是走不进城去,他想,祥子便算完了;他只相信自己的身体,不管有什么病!
晃晃悠悠的他放开了步。
走出海甸不远,他眼前起了金星。
扶着棵柳树,他定了半天神,天旋地转的闹慌了会儿,他始终没肯坐下。
天地的旋转慢慢的平静起来,他的心好似由老远的又落到自己的心口中,擦擦头上的汗,他又迈开了步。
已经剃了头,已经换上新衣新鞋,他以为这就十分对得起自己了;那么,腿得尽它的责任,走!
一气他走到了关厢。
看见了人马的忙乱,听见了复杂刺耳的声音,闻见了干臭的味道,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土,祥子想爬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
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
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
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
才到高亮桥西边,他坐在河岸上,落了几点热泪!
太阳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
河里没有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象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些微腥的潮味。
河岸北的麦子已吐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
河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
东边的桥上,来往的人与车过来过去,在斜阳中特别显着匆忙,仿佛都感到暮色将近的一种不安。
这些,在祥子的眼中耳中都非常的有趣与可爱。
只有这样的小河仿佛才能算是河;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
因为它们都属于北平。
坐在那里,他不忙了。
眼前的一切都是熟习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很乐意。
歇了老大半天,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
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的哆嗦。
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
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
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
"再来一碗!
"
站起来,他觉出他又象个人了。
太阳还在西边的最低处,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他痛快得要喊叫出来。
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摸了摸袋中的钱,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他硬把病忘了,把一切都忘了,好似有点什么心愿,他决定走进城去。
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各样的人,谁也不敢快走,谁可都想快快过去,鞭声,喊声,骂声,喇叭声,铃声,笑声,都被门洞儿——象一架扩音机似的——嗡嗡的联成一片,仿佛人人都发着点声音,都嗡嗡的响。
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西跨一步,两手左右的拨落,象条瘦长的大鱼,随浪欢跃那样,挤进了城。
一眼便看到新街口,道路是那么宽,那么直,他的眼发了光,和东边的屋顶上的反光一样亮。
他点了点头。
他的铺盖还在西安门大街人和车厂呢,自然他想奔那里去。
因为没有家小,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虽然并不永远拉厂子里的车。
人和的老板刘四爷是已快七十岁的人了;人老,心可不老实。
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
干这些营生所应有的资格与本领——力气,心路,手段,交际,字号等等——刘四爷都有。
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
跪上铁索,刘四并没皱一皱眉,没说一个饶命。
官司教他硬挺了过来,这叫作"字号"。
出了狱,恰巧入了民国,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刘四爷看出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儿,即使黄天霸再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
他开了个洋车厂子。
土混混出身,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
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②的。
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得迷迷忽忽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登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弄。
到现在,他有六十多辆车,至坏的也是七八成新的,他不存破车。
车租,他的比别家的大,可是到三节他比别家多放着两天的份儿。
人和厂有地方住,拉他的车的光棍儿,都可以白住——可是得交上车份儿,交不上账而和他苦腻的,他扣下铺盖,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
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只须告诉他一声,他不含忽,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这叫作"字号"。
刘四爷是虎相。
快七十了,腰板不弯,拿起腿还走个十里二十里的。
两只大圆眼,大鼻头,方嘴,一对大虎牙,一张口就象个老虎。
个子几乎与祥子一边儿高,头剃得很亮,没留胡子。
他自居老虎,可惜没有儿子,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
她也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人,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
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
刘四爷打外,虎妞打内,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
人和厂成了洋车界的权威,刘家父女的办法常常在车夫与车主的口上,如读书人的引经据典。
在买上自己的车以前,祥子拉过人和厂的车。
他的积蓄就交给刘四爷给存着。
把钱凑够了数,他要过来,买上了那辆新车。
"刘四爷,看看我的车!
"祥子把新车拉到人和厂去。
老头子看了车一眼,点了点头:
"不离!
"
"我可还得在这儿住,多咱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门!
"祥子颇自傲的说。
"行!
"刘四爷又点了点头。
于是,祥子找到了包月,就去住宅山;掉了事而又去拉散座,便住在人和厂。
不拉刘四爷的车,而能住在人和厂,据别的车夫看,是件少有的事。
因此,甚至有人猜测,祥子必和刘老头子是亲戚;更有人说,刘老头子大概是看上了祥子,而想给虎妞弄个招门纳婿的"小人"。
这种猜想里虽然怀着点妒羡,可是万一要真是这么回事呢,将来刘四爷一死,人和厂就一定归了祥子。
这个,教他们只敢胡猜,而不敢在祥子面前说什么不受听的。
其实呢,刘老头子的优待祥子是另有笔账儿。
祥子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
假若他去当了兵,他决不会一穿上那套虎皮,马上就不傻装傻的去欺侮人。
在车厂子里,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儿作。
他去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支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
厂子里靠常总住着二十来个车夫;收了车,大家不是坐着闲谈,便是蒙头大睡;祥子,只有祥子的手不闲着。
初上来,大家以为他是向刘四爷献殷勤,狗事巴结人;过了几天,他们看出来他一点没有卖好讨俏的意思,他是那么真诚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刘老头子没有夸奖过他一句,没有格外多看过他一眼;老头子心里有数儿。
他晓得祥子是把好手,即使不拉他的车,他也还愿意祥子在厂子里。
有祥子在这儿,先不提别的院子与门口永远扫得干干净净。
虎妞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儿,她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不和她争辩;别的车夫,因为受尽苦楚,说话总是横着来;她一点不怕他们,可是也不愿多搭理他们;她的话,所以,都留给祥子听。
当祥子去拉包月的时候,刘家父女都仿佛失去一个朋友。
赶到他一回来,连老头子骂人也似乎更痛快而慈善一些。
祥子拿着两包火柴,进了人和厂。
天还没黑,刘家父女正在吃晚饭。
看见他进来,虎妞把筷子放下了:
"祥子!
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
"
"哼!
"祥子没说出什么来。
刘四爷的大圆眼在祥子身上绕了绕,什么也没说。
祥子戴着新草帽,坐在他们对面。
"你要是还没吃了的话,一块儿吧!
"虎妞仿佛是招待个好朋友。
祥子没动,心中忽然感觉到一点说不出来的亲热。
一向他拿人和厂当作家:
拉包月,主人常换;拉散座,座儿一会儿一改;只有这里老让他住,老有人跟他说些闲话儿。
现在刚逃出命来,又回到熟人这里来,还让他吃饭,他几乎要怀疑他们是否要欺弄他,可是也几乎落下泪来。
"刚吃了两碗老豆腐!
"他表示出一点礼让。
"你干什么去了?
"刘四爷的大圆眼还盯着祥子。
"车呢?
"
"车?
"祥子啐了口吐沫。
"过来先吃碗饭!
毒不死你!
两碗老豆腐管什么事?
!
"虎妞一把将他扯过去,好象老嫂子疼爱小叔那样。
祥子没去端碗,先把钱掏了出来:
"四爷,先给我拿着,三十块。
"把点零钱又放在衣袋里。
刘四爷用眉毛梢儿问了句,"哪儿来的?
"
祥子一边吃,一边把被兵拉去的事说了一遍。
"哼,你这个傻小子!
"刘四爷听完,摇了摇头。
"拉进城来,卖给汤锅,也值十几多块一头;要是冬天驼毛齐全的时候,三匹得卖六十块!
"
祥子早就有点后悔,一听这个,更难过了。
可是,继而一想,把三只活活的牲口卖给汤锅去挨刀,有点缺德;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就都该活着。
什么也没说,他心中平静了下去。
虎姑娘把家伙撤下去,刘四爷仰着头似乎是想起点来什么。
忽然一笑,露出两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
"傻子,你说病在了海甸?
为什么不由黄村大道一直回来?
"
"还是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