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docx
《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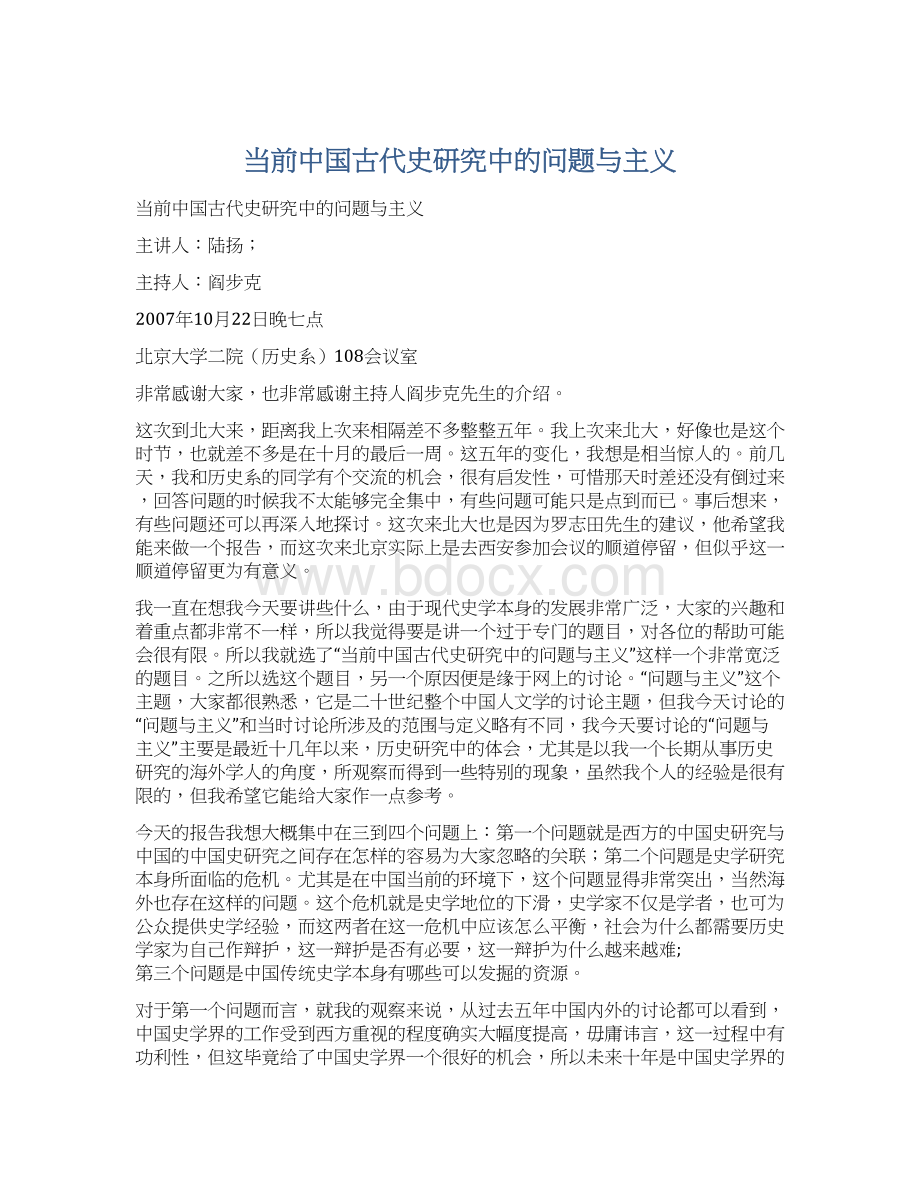
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
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
主讲人:
陆扬;
主持人:
阎步克
2007年10月22日晚七点
北京大学二院(历史系)108会议室
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主持人阎步克先生的介绍。
这次到北大来,距离我上次来相隔差不多整整五年。
我上次来北大,好像也是这个时节,也就差不多是在十月的最后一周。
这五年的变化,我想是相当惊人的。
前几天,我和历史系的同学有个交流的机会,很有启发性,可惜那天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不太能够完全集中,有些问题可能只是点到而已。
事后想来,有些问题还可以再深入地探讨。
这次来北大也是因为罗志田先生的建议,他希望我能来做一个报告,而这次来北京实际上是去西安参加会议的顺道停留,但似乎这一顺道停留更为有意义。
我一直在想我今天要讲些什么,由于现代史学本身的发展非常广泛,大家的兴趣和着重点都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是讲一个过于专门的题目,对各位的帮助可能会很有限。
所以我就选了“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这样一个非常宽泛的题目。
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另一个原因便是缘于网上的讨论。
“问题与主义”这个主题,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二十世纪整个中国人文学的讨论主题,但我今天讨论的“问题与主义”和当时讨论所涉及的范围与定义略有不同,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与主义”主要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历史研究中的体会,尤其是以我一个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海外学人的角度,所观察而得到一些特别的现象,虽然我个人的经验是很有限的,但我希望它能给大家作一点参考。
今天的报告我想大概集中在三到四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之间存在怎样的容易为大家忽略的关联;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研究本身所面临的危机。
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当然海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个危机就是史学地位的下滑,史学家不仅是学者,也可为公众提供史学经验,而这两者在这一危机中应该怎么平衡,社会为什么都需要历史学家为自己作辩护,这一辩护是否有必要,这一辩护为什么越来越难;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身有哪些可以发掘的资源。
对于第一个问题而言,就我的观察来说,从过去五年中国内外的讨论都可以看到,中国史学界的工作受到西方重视的程度确实大幅度提高,毋庸讳言,这一过程中有功利性,但这毕竟给了中国史学界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未来十年是中国史学界的关键十年,一是要使自己的各种研究更成熟,二是中国史学界要更愿意与外界交流、对话,这并不是说要接受外界的看法,而是要更清晰地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同时也要更愿意把中国史学本身变为世界史学经验的一部分,这对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历史研究都同样有意义。
这两天和阎步克、邓小南两位先生的交流给了我很多启发,虽然对他们的研究和著作我都较为熟悉,但交谈后对一个人的解读与单纯读他们的著作然后进行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交流给我的启发使我注意到史学界有个普遍的倾向,也就是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而回到西方中国史学研究的层面来说,大家有个普遍的看法是认为西方史学比较重视理论,中国史学比较注重实证,也就是注重材料的分析。
这个讲法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这个看法往往会影响到对西方史学的评估,也会影响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评估。
其实最近十年以来,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研究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由华语学者带领并渐渐影响到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其实在十年前,很少听到西方人提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学者,更少有对他们的研究。
我记得当时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知道陈寅恪的西方学者有我在普大的老师杜希德,他本来是想要跟陈寅恪先生读书的,但后来一直没有机会。
他的领域是隋唐史,除他而外很少有其他西方学者知道陈先生的名字。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还有一个例外竟然是罗马史专家——彼得·布朗(PeterBrown),他不但知道陈寅恪的名字,还大致知道陈先生的研究领域与观点。
但这些年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西方学者会把中国二十世纪学人的研究反复提出来,虽然他们的解读可能也存在问题,有这样那样的倾向,但中国学界的研究已经被认可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传统,西方史学界的研究也已绕不过已存在的这一传统。
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罗志田先生等等。
我个人觉得,这一研究传统中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的资源。
需要发掘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研究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中国二十世纪初史学上理论贡献最大的几个学派,一个是疑古学派,为顾颉刚先生倡导,还有傅斯年先生对国故的重整以及重建国史的工作,还有后来郭沫若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断代分析,等等。
这些学派本身的分别往往被简化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但实际上这种分法本身是将历史现象大大简化了,结果就是我们对很多问题存在误解,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判定。
比如陈寅恪的研究,应属于史料派还是史观派呢?
这是很难讲的。
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今天有很多,但很少有相当深入的探讨,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还未讲清:
比如陈先生为什么会对唐史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
我很少看到有人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大家似乎都认为这是个不需要解释的问题,但我恰恰以为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重要问题,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情况下对唐代历史产生这么大兴趣,并把他的主要精力转到这个方向上来?
还有个例子,陈寅恪先生在三十年代后期有过一个很有名的给清华学生出考题的掌故,因为他当时出的考题是对对子,他希望对对子成为国文考试的基本项目。
当然这引起了很多争议,后来他写了封信给刘叔雅(按:
即刘文典),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解释为什么要对对子。
这当然使对对子得到了很大的学术提升,但对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大家做的研究工作还是不够深入。
我唯一看过对这个问题有较深入探讨的是桑兵先生几年前的文章,可惜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从中西语文的文化差异角度来理解对对子,他认为当时非常强调传统的陈寅恪等博学学者都把语文作为一个文化的重要特征。
但事实上如果仔细去读陈寅恪的信的话,你会发现那只是很表面的内容,实质上,陈寅恪先生在承认对对子可以体现中国传统语言特征的同时,还提到了另外的问题,即好的上下联对对子几乎就像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应该存在“正-反-合”的关系。
我还没有看到就这一点进行探讨的文章。
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在这里探讨的也是一个史学问题,是他重要史学观点的表达,只是没有详细阐发而已。
大家看看陈先生特别提到的吴伟业的歌行中对句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他所说的对对子绝不是门联什么的简单对子,在他看来,那种对子的水平都是不够高的,即根本达不到“正-反-合”的境界。
他的所谓“正-反-合”的境界是指在语言上不仅完全对应,而且上下联意义要完成完整的叙述,就像吴伟业的歌行中的“南内方起看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那一联。
史学叙事的本质性问题就在这个小小的对子中体现了出来,这才是陈寅恪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只是很多人没有体会他的意思。
前几天有人提到陈平原先生的一个讲法,也就是郭沫若和傅斯年的区别,认为郭沫若代表了美国的汉学传统。
后来我回去想了想,这个转述也许并非陈平原先生的原意,但也体现了一个趋势,因为桑兵教授也提到过,西洋汉学发展到美国汉学是从实证的汉学发展到以社会科学为出发点的汉学。
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存在线性的危险,实际上很多重要的思想在早期的发展中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无疑受了疑古派的影响,而且他对《诗经》的解读不可能不受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影响,因为他对《诗经》的解读是完全象征化的,他眼中的《诗经》中的人和事就并非指对具体历史本身,而是象征某个系统或历史结构。
当然郭沫若先生也有他的原创性,但我还是认为他明显受了葛兰言的影响。
而且我还认为早期西洋汉学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也是有其理论取向的。
这些理论取向到今天已经逐渐被吸纳到新的理论体系中间,比如今天研究《诗经》,更多是从象征性的角度去读,我们很难说大家是直接受葛兰言的影响,但确实最早创发于他的解读。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方法,但不得不去面对他的方法,包括后来的闻一多先生,他的很多处理就很像葛兰言,但比葛兰言要做得精确,有些细节更富创见。
大家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即认为西方史学重视理论,中国史学的长处不在理论。
我觉得这种讲法是有问题的,至少从经验层面上来讲,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就我接触到的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而言,很多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史学家实际上对理论并不重视,而且绝大部分人事实上没有受过很系统的理论训练,更多的是在职业训练中形成了某种表述史学观点、分析解释文献的共识。
他们重视的并不是理论,相反还有人是反对理论的。
尤其是七十年代开始领导史学领域的学者,他们对理论并不感兴趣,而且对理论的运用也并不系统。
即便是费正清的研究,虽说用了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但有非常清楚的证据表明他并没有真正细读过帕森斯的作品,只是作为同事跟帕森斯聊过一次,并接受了部分观点并用到自己的研究中。
所以,很多西方学者对理论还是保持了很大的距离的,相反,倒是中国学者对理论的重视有时还超过西方学者。
因此,我认为这一点还是有必要澄清的,毕竟这一误解可能会影响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评判。
因为西方学者也有从他们立场而来的成见,他们会假定自己的研究在知识掌握上不如中国学者,但同时会认为中国学者即使渊博,其深度还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偏见,即使是现在也依然根深蒂固。
我对这一点很不满意,因为它会影响到各个层面,因此首先有必要打破中国学界对西方学者认识上的误区,也同样有必要打破西方学界对中国学者认识的误区。
这个工作必须由中国学者采取主动,来彻底改变这些印象。
还有个问题是运用理论与中国史学的结合。
有一个近期发生的例子,余英时先生前几年出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后,西方学者对这部著作产生特别的重视。
余先生的著作当然涉及很多内容,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对朱熹及其追随者和同盟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他在研究中借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孝宗为什么会对高宗特别孝顺,又想改变高宗时代的政治格局的怪异行为。
我注意到汉语世界和西方学界对余先生的评价,都特别提到了“心理史学”,认为将它运用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有一点过于冒险。
其实余先生也讲过,这是西方背景下产生的史学理论,他在运用的时候不得不作适当的调整来适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特点。
但汉语世界和西方的学者很多人甚至都认为“心理史学”本身就是个富有争议性的理论,更不用说将它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
就这个问题我在两三年前特别请教过余先生,也就是“心理史学”如何能在这样的场合下使用。
他就给了我一个非常简洁的回答,他说,“实际上,这不完全是心理史学的问题,而是在史学研究上如何借鉴概念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记载中没有这样的简洁概念来表述对父母心里的复杂性,都用孝来概括,但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是普遍存在比如因为过于孝顺而产生逆反的心理的。
”在中国社会中的一些表述和谚语实际也是要呈现出这种逆反心里的,但这些表述就是没有类似心理学上的概念来得简洁。
所以余先生只是借鉴了这些词汇和概念来更有效地表达一些很特殊的情感和心理状态,而在他的分析中,实际大量运用的是传统的史料,“心理史学”只是其表层而不是其分析的基础,也就是说,完全可以不用这一概念,但一旦用了,可以更有力地表达和概括。
所以说,运用理论本身并不是一定对理论有特殊的认可,而实际上重视的是理论的概括能力。
回到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中国学者的研究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往往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不能完成跳跃,他不能把自己最精彩的东西整合起来,让别人感受到他史学的力量。
也就是说,其研究最精彩的问题需要别人来帮他表达,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西方学者很多时候会在这个地方取巧,他们会把中国学者的研究完全接受过来,再转换一种语言,用更符合现代史学的方式将其精义表述出来。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也让人误以为西方学者能将这些问题讲得更清楚,实际上基本工作和史料解读往往并不是西方学者做的。
比如史景迁的作品很好,但他的工作往往是依赖二手文献,他的解读依赖于其他学者的工作,其本身没有做原始文献的解读,这就使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