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欲的交错解读《透明的红萝卜》的隐喻色彩.docx
《灵与欲的交错解读《透明的红萝卜》的隐喻色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灵与欲的交错解读《透明的红萝卜》的隐喻色彩.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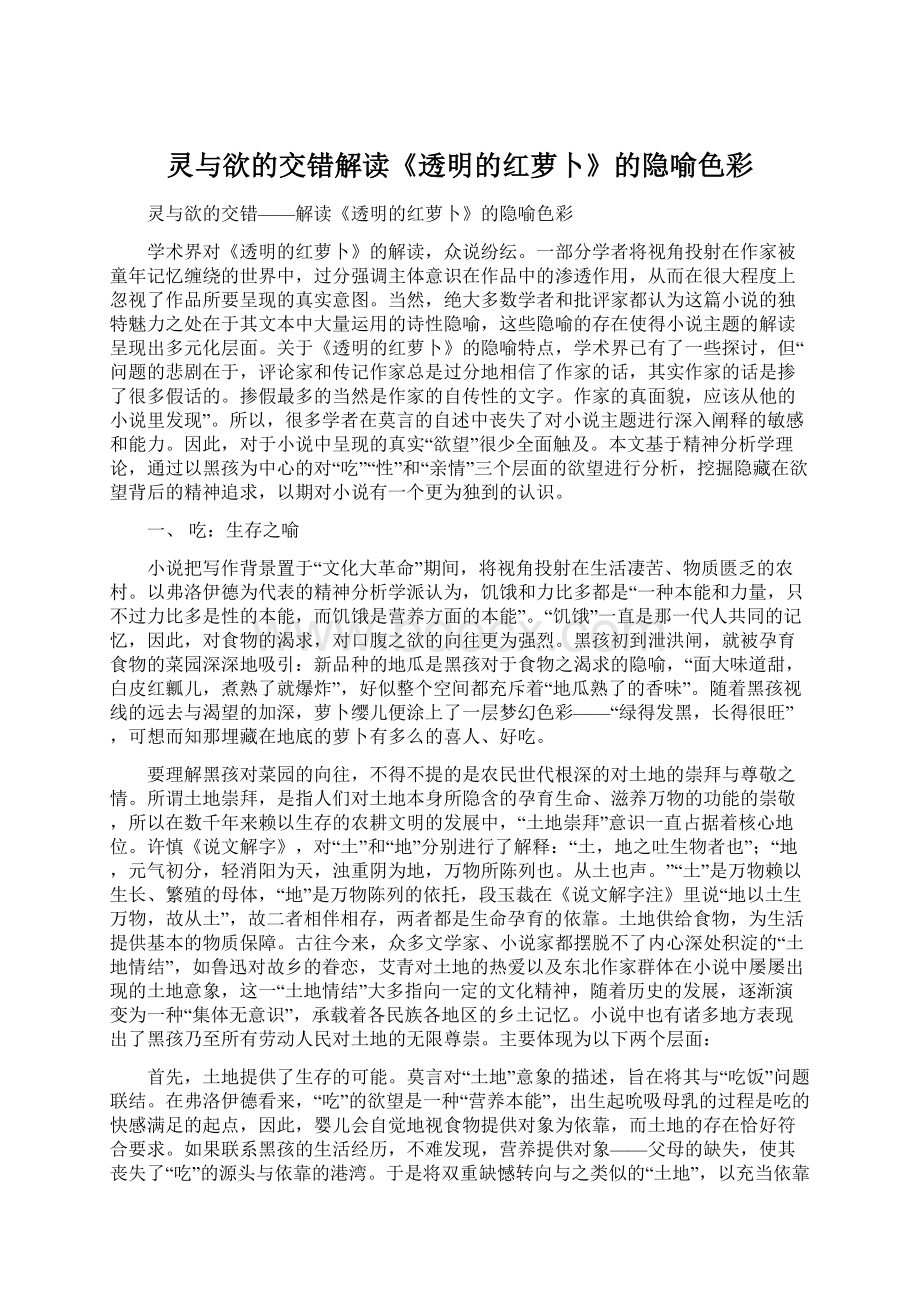
灵与欲的交错解读《透明的红萝卜》的隐喻色彩
灵与欲的交错——解读《透明的红萝卜》的隐喻色彩
学术界对《透明的红萝卜》的解读,众说纷纭。
一部分学者将视角投射在作家被童年记忆缠绕的世界中,过分强调主体意识在作品中的渗透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品所要呈现的真实意图。
当然,绝大多数学者和批评家都认为这篇小说的独特魅力之处在于其文本中大量运用的诗性隐喻,这些隐喻的存在使得小说主题的解读呈现出多元化层面。
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隐喻特点,学术界已有了一些探讨,但“问题的悲剧在于,评论家和传记作家总是过分地相信了作家的话,其实作家的话是掺了很多假话的。
掺假最多的当然是作家的自传性的文字。
作家的真面貌,应该从他的小说里发现”。
所以,很多学者在莫言的自述中丧失了对小说主题进行深入阐释的敏感和能力。
因此,对于小说中呈现的真实“欲望”很少全面触及。
本文基于精神分析学理论,通过以黑孩为中心的对“吃”“性”和“亲情”三个层面的欲望进行分析,挖掘隐藏在欲望背后的精神追求,以期对小说有一个更为独到的认识。
一、吃:
生存之喻
小说把写作背景置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将视角投射在生活凄苦、物质匮乏的农村。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饥饿和力比多都是“一种本能和力量,只不过力比多是性的本能,而饥饿是营养方面的本能”。
“饥饿”一直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因此,对食物的渴求,对口腹之欲的向往更为强烈。
黑孩初到泄洪闸,就被孕育食物的菜园深深地吸引:
新品种的地瓜是黑孩对于食物之渴求的隐喻,“面大味道甜,白皮红瓤儿,煮熟了就爆炸”,好似整个空间都充斥着“地瓜熟了的香味”。
随着黑孩视线的远去与渴望的加深,萝卜缨儿便涂上了一层梦幻色彩——“绿得发黑,长得很旺”,可想而知那埋藏在地底的萝卜有多么的喜人、好吃。
要理解黑孩对菜园的向往,不得不提的是农民世代根深的对土地的崇拜与尊敬之情。
所谓土地崇拜,是指人们对土地本身所隐含的孕育生命、滋养万物的功能的崇敬,所以在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农耕文明的发展中,“土地崇拜”意识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
许慎《说文解字》,对“土”和“地”分别进行了解释:
“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地,元气初分,轻消阳为天,浊重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
从土也声。
”“土”是万物赖以生长、繁殖的母体,“地”是万物陈列的依托,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说“地以土生万物,故从土”,故二者相伴相存,两者都是生命孕育的依靠。
土地供给食物,为生活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
古往今来,众多文学家、小说家都摆脱不了内心深处积淀的“土地情结”,如鲁迅对故乡的眷恋,艾青对土地的热爱以及东北作家群体在小说中屡屡出现的土地意象,这一“土地情结”大多指向一定的文化精神,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承载着各民族各地区的乡土记忆。
小说中也有诸多地方表现出了黑孩乃至所有劳动人民对土地的无限尊崇。
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土地提供了生存的可能。
莫言对“土地”意象的描述,旨在将其与“吃饭”问题联结。
在弗洛伊德看来,“吃”的欲望是一种“营养本能”,出生起吮吸母乳的过程是吃的快感满足的起点,因此,婴儿会自觉地视食物提供对象为依靠,而土地的存在恰好符合要求。
如果联系黑孩的生活经历,不难发现,营养提供对象——父母的缺失,使其丧失了“吃”的源头与依靠的港湾。
于是将双重缺憾转向与之类似的“土地”,以充当依靠。
一望无垠的黄泥地,可以生出“白皮红瓤”的地瓜、“金灿灿”的红萝卜、密密麻麻的黄麻,等等。
在尚未成年的黑孩视域里,土地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够满足人“吃的欲望”。
基于此,吃的满足滋生了他对土地的认同,好似婴儿时期在母亲怀里吮吸母乳那样安全、快乐。
其次,土地所承载的是超越普通生存意识的人类精神的家园与归属。
莫言多次提到,他既憎恨那片土地,又诚然离不开它。
“虽然我身在异乡,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对故乡的记忆里。
”如果说对故乡的这份独特的情感在许多年后才渐渐领悟,那写作《透明的红萝卜》时,已暗暗埋下了这颗矛盾的种子。
矛盾在于爱恨的交织:
恨是基于生活在故土时期承受的身心伤害,留下了既吃不饱,又得不到足够疼爱的童年记忆;爱是源于对故乡对土地深深的眷恋与依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故乡是根的发源地,是灵魂的孕育所,是精神放飞的家园。
莫言揭示的是“土地”与农民世世代代积淀的血脉联系,土地是农民满足“吃的欲望”的供给源,是其生存生活的保障,是中国农民的家园与归宿。
所以,当黑孩的手指被砸伤时义无反顾地选择用“土”来疗伤。
受尽嘲讽与伤害的黑孩,对世界对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意识,对人性充满了敌对情绪,但他丝毫不畏惧、不怀疑生长食物解决饥饿的“土地”,他无条件地信奉着黄泥堆就的土地。
他不相信菊子嘴中说的“土里什么脏东西都有”,待伤口洗净包扎之后,“用牙齿咬开手绢的结儿,又用右手抓起一把土,按到伤指上。
”这种无条件的信奉后来魔怔似的传染了菊子,她推开给予关心的小石匠,“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按在伤口上。
”这些看似不经意或者说愚昧不堪的举动,都是农耕文明积淀的对土地的尊崇与信赖。
莫言将生存的渴望隐藏于吃饭问题之中,并将吃饭与土地联结,既体现了人类自身强烈的生存意志,也蕴含着每一个体心灵深处对故乡的精神眷恋。
这种对土地的眷恋超越生存,是积淀在中华儿女身上的精神力量,是潜藏在人类精神背后的绝对落定感与归属感。
二、性:
繁衍之喻
“性”在小说中占据了较大的篇幅,但是《透明的红萝卜》不是进行简单的性场面描写,而是通过诸多具有象征意味的喻体来隐喻、象征“性主体”自潜意识而发的对“性”的渴望。
因受制于年龄与思维,“性主体”的性意识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寻求身体刺激与性幻想以完成个体快感愉悦。
一部分评论家认为,莫言的小说过分强调性欲望,甚至达到迷狂与泛滥。
我们认为,莫言笔下的“性”的描绘一方面是对隐藏的本能欲望的揭露与剖析,即与精神分析学理论所持的“性是人类的本能”观点息息相通,“儿童的性经验总伴有焦急、禁律、失望、惩罚的痛苦印象”[4],莫言所做的正是对隐藏幼儿“性生活”的揭示;另一方面,它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意味,也具有繁衍、生殖的功能,是全人类生存、生活的源头。
莫言多年以后谈及《透明的红萝卜》的创作源泉时将它化为“梦”的启发。
其高明之处在于,通过梦的形式,将色彩的交混与内心欲望的奔腾置于梦境之中,既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以梦的世界来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营造出虚幻、不真实的艺术效果。
然而,梦是人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欲望的完整呈现,并祈求在梦中满足自身的欲望。
这一点,是莫言传达给我们最为有用的信息——以便于我们对作家“隐藏”起来的东西,把“无意识地嵌入到作品中的无意识”找出来,对作品作恰如其分的分析。
莫言梦中的世界,实则是小说世界里核心思想的缩影和提炼。
那么,这种需要在梦中完成的欲望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黑孩“性意识”的释放与生存、繁衍愿望的双重期待。
要揭示黑孩的“性欲望”,便要找出小说中隐含的“性”之象征。
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孩童自三岁起便有了性意识,莫言笔下的黑孩具有明显的这一特征。
首先,水的象征意味。
“水”是黑孩“性意识”由萌芽到完善的催化剂,暗含着“性”和“生殖”的行为。
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暗喻,“地瓜地和菜地变成一个方方的大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井的形状都是圆形,为什么作家笔下的黑孩眼中的井是“方方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长方形象征着男性生殖器,而圆形则象征着女性生殖器,男性与女性的结合暗含了性行为的开始①。
黑孩将“那些紫色的叶片,绿色的叶片”“三面的黄麻”都融进了井中,混合成了水。
黑孩好像那只变成“绿色翠鸟”的麻雀,捕捉着性结合后繁衍的“鱼虾”。
在此,水是性行为得以实现的催化剂。
除此之外,有关水与黑孩性意识的描写还有多处,遭到后娘打骂而去挑水时,在水中寻求愉快的抚慰,一刻不停地迎着将他“顶得趔趔趄趄”的河水,去感受“两条大腿之间有若干温柔的鱼嘴在吻他”;得到菊子的关爱,便情不自禁地去捕捉“河上发亮的气体”“奇异的声音”;受不了老铁匠的离去,在水中“试探着,摸索着,寻找着”。
河水一方面像一剂良药抚慰了黑孩现实的遭际,后娘的打骂、父性代表的离去,在“性欲”的释放中得到了很好的纾解。
另一方面,河水如同欲望的催化剂,浇灌着黑孩心中点燃的星星之火,向着熊熊大火的生长。
所以,水是黑孩追寻快乐的乐园,也是其释放痛苦的场所。
其次,火的象征意味。
小说中的“火”是欲望的象征,因其视觉感官上呈现为“红色”和“黄色”,故而文中出现的红、黄颜色与“火”一样,都与“欲望”分割不了,都含有“性”的意味。
黑孩盯着小石匠“红色运动衫”的领口,“像盯着一团火”;“目不转睛地看着手绢上的红花儿”,是朦胧的欲火悄悄燃起的表现。
煤炉里“几缕强劲有力的暗红色火苗”,燃起了黑孩内心的欲望,“兴奋地‘欧’了一声”,“红色的火苗”,对初具性意识的黑孩而言充满了挑逗色彩,一瞬间引起了他的激动、兴奋情绪。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表明,“生火,烧火,或者与之相关的事物都被认为是性的象征,通常火焰代表男性的生殖器,而火炉和火灶则代表了女性的子宫”[2]147。
黑孩之不愿离开繁重的拉火工作,虽与其“恋父”情感移置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工作中隐含的“性”的成份。
打铁时飞溅的火星落在他裸露的皮肤上,没有痛的感觉,反而“眼里跳动着心荡神迷的火苗”,一副享受的模样。
当黑孩对以菊子为性对象的情感受挫时,炉中的“火苗”微弱起来,他追寻着火苗跳跃的痕迹而不得,恰好是他渴望如小石匠一般与菊子亲密而不得的反应,不过,这一无法满足的欲望没有如小铁匠一样心绪难平、怒火中烧,反而化为“意淫”的原动力,将对“性”的渴求之欲望推向高潮。
再次,食物的象征意味。
小说中出现的食物既指向“吃”的欲望的满足,也暗藏着“性”的意味。
菊子看望受伤的黑孩时,用她的“紫红色头巾”包来了两个窝窝头。
这里的“窝窝头”是乳房的象征,从后文小石匠把手“捂在姑娘窝窝头一样的乳房上”可以得到确证。
而“大葱”“黄瓜”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这与弗洛伊德性学理论认为一切长形物体皆可代表男性生殖器的看法不谋而合,我们可以看成是作家吸收了这一观点,借用小说形式表明自身的真实意图。
当然,小说中更为重要的食物象征,是多次出现的“红萝卜”意象。
有学者认为,“红萝卜”象征着男性生殖器,“在这里,红萝卜无疑是个‘小阳物’的隐喻”[10]。
基于这一观点,“红萝卜”的得与失便象征了黑孩性能力的能与否。
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莫言真正意图,因为小说刻画黑孩这一形象的重点不在言说黑孩“自体性意识”的觉醒与满足,而是由“恋母情结”生发的“恋乳”意识,所以,我们认为,“红萝卜”象征着“乳房”。
“我不关心萝卜来自何处,我只关心萝卜的形状,它们尖尖的头顶和猛然膨胀的根部,使我想起了乳房。
”[5]莫言没有在小说中明确指出,迷惑了读者乃至评论家的视线,却在其他作品中进行了类似的独白,通过上官金童之口,将“红萝卜”与“乳房”直接划等号。
弗洛伊德指出:
“母亲的胸往往成为了性欲的第一渴望对象。
”[2]293黑孩第一次正视菊子时,深深吸引他的是其丰满的胸脯,“浑圆的下巴”,因此,菊子的出现象征着“乳房”的出现,也象征着黑孩欲望的满足。
“当最初的性满足与营养摄取密切相关时,个体的性本能便把性对象指向自己的身外,即母亲的乳房。
”[6]基于这样的理解,黑孩钟情于“红萝卜”的一系列行为便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
一个暧昧与情欲狂躁的晚上,饱食一顿的众人在老铁匠的歌声里,纷纷按捺不住内心的饥渴,小石匠温存地把手按在“姑娘硬邦邦的乳房”时,激起了他们心中蠢蠢欲动的欲火:
小铁匠变得焦躁不堪;黑孩专注追寻火苗的跳动,在渴望舒缓性欲而不得之后,将目光锁定在铁板上的“红萝卜”上。
黑孩开始了“性的幻想”,从记忆中搜寻婴儿时期躺在母亲怀里吮吸乳汁时呈现的乳房模样,“大个阳梨”“根根须须”“金色羊毛”等活脱脱囊括了乳房的外在形状,幻象中他仿佛看见了乳房内部包孕着源源不断的“银色液体”,“他的嘴第一次大张着,发出一声感叹”,臆想中的红萝卜既满足了黑孩“吃的渴望”,也缓解了其性的焦虑。
他渴望如小石匠一样将它握在手心里,就在他伸手捉住小萝卜时,焦躁的小铁匠与他开始了一场争夺。
在这场抢夺中,我们无法判断小铁匠是否如黑孩一般将红萝卜幻想成充溢乳汁的乳房,也许只是为了纾解内心的躁动而寻求事物的慰藉,但黑孩却至始至终为着得到“乳房”而战斗。
红萝卜的失去,是黑孩爱与性的双重流失,于是“身体软软地”倒下。
黑孩“性对象”的最终丧失,以小石匠与小铁匠的斗争中误伤菊子为标志。
他“跑到地里拔起了所有未成熟的萝卜”,但再也没有找回那颗透明的红萝卜。
所以,如前文所述,“红萝卜”象征着“乳房”,红萝卜的不复存在象征着黑孩“性对象”菊子的离去。
值得注意的是,“水”“火”“食物”除了对“性”的隐喻,更为深层的是对“性”本身所具有的繁衍生殖功能的崇拜。
首先,水是万物之源,是生殖繁衍成长之必备。
兴修水利,加宽滞洪闸是故事得以展开的起因,刘副主任的训话直指水利对农业、对生存的重要性。
与水相伴出现的是黑孩感觉到的“鱼”。
莫言为何会在小说中多次提及“鱼”?
“鱼”意味着、代表着什么?
其实似无关紧要的“鱼”实则是生命符号的象征。
闻一多先生认为鱼隐喻着繁殖功能[7]127,李泽厚先生则进一步探究,认为鱼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生殖与生存能力,二是交往与语言的功能[8]750。
他们的考证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鱼所隐喻的性及由性派生而来的人们对生命繁殖的重视。
“鱼所代表生存意志和生活本身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和感情,已积淀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
”[8]352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并延续至今。
所以这里的鱼与水绝不仅仅是对性欲的扩大化写作,而是暗含着延续生命、维系生存繁衍的大主题。
其次,“火”是旺盛生命力的写照,点亮了人类生存、生活的光芒。
为了强化这种蓬勃的生命张力,莫言惯用色彩来负载情感,红色是其使用最多的色彩。
红色的火苗,红色的运动衣衫,既激发着人们蠢蠢欲动的性欲望,也流露出如酒神般强烈的生命意志。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莫言笔下的万事万物无不表现出一种生命的感觉和生命的欲望。
”[11]他们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下竭力创造着喜悦而保有激情的生活。
因此,人类不仅仅背负着繁衍后代的责任,也天然地享有享受生命、热爱生活的义务。
当然,生命的延续离不开能源的供给,在这里,食物成为了生命得以成长、壮大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总之,三者相辅相成,水使得生命成为可能,而火的发现与存在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由“动物性”而“人性”的文明过渡媒介。
莫言将人类繁衍的重大任务隐匿在“性”的本能欲望之下,在生命原欲的推动下张扬生命活力,不得不说既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吸收,也是基于自身文化价值理念的再创造。
三、亲情:
交流之喻
莫言笔下的小说主人公常常具有明显的孤独意识,就如那幽灵般的黑孩,幼年的创伤使他封闭了自己与外界的言语交流。
生活的苦难,让他由一个充满灵性,说起话来“咯崩咯崩脆”的孩子变成“哑巴”。
并非黑孩不愿交流,而是迫切地渴望与外界交流:
“他不与常人交流,便与万物交流”[12],他不用嘴交流,却用身上的其他感官去听、去嗅、去参与。
我们认为,亲情的缺失是造成黑孩丧失语言沟通能力的主因。
小说中的黑孩,遭遇父爱与母爱双重丧失,长期的关爱缺失使其内心变得焦躁,没有安全感,生活的经验让他以为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逃避。
借斩断与他人的语言交流来封闭,麻木自身以获得短暂的安全。
于是黑孩的生活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交流的回避与亲情关爱的极度渴求。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根据人类动机提出需求层次的金字塔模型,分为基本需求与发展需求[9]。
将生理需要、安全与安全感、爱和归宿感、尊重和自尊划入基本需求的行列。
基本需求的缺乏是黑孩欲望的来源。
马斯洛称之为“缺乏性动机”,在食物和性的欲望得到满足后,关爱与安全感的需求逐渐显露②。
因此,黑孩对“爱”的渴求异常强烈。
小说中真正给予黑孩关怀且受其认同的只有菊子和老铁匠两人,于是,他将生活中的父母情感的缺失移置到他们二人身上,因为他们弥补了这个失去关爱的童年世界。
对菊子的母性认同在诸多评论性文章中已有出现,不再详述,仅从黑孩对老铁匠的父性认同着眼。
众多的研究评论中,最为忽视的便是小说中的老铁匠形象,大多数学者将老铁匠当成黑孩的情敌,或者解读为与小铁匠之间的竞争关系,以照应生存至上主题。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极其表面的关系,老铁匠的存在有其更为隐藏的心理需求,即将其视为黑孩眼中的替代父亲形象。
比如,很多人在解说菊子将黑孩拖出铁匠铺遭黑孩咬的举动解释为对菊子的嫉恨,然而根据小说的人物设定及内在心理结构可知,这一判断之片面性。
小男孩之不愿离开,有多重因素,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其对老铁匠父性情感的期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在给患者进行心理分析时存在移情作用,这一作用“是患者的欲望转移到分析师身上而得以实现的过程”。
黑孩对菊子和老铁匠的接受就存在移情现象:
将菊子视为理想状态中温和的母亲形象,将老铁匠视为走失的父亲形象,并对他有所期待。
黑孩对老铁匠的认同主要有三个层面:
一是遵从老铁匠的话语。
黑孩对父亲的眷恋十分显著,他时常回忆起以前的美好生活——他站在滞洪闸上,“把着栏杆,望着水底下的石头”,想起几年前“父亲没有去关东,后娘也不喝酒”时,他去闸上看热闹的光景;他梦见比马跑得还快的火车,可能有人告诉他,父亲是坐火车走的,这种幻想直至遇见了打铁的老铁匠。
他仔细地观察着老铁匠的外貌神态,或许是因为老铁匠让他留下来,使他产生了好感;或许是老铁匠身上的某些特质与其出走的父亲吻合,这一次,他完全接纳了眼前这个焦麦色的铁匠,“抖动的耳朵”昭示着黑孩的认可,他“手忙脚乱”地拉火,“咬着下嘴唇”坚持,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引起老铁匠的关注。
于是,一幅父厉子勤的画面就展现在眼前:
老铁匠如一位严肃的长者,细心地教导着黑孩:
“少加煤,撒匀一点”“拉长一点,一下是一下”。
正当黑孩享受这久违的“父爱”时,好心的菊子姑娘出现了,她见不得瘦小的黑孩受苦,希望帮助他脱离苦海。
可是这样的举动遭到了黑孩“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反抗,自始至终,黑孩都在反抗着菊子的“好意”,他不愿放弃刚刚触及的父亲般的温暖,为了不离开老铁匠,选择用咬的方式告诉菊子他的决心和坚持。
二是“模仿”老铁匠的行为。
他模仿老铁匠“拦腰捆上一根红色胶皮电线”,“他原来扎腰的那根布条儿不知是扔了还是藏了,他腰里现在也扎着一节红胶皮电线”。
这种看似幼稚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认同作用”,是“无意识同化心理过程”。
黑孩采纳老铁匠的行为方式意味着对老铁匠的认同,既是一个小孩在向大众宣示主权,寻求一种归属感,是一个长期内心孤苦、生活缺乏温暖的男孩对突然降临的父爱的美好幻想,同时也是希望引起老铁匠注意的举动。
三是表现为黑孩对老铁匠的维护。
黑孩敏感的察觉到小铁匠对老铁匠造成的威胁,他不动声色地声援着老铁匠,当小铁匠完整地学习到打铁的技艺而将老铁匠挤兑走时,黑孩十分失望。
小说用两只鸭子的视角,引出了黑孩追赶老铁匠的情节,“老头子走了,来了一个光背赤脚的黑孩子”。
老铁匠的离去对黑孩而言无疑是再一次遭遇抛弃的打击,心里生出的对老铁匠的依赖与对其父爱的诉求顷刻间化为乌有,一时间,他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割裂,“眼里蒙着一层淡淡的云翳,情绪非常低落”,他选择了逃离,逃离这个令他窒息和无所适从的环境,奔向那条专属于他的小河释放内心的压抑与痛苦。
生活的诡谲将黑孩本就不多的渴望一点点击得粉碎,他祈求通过另一个世界寻求解脱,“他得不到抚爱,便在水中寻求,若干温柔的鱼嘴在吻他……凡是人世间得不到的欢乐,他便在另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得到加倍偿还。
”[12]对老铁匠如此,对菊子亦是如此。
黑孩从他们身上索取的是安全感与归属感,隐藏着重新获得交流能力的欲望。
之所以借助亲情重现关爱,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血缘为纽带的思想息息相关。
亲情,是“爱”的一种,暗含着无私给予与奉献,“爱”的施与者心甘情愿地付出,这也是孔子所说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血亲之爱”。
黑孩渴望得到这种关爱,因为对亲情的回归隐含着个体融入群体,获得交流的可能。
人类生活的历史发展轨迹表明,个体难以脱离社会群体独自生存。
黑孩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并非与生俱来,与幼儿时期父母不正当的对待方式或家庭的动荡不安以及当时整体社会生存环境联系紧密。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使个体长期处于焦躁与无所适从的恍惚之中,既因恐惧而逃离,又因渴望而追寻。
从黑孩的成长环境可知,他体验过亲人和睦的快乐,体验过与外界交流的幸福。
他意识到母亲的离去,父母的远走是导致其孤独与不幸的根源。
他开始了亲情的寻求之旅,以便结束长期闭塞的生活,重获交流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亲情的获得与交流能力的重拾同质。
“在莫言的小说中,心理行为的过程远远要大于情节构制过程。
可以这样认为,对他创作灵感有激发作用的往往是心理的行为模式,他的作品总是起始于人的某种情绪状态,或孤独,或畏惧,或忧虑,或压抑。
”《透明的红萝卜》一文,正是在这些情绪状态的触发下,暗藏着对“欲望”的渴求。
莫言曾说,“一部好的作品应当是多元主题的呈现”,留给读者多方面的解读与思考。
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莫言是成功的,他成功地创造构思了作品的多重意蕴,给了每位读者自己选择的权利——选择他们愿意接受的视角,也成功地遮蔽了读者的眼睛。
总之,我们认为,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背景,通过刻画黑孩的基本欲望,将人类精神旨归隐喻于其中。
一方面直击人性的生理之欲,将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农民所面临的饥饿、恐惧、孤独等生存环境予以揭露;另一方面试图进入莫言的思想世界,将潜藏于其意识最为核心部分的对人类生存、繁衍与交流等三大永恒的精神话题淋漓展现。
毫无疑问,这是莫言对人类生存、繁衍问题的价值判断与审美观照,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意识深处高度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莫言小说王国建构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