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第一案县太爷杀了革命者该怎么判.docx
《司法独立第一案县太爷杀了革命者该怎么判.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司法独立第一案县太爷杀了革命者该怎么判.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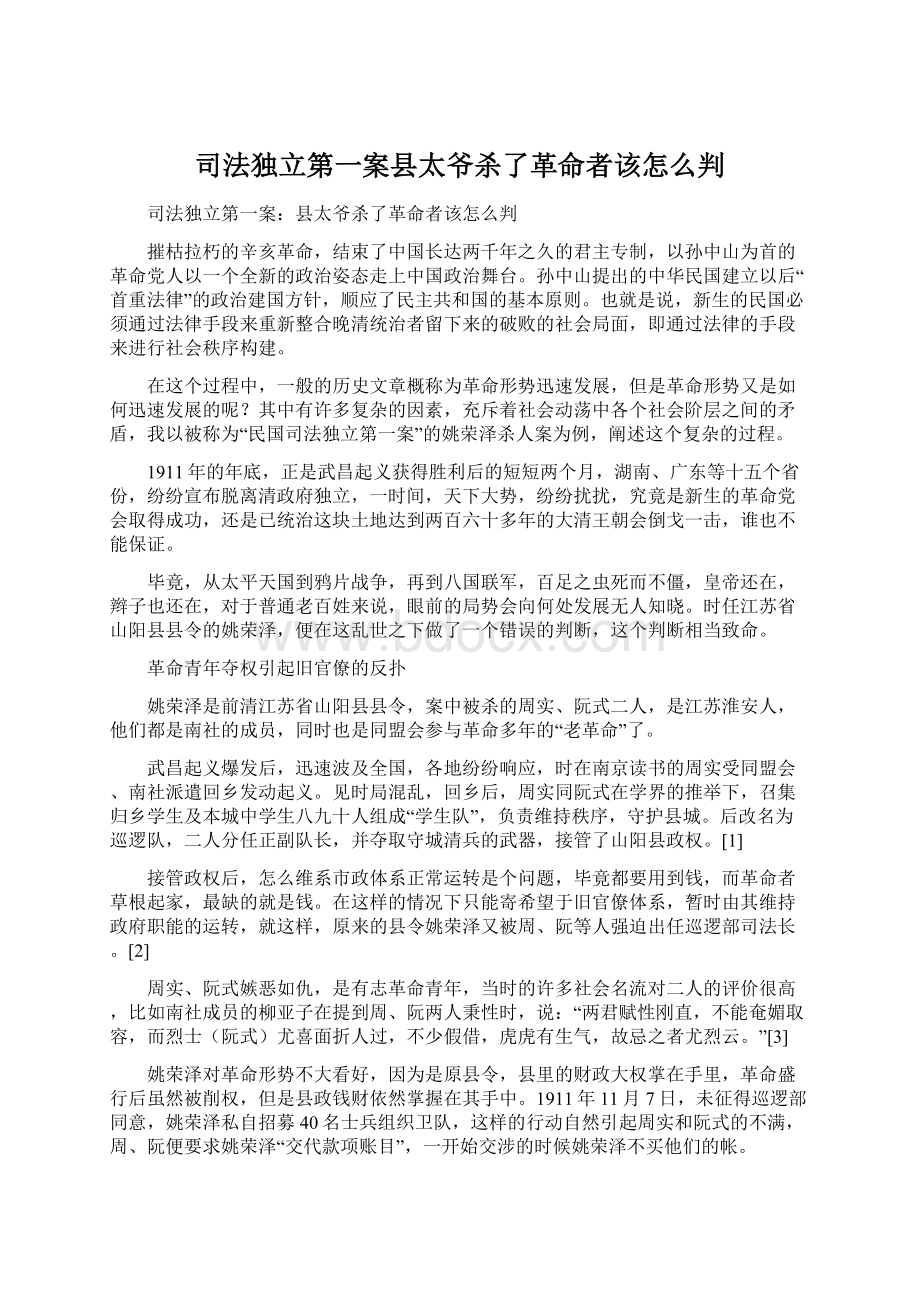
司法独立第一案县太爷杀了革命者该怎么判
司法独立第一案:
县太爷杀了革命者该怎么判
摧枯拉朽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一个全新的政治姿态走上中国政治舞台。
孙中山提出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首重法律”的政治建国方针,顺应了民主共和国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新生的民国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来重新整合晚清统治者留下来的破败的社会局面,即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进行社会秩序构建。
在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历史文章概称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但是革命形势又是如何迅速发展的呢?
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充斥着社会动荡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我以被称为“民国司法独立第一案”的姚荣泽杀人案为例,阐述这个复杂的过程。
1911年的年底,正是武昌起义获得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一时间,天下大势,纷纷扰扰,究竟是新生的革命党会取得成功,还是已统治这块土地达到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会倒戈一击,谁也不能保证。
毕竟,从太平天国到鸦片战争,再到八国联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皇帝还在,辫子也还在,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眼前的局势会向何处发展无人知晓。
时任江苏省山阳县县令的姚荣泽,便在这乱世之下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个判断相当致命。
革命青年夺权引起旧官僚的反扑
姚荣泽是前清江苏省山阳县县令,案中被杀的周实、阮式二人,是江苏淮安人,他们都是南社的成员,同时也是同盟会参与革命多年的“老革命”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时在南京读书的周实受同盟会、南社派遣回乡发动起义。
见时局混乱,回乡后,周实同阮式在学界的推举下,召集归乡学生及本城中学生八九十人组成“学生队”,负责维持秩序,守护县城。
后改名为巡逻队,二人分任正副队长,并夺取守城清兵的武器,接管了山阳县政权。
[1]
接管政权后,怎么维系市政体系正常运转是个问题,毕竟都要用到钱,而革命者草根起家,最缺的就是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旧官僚体系,暂时由其维持政府职能的运转,就这样,原来的县令姚荣泽又被周、阮等人强迫出任巡逻部司法长。
[2]
周实、阮式嫉恶如仇,是有志革命青年,当时的许多社会名流对二人的评价很高,比如南社成员的柳亚子在提到周、阮两人秉性时,说:
“两君赋性刚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阮式)尤喜面折人过,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气,故忌之者尤烈云。
”[3]
姚荣泽对革命形势不大看好,因为是原县令,县里的财政大权掌在手里,革命盛行后虽然被削权,但是县政钱财依然掌握在其手中。
1911年11月7日,未征得巡逻部同意,姚荣泽私自招募40名士兵组织卫队,这样的行动自然引起周实和阮式的不满,周、阮便要求姚荣泽“交代款项账目”,一开始交涉的时候姚荣泽不买他们的帐。
11月14日,周实、阮式组织召开光复大会,姚荣泽依然没有到会,持观望态度的士绅们也都一言不发。
阮式决定在大会“杀鸡儆猴”,当即定性姚荣泽逃避开会的行为是在反对光复行为,一定要严惩。
于是第二天,阮式带着巡逻队员,找到龟缩在县衙的姚荣泽,以双管手枪抵住姚荣泽的胸膛,要他交待清楚县里的财政状况,问他把钱粮放哪里了。
姚荣泽吓得面无人色,立刻答应三天之内把钱粮交结完毕。
[4]
他们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山阳县士绅的忌恨。
此时又有流言,传周实、阮式要杀官劫绅,瓜分他们的财产,导致当地士绅都人人自危,赶到姚荣泽处商量对策,想要除掉二人。
1911年11月17日,姚荣泽派人以议事为名,将周实骗至府学魁星楼下,周实迎面遭到枪击,连中七枪毙命,年仅26岁。
之后姚荣泽又带领人马直奔阮式的住所,把他绑架到县学。
阮式痛骂姚荣泽,换来的只是姚荣泽的冷笑,下令处死了阮式,他牺牲时年仅22岁。
凶残的侩子手竟剖开他的胸膛,五脏六腑俱出,鲜血满地流淌。
姚荣泽杀害周实和阮式以后,称周、阮二人勾结乱匪,扰乱秩序,又将周、阮家属一并拘捕。
随着时间的发展,革命风潮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革命军主力杀到淮安来了,姚荣泽一看坏事了,看来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错的,所以他只好抛家离业然后就跑到通州分府和通州总司令张察家中寻求庇护。
革命军抵达山阳,闻周、阮被害立即四处搜索凶手,结果扑了个空,但是把周实和阮式遇害的消息向上级汇报,等待法律对姚荣泽的制裁。
真正杀人者非姚荣泽一人
周实、阮式的惨案引起舆论哗然,群情激愤。
同为南社成员的柳亚子为伸张正义、惩凶复仇,到处奔走呼号,与朱少屏等联名上书沪军都督陈其美[5],认为在革命形势如此顺利的情况下,有革命志士被杀,影响极其恶劣,应当立即捕杀姚荣泽。
1912年初,根据周实、阮式家属的告发,沪军都督陈其美以“旧官僚残杀革命志士的严重事件”向孙中山电请把姚荣泽押解来上海按照军法进行审讯。
孙中山于1912年2月9日、10日连续三次发电告知有关部门,要求尽快把姚荣泽绳之于法,以顺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6]
有意思的是,在姚荣泽案移交到上海后,案件当事人双方此时却开始想和解了,淮安的六十多人士绅致信司法总长,建议对姚荣泽判处罚款,他们愿意为周实、阮式两人建祠出书。
受害人周实、阮式的家属也致信伍廷芳,说证人在上海很多天了,花销巨大,谋生艰难,一旦回到乡里就不好聚集了,考虑到淮安绅士的从中调停,同意“自愿和平了结”。
[7]
为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有两方面因素。
第一方面因素与辛亥革命的进行方式有关。
革命的进程中,官僚派与草根起家的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是常有的事,也是在每一次革命当中都会发生的。
辛亥革命是一种比较有节制的革命,因此这种关系更加复杂,推动变革的革命派并没有一支组织强大的部队,许多地方的政权更迭是以和平易帜的形式进行的,因此政权结构中依然留存有相当一部分旧士绅阶层,他们中有原来当过官的,比如姚荣泽这样的人并不看好革命,也有一些开明士绅倾向于革命党人。
正因为革命派没把原有的士绅阶层和官僚阶层的权力和势力摧毁,所以他们在广大的基层组织掌握的资源比革命党人要多,尤其在县一级,革命的过程中往往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财富主要掌握在谁手中呢?
就是这些士绅阶层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之间一有矛盾,很可能就是要流血。
所以姚荣泽后来说不是我杀的他们,是那些士绅让我杀的,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方面因素与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有关,在当时的原被告双方看来,打官司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花大价钱也讨不了好,不如息事宁人,士绅出钱摆平受害者家属,好以此帮助姚荣泽脱罪。
“务实”的陈其美与“天真”的伍廷芳
对于姚荣泽案件的双方要求和解的愿望,革命党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
在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破坏革命、残杀革命志士是一件必须要重惩的案件。
姚荣泽押解到上海的时间是1912年2月23日,当时的革命派人士对其是一片喊杀声,革命者竟死于旧官僚之手,是可忍,孰不可忍!
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意见很能代表当时大多数革命派的意见,他们认为像姚荣泽这样罪大恶极的凶犯,证据确凿,何须公开审判?
应当速速按军法行事立即处决。
就在这时,专司司法审判的临时政府司法部和司法总长伍廷芳于2月18日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陈其美来电以及审理姚荣泽案件,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并对审理姚荣泽的具体程序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即由谁来组织法庭和按照什么程序来审理,由此揭开了双方争论的序幕。
伍廷芳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
对于曾在英国受过专门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训练的伍廷芳而言,在中华民国刚成立之际,可以借姚荣泽案件,表现出民国政府有能力采取文明国的审判办法以及先进的审理程序来处理各种诉讼案件。
在伍廷芳的设想里,姚荣泽案应当成为中华民国判案的典型判例,让外国人知道中华民国法治的清明,以此作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和民国司法主权的铺垫。
因此伍廷芳建议允许外国律师在中国法庭出庭办案的方式,来为中国律师参与租界法庭办案提供先例,并选一名精通西方法律和裁判制度的主审官,以体现新兴的民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伍廷芳这样的想法在以陈其美为代表的部分革命者看来是极其“天真”的,反正要重罚,何必搞这样的“形式主义”呢?
反革命就应该立即处决才能立威,否则审一个“反革命”都这么大费周折,革命事业的威信何在?
于是乎陈其美毫不理会伍廷芳的建议,在2月29日私自委任丁榕为陪审官,军法司总长蔡寅为临时庭长、日本法律学士金泯澜等二人为民国代表,就准备这样组织军事法庭审理定案了。
[8]
陈其美的行为引起伍廷芳的强烈抗议。
按道理讲,民国建立伊始就强调司法独立,案件审理过程中,裁判所的人员安排、委派某人为裁判官、某人为陪审员,其权应属于司法部。
而陈其美是沪军都督,是上海的行政军事长官,有何权力干涉司法程序?
1912年3月2日,伍廷芳以此为由致信陈其美,“婉约”地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抗议。
陈其美看到伍廷芳的信,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私自委任司法审判官的行为是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反而以革命军都督府的威信相要挟,把这些任命登在报纸上,公告民众。
这等于告诉伍廷芳,你瞧,公众都知道我沪军都督府的人接手审讯这个事情了,你如果再生事端,朝令夕改,民众眼中政府的威信何在呢?
任命见诸报端后,陈其美于3月4日致信伍廷芳。
在这封回信中,陈其美以“事先将委任审判官一事公诸报端”为借口,继续坚持自己的决定。
孙中山一锤定音:
按伍廷芳说的办!
至此,姚荣泽一案的主角已经不是姚荣泽本人了,反而是伍廷芳和陈其美二人。
伍廷芳知道如果不说服陈其美,案件实在难以有较大进展,因此又下笔一封“再复沪军都督书”[9],主要是三个意思:
首先,提出了自己一整套以西方文明国司法审判办法为张本的司法规则和审判程序,说明自己试图办好此案以此向外国提出收回治外法权的身躯;其次,对陈其美的保守和不符合法制国家的主张,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最后伍廷芳还做了一个说明,说要姚荣泽如果想聘请律师,包括聘请国外的律师,都随他的便。
伍廷芳的这一点说明激起了陈其美的强烈反对,在陈其美看来,我们中国人的案子你聘请什么外国律师,这不是崇洋媚外、丧权辱国么?
所以陈其美很难接受聘请外国律师这一点,写了一封回信从三个方面对伍廷芳的主张给予了强烈的抨击:
首先,外国人不得为他国律师为国际通例,变更需经议院立法;其次涉案地点、人员皆为中国人,与外国人有何干系?
最后,如果要允许外国人参与中国庭审恐怕会为以后外国人干涉中国司法提供机会,中国人有崇拜洋人习性,这也将影响中国以后的司法公正。
伍廷芳对此回信批驳,其后又是几个来回的口水仗,讨论逐渐陷入僵局。
[10]
关于姚荣泽审判的具体实施,伍廷芳和陈其美数次论战都以公开发表的形式见诸报端,长达三个多月的关于“司法独立”的大辩论,引起了社会的轰动。
伍廷芳与革命党人、军方代表的陈其美之间,就实行文明国法制,还是传统的人治或者革命的专制进行审判的争论,体现了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与以陈其美为代表的军方革命派在“道路与方法”上的矛盾与冲突,反映了民国初年法制建设,尤其是实现司法近代化过程中的艰难。
案子总是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问题最后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孙中山身上,时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究竟是快意恩仇,为革命同仁们意气用事呢?
还是维护新政权所确立的司法独立之原则?
这需要孙中山来决断。
孙中山原本是支持陈其美的。
姚荣泽案开始的时候,姚荣泽被与他有私交的通州总司令张察保护起来,对于陈其美将姚荣泽转移上海接受审判的要求以案件细节尚未查明百般拖延,正是在孙中山的支持和严令下,陈其美才将姚荣泽转押至上海。
伍廷芳在与陈其美论争的时候也致信孙中山,他的言辞打动了孙中山,因为姚荣泽案已经成为民国司法独立的试金石。
孙中山针对伍廷芳的电报,随后很快便给出了一个答复,“所陈姚荣泽案,审讯方法极善,即照来电办理可也”。
态度很明确,那就是一切照伍廷芳说的办。
审判中的变数:
“死里逃生”的姚荣泽
3月23日下午,“中华民国第一案”在上海开庭。
由司法部和沪军都督府共同组成“临时正当之裁判所”审判,旁听者包括各署左长、南社社友、记者、各国人员共计一百九十多人。
审判人员按照伍廷芳的设想,陈贻范任临时裁判所所长,丁榕、蔡寅为承审官。
法庭经过23日、30日、31日三次的审判,[11]经历了一番唇枪舌剑,陪审团一致认定姚荣泽为谋杀罪,最后判定姚荣泽死刑。
判决后,法庭给姚荣泽五分钟做最后陈述,没想到一番陈述打动了陪审团。
姚荣泽申辩说,他杀死周实、阮式并非出自本意,而是因为受地方绅团的逼迫所为,请求减刑。
而陪审团也认为,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秩序扰乱之际,与平静之时不同,“该犯虽罪有应得,实情尚有可原”,便决定由陪审员集体禀请大总统“恩施轻减”,将死刑的执行期限延长三个星期。
[12]
但是这个时候南北政府合并,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孙中山、伍廷芳都已去职。
袁世凯刚上任不久,而且袁世凯本人与革命党人也是多有摩擦,乐于给革命派上点“眼药”。
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在1912年4月13日发布一纸大赦令便又免除了姚荣泽的死刑。
[13]
所谓的“打动”陪审团,是部分史料的记载,但是从实际出发,所谓的被告人最后五分钟陈述,承审官和陪审员的同情,以及“恩施轻减”的理由,多少有些牵强附会。
如果没有旧士绅势力的人奔走和运作,陪审团又何必冒着得罪陈其美等大佬的危险向袁世凯提出减刑的申请呢?
姚案的最终改判是民初尖锐复杂斗争形势的真实反映。
结果袁世凯签发了特赦令,姚荣泽等于是一下逃出生天,死刑免过,不到三个月姚荣泽就被放出来了。
[14]
袁世凯的特赦令充分体现了北洋集团与革命派之间的“暧昧”。
究其原因就像章永乐老师在其论文《“必要而危险”的权力:
民初宪政争衡中的行政专权》[15]中所说,北洋集团原本是清王朝的旧官僚、旧军人“借壳上市”的结果,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却不愿意同时继承作为南京临时政府之基础的革命的正当性。
姚荣泽的“死而复生”,令革命党人无法接受。
他们大呼“天理何在?
国法何在?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怨气发泄到年过七十的伍廷芳身上,他们连续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伍廷芳滥用职权、实行专制,破坏民国法制与民权。
一时间怨语汹汹,伍廷芳成众矢之的。
伍廷芳在民国初年的司法独立理想,就这样以尴尬收场。
司法独立之滥觞
案子结束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姚荣泽案的审判过程中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以姚荣泽为代表的旧士绅阶层以及后来给革命派上“眼药”的袁世凯,都很守规矩,严格遵循了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反而是革命派人士不时有破坏法制之举,后来在伍廷芳的坚持下,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却被姚荣泽、袁世凯等人用法律反制,给革命派上了深刻的一课。
从党派利益的角度讲,陈其美的做法和考虑不无道理,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所以深知迟则生变的道理,按照伍廷芳的办法,会给案子带来很多变数,毕竟当时革命派并没有一手遮天的势力,想给革命派难看的大有人在。
果不其然,姚荣泽抓住机会“死里逃生”。
在一个“革命即是正义”的年代,杀了革命者按国家法律审判反而没事,那么什么才是正义?
这个案件结果是革命派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革命党人痛骂伍廷芳是个“老贼”。
在案件审判过程中也深刻暴露出了革命派的部分问题,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在反封建反专制的过程中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当政后,却时不时流露出以军代政的新的专制倾向,关于姚荣泽案与伍廷芳的争论正是这种倾向的表现。
这不是特例,也不是陈其美一人的想法,他只是一个代表,这种思想其实大量存在于革命党人中。
而主持过前清法律制定,并深受西方民主熏陶的伍廷芳以其经历切实希望中国能摆脱专制的影响,反对行政、军政干预司法,但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虽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最终双方都有所妥协而促成了审判的进行,但法治还是人治或军治都仍是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大问题。
姚荣泽案的审判,开启了中国现代司法诉讼新纪元,从始至终,至少在程序正义这一个方面,姚荣泽案的审判完全符合西方法律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只是结果出人意料,让革命派人士心中很不是滋味。
在革命者的谩骂声里,伍廷芳也因此案郁郁寡欢,退出了政坛,深居上海观渡庐,埋头书斋,致力于学术研究。
1916年,伍廷芳东山再起,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次年代总理,旋因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解职出京。
1917年,追随孙中山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
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外长兼财政总长。
1922年6月23日,伍廷芳病逝。
弥留之际,伍廷芳犹谆谆叮嘱其子、法学博士伍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无一语及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