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20世纪末的.docx
《从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20世纪末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20世纪末的.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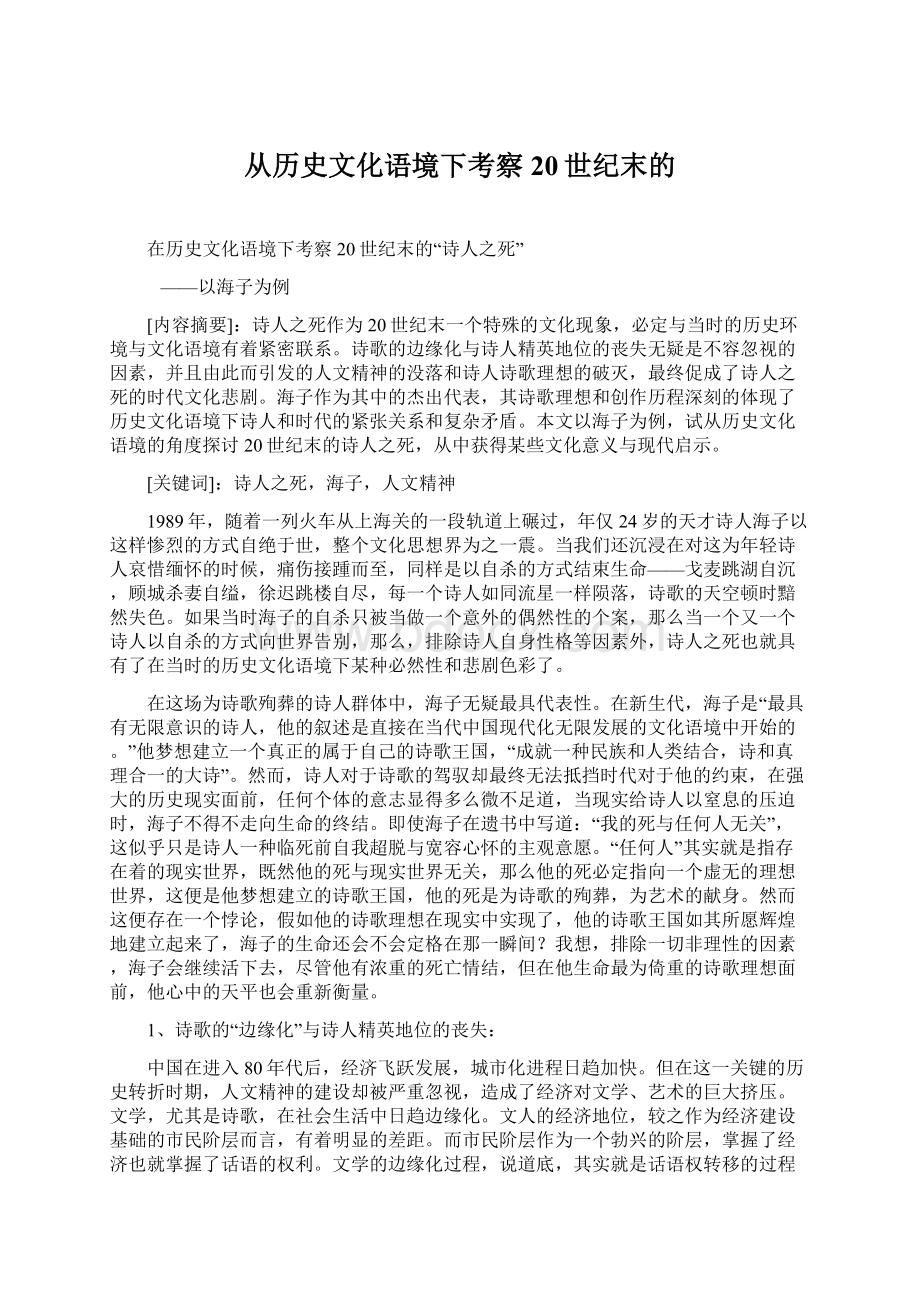
从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20世纪末的
在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20世纪末的“诗人之死”
——以海子为例
[内容摘要]:
诗人之死作为20世纪末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必定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语境有着紧密联系。
诗歌的边缘化与诗人精英地位的丧失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并且由此而引发的人文精神的没落和诗人诗歌理想的破灭,最终促成了诗人之死的时代文化悲剧。
海子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其诗歌理想和创作历程深刻的体现了历史文化语境下诗人和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复杂矛盾。
本文以海子为例,试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探讨20世纪末的诗人之死,从中获得某些文化意义与现代启示。
[关键词]:
诗人之死,海子,人文精神
1989年,随着一列火车从上海关的一段轨道上碾过,年仅24岁的天才诗人海子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自绝于世,整个文化思想界为之一震。
当我们还沉浸在对这为年轻诗人哀惜缅怀的时候,痛伤接踵而至,同样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戈麦跳湖自沉,顾城杀妻自缢,徐迟跳楼自尽,每一个诗人如同流星一样陨落,诗歌的天空顿时黯然失色。
如果当时海子的自杀只被当做一个意外的偶然性的个案,那么当一个又一个诗人以自杀的方式向世界告别,那么,排除诗人自身性格等因素外,诗人之死也就具有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某种必然性和悲剧色彩了。
在这场为诗歌殉葬的诗人群体中,海子无疑最具代表性。
在新生代,海子是“最具有无限意识的诗人,他的叙述是直接在当代中国现代化无限发展的文化语境中开始的。
”他梦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诗歌王国,“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然而,诗人对于诗歌的驾驭却最终无法抵挡时代对于他的约束,在强大的历史现实面前,任何个体的意志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当现实给诗人以窒息的压迫时,海子不得不走向生命的终结。
即使海子在遗书中写道: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这似乎只是诗人一种临死前自我超脱与宽容心怀的主观意愿。
“任何人”其实就是指存在着的现实世界,既然他的死与现实世界无关,那么他的死必定指向一个虚无的理想世界,这便是他梦想建立的诗歌王国,他的死是为诗歌的殉葬,为艺术的献身。
然而这便存在一个悖论,假如他的诗歌理想在现实中实现了,他的诗歌王国如其所愿辉煌地建立起来了,海子的生命还会不会定格在那一瞬间?
我想,排除一切非理性的因素,海子会继续活下去,尽管他有浓重的死亡情结,但在他生命最为倚重的诗歌理想面前,他心中的天平也会重新衡量。
1、诗歌的“边缘化”与诗人精英地位的丧失:
中国在进入80年代后,经济飞跃发展,城市化进程日趋加快。
但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精神的建设却被严重忽视,造成了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巨大挤压。
文学,尤其是诗歌,在社会生活中日趋边缘化。
文人的经济地位,较之作为经济建设基础的市民阶层而言,有着明显的差距。
而市民阶层作为一个勃兴的阶层,掌握了经济也就掌握了话语的权利。
文学的边缘化过程,说道底,其实就是话语权转移的过程。
在文学边缘化的现实下,诗歌同样难逃其历史命运。
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诗歌丧失了其原有的地位。
在其它文学样式在商业文化的浪潮中纷纷找到自身出路的同时,诗歌却陷入了更加边缘化的地步。
这种边缘化态势直接表现为诗人精英地位的丧失。
在晚清以前中国可以说是个诗人的国度,儒家早期经典著作便将《诗》列入五经当中,科举考试中对诗的重视也使创作诗歌和欣赏诗歌成为文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技能,而诗歌也被赋予了“以言志”的重任。
诗歌和诗人都处于社会的一个制高点上。
它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原因在于文人掌握着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诗人掌握着话语权。
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政府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
新兴起来的市民阶层,它的崛起过程就是话语权逐渐由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过渡到以世俗文化为主体的市民文化的过程,在这里,文人包括诗人失掉了其原有的精英地位。
由于有了80年代前期诗人和诗歌群体辉煌扮演“文化英雄”的光荣记忆,90年代诗歌向着社会和文化边缘的滑落,就更让人唏嘘不已。
“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群体的消费需求,也难以符合一些批评家的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的预期”,甚至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诗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业余”身份,此时成为“通例”。
诗歌的滑落趋势,诱发了新诗的“信用危机”,新诗的价值和其合法性再次被怀疑。
当先前一直扮演着文化英雄角色的诗人突然之间经受命运如此巨大的落差,诗人和读者面前横亘一条巨大的鸿沟,诗歌创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狭隘之地,诗歌和诗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尴尬。
海子作为一个为诗而生的天才,他在短短几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行,每一个字都凝结着诗人最本真的生命体验,可以说,他的生命与诗同行。
没有了诗的召唤,生命就会失去回声。
较之于诗人群体在社会地位中遭受的冷淡和被忽视,海子作为其中一份子,他的诗歌不仅在当时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甚至在行内还要遭受一些人的冷嘲热讽。
在燎原的《海子评传》中,讲述了很多这样的事例。
有一次,海子到昌平的一家酒馆对老板说:
“我可以给你朗诵一首诗,你能给我酒喝吗?
”老板说:
“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不要朗诵你的诗了。
”对诗歌如此纯情的海子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简直如同一个小丑,饱受世人异样的目光,美好的理想在现实中轻轻一触就这样如肥皂泡一般破灭。
而来自同行诗友间直接间接的阴暗批判与中伤更是无情地伤害了脆弱敏感的海子,海子隶属的民间诗歌组织“幸存者俱乐部”的“领导级”成员多多对曾经对海子进行无情攻击,指责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它的诗贬得一无是处”,海子为此在好友骆一禾面前痛哭一场。
经济的困窘也好,恋爱的失败也罢,都无法超越诗歌在诗人生命天平中的分量。
一旦外在的否定和排挤转化为自我怀疑与迷失,诗人的精神也就濒临痛苦的深渊。
2、人文精神的没落与诗歌理想的破灭
(1)商业化与人文精神的博弈
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变革不事声张地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
铺天盖地的商业化浪潮滚滚而来,无限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欲望。
摇滚乐、MTV、时装表演、网络媒体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通讯的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
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苗头愈发生长。
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影视、游戏光盘;一切分明使人感到沉重的不再是“精神”而是“肉体”。
“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思消逝,世界沦为彻底‘散文’化了的世界。
”诗歌的存在对于当时的环境简直就是一个黑色寓言,在日益没落中反照着人们精神土地的贫瘠。
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文艺思潮的主题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呈现出复杂色彩。
80年代引领思潮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
与纯洁高雅的知识力量相比,基于世俗的民间的大众的力量对文艺的牵引力显得更为直接有力。
最为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
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
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分化的趋势日益加剧。
至于新时期的文学教育,仍然受制于政治的外在压力,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困境,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往往脱离不了政治层面而严重忽视了作品本体的艺术审美教育。
随着读图和视听时代的到来,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模糊了了品读文学的眼睛,文学品读欲望的减弱和文学审美能力的下滑,使得整个社会的人文教育越发干瘪。
诗歌作为文学语言的精华,不像小说和散文那样可以走马观花,而是需要静下来耐心品味,但这似乎与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大众的阅读需求格格不入。
诗歌创作不能再坚守“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而必须要看风向、看潮流。
坚守于纯诗阵营的诗人们更成了孤独的漂泊者,他们挣扎着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却无奈地发现一切皆是徒劳。
海子也许是看到了这其间诗歌发展和复兴的种种困难,其诗歌所要达到的那种为人类建立家园的梦想从而成了天方夜谭。
海子因此也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
而也就是在矛盾的巨大痛苦中,海子的诗歌逐渐走向了成熟,也渐渐地靠近了死亡。
“也许,海子在90年代的门坎前自杀,正是他以‘临终的慧眼’看到世纪末诗歌将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根叶飘零,濒临绝灭,而先别而去。
”
(2)乡土文明的歌唱者
在海子早期的诗歌作品中,抒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这些诗中海子希望用“麦地”、“月亮”“村庄”等带有原型意味的意象来勾勒出一个纯情的世界。
“麦地”和“村庄”更成为他诗风个性鲜明的代名词。
在西川所编的《海子诗全集》里,只以“村庄”直接命名的就有《村庄》(村庄里住着/母亲和儿子)、《村庄》(村庄,在五谷丰盛的村庄)、《北斗七星七座村庄》、《九首诗的村庄》、《两座村庄》等,而散落在具体诗句中的,由村庄所衍生的“麦子”、“土地”、“日光”“风”、“雨水”等意象更是不胜枚举。
“村庄”是乡土文明的聚落,“土地”是乡土文明的根基,对“土地”和“村庄”的迷恋也就是对乡土文明的执著。
然而当目睹乡土文明一步步被商业文明吞噬,城市化让他被迫与土地割裂,他所看重的最纯最真的人性正渐行渐远,“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的村庄”成了他急切而无力的呐喊。
故乡之于他越来越陌生,当曾经的美好烟消云散终成怀恋,“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可以说,对乡土文明的歌唱伴随着海子一生的创作。
在他最广为流传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他所向往的幸福不过是“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而他留下的最后一首《春天,十个海子》也把村庄作为自己最后的栖居地:
“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但现实中的海子在商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成了无根的浪子,他只能一头扎进诗歌王国,借为诗歌寻根来消解现实中的无归属感。
(3)诗歌理想的破灭
海子是要作“大诗”的,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放置到源头之上,他的诗歌主张可以看作是诗歌界“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次尝试。
海子曾骄傲地宣布:
“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立一种伟大的集体诗,我不想成为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海子的宣言明确的说明他要试图探索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诗歌王国,成为像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一样的“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去缝合一代或几代人的精神创伤。
但在诗人的王国里有太多的情感和不切实际的愿望。
在海子的诗歌创作中提到了集体创作这一概念,并将尼采、凡高收入到他的诗歌王国中。
其目的是想从新恢复包括艺术、哲学在内的大文学来启迪人类,唤醒其蛰睡的灵魂。
然而他的主张在一群病态的人中没有得到重视,他看重的人情人性消解于世俗的精明算计之中,他的呼喊更像是《皇帝的新装》中,勇敢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天真童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者。
在自杀之前的一个月海子写下了他的最后的一首诗:
《春天,十个海子》。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子孤独无依的绝望感和幻灭感: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黑夜里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十个海子代表着已经接受了世俗规则的孩子,也就是芸芸众生。
就连复活后的自己都对曾经活着的自己产生怀疑和反叛,“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诗人对人与人之间的陌生、隔阂以及对人类的堕落的失望,由此可见一斑。
剩下的这个孤单的孩子,不向往尘世的热闹与喧嚣,在“高高堆起”的谷物场自得其乐,任由“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这是一个离群者清贫生活的孤独歌唱。
有它所蕴含的的情感来看,海子的死亡意识达到高潮,他已对人世深深地失望,保定了必死的决心。
诗歌创作对于海子说是他人生意义存在的唯一根据,意义失据对他来说无异于价值被抽空,无异于死亡。
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疾病对于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轮回的必然阶段,方死方生。
自杀在他看来是一种自觉死亡和自我完善的极端方式。
海子是地之子,他尊重生命更热爱生命,当既定的生活方式与他设想的差异太大时,死亡意识就更为强烈。
海子是“驻会作家”之外的诗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却苦守纯诗的高雅,执着于纯诗的创作,当他看作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实现唯一途径的诗歌,在苦苦求索中却终将归于虚无,他完全看不到诗歌的前途。
他终于发现在这样的时代,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进而由怀疑走向绝望。
(4)绝望的选择
以海子为代表的这些真正的诗人,他们坚守于纯诗阵营,诗歌是生活也是信仰,更是他们的最后防线,当诗歌创作不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诗歌贬值,商业文明入主诗坛后,他们理想落空信仰坍塌,再也无路可退。
他们对诗歌和自我的前途感到绝望,在绝望感的撕扯下蛰伏于心灵深处的死亡意识复苏。
既然不能骄傲地活于世间就选择自觉死亡,骄傲地死去,海子卧轨自杀,戈麦毁诗而后自沉,他们都在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维护着诗歌的纯洁。
海子的《土地王》正像他为自己写的一首挽歌: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一如藏棣所言:
“诗歌不是抗议,诗歌是放弃,是在彻底的不断的抛弃中保存最珍贵的东西。
诗歌也不是颠覆和埋葬,诗哥是呈现和揭示,是人类的终极记忆。
”
在物质金山的诱惑下,在消费主义的怂恿下,人们灵魂的航船彻底搁浅,人文精神随着经济的高涨而不断滑落,“诗人一连串的自杀行为成为90年代集体性逃亡文化风景中最为沉重的个体选择‘事件’”。
对其“解释”尽管因个人学养、境界、动机、背景不同而各各不同,但直面生死界面,返回歧路之初,回到思之根基,回到价值理性,“是‘失园’后的汉语写作或汉诗写作进入新世界的标记,也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用诗思把握灵魂甦生的最具有民间意义的心灵轨迹。
”
3、“诗人之死”的文化意义与现代启示
诗歌是精英文学的金字塔尖,诗人也是知识分子中的更高阶层,在规则缺失、价值混乱的时代,诗人更应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责任担当。
诗歌就是他们的武器,而诗歌的势危让他们失去了阵地。
世纪末“诗人之死”引发了90年代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王晓明曾在《刺丛里的求索序》中讲述了自己的困顿:
“八十年代晚期的一系列社会事变,却像扑面而来的风沙,刮得我晕头转向。
仿佛从一个长长的美梦中骤然惊醒,四周的一切都那么陌生……”王晓明所指的一系列社会事变正是八九十年代之交政府与知识界的一连串冲突,而长长的美梦正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代化乌托邦”信仰。
然而面对现实,王晓明发出了愤懑:
“在今天,大概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痛感自己精神上的荒芜吧?
除了那几近麻木的生活感觉,除了那被刺激得异常发达的功利欲望,我们从头脑里竟找不出别的东西,在超验的层次上简直就是两手空空!
”这就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乃至群体大众的信仰危机。
而这场讨论直指文学创作中重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主体价值实现的问题,人文精神的重建和完善可以说任重道远。
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渐渐展开。
西方文化是一种“个性文化”,能更深刻地体验到人的孤独感绝望感虚无感,更注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
到了现代主义那里,则更凸现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寻求生存与人生的意义,寻求对自我灵魂与世界的拯救。
西方文化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间浸染,后现代主义中的虚无、荒诞对以两千年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文化造成强有力的冲击。
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体现为儒道互补的二元文化结构,注重和谐、宁静、中庸、乐天知命。
儒家文化强调的则是一种担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段话恰是对中国儒家“士文化”的集中概括,而真正的诗人也从来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己任。
保持诗歌适当的功用态度才能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既不能沉醉于纯粹的虚无的艺术世界不能自拔,也不能过分放大诗歌的功用性而走向绝望。
20世纪末的的诗人们恰恰是在艺术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中失去了平衡。
可以说,他们的死虽然以中国文化为底片,却更多的沾染了西方文化的色彩。
这就需要我们重拾我们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精髓,反观生命本身,重建心灵家园。
重建以民族大文化为核心的的人文精神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精神幸福指数的必经之路。
对于诗人的死亡,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他们也许在肉体上消亡了,但他们的作品作为其精神的结晶,将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上。
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之一的诗人,也许在经历着各种的苦难,但他们创作着,体验着。
诗人应该明白他们的创作目的是开掘人类灵魂深处的家园,守护这片家园。
面对历史地位的巨大反差,精神追求和物质现实的种种矛盾。
生活在精神巨大痛苦之中的诗人选择自杀的行为,从人文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的诗人有责任活着,因为活着才有希望。
“诗人应更多地接受这个世界,主动地去承担苦难的人生,只有全身心地潜人大地,沉人到事物内部才能揭示深蕴的内含,去承受悲哀,在对悲哀的忍受、认识、接受过程中使灵魂渐趋成熟。
”我想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敢于:
“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海子等诗人的自杀,也许成为一时的炒料,也许终将被人们所淡忘。
但是海子等诗人的诗歌作为人类精神的结晶,必将获得永恒。
海子在死的时候,也许期于用自己的死,来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诗歌。
希望诗歌在被关注的同时能够得到复兴。
但事与愿违,海子的死非但没有拯救诗歌,而且给诗歌以沉重的打击。
一种悲观主义的情调在诗歌界引起一股自杀的浪潮。
这不应该是海子想看到的结果吧。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东西方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个体,关注人自身精神的状态。
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广为提倡。
而“人文关怀”这一词是文人们引入到中国,希望能够唤起对人们对个体的关怀,尊重个体生存价值,尊重个体生命尊严。
然而在人们热切呐喊追求个性的同时,却忘掉了“挖井人”——为我们创设爱与美精神家园的诗人,忘记了文人也需要人文关怀,同时也忘记了尊敬他们的创作个性,并对他们的生存尊严给以关注。
他们个体存在的社会价值也应该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个体的存在如果失掉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
作为新时期的我们应该掉转头来,反思社会只有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才能够创建一个和谐的拥有较高幸福指数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只有物质的追求,没有精神的陶冶,人文精神就会颓败乃至丧失,文化人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许没有经济学家那样明显,但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人的价值,不能只用外在价值尺度来衡量。
对于诗人来说,“死亡不仅具有个体生命的意义,而且拥有群体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能够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能够从死亡中获得警示;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尽量避免再次堕入深渊。
”世纪末的“诗人之死”无疑对新世纪中国诗人的精神出路有着重要的警醒和启示意义,让我们重新考虑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为自己的灵魂找到真实可靠的根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