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系族群的西迁与崛起.docx
《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系族群的西迁与崛起.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系族群的西迁与崛起.docx(3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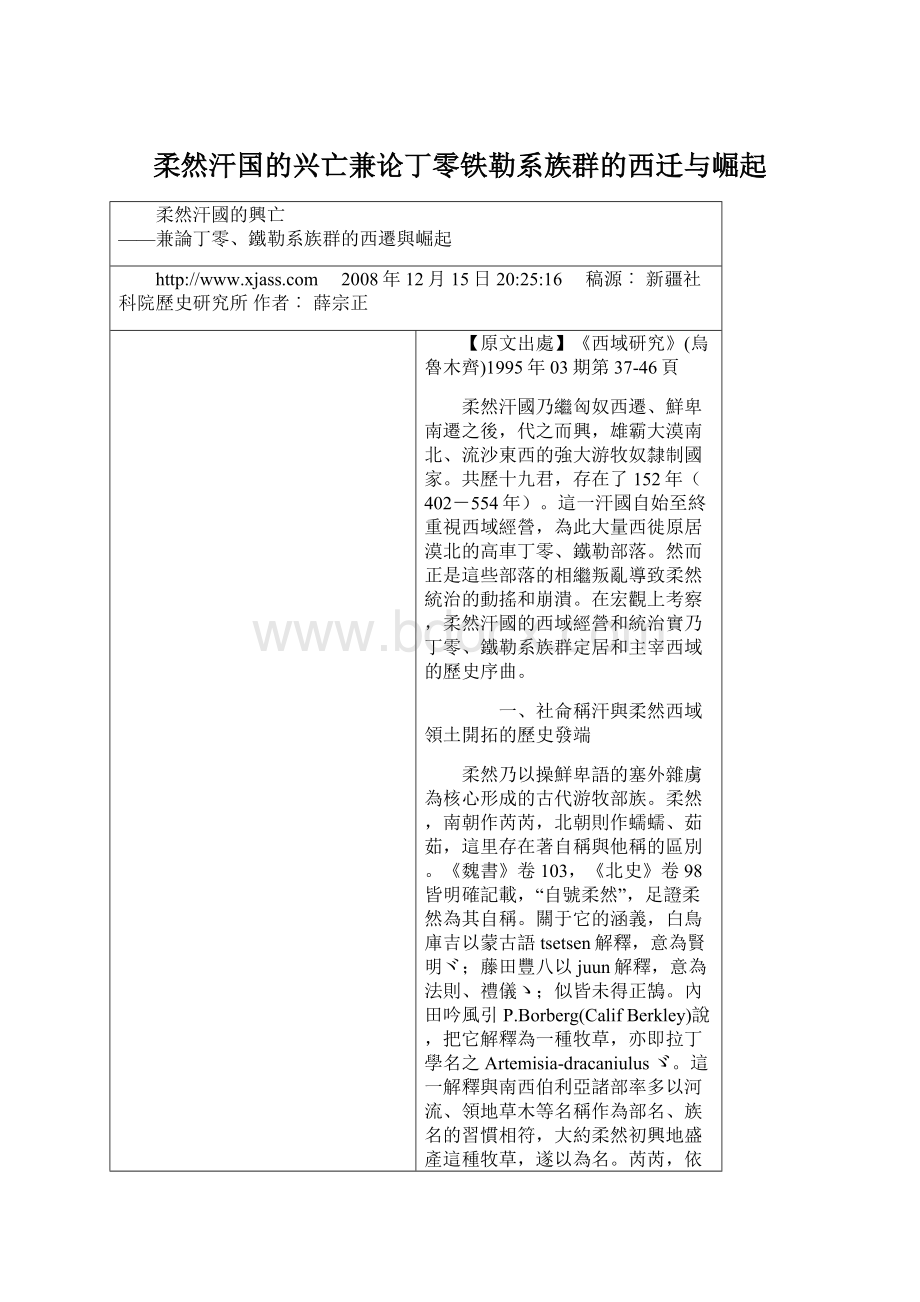
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系族群的西迁与崛起
柔然汗國的興亡
——兼論丁零、鐵勒系族群的西遷與崛起
2008年12月15日20:
25:
16 稿源︰新疆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作者︰薛宗正
【原文出處】《西域研究》(烏魯木齊)1995年03期第37-46頁
柔然汗國乃繼匈奴西遷、鮮卑南遷之後,代之而興,雄霸大漠南北、流沙東西的強大游牧奴隸制國家。
共歷十九君,存在了152年(402-554年)。
這一汗國自始至終重視西域經營,為此大量西徙原居漠北的高車丁零、鐵勒部落。
然而正是這些部落的相繼叛亂導致柔然統治的動搖和崩潰。
在宏觀上考察,柔然汗國的西域經營和統治實乃丁零、鐵勒系族群定居和主宰西域的歷史序曲。
一、社侖稱汗與柔然西域領土開拓的歷史發端
柔然乃以操鮮卑語的塞外雜虜為核心形成的古代游牧部族。
柔然,南朝作芮芮,北朝則作蠕蠕、茹茹,這里存在著自稱與他稱的區別。
《魏書》卷103,《北史》卷98皆明確記載,“自號柔然”,足證柔然為其自稱。
關于它的涵義,白鳥庫吉以蒙古語tsetsen解釋,意為賢明ヾ;藤田豐八以juun解釋,意為法則、禮儀ゝ;似皆未得正鵠。
內田吟風引P.Borberg(CalifBerkley)說,把它解釋為一種牧草,亦即拉丁學名之Artemisia-dracaniulusゞ。
這一解釋與南西伯利亞諸部率多以河流、領地草木等名稱作為部名、族名的習慣相符,大約柔然初興地盛產這種牧草,遂以為名。
芮芮,依《通鑒》卷125胡注︰“芮芮,即蠕蠕,南人語轉耳。
”按“芮”,而銳切,霽韻,中古讀音作,近似于柔然的音讀,應即南音之轉。
至于“蠕蠕”則乃鮮卑“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故改其號為蠕蠕”々,具有鮮明的貶義。
此外尚有茹茹之名,不過以非貶義漢字改寫的蠕蠕漢音而已,使用此名者多為已成為北魏臣民的柔然人;不可遽據雲崗石窟有此名號題銘即斷為本族的自稱ぁ。
柔然的核心乃郁久閭氏,其先祖曾為鮮卑所掠奴,取名木骨閭,意為髡首人,亦即奴隸,聚合諸逃奴,自成部落。
因此,《南齊書》卷39記雲︰“芮芮虜,塞外雜胡也”。
“雜胡”,或曰“雜虜”,所指為血統正源不明的混血族群,以郁久閭氏為核心的柔然正是這種塞外雜虜之一。
あ至于此外還有其它一些記載,如“芮芮國,蓋匈奴別種”ぃ;“蠕蠕,東胡之苗裔也”い等等,不過揭示柔然先世曾先後役屬于匈奴、鮮卑。
這一歷史經歷雖然同血統淵源不存在任何聯系,卻導致這一族體語言的鮮卑化。
這就是為什麼阿那曾認親于魏,“臣先世源出于大魏”ぅ,而魏主亦予默認的緣故,但這絕不意味著柔然與鮮卑同族。
柔然汗國初創于北魏天興五年(402)社侖自建號為丘豆伐可汗。
柔然初本“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う,是歲受北魏大軍追逐,乃率眾“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並諸部,凶勢蓋振,北徙羽洛水”。
(11)高車乃高車丁零的簡稱,游牧于羽洛水,即唐之獨洛水,今之土拉河一帶。
丁零之名早在兩漢之世業已出現,但一直分部而居,力分勢弱,柔然初徙漠北曾投附其中最強大的斛律部(uluk,意為偉大,即後世之胡祿屋部),然不久就叛而破之,遂兼並高車諸部,進而挺進西北,又大破匈奴余種拔也稽部于根河上。
根河應即《通典》卷199所記之康干河,即鄂爾渾河,“其地豐草盛,人皆殷富”(12)。
柔然既然佔領了自土拉河至鄂爾渾河一帶的豐美草原,遂稱雄漠北。
柔然汗國建立以後,立即沿著匈奴鑿通的草原絲路西向發展,逾阿爾泰山,拓境天山北麓,抵于瑪納斯河水域。
對此,《魏書》卷103于社侖入主漠北後接敘︰
號為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流沙,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
于是自號丘豆伐可汗。
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
《通鑒》系此事于晉安帝天興元年,即402年。
可見此年丘豆伐可汗社侖不但已君臨漠北,而且開始拓土西域。
它還表明︰
(1)柔然牙庭不象匈奴或後世的突厥、回紇那樣,建牙于漠北心髒地區,而是置于方位偏向的敦煌、張掖之北。
此即柔然建國伊始,就高度重視西向拓宇的指征。
(2)校以杜佑《通典》,柔然汗國的西部邊界不是“西則焉耆之地”,而是西則“焉耆之北”,應指今天山北麓瑪納斯河水域,柔然勢力到達焉耆之北的瑪納斯河水域,說明開鑿草原絲路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問題在于,柔然以敗亡之眾,君臨漠北已非易事,居然西征也一路破竹,直至焉耆北,未必單憑自身實力,而必役使了大量漠北屬部從征。
漠北本為阿爾泰諸族東支、中支與西支部落雜居的地區,其中東支如原鮮卑屬部的丘敦氏、樹洛干氏;中支如匈奴余種的拔也稽部、烏洛蘭部等,語言都與柔然所操鮮卑語相近,一直倚為維持漠北統治的支柱。
所遣西征者皆為語言相差較大,操西支阿爾泰語的高車丁零、鐵勒諸部,旨在一箭雙雕,既加速西征進程,又減少了漠北腹心地區的敵對勢力。
《魏書》卷103《高車傳》中既有六氏,又有十二姓之別,其區別安在?
據我判斷,即與此次西征引起的分化有關︰
高車,蓋古赤狄之余種也。
初號為狄歷……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侖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參稽其它史料可知,斛律、袁紇等高車六氏一直居于漠北,又稱之為東部高車;副伏羅氏等高車十二姓則後來于車師前部西北開基建國,亦可謂之西部高車;而高車的原居地本在漠北,則發生東部高車與西部高車的分化必與柔然此次西征有關。
其中已有十二姓受召參加了西征,佔全部高車的三分之二部眾後來都已定居西域。
復據《北史》卷99,鐵勒傳,正是北朝時代,西域操西支阿爾泰語的鐵勒部落突然增多,鐵勒實即丁零的異譯,原居地也在漠北,此一變化顯然兆示著這些西徙的鐵勒部落也是作為柔然從征勁旅而在西域定居落戶的︰
鐵勒……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
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薄落、職乙、--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勒兒、十----、達契等一萬余兵……
此外,康國北,傍阿得水,得嶷海東西,乃至拂東都有鐵勒部落的馬蹄印。
他們“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
如果把此傳同《魏書•高車傳》及同書《蠕蠕傳》細加對勘,就不難發現不少部名發音相同,實為同名異譯。
例如居漠北之解批氏應即西遷于伊吾西、焉耆北之契氏,漠北斛律部之西遷部落入唐後已改譯為胡祿屋部。
其西遷路線也恰好同草原絲路相一致。
這些丁零、鐵勒部落的從征西域固然對柔然汗國武功盛世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但也為這一汗國的未來埋伏下無窮的隱患。
二、斛律在位時期柔然國界向烏孫故壤、月氏北鄙的推進
北魏永興二年(410)丘豆伐可汗社侖死,弟藹苦蓋可汗斛律繼立(410-414年在位)︰“(永興)二年(410)……社侖……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眾,部落立社侖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
斛律北並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歷辰部落……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
”(13)可見斛律在位時期柔然的國勢繼續上升。
且有跡象表明,西破烏孫,臣服索格底那亞諸城邦,劫掠大月氏,即寄多羅貴霜北境等柔然所建迄征戰功都發生于此汗之世。
理由是︰
(1)作為游牧奴隸制的柔然汗國,戰爭是保證奴隸供應和游牧奴隸制社會生存的第一需要,傳文明載斛律東征、北伐皆勝,而獨對南方的北魏取守勢,其真正原因絕不是什麼“畏威自守”,而應視為全力西征的重要指征。
(2)斛律在位時期專門委任了主兵西方的將領大檀,亦即後來柔然汗國第四代君︰“大檀者,社侖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于西界”(14)。
以出身言,此人並非汗系正支,後來竟被推立為汗,必與其人主兵西方時所建卓越戰功有關。
足證斛律之世發動西方遠征是實。
聯兵悅般,擊破烏孫,乃斛律在位時期西方遠征的第一大勝利。
烏孫乃游牧于伊犁水域至巴爾喀什湖之間的西域古國,早在兩漢時期已見于史冊。
社侖時期柔然的國界既已推進至焉耆北的瑪納斯河一帶,已同烏孫接壤,不久發生了武裝沖突。
故《魏書•烏孫傳》記載,“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蔥嶺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
太延三年(437),遣使者董琬至其國”。
雖然烏孫國勢久衰,此前已連遭鮮卑首領檀石槐(147-167?
)、拓跋首領郁律(318)等多次重創,但畢竟是個大國,皆未致放棄故土,此時獨遁徙山中,必非柔然獨力所能勝,而乃聯兵悅般,兩面夾擊的結果。
參閱《魏書》卷102,悅般國原在“烏孫西北”,與柔然並不接壤,然自烏孫他徙之後,卻變成柔然鄰國了,說明烏孫舊地已為柔然、悅般二國瓜分。
傳文又記悅般原“與蠕蠕結好”,後來成為鄰邦反成仇敵。
正說明當初兩國“結好”即為了共擊烏孫,故烏孫敗亡山中。
遺憾的是,關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史書中僅泛記為北魏太延三年(437)董琬西使之前事,卻未明載其具體年代,因此產生了種種推測。
例如余太山先生認為烏孫“西徙最早可能在社侖在位期間”(15),這是同社侖之世柔然國界止于“焉耆之北”的明確記載相悖的。
我認為當乃社侖之下任君主斛律在位時期事。
《魏書•悅般傳》透露悅般在“與蠕蠕結好”時期,亦即兩國聯兵擊敗烏孫瓜分其國之初,“其王嘗將數千騎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
此時之大檀猶為主兵西方之柔然邊將,尚未嗣立為汗。
因為會見地點顯然在柔然邊境,否則絕不能容許鄰國王統兵數千直入大牙相謁。
而大檀主兵西方恰貴始于藹苦蓋可汗斛律(410-414)之世。
由此足證,聯兵悅般,擊破烏孫確乃斛律柄國時期完成的偉業,大檀則乃主持這次西征的重要將領。
統率部眾,入主索格底那亞粟特諸城邦,兵鋒一度南逼烏滸水,劫掠大月氏即寄多羅貴霜北境,乃斛律在位時期西方遠征的輝煌頂點。
(16)
柔然汗國的版圖一度與大月氏,即寄多羅貴霜相接事見于《魏書•大月氏傳》︰
大月氏國,都廬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薄羅城。
這一記載包含著重大失誤。
經近人研究,盧監氏城應即《漢書•西域傳》中大月氏都城“監氏”之訛,即後世史書中之白題、縛叱、縛底野、縛底那、乃Baxai的音譯,即今阿富汗之巴爾赫。
薄羅城亦指該地,但另有其名稱來源,即僧徒行傳中之薄--羅、縛渴羅、縛喝,名異而地同。
則大月氏實未遷都。
但柔然勢力一度逼近烏滸水域,數犯其國應是事實。
大月氏所指即貴霜王朝,全盛時代曾為中亞霸主,涌現了丘就卻、閻膏珍、迦膩色迦諸著名國君,成為佛教的護法神。
然傳至庫維什卡、波調諸君時國勢已衰,王朝被迫退縮至烏滸水南吐火羅斯坦,苟延殘喘。
原屬月氏的烏滸水北索格底那亞地區早已分裂出去,及寄多羅時代益加衰落,故柔然得以橫行其北。
柔然勢力既然推進到烏滸水域,必然一度佔領了索格底那亞,即我國史書中的河中地,才能出現大月氏“北與蠕蠕接”的形勢。
然而《魏書•大月氏傳》與同書《粟特傳》下引一段文字卻似乎存在著難以解釋的明顯矛盾。
傳文曰︰
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
粟特的居地即索格底那亞。
根據傳文所述,征服其地者乃“匈奴”,並非“柔然”,而這里所說的“匈奴”是指“白匈奴”,亦即喊噠。
我國史書中又稱之為滑國,滑(gu),實即匈(hun)人的音變。
然而索格底那亞既為柔然佔領,如何又被噠征服呢?
這一表層矛盾只能從噠與柔然關系的歷史演變中尋求解釋。
對此,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兩則史料。
其一是《魏書•噠傳》︰
噠國……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至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
其二是《梁書•滑國傳》︰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
據此可知,噠(即滑國、白匈奴)原出塞北,歷史上曾臣屬于柔然。
問題在于這一關系發生于何時呢?
余太山先生認為︰“如果噠受柔然役屬的話,可能在{k21fc28.jgp}噠南遷索格底那亞之後,入侵吐火羅斯坦之前”。
其時噠已成君臨中亞的大國,同前引史料所記“滑猶為小國,屬芮芮”明顯相悖。
以我判斷,噠“猶為小國”必在塞北與初徙金山南時期。
前引史料提供了兩種時間信息︰一是據《魏書•噠傳》所記,其國于北魏文成帝前八九十年已由塞北初徙“金山而南”。
文成帝年號為太安,《冊府元龜》卷969明確記載︰“(太安)二年(456)十一月,噠、普嵐國並遣使朝貢”。
以此噠初通魏之456年上溯八九十年為366-376年。
而噠入主粟特的時間則另據《魏書•粟特傳》所述,至其王“忽倪已三世”。
這意味著456年入貢北魏之忽倪已是噠第三代王,則其王上距い噠入主粟特僅兩世。
以一世20年計,二世40年,再加上忽倪初登王位之余數12-16年,與斛律在位時間(410-414)基本相合。
則366-376到410-414年間乃噠自金山南西徙粟特的時間。
余太山說的失誤即在于把這兩種時間混淆為一了,以我判斷,噠始臣于柔然必發生于410年社侖稱汗,勢力初步擴展至金山南,而噠“猶為小國”之時。
後沿草原絲路繼續西遷,至斛律之世更發其從征粟特,進軍索格底那亞,並于柔然退師後留其戍守,因而君臨其國,然羽翼豐滿後已不再服從號令。
可見噠亦為柔然西征屬部之一,則柔然佔領索格底那亞與噠入主粟特實為一回事,一切矛盾皆可洞然冰釋。
綜上所述,藹苦蓋可汗斛律在位時期進行的西方遠征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勝利,草原絲路因之重又鑿通。
但是,這些勝利不過是一場暴風雨。
烏孫雖已敗亡,而悅般代興,同柔然的政治蜜月也尋即結束,昔日屬部噠入主粟特後亦割據自雄。
于是輝煌的武功很快化作昨日黃花,剛剛鑿通不久的草原絲路因兵戈歲動而重又壅阻了。
三、大檀、吳提之世柔然勢力向伊吾、高昌、焉耆、龜茲、鄯善一帶的滲透
藹苦蓋可汗斛律死後,繼立者乃斛律長兄子步鹿真(414-415在位)。
他面臨著悅般反目,噠叛離,西方遠征勝利成果喪失等嚴峻形勢,窮于應付,引起部眾離心,因擁立大檀。
大檀久主兵西方,戰功卓著,“能得眾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
”(17)此汗在位時期(415-429)以開拓草原絲路受阻,轉而控制磧口,經營絲路中道。
取得後西涼政權的臣服,控制伊吾乃其最大的成就。
西涼乃漢族李氏家族創建的河西地方割據政權,其版圖西及流沙以外的伊吾、高昌。
早在斛律之世,柔然勢力已進逼其北境。
故建初九年(413)西涼主李--“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18),此之“北虜”即指柔然。
及大檀繼立,西涼敗于北涼,玄始八年(419)失酒泉,九年(420)失敦煌,一般認為此歲西涼已亡。
事實並非如此,李氏王統未絕,西涼余眾尚在,仍然志在復國。
直至玄始十一年(422)晉昌又陷,西涼殘眾雖在河西已無地容身,但仍可退至流沙以西的最後根據地去,遂保聚伊吾,繼續奉行西涼正朔。
其首領乃李--之孫李寶︰“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家),寶傾身禮接,甚得眾心,每希報雪”(19),這一政權一直存在了20年(422-442),實乃西涼王朝一脈相承的繼續,宜正名為後西涼。
大檀既取得了這一政權的臣服,遂牢牢地控制了磧口重鎮伊吾。
乃南攻北涼、北魏。
泰常八年(423)正月攻魏,迫其于“二月,築長城,自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各置戍衛”(20),同歲七月“柔然寇河西”(21),殺北涼世子沮渠政德,從而引起了我國北方諸王朝的全方位震動。
北魏神二年(429)牟汗紇升蓋可汗大檀死後,“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429-444),魏言神聖也。
”(22)吳提繼承了前汗的事業,重點向絲路中道拓展勢力。
對此,《宋書•芮芮傳》留有明確記載︰
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僭稱大號,部眾殷強,歲時三遣使詣京師,與中國抗禮,西域諸國焉耆、龜茲、姑墨,東道諸國並役屬之。
劉宋政權存在于420-478年,上述記錄當于此一時限求之。
余太山先生一古腦兒斷為社侖所為(23),而其時社侖早死,有失年代學依據。
松田壽男以傳文中把芮芮與大檀劃等號,推斷這一系列事件都發生于大檀時代(24)。
其解釋恰可同大檀控制伊吾事緊相承接,體現了柔然戰略思想的一貫性,固然不無道理。
然據《冊府元龜》卷968,柔然通宋始于元嘉十九年(442),正當吳提在位之世。
此汗繼位之初就同北魏息兵言和,“(神)四年(431)遣使朝獻”(25),北魏亦厚加結納︰“延和三年(434)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納吳提妹為夫人,又進為左昭儀……至太延二年(436)乃絕和犯塞”(26)。
看來吳提同北魏息兵未必真的志在和好,而乃別有所圖。
則此約和之431-436年即為全力進行西域經略的指征,焉耆、姑墨、龜茲等“東道諸國”的臣服大約都是在此一時限完成的。
這樣,盡管草原絲路早已壅阻,而又開闢了一條新的輸血管道,通過伊吾——焉耆北,穿天山而至焉耆,經龜茲又與蔥嶺外世界建立起聯系。
而柔然西域經略的巨大成功引起北魏朝廷的憂慮與不安,自太延元年(435)也開始卷入西域爭奪,這就是吳提“絕和犯塞”的原因所在。
北魏乃鮮卑拓跋氏在我國北方建立的一個強大王朝,都于平城,此時已一統華北,國勢日盛,乃唯一同柔然相匹敵的政治勢力。
太延元年(435年)五月“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等九國入貢。
”(27)這些入貢國家中不少已成為柔然屬邦,反映了西域諸國要求擺脫柔然統治的強烈願望。
同月,魏主遣使王恩生、許綱等“二十輩使西域”(28),而“恩生等始渡流沙,為蠕蠕所執”(29),送至柔然汗廷,其時兩國猶息兵言和,釋之歸。
“許綱到敦煌,病死”。
(30)此事載入《魏書•車師傳》,說明王恩生、許綱等是在車師被扣,則車師前部也已成為柔然屬國。
太延二年(436)八月,魏主又“遣使六輩使西域”(31),柔然乃“絕和犯塞”,發兵遮使,使命仍未達。
三年(437)二月,悅般遣使通魏(32),合謀共攻柔然,十一月“魏主受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33)。
其時北涼已稱藩于北魏,因“詔(沮渠)牧犍(即沮渠茂虔)發導護送出流沙”,(34)改而取道北涼屬境高昌郡而西,終于順利到達烏孫。
“烏孫又遣導譯護送董琬至破洛那,高明至者舌國”(35),實現了離間西域與柔然關系的政治目標。
“旁國聞之,分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
”(36)董琬、高明出使的成功初步動搖了柔然的西域統治。
四年(438)“春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于魏”(37),並留京入侍。
這意味著鄯善已改附于魏,昭示著在同柔然的激烈爭奪中北魏一度佔據上風。
正是鄯善王遣弟入侍之太延四年(438),魏主親統大軍,分四道,大舉伐柔然。
而“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38),大敗而歸。
王弟樂平王丕被擒,形勢大變。
吳提因遣使遍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王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39)。
割據河西的沮渠氏北涼遂叛魏,改附柔然,導致北魏決心翦滅北涼,引起流沙東西各派政治力量的重新改組。
太延五年(439)九月魏軍破姑臧,北涼王沮渠茂虔迎降。
但北涼王族沮渠無諱仍固守酒泉、晉昌等城,志在復國。
太平真君二年(441)在北魏強大攻勢下,沮渠無諱退守敦煌,遣其北沮渠安周先渡流沙,三年(442)四月“無諱將萬余家棄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畏之,將四千余家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國中大亂,無諱因據鄯善”。
(40)盤踞伊吾之後西涼主李寶本以規復故國為職志,乘沮渠氏西遷之虛,“自伊吾帥眾四千人據敦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41),叛柔然,臣于北魏。
別遣其舅唐契、唐和兄弟規復高昌,未至,“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余眾奔車師前部伊洛時”。
(42)則車師前部亦早已叛柔然改附北魏。
高昌本為諸涼版圖中的一個郡,乘河西之亂,敦煌人闞爽自署為太守,據郡割據。
唐契來攻,曾求援于沮渠無諱。
北涼軍攻奪鄯善後本已西進焉耆,乃折而東返。
既至,西涼唐契一軍已潰敗,“爽遂閉門拒之。
無諱怒,遣部將衛星奴詐降,誘襲之”(43),因攻佔高昌,據以為都。
仍奉北涼正朔,兼臣于南朝的劉宋與柔然,史稱後北涼(442-460)。
至于伊吾,雖已為後西涼李氏家族所棄,柔然又另委代理人高羔子統治其地。
這個高羔子大約是不肯隨李寶東歸的漢人首領。
可見在這場流沙東西的政治大變動中,柔然依然是得大于失。
不但繼續控制著伊吾,而且通過後北涼沮渠氏政治進一步控制了高昌、鄯善。
所叛離者不過是小國車師前部,而這個小國不久就為高昌後北涼政權吞並,這一切都屬于吳提為汗時所建功業。
四、吐賀真、予成之世柔然與北魏激烈的西域爭奪
由于北魏卷入西域爭奪,柔然在這一地區的霸權地位出現了歷史性反復。
敕連可汗吳提死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
”(44)處可汗吐賀真在位時期(444-464)正值北魏太武帝武功盛世,連遭其重擊,失去了鄯善、焉耆,但仍保住了龜茲、高昌的控制權。
太平真君五年(444)吐賀真初即位,環繞著高昌控制權的斗爭就開始了。
是歲,沮渠無諱死,子沮渠乾壽繼立,北魏通過車師前部王伊洛時誘之叛柔然,沮渠“安周乃奪其子乾壽兵,統領部曲,因而自立”(45),柔然必然插手了這一政爭,並保住了高昌的控制權。
六年(445)北魏發動了第一次西征,以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統涼州以西兵,即降魏之西涼部眾進擊鄯善。
鄯善王比龍之世本已叛柔然,歸附于北魏,然自沮渠氏西遷,其王真達已受其支配,又回到柔然的間接控制下。
是役,“萬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度沙,至其境。
時鄯善人眾布野,度歸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
其王真達自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46),九年(448)五月北魏立“交趾公韓拔為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47),鄯善國境內的樓蘭城長期以來一直是西域長史的治所,城中出土的大量漢、晉漢文簡牘表明那里的漢族居民很多,具備郡縣化條件,韓拔所封之王僅為一種爵號,實際身份完全是由朝廷任免的地方官吏,參稽《魏書》卷30王安都傳,其人以太子庶子出為鄯善鎮將,可見北魏已創置了鄯善鎮,故置鎮將戍守,柔然勢力已被逐出于這一地區。
太平真君九年(448)萬度歸第二次統兵西征。
史載“是歲,(悅般)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擊蠕蠕”(48)。
可見這是一次聯兵悅般,分兵數路,合擊柔然的宏大戰略計劃。
淮南王他一軍北征,萬度歸一軍西征,悅般也發兵策應,迫使柔然窮于應付。
但北伐軍雖發,似戰功不顯。
西征軍則捷報頻傳。
先攻焉耆,“約輕齎糧,取食路次。
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尉犁二城,拔之,進圍員渠。
鳩尸畢以那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沖。
鳩尸畢那眾大潰,俊虜之,單騎走山中。
度歸盡屠其城,四鄰諸城皆降服。
”(49)唐和所統西涼兵及伊洛時所統車師前部兵皆參預了此役。
鳩尸畢那兵敗後,亡奔龜茲,“十二月,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50),“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萬余級,大獲駝馬而歸”(51)。
這一記載問題不少,明明龜茲兵僅三千,居然為魏軍斬首二萬,所奏捷報明屬不實,且龜茲未克,中道班師,更兆示著師出不順。
故史載萬度歸西征,“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52)。
柳驢戍主本已降魏,及是復叛,必與龜茲之戰不妙有關。
有跡象表明,吐賀真雖然在北魏、悅般的兩面夾擊下,不能救西域,喪失了鄯善、焉耆,但卻最終粉碎了這一聯合攻勢。
並聯兵建國高昌的後北涼政權,向北魏發動了局部反攻。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沮渠安周以車師王伊洛時隨魏軍西征,留其子歇守城,兵備空虛,“引柔然間道襲之,攻拔其城,歇走伊洛,共保焉耆鎮,得免者僅三分之一,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53),自是車師前部一部分並入高昌,一部分西徙焉耆,其國名亡匿于史冊。
次歲(451)“(唐)和詣闕”(54),改委車伊洛(即伊洛時)守焉耆,似也抵擋不住柔然攻勢,“正平二年(452)伊洛朝京師,賜以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55),其子也召入內地。
這意味著此歲之後,焉耆又為柔然奪回。
其後,沮渠安周似出現反柔然跡象,乃采取果斷措施。
和平元年(460)“柔然攻高昌,奪沮渠安周,滅沮渠氏,以闞伯周為高昌王”(56)。
這個闞伯周似即前自署高昌太守闞爽的宗親或後裔,從而進一步控制了高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