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与傅山.docx
《王铎与傅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铎与傅山.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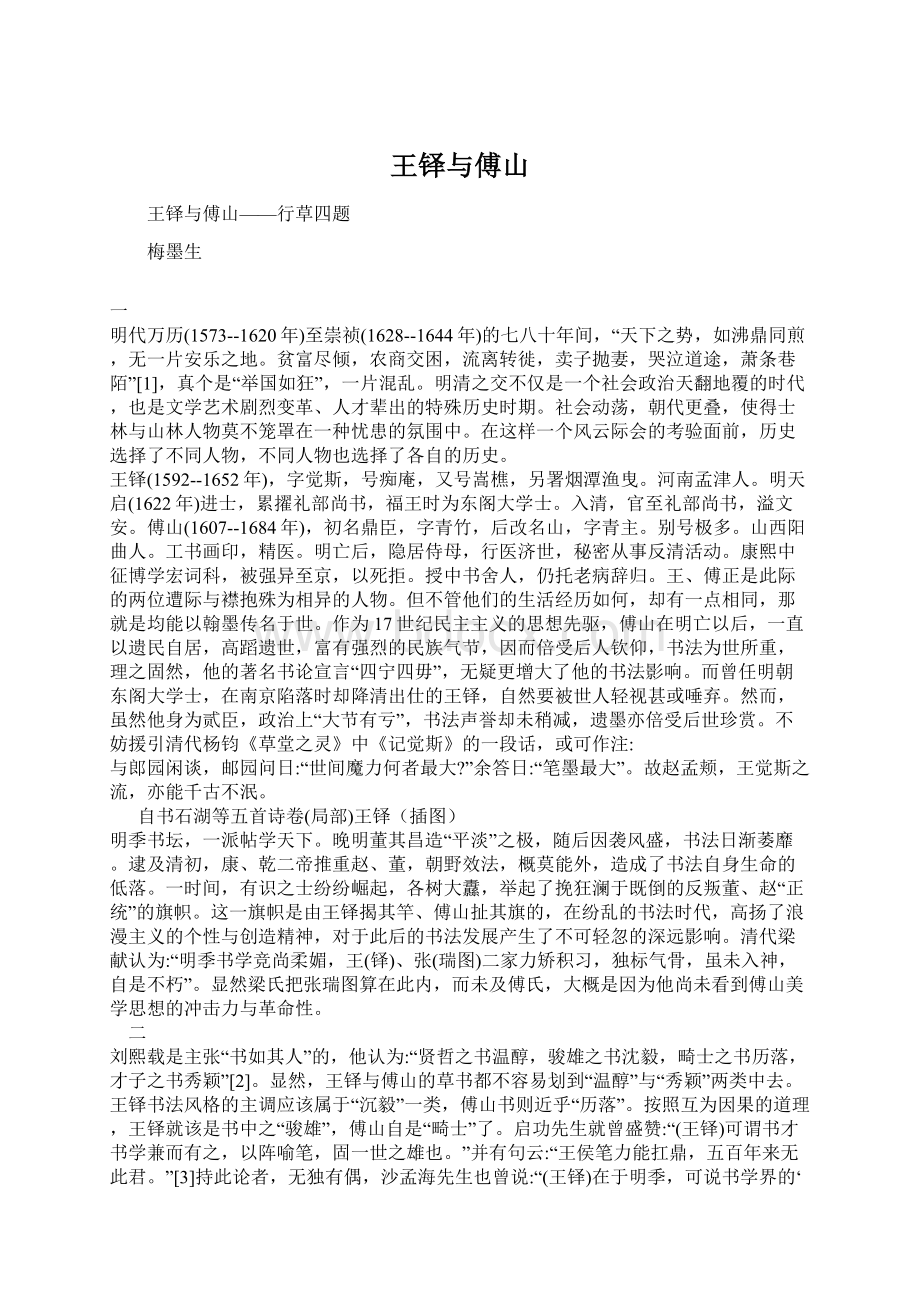
王铎与傅山
王铎与傅山——行草四题
梅墨生
一
明代万历(1573--1620年)至崇祯(1628--1644年)的七八十年间,“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
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1],真个是“举国如狂”,一片混乱。
明清之交不仅是一个社会政治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剧烈变革、人才辈出的特殊历史时期。
社会动荡,朝代更叠,使得士林与山林人物莫不笼罩在一种忧患的氛围中。
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考验面前,历史选择了不同人物,不同人物也选择了各自的历史。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痴庵,又号嵩樵,另署烟潭渔曳。
河南孟津人。
明天启(1622年)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福王时为东阁大学士。
入清,官至礼部尚书,溢文安。
傅山(1607--1684年),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
别号极多。
山西阳曲人。
工书画印,精医。
明亡后,隐居侍母,行医济世,秘密从事反清活动。
康熙中征博学宏词科,被强异至京,以死拒。
授中书舍人,仍托老病辞归。
王、傅正是此际的两位遭际与襟抱殊为相异的人物。
但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如何,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均能以翰墨传名于世。
作为17世纪民主主义的思想先驱,傅山在明亡以后,一直以遗民自居,高蹈遗世,富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因而倍受后人钦仰,书法为世所重,理之固然,他的著名书论宣言“四宁四毋”,无疑更增大了他的书法影响。
而曾任明朝东阁大学士,在南京陷落时却降清出仕的王铎,自然要被世人轻视甚或唾弃。
然而,虽然他身为贰臣,政治上“大节有亏”,书法声誉却未稍减,遗墨亦倍受后世珍赏。
不妨援引清代杨钧《草堂之灵》中《记觉斯》的一段话,或可作注:
与郎园闲谈,邮园问日:
“世间魔力何者最大?
”余答日:
“笔墨最大”。
故赵孟颊,王觉斯之流,亦能千古不泯。
自书石湖等五首诗卷(局部)王铎(插图)
明季书坛,一派帖学天下。
晚明董其昌造“平淡”之极,随后因袭风盛,书法日渐萎靡。
逮及清初,康、乾二帝推重赵、董,朝野效法,概莫能外,造成了书法自身生命的低落。
一时间,有识之士纷纷崛起,各树大纛,举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反叛董、赵“正统”的旗帜。
这一旗帜是由王铎揭其竿、傅山扯其旗的,在纷乱的书法时代,高扬了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创造精神,对于此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不可轻忽的深远影响。
清代梁献认为:
“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显然梁氏把张瑞图算在此内,而未及傅氏,大概是因为他尚未看到傅山美学思想的冲击力与革命性。
二
刘熙载是主张“书如其人”的,他认为:
“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2]。
显然,王铎与傅山的草书都不容易划到“温醇”与“秀颖”两类中去。
王铎书法风格的主调应该属于“沉毅”一类,傅山书则近乎“历落”。
按照互为因果的道理,王铎就该是书中之“骏雄”,傅山自是“畸士”了。
启功先生就曾盛赞:
“(王铎)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
”并有句云:
“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3]持此论者,无独有偶,沙孟海先生也曾说:
“(王铎)在于明季,可说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
”[4]林散之先生更认为他“自唐怀素后第一人”。
由于王铎以明朝阁臣而入清为仕,他的书法长期受到冷落。
随着时光之消磨,人们以政治取舍的观念渐淡,王铎书法的独到魅力因此日显,故而近年来得到了重新评价和关注。
其中韩玉涛先生从美学的高度对王铎书法进行了再认识,他把王铎书法的美学思想概括为“魔鬼美学”,“在艺术,尤其是在美学上,确乎有惊人的成就”,并指出了其隐含的矛盾性。
(5]这是极有见地之论。
王铎传世的行草书作品确确实实传达了一种深沉奇诡的思想情绪。
艺术语言的沈毅骏宕,仿佛在告诉人们,他是别有滋味在心头的。
“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诗句,正表现了他的落寞与伤感;而“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
”[6]又透露了他的埋首翰墨与艺术心志。
王铎没世已340年,可以令这位在隐痛中度过八年宠辱余生的书之骏雄欣慰的是,他终于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留下了“好书数行”。
如:
《行书诗翰四首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草书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开封市博物馆藏)、《行书杜子美赠陈补阙诗轴》(开封市博物馆藏)、《孟津残稿》(洛阳市博物馆藏)《忆过中条语》(刊《中国书法》)、《临柳公权帖》(启功藏)、《题柏林寺水诗轴》(刊《中国书法》)、《临豹奴帖轴》(刊《中国书法》)、《草书野鹤陆舫斋诗卷》(湖北省博物馆藏)、《行书奉孝翁社长诗卷》(刊《书法丛刊》)、《诗卷》(日本高鸟槐安氏藏)、《草书投野鹤诗卷》(美无名氏藏)、《行草锥州香山作诗轴》(刊《书法丛刊》)等等作品,集中代表了王铎的“好书”,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书法风格。
不妨对他传世的代表作进行一番风格分析。
前人认为:
文安学问才艺,皆不减赵承旨,特所少者蕴藉耳。
—清·王宏《砒斋题跋》
余于睢州蒋郎中泰家,见所藏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
明季工书者推董文敏。
文敏之丰神潇洒,一时固无有及者。
若据此卷之险劲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文敏当逊一筹。
—清·张庚《国朝画微录》
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其合作者,苍郁雄畅,兼有双井、天中之胜。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
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
—清·梁献《评书贴》
王觉斯铎,魄力沉雄,邱壑峻伟。
笔墨外别有一种英姿卓荤之概。
殆力胜于韵者。
观其所为书,用峰险劲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
—清·秦祖永《桐荫论画》
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
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清·昊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
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
—马宗霍《霎岳楼笔谈》
文安健笔蟠蛟螭,有明书法推第一。
—吴昌硕诗句
前人评价王书,其审美感受的抽象概括是:
险劲沉著—锥沙印泥之妙—苍郁雄畅—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纵而能敛—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魄力沉雄—力胜于韵—健笔蟠蛟螭。
同时,提出批评:
所少者蕴藉——体格近怪。
显然,王书的风格特征在前人眼里突出体现为“险”、“苍,,、“雄”、“劲”、“力胜”。
这说明,王铎行草书没有完全皈依二王的正统书法的痕迹,无论是向古代书圣的标准看齐,抑或是拿早于他几十年的颇饮时誉的董其昌书法作参照,人们终归无法把王铎的风格纳人纯粹的王羲之流派。
王宏撰认为其书:
“所少者蕴藉”,以及梁献指出的“体格近怪”已经明确表示了王铎书法的变异风格是别具体格的“新理异态”。
尽管他曾自白:
“予独宗羲献”、“学书不参古法终不古,为俗笔也,”;清代吴修也认为“铎书宗魏晋”,且在创作方法上格守“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清·倪灿《倪氏杂记笔法》),但这些似都不足以说明他真正的艺术理想与审美所在。
他是要把潜藏内心深处的积郁、愤感、愧作、哀惋、悲凉、苦寂等等心理意绪“泻注”毫端的,想在一个相对较为自由和抽象的世界里寄托他的情怀:
“自异平生轻洒泪,可堪今日泪如丝”。
“耻心委顺负明时,垂老争执众岂知”。
“大力,如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
”“寸铁杀人!
不肯缠绕”。
“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作文不可不狠鸷深刻”。
“文中有奇怪,浅人不知耳,望之咋指而退……自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
”(《文丹》)王铎的文论暴露了其心灵的另一面,这也许是更真实、更内在的一面。
一颗骚乱纷扰、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心灵掺和着一种对于“奇诡之美”的向往之情,喷发而出,凑合成为王铎的心理基调。
作为一位书法的天才,他令人信服地把这一切转换成一件件书法奇观一一我们今天看到的王铎作品。
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形成了一种迥异前人又有别时人的风貌。
这些作品本来就来自于一个不想再“蕴藉”的心灵。
扭曲的人格、变异的审美理想与“天崩地坼”的时代风云,共同导演了沉雄险怪的王铎书法风格。
也许只有在“笔落风雨”的书法渲泄中,这位“贰臣”的内心冲突才得以熨平,他的审美敏感和个性化的创作精神才得以实现。
故而其书法意蕴肯定不是温柔敦厚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体格也极容易“近怪”起来。
结合王铎的传世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行草书风格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两种:
一种是明快斩截的,所谓“寸铁杀人,不肯缠绕”者。
这类作品以《行书诗翰四首卷》、《孟津残稿》等为代表。
行笔骏爽、锋棱鲠介,笔力挺健,有一种“狠鸷深刻”“力胜于韵”之感。
一种是苍郁沉雄的,所谓“健笔蟠蛟螭”,“飞沙走石,天旋地转”者。
这类作品以《草书杜诗卷》、《临豹奴帖轴》《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草书题野鹤陆舫斋诗卷》等为代表。
笔墨苍润跌宕,结体纵横缠绕,章法腾掷变化,有一种沉郁盘纤之妙。
两种面貌之间当然有必然的联系。
如《题柏林寺水诗轴》、《临柳公权帖轴》、《忆过中条语轴》、《行书杜子美赠陈补阙诗轴》等作品,便是其间的过渡性表现。
王铎精工各体,但以行草为胜擅,其中又可分为行书和草体。
应该说,我们无法在他的行体与草体间强分水平的高低,笔者不能同意“王铎的行书一无足观”[7]的说法。
也不能同意“他创造的‘连绵草’,就是一个新种”——把“连绵草”的开山之功记在王铎帐上的说法。
[8]“‘觉斯书后更无书’,是有道理的”[9]的结论也欠客观。
拙见以为,王铎书法正是以他的深解古人——晋唐风范为根底的,而根底的具体所指落实到他的书法,便是他继承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和米南宫诸古代大师的行楷传统而赋予个性表现的行书。
没有这个“本钱”,就没有王铎草书。
王铎草书应该是王铎行书的一种变化与纵逸,一种“魄力”、“英雄卓荤之概”的烂漫式的合作表现。
如果我们因为感动于王铎的“连绵草”便无视于《诗翰四首卷》、《题柏林寺水诗轴》那样的行书之作的精彩,显然犯了某种失误。
至于“连绵草”鼻祖应该是谁,恐怕无论如何也落不到王铎头上的罢。
不过,在王铎两种形式表现中,确实有一种一致的东西,弥漫团聚,令人激赏。
那是一种“奇奇怪怪,骇人耳目”的新精神、新风格!
韩玉涛先生认为王铎的书法美学是“魔鬼美学”,“是封建美学的辉煌的殿军。
其反叛精神、创造精神的勇猛与锐利,是后世莫及的”。
[10]允为中的之论。
王铎的的确确曾经非常认真地向王羲之、王献之学习过。
他也一再自白:
“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这也许是实话。
但王铎是一个充满内心冲突的人,精神世界的复杂化,必然影响到他的艺术观。
因此,他才在《文丹》中吼出了那一声声惊人胆魄的宣言来。
从心理学角度考虑,那或许是心灵骚动、苦闷,即压抑状态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但王铎书法的逞力与矜奇毕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主客观的限制。
个性的张扬与精神的解放,在他而言是不可能彻底的。
他毕竟是位居首辅的东阁大学士,他是曾经长期供职朝庭的官僚,他不可能象啸傲山林的傅山那样对一切正统的审美道统做彻底革命。
他要在“有动于中”、“发之于书”(钱谦益《王铎墓志铭》)的草书上套上一环理性的控制圈。
这个圈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里,便是有点不自然,即今人所谓“拿劲儿”。
傅山的分析是:
“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
[11]在傅山看来,王铎自称“皆本古人,不敢妄为”的学古时期的书法都是“极力造作”的产物,并且他把王铎的成大家归功于他的“无意合拍”。
显然这是傅山的道家哲学思想——自然主义观念的一个反映。
他们二人共同怀有一腔郁勃、一怀愁绪、一种振奋个性精神的理想,但他们的生活际遇、人格襟抱、道德文章、思想意识,以至文化心理、审美境界等等却是存在极大差异的,因而,其艺术标准、文化立场、表现形式也就必然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王铎虽然在《文丹》里声嘶力竭地呐喊“怪、力、乱、神”,但他终归要保有一种书法的规范与典雅,他从骨子里还是企望秩序——儒家文化的重来。
他不仅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过“极神奇,正是极中庸也”的主张,在实践上似也可发现他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目标所向。
这种不忍彻底反叛传统的矛盾、犹豫,正是傅山所不取的。
也许,王铎的张奇矜怪与领异标新本身,主要的矛头所向却是董其昌。
董其昌书法表现为:
秀、媚、轻柔、韵胜、虚灵古淡;王铎书法表现为雄、老、沉著、力胜、实在奇诡,这种对比不会是纯出于偶然。
王铎不惜“造作”甚或鼓努,用以逆反董其昌的“天真烂漫”与“萧散古淡”。
傅山虽然也喜“天真烂漫”之境,但他与董其昌又自不同。
他一再追求的是书法的“天”——生拙与支离、真率与烂漫的境界。
他比王铎更无所顾忌,他对封建礼教几乎深恶痛绝。
综合前述观点,不妨认为,王铎的审美理想从根本上就不想走温柔敦厚——“温醇”的道路,也不想走风流潇洒的“秀颖”之路,似乎与“历落”也隔膜着一层。
他对于“轻秀”一路的艺术,好象一直抱有成见,在给戴明说的信中他曾批评元代大画家倪璐:
“画寂寂无余情,如倪云林一流,虽略有淡致,不免枯干,尬赢病夫,奄奄气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
可见,他的书作一味沉实而“力胜”,是有历史原因和主观动机的。
(转引自傅申《王铎及清初北方鉴藏家》,载《中国绘画研究论文集》)他从“极力造作”到“无意合拍”,努力于实践的恰恰是一种超迈古今的新精神、新气象、新体势、新表现。
他是借晋唐之古而开自我之今的。
抛开其他不谈,仅从书法角度看王铎,我们无法不承认他的书法“笔墨外别有一种英姿卓荦之概”,无法不承认其书风所内蕴的“魄力沉雄”。
虽然王铎一生偷生仕林、忍辱苟安,实际他仍然没有什么好的政声,“遍询九卿,莫有言铎居官优者”[12],这势必造成他的失落感,他的内心深处难免时时缠绕着一种优患意识。
毕竟他是一个艺术的天才,他对艺术的执著足以说明他期求于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得到发泄、寄托、慰藉与自我肯定。
因此,才有了奔突的线条,有了屈郁拗峭、险变诡怪的字势,有了“渴骥奔泉,怒猊抉石”的墨趣,有了能涵茹古人、包容前人的觉斯书风。
那是大家之风。
吴德旋看到了王铎书法的直接承绪是北宋的“大家之风”,正是有眼力的。
王铎说过:
“凡作草书,须有登吾嵩山绝顶之意”。
这种意念气度的“雄”必然反映在他遗留的墨迹中。
《草书杜诗卷》、《忆过中条语轴》、《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等作品完全可代表其书的“雄”,其书的“沉毅”、“深刻”甚或“奇怪”。
王铎的“自揭须眉”本身亦说明他是书中的“骏雄”而不是“贤哲”、“才子”之属。
王铎的行草书法,多为明人所喜的巨屏长卷样式,且多作于绫绢之上。
这种形制材料的选择无疑有时下风气的影响,但也离不开书家自主的取舍与偏好。
因为书写这种巨屏长卷,既便于满足书家内在心理表现的需要,同时也便于引发书家强烈盛大的创作意兴,显示书家的艺术才能。
明季书家,似乎异常偏爱这一样式,至少说明在书法方面,明季书家是非常地“有话要说的”,不如此不足以尽兴适意。
不知是因为书写长屏时的伸卷人没有伸直绫卷,影响了王铎的整体视野——写得行气时常流注偏侧——欲挣脱中轴线,还是书家有意在这个地方表示他的“无意合拍”于前人传统,反正这是王铎行草书的一个个性特征。
对此进行形式分析对于解剖王铎书法的“奇怪”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比较历史上的其他书家书法,王书的形式语言在这点上与众不同。
试举《忆过中条语》屏条为例:
开头的“予”字很谦卑——与晋人的起首字多数重大相反,“予”与“年”字的“东倒西歪”的关系暗示了一种左右冲突的潜意识。
“年十八岁过”五字迤逦左倚,至“中”字又拉回到右方来,下边的字忽左忽右,曲曲折折地贯穿到首行末尾的“望”字,按说“望”字应当与“予”字相垂直的,却不然,王铎把整整一行字的大势引向了左面,随后第二行、第三行都随了这个“大势”,但他又把第二行与第三行的行距拉近,形成了与第一行、第二行的疏行距的对比。
如此处理的结果是,整幅作品狭长的格局里,奔突着一股“奇气”——“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
”。
行距的左倚右靠,字态的东倒西歪,笔致的俯仰向背,笔墨的起伏跌宕、千回百转合奏了一首交响乐章。
这就是王铎心里的“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
”这就是王铎书法审美的意象世界!
王铎就是用这样的书法语言“说”着自己的话。
这大概就是“明人尚势”的个案与代表。
三
傅山这位传奇人物确是一位“畸士”。
他在甲申之变后“居土穴”,“着道服”,被人“荐应博学鸿儒科”,“固辞”,“尝失足堕崩岩,见风峪甚深,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终日乃出”[13]。
与王铎在他的家乡河南流传着不少“神笔王铎”的故事一样,傅山的家乡山西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写字作画的离奇故事[14]。
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很佩服他,说: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全祖望说“先生之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
”[15]傅山之名在明末清初之际真所谓朝野争知。
按照刘熙载因人论书的理论,傅山书法应该划在“历落”之属。
事实如何?
先援录几条前人的看法:
(傅山)胸中自有浩荡之思,腕下乃发奇逸之趣。
盖浸淫于卷轴者深也。
—清·秦祖永《桐荫论画》
先生学问志节,为国初第一流人物,世争重其分隶,然行草生气郁勃,更为殊观。
尝见其论书一帖云:
老董止是一个秀字。
知先生于书未尝不自负,特不欲以自名耳。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
傅山书法晋魏,正行草大小悉佳,曾见其卷幅册页,绝无毡裘气。
—清·杨宾《大瓢偶笔》
青主隶书,论者谓怪过而近于俗,然草书则宕逸浑脱,可与石斋、觉斯伯仲。
—马宗霍《霎岳楼笔谈》
青主书笔力雄奇宕逸,咄咄逼人,余尝谓顺、康间名书以王孟津为第一,今览青主书,庶可为配,且欲过之。
—赵彦棍
显见前人认为傅山书法以草书为胜擅,其草书的接受审美为:
生气郁勃——绝无毡裘气——宕逸浑脱——雄奇宕逸。
可以独拈出一个“逸”字来括之。
“无毡裘气”就是无华丽的富贵气,而有生气、逸气、山林气。
他自己告诫儿孙们: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作字示儿孙跋》
综观傅山的一生及其文艺思想的主流,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桀傲不驯、寄情烟霞、磊磊落落、大爱大憎的奇才与奇艺。
郁勃、浑脱、雄奇、宕逸的境界正是傅山独特杰出的品性胸怀、学问文章的一种迹化。
这个“国初第一流人物”继承了徐渭的浪漫主义精神传统,把王铎揭竿的反叛赵、董的旗帜高扬了起来,向古淡柔媚的时风唱出了反调。
他提出的著名的“四宁四毋”主张,与王铎的“怪、力、乱、神”的“魔鬼美学”宣言相呼应,从不同角度否定了董、赵的正统地位与艺术价值。
如果说,王铎的美学思想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傅山,那么傅山的美学思想的出现也在相当程度上拓宽和发展了王铎的艺术思想体系。
而且作为此际“艺术的难民”(阿英《海市集》),傅山更富有自己的艺术思想和主张,其思想自成体系,在历史上的影响甚至远胜过王铎。
两者的一致性是,都在回归或者复兴晋代羲献的优秀的古典主义传统的掩护下,大行各自的“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的事实,在明代盛行馆阁书的时代风习中,王、傅不仅以自己的理论更以自己的实践喝醒世人:
“傅山的书法美学,正是为了矫正当时贵族文化腐朽而来的书法领域的虚伪、奢侈、巧饰之弊”[16]。
傅山的书法精神其文化指向是平民思想的审美质朴化。
这一思想的渊源所自不妨追踪到老子与庄子。
建立在尚“真率”和“自然”之美基石上的傅山美学思想,异常鲜明地带有疑古和反叛道统的色彩。
他自负地说:
“一双空灵眼睛,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
”[17]“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话,平原气在中,毛颖中吞虏。
”[18]他强调书法的高境是“天”:
“期于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
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笔至,天也;笔不至而神至,天也。
”(《家训·字训》)
傅山的书法之“天”是什么?
是拙、丑、支离、真率,就是质朴野逸的美境。
丑拙真率,他的书法实践达到了吗?
前人认为其书达到了“宕逸浑脱”的境界。
有人质疑,认为傅山书法与其理论相去甚远。
其实不然。
傅山的书法确实是“人奇字自古”,“历落”不俗的:
“历落”与“真率”之间有必然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傅山理解的质朴自然的美就是拙、丑——不雕饰的朴素表现。
他不仅在理论上反对华丽轻滑的“媚”,他在实践上也是身体力行的。
只不过他并没有在形质的外表上简单地反“媚”——主张形质表象的质直、生拙、呆板。
他是用一股“浩荡之思”所勃发出的“浑脱”不羁之气来驾驭笔墨的。
在他笔下“吞虏”的毛颖喷薄汪洋、纵横淋漓,书之字态、行之气势,都以一个“大”字出之。
显然,他认为“大”、“浑脱”的“天”之境界已经去“媚”于霄壤了。
这种“大”便是他理悟以后提出的“拙”——大巧若拙,大美不饰,返朴还真。
因此,质疑傅山在自作中没有臻至自身理论的高度,或者认为其间极不一致的观点,是没有弄清楚傅山美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他是在追寻、祟尚大美——大巧——若拙的立场上鄙弃小美——小巧——秀媚的。
他的连绵与缠绕的圆曲线是直率历落的精神驱使下的表现。
曲中寓直,外在的屈曲盘纤正是“大”和“直”的内含外化。
傅山希望人们通过他的作品的小的“不直”看到他精神世界的“大”与“直”——“天”。
《易卦、坤卦》日: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所以,傅山在书法中追求的就是“媚”的背反,是大美,是庄周的逍遥自适。
因此他标榜化境。
这是不能简单地按图索骥、刻舟求剑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傅山的书法精神比王铎更自由、更浪漫、更抒情,表现上也就更自然、更讲究、更难以被普遍认可。
诸如《秋逸诗轴》(山西省博物馆藏)、《樵斧诗轴》(山西省博物馆藏)、《草书七绝诗轴》(刊《中国历代书法名作赏析》)、《孟浩然诗卷》(故宫博物院藏)、《丈夫垂名轴》(山西省博物馆藏)、《丹枫阁记册页》(山西省博物馆藏)、《为七伯作草书轴》(刊《中国书法》1989年第2期)等等作品代表了傅山的典型风格。
粗服乱头的傅山风格,磅礴大气,旁若无人;矜奇逞怪的王铎风格,诡变夭矫,行云流水。
毫无疑间,二者之间多有异同。
前者浑脱如草原放马,后者沉雄如金刚裂目,美何大焉!
四
仔细辨别,不难找到王、傅行草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而这区别也一定暗示了什么。
基于“形式与意境,自书法言之,乃不能分开。
意境究出于形式之后,非先有字之形质,书法不能也。
故谈书法,当自形质始”[19]的观点,不妨对比一下王、傅两家行草书:
材料 多用绫绢。
如《王铎书法选》(河南美术出版社)和《傅山书法》(山西人民出版社)中所收作品,王铎20余件墨迹,使用绫绢数为16件,而纸本仅占5件;傅山40余件墨迹使用绫绢数为30余件,而纸本为13件。
虽然,这两集所收作品仅为河南和山西两地的部分藏品,但抽样统计结果的比例仍然可以说明,王、傅二人确实都喜欢用绫本材料作书(这也是明代的一个风气)。
由于绫绢质地较纸质光滑,且有明显的纵横经纬纤维,书写时的笔墨效果自然比纸本不同,墨色易于团聚,渗化时不象宣纸那样易于出现笔痕,因此,书写时的“涨墨”和“枯笔”效果较为特殊。
这种特殊的效果王、傅两家作品共同具备,在书法史上也较有特殊性。
尽管材料的选用或有多种原因,似也不能排除对于上述特殊审美效果的一种下意识的追逐。
用笔与点划线条 王铎:
笔法内撅,方多于圆,起讫着力;线条斩截果断,沉实觚棱,夭娇多变;线型纵横欹侧,透力感强;视觉效果有精金削玉之感。
傅山:
笔法外拓,圆多于方,起讫不经意,线性浑脱虚灵,粗细突兀,轻重对比大;线型圆浑饱满,张力感强;视觉效果有枯藤盘纤之致。
王、傅两家草书,为黄山谷、祝允明、徐青藤后之重镇,不唯直接宋明余绪,实为远绍汉晋者,所谓擅作“连绵草”体。
但王铎行草质胜,力过于韵,实多于虚。
王书在法度内“极力造作”,理性精神跃然卷褚;傅书蔑视规则,意气发越,感性色彩洋溢毫颖。
如果说他们都很重视“古意”,不妨认为王的古意是晋之大王,可将王书《题柏林寺水诗轴》与王羲之的《丧乱帖》联系起来分析;而傅的古意是晋之小王,可将傅书《秋逞诗轴》与王献之的《鸭头丸》对比赏会。
就用笔而言,王铎是格守古法——王法的,傅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