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落尽见真醇.docx
《繁华落尽见真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繁华落尽见真醇.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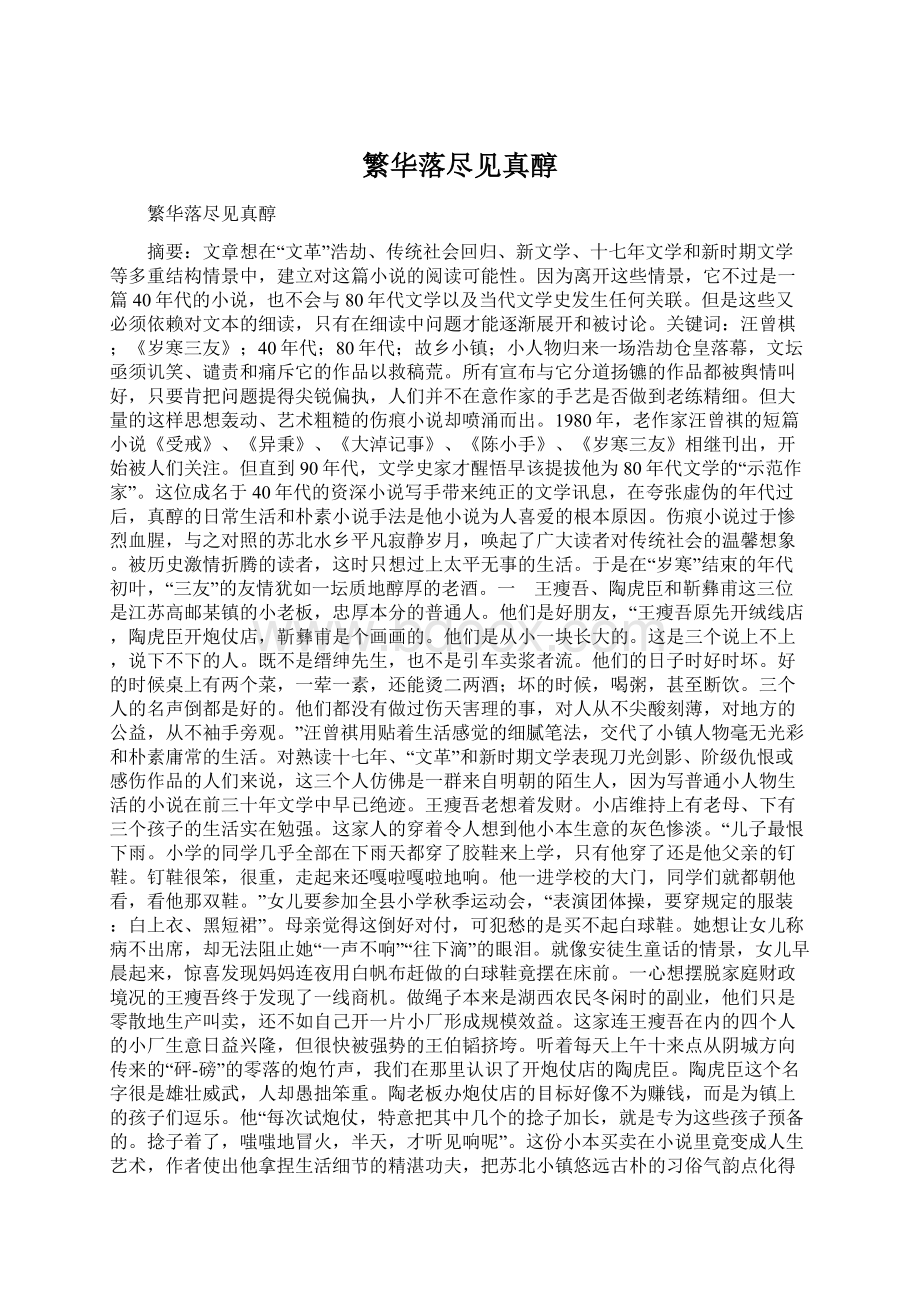
繁华落尽见真醇
繁华落尽见真醇
摘要:
文章想在“文革”浩劫、传统社会回归、新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多重结构情景中,建立对这篇小说的阅读可能性。
因为离开这些情景,它不过是一篇40年代的小说,也不会与80年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史发生任何关联。
但是这些又必须依赖对文本的细读,只有在细读中问题才能逐渐展开和被讨论。
关键词:
汪曾棋;《岁寒三友》;40年代;80年代;故乡小镇;小人物归来一场浩劫仓皇落幕,文坛亟须讥笑、谴责和痛斥它的作品以救稿荒。
所有宣布与它分道扬镳的作品都被舆情叫好,只要肯把问题提得尖锐偏执,人们并不在意作家的手艺是否做到老练精细。
但大量的这样思想轰动、艺术粗糙的伤痕小说却喷涌而出。
1980年,老作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异秉》、《大淖记事》、《陈小手》、《岁寒三友》相继刊出,开始被人们关注。
但直到90年代,文学史家才醒悟早该提拔他为80年代文学的“示范作家”。
这位成名于40年代的资深小说写手带来纯正的文学讯息,在夸张虚伪的年代过后,真醇的日常生活和朴素小说手法是他小说为人喜爱的根本原因。
伤痕小说过于惨烈血腥,与之对照的苏北水乡平凡寂静岁月,唤起了广大读者对传统社会的温馨想象。
被历史激情折腾的读者,这时只想过上太平无事的生活。
于是在“岁寒”结束的年代初叶,“三友”的友情犹如一坛质地醇厚的老酒。
一 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这三位是江苏高邮某镇的小老板,忠厚本分的普通人。
他们是好朋友,“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
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
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
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饮。
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
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
”汪曾祺用贴着生活感觉的细腻笔法,交代了小镇人物毫无光彩和朴素庸常的生活。
对熟读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文学表现刀光剑影、阶级仇恨或感伤作品的人们来说,这三个人仿佛是一群来自明朝的陌生人,因为写普通小人物生活的小说在前三十年文学中早已绝迹。
王瘦吾老想着发财。
小店维持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的生活实在勉强。
这家人的穿着令人想到他小本生意的灰色惨淡。
“儿子最恨下雨。
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的钉鞋。
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地响。
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
”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穿规定的服装:
白上衣、黑短裙”。
母亲觉得这倒好对付,可犯愁的是买不起白球鞋。
她想让女儿称病不出席,却无法阻止她“一声不响”“往下滴”的眼泪。
就像安徒生童话的情景,女儿早晨起来,惊喜发现妈妈连夜用白帆布赶做的白球鞋竟摆在床前。
一心想摆脱家庭财政境况的王瘦吾终于发现了一线商机。
做绳子本来是湖西农民冬闲时的副业,他们只是零散地生产叫卖,还不如自己开一片小厂形成规模效益。
这家连王瘦吾在内的四个人的小厂生意日益兴隆,但很快被强势的王伯韬挤垮。
听着每天上午十来点从阴城方向传来的“砰-磅”的零落的炮竹声,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开炮仗店的陶虎臣。
陶虎臣这个名字很是雄壮威武,人却愚拙笨重。
陶老板办炮仗店的目标好像不为赚钱,而是为镇上的孩子们逗乐。
他“每次试炮仗,特意把其中几个的捻子加长,就是专为这些孩子预备的。
捻子着了,嗤嗤地冒火,半天,才听见响呢”。
这份小本买卖在小说里竟变成人生艺术,作者使出他拿捏生活细节的精湛功夫,把苏北小镇悠远古朴的习俗气韵点化得栩栩如生:
“最热闹的是‘炮打泗洲城’。
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
万花齐放之后,有一个间歇”,“有人以为这一套已经放完了。
不料一声炮响,花盆子又落下一层,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洲’两个字”。
有上万双眼睛跟着陶老板的烟火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叫喊和欢笑不断。
陶老板生意曾受时局拖累,后因这年小镇躲过水灾家家都买鞭炮庆祝发了笔小财。
好景不长,一家人陷入天天喝粥的穷困日子,还以二十块价格把女儿卖给一个驻军连长。
连长日日虐待,还把脏病传给了她。
三人中间,靳彝甫是最文人气的一位老板。
“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
”他是一个业余画家,开店为虚,与人品画赏画为实。
在小说描写中,他不像生意人倒像那种心静如水的高雅隐士。
“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意思天天在艺术中自得其乐。
我们再观周围环境,“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
靠墙种了几竿玉屏萧竹。
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
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上了半寸厚德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
”他还很有骨气,与其切磋画艺的大财主兼收藏家季匋民看上他的三块田黄石章,愿意出二百大洋,可他就是不允。
作者为渲染烘托靳老板的清雅气质,最后玩了一点神秘,叫他在上海办完轰动画展后突然失踪。
说是要去“行万里路”,连最亲密的挚友王、陶都不知他的去向。
汪曾祺这时在小说结尾徐徐展开一轴画卷: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穷愁潦倒的王瘦吾、陶虎臣被突然返乡的靳彝甫邀到如意楼上喝酒。
彝甫从内衣里掏出两封洋钱,用红纸包着,一封是一百大洋。
“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
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送去了。
”在岁寒逼人和朋友落难的境况中,这一描写显然是在释放珍贵友情的温暖——靳彝甫端起酒杯说:
“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
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
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作者还特意署上这篇小说创作的时间:
“1980年8月20日初稿。
11月20日二稿。
”二 那水、那城、那风景新时期初期,批评家都不想掩饰对汪曾祺这类“乡土小说”、“风俗小说”的意外惊喜。
“汪曾祺的小说,极大部分是以他的故乡江苏高邮地区三四十年代乡镇生活为素材的。
时代的久远,地域的局限,本来会使人有点隔膜感,然而读过他作品的人,无论南北,无论老幼,却都有一种既陌生新奇又熟悉亲切的现实感。
他写的是旧社会普通人物的普通生活,写的是故乡那时代司空见惯的风俗人情,只由于作家匠心独运、笔力自逞,成就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风俗画,以及一卷卷清新淡远的南方水乡风景图。
”不仅刚摆脱“文革”噩梦的人有这种强烈的历史反差,连厌烦城市嘈杂和人与人勾心斗角的许多知识者如杨绛也深怀平静淳朴的乡愁。
她借评价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说:
“这个故事平淡无奇,没有令人回肠荡气、惊心动魄的场面。
情节无非家常琐碎,如邻居间的来往、茶叙、宴会、舞会,或驾车游览名胜,或到伦敦小住,或探亲访友等等,都是乡镇上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
人物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或模范,都是日常所见的人”,“有的高明些、文雅些,有的愚蠢些、鄙俗些”而巳。
《岁寒三友》有几处写到小镇旁边的江河水网。
王瘦吾想在商铺密布的街道上租一个铺面,产生了这类联想:
“这城里的街,好像是傍晚时的码头,各种船只,都靠满了。
”高邮地处长江中下游,距扬州60里,京杭大运河横穿南北,城内还有浩波荡漾的高邮湖。
读者能想象这种水乡环境容易培养当地人民亦文亦商的性情气质。
王瘦吾还运销过本地的药材,他用木船装运到上海,“自己就坐在一船高高的药草上,卖给药材行。
”“三叉河出一种水仙鱼,他曾想过做罐头”。
就连靳彝甫的画室和画作也是水汽蒸腾的,充满苏北水乡灵秀湿润的韵致,那里到处是“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
小说家作品中多半是水波荡漾的,《受戒》写明海和小英子的隔河对话,《故乡人·打鱼的》里是默默无语的打鱼人,到《大淖记事》那里简直是山水人物浑然一体了,“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阴城肯定不如奥斯汀笔下的英国乡村小镇那样宁静,但它的古朴神秘也颇吸引眼球。
实验炮仗新产品的陶虎臣带着我们到了那里:
“阴城市一片古战场。
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
现在还能挖出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叫做t韩瓶’,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
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
”孩子们大老远地跟着陶老板来这里毫无顾忌的放鞭炮,一是它的荒远,二是用它壮胆。
“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
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
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
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
不一会儿,又都纷纷地落下了。
”然而读者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对眼前这些小镇风物都毫无感觉,唯有小说外面的汪曾祺在冷静观察,当然从未到过苏北水乡的游客一定会大惊小怪,小说里外这层叠不同的感受,在我今天才能细细地品到。
正像杨绛评奥斯汀的小说作品一样,《岁寒三友》照样是“文笔简练,用字恰当”。
钦佩汪氏小说高超艺术的王安忆赞许地说道:
“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
”不过她也看出,这是他早“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后回复了平静”。
这是汪曾祺写风景的办法,平凡、平淡而且用字恰当,没有任何渲染。
这篇小说的风景,是与三个小人物的平淡生活连在一起的。
而这风景的平凡和平淡,则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
且不说靳彝甫画室里的布置,让读者领略到靳老板重义疏财的气质。
即使他们出生成长的小镇,作者也不愿意多费一点笔墨。
王瘦吾周围的风景是那么瘦削,只有驶往上海的木船、拎着一条鱼走过的街道、儿子上学时的雨,等等。
与陶虎臣有关的风景可能有点儿夸张,比如在阴城施放炮仗的描写,那是对他的生命形式的衬托。
汪曾祺之所以不肯多费笔墨,并不只因他“洞察秋毫装了糊涂”,而是相信读者都是知道的。
他一路老老实实地写来,他古朴老实的故乡小镇风景都在那里摆着。
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这水、城和风景之中。
中国人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对80年代初的中老年读者来说,读《岁寒三友》仿佛深刻感到经历了一次命运轮回,原来不选择激烈的社会改造也照样能过太平日子。
而在年轻读者,则好像“犹在镜中”,是那种在梦中走了一回桃花源的感觉。
难怪作者要说这些小说是托梦于“四十年代”了,他对暴力和聒噪社会运动的厌烦可能已藏其中。
三 那人与那文评价作家某篇小说最难的就是这点。
孙郁称汪曾祺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说他生于古城高邮一个知书达理的中等人家,父亲的画室堆满了字画笔墨之类的东西。
还联系到西南联大那帮散淡清高的教授为人为文对他的熏陶。
这确实是“知人论世”的一个有意思的途径。
汪曾祺也令我想起与他年龄相差无几的孙犁,他们都是来自旧年代,在新时代受过磨练最后又情不自禁地返回去写旧人旧事的精彩的小说家。
就像孙犁影响过贾平凹、铁凝等人一样,汪曾祺也对年轻的王安忆和格非有过明显的启发。
这篇《岁寒三友》给我的印象就是“简单”。
它不像王蒙新时期初期的革命小说工于心计而且老练复杂,语言真假虚实难以弄清。
也不像张贤亮的小说遍布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抄书痕迹。
他虽然一度陷入样板戏制作的可怕漩涡不能自拔,⑩但仍在革命之外。
我们不能说作者80年代写这批旧小说是为洗刷自己,但至少证明他已经幡然醒悟,还是喜爱这种简单的生活,证明他与王蒙、丛维熙和张贤亮等一千从50年代培训班毕业的革命小说家究竟不同。
《岁寒三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陶虎臣和靳彝甫为人做事的糊涂。
如果说王瘦吾生意上稍微有点精明,陶虎臣则整个是一糊涂之人。
他稀里糊涂跑到城外的阴城施放新产品,仅为取悦那些孩子;心里没有客户概念,还被“弄坏了一只眼睛”。
因为躲过水灾,镇上乡亲大买他的炮仗,这本来是一次借机提价大发横财的机会,他却与万人攒动的人群一起陶醉在“泗洲”烟火中,竟像一个傻子,完全想不到应该赶快把生意做大做强,向远近城镇迅猛扩张。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
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
——陶虎臣点着烟火了!
”小说里藏着一个隐蔽的视角,就是王、陶、靳本来就是那种“自娱自乐”的人物类型。
他们的性情来自故乡那水、那城和那风景的恩赐,除了王瘦吾到上海卖药材,靳彝甫有一次莫名其妙的外游,基本是足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