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美学思考.docx
《原创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美学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原创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美学思考.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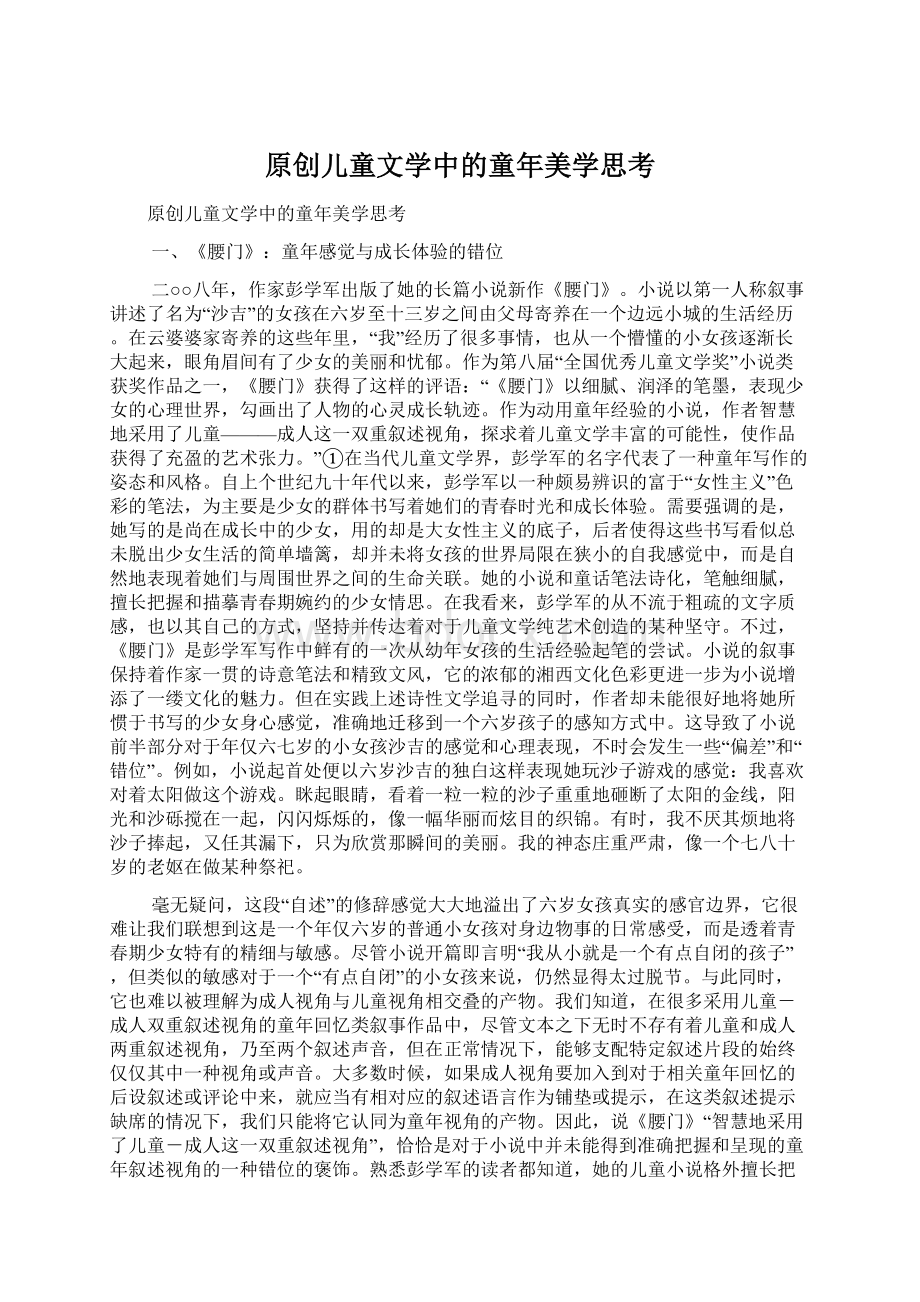
原创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美学思考
原创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美学思考
一、《腰门》:
童年感觉与成长体验的错位
二○○八年,作家彭学军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新作《腰门》。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名为“沙吉”的女孩在六岁至十三岁之间由父母寄养在一个边远小城的生活经历。
在云婆婆家寄养的这些年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从一个懵懂的小女孩逐渐长大起来,眼角眉间有了少女的美丽和忧郁。
作为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类获奖作品之一,《腰门》获得了这样的评语:
“《腰门》以细腻、润泽的笔墨,表现少女的心理世界,勾画出了人物的心灵成长轨迹。
作为动用童年经验的小说,作者智慧地采用了儿童———成人这一双重叙述视角,探求着儿童文学丰富的可能性,使作品获得了充盈的艺术张力。
”①在当代儿童文学界,彭学军的名字代表了一种童年写作的姿态和风格。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彭学军以一种颇易辨识的富于“女性主义”色彩的笔法,为主要是少女的群体书写着她们的青春时光和成长体验。
需要强调的是,她写的是尚在成长中的少女,用的却是大女性主义的底子,后者使得这些书写看似总未脱出少女生活的简单墙篱,却并未将女孩的世界局限在狭小的自我感觉中,而是自然地表现着她们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生命关联。
她的小说和童话笔法诗化,笔触细腻,擅长把握和描摹青春期婉约的少女情思。
在我看来,彭学军的从不流于粗疏的文字质感,也以其自己的方式,坚持并传达着对于儿童文学纯艺术创造的某种坚守。
不过,《腰门》是彭学军写作中鲜有的一次从幼年女孩的生活经验起笔的尝试。
小说的叙事保持着作家一贯的诗意笔法和精致文风,它的浓郁的湘西文化色彩更进一步为小说增添了一缕文化的魅力。
但在实践上述诗性文学追寻的同时,作者却未能很好地将她所惯于书写的少女身心感觉,准确地迁移到一个六岁孩子的感知方式中。
这导致了小说前半部分对于年仅六七岁的小女孩沙吉的感觉和心理表现,不时会发生一些“偏差”和“错位”。
例如,小说起首处便以六岁沙吉的独白这样表现她玩沙子游戏的感觉:
我喜欢对着太阳做这个游戏。
眯起眼睛,看着一粒一粒的沙子重重地砸断了太阳的金线,阳光和沙砾搅在一起,闪闪烁烁的,像一幅华丽而炫目的织锦。
有时,我不厌其烦地将沙子捧起,又任其漏下,只为欣赏那瞬间的美丽。
我的神态庄重严肃,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妪在做某种祭祀。
毫无疑问,这段“自述”的修辞感觉大大地溢出了六岁女孩真实的感官边界,它很难让我们联想到这是一个年仅六岁的普通小女孩对身边物事的日常感受,而是透着青春期少女特有的精细与敏感。
尽管小说开篇即言明“我从小就是一个有点自闭的孩子”,但类似的敏感对于一个“有点自闭”的小女孩来说,仍然显得太过脱节。
与此同时,它也难以被理解为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相交叠的产物。
我们知道,在很多采用儿童-成人双重叙述视角的童年回忆类叙事作品中,尽管文本之下无时不存有着儿童和成人两重叙述视角,乃至两个叙述声音,但在正常情况下,能够支配特定叙述片段的始终仅仅其中一种视角或声音。
大多数时候,如果成人视角要加入到对于相关童年回忆的后设叙述或评论中来,就应当有相对应的叙述语言作为铺垫或提示,在这类叙述提示缺席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它认同为童年视角的产物。
因此,说《腰门》“智慧地采用了儿童-成人这一双重叙述视角”,恰恰是对于小说中并未能得到准确把握和呈现的童年叙述视角的一种错位的褒饰。
熟悉彭学军的读者都知道,她的儿童小说格外擅长把握青春期少女对于“美”的特殊敏感,而在《腰门》中,这种趋于精致、复杂的少女美感经验,也多次出现在了六七岁的沙吉的叙述语言中:
门口的一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那棵快枯死的树在夕阳中熠熠生辉,有着无比瑰丽的色彩。
夕阳透过一溜雕花木窗落在灰白的地板上,依着花纹的形状,刻镂出形形色色的图形,斑驳的地板便有了几许别致的华丽。
②叶子已被岁月淘干了水分,镂空了,只剩下丝一般细细的、柔韧的叶脉,疏密有致,贴在地砖上,如剪纸一般,有一种装饰性的美丽。
③从《腰门》前半部分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段落。
这些文字令我们不时对沙吉的身份产生一种错觉,它不但影响了小说叙事的自然感、真实感,更防碍着小说意图表现的“成长”主题的深入实现。
从《腰门》的整体人物塑造和心理描写来看,沙吉从六岁到十三岁的感觉和心理,缺乏儿童成长过程中本来应有的变化和发展,或者说,作者将主人公的心灵历程做了扁平化和单一化的处理。
与沙吉逐渐增长的年龄相比,她的生活经验的确有了较大的丰富,但她的感觉和心理方式却似乎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这导致了小说中这一段贯穿始终的“六岁到十三岁”的成长,看上去仅仅成为了一种形式上的长大。
这当然并非作者的初衷。
事实上,随着主人公沙吉慢慢长成十三岁的少女,小说的叙述也开始有意无意地触及“成长”的话题。
当十三岁的“我”走进梧桐巷的木雕店,意外地与六岁时相识的“小大人”重逢时,作家为这两个有着忘年之交的朋友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对话。
“我”告诉了“小大人”“这些年来我攒下的故事和从我身边走过的人”,在默默地听完这一切后,已经长成大人的“小大人”这样说道:
“我明白了,沙吉,你就是这样长大的。
”
就在同一天,作者以少女初潮的降临为这段成长的岁月画上了一个标志性的记号。
不过,在这里,相关“长大”的领悟是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直接“说”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从七年来沙吉的生活经历中自不过然地感受到的。
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女孩而言,“七年”的时间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身心变化,但这种变化感在《腰门》的叙事中恰恰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展开。
小说中,作者用她擅长的敏感、多情、多思的少女心理描绘,替代了对于主人公从幼年到少年时代心理和情感世界的长度和过程的描绘。
这一文本事实提醒我们,童年生命在生理或文化上的“长大”过程,并不如其外表所显现的那样易于描摹。
在现实的童年生活中,儿童的成长是伴随着个体年龄的变化自然发生的,但在儿童文学的艺术世界里,仅仅是年龄的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生活闻见的变化,尚不足以构成成长的充分条件。
相反,儿童文学所表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体验,恰恰不是由简单的年龄或生活变迁来标记的。
彭学军本人的另一篇题为《十一岁的雨季》的短篇儿童小说,可以作为这方面很好的例证。
在我看来,《十一岁的雨季》在书写和表现少女的成长感觉和成长体悟方面达到了某种令人称道的高度。
小名驼驼的体校长跑运动员出于青春期少女对身体美的敏感而暗怀着一份体操情结。
在训练场上奔跑和休息的她总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体操区,在那里,少女邵佳慧优雅的体操动作莫名地吸引着她全部的注意力和激情。
当她得知对于体操运动来说,自己已经“太老了”的时候,身体里的某种美妙的东西好像随着这个梦想的破灭而消失了,直到有一天,她从邵佳慧口中意外地听到了她对于跑道上的自己的由衷赞美。
透过两个少女远远地彼此观看和欣赏的目光交错,属于少女时代的那种如微电流般敏锐、精细而又捉摸不定的青春情感脉动,在小说的文字间得到了充分、生动和妥帖的呈现。
小说仅仅截取了十一岁少女生活的某一段落,其时间跨度并不明显,个中角色的生活内容甚至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这些“不变”的因素丝毫不影响作品成长题旨的表现。
小说中,成长的意义在根本上不取决于童年生活环境的变迁,而是表现为生命意识的一种内在的感性顿悟与提升。
在领悟到“我”和邵佳慧之间的彼此对望意味着什么的一刹那,少女生活中某个幽暗的角落忽然被点亮了。
这样一种打开生命的光亮感,才是童年成长美学的核心精神所在。
这并不是说童年成长的美学表现与时间无关。
《腰门》表现时间的变化,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时间的变化中,我们却看不到童年自身的内在变化,因为从一开始,作者实际上就不自觉地将主人公的童年感觉定格在了青春期少女的视角上,而这一视角原本在作家笔下可能获得的表现深度,又在这样的感觉错位中遭到了消解。
这才是这部小说所存有的最大艺术问题。
多年来,我对彭学军儿童小说的总体艺术品质一直怀有充分的信任,但实事求是地讲,《腰门》在童年感觉和成长体验书写方面的上述缺憾,使它在彭学军的作品序列中算不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这与近年来它从相关评奖机构和评论界获得的诸多肯定、赞誉形成了另一种事实上的错位关系。
这些赞誉大多集中在对于作品个性化的童年题材、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诗化的叙事笔法的肯定上,却未能关注到其叙事展开在童年美学层面的深刻问题。
我要说的是,这种错位,同时也传达出了当前原创儿童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童年美学判断方面的双重缺失。
二、《青铜葵花》:
童年苦难及其诗意的再思考
与显然带有童年回忆性质的《腰门》相比,曹文轩的长篇儿童小说《青铜葵花》,其写作包含了明确得多的童年精神书写的审美意图。
在题为“美丽的痛苦”的代后记中,作者强调了儿童文学写作直面童年的苦难以及表现童年生命如何理解和承担这类苦难的精神意义与价值。
作家的这一立场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他严辞批判当下流行的“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的狭隘创作观念,认为“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同样是对童年不负责任的一种文化态度。
他进而指出,在儿童文学能够提供给孩子的阅读快感中,理应包含另一种与苦难相关的“悲剧快感”,它比那类浮浅褊狭的快乐主义更能够丰富童年的生活体验,深化他们对于生命之真“美”的认识。
《青铜葵花》的写作“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①这一富于现实批判意义的创作立场,代表了一种鲜明的童年理解的精神姿态。
无论是从当下童年的生存现实还是儿童文学的艺术追求来看,这一姿态的积极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在这里,苦难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名词,落实到文学表达的实践中,这一苦难的所指究竟为何,关于它的书写又以何种方式在儿童文学的文本内部得到确立,这才是我们得以确认苦难之于童年和儿童文学写作之意义的根本依据。
在《青铜葵花》中,曹文轩为他笔下的童年角色安排的“苦难”经历,大抵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贫穷的生活,二是不幸的变故,二者以典型的天灾人祸的方式先后降临在童年的生活中。
小女孩葵花跟随知青父亲下乡,不料父亲意外溺亡,葵花成了孤儿。
举目无亲的时候,收养她的是大麦地最贫穷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另一个同样不幸的孩子青铜,幼年时因高烧成了哑巴,再不能开口说话。
两个孩子与家人在艰难的生活中相依为命,却又先后遭逢水灾、蝗灾,不但刚刚积蓄起来的一丁点儿生活的期待成了泡影,更要忍受饥饿、病痛和死亡的威胁。
在所有这一切生存的现实“苦难”中,照亮青铜和葵花生命的,是他们彼此间患难与共的兄妹情谊,以及一家人之间毫无计较的相互爱护、关怀、理解和温暖。
《青铜葵花》对于童年苦难事件的上述集中书写和呈现,足以使它成为童年苦难母题在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中的重要代言作品。
不过,这样一种密集、“典型”的童年苦难叙事,与其说是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童年生活苦难的自然呈现,不如说透着更多人为的文学安排痕迹。
这并不是指那时的孩子所经历的苦难不见得这样深重,而是指小说对于其中某些显然被界定为苦难对象的事件的文学叙写,似乎不自觉地离开了现实生活的自然逻辑,甚至赋予了它们某种脱尘出世的非现实感。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小说对于死亡意象的浪漫处理。
例如,葵花的父亲,一位热爱葵花的雕塑家,是在一次意外的行舟中因落水而辞世的。
对于女孩葵花来说,深爱着她的父亲的离去,是她在大麦地所遭逢的生活悲剧的序幕。
不过,从小说的这部分叙述段落来看,雕塑家的溺亡更像是一场浪漫的“自决”。
当其时,他手中的一叠葵花画稿被旋风卷到空中,继而又飘落在水面上:
说来也真是不可思议,那些画稿飘落在水面上时,竟然没有一张是背面朝上的。
一朵朵葵花在碧波荡漾的水波上,令人心醉神迷地开放着。
当时的天空,一轮太阳,光芒万丈。
①这样一幅犹如天喻般的景象,使雕塑家如着魔般“忘记了自己是在一只小船上,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不习水性的人,蹲了下去,伸出手向前竭力地倾着身体,企图去够一张离小船最近的葵花,小船一下倾覆了……”②如此浪漫的意外很难使我们联想到与真实苦难相关的任何身体和精神上的强力压迫,反而像是一次超越生活的艺术表演。
事实上,这种对于“苦难”事件的浪漫呈现,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基本手法。
当老槐树下成为孤女的葵花面临着无依无着的命运时,青铜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