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论新探覃方明.docx
《社会学方法论新探覃方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学方法论新探覃方明.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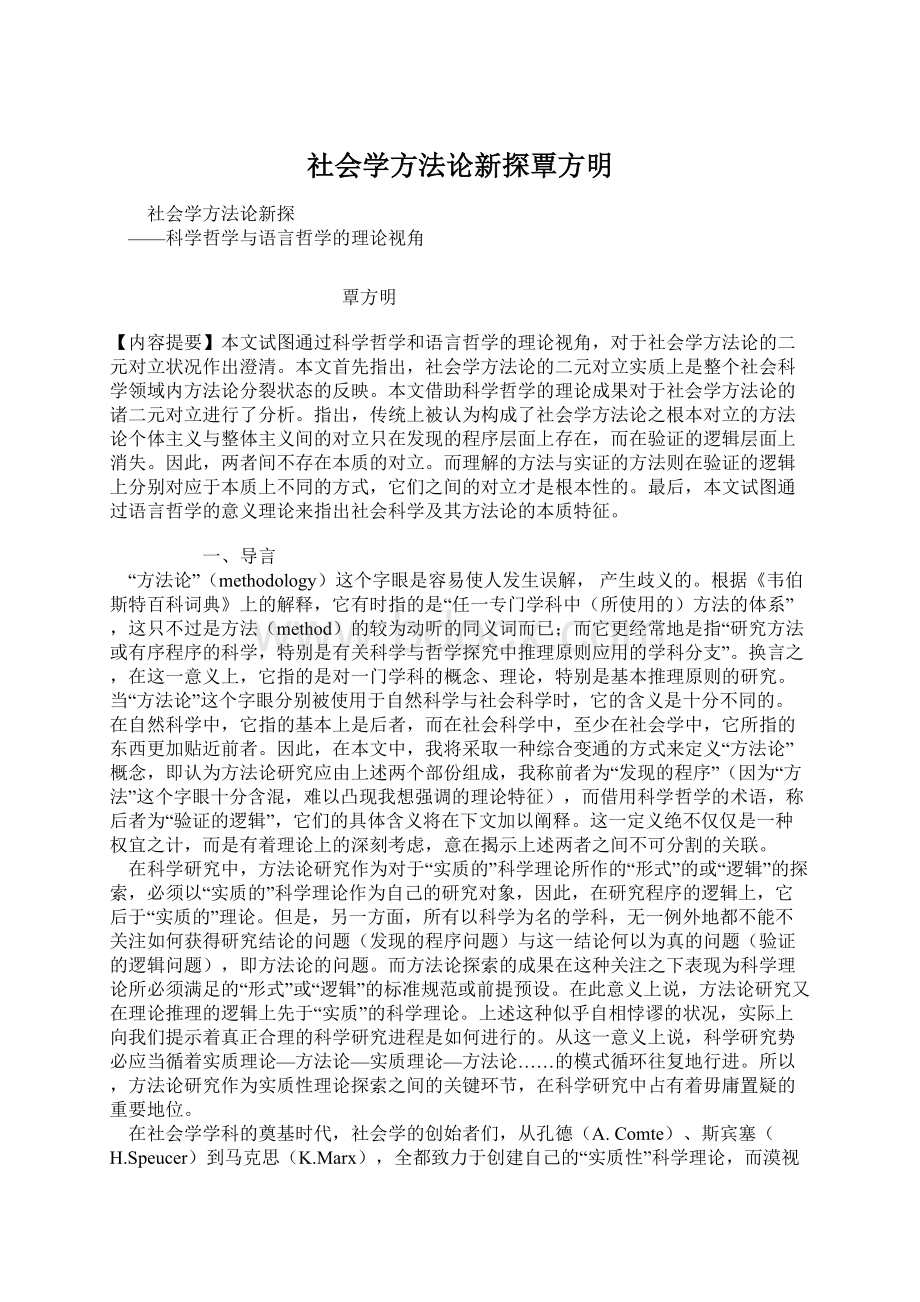
社会学方法论新探覃方明
社会学方法论新探
——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
覃方明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状况作出澄清。
本文首先指出,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实质上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分裂状态的反映。
本文借助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诸二元对立进行了分析。
指出,传统上被认为构成了社会学方法论之根本对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间的对立只在发现的程序层面上存在,而在验证的逻辑层面上消失。
因此,两者间不存在本质的对立。
而理解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则在验证的逻辑上分别对应于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才是根本性的。
最后,本文试图通过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来指出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的本质特征。
一、导言
“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个字眼是容易使人发生误解,产生歧义的。
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上的解释,它有时指的是“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这只不过是方法(method)的较为动听的同义词而已;而它更经常地是指“研究方法或有序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
换言之,在这一意义上,它指的是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特别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
当“方法论”这个字眼分别被使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时,它的含义是十分不同的。
在自然科学中,它指的基本上是后者,而在社会科学中,至少在社会学中,它所指的东西更加贴近前者。
因此,在本文中,我将采取一种综合变通的方式来定义“方法论”概念,即认为方法论研究应由上述两个部份组成,我称前者为“发现的程序”(因为“方法”这个字眼十分含混,难以凸现我想强调的理论特征),而借用科学哲学的术语,称后者为“验证的逻辑”,它们的具体含义将在下文加以阐释。
这一定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有着理论上的深刻考虑,意在揭示上述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研究作为对于“实质的”科学理论所作的“形式”的或“逻辑”的探索,必须以“实质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在研究程序的逻辑上,它后于“实质的”理论。
但是,另一方面,所有以科学为名的学科,无一例外地都不能不关注如何获得研究结论的问题(发现的程序问题)与这一结论何以为真的问题(验证的逻辑问题),即方法论的问题。
而方法论探索的成果在这种关注之下表现为科学理论所必须满足的“形式”或“逻辑”的标准规范或前提预设。
在此意义上说,方法论研究又在理论推理的逻辑上先于“实质”的科学理论。
上述这种似乎自相悖谬的状况,实际上向我们提示着真正合理的科学研究进程是如何进行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势必应当循着实质理论—方法论—实质理论—方法论……的模式循环往复地行进。
所以,方法论研究作为实质性理论探索之间的关键环节,在科学研究中占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
在社会学学科的奠基时代,社会学的创始者们,从孔德(A.Comte)、斯宾塞(H.Speucer)到马克思(K.Marx),全都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实质性”科学理论,而漠视方法论的探究。
从上文所指出的科学研究程序的逻辑之视角看来,这种状况是很自然的。
但与此同时,孔德、斯宾塞与马克思全都受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的重大影响,在他们构建自己的“实质性”科学理论的时候,这些理论与方法潜移默化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标准与前提预设渗透融合进了他们的思想理论之中。
虽然在他们的思想理论中,这种渗透融合的侧重点、程序与表现方式等都各不相同。
社会学学科中自觉的方法论探索始于第二代经典作家们,特别是迪尔凯姆(E.Durkheim)与韦伯(M.Weber)。
然而伴随着这一自觉的方法论探索的开始,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论争与对立也产生了。
众所周知,迪尔凯姆大力提倡整体主义的(holistic)、实证的(positive)方法论,而韦伯与之针锋相对地坚持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理解的(understanding)方法论主张。
在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中,这两种方法论主张分别与迪尔凯姆和韦伯所秉持的彼此对立的社会本体论见解——即,社会唯实论对社会唯名论——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这两种社会本体论立场在方法论领域中逻辑推衍的结果。
然而,从当时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上看来,这两种方法论之间的对立,实质上反映着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状况上的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的对立:
第一种倾向是方法论一元论的主张,即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普适的准则,既适合于自然科学,也同样适合于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只是研究对象、研究工具与研究精度的差异,而在基本的理论推理原则上并无差别。
另一种倾向是方法论的二元论乃至多元论,这种主张认为,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方法论特质,因此,社会科学不可能也不应当在方法论上效法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涉及方法论的根本性质,这一差异无法在一个统一的方法论之内得到弥合。
自上世纪末以来,就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上述两大方法论倾向之间的对立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此期间,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倾向在不断的论争中砥砺自己的理论武器,但时至今日,在难以达成理论共识的情形下,这两种倾向间的对立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束之高阁,存而不论。
然而,一般说来,就各个单独的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它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未因这种搁置所造成的方法论上不统一的局面而受到多少伤害。
这是因为,就每一单独的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它实际上已经在上述两种倾向中作出了符合自己学科根本性质的方法论抉择。
它要么选择接受方法论一元论的基本立场,在方法论上效仿自然科学的特征,追求描述现象之规律性的普适科学(如经济学);要么选择接受方法论多元论的主张,坚持认为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自有其独特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性质,致力于描述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甚至是不可观察的进程与情境(如史学与人类学)。
因此,尽管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上的分裂局面与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内方法论的基本统一适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对于每一单独的、具体的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在学科内部,其方法论立场基本上仍是统一的,尽管可能有局部的、暂时的例外。
唯独社会学这一后发的综合性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涉及以上两类社会科学学科的领域,也由于其学术抱负是试图以统一的方式来刻画整个人类社会体系的状况,所以,不得不单独面对在基本方法论立场上分裂的状况所造成的困境。
在社会学学科内部,从韦伯与迪尔凯姆的时代开始,在方法论主题上的对立与论争贯穿了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
方法论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对立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的”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
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
长期以来,虽然大多数社会学家默认了这一分裂状况,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于彼此对立的方法论立场作出了选择,但是,这一分裂局面仍然引起了关注本学科统一性与学术规范之基础的社会学家们的忧虑,他们力图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来弥合这种分裂。
然而,由于这类弥合分裂的努力大都囿于实质性理论与具体研究程序的范围之内,而并未涉及方法论的层面,因此,不夸张地说,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社会学方法论上分裂的局面产生于迪尔凯姆与韦伯的理论观点之间的对立,并且,在我看来,多年来,尽管在社会学的实质性理论的领域内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但是社会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格局仍然是上述两者之间的对立,并无明显的变化。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在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时代,得到公认的、占有统治地位的科学方法论理论乃是由培根(FrancisBacon)于17世纪前叶奠定其基础,而由穆勒(JohnStuartMill)于19世纪中叶予以完善的归纳论,这种主张尽管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遭到休谟(DavidHume)的严厉质疑,并在当时也已开始受到马赫(ErnstMach)等人思想的猛烈冲击,但仍然是当时科学方法论领域的头号权威。
我们不难在诸如迪尔凯姆的方法论主张中看到它的影响。
然而,就在迪尔凯姆与韦伯分别确立自己的方法论主张前后,二十世纪初叶,物理学革命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理论面貌,归纳论被摒弃了,由此开始了自然科学方法论领域的一个深入探索、不断创新的蓬勃发展的新时代,科学方法论研究也由此一变而成为显学。
从19世纪末叶以来,人们在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史)领域内的理论探索便构成了现代科学哲学。
我们的问题是,尽管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状况的形成涉及当时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权威理论——归纳论,但是,这一状况与归纳论之后的自然科学方法论新的理论探索——现代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现代科学哲学摒弃了归纳论,那么它是否能够消解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引入了归纳论才得以形成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状况呢?
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利用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来分析研究社会学方法论领域中主要的二元对立。
但在进行这一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解决有关将科学哲学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时的适用范围的问题——论域问题。
二、科学哲学的理论脉络与论域问题
要解决科学哲学的论域问题,即,哪些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能够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科学哲学理论上的传承关系予以澄清,对于科学方法论的主题、概念、理论等等在历史脉络中的承袭嬗变、更替扬弃的过程有所了解。
如前所述,近代科学方法论探索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培根的归纳论,就我们所关注的与论域问题有关的层面来说,归纳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虽然培根本人也未必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归纳论既是科学研究实际程序的模式方法(发现的程序),又是科学理论得到验证的逻辑标准(验证的逻辑)。
而后来休谟从逻辑角度对归纳论所作的严厉批判,并未否认归纳论作为发现的程序的地位(虽然在今天的科学史研究看来,这一地位也是深可怀疑的),而是质疑归纳论作为验证的逻辑的资格。
物理学革命的爆发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归纳论的破产。
因为在归纳论的知识直线累积模式中根本就没有科学革命发生的可能。
由物理学革命所孕育产生的现代科学哲学,面对着牛顿力学这一在几个世纪中被奉为真理的科学体系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摧垮的残酷历史事实,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验证的逻辑问题之上。
因此,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波普尔(KarlPopper)的证伪主义,现代科学哲学的早期研究探索几乎都围绕着验证的逻辑这一主题进行。
逻辑实证主义甚至不无偏激地将科学方法论等同于对验证的逻辑的研究,而将有关发现的程序的研究称之为“发现的心理学”,认为这一领域充斥着不确定的偶然因素,无法用理性来加以把握,因此应当将其摒除于科学方法论之外。
波普尔的理论思想诚然没有这么偏激,他所提出的猜想——反驳的理论图式实际上就属于发现的程序范围。
但是,即使是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也同样将验证的逻辑置于理论的根本基础的地位,而将发现的程序建筑于验证的逻辑之上。
在他的理论中,验证的逻辑就是对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要求,猜想——反驳的科学发展图式是奠基于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之上的。
所有这些围绕着验证的逻辑主题进行的方法论研究,都致力于解答“科学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因而这些研究所获得的理论结论,都表现为从外在于科学研究领域的立场对于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方法论上的规范。
在本世纪中叶,由库恩(Thomas Kuhn )、费耶阿本德( PaulFeyerabend)、汉森(N.R.Hanson )等人所创立的科学哲学中的社会历史学派造成了科学哲学中所谓的“历史主义转向”。
这一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主要理论兴趣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变。
简要说来,这一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理论兴趣从验证的逻辑转向发现的程序,从科学方法论转向科学史,从规范转向事实。
在库恩们看来,前者虽然是逻辑上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却是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