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柳人家三年级作文.docx
《蒲柳人家三年级作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蒲柳人家三年级作文.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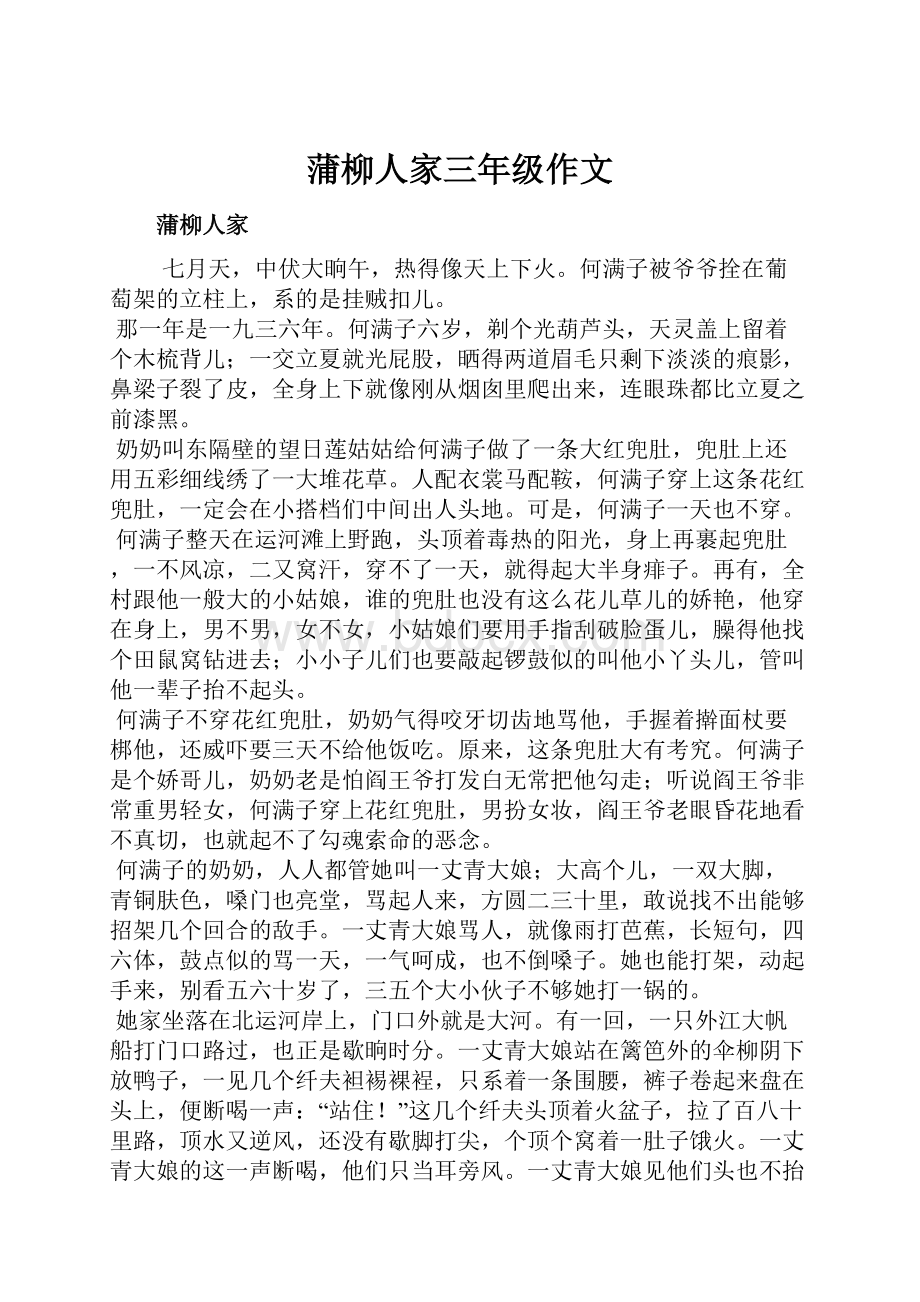
蒲柳人家三年级作文
蒲柳人家
七月天,中伏大晌午,热得像天上下火。
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系的是挂贼扣儿。
那一年是一九三六年。
何满子六岁,剃个光葫芦头,天灵盖上留着个木梳背儿;一交立夏就光屁股,晒得两道眉毛只剩下淡淡的痕影,鼻梁子裂了皮,全身上下就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连眼珠都比立夏之前漆黑。
奶奶叫东隔壁的望日莲姑姑给何满子做了一条大红兜肚,兜肚上还用五彩细线绣了一大堆花草。
人配衣裳马配鞍,何满子穿上这条花红兜肚,一定会在小搭档们中间出人头地。
可是,何满子一天也不穿。
何满子整天在运河滩上野跑,头顶着毒热的阳光,身上再裹起兜肚,一不风凉,二又窝汗,穿不了一天,就得起大半身痱子。
再有,全村跟他一般大的小姑娘,谁的兜肚也没有这么花儿草儿的娇艳,他穿在身上,男不男,女不女,小姑娘们要用手指刮破脸蛋儿,臊得他找个田鼠窝钻进去;小小子儿们也要敲起锣鼓似的叫他小丫头儿,管叫他一辈子抬不起头。
何满子不穿花红兜肚,奶奶气得咬牙切齿地骂他,手握着擀面杖要梆他,还威吓要三天不给他饭吃。
原来,这条兜肚大有考究。
何满子是个娇哥儿,奶奶老是怕阎王爷打发白无常把他勾走;听说阎王爷非常重男轻女,何满子穿上花红兜肚,男扮女妆,阎王爷老眼昏花地看不真切,也就起不了勾魂索命的恶念。
何满子的奶奶,人人都管她叫一丈青大娘;大高个儿,一双大脚,青铜肤色,嗓门也亮堂,骂起人来,方圆二三十里,敢说找不出能够招架几个回合的敌手。
一丈青大娘骂人,就像雨打芭蕉,长短句,四六体,鼓点似的骂一天,一气呵成,也不倒嗓子。
她也能打架,动起手来,别看五六十岁了,三五个大小伙子不够她打一锅的。
她家坐落在北运河岸上,门口外就是大河。
有一回,一只外江大帆船打门口路过,也正是歇晌时分。
一丈青大娘站在篱笆外的伞柳阴下放鸭子,一见几个纤夫袒裼裸裎,只系着一条围腰,裤子卷起来盘在头上,便断喝一声:
“站住!
”这几个纤夫头顶着火盆子,拉了百八十里路,顶水又逆风,还没有歇脚打尖,个顶个窝着一肚子饿火。
一丈青大娘的这一声断喝,他们只当耳旁风。
一丈青大娘见他们头也不抬,理也不理,气更大了,又吆喝了一声:
“都给我穿上裤子!
”有个年轻不知好歹的纤夫,白瞪了一丈青大娘一眼,没好气地说:
“一大把岁数儿,什么没见过;不爱看合上眼,掉过脸去!
”一丈青大娘火了起来,挽了挽袖口,手腕子上露出两只叮叮当当响的黄铜镯子,一阵风冲下河坡,阻挡在这几个纤夫的面前,手戳着他们的鼻子说:
“不能叫你们腌-了我们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
”那个不知好歹的年轻纤夫,是个生楞儿,用手一推一丈青大娘,说:
“好狗不挡道!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
一丈青大娘怒发冲冠,老大一个耳刮子抢圆了扇过去;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乍篷,转了三转,拧了三圈儿,满脸开花,口鼻出血,一头栽倒在滚烫的沙滩上,紧一口慢一口倒气,高一声低一声呻吟。
几个纤夫见他们的搭档挨了打,唿哨而上;只听咯吧一声,一丈青大娘折断了一棵茶碗口粗细的河柳,带着呼呼风声挥舞起来,把这几个纤夫扫下河去,就像正月十五煮元宵,纷纷落水。
一丈青大娘不依不饶,站在河边大骂不住声,还不许那几个纤夫爬上岸来;大帆船失去了纤力,掌舵的绽裂了虎口,也驾驭不住,在河上转开了磨。
最后,还是船老板请出了摆渡船的柳罐斗,钉掌铺的吉老秤,老木匠郑端午,开小店的花鞋杜四,说和了两三个时辰,一丈青大娘才算开恩放行。
一丈青大娘有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种地、撑船、打鱼都是行家。
她还会扎针、拔罐子、接生。
接骨、看红伤。
这个小村大人小孩有个头痛脑热,都来找她妙手回春;全村三十岁以下的人,都是她那一双粗大的手给接来了人间。
不过,别看一丈青大娘能镇八方,她可管不了何满子。
何家世代单传,辈辈一棵苗,何满子的爷爷就是老生儿,他父亲也是在一丈青大娘将近四十岁时才落生的;偏是何满子不同凡响,是他母亲头一胎生下来的贵子。
一丈青大娘一听见孙子呱呱坠地的啼声,喜泪如雨,又烧香又上供,又拜佛又许愿。
洗三那天,亲手杀了一只羊和三只鸡,摆了个小宴;满月那天,更杀了一口猪和六只鸭,大宴乡亲。
她又跑遍沿河几个村落,挨门挨户乞讨零碎布头儿,给何满子缝了一件五光十色的百家衣;百日那天,给何满子穿上,抱出来见客,博得一片彩声。
到一周岁生日,还打造了一个分量不小的包铜镀金长寿锁,金光闪闪,差一点把何满子勒断了气。
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
这一来,一丈青大娘可就跟儿媳妇发生了锋利的矛盾。
何满子的父亲,十三岁到通州城里一家书铺学徒,学的是石印。
他学会一笔好字,也学会一笔好画,人又长得娟秀,性情十分温顺,掌柜的很中意,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何满子的爷爷虚荣心强,好攀高枝儿,眉开眼笑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一丈青大娘却不大乐意;她不喜爱城里人,想给儿子找个农家或船家姑娘做妻子,能帮她干活,也能支撑门户。
可是,她拗不过老头子,也怕伤了儿子的心,不乐意也只得同意了。
何满子的母亲不能算是小姐出身,她家那个小书铺一年也只能赚个温饱;可是,她到底是文墨小康之家出身,虽没上过学,却也熏陶得一身书香,识文断字。
她又长得好看,身子薄弱,言谈举止非常斯文,在一丈青大娘的眼里,就是一朵中看而无用的纸花,心里不喜欢。
何满子的母亲更看不上婆婆的粗野,在乡下又住不惯,一住娘家就不想回来。
等生下了何满子,何满子的父亲就想在城里另立个家。
一丈青大娘是个爱面子的人,分家丢脸,可是一家子鸡吵鹅斗,也惹人笑话;白叟家左右尴尬,偷偷掉了好几回眼泪。
但是,前思后想,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到了儿点了头。
不过,却有个条件,那就是儿媳妇不能把何满子带走。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何满子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
最后,还是请来摆渡船的柳罐斗,钉掌铺的吉老秤,老木匠郑端午,开小店的花鞋杜四,说和三天三夜,婆媳俩才算讲定,何满子上学之前,留在奶奶身边;该上学了,再接到城里跟父母团聚。
何满子在奶奶身边长大,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
长到四五岁,就像野鸟不入笼,一天不着家,整日在河滩野跑。
奶奶八样不放心,怕让狗咬了,怕让鹰抓了,怕掉在土井子里,怕给拍花子的拐走。
白叟家胆战心惊,就像丢了魂儿,出来进去团团转,扯着一条亮堂嗓门儿,村前村后,河滩野地,喊哑了嗓子。
何满子却隐匿在柳棵子地里,深藏到芦苇丛中,埋伏在青纱帐内的豆棵下,跟奶奶捉迷藏,暗暗发笑。
等到天黑回家去,奶奶抄起顶门杠子,要敲碎何满子的光葫芦头;何满子一动不动,眼皮眨也不眨,奶奶只得把顶门杠子一扔,叫了声:
“小祖宗儿!
”回到屋里给孙子做好吃的去了。
不是煮鸡蛋,就是烙白面饼。
这一天,何满子的爷爷回来了。
一丈青大娘跟老头子叨唠这个,嘟哝那个,老头子阴从容脸,哼哼哈哈,一脑门子官司;一丈青大娘气不打一处来,跟老头子叫起了苦,顺口就给何满子告了状。
爷爷是个风火性儿,一怒之下,就把何满子拴在了葡萄架的立柱上,系的是拴贼扣儿,跑不了更飞不了。
而且,在他面前扔下一个纸盒,盒子里有一百个方块字码,还有一块石板和一支石笔,勒令他在这一个歇晌的工夫,把这一百个字写下来。
这倒难不住何满子。
可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失去自由,心里委屈而又憋闷,两眼直呆呆,双手懒洋洋,一点也没有写字的兴致。
不敢有劳王母娘娘的大驾!
”何大学问叹了口气,“我给何家的这个小祖宗儿当大脚老妈子。
”何满子的爷爷,官讳已不可考。
但是,如果提起他的绰号,北运河两岸,古北口内外,在卖力气走江湖的人们中间,那可真是叫得山响。
他的绰号叫何大学问。
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面如重枣,浓眉朗目,一副关公面貌。
年轻的时候,当过义和团,会耍大刀,拳脚上也有两下子。
以后,他给地主家当赶车把式,会摆弄牲口,打一手好鞭花。
他这个人好说大话,自吹站在通州东门外的北运河头,抽一个响脆的鞭花,借着水音,天津海河边上都震耳朵。
他又好喝酒,脾气大,爱打抱不平,为朋友敢两肋插刀,所以在哪一个地主家都呆不长。
于是,他就改了行,给牲口贩子赶马;一年有七八个月出入古北口,往返于塞外和通州骡马大市之间,奔走在长城内外的古驿道上。
几百匹野马,在他那一杆大鞭的管束下,乖乖地像一群温驯的绵羊。
沿路的偷马贼,一听见他的鞭花在山谷间回响,急忙四散奔逃,躲他远远的。
所以,他不但是赶马的,还是保镖的,牲口贩子都抢着雇他。
这一来,他的架子大了,不三顾茅庐,他是不出山的;至于脚钱多少,倒在其次,要的就是刘皇叔那样的礼贤下士。
他这个人,不知道钱是好的,伙友们有谁家揭不开锅,沿路上遇见老、弱、病、残,伸手就掏荷包,抓多少就给多少,也不点数儿;所以出一趟口外挣来的脚钱,到不了家就花个净光。
在这个小村,数他走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他又好戴高帽儿,讲排场,摆阔气。
出一趟口外,本来挣不了多少钱,而且到家之前已经花得不剩分文,但是回到村来,却要装得仿佛腰缠万贯;跟牲口贩子借一笔驴打滚儿,也要大摆酒筵,请他的知音相好们前来聚会,听他谈讲过五关,斩六将,云山雾罩。
他这个人非常富裕想象力,编起故事来,有技有叶,有文有武,生动波折,惊险红火。
于是,人们一半是戏谑,一半是尊敬,就给他送了个何大学问的绰号。
自从他被尊称为何大学问以后,他也真在学问上下起功夫来了。
过去,他好听书,也会说书;在荣膺这个尊称之后,当真看起书来。
他腰里常常揣着个北京者二酉堂出版的唱本,投宿住店,歇脚打尖,他就把唱本掏出来,咿咿哦哦地嘟念。
遇上生字儿,不耻下问,而且舍得掏学费;谁教他一字一句,他能请这位白吃一顿酒饭。
既然人称大学问,那就要打扮得斯文模样儿,干是穿起了长衫,说话也咬文嚼字。
人们看见,在长城内外崇山峻岭的古驿道上,这位身穿长衫的何大学问,骑一匹光背儿马,左肩挂一只书囊,右肩扛一杆一丈八尺的大鞭,那形象是既威风凛凛又滑稽可笑。
而且,路遇文庙,他都要下马,作个大揖,上一股高香。
本来,孔夫子门前早已冷落,小城镇的文庙十有八九坍塌破败,只剩下断壁残垣,湮没于蓬蒿荆棘之中,成为鸟兽栖聚之地;他这一作揖,一烧香,只吓得麻雀满天飞叫,野兔望影而逃。
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何大学问也常常感到阵阵悲凉。
自家祖宗八辈儿,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都是睁眼瞎。
自个儿跳-了大半辈子,已经年过花甲,不过挣下三间泥棚茅舍,八亩河滩洼地;尽管被人尊称大学问,可从没进过学堂一天,斗大的字认不得三筐,而且只会念不会写。
儿子天生文质,也只念了三年私塾,就不得不到书铺学徒。
看来,何家要出个真正大学问,只有指望孙子何满子了。
可是,衡量一下自己这点财力,供他念完中小学,已经是鼓着肚子充胖;而实验中学大学的门槛九丈九尺高,没有白花花的银洋砌台阶,怎么能高攀得上?
自己已经老迈年高,砸碎了骨头也榨不出几两油来;难道孙儿到头来也要落得个赶马或是学徒的命运?
何满子也真是聪明灵秀,脑瓜儿记性好,爱听故事,过耳不忘;好问个字儿,过目不忘。
何大学问在孙子面前假充圣人,把他的那些唱本传授给孙子;何满子就像春蚕贪吃桑叶,一册唱本不够他几天念的。
何大学问惊喜过望,就想求个名师指点。
正巧他在赶马路上,在一座骡马大店里,遇见一位前清的老秀才,在这座骡马大店里当账房先生,写一手魏碑好字;店里生意冷清,掌柜的打算解雇这个穷儒。
何大学问脑瓜子一热,就礼聘这位老秀才到他家教专馆,讲定教一个字给一个铜板。
老秀才来到何家,就在葡萄架下开讲。
他高高在上,坐一张太师椅,手拿一杆斑竹白铜锅的长杆烟袋;何满子低首俯身,坐个蒲团儿,面前一张小饭桌,就像被老秀才踩在脚下。
老秀才整天板着一张阴沉沉的长脸,何满子抬头一看,只觉得头上压着一朵乌云,叫人喘不过气。
老秀才又酸气冲天,开口诗云子曰,闭口之乎者也,何满子只觉得干燥乏味,更加闷闷不乐。
他本是个整天跑野马的孩子,从早到晚关在家里,难受得屁股下坐立不安,身上像芒刺在背。
念着书,一听见篱笆外柳树梢上莺啼燕啭,就想嘬着嘴唇学鸟叫,念书跑了调儿;一听见门外过往行船的纤歌声,心里就七上八下,想跑出去看一看,念书走了神儿。
老秀才的眼睛尖得像锥子,一见他的身子动了动,就伸出斑竹白铜锅的长杆烟袋,敲他的光葫芦头;每敲一下,就肿起一个枣子大的青包,何满子恨透了老秀才。
一丈青大娘见孙子天天挨打,心疼得就像一块一块剜肉;只有何大学问认定不打不成材,非但不怪罪老秀才学规森严,而且还从旁给老秀才呐喊助威。
何大学问每天款待老秀才三顿净米净面,外加一壶酒;这个场面,穷门小户怎能支撑得住?
不到一个月,何大学问就闹了饥荒,拉下了斗大的亏空,只得又去赶马。
何大学问一走,何满子就像野马摘了笼头;天不亮,头顶着星星,脚膛着露水,从家里溜出去,逃开了学。
一丈青大娘早就腻歪了老秀才,先断了每天一壶酒,又撤了一天三顿净米净面。
老秀才混不下去了,留下了几百个方块字码,索取了几百个铜板,忿忿而去。
这时,西隔壁那个在通州潞河实验中学念书的周檎,放暑假回来,何满子整天跟这位洋学生形影不离。
何大学问赶马回来,一见老秀才走了,很觉得过意不去,抱怨一丈青大娘头发长,见识短;但是,一见何满子跟着周檎学会了一大堆字儿,还不花一文钱,又不禁转怒为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