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知己梦最新资料.docx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知己梦最新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知己梦最新资料.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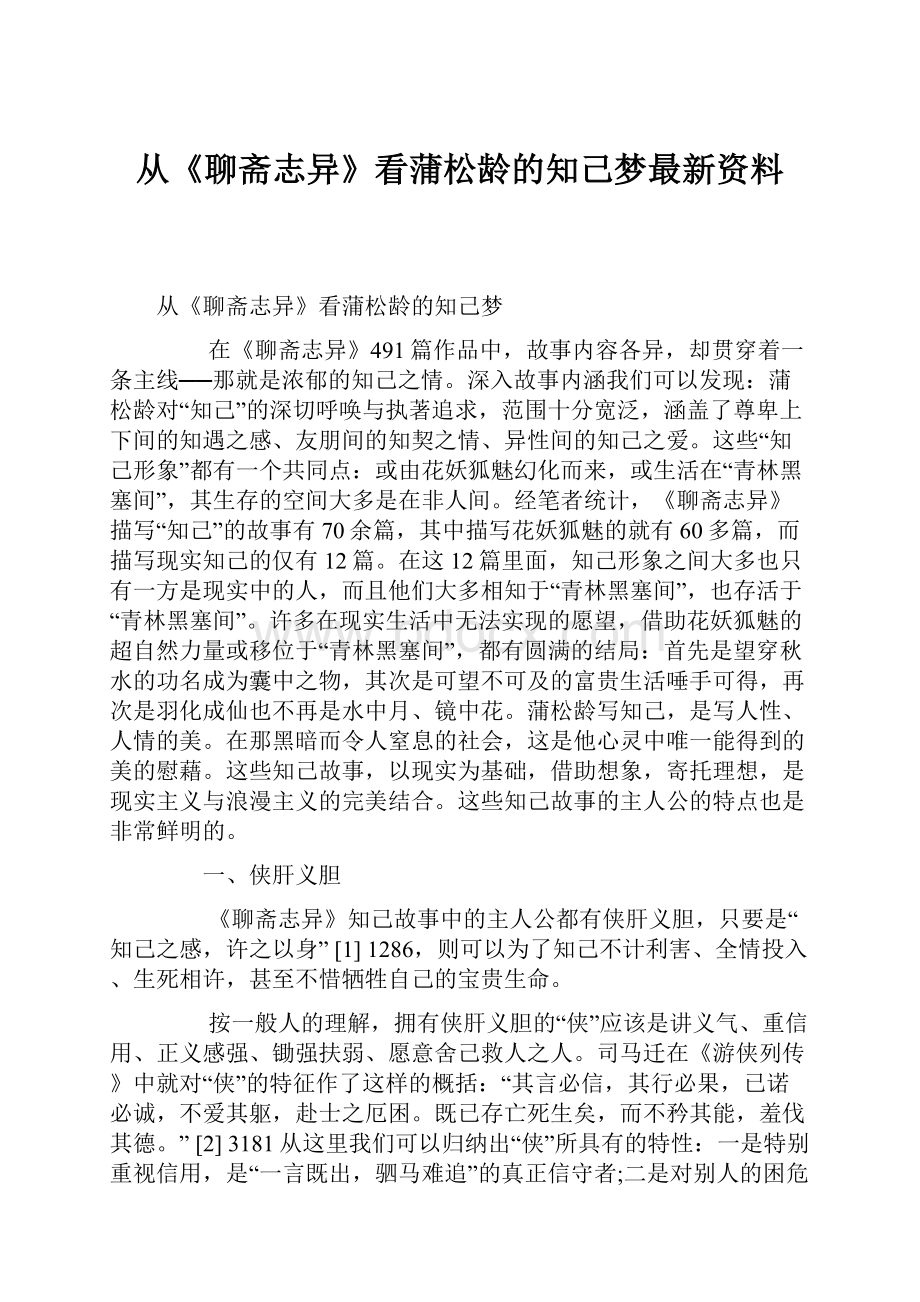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知己梦最新资料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知己梦
在《聊斋志异》491篇作品中,故事内容各异,却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浓郁的知己之情。
深入故事内涵我们可以发现:
蒲松龄对“知己”的深切呼唤与执著追求,范围十分宽泛,涵盖了尊卑上下间的知遇之感、友朋间的知契之情、异性间的知己之爱。
这些“知己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点:
或由花妖狐魅幻化而来,或生活在“青林黑塞间”,其生存的空间大多是在非人间。
经笔者统计,《聊斋志异》描写“知己”的故事有70余篇,其中描写花妖狐魅的就有60多篇,而描写现实知己的仅有12篇。
在这12篇里面,知己形象之间大多也只有一方是现实中的人,而且他们大多相知于“青林黑塞间”,也存活于“青林黑塞间”。
许多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借助花妖狐魅的超自然力量或移位于“青林黑塞间”,都有圆满的结局:
首先是望穿秋水的功名成为囊中之物,其次是可望不可及的富贵生活唾手可得,再次是羽化成仙也不再是水中月、镜中花。
蒲松龄写知己,是写人性、人情的美。
在那黑暗而令人窒息的社会,这是他心灵中唯一能得到的美的慰藉。
这些知己故事,以现实为基础,借助想象,寄托理想,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这些知己故事的主人公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
一、侠肝义胆
《聊斋志异》知己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侠肝义胆,只要是“知己之感,许之以身”[1]1286,则可以为了知己不计利害、全情投入、生死相许,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
按一般人的理解,拥有侠肝义胆的“侠”应该是讲义气、重信用、正义感强、锄强扶弱、愿意舍己救人之人。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就对“侠”的特征作了这样的概括: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2]3181从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侠”所具有的特性:
一是特别重视信用,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真正信守者;二是对别人的困危,可以舍身相救,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三是把别人从死亡边缘救出来,却绝对不居功不图报,甚至从不追求表彰。
蒲松龄具有浓厚的侠义崇拜思想。
他在《题吴木欣〈班马论〉》中说:
“余少时,最爱《游侠传》,五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至《货殖》一则,一涉猎辄弃去,即至戒得之年,未之有改也。
”[3]116所谓“戒得”即“戒之在得”,出自《论语》,是孔子所说: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4]176也就是说,蒲松龄即使到了老年,还是爱读《史记》中的《游侠传》,可见他热衷于“侠”的思想是终其一生的。
与游侠秉性气质的深相契合,更使蒲松龄对侠义精神心领神会,在他看来,“侠”最令人难忘的是强烈的正义感和舍己为人、救人危难的品质。
因此,蒲松龄常常按侠义人格、侠义道德来塑造形象,崇侠意识不断渗透贯注到他的作品中。
可以说,蒲松龄在构建《聊斋志异》“知己”类故事时,这一原则“未之有改也”,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因为只有了解蒲松龄思想性格中的这一“基色”,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聊斋志异》的思想内涵。
《聊斋志异》知己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不计利害地遵循着内心道义价值的指引,在极为巨大的危难险阻下奋不顾身,为了报答知己往往愿意贡献一切甚至牺牲生命。
《娇娜》篇中的孔生雪笠与狐女娇娜就是一对有“侠肝义胆”的知己。
姣美无比的狐仙娇娜以高超的医术治愈了孔生的恶性肿毒,这使孔生对娇娜产生爱慕、怀想之情。
但是娇娜的父兄认为娇娜年龄太小,孔生因此不能与娇娜结为伉俪,可这并不妨碍两人之间结下深厚的知己之情。
后来,娇娜全家面临灭顶之灾,孔生奋不顾身,从雷神的利喙长爪下救出娇娜,并帮助娇娜一家解脱重厄,自己却被暴雷击毙。
娇娜苏醒以后,“见生死于旁,大哭曰:
‘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
’”而后亲自以舌送灵丹的方式救活了孔生。
在患难与共、生死相许的考验中,孔生与娇娜的知己之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孔生与娇娜这对知己在危难关头所发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一种“矢共生死”的大无畏精神,也是一种“义之所在,生死以之”的侠义精神。
《锦瑟》篇中的王生,因不堪妻子的虐待,到阴间寻死,被东海薛侯女锦瑟收留。
无论是背死尸、养狗,还是当管家,王生都尽心尽力,对主人锦瑟忠心耿耿。
在危难关头,他又舍命救了锦瑟。
而当锦瑟感激他要嫁给他时,他又坚决拒绝:
“某受恩重,杀身不足酬。
”王生把锦瑟从死亡边缘救出来,却绝对不居功不图报,这是一种为了知己“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
《连城》篇中的乔大年也是一身侠义:
他可以不管自己生活不富裕,却尽力帮助照顾已故好友顾生的妻儿;他可以“破产”将赏识自己文才、却死于任上的县令的棺木送回老家安葬,往返两千余里而毫无怨言;他可以亲自割下心头之肉给知己连城治病而毫不犹豫;他可以对史孝廉的千金酬谢不屑一顾,却在连城病逝后自愿与之同死。
这一切只是因为“‘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这种为了报答知己愿意贡献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铮铮铁骨不禁令人动容。
这样的篇章在《聊斋志异》知己故事中还有很多:
如《鸦头》篇中的鸦头为追求自主的爱情,百折不挠,敢于与淫邪贪鄙、只认钱不认人的鸨母作斗争,大胆喊出“从一者何罪”?
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侠义行为;《细侯》篇中的妓女细侯,自从结识满生后,誓结永好。
满生在筹资为其从良的过程中,不幸陷入囹圄,一个富商乘机接近细侯,细侯拒绝了他。
富商于是伪造了满生的绝命书,使细侯绝望,从而得以占有细侯,并且生下一子。
满生得其门生之力,昭雪归来。
细侯知悉底细,果断地杀了与富商所生之子来投奔满生。
这也是一种“义之所在,生死以之”的侠义精神。
蒲松龄将细侯这一举动比作他最崇拜的古人关羽:
“寿亭侯之归汉,亦复何殊?
”认为细侯“盟心不改,义实可嘉”。
在《聊斋志异》知己故事中我们还看到了蒲松龄对诚信、仗义、行善行为的旌扬。
最动人的篇章要数《田七郎》。
故事讲辽阳富户武承休在梦中受神的指点,因而去结交猎户田七郎,并“贻金作生计”,被田母坚决拒绝。
田母以丰富的生活阅历,教育田七郎说:
“我适睹公子,有晦纹,必罹奇祸。
闻之:
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
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
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于子矣。
”武承休听说这番话之后,更感佩田母的贤明,千方百计与田七郎交上了朋友。
但他凡有礼赠,田七郎则必定回报。
后来田七郎因为狩猎与人争执,失手杀人而被捕入狱。
武承休慷慨解囊,拿出大量钱财为田七郎上下打点,才保得田七郎平安出狱。
至此田母才同意儿子与武承休深交,因为此时田七郎已受武家的再生之恩:
“子发肤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爱惜者矣。
”从此,武承休但有所赠,田七郎都受而不谢:
“见武公子勿谢也。
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
”不久武承休受到某御史之弟和县宰的联合陷害,身入牢狱,几乎丧命。
田七郎刺杀御史之弟和县宰后自刎而死,用生命保护了武承休。
蒲松龄通过这个故事赞颂了一个“一钱不轻受,正其一饭不敢忘者也”的既诚信又侠义的田七郎及田母;又如《纫针》篇中真诚善良的中年妇女夏氏为素不相识的少女纫针舍身忘死;再如《宦娘》篇中的宦娘、《封三娘》篇中的封三娘、《青梅》篇中的青梅都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的美德;更有褚生为报师恩,千里迢迢赴越,投生为其师吕老先生之子(《褚生》);方子晋有感于陶圣俞的深情厚意,遂投生为陶圣俞之弟(《于去恶》)。
从这些故事主人公的“侠肝义胆”的行为能看出蒲松龄对诚信、忠贞、专一以及仗义、行善行为的肯定与歌颂,并对故事主人公们“知己之感,许之以身”与“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境界给予了高度赞赏。
他赞叹田七郎:
“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世道茫茫,恨七?
O少也。
”[1]473在《褚生》篇中也借“异史氏曰”赞叹:
“吕老教门人,而不知自教其子。
呜呼!
作善于人,而降祥于己,一间也哉!
褚生者,未以身报师,先以魂报友,其志其行,可贯日月,岂以其鬼故奇之与!
”[1]1085他在《连城》篇末也通过“异史氏曰”感叹道:
“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议其痴,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
此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
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
悲夫!
”[1]367蒲松龄对“侠”的钟情,显然寓含在其中。
另外,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段“异史氏曰”也寓含了蒲松龄的怀才不遇的悲叹。
他希望读者在阅读《连城》《娇娜》《鸦头》《锦瑟》等篇章时,不要只单纯地把它们视为抒发男女之情的作品,而应为“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为欣赏乔生的只是连城这一女流之辈的现象而感到可悲。
二、以德相报
“爱人以德”(《礼记?
檀弓》)是我国传统的道德标准。
蒲松龄儒家入世思想深厚,从他对待王鹿瞻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德”的推崇与重视:
他和王鹿瞻是少年时代的至交,一起读书学习,一起参加科举考试;一起结郢中诗社、经常举行诗酒之会;后来他们又曾经同时游幕江苏,互寄诗作以宽慰游幕生活的枯燥寂寥之情。
可以说,相似的处境和经历使他们成为挚友。
可当他得知王鹿瞻听任悍妻把老父逐出家门,他马上不假以辞色,写信痛骂警告老友。
这说明,在蒲松龄心目中,知己之交的原则是“道义”、是“德”。
这种原则深刻反映在他所精心构筑的《聊斋志异》篇章中,特别是在“知己”类故事中。
《乔女》篇“以德字作骨,以不二字作关键,以知己作纲领,存孤御侮作眼目。
写得侠烈心事如青天白日,侠烈志节如疾霆严霜”[1]1286。
乔女是一个“壑一鼻,跛一足”、又黑又丑、残疾在身的女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子,在其内心却有着十分惊人的对“德”的坚守。
她因外貌丑陋,到了二十五、六岁仍“无问名者”,后来虽然勉强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穆生并生下一子,但厄运却又偏偏落到她的头上──不久丈夫就溘然长逝。
因为生活无计,乔女不得已“乞怜其母”,但势利的母亲竟然不念骨肉之情,不耐烦周济她。
乔女“愤不复返,惟以纺织自给”,靠纺纱织布的微薄收入过着贫寒的生活,不再仰人鼻息,不再低三下四地求人,从而保持了高尚气节,也初步显示出她刚强不屈的性格。
同城的孟生因为丧偶,留下一子,急于找到配偶以哺乳其子,“然媒数言,辄不当意,忽见女,大悦之,阴使人风示女”。
阅多人皆不称意,惟独对又黑又丑的乔女情有独钟,孟生可谓是独具慧眼。
但面对姗姗来迟的知己者,乔女却坚辞不就:
“饥冻若此,从官人得温饱,夫宁不愿?
然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
”不卑不亢,言语铮铮,辞婉气烈,令人油然生敬。
乔女所坚守之“德”,有封建社会对女子“三从四德”要求的成分,但也包含了乔女不随便依附他人、坚持独立人格的内涵。
乔女如此持重自爱,孟生由此“益贤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币,而说其母”。
乔女始终没有答应,她的母亲想把小女儿嫁给孟生,“而孟殊不愿”。
孟生不为色所动,唯德是求,是真知乔女者。
正因孟生之知,遂使乔女以德报之,一生无悔。
不久孟生暴卒,乔女却不避嫌疑,“往临哭尽哀”。
世间知音稀,悼知己伤自身,怎不悲从中来!
她不仅对孟生之死深深悼念,而且为报答孟生的知己之情,作了一辈子的奉献。
孟生死后,村中无赖“悉凭陵之”,谋分其田产。
乔女先求助于孟生之友林生,并剖白心迹:
“夫妇、朋友,人之大伦也。
妾以奇丑,为世不齿,独孟生能知我,前虽固拒之,然固已心许之矣。
今身死子幼,自当有以报知己。
然存孤易,御侮难,若无兄弟父母,遂坐视其子死家灭而不一救,则五伦中可以无朋友矣。
妾无所多须于君,但以片纸告邑宰;抚孤,则妾不敢辞。
”一席话以情、以事、以理言之,慷慨激昂,光明磊落,掷地有声。
然而林生惧祸,闭户敛足。
乔女只能“锐身自诣官”,但“官怒其言戆,诃逐而出”。
她不得已哭诉于缙绅之门,得其“代剖于宰”,才使孟生田产尽返。
乔女之果敢刚烈直令须眉生愧。
此后,乔女即依其誓言,抚育孟子乌头,自己则不居其第,不贪其财,仍“抱子食贫,一如曩日”。
后又为乌头“延师教读”,“己子则使学操作”。
长成后,又为乌头聘名族,“治其第宅,析令归”。
乌头泣邀同居,乔女答应了,但仍纺织如故,不辍劳作,“使其子巡行阡陌,若为佣然”。
乔女之报知己可谓鞠躬尽瘁。
而乌头夫妇偶有小过,“辄斥谴不少贷”。
一若佣媪,一若严母,此等角色非乔女做不出。
至其死,乔女仍坚持归葬于穆生,履行自己“不事二夫”的诺言,一个坚韧果敢、勤劳俭朴、善良刚烈的女性跃然纸上。
作为一个寡妇,乔女能有如此的见地和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
可以说乔女是封建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德女形象。
蒲松龄对乔女评价甚高,在“异史氏曰”中赞叹:
“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也。
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
若遇九方皋,直牡视之矣。
”[1]1286乔女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男子也不敢承担的社会角色,有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生存权,她的魅力在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庸、女子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的封建社会里大放异彩。
《红玉》篇与《王六郎》篇写的也是“以德报知己”的故事。
逾墙相从冯相如的狐女红玉,被性格梗直、为人正直的冯翁发现,把他俩严厉地训斥了一顿,红玉只好离去。
冯相如遭遇家破人亡之惨祸后,悲痛欲绝,红玉携带着被丢弃在山口的孩子重来冯家,为冯相如重整家业,使冯家不久便“人烟腾茂,类素封家”。
《王六郎》篇写的虽然是一个鬼,却一点没有恐怖的气氛,而是充满温馨的人情味。
王六郎是一个溺死鬼,因受许姓渔翁的酒祭,便主动帮他捕鱼,并结成朋友。
按照“鬼例”,溺死鬼要找一个替死鬼才可以超生转世,而王六郎的替死鬼却是一个生产不久的母亲,王六郎因为不忍心看母死儿啼,决心放弃投生机会,救治了落水的妇人。
以此“仁人之心”,通于上帝,结果被委任为土地神。
渔翁感于朋友之情,竟不远数百里赶去与之相会。
这段人鬼之间纯洁高尚的友情,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从“异史氏曰”中看,作者主要是借此表彰“置身青云,无忘贫贱”的真正友情,而对那些一阔脸就变的“车中贵介”作了无声的鞭挞。
《雨钱》与《宫梦弼》是体现“道义之交”的反面篇章。
滨州有个秀才,遇到一位“殊博洽”的狐仙,不是将他看作良师慧友以增进见闻,而是将他看作可以“立致金钱”的异士,直言不讳向他“求财”,引起了狐仙的反感。
狐仙不无讥讽地说:
“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
便如秀才意,只会寻梁上君子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
”立即生气地“拂衣去”。
《宫梦弼》篇中也有类似的内容:
“财雄一乡”的柳芳华,“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
急人之急,千金不靳”。
柳芳华死后,其子柳和“贫不自给”,被逼向亡父之门客收回旧债,然多不得要领,“凡二十余日,不能致一文”。
后又到昔日与之定婚的黄家去议定婚期,但“比至,黄闻其衣履穿敝,斥门者不纳”。
这篇小说,极写世态炎凉:
“昔之交我者为我财耳,使儿驷马高车,假千金,亦即匪难;如此景象,谁犹念曩恩、忆故好耶?
”以至深谙人情冷暖变化的蒲松龄也不禁借“异史氏”之口感慨:
“令人愤气杜门,不欲复交一客。
”[1]395
蒲松龄用如此多的篇幅写知己之间的“道义之交”,目的绝不是仅仅进行道德说教,他是用善的心灵去清洗人们的品德污垢,呼唤真情,唤起人们的良知,陶冶人性,用笔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同时给人审美启迪,告诉人们健全的人生应该是什么。
三、有恩必偿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报恩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蒲松龄对这一思想十分推崇并将其反映在作品中,《聊斋志异》知己故事中有动物之间的报恩、人与动物之间的报恩、人与植物之间的报恩、人与鬼之间的报恩、鬼与鬼之间的报恩、人与狐之间的报恩、狐与狐之间的报恩等等。
尤其动人的,是这些花妖树精、狐仙鬼魅所演绎的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报恩故事。
《花姑子》篇中的安幼舆“挥霍好义,喜放生,见猎者获禽,辄不惜重直买释之”。
他曾经放生一只香獐,因为这一善举,他不仅在危难时受到老香獐保护,还跟香獐精花姑子产生了悱恻缠绵的爱情。
在这个奇特的故事中,首先出场的是为恩情效命的老香獐:
章叟。
安生对老香獐有放生之德,老香獐没齿难忘,总想报答。
当安生夜行于偏僻的山路马上要遇险时,章叟出现,救下迷途的安生,使其免受蛇精之祸。
章叟是在安生“迷窜山谷”时出现的:
迷路的安生看到前边有灯火(其实是蛇精的眼睛),就向灯火奔去,他突然看到一个老头儿弯着腰、驼着背、拄着拐杖、沿着曲折的山路快速向他走来。
“伛偻曳杖”,必然年迈无力,却又能“斜径疾行”,沿着崎岖山路快走,表面上看不合理,实际是在暗示章叟的异类身份。
章叟貌与行的矛盾,还有他跟安生交谈时前言不搭后语的反常,更透露出他是特地来救助安生的。
深夜深山,章叟突然出现在安生面前,先问“您是哪一位”?
似乎两人是巧遇;可当章叟带安生回家,给他们开门的老太太却问:
“郎子来耶?
”分明是等待安生到来。
章叟夫妇为安生将受到蛇精的侵害而焦急,挺身而出,尽心救人却不想让人知道。
而后,章叟出妻现女对安生热情招待。
章叟耿直自重,是个憨厚、纯朴、重情义的正人君子。
他以德报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酒友》篇中的车生是一个家贫如洗,却日日饮酒到半夜的穷书生,有天夜里醒来发现一只狐狸喝醉了躺在自己身边。
他非但没有惊奇和捕杀他,反而笑道:
“此我酒友也”,并且“不忍惊,覆衣加臂,与之共寝”。
车生重情,引好酒者皆为知己,哪怕是一只狐狸。
狐狸醒后感谢书生的不杀之恩,书生反请他常来喝酒,并从此在床头常备酒杯,等狐来饮,两者“促膝欢饮。
狐量豪,善谐,于是恨相得晚”。
狐狸为了报答书生,更是为了筹得酒资,常常告诉书生该收购什么粮食,什么时候卖,或者哪里可以捡得到别人丢下的金子等等,时间长了还管书生的妻子做嫂子,把书生的孩子视同己出,直到书生过世。
《义犬》篇中讲的是犬报恩的故事:
周村贾某从屠夫手中救下一犬,“养豢舟上”,后来这犬救出被强盗捆缚抛到江中的贾某,捉住强盗,找到失金。
《蛇人》《褚生》《橘树》等篇章也体现了异类报恩的美好情义。
这些异类受到恩惠,便结草衔环以期报恩,异类这样的行为不免叫人惭愧于心。
《酒友》篇就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落魄书生谁人能够瞧得起?
却得一只狐狸相知相敬、视作知己,人情冷暖,人心之隔,尚不如狐乎?
此其一;书生尚得狐之生死之交,贫病罹难时不离不弃,可以无憾矣,此其二;狐狸尚知报恩,有情有义,看人间背信弃义者遍在,人之为人若何?
此其三。
牲畜与人之区别不在身体形态,而在情义德行:
牲畜有情有德则生似人,人之无情无德者堕入牲畜。
蒲松龄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写这些“异类”,在它们身上秉赋了真善美的自然人性,使花鬼狐妖变得善良温柔、贤淑可人;用独特的幻想,以青林黑塞间的花妖狐魅作为主人公来营构出一个个充满人情味的温馨世界,以此来对抗现实世界的昏暗与污浊,也鞭挞人尚不如石、不如物、不如鳖的心性凉薄、负义寡恩之人。
并希望以此来告诫世人,借以挽救久已颓废低迷的世风。
因此,在《聊斋志异》中,常见这样的话:
“石犹如此,何况于人!
”(《石清虚》)[1]1579“物犹如此,而况人乎?
”(《橘树》)[1]925“鳖不过人远哉?
”(《八大王》)[1]872“呜呼!
一犬也,而报恩如是。
世无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义犬》)[1]1255“褚生者,未以身报师,先以魂报友,其志其行,可贯日月,岂以其鬼故奇之与!
”(《褚生》)[1]1085蒲松龄还在《蛇人》篇末的“异史氏曰”中大发感慨:
“蛇,蠢然一物耳,乃恋恋有故人之意。
且其从谏也如转圜。
独怪俨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数世蒙恩之主,辄思下井复投石焉;又不然,则药石相投,悍然不顾,且怒而仇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1]47蒲松龄认为:
在世俗的社会,往往有一些人不顾数十年的交情和恩义,落井下石,更有甚者,刀兵相见,药石相投,反目成仇,较二青这条蛇差得远了。
以此发出与孔孟“人之异于禽兽”相悖的激愤之言:
“人有惭于禽兽者矣。
”[1]634 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聊斋志异》中的知己故事基本上发生在冥界仙境,故事主人公也大多是花妖狐魅。
蒲松龄以其超凡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构筑起一个亦真亦幻、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从社会批判角度观察,这个幽冥世界乃是人间社会的真实投影,它揭示人世的辛酸悲凉和人物的偃蹇惨痛。
从美学理想角度观察,这个幽冥世界是人世理想的梦幻体现,它揭示出对人世善恶的最后清算和对人生憧憬的重新开始。
因此,《聊斋志异》中的知己故事大都借花妖狐魅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的愿望和要求,故事蕴藏着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愿望。
作者也曾多次借“异史氏曰”表露了他对花鬼狐妖情有独衷的原因:
“若冯生者,一言之微,几至杀身。
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脱囹圄,以再生于当世耶?
”(《辛十四娘》)“惜无好胜佳人,作镜影悲笑耳。
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
”(《凤仙》)正是出于对社会、对人生的美好理想,蒲松龄才不厌其烦地把无数花妖狐魅驱遣到自己的笔端,把花妖狐魅人格化,使之成为人类的“良师益友”。
当他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预期的成功时,便转向另一个更为宽容的世界:
或是洞天仙境,或是幽冥阴间,或是海外异域。
在那里,自由浪漫、公平合理、充满光明,与人世间的黑暗污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蒲松龄用幻想的形式,通过精灵神鬼、花妖狐魅曲折地反映生活,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让生活在绝望中的底层的人们心里抱有一丝希望之火,得到一点温暖慰藉。
正如石昌渝先生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所感叹的,蒲松龄是在“使读者在虚伪的黑暗的礼教社会里看到一线光明”[5]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