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马 汉唐辞赋中的西域意象.docx
《水与马 汉唐辞赋中的西域意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水与马 汉唐辞赋中的西域意象.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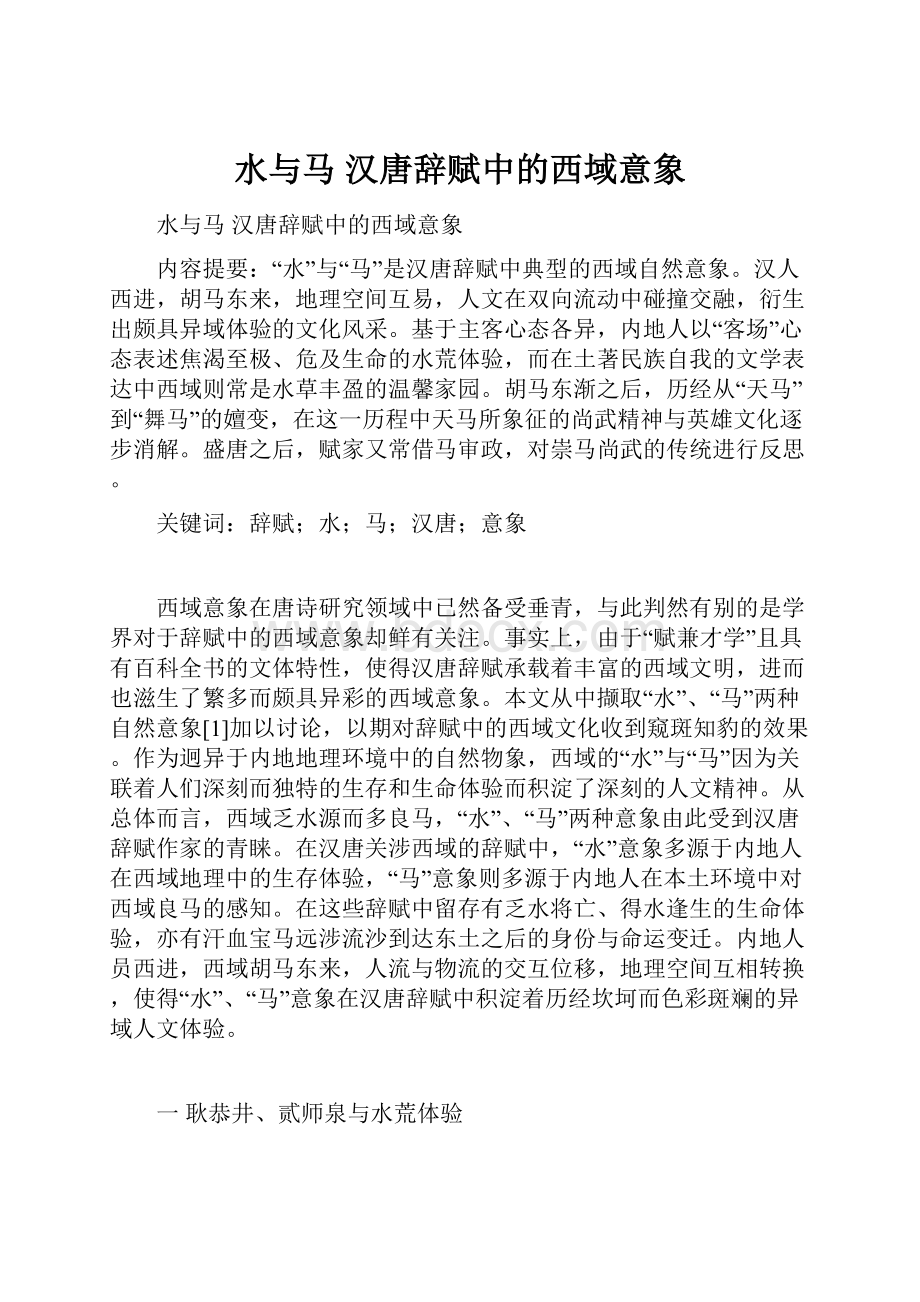
水与马汉唐辞赋中的西域意象
水与马汉唐辞赋中的西域意象
内容提要:
“水”与“马”是汉唐辞赋中典型的西域自然意象。
汉人西进,胡马东来,地理空间互易,人文在双向流动中碰撞交融,衍生出颇具异域体验的文化风采。
基于主客心态各异,内地人以“客场”心态表述焦渴至极、危及生命的水荒体验,而在土著民族自我的文学表达中西域则常是水草丰盈的温馨家园。
胡马东渐之后,历经从“天马”到“舞马”的嬗变,在这一历程中天马所象征的尚武精神与英雄文化逐步消解。
盛唐之后,赋家又常借马审政,对崇马尚武的传统进行反思。
关键词:
辞赋;水;马;汉唐;意象
西域意象在唐诗研究领域中已然备受垂青,与此判然有别的是学界对于辞赋中的西域意象却鲜有关注。
事实上,由于“赋兼才学”且具有百科全书的文体特性,使得汉唐辞赋承载着丰富的西域文明,进而也滋生了繁多而颇具异彩的西域意象。
本文从中撷取“水”、“马”两种自然意象[1]加以讨论,以期对辞赋中的西域文化收到窥斑知豹的效果。
作为迥异于内地地理环境中的自然物象,西域的“水”与“马”因为关联着人们深刻而独特的生存和生命体验而积淀了深刻的人文精神。
从总体而言,西域乏水源而多良马,“水”、“马”两种意象由此受到汉唐辞赋作家的青睐。
在汉唐关涉西域的辞赋中,“水”意象多源于内地人在西域地理中的生存体验,“马”意象则多源于内地人在本土环境中对西域良马的感知。
在这些辞赋中留存有乏水将亡、得水逢生的生命体验,亦有汗血宝马远涉流沙到达东土之后的身份与命运变迁。
内地人员西进,西域胡马东来,人流与物流的交互位移,地理空间互相转换,使得“水”、“马”意象在汉唐辞赋中积淀着历经坎坷而色彩斑斓的异域人文体验。
一耿恭井、贰师泉与水荒体验
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原因,长久以来水一直是西域游牧民族、绿洲城邦的生存所依、生命所系,也是耕种、游牧、武备不可或缺的稀有资源。
诚如清人徐松《西域水道记》自序所言:
“西域二万里既隶版图,耕牧所资,守捉所扼,襟带形势,厥赖导川。
”[2]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水常常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有时候又成为决定战争胜负之关键。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正是在缺水环境下为了解决好生活与生产用水。
张骞出使西域回国之后不久曾作为向导“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
可见,在远征西域途中“知水草处”[3]至关紧要。
自汉武遣张骞凿空西域以后,中原与西域的人员交流日趋频繁。
汉唐盛世,在前往西域的人流中使节、商贾、戍边将士占据了主要成分。
然而,缺水渴水也一直是内地人进入西域后极为深刻的地理感知。
在汉唐关涉西域的辞赋中,有两种“水荒”的意象反复出现,那就是“耿恭井”与“贰师泉”。
东汉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与唐代罗让《耿恭拜井赋》都是直接描写耿恭在极端缺水情况下坚守孤城疏勒,最终拜井得水的故事。
地处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疏勒,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接点,东北、东南与龟兹、于阗相通,历来是匈奴与汉军争夺的战略要地。
汉明帝永平18年(75)耿恭据守疏勒,当年七月遭到匈奴围攻。
匈奴“于城下拥绝涧水”,水源断绝,“吏士渴乏”[4],情势万分危急。
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所存残句有云“日兮月兮厄重围”,描述的正是当时极端危急的形势。
耿恭令“笮马粪汁而饮之”,同时率众于城中掘深井取水,挖到十五丈之深还没有见到泉水。
耿恭于井旁跪拜祈祷,不久有泉喷涌,战争局势顷刻间得以扭转。
匈奴以为汉军有神相助,便引军自退。
自此以后耿恭与疏勒泉水成为了后世诗赋中的数见不鲜的历史典故,也在一定程度上定格为内地人的西域体验。
仅就辞赋而言,对疏勒泉的咏叹从汉迄唐未有断绝。
《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
“盖闻秋之为气,惆怅自怜,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
”[5]释真观《愁赋》:
“箭既尽于晋阳,水复乾于疏勒。
”[6]郑惟忠《泥赋》:
“涂城则疏勒解围,封关则崤函致阻。
”[7]王勃《春思赋》:
“疏勒井泉寒尚竭,燕山烽火夜应明。
”[8]罗让在《耿恭拜井赋》以“感通厚地,神启甘井”为主旨,对耿恭“奋长策以讨虏,由至诚而感神”[9]的传奇故事予以了详陈,堪称耿恭拜井得水的一篇全景“赋史”。
难能可贵的是,汉代的疏勒古城没有像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古城那样被淹没在漫漫黄沙之下,时至今日这座绿洲城市的遗迹尚能在地表找到它的清晰遗迹。
杨镰先生近年曾多次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乡的石城子(疏勒城)实地考察,发现当年耿恭井遗迹犹存,疏勒城旁的涧水依然细流潺潺[10]。
也许这正是对历代层出不穷的《耿恭井赋》或《疏勒泉赋》的生动注解。
无独有偶,除了后汉耿恭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水”体验之外,前汉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也曾有过类似遭遇。
《敦煌遗书》中存有一篇大致产生于晚唐时期的《贰师泉赋》[11],描写李广利征讨大宛凯旋途中的渴乏遭遇。
赋中详细描述了当时将士极度干渴的惨状:
于是回戈天堑,朱夏方兼。
经敦煌之东鄙,涉西裔之危阽。
皑皑大碛,穹隆岩岩。
前无指梅之麓,后无濡溇之沾。
三军告渴,涸困胡髯。
枯山赤坂,火薄生炎。
面对危急情势,于是“我贰师兮精诚仰天,拔佩刀兮叱咤而前……刺崖面而霹雳,随刀势而流泉”。
在因干渴而兵临绝境、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天赐甘泉化解了危机。
唐代王起的《佩刀出飞泉赋》也是一篇描写贰师将军李广利在征途中遭遇干渴,结果诚心感动天地,以佩刀击崖壁而生水的传奇故事。
赋云:
贰师之伐大宛也,耀武经,阐王灵。
入绝域,讨不庭。
近取诸身,拔宝刀之错落;上善若水,出山溜而清泠。
则诚之所至,危无不宁······此画地之成川,如开流之纳泉。
(《全唐文》卷六四三)
赋中有云“岂一勺之多,实一瓢为贵”,揭示了水在西征途中乃至在整个西域的特殊重要性。
无论是“拜井求水”,抑或是“佩刀出水”作为神灵感应之说当不足信,但是这却真实反映了人们在处于西域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时对充沛水源的渴求。
汉代李广利、耿恭的乏水渴水遭遇,在唐代出使西域的使团中亦有类似的情形。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拟册封波斯王质于长安的儿子泥涅师师,裴行俭受命出使波斯。
据张悦《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贺延碛中,遇风沙大起,天地暝晦,引导皆迷,因命息徒,至诚虔祷,狥於众曰:
“井泉不远。
”须臾,风止氛开,有香泉丰草,宛在营侧,后来之人,莫知其处。
此迺耿恭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
[12](《全唐文》卷二二八)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亦记载了裴行俭在西域途中的这一遭遇。
由此看来,内地人在西域屡遭水荒,濒临绝境,结果有如神助,天赐神水是汉唐史书和文学中一种较为普遍的叙事模式。
二“客场”心态下的异域感知
从中原前往西域的人们,无论是征夫、使节、商贾还是被贬谪的官吏、和亲的公主大都是从内地故土走向边塞他乡的,他们的旅程艰险而遥远,这不仅是地理、气候等地域环境的剧变,在对陌生民族、民俗环境的全新感知过程中,人们还要完成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跨越。
一些汉唐辞赋承载了这种独特的“客场”心态下西域体验。
汉武帝时远嫁乌孙和亲的细君公主所作的《悲愁歌》就反映了地理、语言与风俗差异给她带来的凄苦感受。
前文论述了东汉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唐代罗让《耿恭拜井赋》、王起《佩刀出飞泉赋》,以及《敦煌遗书》中的《贰师泉赋》都是描写在战争环境下对水的极端渴求,即可视为内地人在西域特殊地理状况下的一种“客场”文化体验。
其实,此种地域变换导致的特殊文化心理在两汉以前早有发端。
最晚成书于战国的《穆天子传》[13]记述周穆王西巡史事,其中记载了穆王在西域沙漠之中因干渴而不得不刺马颈饮血解渴的故事:
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饮未至。
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
天子美之,乃赐奔戎佩玉一只,奔戎再拜稽首。
[14]
虽然《穆天子传》含有传奇和神话成分,但这对于藉此窥探内地人士对西域的“水”想象和“水”体验则无大碍。
内地人在西域常常会有乏水渴水几至危及生命和生存的体验,从中原通向西域诸国的迢迢丝路也常被视为艰辛而恐惧的畏途。
然而,内地人此种对西域地理环境“畏途”式的想象和感知与西域本土诸民族对西域地理环境的感知却常常又大相径庭。
或许,我们很难从留存的辞赋作品中找到西域土著人对当地环境的认知和体验,但是可以从他们流传下来的一些谚语和诗歌中找到印证。
喀什葛里的《突厥语大词典》所引用的一些诗歌表现了西域诸民族对家乡地理和自然的由衷赞美:
山头被绿色笼罩,遮盖了隔年的甘草,湖泊盈溢着春水,公母牛哞哞欢叫。
(第二卷第77页)[15]
雨点儿纷纷扬扬,百花儿茁壮成长,珍珠脱壳而出,檀麝交融飘香。
(第二卷第122页)
亦的勒河奔驰骤,浪拍两岸夹一流,但见湖水盈盈处,鱼儿成群蛙亦稠。
(第一卷第79页)
从这些西域少数民族对当地的环境描述中,我们感觉到的是田园牧歌式的温馨与惬意,在这里水草丰足,万物生机勃勃,全然没有内地人笔下西域的荒凉、萧瑟与凄苦。
在一些比较成熟的聚居地或绿洲城邦,人们既然已经“逐水草而居”,解决了水源问题,找到了水草丰盈的居所,那么他们以主人翁的心态对家乡生存环境的描述自然也就充满了家园式的快乐。
当然,我们在探讨内地人与西域人基于主客心态的不同而导致对西域地理感受不同之余,也并不否定即便是西域本地人也会有遭受水荒的体验。
这一方面缘于商贸、战争等原因,他们也会有离开故园而远涉流沙的时候;另一方面也缘于西域迥异于内地的水文状况。
《皇舆西域图志》曾有意将西域之水与内地之水进行比较:
“盖内地之水东流就下,而西域之水则东西并流者也;内地之水堤防宣泄兼赖人功,而西域之水则髙下浮沉专凭地势者也;内地之水深浅有定,而西域之水则时因冰雪消融成渠冬夏盈亏者也。
”[16]同样是水,而西域之水与内地之水在地理特性上却迥然有别。
整体性的水资源匮乏,加之区域与季节分布的不平衡,导致西域人也常有对水的关切与焦虑。
或有论者问,以上无论是贰师、耿恭还是穆王在西域渴乏求水的生存考验,均是内地人西进的遭遇,那么汉唐文学作品中有无西域本土人士的类似“水”体验呢?
虽然我们没有在汉唐辞赋中找到线索,但是若将汉唐辞赋中的西域之“水”与唐代小说中一些胡人识宝故事参读,则会有殊途同归之感。
胡人识宝故事在唐代小说中甚为常见,《太平广记》中载有一篇《水珠》。
在小说中,一粒为中原人视为平凡的宝珠结果被来自大食国的胡人认出是至宝。
胡人曰:
吾大食国人也。
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
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
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
此水珠也。
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
自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
(《太平广记》卷四零二)[17]
有的研究者认为在这则故事中唐人不以胡人之宝为宝,其主旨是为了彰显盛唐气象。
不过,若进行本义还原,这则小说实际上表现的是西域缺水的主题。
若将之与以上赋作比读,则可发现小说与赋作的呼应。
在西域行军打仗,“水”具有关系生死成败的关键作用。
可见,“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西域特殊地理环境中又常是人们共同的深刻体验。
“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常见意象,尤其是诗词中的意象宠儿。
然而,汉唐辞赋中的西域之“水”,却与诗词中的常见之“水”的意蕴却大相径庭。
古典诗词中的“水”意象常有两种意蕴:
一是暗指时间,以示时光匆匆而无可逆转;一是暗指心绪,以示愁绪缠绵而未可断绝。
[18]相比之下,汉唐辞赋中的西域之“水”,既非飘渺难求的时光,也不是捉摸不定的思绪,而是人们在西域地理环境中真真切切的生存体验,“水”作为西域生活的一面镜子映照出恶劣环境下人们对生命的真实渴求。
三“胡马”东渐:
从“天马”到“舞马”
汉唐辞赋中的西域“马”意象大体可分为天马和舞马两种基本范型,这又表现为一种历时性的嬗变过程。
汉唐时期中原与大宛、楼兰、车师、龟兹、月氏等西域古国的物种交流频繁。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赞曰:
“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这段记载表明张骞凿空使得西域诸国的物产纷纷涌入内地。
汉唐辞赋中留存有大量的西域物质文化,关涉的西域动物、植物以及器皿等不甚枚举。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汗血马为代表的西域马匹和马种的引入。
尚武崇马的汉武帝决计对匈奴用兵,为改良中原传统的马种颇费心思。
张骞出使西域为汉武帝带来了大宛国出产汗血马的信息。
据《史记》载,汉武帝曾先后得到来自乌孙和大宛的西域名马。
“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
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
”[19]相传,汗血马一日千里,“蹋石汗血”[20]。
汉武帝作有咏叹西域“天马”的辞。
《史记·乐记》载:
“(武帝)尝得神马渥洼水中。
复次以为太一之歌。
”其歌曰: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在汉唐信仰中,天马与龙是有亲缘关系的。
《大唐西域记·屈支国》:
“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
”[21]太初四年(前101),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
汉武帝甚为高兴,作有《西极天马之歌》:
“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武帝在这两首辞中表现出的除了获得良马的喜悦之外,还有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和蓬勃昂扬的大汉气象。
据笔者考察,汉代以后直至隋朝的正史中多次记载西域诸国进献汗血马。
兹录几则如下:
《晋书》卷三《世祖武帝纪》:
“(泰始六年270)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
”《魏书》卷四《世祖太武帝纪》:
“太炎三年(437年)“冬十月癸卯,行幸云中。
十有一月壬申,车驾还宫。
甲申,破洛那、者舌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
”《隋书》卷三《炀帝杨广纪上》:
“大业四年(608)“二月己卯,遣司朝谒者崔毅使突厥处罗,致汗血马。
”这些史料表明魏晋六朝时期亦常有汗血马从西域进献至中原。
据《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玉海》等文献记载,有唐一代大食、康国、罽宾、疏勒、安国、拨汗那、石国、史国、曹国、米国、骨咄国先后20多次向唐朝贡马,多集中于贞元、开元和天宝初年,盛唐时期是西域各国贡马的频率最高。
[22]
西域宝马不仅在汉代被奉为圣物,在唐代亦备受推崇。
陈寅恪先生曾云:
“汉武帝之求良马,史乘记载甚详,后世论之者亦多。
……唐代之武功亦与胡地出生之马及汉地杂有胡种之马有密切关系,自无待言。
”[23]初唐时期,由于太宗的喜爱,西域马在当时备受推崇。
著名的昭陵六骏皆具有西域马的血统,有的甚至具有明显的汗血马的生理特征。
唐太宗《六马图赞》对六骏之一“什伐赤”有“朱汗骋足,青旌凯归”[24]的赞词。
昭陵六骏石雕的马鬃皆成经过修剪或是捆扎成束的式样,像是齿状的雉堞。
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就此指出这种形式最初可能起源于伊朗,认为是中亚和西伯利亚古时的风气[25]。
唐代描写西域马的赋作甚多,其中直接以西域之马入题的就有四篇[26]:
分别是乔彝的《渥洼马赋》,王损之的《汗血马赋》、谢观的《吴坂马赋》、胡直钧《获大宛马赋》。
此外,牛上士作有《古骏赋》(《全唐文》卷三九八),从赋中“渥水龙媒,朱旄逸才”的语句来看应当也是描写西域汗血马的作品。
在这些赋篇中来自西域的宝马是以“天马”、“神马”的意象出现的,作为一种从西域东进的物种,汗血马的身上寄托了内地人对西域的想象,具有超常的力量与神幻的色彩。
两汉以降,“马”赋除写西域千里马之外,开始描写舞马。
这些赋作中的“舞马”堪称西域文化渗入中原娱乐生活的艺术化石。
从汉迄唐辞赋直接以“舞马”入题者今存四篇:
谢庄《舞马赋应诏》(《全宋文》卷三四)、张率《河南国献舞马赋应诏》(《全梁文》卷五四)、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全唐文》卷三七九)、无名氏《舞马赋》(两首)(《全唐文》卷九六一)
开元盛世,每年千秋节即玄宗生日朝廷都要开展各种盛大庆祝活动,其中一项重要活动便是舞马。
钱起作品与两篇无名氏的《舞马赋》就是直接描写玄宗千秋节舞马盛况的。
舞马艺术盛行于唐代,尤其是玄宗时期,但是起源确应远远早于此。
正史之中明确记载舞马者始于南朝刘宋,且贡自西域。
据《宋书·孝武帝纪》载,大明三年(459)“十一月己巳……西域献舞马”。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世祖大明五年(461),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
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
”《梁书·张率传》:
“(天监)四年(505)三月,禊饮华光殿。
其日,河南国(吐谷浑政权的封号)献舞马,诏率赋之。
”又据《梁书·周兴嗣传》:
“其年,河南献舞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高祖以兴嗣为工。
”由此可知,天监四年河南国献舞马之时,梁武帝萧衍曾诏周兴嗣、张率、到沆同时作赋,惜今仅存张赋。
通过上述考察,舞马以及马舞艺术主要从西域传入,当无异议。
唐代舞马盛行,而舞马源自西域也成为唐人之共识。
唐人张悦《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有云:
“圣王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
”诗中所言“海西”泛指西域一带。
由于国力强盛,再加之帝王与上层贵族的喜好,中原的舞马在唐代开元年间盛极一时。
玄宗时代宫廷舞马的规模之巨令人叹为观止,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云: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娇。
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
因命衣以文秀,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朱玉。
其曲谓之倾盆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
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
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于左右,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
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
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
1970年,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其上即有舞马后蹄下蹲,衔杯敬酒的图案,生动再现了开元时期的舞马艺术,是对上述记载的直接印证。
舞马离不开音乐,唐代舞马与宫廷乐更是直接相关。
《新唐书·礼乐志十二》:
“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盃》数十曲。
”“倾杯乐”乃为唐教坊名曲,后成为词牌名。
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云:
“须臾,金鼓奏,玉管传。
忽兮龙踞,愕尔鸿翻;顿缨而电落朱鬛,骧首而星流白颠。
动容合雅,度曲遗妍。
”无名氏《舞马赋》亦云:
“聆音却立,赴节腾凑。
”可见,舞马动作合乎音乐的节奏。
四“英雄”的踌躇:
“尚武”抑或“崇德”?
胡马东渐,历经了从“天马”到“舞马”的嬗变,若将有关辞赋与具体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发现此种嬗变实则为英雄文化向享乐文化的转变。
西汉武帝时期和唐代太宗时期的文学作品的“马”意象多蕴含尚武精神,充满血性与阳刚,体现昂扬进取的英雄文化。
唐玄宗时期“天马”渐退而“舞马”盛行,西域宝马从疆场走向舞场,世人寄寓在马身上的“英雄”情结逐渐被消解,马的娱乐化功用得以凸显。
天宝之后舞马消散人间,大致在德宗贞元年间一些赋家开始借马审政,对“马”反思,或重倡阳刚而摒弃阴柔,或诟病尚武而力导崇德。
中国古代常以西域的神马来隐喻英雄,这一点爱德华·谢弗就曾论及,他在解释穆天子的神奇坐骑“八骏”时说:
“‘骏’在古代汉语中用来指称纯种和健壮的马,这个字常常具有超自然血统的含义,即指那些出自神秘的西方神马种系的名马,甚至它还隐喻地表示具有人性的英雄。
”[27]
汉唐辞赋中的“天马”意象何以彰显英雄文化?
其根源在于马自身在国家政治军事活动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品质和数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地位,这种认识在汉武时代以及初盛唐时期都曾上升到国家舆论的层次。
武帝当年不惜劳师远征以求西域宝马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增强对北方匈奴的作战能力,因此西域马即便被赋予了神话的色彩,但是作为战马才是其意象的核心本质,所谓“一日千里”则是将军与骑士对快速奔袭能力的向往。
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的“马踏飞燕”,以轻盈动感的身姿体现出超凡的力量与速度之美,这既彰显了奔腾进取的大汉气象,也是大汉王朝“天马”崇拜的实证。
武帝时代对优质战马的地位推崇备至,初唐时期亦是如此。
唐高宗永隆二年(681),死亡了十八万匹监牧马,《新唐书》以为:
“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
”[28]显然,在这里优质马匹的储备被提升到了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
与此相关,武帝时代及初盛唐时期的“天马”意象充满了血性与阳刚,普遍具有力量与速度的审美特征。
唐人王损之《汗血马赋》云:
“当其武皇耀兵,贰师服猛,破大宛之殊俗,获斯马於绝境。
”赋家在此乃是借汉写唐,颂扬的是驰骋疆场、征服天下的战马形象。
武帝所作“天马歌”可以与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媲美,两者在彰显臣服四宇、纵横天下的雄心与气度方面可谓异曲同工。
由于对西域汗血马的向往与崇拜,在汉武帝所作《太一歌》与《西极天马之歌》之中西域马被赋予了神话的色彩,以区分于中原所常见的凡马。
唐人乔彝《渥洼马赋》则直接以传说中的渥洼池神马入题,赋云:
“域中之宝,生乎天涯。
天子之马,产乎渥洼。
泽出腾黄,独降精于太乙;神开滇壑,固不涉于流沙。
”唐人王损之《汗血马赋》:
“傥遂越都,甚追风而更疾;如风过隙,似奔电以潜流。
”牛上士《古骏赋》(《全唐文》卷三九八):
“超腾绝壑,走及奔箭。
疑隔汉之流星,似披云而出电。
”此种风驰电掣的神速,正是在瞬息万变战场上获取先机与形成威势的关键所在。
如前所论,武帝《天马歌》与唐人的《汗血马赋》中的“天马”意象乃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实则是英雄文化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图腾式的“天马”崇拜,在汗血马的原产地西域也能找到与汉唐辞赋共通的文学表达。
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的民谚和诗歌中,骏马与英雄往往密不可分。
《突厥语大词典》在解释“马”时引用了这样的谚语:
“鸟靠翅膀飞翔,英雄靠骏马驰骋”(卷一第48页)。
此外,该词典中引用的一首关于马的诗歌也值得注意:
“骏马在疾驰飞奔,马蹄下溅出火星,火星点燃了枯草,火焰在熊熊燃烧”(卷二第137页)。
飞驰的骏马蹄下溅出火星,与《史记》所载“蹋石汗血”的天马特征甚为相似。
唐玄宗时期,承平日久,国力强盛,皇室贵族生活日趋奢华。
开元年间,舞马在玄宗宫廷娱乐生活中。
这一时期,汉唐辞赋中的西域之马逐步从战场淡出,走进了舞场,温驯善舞是成为其典型特征。
钱起等人的《舞马赋》创作于这一时期。
舞马见证了开元盛世承平日久的繁华与安逸,不久又历经天宝战乱散落民间以致消亡。
天宝之乱以后,赋家已经不再热衷于写温顺的舞马了,马意象的内蕴也出现了变化。
这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嬗变趋势有两点:
其一,辞赋中的“马”与开元年间舞马的阴柔形象道别。
由于舞马是开元盛世宫廷享乐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而又最终几乎成为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文化标记,所以“舞马”意象在玄宗以后的辞赋中很少出现。
与此相关,赋家似乎有意恢复大汉时期西域汗血马的赳赳雄风。
一则关于唐人乔彝的赋话或许能折射这一时期赋家们舍阴柔求阳刚的审美倾向。
唐张固《幽闲鼓吹》载: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
彝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矄醉。
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
“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
”遂改“渥洼马赋”。
曰:
“此可矣。
”奋笔斯须而成。
便欲首送。
……京兆曰:
“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
”[29]
乔彝见赋题为“幽兰”,似嫌过于阴柔,非汉子所愿为,易题为“渥洼马”之后,创作欲望得以激发,思如泉涌,一蹴而就。
酒能解放人的天性,乔彝当时的醉态思维展现了真性情,那就是对阳刚之美的真挚追求。
从其赋作中的警句“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也可读出虎虎生威的烈马雄风。
其二,辞赋中出现了以马喻人、审马知政的历史反思。
德宗贞元年间出现了几篇有关西域马的赋作,此时离安史之乱只有几十年,赋家们刚刚从感时伤乱的情绪中挣脱出来,以理性的态度开始进行历史的反思。
他们不再撰写歌舞升平的舞马,也不愿描述沙场征战的烈马,转而描写太平盛世良马之无用武之地,借此表现出对长久以来武力崇尚的消解。
谢观所作的《却走马赋》以“天下有道,无所用之”为主旨,描写贞元初年,天下太平之后,让战马回归原野的景象。
赋云:
“贞元初既平凶丑,海县安阜。
归戍人于田里,却战马于陇亩。
所以示力争之无益,昭静胜之足有。
”“吉行之乘,存六驳而有馀;无战之时,惜万蹄而空老。
”
这一时期的赋家开始对汉武帝以来尚武崇马传统进行反思,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