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也会老的.docx
《声音也会老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声音也会老的.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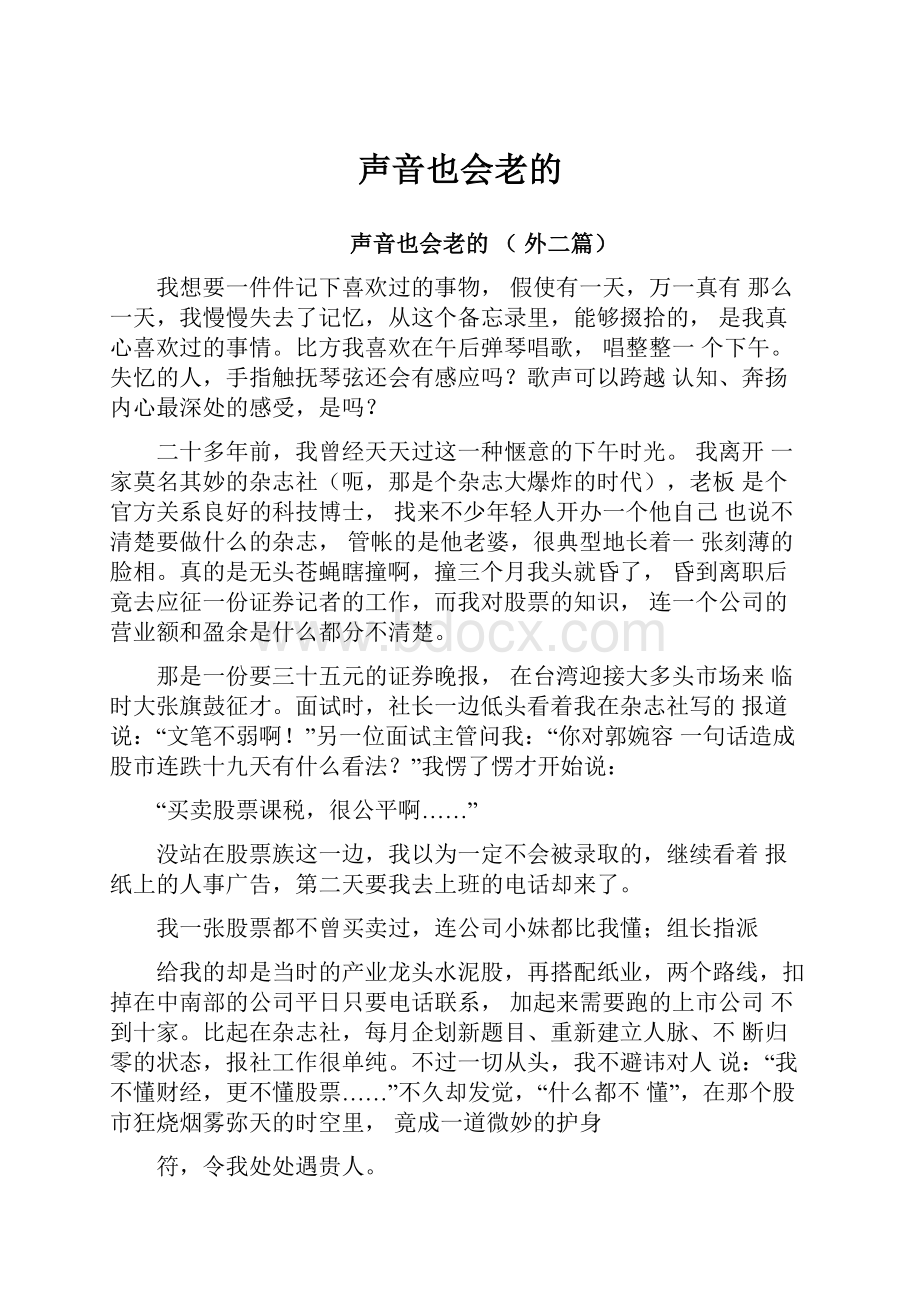
声音也会老的
声音也会老的(外二篇)
我想要一件件记下喜欢过的事物,假使有一天,万一真有那么一天,我慢慢失去了记忆,从这个备忘录里,能够掇拾的,是我真心喜欢过的事情。
比方我喜欢在午后弹琴唱歌,唱整整一个下午。
失忆的人,手指触抚琴弦还会有感应吗?
歌声可以跨越认知、奔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是吗?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天天过这一种惬意的下午时光。
我离开一家莫名其妙的杂志社(呃,那是个杂志大爆炸的时代),老板是个官方关系良好的科技博士,找来不少年轻人开办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要做什么的杂志,管帐的是他老婆,很典型地长着一张刻薄的脸相。
真的是无头苍蝇瞎撞啊,撞三个月我头就昏了,昏到离职后竟去应征一份证券记者的工作,而我对股票的知识,连一个公司的营业额和盈余是什么都分不清楚。
那是一份要三十五元的证券晚报,在台湾迎接大多头市场来临时大张旗鼓征才。
面试时,社长一边低头看着我在杂志社写的报道说:
“文笔不弱啊!
”另一位面试主管问我:
“你对郭婉容一句话造成股市连跌十九天有什么看法?
”我愣了愣才开始说:
“买卖股票课税,很公平啊……”
没站在股票族这一边,我以为一定不会被录取的,继续看着报纸上的人事广告,第二天要我去上班的电话却来了。
我一张股票都不曾买卖过,连公司小妹都比我懂;组长指派
给我的却是当时的产业龙头水泥股,再搭配纸业,两个路线,扣掉在中南部的公司平日只要电话联系,加起来需要跑的上市公司不到十家。
比起在杂志社,每月企划新题目、重新建立人脉、不断归零的状态,报社工作很单纯。
不过一切从头,我不避讳对人说:
“我不懂财经,更不懂股票……”不久却发觉,“什么都不懂”,在那个股市狂烧烟雾弥天的时空里,竟成一道微妙的护身
符,令我处处遇贵人。
那些公司发言人第一次见到我时似乎都觉得怪怪的,那是我
的尼泊尔时期。
一位同业,某报的阿仁有次忍不住对我说:
“去买几套正式点的套装穿吧!
你的形象太不专业了。
”不是我少女病,我解释:
“我穿那种正式的套装、窄裙很难看的,我嫂嫂说我太瘦穿窄裙好像修更。
”“像谁?
”“小卷。
”阿仁大笑。
不必穿名牌套装我也很有自信的,忍不住炫耀:
“别小看我,不信你试试看!
”我问他有哪家公司是平常采访不到的?
他说了家不太理他的水泥公司,唔,那位发言人比起来稍年轻,未婚,很健谈,三句话要夹一个英文单词。
我立刻带阿仁找他去。
阿仁出来后很感慨的样子:
“你知道你们女孩子在这个圈子里跑新闻,最好的出路是什么吗?
”“什么?
”“找个有钱老公吧,把握机会,我说真的。
”阿仁真直接啊。
其实我常接触的都是公司“发言人”,至少都是中年人了,我又没有恋父情结。
而那些发言人,可能平日见到的记者,更在意的是指数与股价,我乱问一些怪问题,比他们有趣多了,大概会有这种心理吧。
“你还是小孩子!
”
那个满口英文单词的发言人曾重复对我说这句话,他说:
“我看
女人的年龄不看外表,讲话的声音、语调,比什么都准。
”那年我二十四岁。
声音也会老的。
种种的回春手术、秘方,针对的都是外型上的。
近日听到一位医师的说法:
都没有用的,因为眼睛会泄露年龄,无法整型!
我想还有声音,声音里饱含时间的残留物,像海浪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碎砾,亦是不能整型的。
有一位纸业公司的副总,每次见面耐心地给我上财经课、建议我找什么书参考,我很快地恶补、熟悉了所有相关术语,才能听懂别人说的话。
有一位水泥公司副总,每个月水泥业各公司发货量报表一出来,首先传真给我,我的新闻刊登出来时,他报记者都才刚收到工会的公告而已。
发货量是水泥业的景气指标,我到同业工会找来历年各月份发货量数据,做成趋势图、比较图表,就把产业新闻当图像诗写好了,有时则找些人物,当小说写吧。
随着水泥业景气的狂飙,我居然成为组里的杰出记者,每个月拿奖金。
像我这样一个数字感奇糟、绝对不要问我身上任何东西多少钱买——从来记不住价格的人,竟然会是杰出财经记者,真是我人生的光荣时刻啊!
在我的好朋友们大牙还没笑掉之前,还真
的有人来挖角了。
那时报禁解除不久,报社普遍人才荒吧,同时有三家报社向我招手,其中之一是阿仁帮我推荐的。
找我去,不怕我抢他饭碗吗?
阿仁笑着重申一次他对我的“出路”的忠告。
我跟他的上司谈过,一切都说好了,结果没去成。
因为妈妈。
妈妈那时已经是癌末了。
她洗完头发,我帮她上卷子,摸到她的头皮底下有地方软软的,紧张得不敢问,我们总不谈病。
我那时几家公司早已跑得烂熟,有什么事情,他们会主动通知。
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不像同事们要早起看盘。
做早餐跟妈妈一起吃,我做的法国吐司不是吹牛的,妈妈不会弄这些西式的东西。
中午以前进报社写稿;下午选一家公司走一趟,甚至有时哪也不想去,两三点钟就回家了。
母亲在楼下,我在楼上弹唱,或者敲扬琴。
我自学的扬琴,已能敲《天山之春》、《春到沂河》这样的曲子。
书桌上,有时妈妈剪枝茶花给我插着。
那是我俩一段亲密的时光,虽然大半时间并不太对话。
我好像处在一种近乎极乐世界的状态里。
常看到一些小故事
描述天堂的样貌,说在那里每个人静静的看书。
那的确是天堂,但有点无聊;怕读书的人吓得说:
还是不要上天堂吧!
我的天堂,早晚读喜欢的书,下午要弹琴唱歌的。
许多作家描述对音乐的痴狂,都只在聆听,但人体就是一个最好的乐器啊。
太多人写美食、看画、听音乐的美感经验;而歌唱,声气从腹部悠悠通过咽喉、唇齿,把具象的歌词、抽象的旋律抛吐出来,听觉器官同时承接住这歌声,不更是一个完满自足的美感创造!
那真是一段奇异的时光,我在股市疯狂长红的年代,近距离从事报道工作,心灵却是彻底的与世隔绝。
一边陪伴生病的妈妈,一边整个人放空了,暂不考虑未来,完全没有工作压力、成就压力,一旦换工作,这个状态就结束了。
我跟妈妈说了,大报大概吵得比较凶吧,以后没有这种好日子了,最主要日报是晚上进报社,白天跑新闻,以后要很晚才能回家哦!
我忘不了妈妈失落的眼神。
那完全不是她,她是极好强的女性,我大学成绩不错,但对自己的未来彷徨犹疑不想考研究所,她曾失望得不得了,她希望我当教授。
她不是那种要小孩陪在身边的人。
那时候的她,真的不像她。
在我书桌上插瓶花?
她从来不做这种文诌诌的事,在以往,大概连听到都会啐一口:
“肉麻!
”也许,她已经预感自己的时候到了。
我们又亲密,又遥远,一个在楼上弹琴唱歌,一个在楼下翻报纸读小说;仿佛我是退休的人,而她倒比较像蕴酿着要写作的样子。
我已经预演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吧?
那些午后,我玩吉他玩得
指尖长了茧,声音在最好的状态。
可那声音是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春雷大作的午后,母亲突然休克倒在路上,送到医院时已经不治。
我想不起妈妈最后对我说过什么话,我们总只是静静的相处啊!
我像小时候在夜市里迷路找不到妈妈那样大哭。
一心一意弹琴唱歌的午后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母亲过世不到一个月,便有报社的文化中心来找我。
那位留着两撇短髭的主任跟我面谈时,手上拿着一份过期的流行杂志,原来是一位老同事向他推荐了我。
我毕业后为那份杂志工作了一年多,每天早出晚归,是真的“上山”、“下海”采访,月月熬夜写稿、校对,那可能是我工作至今吃最多苦头的一年,严重睡眠不足,也面对最
多不可预期的状况。
比如在人马杂沓的屏鹅公路上,犹豫自己要不要坐上飚车少年的摩托车?
比如在超轻航机上,亲手握住驾驶
放开手丢给我的操纵杆,呼啸掠过脚下的大地、河川。
比如面对一位帅得不得了的建筑师,考我某某他佩服的名女人,“你知道她吗?
”我尴尬地摇摇头,“你完蛋了!
”他目光犀利地盯着我
说。
我痛苦得要窒息,到现在想起还难受,即使后来那“名女人”的名声并不光彩、实在不怎么值得佩服,我想起当时的难堪还是笑不出来。
又比如我采访过一个作风特异的设计师,他住在交通
不便的山上,经营公司只用电话遥控;在家,他喜欢裸体。
我奉命约访他,挂上电话前,忍不住问了一句:
“可是我去的时候,你会穿衣服吧?
”话筒里传来狮子般的狂笑。
那位留着两撇
短髭的主任,手里拿的正是那一期的杂志。
我如愿进入那家报社跑音乐,不知道自己即将卷入生命里一段痛楚的风暴。
风雨来临之前,我每天为那架五桥半大扬琴一弦一轴细细调音。
敲琴时,手腕要松,两手力度要平衡,轮竹才轮得均匀……不久,这些全都失衡、走音了。
情感世界像有人把我的琴轴乱拨乱转一通。
自己想做什么,更不知道了。
好像忽然失了声,也无法唱歌了。
一年后,我终于打起精神,到美国去。
临行前,我一一到那些久违的公司告别,谢谢他们的宽容。
尤其那位纸业公司的副总,我对他深深一鞠躬,感谢他如师如父的教导。
还有那位水泥公司发言人,临别那天我对他说了很多话,说自己这一年来的近况,
过去总是我听他说。
我们握手道别时,他说:
“你比较不像小孩子了。
”
唉,声音也是会老的。
指尖滑过冰块十一年了,你离开这个世界,在我渐渐迈入中年的旅途上,你,还是永远的三十三岁,与我的那些记忆,一同冰封,凝固。
那一通电话,现在想起,犹觉得惊心。
你在半夜里突然一阵抽?
,之后就不醒人事了。
血癌、脑出血,手术后,你的小妹在电话里对我说:
“我哥现在情况还好,但是伤到了语言神经,所以……不能讲话了。
”我手持话筒,茫然地听,好像完全不能理解那话的意思。
那些日子,我甚至认真阅读心理学书,从最基础的脑部行为部分逐句逐句的读。
读到“接受性失语症”这个词汇一一“接受性失语症通常是在左脑的颞叶与顶叶的地方有受伤。
这个区域在医学上叫做维尼基区域,邻近听觉投射区。
”这大约就是你动手术的部位,那么,你将会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一一手术之后,你丢失了对于语言的认知?
本来就不擅言词的你,动脑手术之后第一个抛掉的就是语言能力?
而你能恢复多少记忆呢?
你的手还可以拉琴吗?
推开病房门,你的父亲、弟妹们都在,你睡着。
他们把你喊醒,说你也该起来复健了。
要我走上前给你看,
问你认不认得?
你很快地摇头。
我几乎立刻就涌出眼泪,小妹拍拍我说:
“你要让他看久一点,他动完手术后才第一次看到?
,连我们他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只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所以他知道是他家人。
”
小妹鼓励你回想,她说着我的名字,“你最要好的朋友啊,你再想想看。
”我不忍了,要他们别再逼你想了吧。
我从包包里拿出一卷录音带,收录的都是你喜欢的音乐。
俞逊发的《汇流》。
才几个音符淌出来,你的眼睛就有了神采,开始跟着哼,左手大力地摆动,小妹笑着对我说:
“你看,你一给他音乐,他又要指挥了!
”
我惊讶地看着你的手,真是指挥家的态势呢!
你从高中时就拉南胡的,现在不懂得压抑自己,更能挥洒开来。
我在你耳边说:
“那是俞逊发跟中广民乐团合奏的,彭修文指挥的哦,比以前唐山出的那卷有气势哦!
”你看来是听不懂,但仍专心地哼,连曲中的水滴声都噘着嘴尝试去做出来,听完,你自然而然地说了一句:
“好听。
”
我又试你一向喜欢的《月儿高》,你同样跟着哼、跟着指挥。
我向你家人叹口气:
“他的音感、对音乐的记忆力倒是一点一分都没失去,真不可思议!
”小妹说:
“对呀,我哥当初实在应该做音乐家的!
”口气中对你怀着无限崇拜。
再从病床底下找出一卷校园民歌,心想什么年代了还在听这个!
《小木船》,我高中时代喜欢的一首民歌,以前常常唱给你听的。
我跟着陈明韶的歌声哼唱:
“小木船哪,小木船哪,几番风雨,几回夕阳,我们都曾历经人生……”
你弟弟忽然打岔:
“你跟她的声音好像卩育!
”我愣了一下,发觉病床上你的表情似乎也停下来在倾听,像你从前听我唱歌时的样子,又像是在思索回忆着什么,我又忍不住滚下眼泪来,唱不下去了。
那当儿你的表情一一好像是记得我的歌声?
我想,难道你完全忘了我这个人,我的形貌、个性、相处过的种种细节,情爱、争执、离苦,去卩独独记得我的歌声?
走出医院时,我的脑海里仍然转着那支《小木船》,我又想,或许你记得的正是我最好的部分呢?
六月的这一天,又是走向台大医院的路。
半年来,常走的这条路,愈来愈艰难。
而过去种种,动不动就像又翻倒了什么,声音、影像滚落一地,不可收拾。
这一天,他们叫喊你,要你看看我,你的两眼无意识地张开,喉咙发出的唯有呻吟之声。
小妹说你白天因为药物,意识特别不清楚,有时到晚上勉强可以认得人的。
但是下午你就要回到后里的家中了,我隐约知道他们的暗示,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
你闭着眼,枯萎地躺着,虽然盖着被子,仍然看得出整个身躯缩小了。
你吊着点滴的左手露在棉被外头,干缩得像老人的手,上头布满了瘀痕、针孔,两嘴微微张着,更显出两颊的凹陷,心电图在枕畔低沉安稳地画过一道一道浅波画面。
我凝望你,这会是我最后见到的你吗?
我不相信你会病重,病重之后,我不相信你会撑不下去,我不相信。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到医院看看你,那时你的复健
情况令人鼓舞。
你的家人盼望我常常出现,帮助你恢复记忆。
陆续来看你,感觉你慢慢在进步。
而且熟悉了我的面孔,见到我时常常陷入沉思,可能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吧?
皱着的眉头显示你想不出来。
“认得你们了吗?
”我问你弟弟。
“还是搞不清楚我们是谁,连我爸也不认得。
”你弟说,“但是他有学习能力,很多新教他的词汇都能听懂。
”他示范给我看:
“眼睛眯眯,休息!
”你立刻很乖地把眼睛闭起来。
“来,哥你该做运动了!
”你弟把两手手指交叉握住举到头上示范给你看,你照着做了,放下来、再举起,如此可以帮助手部的复健。
你弟要你自己数,于是你一、二、三、……一下一下地数数目,但是不完全按次序,有时十九完了跳到三十,而且通常逢四都省略,十三、十五、十六……
看着你不按次序地数数目,我忍不住心疼,当年你大学联考数学是满分的啊!
你做累了,自己数到三十的时候说:
“三十、休息!
”手便放下来了。
我和你弟不禁好笑。
而喂你吃东西,问你好不好吃?
你总是非常认真地回答“很好”或是“不好”,这是你新学会的。
愉快时你已经懂得微笑,一着急、恐慌便大声地哭泣,完完全全是个孩子。
看着你纯真的脸,你亦看我,带着几分好奇和困惑,你一定在想:
这个人常常来,想必跟我有什么关连吧!
可是到底跟我有什么关连呢?
而我脑海里浮起的是好多年前的画面,清境农场,那年我二
十一岁。
我露营早起,随身带着一本袖珍本的《庄子》,坐在帐篷口面对无垠绿草愉快地读着《逍遥游》里的句子。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从背后环抱住我,问我:
“一大早在读什么?
”
我用做作的声腔念出来: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这是说你吗?
”你很难得地谄媚。
“哼!
”我愉快地笑着说,“神人一定是很老很老的吧!
”“那还肌肤若冰雪呢!
”你笑着,轻抚我年轻的脸庞。
人几岁算老呢?
我说:
“三十岁就算老了吧,上帝造人为什么不让人从老人长成小孩呢?
渐入佳境不是比较好吗?
”
你说:
“长到小孩然后呢?
”
“婴儿呀!
”
“然后呢?
”
“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啊,消失啊。
”你把我搂得更紧些,说,“我真怕你有一天真的从我身边消失!
”
我消失了,为了热情的消失,我离开。
那造成你深沉的伤痛和挫折,而你是鲜少遇到挫折的,在病
魔还未折磨你以前,你一直顺利,从一中到清大,到台大研究
所……
这时候,站在病床前的我已经三十一岁了,依照从前的想法,早该很老了,而你,却变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婴孩。
你的语言逐渐在复健中。
转来台大医院后,跟你同一个病房的也是个血癌病患,已经跟病魔奋斗很多年了,他给你很大的鼓励,也经常热心地跟你沟通。
那一阵子你的病房很是热闹,因为你变得多
话,你这辈子也许从没讲过那么多话吧。
有一天,你想要对你病房的难友介绍我,你不会说名字,那阵子把每天照顾你的弟弟叫成“爸爸”,其余的人一概被你取了
新名字,“阿伊诺”、“莎宾诺”、“卡及诺”……我们面面相觑:
他上辈子是哪国人啊?
你急于要对他介绍我,你说一句,我们猜一句,把我们揣测
的意思告诉你,“是这样吗?
”因为你的语汇都变得很怪异。
譬
如有一天你妹夫来过,你想问你小妹是不是怀孕了,你说:
“你有没有那个,很多人、很少人的?
”我们猜测了老半天,加上肢体语言,最后终于明白你的意思是“怀孕”。
而你所有的形容词只剩下“好”与“不好”。
你说了一堆
话,竟也让你的室友弄懂了一一我是写作的。
然后你举了身边所
有的人,你说他们都很好,可是我,你费力地再点头,你的室友说:
“你是说其它的人也很好,但只有她最好?
”你很开心地笑了,我站在你二人的病床中间听着你们奇怪的沟通方式和赞美,竟脸红起来。
你却“话锋一转”,我实在很难记住你断断续续又叨絮着什
么,我们翻译了很久,不断修改之后终于得到你的豁然同意,原来你是要告诉我,我有时会陷入沮丧,可是你要我知道,你一直认为我是“最好”的,要我不要失去信心我不敢相信此时此
地你这般费力表达的,竟是对我的鼓励!
我感伤地挪动脚步,要去洗手间,你的室友忽然指着我颈上的项链,问你漂不漂亮,你点点头,然后把眼光往下移,指着我的裙子笑。
我吃了一惊,想起来这条黑色的大圆裙是好几年前你陪我去买的。
“你认得这条裙子?
”你点头,并说很好,你只会说很好。
你室友指着我上身的毛衣问你认得吗?
你摇头,指着我的靴子问你认得吗?
你还是摇头。
不错,那些都是后来添购的,唯有这条裙子你该认得。
他还问你那毛衣好看吗?
你竟摇头,然后很像怕我生气,说错话似地羞赧地笑。
你记得我穿过的衣服!
你室友对我说:
“你以后常常穿戴他看过的服饰来,也许可以刺激他的记忆。
”其实那一刻,我深深觉得,你已经什么都想起来了,只是说不出口而已。
如果世上真有所谓信心这种东西,那么我确实曾经惨烈地失去过。
惨烈。
你曾经那样地为我痛惜,而我却那般地不可自拔。
“你是一个完全没有想象力的人。
”这是C伤我最深的一句
话。
“没有想象力?
”当我无可救药地对我几个好友诉说时,敏敏直接打断我的话头:
“那是因为他知道你比他聪明一百倍!
我告诉?
,有些男人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贬低你、压抑你,来掩饰他对自己的焦虑!
”话头转入她的痛苦经历,啊,男人,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苦苦地再喝一杯咖啡。
想象力是什么?
而我现在对你的自白里,有多少是真实?
多少是我自己的想象?
具有想象力的人,会不会比较具有爱的能力?
人对音乐有所谓音感,对于色彩有所谓色感,眼耳鼻舌,无不可测量其灵敏度,对于爱情呢?
如何测量?
生命中有那么几年我执迷于追究爱向何处流逝,回首才悚然察觉失去的不只是爱情,信心,这个我甚至怀疑它是否真正存在的名词。
人啊,要怎样才能够不依傍别人的爱、眼光、评价而独立存活?
我今生到底能不能够?
一段注定作废的爱情,是指尖偶然滑过的神秘电台。
指尖滑过铜钱草。
指尖滑过吉他的六条弦。
指尖滑过冰块,辨认记忆的触感……
一行人穿街走巷回报社时,C与我并肩而行,他说:
“你喜欢黑塞。
”我很好奇他怎么判断?
他说刚才他们提到黑塞时看你眼睛好亮。
那是没有的事,我不过是感到惊奇罢了。
不过,我是
真的喜欢黑塞,近乎羞怯地深深喜欢。
我点点头,算是默认了他的观察,过马路时,他忽然就牵住了我的手。
从此,把我安稳的世界炸得粉粉碎了。
C的爱情在很多方面对我而言都是一种启蒙。
从游戏的本质,
到无可挽救的厌倦,我学会去正视爱情里一些残酷的面相。
爱一个人,常常带点糊涂,即使欲生欲死也是迷茫昏?
的,然而,不再被爱的感受却绝对是清醒酷寒的。
那年我已二十五岁,无论如何都算晚熟。
和C相恋,退掉与
你的婚约,和家人几乎反目,可谓众叛亲离,后来甚至辞去工作,远走美国。
在这些过程里,真正扮演我的精神支柱的人,仍然是你!
只有你原谅着我、安慰着我。
我的心灵曾经一片疮夷。
现在想来好笑,当我得知C同时有了新的女友,一位插画家。
我问C,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
C淡淡地说,“她跟你不同。
”我又问C一位写诗的朋友,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
诗人一脸坦白从宽地说:
“她一一确实很漂亮!
”
我敏感得像林中的鹿,遍察周身的足迹。
我的脏腑痛楚异常,
我不停地哭,哭得十分哀伤。
硕大的黑蝙蝠在我的灵魂里滑翔。
咬嗫我的神经,啃食我仅存的一点点自信。
噢!
那长长的一段萎敝的生命,我惊异自己好好地活过来了!
过去,我一直不曾对你诉说这个过程,无颜啊。
但你仍然在我俩偶尔的联系中感觉到了我的消沉,默默地给我支撑。
甚至,当你病了,失去了语言能力,仍不忘以你的手势给我鼓舞。
上帝却对你做了什么样的手势呢?
你离开世界的那几天,连续下起滂沱的大雨。
午后,我惯于听着音乐小睡,音符却像小舟在浪涛里颠簸。
那天睡不着了,起身到书房换个音乐吧,一进和室,差点滑了一跤,地板上有一滩水!
那水,流到木板底下去了,我存放旧物的“地窖”进水了。
那里边有我的日记,有你所有的信件,有我的少女时光啊!
我拉不起那厚重的木板,只能呆愣地等待丈夫回来。
我始终没有跟你聊过他。
清大毕业、擅长数学二事,大概是你俩最大的相似点吧。
不知是不是辨识出一种前世的印记,遇见他,使我那几年里躁动和受伤的心平静下来。
结婚前夕,我曾犹豫再犹豫,彷徨地说,渴望海洋,不愿待在鱼缸,他回答我:
“海洋,也是鱼缸。
”
我等待他回来,帮我拉起了木板,确认所有的东西都安然无恙
丿匕、O
我和他对坐在和室木板上,空间局促得无法呼吸。
我对他说,下午发现地窖进水了,我以为关于我大学时代的“记忆”已经全部淹没了。
他想了想说:
“文字,怎么能代表所有的记忆?
”
除了文字,还剩下什么呢?
“他过世了!
”我以为我是?
喊着说出来的,却只听见自己细细小小的声音。
他轻轻拥着我,任我放情地哭了。
那房子,那时光
梦见老房子,并不是我回到那里,而是梦见当年我住在那里的时光。
大概是白天去参加好友清志的告别式,会中反复播放的幻灯片里不断出现我的老房子,我就梦见它了。
它夹身在小山坡上一栋七层楼旧式大厦里,前屋主是中研院的研究员,太太从事室内设计,因为两个孩子大了,另觅新屋;而我们注定也只能是过客,住了五年,在孩子两岁半时,一样另寻新巢,寄居蟹一般换了较大的壳。
按理说,那房子连同阳台有三十坪,三口之家未见得住不下,但前屋主太太显然是在新婚时做的设计,完全没考虑未来,她做了两个和室,主卧室小到不能买床头柜组,把空间留给了客厅。
我们接手时正新婚,一样地没有考虑未来,只因为它离娘家近,只因为我从客厅起居间望向其中一个和室的窗,幻想自己坐在里边写作的画面,便觉得那是我的房子了。
两个和室都做了隐藏的收纳空间,把榻榻米上的铜环拉起来,底下有四个置物格。
其中一个没有窗的和室我放棉被。
我喜欢那间有窗的和室,把它做为书房,两面墙摆满书柜,而它的收纳格里我放的是过去所有的日记和信件,我把它称为地窖,放进一包包日记、信件时,有一种封藏、酿酒的感觉,酿的是我的青
书房和室的门不但从不拉上,我更把窗纸拿掉,留下空空的格子做为装饰,让客厅的视觉更宽敞些。
和室是垫高的,走上和室有个台阶,那和室门口便是我弹吉他的好地方,脚刚好可以放在台阶上不会酸麻,我可以弹唱一整个下午。
也可以听一整天的音乐。
我从美国带回来的音响一次可放六片CD,
把六种版本的《二泉映月》放进音响,或者几种版本的巴哈大提琴奏鸣曲,反复反复反复。
我婚后工作一段短暂的日子便辞职在家里,享受这一段悠闲写作,毫无压力的时光。
除了睡觉是在那小小的卧室,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或书房外的那张木头小餐桌前。
那时候我不太知道外面的世界,不认得文坛上的什么人,默默的写作,投稿,几个月后刊出,展开收到的剪报看了又看,便觉得欢喜。
那房子真的适合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心情。
那房子有一个L型的大阳台,公公说该种些花,我那时不谙花事,种过一两盆据说最好养的黄金葛,居然被我种得奄奄一息,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