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哀歌.docx
《未名哀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未名哀歌.docx(4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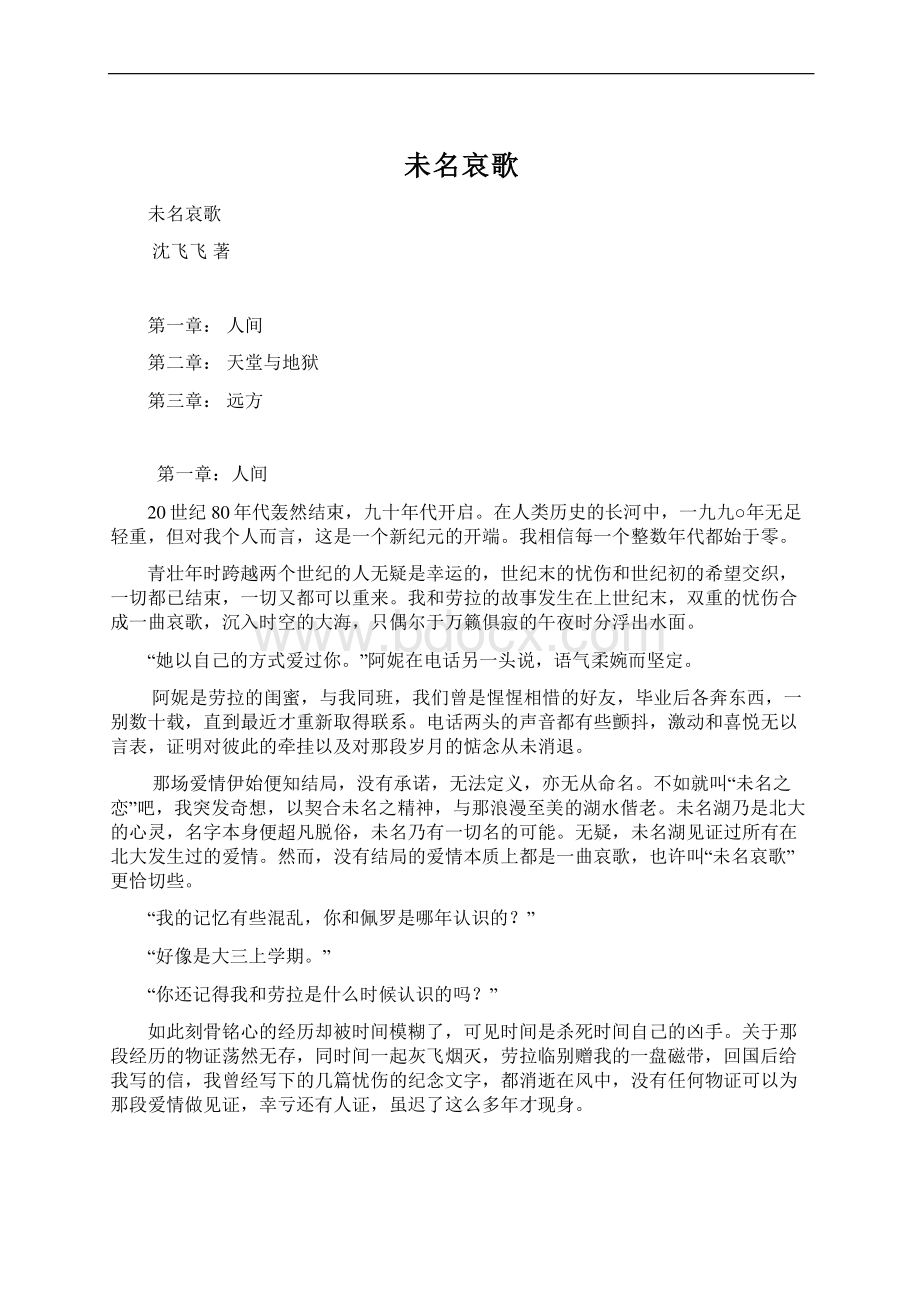
未名哀歌未名哀歌未名哀歌沈飞飞著第一章:
人间第二章:
天堂与地狱第三章:
远方第一章:
人间20世纪80年代轰然结束,九十年代开启。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九九年无足轻重,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
我相信每一个整数年代都始于零。
青壮年时跨越两个世纪的人无疑是幸运的,世纪末的忧伤和世纪初的希望交织,一切都已结束,一切又都可以重来。
我和劳拉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双重的忧伤合成一曲哀歌,沉入时空的大海,只偶尔于万籁俱寂的午夜时分浮出水面。
“她以自己的方式爱过你。
”阿妮在电话另一头说,语气柔婉而坚定。
阿妮是劳拉的闺蜜,与我同班,我们曾是惺惺相惜的好友,毕业后各奔东西,一别数十载,直到最近才重新取得联系。
电话两头的声音都有些颤抖,激动和喜悦无以言表,证明对彼此的牵挂以及对那段岁月的惦念从未消退。
那场爱情伊始便知结局,没有承诺,无法定义,亦无从命名。
不如就叫“未名之恋”吧,我突发奇想,以契合未名之精神,与那浪漫至美的湖水偕老。
未名湖乃是北大的心灵,名字本身便超凡脱俗,未名乃有一切名的可能。
无疑,未名湖见证过所有在北大发生过的爱情。
然而,没有结局的爱情本质上都是一曲哀歌,也许叫“未名哀歌”更恰切些。
“我的记忆有些混乱,你和佩罗是哪年认识的?
”“好像是大三上学期。
”“你还记得我和劳拉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吗?
”如此刻骨铭心的经历却被时间模糊了,可见时间是杀死时间自己的凶手。
关于那段经历的物证荡然无存,同时间一起灰飞烟灭,劳拉临别赠我的一盘磁带,回国后给我写的信,我曾经写下的几篇忧伤的纪念文字,都消逝在风中,没有任何物证可以为那段爱情做见证,幸亏还有人证,虽迟了这么多年才现身。
阿妮是当年故事的缘起,故事自行发展、结束,故事的再度发生需要同一个缘,她的重现唤醒了那段记忆,成就了一个完美的圆,仿佛时光可以逆转,过去以全新的面目归来。
“大概是秋冬之际。
”短暂的沉默后,电话里再度传来阿妮的声音。
我顿感释然,看来记忆没有骗我,只是不敢确定罢了。
此刻秋意正浓。
早些年,每至深秋,还会触景生情,记忆的鸿毛翩然而坠,但南方的秋气毕竟与北方不同,久而久之,季节似与记忆也不相干了。
今年的秋雨特别多,深秋已具冬相,显得意味深长。
正如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因为种种缘由,被遗忘,被漠视,但暗中发酵的过程从未停息。
我生命中这段历史的影响力,并不因其短暂和久远而稍减。
之所以没有贸然触及这段回忆,因为无论阅历和文字都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中心,中心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场景,中心季候,那时是劳拉,性与爱,北大,秋末冬初。
阿妮约我去她宿舍,要介绍几个留学生给我认识。
我们所学的专业是法语语言文学,而中学学的是英文,法语基础为零,这门优美的语言并非总那么面目可亲,时常与人为难,尤其是我们几个兴趣广泛对专业课程却比较疏懒的男生,课堂上老师一提问就低头,将抢答的机会都大度地让给女生。
阿妮交游广,与留学生接触频繁,法文说得流利而动听。
一个聪慧可爱的女生当然有资格接触我无缘接触的世界,在我眼里,那个世界充满了神秘。
北大的留学生楼叫勺园,邻近古色古香的西校门,而我们因宿舍楼离小南门近,以小南门出入为主,留学生们因此得地利之便,比我们与朱红大门及门前的那对石狮更亲近。
楼前有一块网球场,时常有英姿勃发的留学生在上面挥汗如雨,我路过时不免驻足,流露出神往之意,但终我整个大学四年生涯,我只颤颤巍巍碰过两次网球拍,便知难而退,究其原因,既无闲暇又无闲心,况且网球号称贵族运动,令我这个乡下来的外省学子不免自惭形秽。
之所以问及佩罗,一是出于礼貌,做人不能先顾自己,顺便也做个话头,二是出于好奇,想知道她和佩罗的爱情是否结出善果。
阿妮的追求者甚众,本国的,外国的,但她绝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花本无心蝶自忙。
佩罗是典型的法国男子,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有很深的东方情结,而中国代表东方,先验地坚信会在这里找到挚爱的姑娘,果如所愿,他找到了阿妮。
佩罗洁身自好,阿妮也视爱情为神圣,视身体为神圣爱情的象征。
这样的两个人,未名湖畔的偶遇似乎早已注定。
他得到了她的东方,而她收获了他的西方。
在后来共同的生活中,他们携手将对方的文化译成各自的母语,做了东西方的媒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替阿妮深感欣慰。
同阿妮和佩罗的纯情相比,我和劳拉似乎是肉体的另一个极端,结局也截然相反。
我们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短促的时光也不容有复杂的经历。
像佩罗一样,劳拉也是北大的上千名留学生之一,墨西哥人,我们通过阿妮相识,她很快与中文名叫朱的美国男友分手,与我正式交往,不久便启程回国。
我经历了成为男人的蜕变,但并未止步,在灵与肉的路上走得很远,甚至劳拉离去后还独自前行,一直走到今天。
我得承认,当年低估了这段短暂恋情在我生命中的持久的影响力。
有些经历不能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漫漫人生里,那故事只是昙花一现,但至今还在讲述。
那段感情要跨越很多人和事才能来到今天;同样,要打此刻回到那段感情,也须跨越同样纷繁复杂的人和事。
那天下午,应阿妮之邀,我前往女生宿舍赴会,到达时已坐了一屋子人,除阿妮外都是外国面孔,各种肤色的都有,本班女生一个都不在。
我有些局促,向所有人茫然点头,与劳拉的目光相遇,空气瞬间变得黏稠,将我们的目光黏住。
我们觑定了对方,很强烈也很虚幻的感觉,这莫非便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阿妮万万没想到我和劳拉会对上眼,据她所知,劳拉有男朋友。
我渐渐适应了热烈的气氛,与劳拉用法语交流,得知她并非法语国家的人,而来自遥远的墨西哥,深感惊讶,同时觉得神秘,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整个拉美于我都很陌生,有限的认识都来自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的虚构作品。
用别人的语言交流,语言似乎变成了游戏,只可惜我的口语还远未达到可以自由交流的水平,情急之下只好用中文和英语补拙。
劳拉的父亲是外交官,满世界跑,在巴黎长住过,打小家里就让她学法语,类似十九世纪的俄国上流社会,视法语为贵族语言。
聊至晚饭时间,阿妮提议同去学三吃饭,晚上再一起跳舞,群起响应。
当年的校园食堂名皆以“学”字打头,“学三”自然就是编号为三的食堂,位于大讲堂隔壁,也是我最常涉足的食堂,前方的空旷地带有很多柿子树,秋深后残留着几个柿子,不舍得离开枝头,金黄耀眼,时刻威胁着从下面经过的脑袋。
不远处是声名远扬的三角地,一溜公告栏上贴满学生自己写的告示,大多逗留时间不长,很快便被新写的字纸覆盖,内容驳杂,严肃的,高深的,搞笑的,小广告,甚至公开的求爱信,应有尽有,路过者无不习惯性驻足,常因发现有趣的内容而会心一笑。
此二处一代表肉体所需,一代表精神所需,而今皆已被拆除,学三也就罢了,一食堂而已,三角地拆得没道理,死不瞑目,呜呼哀哉!
食堂内外热闹非凡,打饭的队伍排成长龙,劳拉东张西望,似乎看比吃更有乐趣。
她深喜这种氛围,无奈被限制在勺园内,不理解为什么不能与中国学生同住同吃;换作我,也爱与所在国的同龄人朝夕相处,如此方能更好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活,对语言学习的裨益更不待言。
我笑言:
怕你们的自由思想毒害我们。
大家回去休整后重新聚齐,再度步入学三食堂。
学三还是学三,清理后摇身变成空旷的舞池,散发着菜味儿和更加隐秘的泔水味儿,但很快被夜幕中炫目的球形旋转灯稀释,并与各种廉价香水味儿一起五味杂成。
我先和阿妮跳了两曲,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共舞,音乐舒缓,歌声悠扬。
同阿妮在一起感觉温暖而踏实。
她是北京女孩儿,说话慢声细语,京腔自然悦耳,嘴里仿佛含着珠玉,总是用充满关切的眼神看人。
我是家中的头生子,汉人自古长兄为父,可我还是个走出山里不久的孩子,难以承受生命之重,暗里视阿妮为姐姐,替我分担了一部分忧愁。
海子诗里姐姐的意象一度令我泪流满襟。
接下来便只跟劳拉跳,她与别人跳时就远远看着,直到她又重新回到我的怀抱。
正流行罗大佑的恋曲1990,“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旋律缓慢悠长,反复播送,很应景,劳拉也会唱,我们边跳边小声合唱,时而相视一笑。
那双棕色眼眸在黑暗中兼具猫科动物的迷离和光彩。
北大的舞会不只学三一处,二体的周末舞会曾经风靡一时。
体育馆里办舞会堪称一绝,规模空前,轰动首都高校,吸引了不少外校的大学生,拿跳舞当体育项目操练,一曲下来跟绕操场跑两圈似的,而魅力四射舞伴不绝者,整晚下来的运动效果不亚于跑全马。
说实话,我不喜欢跳舞,也不太会跳,偏偏最流行跳舞,周围人都乐此不疲,不由你不动心,而常在一起促膝谈心的同窗好友小十因自杀未遂休学,一人的周末之夜难免寂寞伤感。
跳舞自然可以增加与异性接触的机会,这也是大家伙儿心照不宣的主要目的,但舞池中撞出火花的毕竟是少数,常常满怀希望而去,落寞沮丧而归。
去舞会之前照例要沐浴,要打扮一番,头面尤其重要,发型是重中之重。
那会儿男子兴烫头,回头看当时的照片不免哑然失笑,但时髦无须理由,甚至无关美丑,烫过的发洗浴后卷曲,去发廊吹费时费钱,不知谁买了个吹风机,吹头的重任无故就落在了我身上。
我倒宁愿替他们吹头,以打发并不总是有趣的时间,顺便练就一门手艺,毕业后没工作也不至于饿死,况且我也热爱手艺活儿,大家各得其所。
就中以隔壁的K最挑剔,总不满意,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吹毛求疵,似乎舞会的成功端赖发型。
他是典型的南方小个子,头发务必要往上昂起,以弥补身高的劣势,常常要求再三返工,吹多了,发质受损,显得枯黄,但他一意孤行,两眼于镜片后放光,对舞会的憧憬好比饥者对美食的想象,与每每落寞而归的表情恰成对比,但绝不言弃,屡败屡战,踯躅于自卑与妄想间。
待一众人吹完头,我已累得失了去舞会的兴致。
青春的豪情和理想戛然而止,颓废思潮风起云涌,像瘟疫一般弥漫,像跳舞一样流行。
小十的自杀多少与此有关。
小十选在去年的金秋十月卧轨,仿佛死亡也是丰收的粮食。
难道是为了呼应他的外号?
这事多少有些神秘的意味。
所有人都叫他小十,小十当然不是大名,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叫小十。
他自杀未遂,我还会一直管他叫小十,别的熟识他的人也会一直管他叫小十。
问题是,小十为什么自杀?
不仅仅是因为爱情和诗。
大家抱定了一种全新的态度,不管去年,无论明朝,今朝有酒今朝醉,学垮掉一派的作风。
近来有人怀旧,说我们这茬人的青春赶上了好时代,说那是黄金十年,我不懂这个说法的深意,但要让我把那十年挪前或推后,说实话,还真不愿意。
俄语系写诗的哥们醉得越发厉害了,偏偏那厮的身材像俄国大力士,要几个人挥汗如雨才能搬将上楼,杀猪声不绝于耳。
说他是案板上的猪吧,又口口声声要杀人,不知要杀谁,不省他到底有多大的冤屈,诗之不足醉之,醉之不足叫嚣之,大家习惯了,懒得再到楼道里看热闹。
有一阵子,这哥们每天都在学三门口晒诗,将诗稿贴在几块大纸板上,靠墙而立,几行醒目的卷首语声称千古杰作,境界直追庄子,慨叹怀才不遇。
有人边吃饭边站着围观,诗风古雅,内容高深莫测,终无人赏识,只好继续借酒抒愤。
学三门口还有人晒摄影作品,引所有人驻足,赞美之声不绝,照片内容来自遥远而陌生的丝路西北端,绿洲,维吾尔族女,中亚风格的古城,大漠。
摄影作者立在一旁,长发卷曲,山羊胡密实,宽边近视镜,边吃饭边得意地回答观者的问题。
大家都叫他方同学,与我们住同一楼层,高中毕业没考上理想的大学,不愿复读再考,索性与考上北大的老乡一道出发,居然找到一张空床,从此寄居下来,做起了旁听生,混迹北大数年,神不知鬼不觉。
似他这样的北大编外人员不在少数。
因为不是正宗的北大人,难免有些自卑,因此他坚持让人叫他方同学,以弱化身份的尴尬。
后专攻摄影,不时外出拍片,回来办展览,也不知从哪里拉来的赞助经费,渐渐找到自信,俨然以摄影艺术家自居。
艺术家的外形自然要与众不同,周末舞会前也不屑于将自己拾掇一番,昂然走进舞厅,不幸屡屡受挫,大为光火,对公然拒绝邀请的女生说:
你会后悔的,请保留好这个。
迅速掏出一张菜票,在上面龙飞凤舞签上自己的大名后递给对方,一甩头转身,从此绝迹于舞厅。
也不知他后来有没有混出让那个女生后悔的响亮名头。
小十那会儿诗兴勃发,有一天忽发奇想,要与方同学合作一组前卫艺术照,两人一拍即合。
小十身兼主创和模特儿,方同学负责拍摄,我全程协助观摩。
我们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拍了一组又一组照片。
小十很亢奋,完全沉浸在自己设计的情景里,认真摆造型,务求出格,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叛逆。
整整一个下午,摄影艺术家被诗人折腾得够呛,有两组照片的拍摄给我留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