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一线的卫生学校 钱枞洋.docx
《抗日一线的卫生学校 钱枞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抗日一线的卫生学校 钱枞洋.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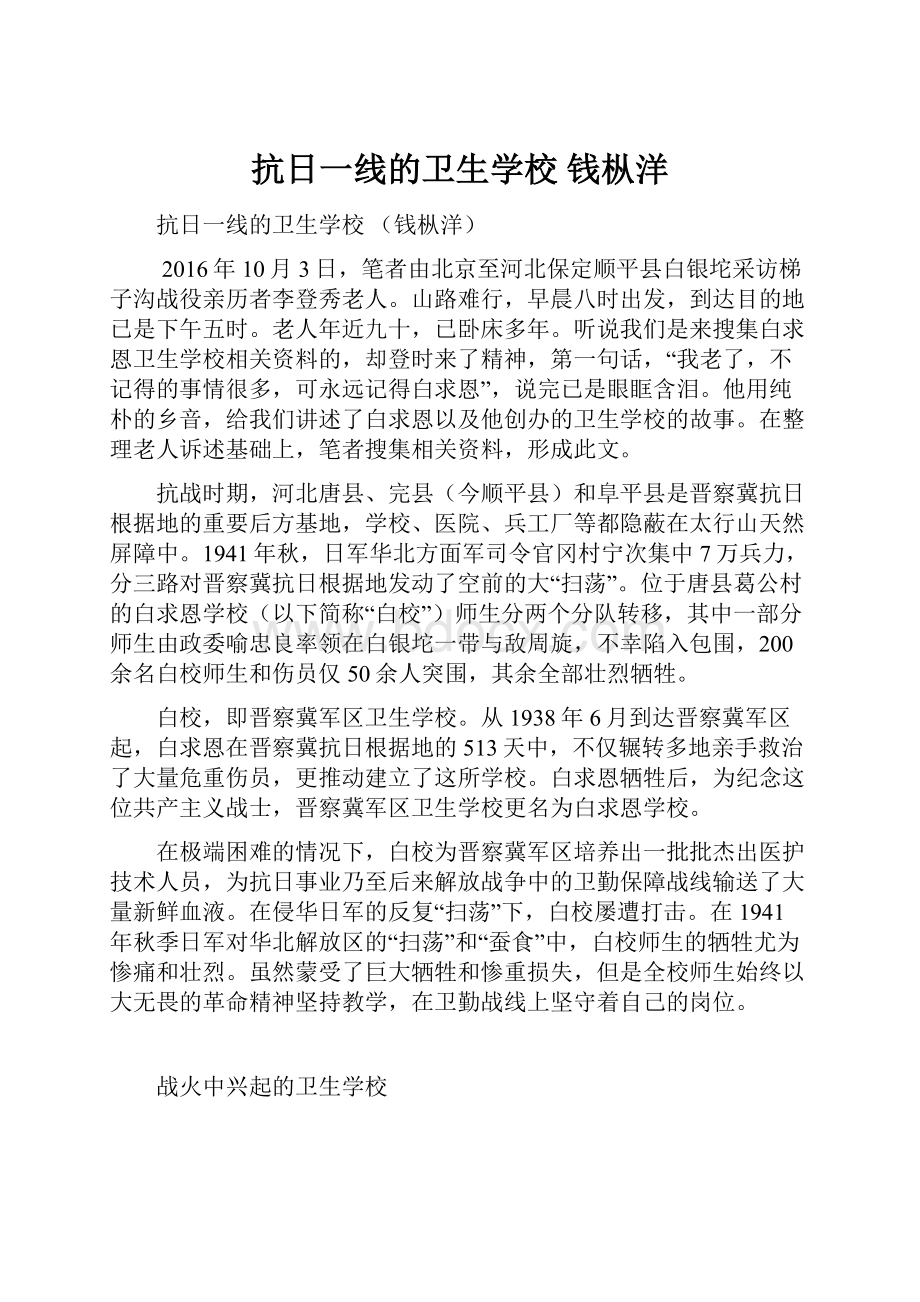
抗日一线的卫生学校钱枞洋
抗日一线的卫生学校(钱枞洋)
2016年10月3日,笔者由北京至河北保定顺平县白银坨采访梯子沟战役亲历者李登秀老人。
山路难行,早晨八时出发,到达目的地已是下午五时。
老人年近九十,已卧床多年。
听说我们是来搜集白求恩卫生学校相关资料的,却登时来了精神,第一句话,“我老了,不记得的事情很多,可永远记得白求恩”,说完已是眼眶含泪。
他用纯朴的乡音,给我们讲述了白求恩以及他创办的卫生学校的故事。
在整理老人诉述基础上,笔者搜集相关资料,形成此文。
抗战时期,河北唐县、完县(今顺平县)和阜平县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后方基地,学校、医院、兵工厂等都隐蔽在太行山天然屏障中。
1941年秋,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7万兵力,分三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的大“扫荡”。
位于唐县葛公村的白求恩学校(以下简称“白校”)师生分两个分队转移,其中一部分师生由政委喻忠良率领在白银坨一带与敌周旋,不幸陷入包围,200余名白校师生和伤员仅50余人突围,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白校,即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
从1938年6月到达晋察冀军区起,白求恩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513天中,不仅辗转多地亲手救治了大量危重伤员,更推动建立了这所学校。
白求恩牺牲后,为纪念这位共产主义战士,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白校为晋察冀军区培养出一批批杰出医护技术人员,为抗日事业乃至后来解放战争中的卫勤保障战线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
在侵华日军的反复“扫荡”下,白校屡遭打击。
在1941年秋季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中,白校师生的牺牲尤为惨痛和壮烈。
虽然蒙受了巨大牺牲和惨重损失,但是全校师生始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教学,在卫勤战线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战火中兴起的卫生学校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兵分两路开赴敌后战场。
其中一路由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343旅等共计两千余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率部广泛发动群众,打击日寇,根据地面积很快扩大到80万平方公里,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和辽宁5省各一部。
晋察冀军区在抗日战争中共作战6.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3万余人,军区部队伤亡8万余人。
由于战事频繁,加之对驻地群众实行免费医疗,晋察冀根据地的卫勤保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在日寇的严密封锁下,当时不仅缺少医疗器械和药品,也缺少具备合格技能的医护人员,一些伤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在痛苦中牺牲。
人命关天。
战场上,官兵生命关乎胜负、关乎士气,也关乎民心。
伤亡大了以后,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对部队战斗力造成的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削减,还有精神上的削弱。
邓小平曾说,治好一百个伤员等于恢复了一个加强团。
当年在华北抗日战场,官兵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看到白求恩,打仗就放心。
白求恩是一个符号,代表着成百上千奋战在最前线的战地医护工作者。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
1938年,他率“加美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6月17日,他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如获至宝,当即聘请他出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此后几周,他走访检查了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为157位伤员实施了手术。
后方医院医务人员的抗日热情和吃苦耐劳的作风感动着白求恩,但他也发现了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偏低,医院管理经验不足,缺乏必要医疗物资等问题。
他看到护理人员大多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十几岁的孩子,有的甚至是文盲,感到培养医务人员的工作迫在眉睫。
他对与自己一同战斗的中国战友说:
“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
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
他倡导建立一所模范医院,并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说:
“目前有必要在整顿医务工作的同时改进技术训练。
”白求恩的想法与聂荣臻不谋而合。
1938年8月13日,白求恩给聂荣臻打报告,提出创办卫生学校的具体意见。
他在报告中说:
“关于在此建立训练学校的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其迫切性,其次应有建校规划。
”他还主动提出编写和编译教材,拟定教学计划,并亲手设计制作了多种简易医疗器械。
1939年春天,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挺进冀中。
在冀中四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中,白求恩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发现冀中有一些医科学校毕业的专门人才,很适合担任学校教员,并向军区推荐了殷希彭、刘璞、陈淇园等人。
殷希彭曾赴日本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河北大学病理学教授。
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参加八路军。
解放后,殷希彭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陈淇园曾任冀中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参与筹建卫生学校,后来当过华北医科大学校长。
白求恩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晋察冀军区有20万军队(包括民兵游击队),经常有2500受伤的人住在医院,在过去的一年中经过1000次以上战斗,却只有5个中国毕业的医生,50个中国的未经正式学校毕业的医生,和一个外国医生做一切工作。
”这里的“5个中国毕业的医生”,指的就是殷希彭、刘璞、陈淇园、张文奇和张陆增。
白求恩还利用战斗间隙起草了学校教学方针。
方针中提出,要有一个特殊的医院附属学校,称为“卫校医院”。
这个方针十分详细,小到学生的作息时间、校徽等都作了考虑。
聂荣臻曾想请白求恩亲自出任学校校长,但被白求恩婉拒了,原因是他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前线抢救伤病员上,不想被“拴”在后方医院。
但对于创办卫生学校的工作,白求恩十分看重,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努力。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
“我正力图把农家子弟和青年工人培训为医生,他们具有读书能力,多数人具备一些算术知识。
我手下的医生中无人上过专业学院或大学,没有一个在现代化医院里工作过;大部分从未在任何医院工作过,入过卫生学校者更少。
从这批人中,我必须用半年时间培训出护士,用一年时间培训出医生。
”他在《加美流动医疗队月报》中还写道:
“如果我们要问一个医疗队是否完成了它的任务,那么就看它是否培养了许多人才代替了他们的工作。
”
据陈淇园回忆,白求恩曾拉着他坐在自己发明的马拉担架上,边抽烟边说起自己的打算:
“这一年来的工作使我感到,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军队不断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我们的医生、护士,我们的卫生工作力量,是不能适应最基本的要求的。
我时时考虑这个问题,再来几个甚至十几个外国医疗队,再来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外国医生,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为了战争的需要,我想过我们应该办一个卫生学校。
我办了特种外科实习周,给医生、护士们讲课,我认为他们是好学的,是聪明的,虽然有的连小学都没上过,可是他们学习文化技术都学得很快、学得很好!
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假如以一年多的时间把他们培养成为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有一定实际技术水平的干部,是完全可能的。
这不仅是为了今天,而且也是为了明天,为了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所需要的。
我们在为未来的事业奋斗着,也许我们不能生活在那未来的幸福之中,可是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
在白求恩的推动下,筹建卫生学校的工作全面展开。
江一真负责筹建工作,抽调了病理学专家殷希彭、微生物学专家刘璞、小儿科专家陈淇园、眼科专家张文奇等参与建校工作。
学校最初选址在完县(今顺平县)神北村,距离敌人据点较近。
聂荣臻指着地图说:
“神北处于唐河以东,如果完县敌人出动,背水扎营违背军事常识,你们将来还是在唐河以西如葛公、张各庄建校为妥。
”后来,学校强渡唐河,搬迁到了西岸的唐县牛眼沟村。
1939年9月18日,学校在牛眼沟村正式成立。
江一真任校长,殷希彭任教务主任。
学校开办了军医、调剂和护士三个期,学制分别为一年半、一年和半年。
学校成立不久,延安军委卫生学校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突破敌人封锁,到达晋察冀军区,与之合编,壮大了学校的教学力量。
合编后,江一真仍任校长,从延安过来的喻忠良任政委。
1939年11月,学校在反“扫荡”中转移到唐县葛公村。
葛公村背山面水,人口较多,物质条件稍好,白校在此度过了较长时间。
敌人眼皮子下的医疗教学奇迹
在学校正式成立前的1939年6月,各单位选送的学员就陆陆续续到达了神北村。
这些学员之所以来这么早,一方面是参与建校劳动,另一方面是来补习文化课的。
学校创建之初,可以说除了困难和决心,什么都缺。
当时没有教室,教员都在老乡的场院上课;没有骨骼标本,师生们就从附近的乱坟岗上挖尸骨,洗刷煮沸后,用石灰水浸泡漂白,消毒后用铁丝连接起来;没有模型和教具,大家就用泥巴、木头、废铁等,自己动手制作。
白求恩曾向学校捐赠了显微镜、小型X光机和内外科书籍等。
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在弥留之际写给聂荣臻的遗书中还专门提到,把自己“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后来担任过白校教务长的康克说,在教学中,用苇管代替胶管做听诊器,用裁衣剪代替手术剪,用剃头刀代替手术刀,用木工锯代替骨锯做尸体解剖,用猪肠子指导学生练习肠缝合,既完成教学任务,又培养了学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当时学校仅有两台显微镜,师生们把它们视若珍宝,在反“扫荡”中遇到敌机轰炸,学生就用身体保护显微镜,宁愿自己受伤。
白求恩留下的小型X光机,怕被敌人毁坏,平时藏在山洞里,学员实习或需要给伤员检查时,就去山洞里使用。
教材也十分匮乏,只能由教员自己编写。
因为很难找到参考书,凭自己编写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史馆里陈列着一部殷希彭编写的《病理学各论》手稿,全书100多页,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整,无一处涂改。
病理学授课需要大量人体标本和显微镜标本来配合,但当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只能用挂图代替。
殷希彭用几块小黑板,用五色粉笔在上面描绘,画得又快又好。
在白校师生眼中,当时只有他画的解剖图能与白求恩的媲美。
他的解剖图和板书被称为“白校一绝”。
据康克回忆,殷希彭每天晚饭后同教员们一起种菜劳动,夜间备课。
上病理课前一天晚上,点着油灯在小黑板上画病理解剖图,第二天带到课场,把小黑板挂在树上或靠在墙上讲解。
学员以石块当坐凳,膝盖当桌子,听课做笔记。
作为一所创办于战火中、又位于抗日一线的特殊卫生学校,白校的教学注定有其特殊性,其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教学制度等都要适合当时的战斗特点。
白求恩审定教材的时候,专门提出了三条主要意见:
一是教学内容要联系当时实际,应多讲一些根据地条件下实用的诊断技术。
二是内容不能过多。
一些药物是过时的老药,可以不讲,应多讲常用药。
三是要充分考虑军医一年半学制与教学内容的关系,把急需的内容讲深讲透。
白校学习时间抓得很紧,每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一天有四五个小时是上课,两个小时实习,两个小时自修,两个小时课外活动或生产劳动,晚上大家围坐在油灯下学习,油灯油用光了,就摸黑讨论。
开学不久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一天晚上,殷希彭到课堂检查学员自习情况,发现明亮的煤气灯下只有一半学员在上自习。
他生气地集合全体学员讲话:
“你们知道这盏煤气灯的来历吗?
它是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从加拿大漂洋过海带到中国来,带到我们边区来的……因为你们在老百姓的豆油灯下看书不方便,今天在教室里点起这样亮的灯,有的同学不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条件,不来上自习,你们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白求恩对你们的希望。
”
白校在教学中坚持“教学合一”“学以致用”的原则,基础课服从临床课,临床课服从战争。
时任校长江一真在回忆录里说: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是我们提出的战斗口号。
在反‘扫荡’中,除行军外,一有空隙,就抓紧时间进行教学。
同学们背起背包,带上武器,到驻村外的树林里或山洼里便于防空的地方,把队伍集合好,教员便来上课,同学们称这种上课叫‘武装上课’。
常有这样情况:
那边武装部队在战斗,能听到隆隆炮声,而这边同学们仍稳坐钓鱼台,照样聚精会神地上课。
”
每次行军出发时,教师会给学生布置好学习内容,让学生在行军中思考。
先行的学员用粉笔在路边写上医药技术问题,向后边队列中的某同学点名,请其回答。
这种方法既可消除行军中的疲劳,又可以复习功课。
同学们还用纸写上比较难记的内容,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边走边看边背诵。
1940年“百团大战”打响,教师们提出“战场就是课堂”,带一、二、三期学员开赴前线,参加救护伤病员的工作。
白校只有十多名教员,却担负着数百名学生的教学任务,每名教员要担负两三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还要担负一定的医疗任务,工作量很大。
校长江一真也要授课。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教课有困难,但我愿意学习,有时行军骑在马背上也要看书,上课前我认真备课,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滥竽充数。
”
尽管边区生活条件很差,但各级还是想方设法照顾教员们的生活。
每逢反“扫荡”,教员都配有马匹和警卫员。
吃饭也是专门开小灶。
军区还经常把缴获的罐头、香烟等送到学校。
但教员们总是把组织上照顾的东西让给老人或病号,吃粗粮,自己种菜打柴。
白求恩牺牲后,白校还来过一个外籍医生,就是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的印度大夫柯棣华。
1940年秋季,柯棣华到白校担任外科教员,后被任命为学校附属医院院长。
刚开始上课时,他因为汉语不好,曾把“一般战伤急救”写成了“一般战伤急球”,学生哄堂大笑。
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以适应教学需要,柯棣华经常在菜油灯下看一本自己装订的毛边纸本,上面写满了注音的中国字,那就是他自编的“汉印字典”。
后来他不仅能够完成教学,还学会了不少中国的成语和歇后语。
柯棣华在教学中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考虑到学员毕业后面临的恶劣工作条件,他想方设法教给大家一些简易诊断方法。
比如讲述诊断糖尿病时,告诉学员,让病人在蚂蚁洞附近撒尿,如果有蚂蚁来吸食,就证明尿中有糖。
这个方法虽不十分灵敏,但也是在当时条件下被逼出来的“土办法”。
后来,聂荣臻亲自找柯棣华,请他出任白求恩学校附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柯棣华欣然同意。
他医术精湛,对病人十分负责,曾对大家说:
“作为一个医生,抢救病人是第一位的事,休息是第二位的事。
”在唐县葛公村百姓中传颂着一副对联:
华佗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
老百姓还亲切地称他为“黑妈妈”。
在教员、学员的共同努力下,白求恩学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创造着世界医疗教育史的奇迹。
从1939年9月正式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6年时间里,共培养了各类医务人员920人,为加强边区卫生建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校学子血染梯子沟
在战火中不断发展的白校,1941年秋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1941年8月下旬,驻察哈尔和华北的日本鬼子同时对平汉路以西的山区进行了残酷的秋季大“扫荡”,目的是报复一年前八路军开展的“百团大战”,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攻势。
日军将这次“扫荡”的方式称作“铁壁合围”。
由于叛徒的出卖,晋察冀根据地在日军的这次“扫荡”中蒙受了巨大损失。
日伪军在汉奸指引下,集中优势兵力直扑晋察冀军区的后方基地。
唐县作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冀中军区卫生部、供给部所在地,成为日本华北派遣军进攻的重点。
反“扫荡”一开始,白校师生统一行动,向陡峭的青墟山转移。
后来决定分两部分突围,一部分由校长江一真率领,包括军四期、调四期、护三期、高一期和妇产班,因为军四期、调四期、护三期快要毕业,为尽快讲完剩余课程,教员们也随这些学生行动,计划在游击途中继续上课。
另一部分,由政委喻忠良率领,包括军五期和六、七合期。
1941年10月5日,天刚蒙蒙亮,率领一分区指挥机关700多人突围至花塔山的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在望远镜里猛然发现,镜头里到处是敌人的帐篷,跑了一夜,反而又钻进了日军的包围圈里。
同样被包围在这里的,还有喻忠良带领的白校师生200多人,以及冀中军区后方留守机关和当地干部群众,总计约3000人。
几支部队从不同的地方突围至此,都陷入了绝境:
花塔山三面发现敌人,北面虽然还没有,但很难走,都是山崖。
白校所在地葛公村已被日军占领,学校房子被炸。
师生们连夜钻山突围,被敌人发现,尾追不舍。
这样的情景,让杨成武也很犯难。
他在回忆录里说:
“说实话,如果光是我们这些惯于战争的部队还会好些,我们好多班长、连长都是长征过来的,经历战斗上百次;可是,难就难在还有这么多手无寸铁的群众,特别是这么多已经被追得散了架的白校学生!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不少女同志放弃了名门闺秀的优裕生活,自愿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
他们是我们整个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说什么也得把他们带出去!
”
杨成武要求被围的人员统一听他指挥。
在当地百姓指引下,杨成武决定带领大家从梯子沟突围。
这条沟有十几里长,沟里满是积水,坑坑洼洼,如果被日军封住出口,很难冲出去。
但杨成武还是决定冒险突围。
在向梯子沟转移的过程中,大家发现日军扑向了石家庄子方向。
石家庄子是军区后方医院,连伤员带医护队员有约300人。
那里的伤员大都是行动不便的重伤员。
白校师生虽然连续行军后已经十分疲惫,但还是主动请缨,要求前往后方医院转运伤员。
后方医院在匆忙中开始转移。
转移中,有的重伤员知道敌情万分危急,怕连累大家,便向自己头部开了枪。
一位女护士正赶上难产,她拼尽全力将孩子生下后,交给最后一批撤离的白校学生,知道自己怎么也走不动了,半路上跳入龙潭湖里自尽。
梯子沟两边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盘绕在其间。
为了顺利突围,杨成武命令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带侦察连和三连牢牢守住梯子沟入口,坚决顶住鬼子的进攻,为大部队冲出梯子沟争取时间。
日军疯狂追击,侦察连和三连在梯子沟进口两侧山头顽强阻击,敌众我寡,打得非常艰苦,两个连伤亡四五十人,三连连长胡尚义光荣牺牲。
由于担心梯子沟出口有日军堵截,杨成武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组织部队拼死也要打开一个突破口,让包围圈里的亲人们脱离险境。
所幸的是,梯子沟并没有日军把守,大家暂时摆脱了危险。
杨成武立即派出两名侦察员,前往大平地摸清情况。
当时突围的情景,杨成武在回忆时说:
“最苦的算是‘白校’的女同志了。
她们近半数是不满二十岁的姑娘,有的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身上背着沉重的背包、粮食和医学讲义,有的还背着枪。
连续艰苦、紧张的突围,使她们脸上、手上和军衣上都被泥土和青苔蹭得乱糟糟的,裤管被荆棘割破了,腿脚鲜血淋漓。
有几位姑娘披着散发,脸色苍白,被同伴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走。
战争年代的女同志,确实比我们男同志艰苦得多。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姑娘们能在暗夜里爬上陡峭险峻的花塔北山,能在敌人合围的危急关头跟着我们急行军,通过这狭长而阴森的梯子沟。
”
出了梯子沟后,身经百战的杨成武意识到危险并没有远去。
他向冀中军区后勤部和白校的负责人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他准备带队前往大平地,然后连续行军一百多里,跳到狼牙山的北面去,那样才能彻底跳出日军的包围圈。
然而,白校师生此时已经精疲力尽,丁一和喻忠良看着满地趴着、躺着的学员们,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和伤员,犹豫再三,决定不跟杨成武的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转而向东南的大洼地、槐树青、道士观一带转移。
10月6日,白校师生到达道士观村附近,隐蔽在玉米地里待命休息,许多人一坐下,顾不得秋夜的寒气和浓重的雾水,依偎着打起瞌睡。
一些学生到附近老乡家煮粥。
可是粥还没吃上,敌人就出现了。
丁一急促地对喻忠良说:
“敌人从大台那边上来了,部队赶紧转移!
”
此时,日军一排机关枪都对准了这块大洼地,还没等他们组织撤离,敌人的机关枪就响了。
有的女学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懵了,竟对着敌人的枪口跑了过去,一个个应声倒下。
敌人是全副武装的7000多日军,强弱立判。
喻忠良命令机枪掩护,队伍向南冲。
他和左克、后方医院的院长等带着仅有的几支枪阻击敌人,掩护学员们转移。
在老乡家做饭的郜靖芳把热粥往地上一扣,塞起搪瓷碗,和肖敏等四个女同学大步流星地向山沟里跑去。
她们刚刚跑出沟口,拿着枪的杨青龙突然停下,“不好,前面有敌人!
”举起枪来便射击。
郜靖芳也急忙冲后面赶上来的队伍扯开嗓门大喊:
“赶紧回去,这面有敌人!
”然后掉过头来向山坡上跑去。
又跑了一阵子,已经快到道士观村头。
丁一突然警觉地停了下来,迅速察看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然后气喘吁吁地命令:
“叫同志们不要再往前跑了,前面可能有敌人,马上向东面转移。
”丁一话音未落,侧面扫来一排敌人的子弹。
白校的队伍立刻调转方向往东山坡跑去,大家奋力爬上山坡。
在两面高山林立的白银坨峡谷,手无寸铁的白校学员和医务人员沿着小道向南冲,然而沟门很快就被日军堵住了。
北面的鬼子也追了上来,学员和伤员被堵在了白银坨下的白银湖。
白银湖东口有一条峡谷叫白银谷,一些学员们想从这里出去,却因地形而受阻。
日军在白银谷北面山头架起机枪,猛烈扫射。
学员们赤手空拳,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但最后除小部分人生还外,左克、肖敏、陈金全等150余名学员全部遇难。
有的女同志受伤了,实在跑不动了,怕拖累战友,就给自己一枪。
突围不出去的男学员为了保护女同志,与敌人扭打在一起,被刺刀捅穿了胸膛。
一些白校的女学生被凶暴的日军当作练习拼刺的活靶。
李登秀老人当时就躲在白银谷北面的草栅里,亲眼目睹了白校学员牺牲的惨状:
白校学员的尸体堆积着,什么样的都有。
幸存的郜靖芳看到,左克的遗体半卧在一个流水冲成的小坑里,身上有好几处敌人刺刀留下的伤痕。
左克出身于革命家庭,原名裘振先,是辛亥革命烈士尹维俊和裘绍的小女儿,出生时因为母亲遇害而早产,父亲半年后牺牲。
李登秀老人哽咽着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现场的惨状:
山野上到处是丢弃着的被刺刀挑破的背包,乱纷纷的医学讲义,破碎的锅碗和女同志的头梳、发夹。
遇难者的遗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石头间、草丛中。
男同志的脑袋被敌人的大皮靴踩扁了。
女同志被敌人野蛮地糟蹋后,胸部被刺得乱七八糟,惨不忍睹。
前往掩埋烈士遗体的民兵全都哭了,情报站的同志向杨成武汇报情况时,说着说着也哭了。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他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这次反“扫荡”,是白校牺牲同志最多的一次。
10月15日,整个反“扫荡”斗争结束,各路师生陆续返回学校驻地葛公村。
在历时50多天的反“扫荡”斗争中,白校坚持教学26天,军医四期、调剂四期和护士三期都按时完成了教学计划,于10月18日毕业。
在反“扫荡”结束后,师生们又马上投入到新的教学中。
以调剂四期学员为主体,组成了军医八期。
11月,组成了高二期和军医九、十合期和调剂六期,并于12月中旬开学。
尽管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白校依然坚持战斗。
到1941年底,学校先后毕业422人,学校附属医院初步成为了综合性医院,成为晋察冀军区的医疗中心,仅1941年就治疗3.3万余人次,施行各种手术1600多例。
历经战火洗礼的白校,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