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一.docx
《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一.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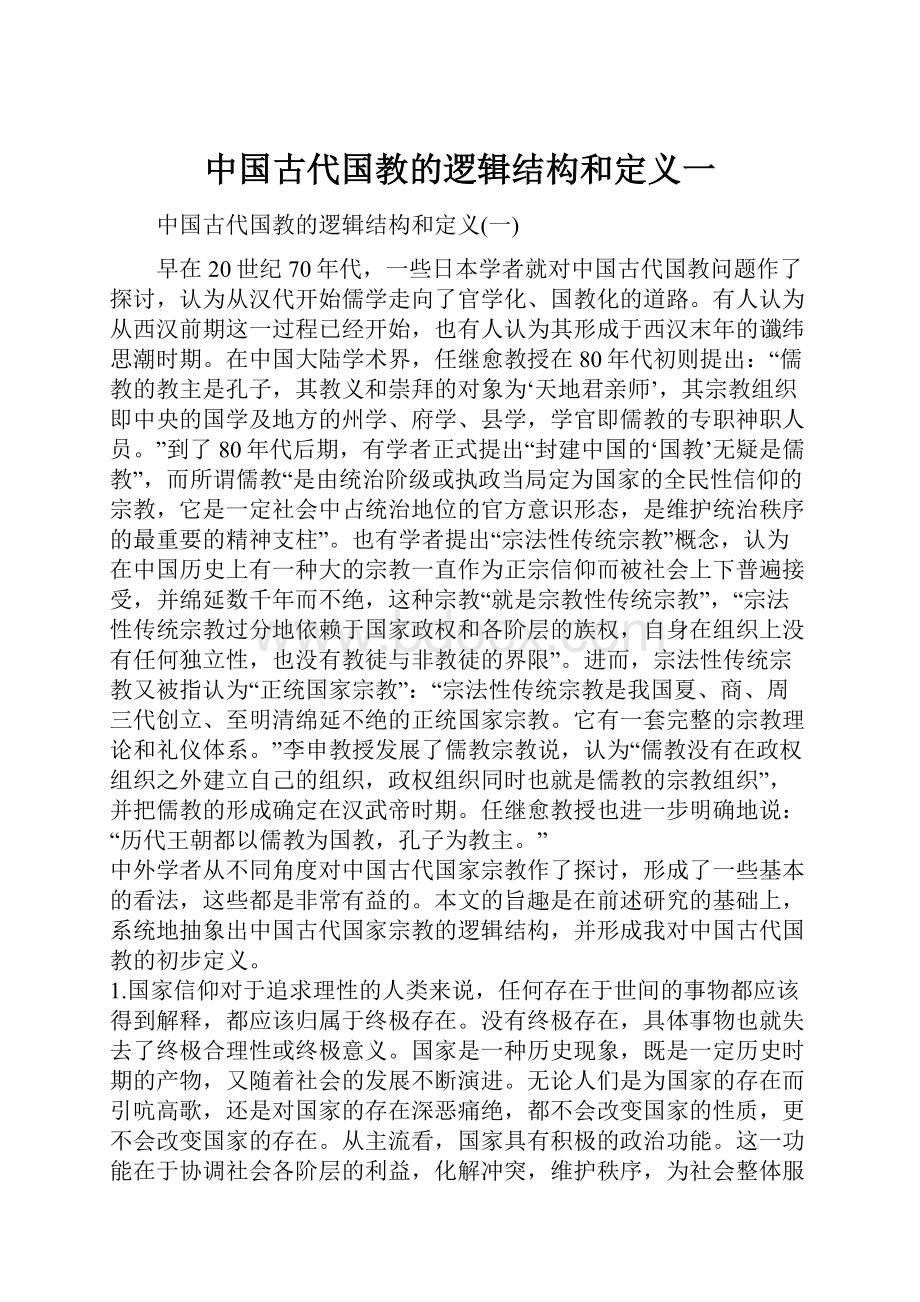
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一
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
(一)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对中国古代国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从汉代开始儒学走向了官学化、国教化的道路。
有人认为从西汉前期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也有人认为其形成于西汉末年的谶纬思潮时期。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任继愈教授在80年代初则提出:
“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拜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
”到了80年代后期,有学者正式提出“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而所谓儒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也有学者提出“宗法性传统宗教”概念,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被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这种宗教“就是宗教性传统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过分地依赖于国家政权和各阶层的族权,自身在组织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也没有教徒与非教徒的界限”。
进而,宗法性传统宗教又被指认为“正统国家宗教”:
“宗法性传统宗教是我国夏、商、周三代创立、至明清绵延不绝的正统国家宗教。
它有一套完整的宗教理论和礼仪体系。
”李申教授发展了儒教宗教说,认为“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并把儒教的形成确定在汉武帝时期。
任继愈教授也进一步明确地说:
“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
”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国家宗教作了探讨,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的旨趣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抽象出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逻辑结构,并形成我对中国古代国教的初步定义。
1.国家信仰对于追求理性的人类来说,任何存在于世间的事物都应该得到解释,都应该归属于终极存在。
没有终极存在,具体事物也就失去了终极合理性或终极意义。
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进。
无论人们是为国家的存在而引吭高歌,还是对国家的存在深恶痛绝,都不会改变国家的性质,更不会改变国家的存在。
从主流看,国家具有积极的政治功能。
这一功能在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化解冲突,维护秩序,为社会整体服务。
国家这一功能的削弱和丧失,也就意味着特定国家的沦落甚至覆亡。
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社会中存在冲突,要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就需要社会各阶层的整合。
整合方式有二:
一是物质关系的整合,一是精神关系的整合。
就精神整合而言,它是政治价值的社会认同过程。
政治价值认同是一种思想运动,最终结果是形成政治信念。
当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某种社会行为是对的,某种社会行为是错的,表明该社会已然有了特定的政治道德观,而政治道德又依赖于终极政治价值观的支持。
政治价值观反映了对特定政治状况和政治结构的认同。
人们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通常不是独立思考之后的结果,更多地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社会下层民众来说尤其如此。
在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方面却大体一致。
如同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眠一样,缺乏特定的政治价值观,一个人就难以容身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
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思想锁定”,它要求并限制人们依照一定的规则去做,却不要求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样做。
政治价值观是政治信念或政治信仰,而信仰是无条件的认同。
因而从一个角度看,信仰是一种宗教精神,而不是理性精神。
理性面前无“定论”,而信仰的本质属性是预设“定论”。
思想的僵化既是社会稳定的功臣,也是社会迟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任何一种政治价值观都是人为设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
当它被社会中大多数成员认同并固化之后,便被视为“理性”。
这种“理性”却不容讨论,在理论上是“盲点”,被确定为“纲常”和“基本原则”。
这显然是逻辑上的悖论。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前一个历史时代中被奉为“理性”的信念,在后一个历史时代又往往被视为“非理”和愚昧,被拒斥和否定。
人类政治精神的演进就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过程,从粗陋走向精致。
人类对政治文明的敏锐洞察力就在这一精致过程中钝化了。
事实表明,生活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有局限性。
这是一种“井蛙效应”。
当蛙从原来所处的井中超越出来的时候,它才会蓦然发现,原来的井实际上是它认识世界的牢笼。
宗教精神正是思想的牢笼。
当我们作出这种认识判断的时候,并不表明我们对国家信仰持消极态度,更无意否定国家信仰的积极功能和意义。
我们所要表明的是,国家信仰或政治信念是一柄双刃剑,而政治引导者的责任就在于认识政治信仰的双重功能,将政治引向日益昌明的通衢大道。
2.政府国家信仰的形成既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政治化过程。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几经变迁,在每一次国家形态的转型期都发生过新旧政治信念的冲突,旧的国家信仰体系和政治信念被淘汰是必然结局。
这并不是说政治工具——政府及其权力不发挥作用,而是说随着政府性质的转变,旧的国家信仰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
任何政府都在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宣扬自己的政治价值观。
毫无疑问,政府是贯彻特定的国家观念的工具。
然而政府本身需要权威,一个没有权威的政府形同虚设。
权威的获得通常依赖两种手段:
一种手段是运用暴力,强制社会成员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另一种手段是使政府本身偶像化、神圣化。
实践表明,单独运用其中的一种手段特别是仅仅运用暴力手段并不成功,它往往导致作为政治工具的政府本身的毁灭。
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是二者并用。
如此一来,作为传布国家政治信念工具的政府或统治者首先被信念化、神圣化,成了政治信仰体系的中枢。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中有关部族领袖的神话和帝王神话是那样斑斓多姿,累累不穷。
3.典礼仪式政治信念和政治神话是抽象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它需要以一定的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变成形象化的可视的语言。
只有这样,信仰才能固化在人们心中,并进一步贯彻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中。
我们看到,宗教的演进过程就是信仰的不断抽象化过程,也就是对偶象崇拜和礼仪形式逐渐扬弃的过程。
然而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无论是国家宗教还是民间宗教,能完全摆脱偶像崇拜或典礼仪式。
宗教仪式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宗教信仰的“外化”程度与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成反比。
在中国上古时代,国教典礼的核心是血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朝实行的是周祭制度;而在中古时代,无论是封禅还是郊祀,政治祭祀在频率上和规模上都大为逊色。
即使在现代政治中,国教典礼仪式依然存在。
罗伯特·贝拉(RobertBallah)在《美国的公民宗教》中提出,在美国社会中有一种存在于教会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之中,同时又超然于各个教会之上的为政治服务的宗教,他把这种宗教称之为“公民宗教”。
沃纳尔(W.LloydWarner)对美国的国觞节神圣典礼作了专门研究,认为“国觞节是对死者的崇拜,但又不仅仅是对死者的崇拜,因为经过或认同于基督教会对上帝的礼拜而象征性地对为国捐躯者的祭奠,这些为国捐躯者的死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组织、引导并不断地呼唤出社区和整个国家的集体理想”。
因而,国觞节礼仪是典型的公民宗教仪式。
顾迪(JackGoody)对典礼仪式素有研究,他把典礼仪式分为三类:
巫术的,宗教的,世俗的。
他认为“宗教典礼……是唯一的关涉神秘信仰或上帝,即超自然存在的”。
韦斯勒(H.J.Wechsler)补充道:
“典礼是一种象征性的陈述形式。
”说得更明确些,宗教典礼是宗教信念和宗教精神的外化,是宗教精神的模式化和行为化。
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宗教精神得以强化和渲泄,使信仰变成了看得见的行为,并使宗教角色不断得以表达和确认。
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政治礼仪或国教典礼无足轻重,甚至荒唐无稽。
从国家宗教研究的立场看,实际情形刚好相反,政治典礼对国教信仰的维护至关紧要,有形的信仰与无形的信仰互为表里,不可或阙。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表达方式,在抛弃旧的信仰表达方式之后,有必要建立新的信仰表达方式。
国教典礼仪式的真空或缺失同国家信仰的缺失一样,后果是严重的和灾难性的,它会造成政治价值的流失,并有可能导致特定政治秩序的衰亡。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主张与所谓“政教分离”的时代精神相悖,但历史已然表明,“政教分离”的根本要求在于,在一个民间宗教多元化的国度中,政府应该与某一种民间宗教或某一个宗教教派分离,而不是政治与政治信仰分离,也不是政治与为国家信仰服务的典礼仪式分离。
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国家宗教十分重要。
4.政治伦理政治信仰的意义是为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确立一个理论支点,为政治道德找到最终的依据。
因而从实际上说,国家宗教追求的目标不是终极价值本身,而是植根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体系和政治秩序。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国度中,政治道德千差万别,并且往往相互冲突,但它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特点,即与现实的政治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家道德或政治道德是一定政治状况的反映,它表明了一种需要,一种维持秩序的需要。
如果说法律反映了这一需要的行为强制,那么,国家道德反映了这一需要的精神专制。
法律限制人们的行为,而道德束缚人们的心灵,心灵束缚比法律限制更彻底、更深刻。
政治道德反映了政治关系,并为政治关系服务。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政治道德或政治伦理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中国上古时代,它反映为维系部族之间关系的“天命”和维系部族内部等级关系的“礼”。
秦汉以后,血缘国家解体,地缘国家形成,政治伦理也就演变成以三纲、六纪、五常为内容的新体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说教不仅可恶,而且可笑。
然而,董仲舒把三纲说成是上天的意志,朱熹更把这说成是天理。
在尊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训条下,现实政治秩序变得神圣不可触犯,违背国家道德就是邪恶,甚至是大逆不道。
在传统中国,国教道德与民间宗教道德既相联系,也各有侧重。
这种联系与区别在儒教道德观与佛教、道教道德观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
作为中国中世纪的国家宗教,儒教强调的是政治纲常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有道伐无道”等等,总之一句话,正像韦伯(MaxWeber)反复强调的那样,儒教是“入世”的宗教。
与儒教大相异趣,道教关注祛病健身和修炼成仙,佛教追求精神不死和涅槃境界。
然而在基本的道德诫条方面,儒教与佛、道二教却有很大的相似性,儒教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被注入到道教和佛教道德准则中去,不杀生、不淫欲成了道教和佛教对儒教道德的进一步运用。
民间宗教道德是国教道德的深层基础,国教道德是民间宗教道德向政治领域的延伸。
用这一观点透视近代美国社会,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相似性。
哈切森(R.G.Hutcheson)指出,在美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公共道德关系上,“一方面人们所关心的是在这个具有多种宗教的社会中如何为所有的人提供充分的良知自由和同等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关心如何形成一种民族的文化。
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社会道德的支柱所在是宗教。
正是这种关心导致这么多的人坚持要确立某种官方宗教”。
他认为,这种官方宗教可能是“一种多信仰的国教”,因为在这里“显然没有一种单独的宗教能获得大多数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正是国教的必要条件”。
与中国传统的儒教类似,美国的官方宗教也是隐性的,但却是存在的。
它所具有的“公共道德”的基础,正是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干的民间宗教道德体系。
5.政治学术政治道德既是政治传统的延伸,也是政治现实的产物。
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统一与对立,促成了“经”与“经学”的矛盾统一关系。
经是文化的原典和历史的陈迹,是传统道德的渊薮。
可是社会在不断变化,经却一成不变。
因而在经与现实所需要的教义之间需要架起一座桥梁,以便将传统信仰和道德与现实需要联结起来,这座桥梁就是经学。
经学是对经的现实化诠释。
仔细考察中国传统国教的“经”就会发现,一方面后人对经义的抉择完全以现实需要为前提;另一方面经的容量也在不断变迁,从五经、七经、九经直到十三经,还有精致的四书五经。
经仅仅提供一种文化资源和精神权威,而不是现成的答案;经学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可用的理论或思想工具,即现成的答案。
因而,经与经学具有不同的功能。
在通常情况下,经被认为是教主的言论和行迹,它被视为神启或神圣的产物。
国教的经通常反映传统的、保守的政治观和政治道德,从传统的道德立场来看,是高尚的、善美的,它能引导人们进入理想境界。
儒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正是此种情景的反映。
经学则是经师们阐释并以教皇名义钦定的教义。
儒教经典的杂博是众所周知的,它既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而成,内部的龃龉矛盾颇多。
正是这种经内的矛盾引发了经师之间的争论和经学的发达。
对经的阐述不是随意的,有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在汉代被称为“师法”或“家法”,在朴学家那里被称为“考据”。
经学本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繁荣、调整磨合、衰落危机的过程。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主唱,东汉古文经学兴起,虽经宋学的更新,但到清朝的朴学,正反映出经学本身“攻”和“守”使命在总体上的转换。
近代中国今文经学的复兴,正是传统国家宗教危机的反映。
经学有两重属性,一重是神学权威,一重是理论思辩。
前者要求盲从,后者要求思考,这两重属性既矛盾,又统一。
它意味着,作为政治学术的经学需要理性的思考,以便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与不变的经之间经常协调;另一方面,人们的思考必须以不危害经的权威为前提。
这就好像是画圆,经学家是站在圆内画圆,而决不允许圈外的人画成方。
经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以经注解现实,但在表面上却是以现实的活动注经,现实政治是在不断地实践经的内容。
这似乎是一种有着双重规则的政治游戏和学术游戏。
经学正是政治与学术的合二而一,是不变的权威与多变的现实的协调和统一。
6.国教组织中国古代国家宗教作为一种隐性的宗教,它在以往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研究,乃在于它没有像民间宗教一样的教团组织和教会机构,以至于人们忽略了在民间宗教之外还存在所谓的“国家宗教”。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对国家宗教概念的运用可能会导致可怕的误解。
在历史上民间宗教一元化的国家中,民间宗教通常与国家宗教合而为一,在信仰体系、宗教道德、宗教典礼、宗教组织、宗教领袖、宗教教义诸方面二者是混合的。
缘于此故,人们用“国家宗教”来表述这种一体化的宗教。
但是,从国家宗教研究的立场看,纯粹的“政教合一”是一种逻辑上的古典形态,它与我们所说的国家宗教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
这就犹如起初是一条大河,但在后来的流程中分成两条支流一样,我们既可以说支流之一与未分流前的大河有相同性,又应该注意到支流之一并不完全等同于未分流前的大河。
所以,国家宗教是对具有政治属性、为政治秩序服务的宗教的规定和命名,是一种对属性的逻辑判断。
当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走向二途以后,民间宗教从古典的一体化宗教中蜕变出来,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团组织机构。
但国家宗教的组织机构在哪里?
其实,国教组织正是国家的行政组织,国教机构正是国家行政机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国家组织作为国教组织、国家行政机构作为国教机构的真相,恰恰是由中国古代最不具有国教信仰特征的秦王朝赤裸裸地揭示出来的。
秦朝丞相李斯声称: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如果把这话移植到汉代,当然是“以儒为教,以吏为师”。
执掌国教布道职能的不是民间僧侣,而是政府的经学博士和士大夫,他们布道的对象正是治下的民众。
因而实际上,国家行政组织充当着国教组织,各级官员兼任着国教牧师或政治牧师的角色。
国教组织比民间宗教组织具有更强烈的排他性和独占性。
如果说在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一体化时期二者是平分秋色的话,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分离后,惟有国家宗教组织具有普世性,是全体国民的组织,而无论它的国民分属哪一种民间宗教。
在民间宗教组织最初兴起的过程中,它们也试图建立一种普世性的组织,如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但“国不堪贰”,国中之国或权外之权显然不能被官方接受。
其结果众所周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后来均遭覆灭的厄运。
在汉代以后的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民间宗教组织规模很小,政府通常规定某一个州、县大致固定的职业僧侣名额,以度牒作为合法僧侣的身份证件。
作为臣民,可以自由选择某一种民间宗教信仰,但通常不被允许与某一民间宗教结成过于紧密的组织联系。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是一般化的信徒,而不得随意成为职业僧侣。
一旦这一原则受到破坏,便预示着破坏这一原则的民间宗教的灾难来临。
“三武一宗法难”的根源之一,正在于民间宗教组织的扩张危害了国教组织的独占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