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讲演录芝诺.docx
《哲学史讲演录芝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哲学史讲演录芝诺.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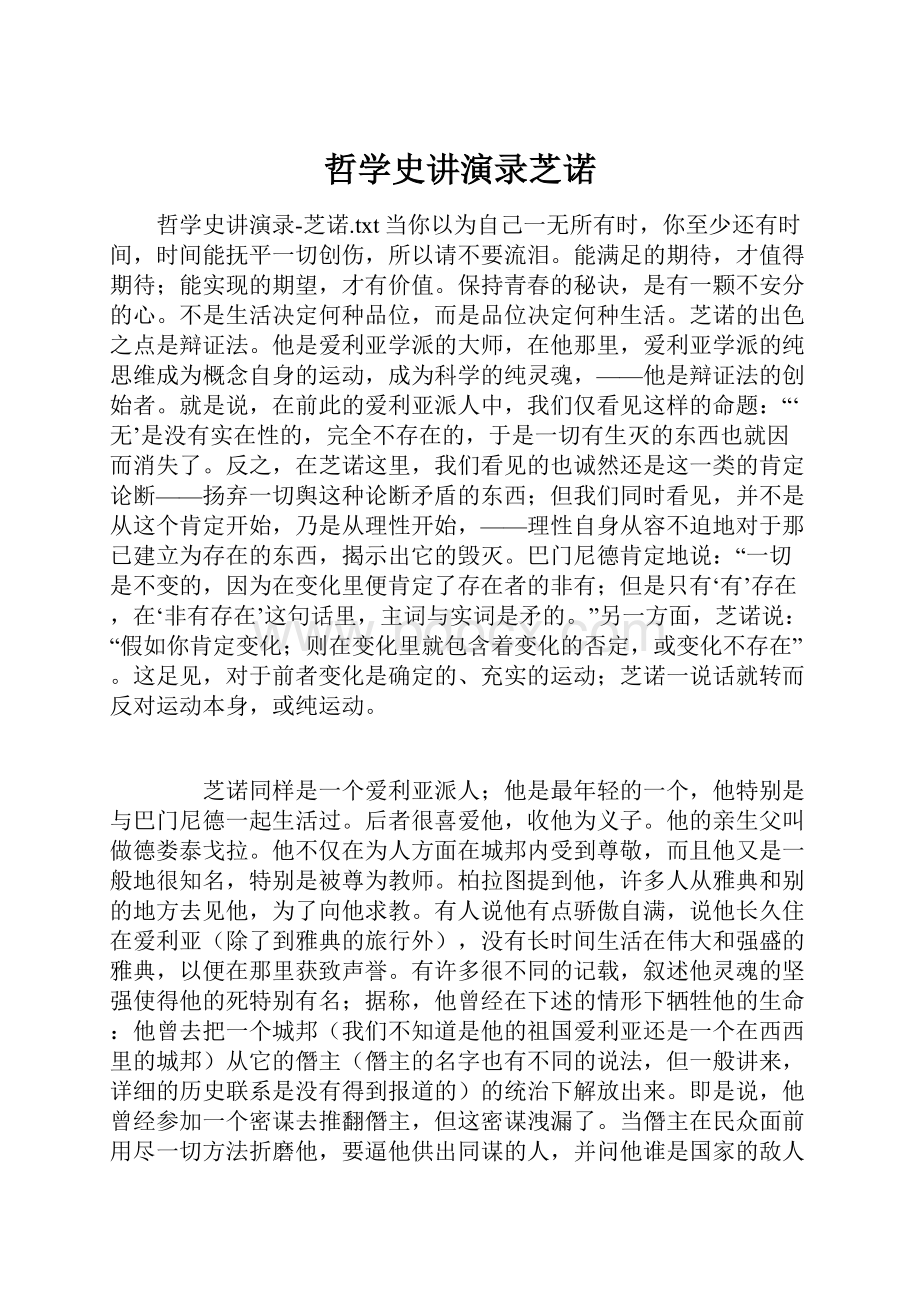
哲学史讲演录芝诺
哲学史讲演录-芝诺.txt当你以为自己一无所有时,你至少还有时间,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所以请不要流泪。
能满足的期待,才值得期待;能实现的期望,才有价值。
保持青春的秘诀,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不是生活决定何种品位,而是品位决定何种生活。
芝诺的出色之点是辩证法。
他是爱利亚学派的大师,在他那里,爱利亚学派的纯思维成为概念自身的运动,成为科学的纯灵魂,——他是辩证法的创始者。
就是说,在前此的爱利亚派人中,我们仅看见这样的命题:
“‘无’是没有实在性的,完全不存在的,于是一切有生灭的东西也就因而消失了。
反之,在芝诺这里,我们看见的也诚然还是这一类的肯定论断——扬弃一切舆这种论断矛盾的东西;但我们同时看见,并不是从这个肯定开始,乃是从理性开始,——理性自身从容不迫地对于那已建立为存在的东西,揭示出它的毁灭。
巴门尼德肯定地说:
“一切是不变的,因为在变化里便肯定了存在者的非有;但是只有‘有’存在,在‘非有存在’这句话里,主词与实词是矛的。
”另一方面,芝诺说:
“假如你肯定变化;则在变化里就包含着变化的否定,或变化不存在”。
这足见,对于前者变化是确定的、充实的运动;芝诺一说话就转而反对运动本身,或纯运动。
芝诺同样是一个爱利亚派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特别是与巴门尼德一起生活过。
后者很喜爱他,收他为义子。
他的亲生父叫做德娄泰戈拉。
他不仅在为人方面在城邦内受到尊敬,而且他又是一般地很知名,特别是被尊为教师。
柏拉图提到他,许多人从雅典和别的地方去见他,为了向他求教。
有人说他有点骄傲自满,说他长久住在爱利亚(除了到雅典的旅行外),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伟大和强盛的雅典,以便在那里获致声誉。
有许多很不同的记载,叙述他灵魂的坚强使得他的死特别有名;据称,他曾经在下述的情形下牺牲他的生命:
他曾去把一个城邦(我们不知道是他的祖国爱利亚还是一个在西西里的城邦)从它的僭主(僭主的名字也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讲来,详细的历史联系是没有得到报道的)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即是说,他曾经参加一个密谋去推翻僭主,但这密谋洩漏了。
当僭主在民众面前用尽一切方法折磨他,要逼他供出同谋的人,并问他谁是国家的敌人时,芝诺最初指出僭主所有的朋友作为同谋者,后来并称僭主本人为国家的瘟疫。
于是,他的强有力的抗辩以及所遭受的酷刑和他的惨死激起了市民,提高了他们的勇气去冲击那僭主,把他杀死,并解放了他们自己。
对最末一幕的情况——那猛烈愤怒的心情——特别有不同的叙述。
据说他假装着对僭主还有几句话要靠近耳边说,于是他就咬下僭主的耳朵,并那样地紧紧地抱住僭主,一直到他被别人打死。
另有人报称:
他用牙齿咬了僭主的鼻子。
又另有人说:
当他由于他的答覆遭受着重大的酷刑时,他自己咬脱他的舌头,将舌头唾到僭主的脸上,为了表示给僭主看,他再也不能从他那里逼出什么口供;于是他就被放在一个石臼里捣碎而死。
(一)芝诺哲学的论旨,就内容说,完全与我们在塞诺芬尼和巴门尼德那里所看见的相同。
只有这点区别,即芝诺把理论中的各环节和对立更多地作为概念和思想表达出来。
在他的论旨里,我们已经看见进步;在对于各个对立和规定的扬弃里,他更进了一步。
他说:
“如果说有物存在,有物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他这里的‘物’是指神而言);因为它若不从相同者发生,必从不相同者发生,但两者皆不可能:
因为相同者既没有权力产生相同者,也不会被相同者产生,由于相同者必然彼此都具有相同的规定。
”一承认了相同性,则产生者与被产生者的区别就消失了。
“不相同者从不相同者发生也同样不可能;因为如果是从弱生强,或从小生大,或从劣生优,或反之从优生劣,那末从有就会生出非有: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神是永恒的。
”这种说法从来被说成泛神论(斯宾诺莎主义),泛神论是建筑在“无不能生有”这一命题上面的。
在塞诺芬尼和巴门尼德那里,我们得到了“有”与“无”的范畴。
无就直接是无,有就是有;本来就是如此。
“有”就是直接地说出来的“相同性”;反之,相同性,作为相同性,是以思想的运动和间接性、自身反思为前提。
有与非有这样地彼此并立着,而没有把握到两者不同中的统一。
这些不同的东西并不是作为不同的东西表达出来。
在芝诺这里“不同”是与相同”反对的另一环。
进一步他又证明神的统一性:
“如果神是万物中最强有力者,则它应该是一;因为若是有了两个或更多的神,则神将会没有力量支配万物;而只要它缺乏力量支配其他的东西,则它就不会是神。
因此假如有很多的神,则它们之间必会有一些较强,有一些较弱,那末它们就不是神;因为神的本性在于没有东西比它更强有力。
假如它们是相同的,则神就不复具有最强有力者的性质了;因为相同者既不较坏也不较好于相同者”,——换言之,相同者与相同者是没有区别的。
“因此如果神存在,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神,则神便只有一个;假如有了许多的神,则神将不能为所欲为。
”
“既然神是一,则它便处处相同,它能听一切,看一切,并感觉一切,因为假如不这样,则神的各部分中,这一部分将会较另一部分更强有力”(这一部分所在的那里,别一部分不在,这部分挤走了那部分,——这一部分有某种性质,而另一部分则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
神既然是一切方面相同,所以它是球形。
因为它不是这里如此,那里不如此,而是到处如此。
”再则:
“神既然是永恒的,是一,是球形的,所以它既不是无限的(无限制的),也不是有限的。
因为
(一)无限制就是非有;因为非有既无中间,也无起始,无终结,无部分,——这样的东西就是无限制者。
但如果‘非有’存在,则‘有’就不存在。
”无限制者就是不确定者,否定者;它是非有,是“有”的扬弃,而这样一来,它自身便被规定为一个片面的东西。
(二)“假如有许多神,则它们就会互相限制;今既然只有一个,则它便是没有限制的。
”芝诺又这样指出:
“这太一是不动的,也不是不动的。
因为不动的是
(一)非有”——(在非有真没有运动发生,非有是被认作静止不动和空虚,不动者是否定的);——“因为没有别的东西进入不动者里面,不动者也不进入别的东西里面。
(二)但是只有多物才运动;因为一物必须进入他物,才有运动。
”只有异于他物的东西才是运动的;这就假定了时间、空间的复多性。
“太一因此既不静,也不是动的。
因为它既不同于非有,也不同于多。
在这一切里,神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它是永恒的,是一,自身同一,是球形,既非无限制亦非有限制,既不静也不动。
”由于没有东西可以从相同者或不相同者发生,亚里士多德便推出这一结论:
“或者是在神之外没有东西,或者是一切其余的东西都是永恒的。
”
(二)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在芝诺这里同样看到真的客观的辩证法。
芝诺很重要的方面都是作为辩证法的创始人,究竟他之为辩证法的创始人,是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意义下的呢,还是只不过是初步有那个意义,这一点是不确定的——因为他否定了正相反对的宾词。
塞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皆以下面这一原则为根据无就是无,无完全没有存在,或相同者(如麦里梭)是本质;这就是说他们肯定对立的宾词中的一个作为本质。
他们坚执这一点;当他们碰见了一个规定中有对立者时,他们便扬弃这一规定。
但这一规定之被扬弃只是通过别一规定,通过我的坚执,通过我所作的区别,即认为一方面是真理,另一方面是空无,——(这是从一个规定的命题出发);一个规定的空无性并不表现在它本身,并不是它自己扬弃它自己,这就是说,并非它有了一个矛盾在它里面。
例如运动:
我坚执某物,说它是空无,我又按照前提指出它是在运动;因此就推出说,运动是空无者。
但另一个人并不坚执这种说法。
我宣称一个东西是直接地真的,另一个人也有权利坚执某种别的东西是直接地真的,例如运动。
当一个哲学系统反驳另一个系统时,就常是这样的情形。
人们每每是以前一个系统为根据,从这个系统出发,去向另一个系统作斗争。
这样,事情似乎就容易辩了:
“别的系统没有真理,因为它同我的不相符合”;而别的系统也有同样的权利这样说。
我不可通过别的东西去指出它的不真,而须即从它自身去指出它的不真。
如果我只是证明我自己的系统或我自己的命题是真的,便从而推论说:
所以那相反的命题是错的,——这种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前一命题对于这另一命题总是表现为一种生疏的外在的东西。
错误的思想之所以错误,决不能说是因为与它相反的思想是真的,而乃是由于它自身即是错误的。
我们看见这种理性的识见在芝诺这里觉醒了。
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里这种辩证法得到很好的描述。
柏拉图在这篇对话里讲了这种辩证法。
他让苏格拉底说:
“芝诺所主张的基本上与巴门尼德相同,即一切是一,但由于绕了一个弯子就想欺骗我们,好像他是说了一些新的东西。
譬如说,巴门尼德在他的诗里指出,一切是一,而芝诺便指出,多不存在。
”芝诺答覆道:
“他写这篇论文的目的乃在于反对那些力求使得巴门尼德的命题成为可笑的人,因为他们指出即从他的主张的自身就可表明其如何矛盾可笑,自己反对其自身。
因此他是在向那些肯定‘多’是‘有’的人作斗争,藉以指出,从‘多’出发也会推出许多比起从巴门尼德的命题出发更加不通的结论。
”
这就是客观辩证法的进一步的规定。
在这个辩证法里,我们看见单纯的思想已不再独立地坚持其自身,而乃坚强到能在敌人的领土内作战了。
辩证法在芝诺的意识里有着这个〔消极的〕方面;——但是我们也可以来观察辩证法的积极的方面。
按照对于科学的通常观念,命题总是被认作由于证明而得的结果,证明就是理智的运动,就是通过媒介而达到的结合。
这种辩证法一般是:
(一)外在的辩证法,即运动的过程〔内容〕与对于这个运动过程的整个掌握〔形式〕是区别开的;
(二)不仅是我们的理智的一种运动,而乃是从事实自身的本质出发,这就是说,从内容的纯概念的运动出发去证明。
前者是一种考察对象的方法:
提出一些理由,指出一些方面,加以反驳,藉此使得通常当作固定不移的对象,都摇动起来。
这些理由也可能是十分外在的,在智者派那里我们对于这种的辩证法将有更多的要说。
但那另一种辩证法则是对于对象的内在考察;这是就对象本身来考察,没有前提、理念、应当,不依照外在的关系、法则和理由。
我们使自己完全钻进事实里面,即就对象本身而加以考察,即依它自己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去了解它。
在这样的考察里,于是对象自身便显示出其自身〔的矛盾〕:
即自身便包含有正相反的规定,因而自己扬弃自己;这种辩证法我们主要地在古代哲学家那里见到。
那种从外在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观辩证法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人们〔只是〕承认:
“在正当的里面也有不正当的,在错的里面也有真的。
”真的辩证法却不让它的对象有任何剩余,以致可以说,它只是就一方面看来好像有缺陷;而乃是就对象的整个性质看来,它陷于解体。
这种辩证法的结果是空无,是否定;它里面所包含的肯定方面还没有出现。
这种真的辩证法是与爱利亚派的工作分不开的。
不过在他们那里〔哲学〕理解的意义和本质还没有得到广大的发展;而他们只是停留在那里,说:
由于矛盾,所以对象是一个空无的东西。
芝诺关于物质的辩证法,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反驳掉;我们还没有超出他的论证,而仍让这问题处在不确定的状况中。
据辛普里丘说:
“芝诺证明,如果‘多’存在,则它会又是大,又是小:
如果多是大的,那末它在体积上(在一般的量上)就会大到无限”,——超出那作为无差别的限制的多,进而成为无限,而无限者即不复是大,不复是多,无限就是“多”的否定;“如果多是小的,那末它就会小到没有体积”;——而成为一个原子,非有者。
“这里他指出,凡是既无体积,又无厚度,又无质量的东西,也就是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因为如果把它加在另一物上,而此物并不因之增多;因为它既没有体积,加上去,也丝毫不能增加他物的体积,因此所加者,将是‘无’。
同样,如果把它减去,则他物亦不因而有所减少;因此它将是‘无’。
”
“如果存在者是存在的,则它必然有体积和厚度(广袤),是彼此外在的,是彼此离开的。
并且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也有体积,并且在它里面也有相互不同的东西。
但对于某种东西说一次,和老是说它,乃是一样的;在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者,也没有一个东西比另一个东西更不存在。
如果‘多物’存在,则它们既是小又是大:
是小则它就会小到没有体积;是大则它就会大到无限。
”
(一)芝诺的证明的第一个形式是这样的,他说:
“运动没有真理性,因为运动者在达到目标以前必须走到空间的一半。
”亚里士多德对这点陈述得这样简短,因为他前此曾经详尽地研究并发挥这问题了。
这话应当一般地来了解,这是预先假定了空间的连续性。
运动者必须达到某一目的地;这一途程是一个全体。
为了要走完这全部途程,运动者首先必须走完一半。
现在这一半途程的终点就是他的目的地。
但这一半又是一个全体,这一段空间〔或途程〕也还是有它的一半;因此这运动者首先又须达到这一半的一半,如此递进,以至无穷。
芝诺在这里提出了空间可无限分割的问题。
因为空间和时间是绝对连续的,所以可以没有停顿地分割下去。
每一个量——每一时间和空间总是有量的——又可以分割为两半;这种一半是必须走过的,并且无论我们假定怎样小的空间,总逃不了这种关系。
运动将会是走过这种无穷的时点,没有终极;因此运动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地。
人们都知道,犬儒派人西诺卜的第欧根尼对这种关于运动的矛盾的证明曾如何用十分简单的方法去反驳;——他一语不发地站起来,走来走去——他用行为反驳了论证。
但这个轶事又继续说,当一个学生对他这种反驳感得满意时,第欧根尼又责斥他,理由是:
教师既然用理由来辩争,他也只有用理由去反驳才有效。
同样,人们是不能满足于感官确信的,而必须用理解。
这里我们看见〔坏的〕无限〔或纯现象〕初次出现了,在它的矛盾里发展了,——达到了对它自己的意识。
运动,纯现象自身是对象,并且作为一个被思维的、就它的本质说是被假定的东西而出现:
即(我们试从时点的形式来考察)在它的纯自身同一和纯否定性的区别里,——在它的点的区别里,与连续性相反对。
对于我们,在表象里假定空间中的点,或假定在连续性的时间中的时点,或假定时间的现在作为一个连续性、长度(日、年),并没有什么矛盾;但它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
自身同一性、连续性是绝对的联系;消除了一切的区别,一切的否定,一切的自为性。
反之,点乃是纯粹的自为之有、绝对的自身区别,并与他物没有任何相同性和联系。
不过这两方面在空间和时间里被假定为一了;因此空间和时间就有了矛盾。
首先就要揭示出运动中的矛盾;因为在运动中那从表象看来相反的东西也被建立了。
运动正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和实在性;并且由于时空的实在性表现出来了,被建立了,则同样那表现的矛盾也被建立了。
而芝诺促使人注意的就是这种矛盾。
空间的连续性,以及由二分空间而得的限度,均被假定为肯定的东西。
但那由二分得来的限度,并不是绝对的极限或自在自为的东西,它是一个有限度的东西,而又是连续性。
但这种连续性亦复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乃是建立反对者于其内,——二分的限度;但这样一来,连续性的限度又没有建立起来,那一半还是连续性,如此递进,以至无穷。
一提到“进到无穷”,我们就想像着一个“他界”,这是不能企及的,外在于表象,而为表象所达不到。
那是一个无穷的向外驰逐,但却呈现在概念里——一种向外驰逐,由一个相反的规定到另一相反的规定,由连续性到否定性,由否定性到连续性;两者皆呈现在我们前面。
这种无穷进程的两个环节中的一个环节,可以被肯定为主要的一面。
现在芝诺首先这样假定了这种连续的无穷进程,以有限的空间终究是不能达到的,既然有限的空间不能达到,因此就只有连续性了;换句话说,芝诺肯定了有限空间中的无穷进程。
对芝诺的矛盾,亚里士多德的一般的解答是:
空间与时间并不是无穷分割了的,而只是可以分割的。
但是既然时空是(潜在地,不是实在地)可分割的,似乎它们也就应该是实际上无穷分割了的;因为若不然,它们就不能被分割至无穷;——这是表象的看法〔于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解答时〕的一般的答覆。
因此贝尔(Bayle〕说亚里士多德的解答是“可怜的”:
“承认这个学说是正确的实无异于对世界开玩笑;因为如果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则它必包含有无限数目的部分。
那末它就不是一种潜在的无限,而是一种实在地、实际地存在的无限。
但是即使承认这种潜在的无限会由于它的各部分之实际地被分割而变成无限,也不会失掉什么要好处;因为运动是和分割具有同样性质的东西。
运动接触空间的这一部分时,并不接触其另一部分,它是一部分跟着一部分地接触所有各部分的。
这不就是把这些部分实际上区别开来了吗?
一位几何学家在一块石版上书出一些线,把每半寸每半寸都一一指示出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他并不把石版打碎成半寸半寸的,但他却是在上面做了一种分割,指出了各部分的实际区别;我相信亚里士多德不会否认:
如果在一寸长的物质上书了无数条线,也就是作出了一种分割,把那种照他所说只是潜在的无限变成实际的无限。
”这个“如果”真好!
从哲学看来,单纯的概念、普遍,乃是无限性的或纯粹现象的单纯本质,——无限性就是纯概念的运动。
可分性、可能性〔即潜在性〕是普遍;它既是连续性也是否定性,“点”便在这里面假定了,但只是作为其中的环节,而不是作为自在自为的存在。
我能对物质作无限分割,但也只是“我能”罢了;我并不实际地对物质作无限分割。
正因为无限者的性质是这样,所以它的环节没有一个是具有实在性的。
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即一个环节是潜在的,或实际地发生,——既不是绝对限度,亦不是绝对连续性,以致另一环节却老是没有发生。
这是两种绝对相反的东西,但作为环节,这就是说,它们是在单纯的概念里或在普遍里,——也可以说,在思维里;因为在思维(一般的表象)里那被假定的东西同时存在而又不存在。
那被表象的东西本身,或就它之为表象中的形象而言,并不是实物:
它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普遍,不论在意识内或意识外,乃是一中立的〔即非有非无的〕单纯统一。
空间和时间是限量,有限度的量,因此是可以经过〔衡量〕的。
一如我既没有真实地无限地分割空间,同样在运动中的物体也没有真实地经过无限的空间;那一定的空间作为有限的东西呈现在那里,为那运动的物体而存在着。
所以在运动中空间是作为一个普遍的东西为那运动者而呈现着。
那被分割的空间并不是绝对的点积性〔即非连续性〕,而那纯粹的连续性也不是未被分割的和不可分割的;同样时间也是普遍的东西,不是纯粹的否定性、点积性,而也是连续性。
两者皆表现在运动里:
纯否定性表现为时间,连续性表现为空间。
运动本身正是这对立中的实际的统一;这两个概念〔即否定性和连续性〕在运动里从表象看来得到了实在性,而且普遍在这运动里得到这两个概念的统一、作为统一的普遍性的环节,和两者在统一中的相互分离,以及两者在相互分离中的统一。
时间和空间的本质就是运动,因为本质是普遍;理解运动即是在概念的形式内表达它的本质。
运动作为否定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是被表达为概念、为思想;但在时空里,连续性以及点积性均不能单纯地认为本质。
从表象看来这两个环节本身都是不可分离的。
假如我们把空间或时间表象为可以无限分割,则我们因而就会得到无限数的点,但里面也同样存在着连续性,——这就是包括无限数的点的空间。
但这种连续性作为概念即意谓着所有这些点都是相同的;因此正确讲来,它们不是被当作点,被当作相互外在的“一”。
运动是作为时空对立之统一的无限者。
这两个环节〔时空〕也同样表现为存在的东西;它们是那样的无区别,以致我们不假定它们为概念,而假定它们为存在。
在作为存在的时空里否定性就是有限度的量,它们是作为有限度的空间和时间而存在着。
而实际的运动就是通过一个有限度的空间和时间,并不是通过无限的空间和时间。
芝诺的其余的命题也可以从同样的观点去了解,不要把它们了解为反对运动的实在性的辩驳,像最初看来那样,而须把它们了解为如何规定运动的必然方式,但同时又须指出规定运动的方法应如何进行。
推翻对方的反驳即意谓着指出这些反驳的空无性,好像这些反驳必然会站不住,根本不须提出来一样。
但我们必须像芝诺对于运动所曾思维过那样去思维运动,而使得运动的假定本身进一步向前运动。
说运动者必须达到一半,是从连续性,亦即分割的可能性,——单纯的可能性——出发而得到的肯定;因为这种分割的可能性无论在怎样可以想像的每一细小的空间里都永远是可能的。
人们很自然地就承认必须达到一半:
这样一来就必须承认一切,——承认达不到一半;一次那样说就等于说了无数次。
反之,人们总以为:
在一个较大的空间里是可以承认〔达到〕一半;但人们设想着必须来到这样的一点,在这里分割成两半已不复可能(亦即在我们不可能),——即必然会达到这样细小的一个空间,对它已不复能说一半:
这就是说,来到一个不可分的,不连续的,没有〔余地的〕空间。
但这个想法是错的,——连续性本质上是一个规定。
当然空间内有最小的东西,这里面包含有连续性的否定,——但这是抽象的否定;但抽象地坚执着那假想的一半一半地分割,也同样是错的。
当接受一半一半的分割时,就已经接受时空连续性的中断性了。
我们必须说:
没有一半一半的空间,空间是连续的;一本书,一块木头,我们可以把它劈成两半,但对于空间我们却不能这样作,——因为空间只存在于运动中。
人们马上可以这样说:
空间是无限多的点、亦即无限多的限度所组成,——因此是不能通过的。
人们假想着可以从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点过渡到另一个点;但是这样他们便不能前进一步了,因为不可分的点是无限的多。
连续性被分裂成它的对方,不确定的多,——这就是说,不承认有连续性,也就没有运动。
人们错误地主张,以为达到一个没有连续性的东西时运动是可能的;殊不知运动就是联系。
因此当我们以前说,连续性是无限分割的可能性的根据时,则意思是说,连续性只是假定,不过对这种连续性所假定的,乃是无限多的、抽象地绝对的限度之存在。
(二)“第二个证明”(这个证明同样以连续作为前提并假定了可分割性)叫做“阿基里斯”,那行走如飞的人。
古代的哲学家喜欢使思想上的困难穿上一层感官表象的外衣。
有两个往同一方向运动的物体,其中的一个走在前面,另一个与它有一定的距离,比它运动得更快,在追赶它,——我们知道,第二个是可以追得上头一个的。
但芝诺说:
“那走得慢一点的永远不会为那走得较快的所追赶上。
”这一点他是这样证明的。
追赶者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被追赶者于这一个时间开始时出发之处”。
当第二个达到第一个动身的地方时,第一个已前进了一步,留下一段新的空间,这又需要第二个费一部分时间才能走过;依此递推,以至无穷。
例如,乙在一小时内走两哩,甲在同样时间内走一哩。
如果他们彼此相距两哩,则乙在一小时内就达到甲在这一小时的开始所在的地方。
而甲所留下的这一段空间(一哩),乙于半小时内就可以走过,如此以至无穷。
较快的运动对于第二个物体为了走过那中间相距的一段空间毫无帮助;所需的那一点时间,那走得较慢者也永远可以利用,并且“因此他永远占先”。
当亚里士多德讨论这点时,他简略地这样说:
“这个证明还是假定了同样的无限分割”,或假定了通过运动的无限分割。
”这是不真的;因为走得快者将赶上那走得慢者;如果容许他超过那局限他的限度。
”这个答覆是不错的,包含了一切。
就是说,在这种看法里承认了两个彼此分离的不同的时点和两个彼此分离的不同的空间,换句话说,它们是有限度的,它们彼此互为限制。
反之,当人们承认时间和空间是连续的,则这两个时间点或两个空间点便是连续的、互相联系的:
则它们同样是两个,也不是两个,而是同一的。
(一)就空间而论:
在同一段时间里甲走完距离bc,而乙走完距离ab+bc。
在表象里我们最容易解决这问题:
即因为乙走得较快些,他在同一段时间内比起那走得慢的人可以通过较长的距离;所以他可以走到甲出发的地方,并且还可走得更远。
(二)但这应该有的一段完整的时间,却可分为乙走过ab的一段时间和乙走过bc的一段时间。
甲先有第一段时间以走过bc;所以甲到了c的时点,就是乙到了b的时点。
照亚里士多德说,必须超出的那个限度,那必须通过的,就是时间;既然时间是连续的,所以要解除这困难就必须说:
必须把那被区分为两个时段的时间认作是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乙由a走到,又由bb走到。
在运动中,这两个时点当然是一c个时点。
当我们一般地说到运动时,我们总是这样说:
物体在这一个地点,然后走向另一个地点。
由于它在运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