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经典散文青春卷.docx
《百年中国经典散文青春卷.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百年中国经典散文青春卷.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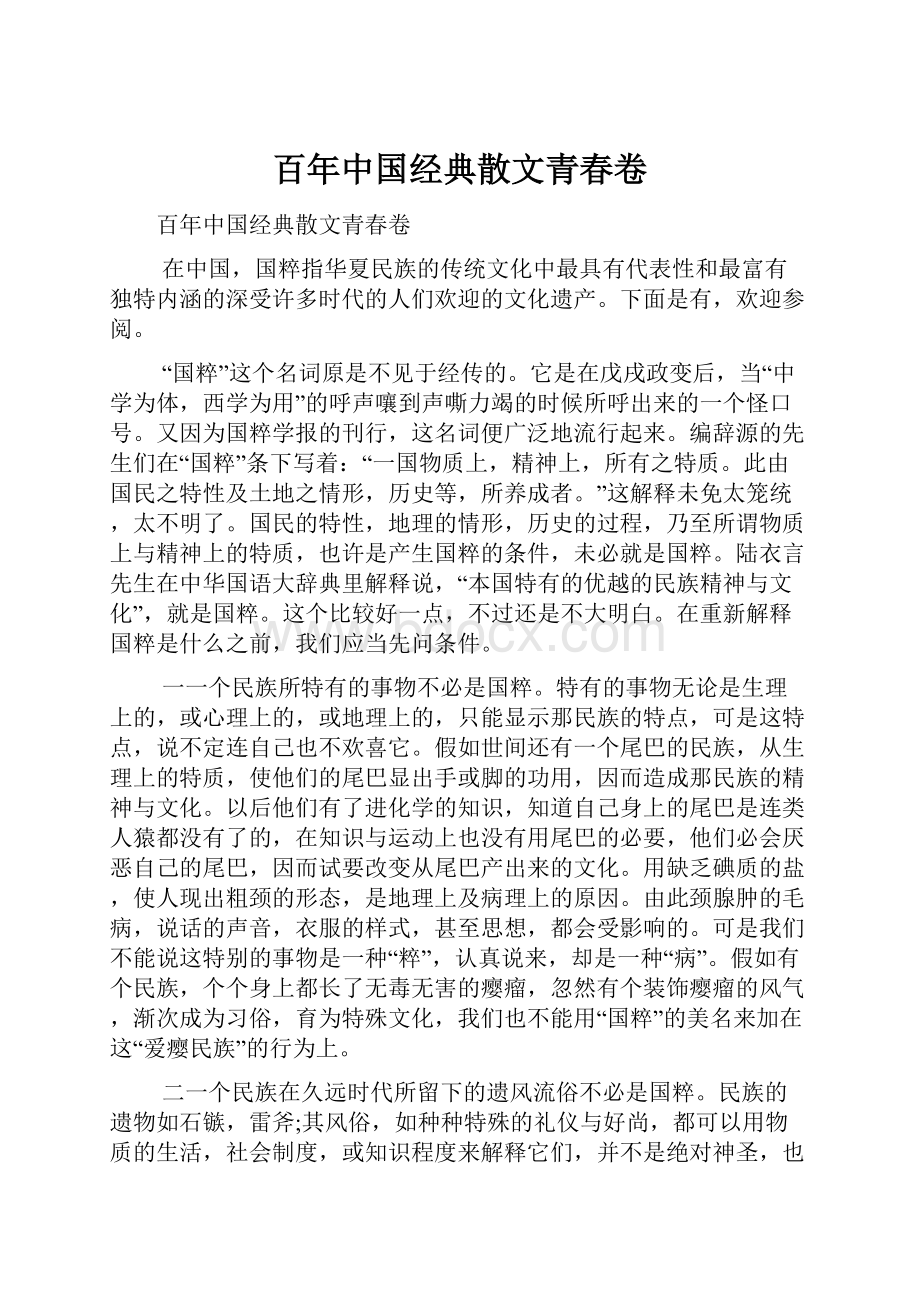
百年中国经典散文青春卷
百年中国经典散文青春卷
在中国,国粹指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深受许多时代的人们欢迎的文化遗产。
下面是有,欢迎参阅。
“国粹”这个名词原是不见于经传的。
它是在戊戌政变后,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声嚷到声嘶力竭的时候所呼出来的一个怪口号。
又因为国粹学报的刊行,这名词便广泛地流行起来。
编辞源的先生们在“国粹”条下写着:
“一国物质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质。
此由国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历史等,所养成者。
”这解释未免太笼统,太不明了。
国民的特性,地理的情形,历史的过程,乃至所谓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特质,也许是产生国粹的条件,未必就是国粹。
陆衣言先生在中华国语大辞典里解释说,“本国特有的优越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就是国粹。
这个比较好一点,不过还是不大明白。
在重新解释国粹是什么之前,我们应当先问条件。
一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国粹。
特有的事物无论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或地理上的,只能显示那民族的特点,可是这特点,说不定连自己也不欢喜它。
假如世间还有一个尾巴的民族,从生理上的特质,使他们的尾巴显出手或脚的功用,因而造成那民族的精神与文化。
以后他们有了进化学的知识,知道自己身上的尾巴是连类人猿都没有了的,在知识与运动上也没有用尾巴的必要,他们必会厌恶自己的尾巴,因而试要改变从尾巴产出来的文化。
用缺乏碘质的盐,使人现出粗颈的形态,是地理上及病理上的原因。
由此颈腺肿的毛病,说话的声音,衣服的样式,甚至思想,都会受影响的。
可是我们不能说这特别的事物是一种“粹”,认真说来,却是一种“病”。
假如有个民族,个个身上都长了无毒无害的瘿瘤,忽然有个装饰瘿瘤的风气,渐次成为习俗,育为特殊文化,我们也不能用“国粹”的美名来加在这“爱瘿民族”的行为上。
二一个民族在久远时代所留下的遗风流俗不必是国粹。
民族的遗物如石镞,雷斧;其风俗,如种种特殊的礼仪与好尚,都可以用物质的生活,社会制度,或知识程度来解释它们,并不是绝对神圣,也不必都是优越的。
三代尚且不同礼,何况在三代以后的百代万世?
那么,从久远时代所留下的遗风流俗,中间也曾经过千变万化,当我们说某种风俗是从远古时代祖先已是如此做到如今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感情上觉得是如此,并非理智上真能证明其为必然。
我们对于古代事物的爱护并不一定是为“保存国粹”,乃是为知识,为知道自己的过去,和激发我们对于民族的爱情。
我们所知与所爱的不必是“粹”,有时甚且是“渣”。
古坟里的土俑,在葬时也许是一件不祥不美之物,可是千百年后会有人拿来当做宝贝,把它放在紫檀匣里,在人面前被夸耀起来。
这是赛宝行为,不是保存国粹。
在旧社会制度底下,一个大人物的丧事必要举行很长时间的仪礼,孝子如果是有官守的,必定要告“丁忧”,在家守三年之丧。
现在的社会制度日日在变迁着,生活的压迫越来越重,试问有几个孝子能够真正度他们的“丁忧”日子呢?
婚礼的变迁也是很急剧的。
这个用不着多说,如到十字街头睁眼看看便知道了。
三一个民族所认为美丽的事物不必是国粹。
许多人以为民族文化的优越处在多量地创造各种美丽的事物,如雕刻,绘画,诗歌,书法,装饰等。
但是美或者有共同的标准,却不能说有绝对的标准的。
美的标准寄在那民族对于某事物的形式,具体的、或悬象的好尚。
因好尚而发生感情,因感情的奋激更促成那民族公认他们所以为美的事物应该怎样。
现代的中国人大概都不承认缠足是美,但在几十年前,“三寸金莲”是高贵美人的必要条件,所谓“小脚为娘,大脚为婢”,现在还萦回在年辈长些的人们的记忆里。
在国人多数承认缠足为美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这事是国粹,因为这所谓“美”,并不是全民族和全人类所能了解或承认的。
中国人如没听过欧洲的音乐家歌咏,对于和声固然不了解,甚至对于高音部的女声也会认为像哭丧的声音,毫不觉得有什么趣味。
同样地,欧洲人若不了解中国戏台上的歌曲,也会感觉到是看见穿怪样衣服的疯人在那里作不自然的呼嚷。
我们尽可以说所谓“国粹”不一定是人人能了解的,但在美的共同标准上最少也得教人可以承认,才够得上说是有资格成为一种“粹”。
从以上三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国粹”必得在特别,久远,与美丽之上加上其它的要素。
我想来想去,只能假定说:
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
我们假定的标准是很高的。
若是不高,又怎能叫做“粹”呢?
一般人所谓国粹,充其量只能说是“俗道”的一个形式俗道是术语Folk-Ways的翻译,我从前译做“民彝”。
譬如在北平,如要做一个地道的北平人,同时又要合乎北平人所理想的北平人的标准的时候。
他必要想到保存北平的“地方粹”,所谓标准北平人少不了的六样——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他必要具备。
从一般人心目中的国粹看来,恐怕所“粹”的也像这“北平六粹”,但我只承认它为俗道而已。
我们的国粹是很有限的,除了古人的书画与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乃至精神上所寄托的神主等,恐怕不能再数出什么来。
但是在这些中间已有几种是功用渐次丧失的了。
像神主与丝织品是在趋向到没落的时期,我们是没法保存的。
这样“国粹沦亡”或“国粹有限”的感觉,不但是我个人有,
我信得过凡放开眼界,能视察和比较别人的文化的人们都理会得出来。
好些年前,我与张君励先生好几次谈起这个国粹问题。
有一次,我说过中国国粹是寄在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上,从祖先崇拜可以找出国粹的种种。
有一次,张先生很感叹地说:
“看来中国人只会写字作画而已。
”张先生是政论家,他是太息政治人才的缺乏,士大夫都以清谈雅集相尚,好像大人物必得是大艺术家,以为这就是发扬国光,保存国粹。
国粹学报所揭露的是自经典的训注或诗文字画的评论,乃至墓志铭一类的东西,好像所萃的只是这些。
“粹”与“学”好像未曾弄清楚,以致现在还有许多人以为“国粹”便是“国学”。
近几年来,“保存国粹”的呼声好像又集中在书画诗古文辞一类的努力上;于是国学家,国画家,乃至“科学书法家”,都像负着“神圣使命”,想到外国献宝去。
古时候是外国到中国来进宝,现在的情形正是相反,想起来,岂不可痛!
更可惜的,是这班保存国粹与发扬国光的文学家及艺术家们不想在既有的成就上继续努力,只会做做假骨董,很低能地描三两幅宋元画稿,写四五条苏黄字帖,做一二章毫无内容的诗古文辞,反自诩为一国的优越成就都荟萃在自己身上。
但一研究他们的作品,只会令人觉得比起古人有所不及,甚至有所诬蔑,而未曾超越过前人所走的路。
“文化人”的最大罪过,制造假骨董来欺己欺人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我就要死在座位上了!
一点也不夸张。
事实就那样。
虽然我两年多以前访问过瑞典,参观过皇家剧院,观看过现代芭蕾舞《培尔·金特》,并且在更早些时在法国巴黎领教过瑞典艾茨·玛克舞蹈团让《天鹅湖》里的天鹅一律秃头的演法,我不能算是个艺术眼界鼠寸、欣赏趣味褊狭的老朽,可是,1995年1月19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听瑞典ROXETTE乐队的演唱会,刚刚开始第一首曲子,我便承受不住了——不是陶醉其中,而是惊恐万状,那摇滚的声响,用“雷霆万钧”来形容,于我都还有轻描淡写之嫌,因为其开唱的方式,是在一片黑暗与寂静中,突然台上灯亮,并且架子鼓、电子震荡器、电吉他与歌手的声音立即达于极致,仿佛火山陡地喷发、海啸狂卷千里……刹那间,我只感觉到那架子鼓的每一重击都锤在我的心脏上,并且我一身的血浆被迫倒泵进心室,在那外击内胀的情势下,我的一颗心真是马上就要进裂破碎了!
怎么办呢?
我用双手捂住耳朵,总算熬到一曲终了,在短暂的间歇里,我凑拢身旁儿子的耳边说:
“我受不了……我要出去……你一个人听吧……至少,我得到休息室里呆着去!
”儿子吃惊地望着我,说:
“那怎么行!
”
确实难以实行。
因为我们座位左右前后都已坐满了观众,并且,我朝出口处一瞥,因为是大爆棚,连过道上都站着许多观众,此时要挤退出去,噫吁欷难哉!
更何况,我拿的是瑞典大使宫的赠票。
头一天,瑞典大使馆为ROXETTE的访华演出在大使官邸举办洒会,我应邀参加,使馆文化专员还特别把我介绍给主唱Maire小姐和Per先生,记者们还拍了若干照片,拍照时Maire小姐还非常亲热地同我头挨头,并且还在他们特制的卡片上为我签名,ROXETTE发烧友有知,一定羡煞!
我和儿子去看他们演出时,刚下出租车,便有人冲上来问有无余票,当晚开演前首都体育馆前面人头攒动,走进大门,很费了一番力气;求票者甚多,而我们没见到一例转让的;门口有小贩发售荧光棒,生意极火;进到休息厅,几处卖ROXETTE磁带与CD盘和演出海报与说明书的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儿子奋勇抢购,却只买到磁带,一百五十元一张的CD盘早已售罄,那景象,就仿佛是不要钱一样。
开演前,偌大的体育馆已黑压压坐满了人,而且,场心的上千个加座,也坐满了看客,那些座位上金发碧眼的较多,儿子在那些座位里认出了中国歌星潘劲东、黄格选,兴奋地指给我看;找座位时遇到了几位相识的年轻艺术家,打招呼时有一位跟我说:
外地还有坐飞机来看的啦!
当时我认定他是“危言耸听”,后来得知,起码上海是确有坐火车赶来的发烧友;因我是赠票,故开始没大注意票价,落座后才知道最贵卖到600元一张,然后是400元、200元,只有边远座位卖100元……在如此这般的“背景”下,我刚开演便要退场,当然令儿子莫名惊诧;发烧友们倘若有知,更不知会视我为何等痴傻怪物呢!
演出继续在我有生以来头一回面临的訇响中进行,为防止我耳膜被震聋计,我都想拿围巾兜住头,在下巴狠系,以把我的耳朵挡住;在第二首曲子进行间,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求生欲望”,我悲哀地意识到,我的心脏确实有不小问题……但不知是为什么,也许主要是惰性,我竟终于还是熬过了第二、第三首曲子……后来演唱者开始唱不用架子鼓伴奏,节奏也不那么狂野的曲目,我这才如聆大赦,长长地吁出几口气来。
我周围的听众们怎么样呢?
满场是怎样的景象呢?
开头,在昏暗的观众区,是无数的荧光管在狂热地晃动,后来,虽不允许,许多的男发烧友还是点燃了他们的打火机,不住地摇晃;头一曲唱响时,便有观众从座席上站起,随着摇滚节拍扭动身躯,几曲过后,越来越多的观众站起来呼应,有的更将双臂高举过头,即兴摆动,很快的,我和儿子两人便成为难堪的“盆地”——惟有我俩没站起扭动;儿子比我“开化”,他知道ROXETTE几年前便风靡欧美,自为美国好莱坞一部名片配过插曲后,更是声名腾天,在摇滚金曲排行榜上连续称霸,但他毕竟“近墨者黑”,受我的影响,还是喜欢读古典文学名著、听古典音乐,所以他听ROXETTE时虽也晃肩击掌,毕竟还不狂热。
我陷于狂热的发烧友之中,不禁有所腹诽:
他们是盲目地崇洋迷外吧?
他们真能欣赏这玩意儿吗?
……那Marie一头短得没有道理的银发,穿着镶闪光片的紧身衣裤,而Per却是一头长长的披肩褐发……整个乐队在台上放肆地跃动着弹奏着狂歌着,尤其是Marie,她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激烈地舞动,说她是用全身心演唱,是极端地投入,都还不能传达出她彼时的情态,也许,她已化为了一种抽象的曲线与音团,在她是彻底地忘我,在发烧友是醉入膏肓……可是Marie唱到一首曲子,她唱了一句便停下来,不拿麦克风的那只手遮在耳后,作期待状——她何用期盼,整个体育馆里顿时响起了接续她那一句的合唱声,令我在惊悚中不禁自责:
我有什么道理说中国的摇滚发烧友“盲目”?
他们对这一POP艺术门类的资讯掌握、熟悉程度、欣赏水平、迷恋方式,都已与欧美的发烧友不分伯仲,要说“盲目”,那是我自己……Marie在获得这与在纽约、巴黎、斯德哥尔摩、香港等地并无二致的呼应后,欣喜地用中国话高呼:
“北京,你好!
”
我居然坚持到了终场。
我的心脏并没破裂。
场子里发烧友的狂热并没引发出任何问题。
演出结束人们鱼贯而出,秩序井然,令我和儿子狼狈的是,出了体育馆我们叫不到出租车,不止我们两人如此,我们一边步行一边期待空的出租车,可是一路上不断遇到先我们出来而依然未打到“的”的人……我们俩差一点只好步行回家。
我不是完全没听过摇滚乐,但以前听的只是磁带,现场感受这还是头一回,据儿子说他以前所听的中国摇滚歌手的现场演唱,音响效果也没这么大分贝值。
当晚我躺在床上以后耳鸣了很久,甚至于第二天起床后耳膜还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第二天傍晚我同妻子到一家星级饭店大堂喝茶,为的是听大堂一侧的钢琴演奏,当那位坐在三角钢琴前的小姐奏出肖邦的C小调幻想即兴曲时,我有一种从噩梦中醒来,憩息在蓝天下碧水旁的欣悦感,谢谢上帝,我的耳膜还没有丧失捕捉这天籁的能力!
我不会再去现场听摇滚乐了。
我不喜欢,甚至恐惧。
但是我珍视听ROXETTE的这次人生体验。
儿子事后对我说:
“您知道吗?
在我们这个年纪,这种音乐能让我们释放出身体里和心灵里的那騷动着的能量,特别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挺神秘的心火……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用这样的方式宣泄出了心火,耗散出了多余的能量,他就多半不会再到社会上胡闹,就可以更好地学习、工作,更通情达理地跟你们往上的一代人相处……”
是的,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狂暴的POP音乐,可是,我冷静地意识到,年轻一代有权利享受与他们生理、心理发展状态相谐的各种艺术,土生的与外来的,雅的与俗的,古典的与后现代的;不仅代间,异性间,社会群体间,艺术趣味的取向也应允许多元;除了特别恶劣的嗜痂之癖,对社会上各色人等的艺术欣赏取向,我们只能悉听尊便。
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地揄扬高雅的艺术,却不能排斥我们个人不能理喻的POP艺术。
在这个世界上,排除危害人类的东西不论,在形形色色的东西里,有某些我们很不喜欢,可是却很有一些人非常喜欢,那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喜欢它的权利,至少应当宽容地看待别人对那东西的狂热与痴迷。
反过来,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很可能又是别人所厌弃的,难道我们能接受别人的禁绝吗?
ROXETTE啊,你们想得到吗?
我不能喜欢你们的歌,却万分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样的启示!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
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
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
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规定的。
1957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
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
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
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
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
我们在洛陽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两三天。
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
收集了不少民歌。
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漫主义的想像,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
上了一次中岳嵩山。
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
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
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
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
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
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
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陰影。
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
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
我顿时傻了。
运动,都是这样:
突然袭击。
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这可以说是暗算。
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
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
我是有实际数据的。
“”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
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
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
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
不发言是不行的。
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
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
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
这位同志说:
“你对谁仇恨?
轻蔑谁?
自豪什么?
”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
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
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
我想辩解两句,行么?
当时我想:
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
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
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辨认”,他辩你认。
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
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
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
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
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
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伸解释的。
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
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
他们也并不好受。
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
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
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
“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
她想:
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
”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
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
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
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
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
“……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
”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
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
“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
”有人说这不可靠。
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
“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
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
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
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
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
我留了一个条子:
“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
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
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
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
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
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
真够一呛。
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
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
我当时想:
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不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坡。
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
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
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
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
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
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
叶面、叶背都得喷到。
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
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
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
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
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
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
我去给他们化妆。
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
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
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
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巍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槍》。
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布景。
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
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
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1959年底给我们几个人作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
工人组长一致认为:
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
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
这样,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
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
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
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
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
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
为什么设在沽源?
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
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
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
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
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8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
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
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
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
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
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