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导论.docx
《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导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导论.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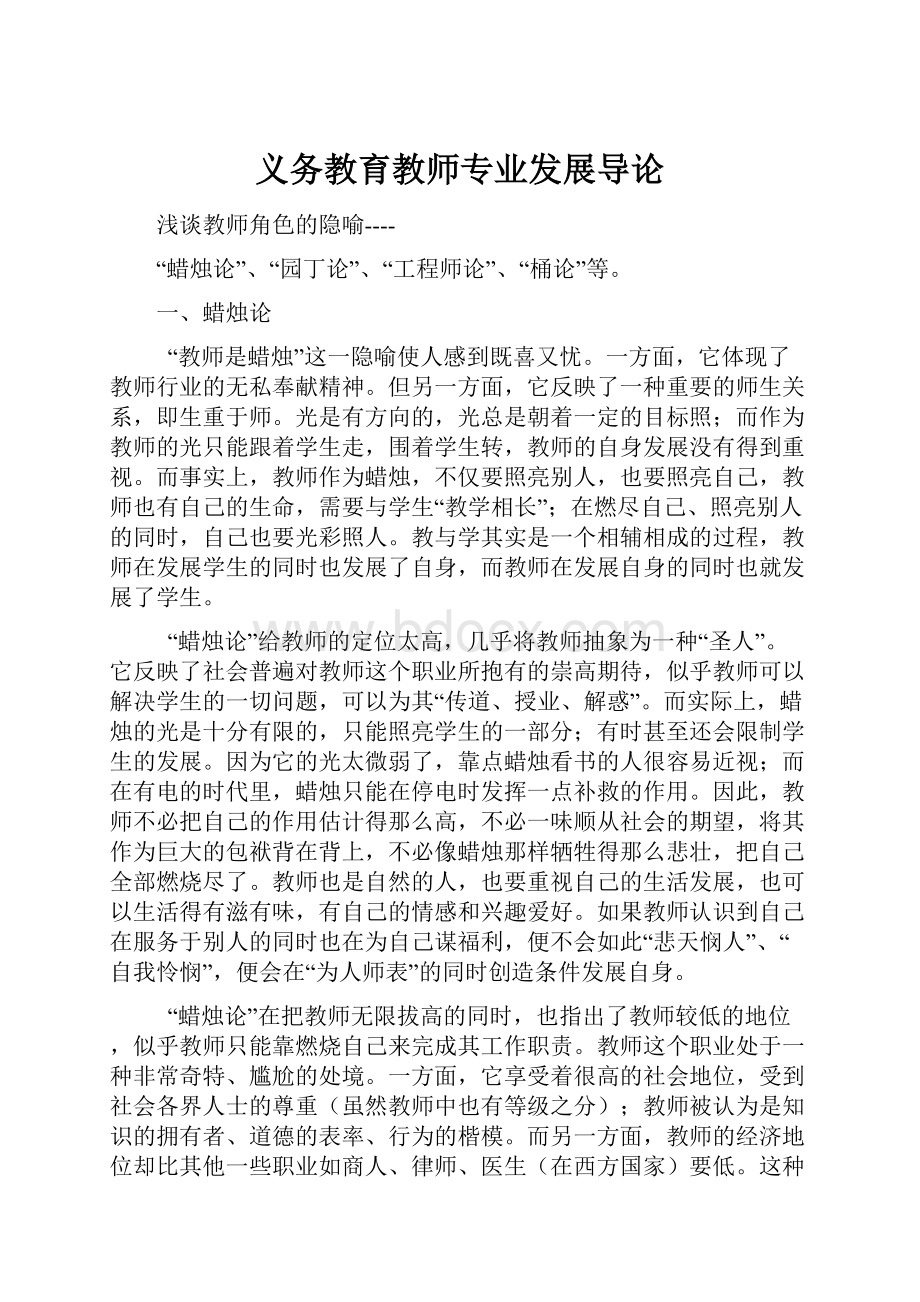
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导论
浅谈教师角色的隐喻----
“蜡烛论”、“园丁论”、“工程师论”、“桶论”等。
一、蜡烛论
“教师是蜡烛”这一隐喻使人感到既喜又忧。
一方面,它体现了教师行业的无私奉献精神。
但另一方面,它反映了一种重要的师生关系,即生重于师。
光是有方向的,光总是朝着一定的目标照;而作为教师的光只能跟着学生走,围着学生转,教师的自身发展没有得到重视。
而事实上,教师作为蜡烛,不仅要照亮别人,也要照亮自己,教师也有自己的生命,需要与学生“教学相长”;在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要光彩照人。
教与学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教师在发展学生的同时也发展了自身,而教师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就发展了学生。
“蜡烛论”给教师的定位太高,几乎将教师抽象为一种“圣人”。
它反映了社会普遍对教师这个职业所抱有的崇高期待,似乎教师可以解决学生的一切问题,可以为其“传道、授业、解惑”。
而实际上,蜡烛的光是十分有限的,只能照亮学生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还会限制学生的发展。
因为它的光太微弱了,靠点蜡烛看书的人很容易近视;而在有电的时代里,蜡烛只能在停电时发挥一点补救的作用。
因此,教师不必把自己的作用估计得那么高,不必一味顺从社会的期望,将其作为巨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不必像蜡烛那样牺牲得那么悲壮,把自己全部燃烧尽了。
教师也是自然的人,也要重视自己的生活发展,也可以生活得有滋有味,有自己的情感和兴趣爱好。
如果教师认识到自己在服务于别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谋福利,便不会如此“悲天悯人”、“自我怜悯”,便会在“为人师表”的同时创造条件发展自身。
“蜡烛论”在把教师无限拔高的同时,也指出了教师较低的地位,似乎教师只能靠燃烧自己来完成其工作职责。
教师这个职业处于一种非常奇特、尴尬的处境。
一方面,它享受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虽然教师中也有等级之分);教师被认为是知识的拥有者、道德的表率、行为的楷模。
而另一方面,教师的经济地位却比其他一些职业如商人、律师、医生(在西方国家)要低。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明显。
因此,当我们想到“教师是蜡烛”这个隐喻时,不仅想到教师自身生命的销蚀、知识的耗尽,而且想到自己经济地位的低下、捉襟见肘的窘迫和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穷酸”态。
然而,教师不应该就此自暴自弃,接受蜡烛甘于自焚的命运。
如果自认为是蜡烛,一味燃烧,蜡烛会越烧越矮,终有熄灭的一天。
教师不仅要把自己的光照到需要光的地方,而且需要自己不断充电。
因此,有老师认为,与其把教师比喻为蜡烛,不如比喻为长明灯,为学生的发展和自己的成长而不断充电,于人于己都受益无穷。
二、工程师论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隐喻包含了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
一方面,它表明教师从事的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目的是塑造学生的灵魂。
因为只有人才有灵魂,因此教师的职责是育“人”,注重学生的心灵发展,而不仅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和能力。
然而,工程师论是一个“混合型隐喻”,将一些互不相容的形象生硬地并置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牵强、不太协调的图象。
首先,将教师比喻为“工程师”,反映的是一种工业模式,似乎学生是一块没有生命、任人摆布的钢铁,可以任工程师按照自己的蓝图塑造成产品。
而与此同时,“灵魂”这个概念将教师提升到一个神圣的境地,似乎教师是一个万能的上帝,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方案塑造学生的精神。
也许,这个隐喻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将抽象和具象、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人和宇宙合为一体。
这个隐喻在操作方法上与西方的绘画隐喻和雕塑隐喻非常相似,似乎学生是一张白纸或一团泥巴,可以任艺术家画自己想画的图像,塑自己喜欢的模型。
与这些隐喻所不同的是,工程师论强调塑造学生心灵的重要性,这也许与中国文化注重道德教育有关。
随着西方科学主义的兴盛,西方发达国家对教师作用的规范越来越狭窄,教师被认为是知识的启迪者、能力的培养者,而价值观、道德观以及道德行为的形成主要是家长、社会和学生自己的事情。
特别是在美国这类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里,学校已不开设道德教育课程,只有公民教育。
价值多元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多元,学校教育已经主动拱手让出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权利。
西方国家不像中国,要求教师事事“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教师的言谈举止和衣着装扮也不必完全符合社会规范。
对理想教师的要求通常是具有创造力、想象力和反思能力,而不必具有塑造“人类灵魂”的崇高道德水准和规范行为。
正是由于对“灵魂”的重视,与西方的雕塑模式相比,工程师模式似乎更加注重被塑者的有机性和生成性。
灵魂是一个有自己内在生命的有机体,需要工程师采取恰当、灵活的处理方式。
而雕塑家面对的是一团没有生命的泥土,可以随雕塑家的意愿和动作而改变形态。
雕塑作品一旦成型以后就不再改变,而学生的灵魂离开学校和教师以后仍在变化。
一幅好的雕塑作品可以将一种精神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下来;而对灵魂的雕塑可以动态地、一代接一代地发展和延续一个文化,教师作为雕塑灵魂的人,可以通过教育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保存下来。
然而,与雕塑家一样,工程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活生生的人采取灵活、多样、个性化的指导。
虽然工程师(像雕塑家一样)必须根据材料的特点决定工艺程序和施工方法,但是材料在操作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学生作为人其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从教育质量观看,工程师论似乎暗示了一种固定、统一的质量标准。
教育被作为一个大工厂,教师是工厂里的工程师,学生是被批量生产的、规格整齐划一的产品,教师在从事教育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张事先设计好的蓝图。
从教师自主权考虑,工程师论也隐含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它似乎比较重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计塑造学生,改变学生。
而另一方面,它又表明教师缺乏必要的自主权。
上级对产品通常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工程师只能按照一定的工艺要求、方案和流程操作,不具备教师所应该具有的主动性。
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术,教师的工作不能完全被规范,必须给予一定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上面的分析表明,工程师论隐含了一个致命的矛盾,即活的(有生命的)灵魂和死的(无生命的)工程之间的冲突。
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使用这个隐喻,也许与我国解放后崇尚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有关。
我国的社会体制、经济和教育都深受前苏联的影响,教育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工程,可以事先自上而下地建立规划蓝图,可以被操纵、计划和规范。
国家可以像建工厂一样统一建学校,像培养工程师那样按一定规格培养教师,像购买原料那样招收学生,像生产产品那样产出毕业生,也可以像考察产品那样检验毕业生是否合格。
其实,教育是活生生的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学生在与教师和其他学生的交往中会生成新型的人格,而不是没有生命的、事先被规定好规格的产品。
学生是具有灵性的人,其灵魂所需要的不是被“塑造”,而是被“唤醒”、“激发”和“升华”。
三、园丁论
与上述工业模式相对应,“教师是园丁”这个隐喻反映的是一种农业模式,认为学生像种子,有自己发展的胚胎和自然生长的可能性,但需要教师来浇水、培土。
与工程师论相比,园丁论更加重视学生的生长性,既考虑了学生发展的共同规律(可生长性),同时又照顾了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每一颗种子可能开出不同的花儿)。
同时,这个模式也考虑到了教育的过程性,而不仅仅是结果。
教育学生就像是培育花朵,需要经常、定时地浇水、施肥、松土。
“园丁论”所反映的教育观点在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推崇的“镜子论”里被推到了极端,教师被认为是学生的一面镜子,为学生提供一个相对清澄的、观照自己的工具,帮助学生看清自己,了解自己,进而设计和促进自己的发展。
学生有自己发展的潜能,教师的作用只是为其创设条件,提供互动的机会,让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发展自己。
然而,“园丁论”似乎隐含着学生的发展类型和阶段基本上是不变的,教师的作用只是辅助其生长。
园丁无论多么努力浇水施肥,都无法将一株玫瑰培育成一棵紫荆;他们能够做的就是顺其自然,使这株玫瑰长得枝繁叶茂,花开似锦。
而且,学生与花儿一样,其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如果前一阶段发育不良,下一阶段将很难弥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这种观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1986)十分相似,似乎早期的创伤会终身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而根据艾里克森(1959)的理论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人在发展阶段的过失是可以修复的。
教育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过程,需要教师运用自己的智慧去面对很多事先无法预料的新问题。
在这一点上,“镜子论”提供了更多的可供学生变化的空间,镜子只是反映出照镜人的变化,并不限定其变化的内容和速度。
从学习论的角度看,“园丁论”反映的是一种认知主义的观点,认为学生有自己既定的认知结构,教师应该在了解学生现有知识水平的同时了解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在教学中提供适当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内容。
而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构主义已经超越了这种静态的学习观,认为学生所学到的知识是与教师、教学资源以及其他学生的互动中建构出来的,学生的知识结构是一个网络,新的知识可以随机进入,其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化、动态的过程。
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知识和辅助学生学习,其本身也就是这个建构过程中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与社会学中符号互动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的存在是人际的,人的观念和行为都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
同理,教师在学生的自我概念、知识、能力、素养等方面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园丁论”一方面似乎没有充分肯定教师的形成性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意识到教师的作用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种子没有园丁的培育也能自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虽然这种生长可能质量不高。
学生没有教师的帮助也会自行发展,虽然这种发展可能“误入歧途”。
但是,如果教师不能提供学生所需要的帮助,也有可能阻碍学生的发展。
学校本身便是一种社会机构,如监狱、医院。
如果学校办成了一个封闭的、“关押”学生的场所,学校教育成了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复制,这种教育不仅不能帮助学生成长,反而会给学生的心灵造成危害,扼杀他们的好奇心、创造力和正义感。
因此,有老师认为,与其把教师比喻为园丁,不如比喻为太阳。
教师是太阳,是一个充盈的、热情的、开朗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载体。
它的情怀和快乐在于奉献,把给予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而不是索取。
教师是有自己的生命的,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像太阳一样有自身的充盈,才能够慷慨地给予;而不能给予的人是自身匮乏的表现。
蜡烛由于自身的匮乏,越烧越矮,直至消亡;而太阳有永恒的光和热,能给天地万物提供温暖和阳光,使种子发芽、成长,使世上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成为生命的独立体。
每一个年轻人都要经历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教师就像是一轮太阳,可以为学生的发展播下光和热,使学生变得强健有力、自强自立,完成自身生命的追求。
四、桶论
“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一隐喻强调的是教师知识和能力的必要储备,对教师的职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有人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教师只有“一桶水”已经不够了,应该是“自来水”,什么时候想要,都可以随时拧开水龙头;不管要多少水,都可以哗哗地流出来。
然而,在教育理念上,“桶论”显然已经过时了。
它强调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这使人立刻想到“灌输”的形象。
似乎教师的作用就是要“给”学生“灌”知识,而且这种“灌”采取的是从上往下“倒”的姿势。
教师的桶和学生的碗里装的都是“水”,教师倒给学生的知识没有经过学生本人的处理。
“桶论”反映的是一种应试教育的模式,学生被当成被动的容器,被教师注入知识,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原样倒出来。
这个隐喻对教师的知识和能力要求很高,似乎教师的储备一定要多于学生。
而在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教师的知识储备并不一定多于学生。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机会接触新鲜事物,可以在新闻媒体、网络和与人交往时学到很多老师不知道的东西。
教师之所以作为“教师”,主要是因为其阅历比较丰富,在专业知识上比学生先走了一步而已。
教师也要不断地学习,甚至主动地向学生学习,才有可能走在前面。
其实,教师不必害怕在学生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有时甚至需要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无知,与学生一起探讨问题,以使学生去除对教师的神秘感和权威感,主动承担起学习的责任。
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是在主动探究而不是被动接受中形成的。
如果教师放掉自己的权威,与学生一起探讨问题,学生可以看到教师的思维方式和探究过程,有利于他们建构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
“桶论”所隐含的学习观非常狭窄,似乎学习涉及的主要是学校内、课堂上、书本上和教师拥有的知识,而没有意识到学习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可以超越书本、课堂、学校和教师,延伸到不断变化着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
“桶论”没有考虑到学生作为独立学习者和终生学习者的能力和条件,似乎学生从老师的桶中接到的水可以够自己一辈子受用。
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坚持“桶论”,将很难使自己的学生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桶论”对教师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主要是一种量上的储备,似乎越多越好。
而我们不得不考虑,教师桶中水的质量如何?
这涉及到“什么是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这类问题。
即使教师自己也很难肯定自己这桶水对学生是否有用,这桶水倒给学生,学生是不是想要。
特别是在当前这个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教师如果不及时更新自己,自己原有的那桶水恐怕不但没有用,而且早已腐烂发臭了。
目前,在我们的学校里,十几年使用同样教案的老师不乏其人。
当然,强调质并不是说就不需要量,但质和量必须结合起来。
教师光有满满一桶平常的水(信息、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加精练的、具有丰富营养的、高质量的水(智慧、修养、情操、全面素质)。
此外,“桶论”不仅没有强调教师知识储备的质量,而且没有考虑到对教师教学方法的要求。
似乎教师只要有一桶水就够了,至于他们应该如何倒这桶水、往学生的碗里倒时会不会倒歪了、会不会溢出来等问题都不在被考虑之列。
因此,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充满自信的教师应该告诉自己的学生:
我这里没有一桶水倒给你们,你们都得拎上自己的装满水的桶来,和我桶中的水相互倒,这样我们大家就能倒出一大盆水。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共同学习、相互促进、教学相长的关系,教师并不是万能的上帝,不可能无所不知。
教师在教学中只是一个协调人,其作用是为学生的学习尽可能多地提供资源,创造一个积极学习的环境,让学生自己健康、和谐地发展。
教师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积极的观察者,应该时刻准备着,在儿童需要帮助的时候助其一臂之力教师就像是学生的“拐杖”,在学生需要的时候助其行走;而一旦学生可以自己上路,教师的扶持就成为多余的了。
教师不应该让学生依赖自己,总期待着学生对自己表达感激之情。
如果教师自己内心充实,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充当了学生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拐杖”而已,就不会需要学生的回报来填补自己内心的不足。
因此,有老师认为,与其期待教师时刻有一桶水往学生的碗里倒,还不如把教师当成一个帮助学生挖掘泉水的人。
学生就是一眼泉,一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而教师就是引导发掘泉水的人,使泉水喷涌而出,永不停息。
教师应该从“倒水人”变成“挖泉人”,为具有不同个性的学生的终生发展出一镐之力。
成为与学生平等相待的“良师益友”。
同时,“桶论”所隐含的一些观点也可以被改造或延伸。
比如,“水”在人类的语言中象征着生命、活力和绵延;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万物之本。
用“水”来比喻教师的知识和能力,暗示着教师对人类精神生命的维护、延续和更新。
教师所拥有的水应该是不断更换的、常清的、流动的,应不同学生所拥有的不同大小、不同形状、不同质地的碗的要求而变换相互倒水的位置、姿势和水的总量。
五、结语
分析表明,上述隐喻分别强调了教师的不同功能。
“工程师论”主要表现的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很难发挥出来。
“园丁论”主要反映的是教师的辅助作用,注意到了学生自身的生长性,但过于强调学生发展的固定类型和阶段性。
“桶论”主要强调的是教师在知识方面的储备,对教师的知识质量和教学方法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蜡烛论”体现的是教师的献身精神,忽略了教师自身生命的成长和职业发展。
由于隐喻具有意义不确定、解释多元、边界不清楚、情感卷入等特点,上述隐喻同时也在教育教学的其他方面引导我们思考。
如果只停留在语词层面,我们会发现上述一些分析显得牵强附会;而如果我们深入到话语和语用层面,就会看到这些隐喻其实已经在严重地影响着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期待以及教师本身的工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