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之花 文档.docx
《沙漠之花 文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沙漠之花 文档.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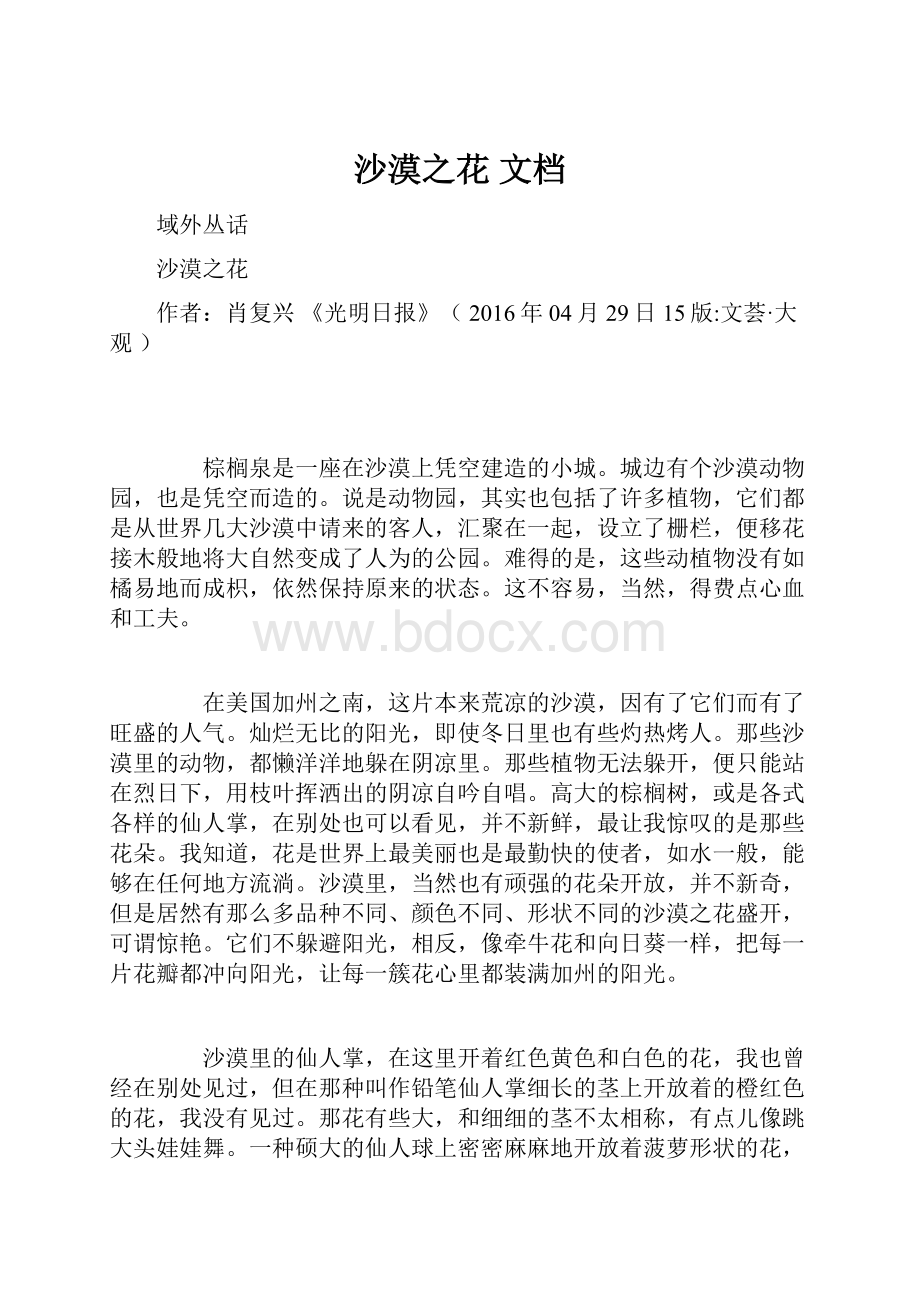
沙漠之花文档
域外丛话
沙漠之花
作者:
肖复兴《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9日15版:
文荟·大观)
棕榈泉是一座在沙漠上凭空建造的小城。
城边有个沙漠动物园,也是凭空而造的。
说是动物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植物,它们都是从世界几大沙漠中请来的客人,汇聚在一起,设立了栅栏,便移花接木般地将大自然变成了人为的公园。
难得的是,这些动植物没有如橘易地而成枳,依然保持原来的状态。
这不容易,当然,得费点心血和工夫。
在美国加州之南,这片本来荒凉的沙漠,因有了它们而有了旺盛的人气。
灿烂无比的阳光,即使冬日里也有些灼热烤人。
那些沙漠里的动物,都懒洋洋地躲在阴凉里。
那些植物无法躲开,便只能站在烈日下,用枝叶挥洒出的阴凉自吟自唱。
高大的棕榈树,或是各式各样的仙人掌,在别处也可以看见,并不新鲜,最让我惊叹的是那些花朵。
我知道,花是世界上最美丽也是最勤快的使者,如水一般,能够在任何地方流淌。
沙漠里,当然也有顽强的花朵开放,并不新奇,但是居然有那么多品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的沙漠之花盛开,可谓惊艳。
它们不躲避阳光,相反,像牵牛花和向日葵一样,把每一片花瓣都冲向阳光,让每一簇花心里都装满加州的阳光。
沙漠里的仙人掌,在这里开着红色黄色和白色的花,我也曾经在别处见过,但在那种叫作铅笔仙人掌细长的茎上开放着的橙红色的花,我没有见过。
那花有些大,和细细的茎不太相称,有点儿像跳大头娃娃舞。
一种硕大的仙人球上密密麻麻地开放着菠萝形状的花,它们拒绝分散着开,而是手挽手肩并肩簇拥在一起。
每一朵花尖上都矗立着一枚长长的刺,像是卫兵握着一柄柄剑戟。
那剑戟既像在卫护,也像在表演,刚劲而修长的线条,是男舞者挥舞出的棱角鲜明的手臂。
淡紫色的马兰花,比曾经在田野里见过的马兰花还要娇小。
细碎的花瓣,像打碎了一地的碎星星,是那种只有在童话中才会出现的碎星星——似乎由于不甘于四周荒凉与干燥的包围,在做着努力挣脱而出的七彩的梦。
但这也许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它们恐怕乐于在这里。
沙丘草和沙马鞭草,尽管都是粉红色,一眼还是可以分辨出来。
沙丘草的颜色要淡一些,花朵要大许多。
沙马鞭草不能望文生义,它一点儿也不像马鞭子,而是五角星一样呈五瓣形状,边长一样,规规矩矩,和城市里小学生一样娇小玲珑而笔直齐整。
扁果菊,和城市里的那种小叶菊和雏菊很像,不知它们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是进城的乡野之人,还是远走他乡的旅者?
扁果菊不像是从各处沙漠里请来的,倒像是从我们家的客厅或城市公园来到这里客串的,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
只是,它们的茎很长,叶很小,花也很小,瘦弱得有点儿像水土不服,几分楚楚可怜的样子。
这里的扁果菊都是黄色的,黄色最打眼,别看花小,却像如今流行的小眼睛男人,格外迷人。
我第一次见到了茛苕。
在书中,我不止一次见过,知道它非常古典名贵。
举个经典的例子,这种花叶用在欧洲建筑中最常见的科林斯柱头的雕刻花纹里,其对称的古典之美,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流行。
如今,在那些仿古的西式建筑甚至家具中依然经常可以见到。
茛苕名字古怪,远不如其花叶美丽,但它却属于沙漠之花中的贵族。
它锯齿形的叶子,在风中摇摆,像跳着细碎的小步舞曲的精灵。
它金红色细长的小花,随叶子一起摇头晃脑,像抱着古老乐器为舞者伴奏而自我陶醉的乐队。
在这里所见到的花,大多是草本,也有灌木,最多的是墨西哥刺木。
这种刺木才真的像马鞭,细长而柔软,是歌里唱的那种“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鞭子,温柔多情,带着无伤大雅又有些撩人的刺。
它的花朵都是顶在刺木的顶端上,像是丹顶鹤头上的那一点红。
只是,那一点红花,是茸茸的,弯弯的,带一点点的尖儿,如果再大一些,就更像圣诞老人头顶上的那顶红帽子了。
在树上开花的,在这里我只见到了两种。
一种叫作烟树,不是我们唐诗里说的“鸟从烟树宿,萤傍水轩飞”的烟树,那是我们诗意中带有炊烟带有家的味道的树。
这里的烟树,也是野生的,家被放逐在外,远远看,真的像是一片蒙蒙的烟雾。
近看,它的枝条上没有叶子似的,大小每一枝都像海葵向四周伸出的触角,细细的,软软的,晶莹剔透的灰白色,如同蒙上一层清晨的霜。
或许它的枝条就是它的叶子,它的叶子就是它的花。
另一种音译为帕洛弗迪。
它的花开在树的顶端,一片灰黄色,并不鲜艳,但面积很大,铺展出一片。
由于枝干比烟树要高,在一片低矮的花丛中,它的花鹤立鸡群一般醒目,一览众山小般迎风摇曳,像是挥舞着一面单薄得几乎透明的旗子,力不从心却并不甘心地与浑黄的浩瀚沙漠进行着对话。
还有好多我不知道名字的沙漠之花,我真想一一查出它们的名字,描绘出它们的样子。
它们有的开着细小球状的花,有的开着细长穗状的花,有的开着扁扁耳朵样的花,有的开着软软长须样的花,有的开着雪绒花一样茸茸的花,有的开着合欢花一样梦境里的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这样小,又这样神奇的沙漠之花。
面对它们的色彩纷呈和变幻无穷,竟然一时理屈词穷一般,找不出更合适的语言去形容。
忽然想起曾经读过一位陌生的作者写过的话:
“只有小孩子们的心里才能想象得出来,只有他们的小手才画得出。
”这些花开成的样子,也“一定与它们长时间的曲折跋涉,以及它们的美好想法有关”吧。
没错,这些花富于远离尘嚣的童真,拥有未曾经历都市化改造过的纯朴,未曾经过人为修剪。
它们一定不情愿从世界各地那么多沙漠里那么老远地被移植到这里来,尽管这里也是沙漠。
沙漠恶劣的环境,磨炼了它们,也成就了它们。
它们就像旷世的隐者,远离着我们。
它们又像静心的修炼者,确实是在沙漠中跋涉了很长时间,有着相当曲折却美好的想法,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它们无意争春和走秀,也不管云起云落,只管自由自在地花开花谢。
(作者为散文家,《人民文学》杂志前副主编)
说文谈史
遥想胡姬
作者:
朱鸿《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9日15版:
文荟·大观)
遥想胡姬,我的注意力难免会停留在她们的素手皓腕上。
不要讥我,谁不倾慕胡姬的素手和皓腕呢!
举素手,露皓腕,长安的风雅之士无不赞而叹之。
胡姬是西域国族之女,多在长安酒肆工作,能歌善舞,魅力强劲,可惜不见于文献。
她们什么时候到长安来的,怎么到长安的,何以在酒肆当垆,酒肆之主是谁,父母兄弟或丈夫又是谁,收入多少,收入是否能够自由支配,新旧唐书一律不录。
实际上我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不仅仅在她们的素手皓腕上,也在她们的身份上,生活上,甚至遭遇上,遗憾官修之史,统统无纪。
李白有一度任翰林供奉,无非是赋诗填词,以图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高兴。
诗词也可以务,他有的是天才,很在行,然而他还有救世济民之志。
赴长安,他就是要做大业的。
总是弄这种淡事,李白便生苦闷,遂常进酒肆以浇深愁。
杜甫所颂的“酒中仙”,大约就是李白此间之自谓。
李白喜欢胡姬,他所入酒肆,也往往有胡姬招待,诗可以为证。
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
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
一旦决定厮混着胡姬喝酒,便情绪高涨。
时在春天,下着细雨,落花缤纷。
骑白鼻騧,用银鞍,用障泥锦,阔气且豪气!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
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酒肆的环境甚好,瑟由嘉木而制,酒以玉壶而装。
曲子醉人,胡姬更醉人,胡姬跳起舞尤其醉人。
喝吧兄弟,不必急着回家。
不过我还是欣赏胡姬的笑: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李白所看到的胡姬健康、明净、喜悦,吸引李白,也吸引我。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金市就是西市,胡人经商之地,这里设酒肆是非常适宜的。
长安的权贵子弟骑马走遍长安山水,固然得意至极,只是还未尽情。
到何处去呢?
似乎也没有特别有趣的场所。
一个少年说:
“干脆喝酒吧!
”众子弟心领神会,笑着直奔胡姬酒肆。
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
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
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
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
长安的酒肆显然也并非晚上9点或12点关门,或者,夜禁制度也并非总是严格实行。
有一次,李白与朋友喝酒便从天黑喝到了天明。
他们相互争胜,彼此不服,你干一杯,我干一杯,有十足的意气。
两个胡姬陪他们,也很是激励吧!
胡姬双歌,也一定妙态横生,浓姿纵呈。
只有性格契合的朋友才能这样邀胡姬相陪畅饮。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
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
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
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
青绮门是汉长安城东出南头之门。
实际上它为霸城门,因为门是青色,遂为青绮门,也呼青城门或青门。
唐人有借汉论唐的习惯,李白不过是用青绮门指唐长安城东出之春明门而已。
唐长安城的外廓城东出共有三门,南头之门是延兴门,北头之门是通化门,中为春明门。
东出春明门,有路宽广,长安人往往在此送别。
裴图南当是一位隐士,欲归嵩山,李白遂在春明门附近的酒肆为之饯行。
不受唐玄宗重用,甚至被排挤,李白也生去意。
这些私曲平日也难倾诉,恰逢朋友离开京师,便一吐为快。
春明门一带的酒肆应该不是一家,然而胡姬素手一邀,李白就选定了。
我也随着李白的眼睛,看到了胡姬之素手。
岑参也选在春明门送别朋友,不过他以青门指春明门。
送张判官往洛阳去,是在早晨,夜雨初息,日出照楼,灞柳依依,无不堪折。
胡姬怎么样呢?
诗曰:
“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
”看起来岑参请张判官喝的是长安的米酒,然而胡姬酒肆,不唯米酒,当还备葡萄酒、龙膏酒和三勒酒。
岑参送宇文南金回太原,也是在早晨,显然比较轻松,诗曰:
“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
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
”春明门一带包括了向北去的通化门,向南去的延兴门,甚至再向南去的曲江池,否则无以生意兴隆,熙熙攘攘。
杨巨源有诗颂胡姬,他所登临的酒肆当在曲江池附近。
诗曰:
“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
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
香渡传蕉扇,妆成上竹楼。
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留。
”意近暧昧,然而还不至于淫,只是好色而已。
皓腕隐喻了胡姬的丰腴和白皙,也暗示了她的性感。
唐诗人有狎妓之风,胡姬是否在卖酒的时候也卖身,岂敢乱猜。
不过资料显示,“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
长安大了,遂无奇怪之事。
胡姬做什么都有可能,在酒肆卖身也是可能的。
客到酒肆来发现胡姬粲然妩媚,想谋肉体之乐,当然也是可能的。
胡姬以卖酒为业,助推消费,可以唱唱歌,跳跳舞,然而仅仅止于斯,也是有可能的。
客存非分之想,竟动手动脚,冒犯胡姬之尊严,受到拒绝并遭训斥,因为胡姬并不卖身,也有可能。
我当然不愿意相信胡姬有歌舞之外的举动。
霍家是汉之权贵,家有羽林郎,至酒肆,见胡姬长裙冉冉,广袖飘飘,头饰蓝田玉和大秦珠,窈窕俏丽,几为举世之稀,遂借喝酒纠缠。
胡姬只有15岁,然而品含坚贞,不惜拉断罗衫,也不会要霍家羽林郎所赠的铜镜。
汉有这样的胡姬,唐也会有这样的胡姬。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
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
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
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贺朝当是活跃在唐睿宗时的诗人,他的作品颇为细致地表现了酒肆的豪华程度:
这里有乐队,有歌舞之伎,铺有红毾,坐有貂裘,吃既有鱼,又有羊,所用餐具是玉盘和金鼎。
酒肆分档次,长安的星级酒肆,应该多在西市一带和春明门一带吧。
胡姬当垆,初唐就有,这在王绩的诗里得到了反映。
王绩很有意思,曾经赊账喝酒,遂示惭愧。
其诗曰:
“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
”酒肆之用胡姬,一直到晚唐还能看到,这有韩偓的诗证之。
他借题发挥说:
“后主猎回初按乐,胡姬酒醒更新妆。
”韩偓大约生于公元842年,死于公元923年。
胡姬多是踏着丝绸之路到长安来的。
然而丝绸之路能否让她们返乡呢?
长安有没有令她们动心以嫁且生儿育女的武士或儒生?
我偶尔会怀着这样的奇思异想,去打量长安乃至中国北方的姑娘,图谋从她们的素手皓腕上发现一点什么秘密。
(作者为散文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关中祠堂
作者:
吕向阳《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9日14版:
文荟·作品)
插图:
郭红松
金台区的葛河村紧挨着贾村塬,黄中泛白的条条上塬小路,与穿村而过泛着金光的金陵河,像数条彩带缠绕着村子。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这里散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背依平台,龙脊青瓦,粗粗的廊柱,红红的门窗,我以为是盖什么庙,走进去一看,一头发稀少的中年人正蹲在大梁上描龙绘凤,四壁已画满了古装戏上的人。
我说能画庙手艺一定不错,那中年人却说是画先人呢!
原来是画祠堂呢!
问及祖上出过什么大人物,他回答道:
“明代时出过个大将军,保驾朱元璋有功!
”我细看一面墙壁,上面是宝塔状的人名,葛家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都记载得一清二楚。
这虽是一座只有三间大的仿古祠堂,却点燃了我记忆深处的老祠堂。
幼年的我,乡村早就没了族长的影子。
我哪知道祠堂是安顿先人灵魂的圣殿,是珍藏家族脉气的宝匣,是倾诉心愿祈求福禄的密室,要说对祠堂的记忆,最多的却是一肚子的疑团。
我怀疑祖先是猿猴变的,猿猴怎能变成人?
那猪羊骡马怎么就不能变成人?
最早的祖先是谁,他们也吃的是臊子面吗?
他们怎么知道臊子面要放葱花韭菜萝卜木耳黄花菜呢?
先人为何不住在鱼虾蹦跳的海边,却住在远离城市缺这缺那的荒山下?
每当我冻得嘴脸乌青、饿得头昏眼花,却看见祠堂先人轴子上的先人坐在阔气的厦房下,一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大方桌上摆满了果蔬美食、诗书画卷,还有闪闪发光的金锞银锞,两旁还站立着侍奉丫鬟,几盆鲜艳的牡丹花或含苞或怒放,心里就更多了七分委屈三分抱怨。
哎!
要是我生在我先人那时光,爷爷奶奶肯定也让我穿金戴银、吃饱喝足的!
农村孩子,都是在无数次跟着大人给祠堂叩头烧香时长大的。
老人哄娃娃说,要学乖娃、要学勤快、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说谎、不要偷懒、不要走歪门邪道,你做啥事老先人都知道,老先人喜欢老实娃,总在暗地里给老实娃指路,要榜上有名,要走州过县,就得恭恭敬敬敬先人。
于是,我叩头时比伙伴们叩得响,献礼时比伙伴们拿得多,平时我也爱在画得花里胡哨、盖得飞檐斗拱的老祠堂转悠,我要让老先人记住我,千万不要把我与狗蛋、六喜、科娃、引弟他们搞混了。
然而,祠堂的学问却远不止这些朴素的感情与肤浅的概念,起初我以为它只是乡风民俗,甚至是装神弄鬼,哪懂得它的学问贯穿着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社会治理理念。
它不仅仅是一处供烧香叩头的建筑,它从里到外联结着整个社会。
周人在它里面找到了礼的精华,懂得了少数人如何统治多数人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奥秘;孔夫子在它里面找到了仁的本原,懂得了它影响人们的道德素质、风俗习惯以及对整个民族有着巨大的凝聚力;秦人在它里面找到了勇的砝码,懂得了刚直威猛才能横扫六国。
我不知道西方是否也有宗祠,但革命导师马克思正是从宗祠、族长、公共财产、赋税差役这些司空见惯的枝节,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逐步构建起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理论大厦,从而描绘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它因此也走进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伟人在文章中把它的代言人——族长的族权,与政权、神权、夫权,一起列为全部的封建宗法制度,并尖刻地批评它们“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巨人围绕祠堂在战斗,文豪也不甘寂寞,郭沫若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主编《中国史稿》,对宗族势力以大量笔墨抽丝剥茧,回答着来龙去脉。
鲁迅则以《祝福》《药》《孔乙己》《阿Q正传》等,斥责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礼教”。
而我与我的父老乡亲,绝不知道各式各样的祠堂有这么大的来头,它的角角落落、里里外外竟是哲人们竞相争鸣的战场,那些泥巴塑造、颜料勾画的祖先肖像,那些生前一文不名、艰难困苦的祖先,怎么就属于文绉绉、怯生生的“上层建筑”呢!
如此高深的哲学问题,农人显然是琢磨不透的。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
关中的祠堂虽不比皇宫结实,却比皇宫耐久。
一般而论,皇宫被烧了,重建的是另一个朝代;祠堂倒塌了,新建的仍属于家族。
只要这个家族还有一个人,劈块板子、写上姓氏,这个人就有了皈依,走到天南地北,也不是孤魂野鬼!
到祠堂去寻根!
趁着关中的“上层建筑”还没有消失殆尽,我应当“抢救性”地为后人留下一个祠堂的模样。
昔日关中乡村,祠堂正中都悬挂着“某家祠堂”的雕漆牌匾,里面是一张两头翘起的供桌,供桌上是一排排按嫡庶、按支系、按辈分罗列的先人名字,五服之外的则笼统以“祖先”而论,祠堂正中悬挂着正襟危坐、栩栩如生的始祖肖像。
有讲究的大族还把先人创业的历程画成精彩故事,有余力的则设法把修好的族谱放在香案上。
上香奉献念祷文,当是族长的权力,为先人唱戏、耍社火以及修缮支出,则是族人自愿出资或均摊。
婚娶、添丁、亡故以及日常邻里纠纷、田产争讼、违法犯罪的均要到祠堂奉告。
祠堂的大门不像庙门经常大开着,只有过年和清明、端午、中秋、冬至才香火缭绕、张灯结彩。
当然,因金榜题名、受封旌表等光宗耀祖的,少不了要随时锣鼓喧天一番。
国人祭祀先人由来已久,这正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训。
古时祭祀天地专属天子,祭祀山川则由诸侯大夫,士庶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
《史记·礼书第一》说: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而宗祠、家祠最早立于汉代,位于逝者墓旁,也叫墓祠。
宋代朱熹出台《家礼》后,才大兴祠堂,将家庙改为祠堂,明嘉靖年间“许民间皆联宗立庙”,于是,每族不论大小,也不分穷富都大建祠堂。
山东曲阜的孔庙、安徽旌德的江氏宗祠、山西代县的杨家祠堂、无锡的过家祠堂甚至韶山的毛家公祠、陕西眉县的张载祠等,皆排场极为考究,是中国祠堂的代表作。
祠堂成了光宗耀祖的徽记。
姓氏与故里,对国人而言,永远是座斑驳陆离的大迷宫,对祖上的追根溯源,对姓氏的探赜索隐,从人一懂事就挂在嘴上,常常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祖上是一棵大树,孩童会看自己能长多高;祖上是一口油井,孩童会看自己能否发生井喷;祖上是一座窖藏,孩童会掂量自己是什么宝物;祖上是一面镜子,孩童会看出自己能长成什么样子;祖上是一根脐带,孩童会在亲情温暖下崇德尚礼。
他们把先人芝麻大的事都看成英雄事迹,把先人的善德善行夸张成《一千零一夜》故事。
先人成了他们的庇护神,他们懂得没有先人就没有他们。
先人虽已埋在地下不出气了,但他们是先人的影子、先人的复活。
于是大年初一,这个家族的老老少少,都要进祠堂献白馍、献果子、献羊头、献猪头、献美酒,击锣敲钹,三拜九叩,族长重申家规家法、族训族约,神圣的灵光四处弥漫,先人的灵魂立马钻进后人的血脉中。
家境贫穷的孩童面对先人,会庄严宣誓:
一定要发愤图强,活出个人模样,为祖上争口气。
而更多的族人,眼中流露出丝丝惶恐,希望先人保佑平安健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
族人也消除了隔膜,捆绑得更结实牢固了,也没有了是非曲直,与同族不论哪个人过不去就是与自己过不去,本族中不论谁的仇人都是自己的仇人,一个家族成了一张脸,说话成了一口腔,吹号成了一个调。
就是面和心不和,遇事也要看祖先的面子,看族人的面子。
乡村的话语权就看族强族弱、族富族穷。
族大的就是老虎,族小的就是绵羊。
同一族的人在繁衍生息中流落他乡,也要辗转寻根祭祖。
岐山蒲村乡有个村子叫孙家庄,几户人家遇饥荒扎寨青化乡,后又分支出另一孙家村,同根同族使青化孙氏人家大年初一必来拜祖。
四十多里路程,顾不上喝口水,赶到时已是晌午。
族长常埋怨拜祖错过了良辰。
青化孙家人就想出良策,于某年的大年三十偷偷牵着牛来到孙家庄,说是提前来虔诚祭祖,结果到半夜三更时分,偷出“先人牌”用牛驮回村上,独自供奉。
这种用牛驮走先人牌的事,曾发生过不少,也往往是怎么要也要不回的。
“先人牌”是不能用人背的,也不能用马拉,用牛驮寓意先人是很牛的,后人会像牛毛一样密密匝匝、红红火火。
祠堂是族长惩恶扬善、施行族法的“乡村法庭”,是宣讲圣谕、劝世勉励的“道德讲堂”。
族长往往是一个族中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领袖。
他们按照传统伦理给每个族人打分,也把法律的鞭子抽向每个族人,把礼治与法治请在祠堂中,族约、家规训词大都提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有些族规对越轨者处罚甚严:
“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治之。
”有些族约规定:
“本支子孙有作过者,有败俗者,有婚姻不计良贱者,有弃卖坟墓者,俱以不孝论,并鸣众,揭谱除名。
”有些族长一怒之下,除罚站、罚跪、鞭笞、拷打外,也会发生把人活活吊死或打死的惨剧。
被关中人骂作“羞先人”“丧德”者,是不能进祠堂祭祖的。
祠堂是乡间的法庭,族长就是法官,族规就是法律,这里没有律师,也不容辩解,族长说对就对,说错就错,说打说罚都由他。
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祠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础就是根须。
“听话循规”也就成了乡间人教育孩子的座右铭。
祠堂是维持乡间秩序的皮鞭,也是反对革新的道袍。
每年初一的大祭祖,有做错事者,都要受到族长点名训斥,这无异于面子扫地、尊严丧尽。
所以,平素祠堂是威严高大的,族长也是威严高大的。
祠堂是族人的旗帜和纽带。
先人就是本族的宗教领袖。
而本族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团体。
常常为了利益争执,发生族与族之间的械斗。
如果谁被打死了,会在族人中无上光荣。
在平时,一个族大大小小的人会受到宗族的保护。
小孩一出生,就在宗族圈子中成长,大人爱谁他就爱谁,大人与谁有仇他就与谁有仇。
一些族与一些族有仇,子女是不能通婚的,而且通婚要讲名门望族,讲门当户对。
春节期间的一些宗族活动,迎神赛会、演戏等,更让族人有了自豪感、荣耀感。
族人去世,全族人要打墓抬棺;族人结婚,全族人要帮忙贺喜。
遇有红白喜事、盖房打墙之事,族人都要放下家中事出劳相助。
在农耕时代,宗族是互依互存、互帮互衬的合作社,在迎击外来欺侮、土匪骚扰上,更显示出“全民皆兵”的威力。
关中祠堂,大都于“文革”中被毁坏,有些做了仓库,有些做了校舍。
不少人不知三代以上的祖先。
祖母在世时,我曾问到我的“爸爷”(曾祖父)是何等人?
祖母说:
“他是个医生,也是个善人,一生救过好多穷人的命。
”祖母还说:
“我一到你吕家,一天要做十几次饭,都是做给要饭的。
我一生谁都不服,就服你爸爷。
你们兄弟三个能端上公家饭碗,能在外面干点事,不是你们本事有多大,是你们先人积下了德。
”据村上上了年纪的人回忆,我的曾祖父吕万统,有炼丹绝技,把药装在钵中埋入地下,用木炭烧一天一夜,药味几十里远都能闻见,开炉时全村会落下一层蚊子。
此药叫“九转还阳丹”,可根治不少顽疾。
在没有青霉素的年代,有神奇功效。
有一年,他在路上遇到一逃荒要饭、奄奄一息的川人,背回家后服侍了半年,川人大病痊愈,走时用此药方答谢救命之恩。
幼时我从家中的“先人案”上见过曾祖父名字,破四旧时家人用此案做了头门。
我知道,曾祖父在庇护着他的子子孙孙,子孙们更应眷念穷人,多做善事。
因为“人做好事,好事等人”。
大人说,过去有威望的族长比县长忙碌,自己就是言行一致的“人样子”,族里出了偷鸡摸狗、不守规矩的败类,除了按族规处罚,族长就在祠堂下跪几天几夜反省赎罪,吓得当事人一家陪跪不说,还要搬出年事已高的长者求情。
所以,乡村很少有什么乡匪村霸之类的害群之马,县长老爷自然是无为而治坐享清福。
祠堂的消失,无疑是中国乡间政治进步、文明开化的结果。
但乡间也出现了教化缺失、传统丧失、伦理颓废的一面。
乡间赌博成风,二毛子横行,老人被子女当成累赘无人赡养,麻糜婆娘更是无人调教,只觉得“风俗人心堕落迅速”,要是有个族长管管事,要是有个祠堂罚罚跪,或许一切会变得好些。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在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一文中说:
“县既是古代的一国,县令即等于国君,是不能直接办事的,只能指挥监督其下。
真正周详纤悉的民政,是要靠乡镇以下的自治机关举行的。
此等机关,实即周时的比长、闾